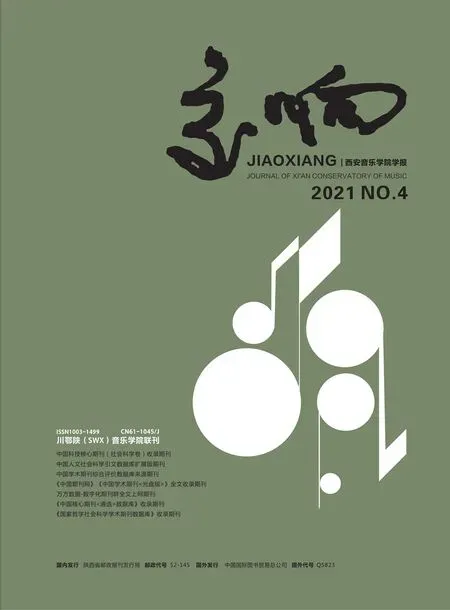《第二“长城”交响曲》创作特征与美学建构
●刘 鹏
(渭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闭幕式于深圳保利剧院顺利召开,指挥家胡咏言携手国家交响乐团,以《第二“长城”交响曲》作为闭幕压轴为鹏城人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笔者有幸观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第二“长城”交响曲》是一部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委约,著名作曲家叶小纲精心打造的大型交响乐作品(邹航作词)。作曲家以“长城”,这一凝聚着中华民族古老智慧与不屈精神的历史建筑为题材,对其进行深刻的历史性回顾与展望。整部作品由九个乐章构成,分别为:序曲、长城硝烟、汉唐风采、中原一瞥、嘉峪关、长城好汉、寂寞英雄、笑傲江山、壮哉长城。叶小纲以盘踞在华夏大地的“长城”为路标,将宏阔辽远的北国景色与我国丰富的多民族精神内涵融合起来,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表达了对人类最伟大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审视,激励人们不断奋进向前。作品以深邃的思想、多元的思维方式与饱满的艺术激情,表达对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与坚韧品格的向往。通过讴歌“长城”这一代表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存在,来表现人类对未来理想的执著追求。
一、内化传统音乐特质尽显中国式审美
在西方国家眼中,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的神秘东方国度,其文化、文明,乃至文字呈现和语言发音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中国传统音乐也因这份独特性,而具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表达——腔音。“腔音,指‘音高变化的音’,不同于西方‘音高不变的音’”[1](P29-36)“包含有某种音高、力度、音色变化成分的音的特定样式”[2](P26-68)“对于形成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格和韵味具有重大意义”[1](P29-36)。
(一)美声独唱腔音化
腔音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惯性表达,具有着深刻的人文历史内涵。中国的汉字分属于表意文字中的词素音节文字类,因此单独音节便具有符号意义。而这恰恰为腔音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每个音节都可以进行自由的延长,而仍具有指向性。由于单独音节具有符号意义,中文发音独特的语声(即语调)特征,以及中国传统声乐作品一叹三叠的艺术审美,使得其可以将单独的字进行延长,并形成头、腹、尾音。即,每一个字都具有了过程感与流动性。而西方文字属于表音体系。即,需要依靠单音节词之间的停顿,形成语义。因此,拼读类表音文字根本无法进行拆读,也就更谈不上使用腔音了。可以说,腔音是一种带有中国地缘特征的个性化音乐处理方式。叶小纲在交响乐这一西方体裁上,紧密贴合传统民族音乐中的腔音观念,声乐选段进行高度腔音化处理,贴合中国式审美,在作品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特征。
谱例1:

如谱例1所示,该部分为男高音独唱部分。作曲家以2小节为单位,将语句含义与音乐表达进行同步切割(我晓得)。之后,通过“加头”的方式对其进行重复,并对结构进行延伸,最终构成了4个小节。在“天下长城”的演唱中,对于“城”字的解构,尤其凸显出腔音特质。“城”的发音由cheng最后演变为eng。因此,本该出现的g2-d大跳,被作曲家以自由式级进下行的方式进行填充,并借助附点节奏、渐慢处理,令其产生一定的韵律感,再现了中国传统声乐作品中“一字多音”的腔音特点。此外,在以2小节为一个环节的重复中,叶小纲通过倚音、自由延长、波音、渐慢等方式,将每个文本都进行延长、修饰。由于第二次重复“加头”的使用,令相同音高材料产生演奏法上的细微差别。因此,腔音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变奏特征,是西方动机式展开与中国传统腔音的一种结合。
谱例2:

如谱例2所示,作曲家在处理“山”时,以弱拍进入的方式打破歌词与旋律的四分律动。在处理“峨”时充分考虑到字音、语义、旋律间的通达协畅。切分节奏以及上行大跳包含了巍巍高山之态,而波音、下滑音、自由延长的使用,又有了腔音之态。作曲家以平直之音(#g2)描述山高,以下行大跳(#c2-#f2-#e1)描述曲水;用切分节奏描述高山之态,以长线条的下行级进描述流水之姿。节奏的灵活多变,腔音的长短不一,令旋律灵动而富有特点,仿佛具有着传统音乐中即兴的特点,在这些丰富的表象下又有#f2-#d2-#c2与#c2-#f2-d2音高材料间的毗连,使得旋律变化多端却不散乱。这种以旋律描摹意境的处理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含蓄表达异曲同工之妙。
(二)西洋交响乐呈现方式民族化
作曲家不只在声乐创作方面,贴近中国传统审美;在乐器音响的表达上也依旧秉持着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特征。《第二“长城”交响曲》的创作基于西方交响乐的底色,并融入了声乐以及部分中国传统乐器。西方音乐体系建立于十二平均律之上。因此,管弦乐的传统演奏方式限于直音①演奏,但作曲家却以西方交响乐、中国传统乐器建立乐队编制,表现“长城”这一标志性题材,传递中国文化思想,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传统音乐表达与中西方乐器呈现之间的适配度。
谱例3:

如谱例3所示,此片段为打击乐片段。自上到下分别为:叫锣、通通鼓、邦戈鼓、康加鼓、小对锣、小锣。作曲家在纯粹的打击乐片段中加入钢琴,并对其进行打击乐化处理。从音高处理上看,作曲家使用半音关系的和弦#c1-#f1-#g1与b1-f1-g1,模拟打击乐的音频变化。从和弦本身构成上看,两个纯五度音程的叠置-三全音与大三度叠置,在紧张程度上为递进关系。从演奏方式上看,作曲家采用柱式和弦,左右手交替自由演奏的方式,凸显打击乐敲击特点。在第7-8小节中,对于打击乐片段重新进行内部功能分割,使钢琴成为一个持续型背景层,对前景和中景进行持续性铺底,这是对于小对锣持续功能的延伸。可以看到,作曲家从形态、音响、演奏方式入手,将钢琴打击乐的身份建立了起来。作曲家将钢琴打击乐化,也是源于该乐章的艺术表现需要。此乐章为《长城硝烟》,钢琴的出现象征着嘶喊、混乱以及脚步的跑动,通过打击乐与钢琴的交织令该部分在音乐表现力方面更加立体。
同时,作曲家在处理民族乐器与管弦乐的关系时,采用室内乐化的写法,稀释西洋乐与民族乐器在自身属性上的矛盾。如作品主题由钢琴纯音色变为由琵琶、二胡、马头琴构成的同度混合音色,此举降低了民族乐器的个性,增加中性属性。长笛在其低音区演奏持续的中景层。由于该音区长笛的辨识度较低,且在功能上属于持续中景层,因此并不会与前景层旋律产生摩擦。钢琴声部由旋律变为具有跳动感的持续中景层——承接了打击乐中景层功能,音区上与前景旋律分离。由于钢琴声部的持续性,令声部之间的衔接更为顺畅。大提琴与贝斯持续点状发音,更是增加了音乐的整体弹性。
二、民族底色与西方思维相互浸染
“音乐是感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他有很强的技术要求,但是它更需要操作者的思想。”[3](P117-118)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到旅美留学,中西文化的交融与沁润,使得叶小纲的音乐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这种独特性更是深刻表现在《第二“长城”交响曲》中,作曲家赋予该作品浓烈的民族底色,将民族音乐的灵魂注入到“交响乐”体裁中,令中华文化可以无障碍地与西方进行沟通、交流。
(一)重复结构下的弹性表达
中西方对于音乐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通过论证音乐协和感与数量的关系,提出音乐的美来源于数的和谐,为西方乐音数理逻辑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中国音乐不同于西方的形式和谐,更多强调心灵感悟,是一种精神实质的心理和谐。即,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因此,自娱性和即兴性、弹性律动,成为传统音乐的内核。对音乐认知的本质区别,导致中西方音乐在创作之初,便朝着不同方向前进。然而叶小纲立足于当下,立足于音乐的传播与交流,以一种开阔的眼光令本该南辕北辙的两方达成了和解。
如谱例4所示(缩谱),该部分构成5+6的重复性结构。在第一个环节中,共进行三次节拍(6/4-5/4-4/4)变化,从节拍关系来看,彼此呈递减发展。但在节奏律动角度,该部分又具有变头合尾的特点。每小节内部最后一个音固定地表现为3拍,而第一个音的时值却被不断删减。因此,第一环节内部形成数理逻辑化的节奏、节拍递减关系。在第二个环节中,由于3/4拍为高点,因此,节拍运动以3/4为轴呈现出倒影关系。通过对比可以看到,作曲家在进行结构重复时,采用了相同的音高材料,却调整了节奏。节奏的调整以及节拍的变化,令其与第一环节产生明显的变化,使得该旋律在艺术表现力上更加贴近中国传统音乐弹性、即兴的特征。
谱例4:

谱例5:

如谱例5所示,动机从弱拍开始经历e-d-c-e-d-e-c-#f-a-d-f-e一系列音高变化,在第一次重复中(第5-6小节):首先改变了节拍位置,动机由次强拍进入;其次改变动机节奏,将前八后十六节奏改为大附点,节奏时值上的延展并没有改变原动机节奏特点;最后对动机尾部进行加花处理,将动机尾部#f-e扩展为两拍,并着重于对#f音的加花。在第二次重复中,首先改变节拍以及进入位置,动机由正拍进入。从结构上看,第一次动机构成五小节单位,第二次、第三次动机构成两小节、三小节单位。表面上体现为结构的减缩,但是从内部构成上看第二、三次反倒是一种结构的内部增殖。即,第1-5小节是依靠动机的外部重复而形成。第5-6、7-9小节则是由于动机内部节奏变化与加花而形成的内部扩展。作曲家在重复的思维的主导下,由外部扩展走向内部的扩展。而这种具有生长意义的内部扩展,正是我国传统音乐中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具体体现,依旧蕴含着弹性、即兴的特征。
(二)核心材料贯穿
套曲是一种“按照一定音乐意图和形式逻辑,将若干在曲式结构、体裁、音乐性质相互对比的乐章,组合在一起”[4](P318)的大型音乐体裁。《第二“长城”交响曲》不同于传统的交响乐作品,其建立在作曲家对于西方交响乐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中国民间音乐独有特征的双重审美基础上。九个乐章各自结构独立,分别描述了不同场景与不同的情绪,为多乐章套曲结构。在整部作品中,序曲承担了营造氛围、点题的重要作用。九个乐章虽然各有侧重,但作曲家仍旧通过序曲动机材料的不断演变和闪现,加强乐章彼此间的联系。
九个乐章中序曲动机共出现六次,分别为: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六次动机材料,在节奏、音高方面极为相似。因此在音色上频繁变化,这其中包含民乐又有西洋乐;既有打击乐又有人声。同时动机材料的出现体现出一定规律性:首尾部分各出现两次,中间部分间隔出现。虽然在第三、五、七章并没有完整的动机材料出现,但却出现了与动机紧密相关的音高材料。在第三乐章中,动机d-a-d-f,就是序曲动机:#f-a-d的逆行。第五乐章动机e-f-g-a-bc-d-e-f,就是序曲动机e-f二度音高素材的横向扩张。第七乐章仍是以级进思维构成。并未出现序曲动机材料的三、五、七章,实则却是对动机材料的局部裁截。即,三个乐章共同拼成了完整的序曲动机音高材料。因此,显性的序曲动机材料与隐性的音高材料交相呼应,成为统领作品全局,令该交响套曲多而不杂、繁而不乱的有力保障。作品既有了追忆过去、展望未来,可以容纳祖国大好河山的千姿百态;又有了结构化、理性化的内在秩序与逻辑美感。
三、中国式哲学的体现
“中国的人文主义,明确宣称人是宇宙间各种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足以浩然与宇宙同流,进而参赞化育,止于至善”[5](P141)。中国的哲学集中于生命,任何思想体系,归根到底都是对于生命精神的发泄。儒家、道家、墨家……每一位哲学家著书立说,都是在表达自己的生命精神,是一种生命精神的浓缩与释放。他们借由生命去体验宇宙,生命的活动需要依据道德理想、艺术理想、价值理想而达成。叶小纲的作品恰恰蕴含着中国式哲学对于生命、艺术的探讨。
(一)九九归一,道法自然。
道家起源于到春秋战国时期,其思想的形成是以总结、发展、著典籍为主要路径,每一次思想的跳跃都经历了极其长时间的积累。《道德经》的问世为标志着道家思想的成型。道家学说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理论,也是诸子百家思想的源头。道家以道、自然、天性为核心理念,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据此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等理论。“九九归一”便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变幻,九九八十一后又再循环,归一。“九九归一”指“周而复始”或“归根到底”,但不是原地轮回,而是由起点到终点、由终点再到新的起点,循环往复,无穷无尽,螺旋式前进和发展的运动过程,它体现了人类对一切事物发展认识的辨证唯物论的哲学思想。佛语有云“九九归一、终成正果”。在这里,“九”是最大的,也是终极的,又与长长久久同音,古今人文建筑都以之为“最”。“九”这个在中国文化中极具指向性数字,作为一种隐性的人文理念散落于这部作品中。
在作曲家的眼中,《第二“长城”交响曲》不仅是在刻画一个伟大的古代建筑,更是在描摹一个伟大民族和国家的身影。因此,作曲家以极限之数“九”为单位,共创作了九个乐章,在内容安排上,既包含了人文,又包含了历史,既有对古代的追忆,又有对未来的展望。尤其是第八乐章男女合唱《笑傲江山》:“九意九声九乐九章,九子龙腾九重霄汉,九钟齐鸣九州方圆,不言朝歌夕雪似等闲,只等英雄笑傲千万代。”作曲家将对祖国美好的祝愿以“酒歌”的形式宣之于口,着力打造一片热情洋溢、激情澎湃的气氛。
(二)中国思维“合”的隐喻
“任何一位作曲家都无法褪去他的国家和民族在他心灵和精神上打下的烙印”[6](P138-141),在对于如何处理中国元素这一问题上,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对于成熟的作曲家来说,他们往往通过创作,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感受或者某种思想。因此他们往往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和知识底蕴,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不断学习,摆脱西方创作思维的掣肘,令创作技法与审美体验提升至一个更加开阔的角度。
在西洋管弦乐队中,加入民族器乐增加东方特质。琵琶与男高音这一组合更是十分具有特点。在中国传统乐器中,琵琶素有乐器之王的美誉,能文能武。既可以出现在弹词、鼓词一类说唱音乐中,充当伴奏;又可以独挡一面,塑造金戈铁马之声。琵琶伴奏声乐唱段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民间音乐形式的一种隐性回归。在作品中部分男高音唱段,作曲家没有使用大篇幅的西洋乐器进行伴奏,而是选择使用琵琶这一兼具旋律与和声功能的乐器。琵琶声部既与男高音声部形成八度带状旋律,其本身又承载了和声功能。此外,作曲家选择与琵琶较为接近的竖琴音色进行和声的辅助与点染。当二胡声部开始演时,并不会产生矛盾,仍是在民族化的语境下完成了声部的交接。作曲家选用“搭桥”的方式使用钢琴进行过渡,连接了管弦乐队全奏与民族乐器合奏之间的分裂感。
作曲家选择世界性的公共载体——交响乐,通过西洋管弦乐队加入民族乐器的方式,呈现对“长城”的思考,就是一种对西方惯性表达方式的突破。东西方乐器虽然从发声到形制甚至是律制都各有特点,鲜明地表现出了区域性文化差异。但乐器是声音的载体,这一根本性质并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而改变。作曲家正是利用了这一特质,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的乐器、设计不同的配置,令中西方乐器得以相互应和、交织、碰撞,共同谱写中华二字。
四、文学与戏曲的交织
语言被锤炼成为了文字,音响被梳理成了音乐,尽管二者在形态上千差万别,由于同样源于对生活感知的实质,使得它们别无二致、血脉相通。音乐与文学作为人类情感的凝结,它们凝诗成篇,凝音成作,以各自的方式抒发着作者对人生、生活的感悟。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诞生出无数优秀的作品。正是二者血脉相依、殊途同归的本质,使得中国近代作曲家们纷纷回归传统文学、戏曲音乐,不断从传统中汲取养分,绽放出新时代的中国之花。
(一)音乐的章回性
林语堂认为,文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起着教化作用,教人明理、思辨;另一种则是为了抒情、娱乐。音乐(文学)属于后者,但却又与其他抒情文学(诗歌)不同,音乐在处理情感与美感方面往往表现得更为浓烈。音乐慰藉情感、美感阐述哲思,其中蕴含的哲思不能暴露于外,一定要深埋其内,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令人的情绪得以随音乐共同展开。
从古至今,中国的音乐一直延续着书写标题的传统,但具有标题并不等同于具有故事情节,尤其是文人音乐,很大一部分属托物言志类,如《潇湘水云》《梅花三弄》等。这些作品的特点常是以小标题来综述每一个部分所表达的意象,叶小纲的这部作品亦是如此。诚如作曲家在扉页写的那样:作品一共分为九段,其标题是对于作品内容的联想。《第二“长城”交响曲》每一个章节的内容都有所不同:《汉唐风采》以古乐舞为素材;《长城好汉》则以少数民族音调为基础;终章《壮哉长城》则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抒发新时代下的长城精神。叶小纲以地缘为线索从中亚西域、甘肃嘉峪关一直写到宁夏、陕西、山西、河北、辽宁、长城入海的老龙头;又以时间的角度从先秦、汉唐一直写到现代。与其说作曲家在创作一部作品,不如说作曲家在用乐的方式书写历史。这种创作方式犹如在创作一部章回体小说,一部音乐的章回体小说。似以“讲史”为本质,更似是说书艺人讲述历代的兴亡和战争的故事。可以看到,作曲家的创作方式与章回体小说的写作方式具有一致性与传承性。
(二)板式变化的运用
戏曲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瑰宝,在每个国人心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作曲家来说,戏曲作为凝结着古代智慧、体现中国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如此。叶小纲作为一个深受戏曲艺术影响的作曲家,在《第二“长城”交响曲》也有所体现——运用多种板式变化,其中既有灵活的散板亦有规整的垛版。
散板是一种十分自由、灵活的板式。由于其无板无眼的特性,在传统戏曲表演中,经常通过唱词的语言节奏和语气来达到形散神不散的审美要求。如前文谱例2所示,半吟半诵的演唱形式、非规律性的节奏、抑扬顿挫的语气、自由延长的拖腔以及在散板节奏中,小锣、小对镲、中锣犹如一声惊叹的强奏,无疑不显露出戏曲因素对于该部分的影响。作曲家既突出了一叹三叠的唱腔特点,又辅以了戏曲音乐中常见的打击乐组合对旋律进行增色和强调,使得该部分戏曲意味十分浓郁。
作为世界第七大建筑奇迹之一——长城,在叶小纲的音乐世界里,不仅是一条连接东西方的长廊;还从时间的维度连接了不同的时代。在《序曲》中,歌词的创作与陕北民歌《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中,“我晓得,天下黄河有九十九道弯”不谋而合。“高山峨峨,流水泱泱”则是依据《诗经·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与“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化用而来。这既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回顾,又是对于传统文化进行的创新与展望。它代表着当代作曲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再思索。
音乐自出现伊始,便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音乐分析的终点是对于作品中人文情怀的探析;而人文情怀的根本则是一种对文化追索的哲学思辨。音乐创作作为一种人文活动,归根到底既是作曲家对于自我的定位与追求,其以个体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为展开。而音乐作为主体化的社会艺术,始终承载着文化本位与主题诉求的艺术表达,是一种满足个体社会实现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国审美的凝聚过程。音乐是人类艺术化的反映,作曲家在创作中,一直秉持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于中国式哲学、中国式审美的再构建,以世界通码②的方式重现中国意蕴。不仅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也是对于自身文化形式的现代反思与重构。
注释:
①直音:只体现固定音高,相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音腔。
②世界通码:世界化的通用音乐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