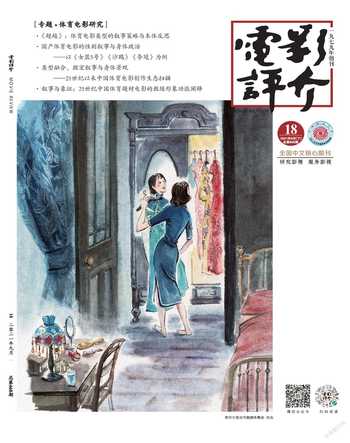《红色沙漠》:安东尼奥尼概念化色彩的情绪表征研究
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大地时,人类便开始了色彩的旅程。电影作为一种较为年轻的艺术形式,受到科技手段的影响,一开始是以黑白默片的形式出现。直至1935年,《浮华世界》在美国上映,电影才从黑白走向彩色。色彩也正式作为电影语言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进入大银幕。虽然《浮华世界》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彩色电影”,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但此时电影里的色彩只不过是满足了人们再现客观物质世界表象的愿望。
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同为视觉艺术的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色彩出现在绘画上,可以追溯到几万年前的史前壁画。在漫长的岁月中,通过艺术家的努力和探索,色彩的本质逐渐地被发掘和运用。从最初仅仅作为再现自然的手段走向主观内心的表达,色彩不再仅仅是造型的锦上之花,而是具有了独立的意义。艺术家在色彩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这就注定电影对色彩的要求不会止步于简单的复制再现,色彩更深层次的表现力和内涵注定被发掘和运用。
1964年上映的《红色沙漠》,导演安东尼奥尼用绘画的方式拍摄影片,突破了色彩在电影中再现自然的功能,主观地处理色彩,充分运用色彩引起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感受来强化影片的戏剧性,影片中人物内心的感受和剧情发展同色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色彩运用上的大胆尝试,使《红色沙漠》被誉为“第一部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彩色影片”,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的盛宴,也充分展示了绘画领域的色彩研究在电影拍摄中的创作性运用。
一、象征性的色彩引导着影片情绪的变化
有了光便有了色彩,人类很早就意识到色彩对于特定的人群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即使在颜料种类匮乏的年代,也赋予了仅有的色彩以不同的内涵。象征性成为早期艺术家运用色彩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此时还只是对象征性片面地认识,色彩在这里更像是一个宗教或者信仰的符号,其自身的魅力和独特性还没有被发掘。随着科学家在光和色方面的深入研究,色彩的本质逐渐得到正确的解释。艺术家对色彩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研究色彩,色彩的象征性也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运用。到了20世纪,艺术放弃了统一的、绝对的美的标准,不再以肖似来评价作品,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色彩在艺术家的笔尖得到释放,以独立的姿态走向心灵,成为表达情感的重要元素。一些艺术流派,比如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的艺术家放弃了色彩再现自然和解釋说明的功能,开始探索色彩自身的表现力。抽象派艺术家更是抛弃了具象造型,将色彩作为创作的主体。他们研究色彩的冷暖、明暗、饱和度的变化以及在画面中所占面积的不同带给人们的视觉印象和心理感受。色彩的象征性在现代艺术里得到全面的、深入的探索和实践。
在《红色沙漠》中,导演安东尼奥尼放弃了通过传统的台词或者演员的遭遇来强化剧情的方式,直接用色彩来突出影片的戏剧性。如同现代艺术家一般,将色彩作为独立的元素运用到创作中,极大地发挥了色彩的象征性和情感作用。在颜色的选择上,导演更倾向于简单的、纯粹的色彩,就像抽象绘画用最单纯的颜色来表达丰富的情感一样,色彩被赋予了深刻的寓意,主导着影片的整体基调和情绪的发展。
影片一开始映入眼帘的是烟雾弥漫的巨大灰色工厂,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顿时让人感到烦躁和压抑。灰色属于中性色,没有色彩倾向,在影片中它是水泥的颜色,是现代工业的代表,也是拉文纳这座城市的写照。人们行走在冰冷的灰色城市里,早已习惯了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人类精神的缺失。当满载传染病人的轮船缓缓驶来,海岸被浓浓的灰色大雾笼罩,岸边的人物如同失去了灵魂的躯壳一般矗立在大雾之中,直至被大雾吞噬。在这里灰色是麻木的、压抑的。
绿色象征着生命,是希望的颜色。安东尼奥尼将象征生生不息的绿色安排在有些神经质的女主人公朱丽安娜身上,让她穿着一身绿色的大衣穿梭在烟雾笼罩的、被污染的城市里,犹如荒野中的一小片绿洲,显得格外醒目。朱丽安娜在一次车祸中受到惊吓,精神异样,常常会出现难以自制的反常行为,表现出极度的不安和对周遭事物的反感。但也正是这种异常的举动让她和在工业笼罩下如同幽灵一般麻木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这种不安和异样的行为在导演看来是长期压抑下精神的释放,是对现代工业化的质疑,对工业时代被摧残的人性的反抗。也许这一点点绿色并不足以撼动整个工业时代,但它至少能够点亮人们心中的一丝希望。大面积的绿色出现在朱丽安娜和克拉德爱情萌芽的地方。绿色的背景安逸而舒适,配合着轻松的话题、一束象征着爱情的粉色小花,让人忘却了机器的轰鸣和遍布工厂的令人窒息的城市。在这里,绿色是朱丽安娜心中的色彩,是她向往的世外桃源和精神的寄托。
属于朱丽安娜的颜色还有紫色。在绘画里,红色和蓝色调和形成了紫色,它相比红色的热烈与激情多了一分克制,相比蓝色的冷酷和忧郁多了一点温度。紫色是优雅的、浪漫的色彩。紫色在朱丽安娜和克拉德相处时多次出现。无论是和克拉德初次独处时穿的紫色裙子,还是他们在河边交谈时克拉德身后淡紫色的天空,缠绵时天花板上出现的紫色的云团,这些都是朱丽安娜对爱情的美丽幻象,虽然短暂,但也能使她的心灵得到片刻的慰藉。
象征着纯洁的白色,在影片中却是病态的存在着。在朱丽安娜犯病以及她的儿子装病时,导演都使用了大面积的冰冷的白色墙壁,配合空间上直线条的分割,无疑强化了镜头画面中孤独无助的氛围。朱丽安娜在得知儿子欺骗自己后精神无法自控,前往德拉克所在的酒店寻求帮助。导演将酒店的内饰全部刷成了白色,甚至包括象征生命的绿色植物也被隐藏在白色颜料之下,在这里没有生命的温度,只有孤独和寂寞的灵魂。一条悠长而苍白的走廊,让朱丽安娜的痛苦无情地延续着。
黄色在影片中与欺骗、背叛和衰败联系在一起。巨大的烟囱喷出的工业废气、被污染的河流、轮船上升起的代表传染病的旗帜都被导演描绘成黄色。导演在讲述朱丽安娜的儿子装病时也用了大面积的黄色作为欺骗的隐喻。克拉德和朱丽安娜的丈夫乌戈在工厂交谈时,墙壁上抽象的黄色构图,似乎暗示着克拉德与朱丽安娜将来的出轨。当朱丽安娜来到克拉德所在的酒店房间,突然亮起的黄色灯光,以及她从房间出逃在街道上时,一闪而过的黄色背景,都充满了堕落和背叛。
蓝色属于冷色系,是忧郁和冷漠的代表,也是影片中最冷的颜色。蓝色大面积地出现在朱丽安娜的家里,使得本应温暖的家失去了温度。正如朱丽安娜和乌戈的感情一般,早已没有了关怀和激情。朱丽安娜生活在被蓝色环绕的家中,也生活在忧郁和孤独之中。明显的蓝色还出现在朱丽安娜想要逃離这座城市时遇到的水手的帽子上。因为语言不通,朱丽安娜最终选择放弃。蓝色在这里同样是冷漠地存在着,在朱丽安娜通往精神港湾的路上形成了一道冰冷的墙。
黑色象征着死亡与恐惧。被污染的黑土地、大片的黑色工业废墟、满载传染病人的黑色轮船、矗立在郊外已经荒废了的黑色小木屋。它们的存在犹如一座座墓碑,记录着现代人的罪行,控诉着工业化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性的摧残。为了强化这种效果,在影片开头部分,导演将工厂旁边的灌木林喷上黑色的油漆,与朱丽安娜绿色的大衣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生与死的对比,是绝望与希望的对比。镜头里朱丽安娜在黑色的灌木林里,吃着一块从路人手中买来的已经吃过的面包。当她看到眼前一片冒着白烟的黑色废墟,眼里满是绝望、不安和恐惧。朱丽安娜被包裹在黑色的世界里,挣扎地生存着。
红色在影片中是暴力和情欲的象征,也是使用最频繁的色彩。在海边红色小木屋中,几对男女缠绵在拥挤的房间里。红色在这里是暧昧的,肉体的欲望在红色的氛围中被点燃,但狭小的空间和道德的约束又使欲望得不到释放,直到克拉德将红色的房间拆除,这种压抑转换成暴力。红色象征激情和爱恋,也出现在朱丽安娜对克拉德表白的轮船上和他们缠绵时的床架上。所不同的是床架上的红色被压缩成细窄的线条,仿佛暗示着朱丽安娜内心的孤独和空虚并没有因为克拉德而得到抚慰。大面积的红色还被用在郊外高耸的金属架上。这些暴力的红色线条无情地分割着画面,犹如一个无法冲破的牢笼,将人们禁锢在这个工业时代。在朱丽安娜想逃离这座冷漠的城市时,背景同样出现了大面积的红色,在一大堆工业废墟的后面,红色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温度,更像是一种警示,预示着朱丽安娜将无法登上那条远去的船只,无法摆脱痛苦的折磨,只能继续挣扎在这片血淋淋的精神沙漠里。
二、抽象化的色彩构成带来的审美享受
20世纪的欧洲是现代艺术绽放的时代,也是彻底摆脱传统艺术观念的崭新阶段。艺术超越纯美学范畴,打破了文艺复兴一直以来建立的模仿再现的美学体系,走向主观精神的表达。艺术所承担的部分文学功能也被放弃,而突出强调它的纯视觉性和审美功能。[1]艺术开始走向大众、走向生活,在这种背景下抽象艺术应运而生。它突破了艺术强调写实再现的局限,把线条、色彩这些绘画的基本要素作为独立元素进行创作;摒弃了色彩的空间和明暗表现,讲究平面化的构成,强调用最简单的色彩来表达丰富的情感。色域绘画是抽象主义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色域绘画的艺术家通常用大片统一的几何抽象色块构成画面,作品纯粹而富有张力。几何形的构图让画面看上去更为理智、冷静,但这并不影响艺术家表达强烈的情感。几何色块的抽象构成也让色域绘画作品充满了现代感。
《红色沙漠》中,导演在处理镜头画面时,将色彩压缩,放弃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用抽象的色块和几何的线条来分割组成画面。常常以大面积的主观色块作为影片的背景,简洁、明了而富有寓意。很显然安东尼奥尼领悟到色域绘画的精髓。在剧中,大到场景的布置、小到人物的服装、道具的选择上都是简约的、几何化的,没有多余的装饰,更在乎的是色彩的搭配,突出强调色块的运用。在视觉上,人物更像是移动的色块,整部影片仿佛是一幅幅抽象绘画的组合。
在女主人公朱丽安娜的丈夫乌戈工作的工厂里,布满了巨大的机器和纵横交错的管道。安东尼奥尼利用工厂自身的几何形构成和直线条分割进行创作。他仿佛在绘制一幅巨大的抽象艺术作品,选择性地将一些机器和管道涂上单纯的、明亮的色彩,将琐碎的零件统一在灰色调里。这样的色彩分割,压缩了画面的层次,使原本杂乱无章的工厂变得井然有序。色彩的加入在这里并没有破坏整个工厂给人带来的压迫感,却增加了画面的现代感和构成感,使得工厂的镜头不会过于枯燥无味,一切都显得格外和谐,在描述故事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审美的享受。
在朱丽安娜和克拉德相见的街道上,富有层次的灰色调让画面显得简单而不单调。朱丽安娜的紫灰色长裙除了一条黑色的围巾外没有多余的装饰,克拉德身穿一件干净利落的深灰色大衣,搭配一条黑色的裤子,正好与朱丽安娜的黑色围巾相呼应。小面积绿褐色的领带与两人的发色也属于同一色系。一个个抽象的色块,被统一在暖灰色的背景里。在他们随后走进的朱丽安娜正在装修的小商店里,导演在墙上留下不同颜色的色块,形成如同色域绘画一般抽象的色彩构成,既符合故事情节,又增加了画面的美感。同样是在那条相见时的街道上,当朱丽安娜和克拉德从小店铺出来时,导演把卖杂货的木板车和车上的物品都处理成不同明度的灰色,削弱了物体本身的特性,将其隐藏在色彩之下。在导演的镜头里,它们或许就是一个符号、一个色块。此时,它们的色彩比它们本身更具有意义,不仅增加了画面的灰色层次,丰富了黑白灰构成,也与小商店里充满生机的彩色色块形成鲜明对比,凸显朱丽安娜莫名而来的伤感和这座毫无生机的城市。
《红色沙漠》里最著名的镜头应是作为海报出现的红色房间。在拍摄时,导演将一个海边的小木屋刷上色彩。在小木屋内,墙面以白色为主,其中一个房间刷上鲜艳的红色。值得注意的是,白色的墙面是先刷了一层红色的油漆,再在上面覆盖一层白色涂料。使得并不平整的白色木板墙透露出斑驳的红色,强化了木板墙的肌理感。如同抽象艺术家在创作一般,总是想办法让单纯的色彩拥有丰富的层次。再加上一块块几何形的木板自带的构成感,白墙本身就是一幅独立的、完整的抽象画。红色的房间里,几对男男女女慵懒地挤在狭小的垫子上。在导演的镜头中,他们就像是一些移动的色块,随着镜头的变换,在红色的背景里肆意地翻腾着。在房间内人物服装的选择上,导演也非常考究,都统一在墙面的暖红色调里。即使是一位女士的绿色裙子也选用的是偏暖的豆沙绿,并没有产生红绿对比的冲突感。反倒是朱丽安娜的黑色裙子具有极强的吞噬感,在红色的反衬下,显得尤为突出。黑色是镜头画面中最重的色彩,当朱丽安娜起身时,镜头里出现黑色的天花板,它和处在红色背景里的黑色裙子相呼应,此时的黑色裙子也起到平衡画面的作用。小木屋的外墙是蓝色的,当朱丽安娜被远处驶来的轮船所吸引站在窗口眺望时,导演将镜头短暂地停留在这片蓝色上。湖蓝色的墙面,蓝绿色的木门,隐约透露出红色的两扇白色长方形木窗,玻璃窗里呈现出几乎将朱丽安娜吞没的黑色。别具匠心的色彩搭配和独特的取景方式,配合小木屋天然的构成,让人过目难忘。
在郊外的工地上,当朱丽安娜独自走向巨大的红色金属架时,导演从金属架的局部取景,透过金属架聚焦在朱丽安娜身上,让处于镜头前的金属架因为失焦而显得模糊,只留下抽象的构成和色彩。此时的画面里,金属架本身的意义已经被淡忘,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红色的线条无情地分割着画面,犹如一张巨大的网,将朱丽安娜囚禁在这片毫无生机的红色沙漠里。同样的拍摄方式还出现在朱丽安娜和工地上的工人交谈时,导演缩小了景深,让朱丽安娜身后的一大片红色金属架处于模糊的状态,压缩了它们的空间感,此时留在观众视觉里的背景就只剩下红色线条的抽象化构成。背景平面化的处理,使镜头层次变得简单,人物也更为突出。在酒店房间里,朱丽安娜和克拉德缠绵时,画面中总是出现一条红色的线,随着镜头的变换以不同的角度分割着画面,使画面变得抽象而富有寓意。這其实是酒店床架的局部。导演运用床架简约的直线条构成和单纯的色彩直接组成画面,弱化了床架本身的含义,更在乎的是它作为一条线、一个色块在镜头里带来的视觉审美。导演对色彩抽象化的处理方式,增加了影片的艺术性和现代感,也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结语
在《红色沙漠》中,安东尼奥尼将绘画领域的色彩研究运用到电影的创作中,处处体现了在色彩方面的用心。他将色彩抽象化、概念化,使整部影片的色彩变得简单、纯粹而富于美感;充分发挥色彩的象征性作用,用色彩来突出影片的情绪变化,给观众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增加了影片的参与感,色彩在影片中被赋予更深层次的内涵。与其说《红色沙漠》是导演用摄像机拍出来的,不如说是用摄像机画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像画油画那样涂抹我的电影,我想在色彩中发现关系,不想局限于摄影机提取的自然色彩。”《红色沙漠》是导演带给观众的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虽然在安东尼奥尼之后,导演们很少有像他这样彻底地将绘画融入电影拍摄中,但他在色彩方面的大胆尝试,却给后来者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随着电影拍摄技术的发展和表现内容的多元化,色彩在电影制作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它的自身魅力和情感表现力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和运用到电影创作中,影片中色彩的发挥空间也越来越大,极大地增加了影片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我们观影经验的一部分。意大利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曾经说过:“色彩是电影语言的一部分,我们使用色彩表达不同的情感和感受。就像运用光与影象征生与死的冲突一样。”色彩的探索仍在继续,电影也必定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审美享受……
【作者简介】 刘婷婷,女,四川成都人,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书画研究会主任,主要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研究。
参考文献:
[1]陈洛加.外国美术史纲要[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