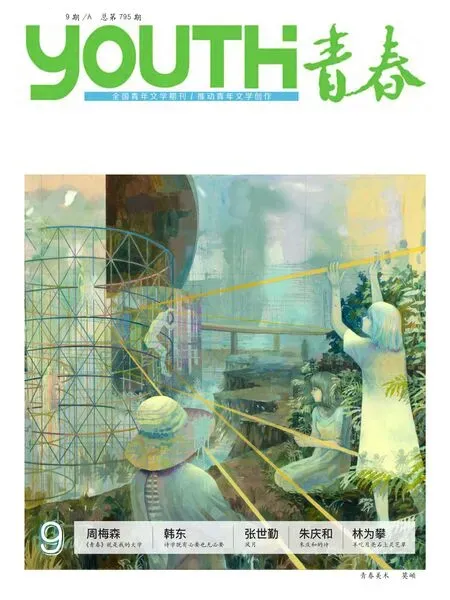雨 水
雨下了一夜,朱丽躺在床上听了一整夜的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不眠夜,朱丽将这首少女时代就非常喜欢的词默念了无数遍。窗外天光渐明,她起身,把床头的珊瑚绒睡衣裹上身,趿拉着拖鞋去卫生间。她摸索着刷牙,洗脸,天还未大亮,且卫生间的采光不好,可她并不开灯。她不开灯,因为怕见到镜子里被明晃晃的镜前灯照耀下的那张脸。那张黑黄不均的惨败的脸。
洗好脸,撕了张面膜敷在脸上。朱丽这才打开灯,将换衣桶里的衣服拣起来,内裤和袜子分别放两个小盆里,王剑的浅色衬衣捞出来放面盆里等下手洗,其他的衣服塞进阳台的洗衣机里。
到阳台,朱丽被吓了一跳。花架上的文竹简直成妖了,一夜之间居然生出了一根长须,蜷蜷曲曲迈过一盆兰花,一株三角梅,攀到了阳台顶的晾衣杆上了,文竹疯狂的长势如此骇人。究竟还有多少类似暗中疯长的事物啊,朱丽仰头望着空中的文竹须想。
今天是大年初四,按理,初四不作兴出门的。但朱丽年前就和他约好了,2月19日见面。219,爱要久嘛。也是他说的。
朱丽把目光从文竹须上收回来,投到窗外。从二十层楼的阳台朝外望去,隔了一条马路可见纵穿寿春公园的那条河。那河原是人工开掘的截涝渠,但与淝水一接应,水便活了。从高处看,这弯曲曲折白亮亮的河像只水袖,让朱丽真想把它拎起来甩上一阵。
洗衣机注满水,咯吱咯吱地转了起来。朱丽从阳台回到卫生间,给王剑的衬衣打透明皂的时候,朱丽发现领口除了一圈油渍外,还有一块暗红。那暗红里隐隐有点洒金亮片,像,口红。那款她在商场里试过,但没有舍得买的豆沙色口红。她的手指在那块暗红上轻轻地划过,就像那天对着镜子,轻轻触碰自己涂了免费大牌口红的嘴唇。
朱丽洗好衣服,换好衣服,并化了个淡妆。此刻,她热了几个荠菜圆子,坐在餐桌旁边吃边看微信。微信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年祝福,还有不同商家的发送的推销链接,就是没有他的消息。朱丽把那些不相干的消息一条条删除,微信总算干净了。只有“他”独踞此方。只是,昨晚九点多,朱丽问他,明天几点见?至此,十二小时过去了,他还没有回复。
又胡乱翻了会儿朋友圈,再转回来看信息栏,还是没有信息。朱丽感觉心里有点毛躁躁的焦虑。
初四,戳事。那天,他说2月19号见面的时候,朱丽翻了一下台历,一看是大年初四,心里就有点膈应。但,她的反对意见还没出口,就被他那句“219,爱要久嘛”给堵截了。
算来,他们认识也快两年了。两个“年下”都要熬过去了。时间疯了似的撒开了脚丫子往前跑,可很多旧事,还是带不走抛不掉。
朱丽把手机从微信按回主屏,屏保图是大山龇牙咧嘴扮鬼脸的照片。朱丽突然想起来,这张照片是三年前年初四拍的。初四不出门,一家三口窝在家里看看电视吃吃零食玩玩手机,无聊而乐呵。谁知,没过几个月,大山就成天嚷嚷头疼。开始还以为他偷懒不想做作业呢,但看他喊疼的时候额头会沁出一颗颗的汗珠子,她才把那疼当了真。带孩子去县医院看,说赶紧到省里吧。到省里,不几天又转到了上海,得到“淋巴癌晚期”五个血淋淋的字。从确诊到孩子离世,不过五个月。仅仅五个月,死神就把她十月怀胎,辛辛苦苦从个小肉球养到一米七五的十五岁帅小伙给掠走了。
朱丽回想起大山走后,她经历的那段不吃不喝不睡甚至也哭不出来的日子。那段日子犹如炼狱。她像被绑在一块大石上给沉了潭,就感觉身体不停地往下坠往下坠,无法呼吸,无法呼救,既踏不到底也见不到光。她多希望王剑能伸出手拉她一把,可王剑出现在那个寒窑似的家里时,不是烂醉如泥就是木然无语。
“没出去?”
朱丽在开门声、脚步声之后听到王剑瓮声瓮气的发问声。她“嗯”了一声就起身,把碗筷收拾好端到厨房。“你也不出去?”见王剑从卫生间出来后竟坐到了餐桌旁,朱丽问。
“不出去了,今天我收拾收拾准备搬走。”王剑抹了抹头脸,打着哈欠说。
朱丽心下一凛,想到刚在王剑衬衫上看见的那个口红印。刚还自劝自地想,也许是在哪蹭上的什么脏。哪蹭上的?女人蹭的!
大山走后不到一个月,患肺癌五六年的公公也去了。朱丽和王剑一起把婆婆接过来。婆婆七十了,年轻时是县剧团的台柱子,现在是老年大学的戏剧老师,寿州锣鼓队的队长。老太太穿着大红的中式棉袍,拎着唱戏机进了门,把这个因为丧父失子而黯沉沉的家给激活了。原来成天窝在家里不肯出门的朱丽被婆婆拽着,“给我提溜机子,帮我拉行头箱子”,婆婆这么吩咐她。
朱丽跟着婆婆,学会了唱戏。唱戏真好,上了妆,换了行头,水袖一摆,就成了杨贵妃:“人生在世如春梦……”成了杨贵妃,就能忘记自己的疼了。
“搬哪去?”朱丽端了一碗圆子放在王剑面前问。
“搬回老院子。”王剑埋头吃圆子,顺带含糊回答。
“老院子不是要拆了吗?”朱丽记得年前陪婆婆回去拿东西时,听巷子里邻居说的,说是拆迁办的人已经开始入户测量了。
“不是还没拆吗?”王剑猛地抬起头,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朱丽有点按捺不住,差点脱口而出:“少在我面前摔摔打打!”但她生生地咽下了那句话。她转个身,拿抹布去擦拭酒柜上莫须有的浮尘,她告诉自己,没有和他再争吵的必要和意义了。
“这下你解放了,可高兴?”王剑似乎并不觉得他们这对离婚不离家的夫妻就不能继续拌嘴,就像朱丽也不觉得继续把他伺候得跟个爷似的有什么不对。习惯了。
朱丽十九岁从省林校毕业就跟男朋友王剑到他家了。朱丽老家在阜阳农村,初中毕业高分考进了省林校,心想过三年就能成吃皇粮的了,再也不要像父母那样辛苦地土里刨食。可谁想到呢,到她毕业时,中专不包分配了。她在学校参加文学社团时认识了隔壁警校的校刊主编王剑,多亏文学做媒,给她和王剑之间牵上了红线。她不想回家务农,便跟王剑去了她家所在的小县城。
因为有个当派出所长的父亲,王剑毕业回去没费周折就到所里当了片儿警。王家二老见儿子带回一个勤快水灵的姑娘,没二话,认下了。朱丽在小城里落下脚,在王家人的推荐下进了新成立的联通公司。翻过一年,朱丽年满二十,就和王剑领了证。婚礼因为朱丽肚子已经大起来,就不方便办了。儿子出生在一个雨后的清晨,从县医院的病房往外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北的四顶山上的奶奶庙。婆婆拨拉着新生娃娃的小鸡鸡,一叠连声地说,四顶奶奶显灵了,显灵了!四代单传的王家,因为大山的到来充满了欢笑。
有过多少欢喜,失去就要付出多少泪水。
此刻,王剑放下碗筷,咄咄地问朱丽“可高兴”。
朱丽把抹布往餐桌上一放,直视着王剑的眼睛说:“你高兴就好。”
朱丽望着二十年前吸引自己目光的那两道剑眉,此刻滑稽地虚悬在王剑油腻的脸上,肿胀的眼皮与布满血丝的红眼睛显得他眼神空洞。他过得也不好。朱丽感到心头紧紧地一蹙。
“我高兴?我凭什么高兴。娘老子都没了,儿子也丢了,老婆也是人家的了,我能高兴?”王剑经不住朱丽的目光,把椅子往后一靠,裂了条缝子,起身走了。
朱丽听他这么一说,心火腾地窜了上来。她起身把椅子往边上一顶,跟进了王剑的房间。房间里烟味呛人。她咳了两声,指着正拉开衣橱找衣服的王剑说:“好像天底下就你吃了亏似的,你没了娘老子,丢了儿子,你儿子不是我儿子?你娘老子不是我天天伺候着的?我跟了你快二十年,自己爹妈走的时候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倒是说清楚,我还是你老婆的时候到底跟过谁呀?是你自己成天在外头厮混,倒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泼!”
朱丽没说完就连扑带撕地砸向了王剑。王剑被扑得猝不及防。他只有张开铁钳似的手臂把朱丽牢牢地箍进怀里。
这场毫无道理的男人与女人的战争莫名其妙从地上移到了床上。朱丽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醒来发现自己枕着王剑的胳膊,并且他的一条腿还蛇一样地缠在她腰上。他们居然像许多年以前那样亲密地睡在了一起。是王剑的手机在边上响,而他丝毫没有察觉地继续大奏鼾音。
朱丽从他的怀抱里挣出来,想去拿手机。王剑醒了,翻身抓过手机,看了一眼就关了。
“谁?”朱丽问。
“搬家公司的。”王剑伸过手继续来楼她。
“那你不接?”朱丽推开他的手问。
“又来了是吧?你还记得当初我们怎么弄掰的吗?就是你成天疑神疑鬼。孩子走了,你能哭,能找人叙。我怎么办?我一个大男人,就只有出去喝酒。喝酒回来迟了你就闹。非说我跟楼下开饭店的好上了,不就因为是邻居,她家被偷找我帮忙破了个案子吗?你说,我俩这都离了两三年了,我跟谁好了?”王剑一骨碌坐起来,与她目光对视着说。
朱丽埋下头,泪无声无息地涌了满脸。能怪她吗?那是婆婆一过来,就跟她说,赶紧把环子取了,再要一个。要什么呢?播种的人总是半夜才回来,上了床溜着床沿子侧着身子背对她。他不动她,她能主动?别说她压根没这个心思,就是有,她这种好面子的传统女人也不会那么不要脸皮地上赶着的。
不碰就不碰了,大家各睡各的,也倒安泰了一阵子。可有天夜里,朱丽被一阵嘀哩嘀哩的声音吵醒了,醒了发现他正拨弄手机呢。后来,屡次发现他半夜抱着手机玩。能玩什么呢?朱丽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玩微信的,也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他”的,就是今天爽约的那个他。
想到“他”,朱丽有点委屈。一委屈,泪就更多了。
王剑下了床,趿拉着走出房间。过了会儿,他拿进一包纸巾,连扯了几张,往朱丽脸色胡乱地蹭。
朱丽的心突然就被他这笨拙的举动给蛰疼了。王剑从来就是一个不懂温存的家伙,能替她揩泪,就是宠她,疼她,待她温柔到极致的表现。
女人一被宠,就想撒娇。朱丽许久没有被宠了,连撒娇的分寸都掌握不好了。她甩开王剑的手,说:“你不是说要搬走吗?走啊!”
“这么盼我走?”王剑问。
“赶紧走,走了干净。今天我给你洗染了女人口红的衬衫,不知道明天我要给你洗染上什么脏东西内裤呢!你妈在,我们是为瞒着老太太装着在一块儿,现在她走了,你爱干啥干啥吧,再也不用顾虑了。”朱丽说着,把刚才不知怎么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上身。
“什么口红?”王剑一把拉过要下床的朱丽说。
朱丽并不说口红的事儿,她说:“别拽我,我今天还有约会呢!”
王剑还想再说什么,但朱丽猛地挣开他,冷笑道:“再不撒手,告你强奸!是不是干不是老婆的女人特有劲啊?变态!”
朱丽说罢,冲到客厅,拿起手机。打开微信,“他”还是无音无讯。男人都是他妈的说话不做数的货!朱丽在心里忿忿地骂。
两年前,朱丽发现王剑整天半夜偷偷看手机。然后又发现他的车老停在楼下女人开的饭店门口。最可恶的是,有一天她还亲眼看见他大中午的从楼下女人房间出来。她认定王剑不碰她是因为楼下那个妖冶的女人。
“离婚!”那天夜里,朱丽在他醉醺醺地回到家后,跟他摊牌。那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婆婆都记得呢。她穿上那件过去他总说比不穿还勾人的粉色睡裙,他却视她为空气。
第二天,俩人就离了。离婚之前,王剑说,离可以,但得有约法三章,一是离婚不离家,老太太有心脏病,受不得刺激,离婚的事先要瞒着她;二是双方都不能带外人来家;三是不得骚扰对方。朱丽说,行。
大红本本换成了紫红本本,离婚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
离婚那天,朱丽在微信 “附近的人”上加了“他”。原因很简单,“他”看上去很像大山,而且他在微信上的名字就叫“大山”。朱丽觉得,这些年,她的世界被大山给填满了,几乎还不懂事呢,就稀里糊涂地生下他,当了妈。大山上初中后,王剑就让她辞职回家带孩子了。孩子没了,她的世界也空了。空得不知道用什么去填,就指望能从王剑那得到点安抚,或者,得到一颗种子,再在她肚子里种下一棵树,她不奢望能再生出一座山,就要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好的呀。可是,王剑不肯给她。
要不是七十多岁的婆婆整天风风火火地拉着她忙着忙那,她估计自己能把自己活活憋闷死。离婚后,朱丽白天陪婆婆东奔西跑,晚上躺在床上玩手机,在微信上和“他”说说话儿。“他”好像也很孤独。“他”说自己很苦闷,没有可以说上一句真话的人。她说她也是。
于是,他们就成了对方倾诉的对象。有时候半夜,“他”说:“我喝多了。”
朱丽醒来看到信息,就回复他:“一个人,尽量别喝醉。泡杯蜂蜜水,解解酒吧。”
第二天,他会回复一大堆玫瑰、拥抱和爱心。她笑眯眯地回复咖啡礼物和拥抱。
就这么你来我往地闲聊着,一晃两年过去了,之前他们从来都没有提过见面,也没有问过彼此的情况。甚至不用语音、视频,不发照片。他们俩都从不发朋友圈。也许就因为这些,朱丽觉得“他”是一个可信的人。一个在网上对女人什么都不图的男人,难道不可信任吗?
情人节那天,婆婆组织锣鼓队给一家新开的主题餐厅做庆典,不知道是不是表演得太投入了,她在低头击鼓时,突然跌倒在地。送到医院,心电图就直了。老太太没有任何征兆地去了,这对朱丽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处了近二十年,对于外乡人朱丽而言,婆婆早成妈了。
送婆婆走的那三天里,朱丽没有上微信。很神奇,送走婆婆后,朱丽回家躺在床上打开微信,发现平时几乎每天都会跟她说几句话的“他”也没有发消息过来。而就在她刚打出一个咖啡的表情后,“他”也发过来一个拥抱。
朱丽说:“这几天很累。心力交瘁。”
“他”说:“我也是,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成了一个可怜的弃儿。”
朱丽发过去一个拥抱,说:“别难过,你还有我。”
“有你真好。”“他”说。
朱丽抱着手机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看见手机上堆满了一长串消息。“他”说:“好想有个家,有个能和自己说说话的人。”
朱丽赶忙回:“一定会有的。”
“他”问:“你愿意做陪我好好说话的人吗?”
“嗯。”朱丽答。
于是,那一天,他们约定,要见面。“2月19号见吧,219爱要久嘛。”“他”说。
朱丽答应了。
可今天,2月19号,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28分了。“他”还是没有消息。难到“他”在调戏她吗?不会吧。或许,“他”要等到5点20分?520我爱你嘛。
时间分分秒秒,磕磕绊绊地。朱丽心里更是疙疙瘩瘩的。她想到刚才和王剑在房里不明不白地做了一次爱,感觉心里很愧对“他”,像背叛了他感情似的内疚着。而转念一想,“他”总是与她在很多细微的感受上都神同步,那么,一直没有消息的“他”是不是也和什么女人在床上缠绵呢?想到这儿,朱丽的心就像被揪起来似的。她想也不想,直接发了一个问号。
“你好。”对方很快地回复。
朱丽看出来这是“他”疏远她的口气。她顾不了那些了,第一次,毫不犹疑地按出来语音通话键。
朱丽隐约听到王剑的手机也响了起来。她挪步,走到阳台:“喂!”
“喂……”
朱丽像扔烫手山芋似的把手机扔到了洗衣机盖上。王剑已经光着身子跑出来了。
王剑还握着手机,他们面面相觑。
雨下得很大,阳台玻璃上,挂着一层水帘。透过水帘往外看,世界一片混沌。如盘古开天地之初。文竹的新芽似乎长得更长了,在晾衣架上颤巍巍地往下伸展着。朱丽突然想到,今天不仅是大年初四,不仅是219,还是“雨水”节气呢。“雨水后,鸿雁来,草木萌动。”台历上写着。朱丽不由自主地摸着自己的小腹,想,会不会有一颗种子,也在这里萌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