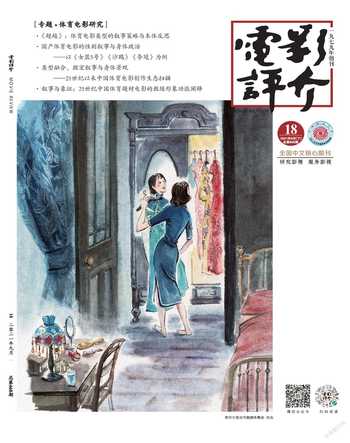潘诺夫斯基图像学视域下的中国动画电影研究
电影《姜子牙》是2020年由中国彩条屋公司出品的一部以姜子牙为主角的3D动画作品。因为与先期同公司出品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关联宣发,动画制作精良的《姜子牙》受到广泛关注,并取得同期票房第二且超16亿元票房的不俗成绩,成为中国当代动画电影的代表作品之一。
《姜子牙》作为中国公司出品,又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人物为主角的电影,决定其大概率是一部兼具中国味道、中国风格与中国气质的电影。当然,动画电影是否“中国”,仅携带“中国”标签远远不够,还需考量其是否采用经典的中国传统题材、是否使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更应看其最终形成的有机整体,能否体现中国审美意趣以及中国文化内涵。一部影片涉及的因素众多,本文借鉴潘诺夫斯基在图像阐释中对图像进行分层的思路,换言之,一幅图像作品由基底层向上依次能区别为材料、形式构成、人物形象、情节、文化与观念等多个层次。[1]這种分层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区分,旨在便于讨论与理解,因此,将图像作品中同时呈现的多重信息从不同角度区分为不同范畴。除潘诺夫斯基的方法外,还有其它版本的区分方式,如段炼将画面作为一个整体的蕴意结构,并区分为形式、修辞、审美、观念四层。[2]
常见的“内容与形式”二分法其实也是一种分层,区分各层次的标准和各层次的命名因思路不同说法不一,有时概念也有混淆或重叠,但对于图像、视觉作品这类难以完全用语言描述的“文本”来说,“分层”无疑是帮助思维深入的“利器”。
一方面,电影画面是介于视觉与文学之间的一种动态且有情节发展的艺术图像。其中,平面图像部分基本可直接套用绘画分层概念,如媒介材料层、形式构成以及人物形象等。另一方面,电影拥有对事件、情节以及语言的表达,使其更近乎一部长篇文学作品,可进行连续、完整而复杂的叙事,这是绘画等静态图像无法拥有的表现能力。因此,电影中的情节、观念等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要远大于绘画中相关元素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形象”这一概念不仅指可视的形象,也包含通过文学手段、情节事件等只能在意识中构建形成的“语象”等想象中的形象。[3]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是双重乃至多重形象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复调形象。从多角度分层解析一部电影,能更加清晰地体会其中散发出中国味道的差异。
一、媒介材料层面
媒介材料是作品最基本的支撑,任何形象地展现都需要依靠具体客观的媒介材料。麦克卢汉言:媒介即讯息。[4]而这一点在大部分时候不为人所察觉,譬如新闻由电视播报还是收音机传播似乎并不重要,现代化信息传播媒介的能力越强,其本身的存在感反而越低。在传统媒介材料中,由于表达的受限和吃力,要求特定材料和相应技术,比如国画只能用宣纸才能产生水墨层次等,因此,媒材的特质与作用反而更加明显。
电影作为19世纪末才出现的“新媒介”,其方式虽然复杂,但与以往视觉艺术作品凝聚于实体材料内不同,真正呈现形象的是几乎没有实感且能随意变幻的色光,换一块屏幕,或投到白布与白墙上,无论拍摄何种内容,器材本身特点并不会突出影响形象塑造。受惠于现代科技发展,电影流传与应用的范围迅速扩张,与以往美术作品在特定地域流传发展的漫长时间相比,电影称得上迅速漫延至全球,导致电影虽然作为一种媒介,但并未与任何文化形成如国画与东方、油画与西方等类似的特定紧密关联。
要想探究电影媒介所携带的文化基因,与其发源地脱不了干系。例如银幕呈现为稳定且近似黄金分割比的长方形,长宽比例更接近西方经典画幅。而中国传统绘画不讲究定点观察,因此,往往需要画幅能提供一种流动且“线”性的观看,最典型的是长长的手卷。大画幅模式也更接近西方的审美习惯与观看习惯。中国倾向于“卧游”“神游”的欣赏要求,使书画作品更加适合室内观赏尺寸,还有小品、信札等适合私密赏玩以及信件来往的更小幅的形式。西方有追求真实、再现、定点、舞台式观看的传统,一旦材料媒介允许,该要求立刻实现“超大号”,基本等同于舞台加上天空,几乎能遮挡整个视野银幕。
电影并不等于绘画,不是静止而是连续的图像。因此,就“能提供流动而连续的观看”这一点来说,其与中国传统审美要求不谋而合。尤其在视角辽阔且平缓移动的长镜头中,银幕仿如化身为缓慢打开的“中式画卷”。电影“观看”天然呈现持续式,“蒙太奇”手法间断、拼插的效果反而需要再次加工创造才能实现。
动画电影相较于实景拍摄型电影,与绘画的联系更加紧密。早期动画电影大多完全依靠二维手绘画面,整体风格受原画媒介材质影响。如1960年的水墨动画作品《小蝌蚪找妈妈》,以中国独特的水墨技法作为人物造型和空间造型的表现手法[5],深得国画意趣,温和清新,诗意盎然,整部电影极富中国气质,是“中国动画学派”的力作。
在图像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代动画电影中,影片不仅能间接利用各种传统媒介材料进行造型,还可直接使用电脑造型,制作各种特效。与“手绘”相比,“电脑”像是一种能直接处理“意识”的媒介,制作图像不需要处理实物材料,也不会因此产生对制作人员的种种具身性的技法要求,拥有近乎全能的视听表现能力,可极大地满足大众感官享受。然而,无论动画电影能表现何其“逼真”的形象,本质上都是“人造形象”,需要“无中生有”而非“随心所欲”。甚至,用电脑造型的困难一点不比手绘困难要少。因此,3D动画无论效果多么酷炫,本质上都与手绘动画一样,保持着与绘画一脉相承的“主观”基因,而这种“主观性”也符合中国图像传统。
《姜子牙》充分发挥了3D动画电影的媒介优势,打造出“中国古风世界”,借助现代化视听手段建构恢宏场面。影片在二维与三维之间形成统一的视觉风格,既体现出中国造型传统,又有对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融合与创新,由于动画表现想象事物的自由,天空中玄鸟的流转生辉,北海白雪皑皑、水波不兴的空旷幽远等,得以美轮美奂的呈现,整部影片充分体现出3D动画媒介与中国神话故事的相得益彰。
二、形式构成层面
如果说媒介材料层是一部作品最基础的底层,其作用容易被忽略,那么形式层的作用则更加稍微明显一些,“形式”是指视觉元素构成的形式,其与媒介材料密切相关,不能绝对分开,只在理论层面单独讨论。形式层针对的是跨越了材料实物整体特点的视觉因素,例如,无论是油画材料还是国画材料都具有的色彩、形状、质感等基本范畴。当媒介材料层成为作品支撑层时,被重点考虑的是其能影响作品的相关属性,包括但不限于视觉属性,部分隐藏属性都潜在地发挥作用,参与到作品表现中。例如,青金石在作蓝色颜料使用时,价格昂贵且稀少难得的特性,影响其在作品中的使用。
《姜子牙》与《哪吒之魔童降世》属于同公司产品,这种关系作为《姜子牙》的“属性”,显然使观众产生“高期待”心理。当然,完全与作品无关,或相对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属性依旧容易被忽略。当只关注形式时,这种“忽略”会更进一步,仅着重考虑抽象的视觉形态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构成关系,例如形状、结构、光线、色调、虚实、对比度、动势等。
形式构成层属于相对基础的一层,其作用并不明确地体现在具体作品内容中,而是潜在地发挥一种基调般的作用。例如周杰伦的《菊花台》颇有中国古风韵味。除歌词的内容与形制外,其谱曲采用中国古音制——只有宫商角徵羽,相当于西方音制的1、2、3、5、6没有4、7半音,这是曲调具备中国风的重要原因。随着现代交流方式不断发展,人们获取视听艺术作品的方式早已不再局限于生活地域。技术发展使创作艺术作品的门槛逐渐降低,盛行的短视频创作更是为每个人提供了创作机会。各种形式风格变化多端,演变迅速,无法与某种地域形成固定联系,从而难以再以地域命名某种风格。作品形态是否有“中国”味道,指的更多的还是传统中国味道。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受传统东方审美观念影响,中国艺术作品总体、稳定呈现出方中带圆、中庸柔和;造型以线为主、以色为辅;散点观察、更强调平面构成关系等形式特点。
在《姜子牙》片头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中国传统美术造型。首先,以线条为主要的造型元素。无论人物、马匹等具有明确外轮廓的实体,还是烟、火等偏虚的非实体形象,都有稳定明确的形状,由清晰的线结合平面色彩塑造而成。其次,造型柔中带刚。图中并排站立的战马形成连续起伏的线条,既富装饰性,又具排山倒海的力量感,整体造型刚劲圆润。整个片头部分的空间不依靠焦点透视建立深度,主要通过遮挡创造层次,充分彰显中国美术造型的传统风格。
正片中,尽管线条与平面形状消失,改为由借助透视、光影等因素塑造的逼真立体的空间结构,并追求大对比且强烈的视觉刺激,但审美内核却充分浸透了中国传统味道,在大量借鉴中国传统绘画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引入东方气、空、玄的概念打造出一个融合了中国上古传说和《山海经》中诡谲异兽世界的中国神话图卷,画面美感强烈而独特。[6]
三、具体内容层面
视觉作品中的人物、事物是层次中最明显且相对具体的内容,是由基础视觉形式元素组合后形成的整体结果,这也意味着对形式和材料前两个基础层次的忽略。相较于材料与形式,具体人物形象与现实世界具有更加清晰的联系,一旦形成,不仅提供视觉效果与审美观念,还会提供特定的身份信息与明确的意图观念等。在电影中,这一层面包含两个突出因素,一是人物造型,发括发型、服饰、表情以及姿态等;二是人物身份设定、性格色彩。后者需依靠前者的烘托,有时甚至不惜让造型摆脱事实以符合人物整体形象。83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杨康一角,若按照人物身份在历史上的真实状态,作为金国小王爷长大的他,不会留大宋男人的发型,但如果将杨康头顶剃秃,实在难称“风流倜傥”。古代发型还关乎个人的家国观念与民族立场,因此,这一明显为了美感的改动不免被置疑。无论怎样,可以确定的是,“风格如何将意义赋予主题”、人物造型与人物身份、性格设定之间的配合或矛盾,正是这一层面中最重要的范畴。
影片中绝对主角姜子牙的造型,无论在年纪还是服饰上,都未严格按照读者既有的刻板印象塑造。整体造型既有明显的中国特点,又有创新与变化,能发现一些现代经典造型套路的影响。在片头中大战狐妖的姜子牙保持中国经典古代男性发型,右衽服装也是明显的古代汉族服饰特点。正片中,发型相对活泼——脑后辫子变短,额前有刘海与碎发;服饰由静虚宫大弟子时华丽的宽袍大袖变为被贬后的粗布短打,还加上了颇有自然风味的羽毛披肩,服饰的转变完全配合着他境遇的转变。影片中姜子牙的另一个造型则体现他心态巨变下的“一夜白头”。“白发造型”中隐约有西方绘画中基督悲悯形象的影子,但又增添了几分中国人物特有的苍凉与坚毅。对于常见的动画观众而言,该造型并不讨喜,令人深思,暗合片中“愿天下再无不公”之呼喊。
影片中另外一位较为重要的角色是半狐半人的小女孩“小九”,作为虚构的人与狐妖结合的人物,她并不像“姜子牙”一样有明确规定的身份,造型可以更加自由。作为姜子牙的对照与辅助组,该形象具备更多现代气息。示意小九狐妖身份时依靠蓬乱的短发中顶出的两只尖耳朵,与西方童话中精灵的经典形象有所重合;勾勒出女孩一双漂亮长腿,细想之下,也并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风情,并完全超越当时技术,而脸上最关键的眼睛则明显是中国式狐妖标准——既含蓄又传神。
四、叙事层面
叙事层在绘画、雕塑等静态作品中没有能完全对应的层次。电影叙事内容丰富且形式多元,建立在稳定的具体内容层之上,在人物、事物以及场景中推进发展,最终形成能单独拿出来讨论的范畴,如情节与观念等。与具体内容相比,情节、观念等像是其中能抽离具体人物的线索、运动和想法,在整个叙事中形成一个系统,完成“情节美学”的作用。[7]
《姜子牙》情节错综复杂,简单概括可理解为,讲述了一个心怀天下的英雄拒绝封神诱惑,为了绝对公平的理想而勇敢反抗师尊权威并取得成功的故事。片中情节与作为设定背景的《封神演义》几乎没有密切联系,原故事中的封神大战在片头就华丽地打完了。《姜子牙》在封神演义背景和人物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大量新创作。由于相关前因后果交待不够清晰,《姜子牙》的情节也遭人诟病。比如师尊为什么一定要将狐族与人类用宿命锁锁起来?不锁的话会影响他统一三界吗?难道仅仅是为了考验姜子牙?统一三界一定会导致苍生受苦吗?师尊上面的师祖为什么闭目塞听没有主动监管他?更奇怪的是,后面的情节证明师尊明明自己就可以杀九尾,却一定要逼迫姜子牙。尽管的确暴露出一些问题,但并不妨碍这种情节设置的层叠往复具有非常浓厚的中国意趣——类似中式园林的層层铺垫、曲径通幽。更不用说故事发展中所涉及的归墟、幽都山、四不相等,无一不是从名字到造型都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趣。
此外,关于“救一人还是救苍生”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一个假命题——并非不杀小九而导致天下生灵涂炭,而是为此搁置了对九尾的处决,并耽误了姜子牙自己无涉生死的封神利益而已。由此可见,问题只是用一种看似激烈的形式提出,在中国也早有类似的疑问与思辨,即著名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应该说,比起“电车问题”中以生命作例,“扫一屋”还是“扫天下”的比喻极具东方文化的温和味道。两个问题其实反映的是相对理想主义和绝对理想主义的矛盾。在强调个体人权的西方现代思想里,仅仅“多”与“少”的对比已无法说服人们理所当然地放弃作为“少”的那一部分的权益。《姜子牙》影片中给出的答案是苍生要救,一人也要救,这无疑是对重视个体权益、反抗公权力的现代西方观念的一种改造。
结语
通过对电影《姜子牙》四个不同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在视觉效果还是主题立意方面,其都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国漫代表。在最容易为观众提取的具体内容层面,使用能作為文化符号的历史人物姜子牙以及经典神话封神演义的背景等,构成中国风味的绝对基础,同时在相对潜在发挥作用的层面中,譬如媒介材料、形式构成以及人物造型等,也同样配合渲染着中国文化精神内核。影片中的姜子牙摆脱了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头、印有太极图案的道袍等刻板形象,在造型上做出近乎颠覆性的改变,并非无本之木,随意为之,而是紧扣主题,暗合人物与剧情需要。总而言之,影片中多个层面互相配合,形成富有张力的综合效果。《姜子牙》不是3D动画电影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成功结合的孤例,影片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其对中国精神内核的把握与创造可谓中国动画电影的精彩案例。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蕴涵深层中国味道的优秀国漫,吸收中国传统造型之美,彰显真正的文化自信,而不是仅套用中国题材的外壳讲述西方味道的故事。
【作者简介】 冯晓威,女,河北徐水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油画创作与理论研究、视觉艺术研究、电影艺术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楚小庆.艺术史研究中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视角及其阐释[ J ].江西社会科学,2011(4):187-192.
[2]段炼.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艺术史研究的新视角[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3]胡易容.多模态符号认知维度下的图像谱系考察——对米切尔图像谱系的一种拓展[ J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30(6):3-12.
[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4.
[5]张先云.从“中国学派”到“中国风”——综观国产动画片七十年的发展历程[ J ].艺术广角,2019(05):15-25.
[6][7]李晓愚.文化、媒介与风格:论潘诺夫斯基的风格研究方法[ J ].江海学刊,2020(06):6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