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称:从交锋到融合
甘鹏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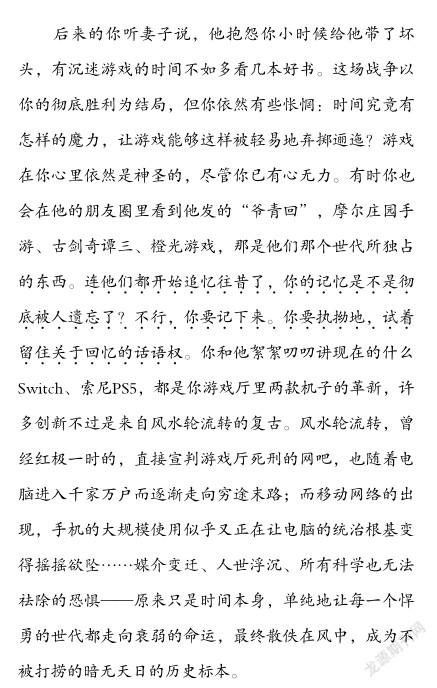
加重的部分可能是我家庭史写作的隐含主题所最外显的一次——即以游戏作为载体,承载我与父亲旷日持久的有关话语权的争夺。从小时候的亲密无间,到青春期时他对我的试图操纵,再到现如今作为新媒介时代的原住民的我,拥有书写权以反制他。我们之间话语权力的此消彼长,背后始终内隐的是媒介与社会的飞速变迁。

包括家庭史的整体写作过程中,我与他之间的话语权争夺也从未消弭。我始终记得当我对他说周日要采访他有关20世纪90年代开的小城游戏厅的往事的时候,他所试图发出的自己的声音——他在采访的前一天晚上,给我发来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足足有近4000字,起的标题叫《时代变迁与家庭生活》,里面包括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他和我母亲的恋爱史,从物资局下岗到自己创办游戏厅,游戏厅衰落以后他再进入事业单位编制的全过程,唯独很少讲游戏厅本身的那段时光——而这才是我更想看到的东西,从日常的游戏厅空间中,看到他如何迎客,如何人际交往,又如何在客人结束以后自己玩游戏机——在慷慨激昂的历史罅隙里,看到他作为普通的“人”被留存下来。

写的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瓶颈,我不知道怎样去平衡我与父亲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我总认为过于顺从他的原意,最终的结果就是:时代风卷云涌,但是没有他;但我也始终怀疑,我的思路就能够让他显现出来吗?我笔下的父亲究竟是鲜活的他,还是基于当下,对20世纪缺乏历史体认的我,脑海里所想象的他?我第一次意识到写作有如此大的权力,能够轻而易举地想象、歪曲以及重塑被书写者,但越是这样我越谨慎,我始终不希望父亲成为我文字下的提线木偶。我始终无法像其他的朋友一样用第三人称,尽可能地客观叙述,我始终怀疑自己的客观的限度。最终受骆以军《降生十二星座》的影响,我下定决心用无论是非虚构/家庭史中都很难出现的第二人称作为文体,我希望我最终的呈现,能让大家直观看出,哪些是父亲本人,哪些是我眼里的父亲,既然客观始终无法抵达,那么我就让自己也进入文本。我所认为的家庭史,不仅是一次客观的历史复现,还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跨时空对话。
只是仍会觉得行文中自己的“ego”過于巨大,容易流作一种过分感伤的混沌,想必父亲没有这样的别扭。还好有很好很好的朋友看过作品后劝慰我:“因为是父子,反而允许无限膨胀的声音浑然天成。”那一瞬间确有豁然开朗之感,才意识到我一直都把父亲当作争锋的两端,却忘记了我是他的延续,我们在不同时空里的声音当然可以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就像《看见》里说的那样:“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