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衡·重塑·掌控
徐智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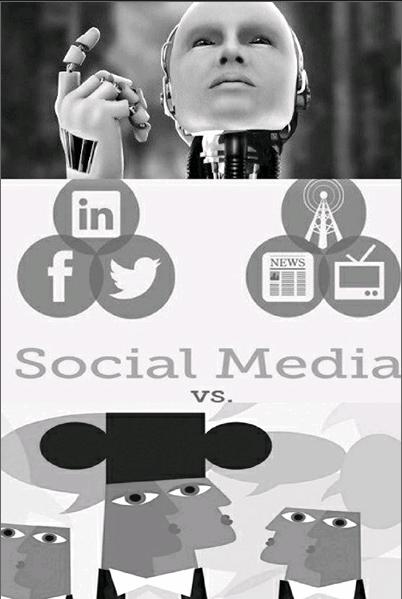
勿庸讳言,以数字化引领着的新媒体,不仅为媒体带来了光速的无界传播,同时,也为话语权关系带来了一次伟大的变革,信息以光媒作为织体的无极自由交互颠覆了传统的公共话语权架构,致使传统的公共话语权的权威性、官方性、唯一性等均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从而形成了广播电视、新媒体、民间舆论等三分天下的媒介大势,小而言之对于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而言均是一场权力重塑;大而言之首先是一场广播电视的巨大的危机,同时,亦可以将其看视作是一次广播电视泛化为新媒体的转机,而从励志的视角则可以将新媒体与广播电视的争衡当做一次发展的契机。
一、 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公共话语权争衡
(一)新媒体对广播电视的公共话语权挑战
传统的、显性的由广播电视所主导的公共话语权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即出现了重大的转变,20世纪末叶开始萌芽并出现的新媒体,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助推之下,有意识地增加了丰富的互动特质,这种互动性使得无法交流的最初的纯粹技术性的互联网,在互动性的支撑下变得人性化起来,这种互动性同时也极大地以其反馈作用刺激了互联网的更加蓬勃的光速发展。一方面,广播电视等传统主流媒介主导地位的被消解,以及主导效应的隐性消解,直接地造成了福柯理论视阈下的广播电视新媒体中话语权断裂;而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无约束下的强势崛起更向传统的广播电视提出了公共话语权的巨大挑战,从21世纪的最初十年而言,新媒体显然后发先至式地全面占据了公共话语权这一关乎国家同时也给国家舆论安全带来了迫在眉睫的挑战。
(二)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公共话语权争衡
广播电视的公共话语权的断裂与消解,为新媒体的强势崛起带来了最佳的可乘之机,新媒体对广播电视的公共话语权的挑战,同时也为广播电视的公共话语权的交互式建构与主导式重塑带来了最佳的发展契机。[1]仅从新媒体视角而言,新媒体如果能够被善加利用,则其将成为一种顺向式的强力和谐工具;而新媒体如果不能够被善加利用,则其必将成为一种公共话语权逆向式风潮爆发的强效助燃剂。由此可见,新媒体与广播电视二者实际上是未稳性与稳性的社会舆论与媒介关系,随着公共话语权表达的民间表达意愿的越来越强烈,新媒本的未稳性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虽然从社会表象上暂时仍然看不到任何广播电视与新媒体之间的显性竞争,但事实上,广播电视与新媒体之间早已展开了一场关乎公共话语权主导、公共舆论高地占领、公共服务互动争夺等全方位的竞争。
(三)广播电视对新媒体的公共话语权平衡
从公共话语权的逻辑关系而言,公共话语权有时甚至会在错误式误导与煽动式鼓动之下,出现一种逆逻辑性生长,同时,新媒体管理的复杂性、无序性、无力性,更是给这种逆逻辑性生长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由此可见,新媒体主导下的公共话语权极易造成不可控式的全面失衡,这种失衡往往会使得公共话语权的非正义性占领舆论高地,而正义性的一方则极有可能被这种泛滥式的非正义性绑架,进而形成一种公共话语权的强势对弱势一方的霸凌,这也是公共话语权失衡的一种必然性畸形。[2]同时,这也是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公共话语权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公共话语权平衡的关键恰在于公共话语权体系的全方位、立体式、互动式构建,客观而言,广播电视的公共话语权虽然近年来已经显失其权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强有序性、弱主导性、可继承性等特质仍然存在因势利导的可能性。
二、 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公共话语权重塑
(一)公共空间的构建关键
越是强势的公共话语权就越是需要据有公共空间,因此研究公共话语权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公共空间问题。与新媒体有所不同的是,广播电视在公共空间方面拥有着继承于其先天的强大优势,同时,仍然拥有着公共空间暂时的官方性、政治性、权威性,显然,这些强大的优势为进一步构建基于新媒体的互动式、多元化、即时性公共空间,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优势,而新媒体在公共空间方面的互动性上则拥有绝对性的强势,并且更易透过强势这种互动强势打造强势语境,从而获得公共空间下的公共话语权。[3]如果不试图尽早针对传统广播电视媒体进行新媒体,乃至全媒体深度融合的重塑,那么,广播电视媒体成为“昨日黄花”只是迟早的事情。新媒体虽然在公共空间的先天性、基础性、权威性、政治性、官方性等诸多方面处于暂时的绝对弱势地位,但是,应该看到,呈几何级数增长着的公共空间的争夺过程中,互动性显然是核心构建的关键。
(二)公共话语权的拓展关键
公共空间的构建为公共话语权的进占,提供了基底式的依托积淀与容纳式的发展空间,从广播电视视角而言,公共话语权的拓展在新时期新常态下具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种拓展不仅能够帮助广播电视内容的数字化无极传播,而且更能够帮助广播电视实现未来公共话语权弱势地位的逆转,同时,公共话语权的拓展也能够实现广播电视与新媒体之间的公共话语权的重新平衡。从具体的广播电视公共话语权的拓展操作来看,最切实际的行动莫过于率先进行内容的更广泛的数字化传播,即与更多的新媒体达成合作与共识,在这些新媒体的助力下实现广播电视内容传播效应的最大化影响,从而实现广播电视公共话语权的初步拓展;此外,广播电视在既有的内容公共空间中必须尽快实现互动式拓展,即全面升级用户端设备,实现用户在公共空间互动性的进一步完善。
(三)公共话语权的重塑关键
无论是广播电视内容传播的拓展,还是广播电视既有公共空间互动性的实现,都为公共话语权的重塑提供了奠基式的拓展关键,接下来,广播电视就可以透过自建站点与合作站点的连点成面,实现全面的基于内容的交互性,并在内容优势下以内容讨论等形式强化基于内容的话语政策性、话语指向性、话语交互性,引导公民自觉意识觉醒下的全民传播语阈的形成,由此可见,传播语阈将成为广播电视话语权重塑成败的关键。而对比新媒体的传播语阈,我们看到,从目前状态而言其仍然处于一种散漫式、自发式、无序式状态之下,这显然给了广播电视重塑公共话语权一个极佳的时机,一时新媒体的时代性、规训性、有序性在有组织的情况下率先建立起来,则广播电视的公共话语权重塑将更加艰难,新媒体的组织失范与管理失范既是其无级互动的优势,同时,也是其无组织与无序化的劣势。
三、 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公共话语权掌控
(一)国内公共话语权掌控
国内公共话语权的掌控主要分为国内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掌控以及国内互联网空间中的话语权掌权。国内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掌控在20世纪50-60年代达到其巅峰状态,政治逻辑的诠释至此发挥到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极致状态,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单向式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掌控特例。21世纪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掌控则只能通过双向式的公共服务与单向式的公共宣介等共同完成。互联网空间是新兴的一种由光媒与数字共同虚拟起来的,非永久性的,较之公共空间相对更具暂存性的,一种可溯源式数字化记录空间,与传统公共空间的弱交互性不同的是,互联网空间具有极强的交互性,并且绝大多数互联网空间均由新媒体一手掌控,但新媒体目前的话语权状态事实上仍然处于一种群体无意识,即无组织的一种散漫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较弱的关联性。
(二)国际公共话语权掌控
从广义而言,公共话语权掌控还包括针对国际公共话语权的掌控。从现代国际关系观察,国际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公共话语权下的政治权力表达,我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由于过去传统意识下的开放性不足而形成了一种先天性的国际话语权失语状态。加之我国的国际广播电视的窄幅式单向传播,与国际新媒体的泛化式无极传播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性,同时,中国广播电视对外传播亦存在着较大的局域性,这种差异性与局域性,更使得中国在国际公共话语权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也是中国这一大国形象屡次在国际遭到抹黑却又无力对等抗辨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4]不仅广播电视这一获得国际公共话语权的渠道过于弱势,而且,从新媒体方面而言,中国的新媒体亦远远无法与国际新媒体抗衡。从近年来国际公共话语权的掌控趋向来看,国际话语权的歧视与偏见止于开放、沟通、交流,国际话语权体系的建构与掌控亦必须透过开放、沟通、交流完成。
(三)公共话语权掌控途径与过程
国内公共话语权的掌控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与三个过程加以实现,这两种途径之一即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话语权掌控,另一种途径即新媒体空间中的公共话语权掌控。而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两种途径都亟待强化。三个过程即国内公共话语权掌控的短期、中期、长期过程。短期过程即争衡过程,中期过程即重塑过程,长期过程即全面掌控过程。而国际公共话语权的掌控则重在国际传播视阈的无极展开,与国际公共空间的全民参与,这两个要件缺一不可。国际公共空间的全民参与,必须通过国际公共政策的开放性方能得以实现,从囚徒法则可知,越是封闭的国际公共政策越容易造成国内舆论、内部争执、内部分化等的加剧,反而是开放的国际公共政策下的全民参与更易消解国内舆论问题,从而使得全民一致对外,进而快速形成与西方发达国家平分秋色的国际公共话语权的掌控。
结语
媒体格局巨变必然造成了公共话语权这一权力格局的改变,新媒体以其强交互性、亲民性、无极性、平等性而成为21世纪虚拟公共空间之中公共话语权的一种主导力量,新媒体也借由这一优势而向广播电视提出了挑战,广播电视的传统优势公共话语权主导地位岌岌可危,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公共话语权争衡与平衡将取决于公共空间的交互性构建,同时,这也是决定公共话语权拓展与重塑的关键。公共话语公不仅包括国内公共话语权,也包括国际公共话语权,公共话语权的实质其实就是国家级公共政策,以及国家级价值取向下的一种必然的政治逻辑现象,公共话语权的掌控不仅能够消解国内舆论、内部争执、内部分化,而且还能够快速提升中国的公共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