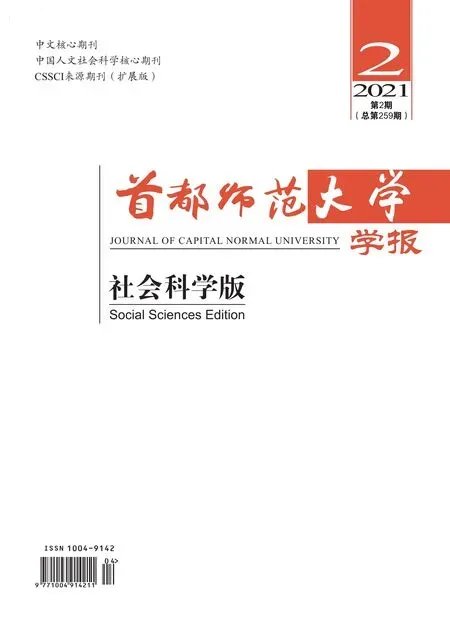“士”的再造:战时中国的思想潜流
袁一丹
一、士的余荫
关于“士”的历史问题及其现代命运的讨论,并非始于抗战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士”的再造就已成为知识阶层关注的核心话题。北大出身的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中便以士大夫身份的发生、变迁为线索,组织起他对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①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中间最有现实针对性的环节是如何处理士大夫身份与知识阶级的关系。陶希圣承认士大夫是知识阶级的特定形态,却不愿以这一称谓指代现今的知识分子,他从生活方式上将士大夫身份定义为“观念生活者”。这一“观念生活”阶级上面连缀于统治阶级的军阀,下面抑制着被统治阶级的庶民。②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第10页。在陶希圣看来,“观念生活者”虽不是基本的社会阶级,仍不失为一个社会阶层,有门第的超越、知识的优异,是一个难得看透现实而易于追随幻影的阶级。
知识阶级与士大夫身份藕断丝连的原因,陶希圣以为在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供过于求,不能被学院体制吸纳的“多余人”,或走上革命加恋爱的道路,或流入官场猎取政治地位。要么革命化,要么官僚化,是过剩的边缘知识分子最主要的谋生之道。士大夫曾经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只因其为士大夫之故,便自然获得政治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在朝为官吏,在野为缙绅。时至今日知识阶级还保持着士大夫身份的传统意识,士大夫时代虽已过去,介于专家与通才之间的知识人仍希望维持其在社会上的领袖地位。①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第13—14页。
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换,社会学意义上的更迭比心态的转变要彻底得多。读书人的主体虽已是知识阶级,上一代的“遗士”“遗儒”不免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所覆盖,但知识分子既填补了士的位置,也继承了士的社会责任,故在意识层面处处可见出士的余荫。士与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似乎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绝。
借用当时流行的两个概念“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②1933年孙志曾编《新主义辞典》(上海大光华书局)对“自然生长性”(Spontaneity)的解释是:“劳动者因感受现实生活的不满,自发地起来反抗资本家,要求改善生活。他们由最初的漫然的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由自然生长的运动发展为目的意识的运动。”关于这两个概念引入中国革命实践后引发的论争,参见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月刊第2期,1928年9月15日。,陶希圣指出知识阶级的唯一出路,在于“克复观念生活阶级的自然生长性,尤其是克复士大夫身份遗留下来的传统意识,认清历史运动整个过程的本质与倾向”,将他们对历史过程的整体把握与理论认识,灌输到革命民众中去,这才是看透社会现实的知识阶级在大革命时代的历史使命。③陶希圣:《士大夫身份与知识阶级》,《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附录一,1928年12月作于上海。由此即知,士大夫身份的意识残留,在陶希圣这里,是作为趋于革命的知识阶级的负面遗产而需要清除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士大夫”这个过时的概念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被重新启动,用来唤起知识分子的社会承担意识。清末留学日本专攻政法,民初转入明清史研究的北大教授孟森,用他早年习得的法学术语重新阐释传统的君臣关系,试图将士大夫从臣的位置解放出来。④孟森:《论士大夫》,《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
孟森以为“君治”的本义是以君为机关之法人,并不担负全责,机构中的自然人即士大夫才是真正的责任人。近世发明的政体,无论立宪还是民主,无不是对君主制的补救,因为君主以自然人充当机构之法人,难免露出其本来面目,破坏法人制的精神。“士大夫”这个名词,在孟森那里,“非前古士与大夫分职尊卑之官品之名,亦非近世士与大夫分占朝野之阶级之名”,而“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殛所可加者也”。
孟森借用“法人”与“自然人”的概念对“士大夫”一词的再解读,缘于与胡适的一席话。胡适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在他看来,士大夫问题“为当今一大事”,不过他放弃“士大夫”的称谓,而用“领袖人物”这种毫无历史感的名词代替。⑤适之(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他以为孟森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叹息近代中国居领袖地位者,既抛弃了古代“士大夫”的风范,又不知道外国“士大夫”的流风余韵,不足以表率人群。二人于是生出“集中国外国士大夫之事迹而互译之,使人知士大夫之共有真谛”的想法,孟森发愿作一部“士大夫集传”,并希望有人搜集外国的模范人物作为教育材料。
有意思的是,为何要用“集传”的形式呈现士大夫的风貌,作为知识阶级的仪范。这涉及士阶层崇信的史传的塑形作用。尽管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标准,宣称中国的纪传尤其是人物传的传统太过贫乏,仅靠枯窘的碑版文字或二十四史的列传,缺乏可信度及可读性。但从他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仍不能否认史传或经典中关于人物片言只语的描写,如朱子《小学》里记载的汲黯、陶渊明之流,在少年成长过程中发生的深刻效力。
与孟森对“集传”的乐观态度不同,胡适意识到传记文学的贫乏,并不能解释近代中国领袖人才的稀缺且不高明。他所期待的现代意义的领袖人物,绝不是靠几册“士大夫集传”就能陶铸成功的。胡适对士大夫的史的追溯,不是从春秋或孔门之士讲起,而是从《颜氏家训》中读出他倾慕的“士大夫风操”,以此作为士大夫阶级律己律人的生活典范及教育手册。胡适将士大夫的理想型放在南北朝时代,并不是追悼这一阶级的崩坏,更不是希冀那种门阀训练的复活。在他看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作为范型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逃不出所受的教育训练,史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被化解到教化的范围内。胡适掌控着包括北大文科在内的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几股教育资源,他理想中的领袖人物,即现代意义上的士大夫,“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被他寄托到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这条狭路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渐趋紧张的态势下,胡适、孟森这一群讲学复议政的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受到“盲人骑瞎马”的危机,不得不乞灵于潜伏于意识深处的士大夫传统,并希冀以史传的形式复活这一传统。
二、士的拟态
不妨从日本文化人的视角来看抗战时期沦陷区北平的士大夫相。1936至1938年间留学中国的奥野信太郎,正好目睹了北京“笼城”前后世局的推移。他通过与周作人、钱稻孙等人的交往,对中国智识阶层做出如下判断: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于国民党执政,这二十年间中国的智识阶层从根底上发生着持续的动摇。当看到他们的彷徨,极容易生出这样的错觉——其所表现出来的姿态,似乎处处失掉了传统的依凭。但如平心静气地观察过去与现状,便知道纵使智识阶层的形象有所改变,他们依然是“中国人”。代替了十三经和八股文的繁劳,挟着西洋书,精通日本文的他们,那种澎湃于全体的动力,还是梦一般经世济民的志向。从文学革命的视野出发,奥野信太郎觉察到,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初,胡适提出八不主义,看似从语言文字的层面根除了所谓的旧思想,但新文学很难将政治置之度外。五四一代佯装抛弃的旧思想,毋宁视为“支那智识人”真实存在的传统及其承续。①奧野信太郎:「支那の智識人」,『隨笔北京』,東京第一書房1940年版,第80—81页。
奥野信太郎感兴趣的不是“士”或“智识人”的称谓,而是中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将官吏视为知识阶级的代表,或者说“士”与“大夫”之间的连锁关系。借用何炳棣从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的视角对帝制时代晋升之阶的描述,个人向上攀升,虽然可以有其他途径,经由科举制,从士到大夫的身份转换恐怕是最稳妥的进路。②Ping-ti Ho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换言之,“士”与“大夫”几乎等同的内在逻辑关系,是这一称谓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1905年废科举制,导致道统与治统的分离,也就意味着作为二者载体的士与大夫的拆伙。社会学意义上的士渐趋边缘,甚至被学校出身的知识阶层完全取替,然而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以及物质形态的残存仍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长期作为帝都的北京。
滞留燕京这两年,奥野信太郎有意寻访士大夫的黄粱一梦彻底幻灭后残存的物质躯壳。士阶层昔日的荣光,在他看来,已如同孔庙中松柏苍郁间林立的碑碣一般硬直风化了。仿佛老大帝国的死面,纵然带有不尽的哀感,也只能封存于石块中,化为碑面上密密麻麻排列的,对时人而言毫无意义的士子的名字。士的“历史遗形物”,不仅是沦为大杂院的会馆,贩卖煤球的状元宅第,对士大夫而言最有象征意味的衣冠,他们礼服上的刺绣,也被当作旅行者的纪念品,装饰到各种小物件上。纤细之至而极尽华美的色彩、构图,让人回想起将此作为服饰之一角的士君子,他们的风貌、举止以至于笔下金玉般的诗文意趣。由这些碎片,奥野信太郎试图拼贴出他理想中的士的光辉形象。①奧野信太郎:「支那の智識人」,『隨笔北京』,東京第一書房1940年版,第74页。
拆碎后的衣冠化为异国情调的点缀,在奥野信太郎那里充满怀旧的光晕,而经历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中国知识人对衣冠——无论是实体还是作为隐喻——的态度则更为通达,乃至决绝。即便沦陷时期貌似摆出士大夫的姿态,周作人谈起胜朝衣冠也丝毫不带怀旧之情。他以为“前清的一套衣冠,自小衫袴以至袍褂大帽,有许多原是可用的材料,只是不能再那样的穿戴,而且还穿到汗污油腻”②周作人:《〈药堂杂文〉序》,《药堂杂文》,作于1943年12月30日,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文学革命时虽然有人吵嚷着要将这衣冠撕碎了扔到茅厕里完事,但也不曾这么做,只是脱光了衣服,赤条条地先在浴堂洗个澡,再挑拣小衣、衬衫等洗过了重新穿上。
这里所谓的“衣冠”或洗澡,当然是比喻义,是指五四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暗中袭用的传统资源。民国成立后的服制变革,亦是如此,朝服的舍利狲成为冬大衣,蓝色实地纱何尝不是合适的常礼服,孔雀补服做成椅靠,圆珊瑚顶拿来镶在手杖上,问题只是不要再把补服缀在胸前,珊瑚顶装在头上,用在别处是无所不可的。周作人看重的不是错位的衣冠,或用作装饰的旧物,而是掩盖在大衫小衫以至袍子底下洗过澡的身体,即文章承载的思想。
熟悉中国古典,对五四话语亦不陌生的奥野信太郎,从士君子的形象中看出文学与政治难以切割的关系。在他眼里,周作人这样的文学者同时也是士君子,虽有文人的洁癖同时也难以抑制干政的热望。奥野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史论、政论与文论的界限是极端暧昧的,史家、政治家与文士的身份也往往叠合在一起。譬如在文集固定的编纂序列内,某某论、某某表,或送某人赴某地序,必定要触及当时的政治话题,吐露从政者的心声。文集的固定模式,尤其是其内部的文体排序,已展示出从政论、史论到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的小品文字这一渐变、混融的光谱。③奧野信太郎:「支那の智識人」,『隨笔北京』,東京第一書房1940年版,第76页。奥野信太郎担心滞留在沦陷区的中国知识人,这些有意无意地承续着士大夫传统、大体认同于士的社会角色及伦理承担的知识人,能否理解或愿意去理解事变后日本的“文化工作”④奧野信太郎:「支那の智識人」,『隨笔北京』,東京第一書房1940年版,第81—82页。。
奥野信太郎对中国知识人的观察,尽管只是一个笼统的印象,却触及士大夫不同于近代职业政客,以文人兼官僚的双重角色。士大夫政治确实是中国独有的政治文化模式,其关键在于士与吏,或者说儒生与文吏(又称“文法吏”“刀笔吏”)的分化。⑤关于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以及学士与文吏的分合,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如《论衡》“程材”篇所言:“文吏以事盛,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规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儒生务忠良,其所学者,道也;文吏趋理事,其所学者,事也。儒生治本,文吏治末,道本与事末相比,可定尊卑高下。所以从儒家的观点看,志于道的士大夫政治无疑优于志于事的文吏政治。改朝换代之际,需要担负道义使命的仅限于士大夫阶层,对专于理事的文吏集团冲击不大。
1940年作为《华文大阪每日》的大陆视察特派员,柳龙光回到沦陷下的故土北平——这个事变后人口忽然增加到一百七八十万的“华北首府”,拜访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在外交大楼里,刚刚东游归来的王揖唐脱掉一路在日本穿着的西装礼服,换成长袍马褂来迎客,出场时笑容可掬,连连躬着身子,用皖省腔调的国语说着客套话,随即坐在红缎子团龙花的小椅子上谈起东游见闻。柳龙光对这位飘着长髯的蹩脚诗人兼老牌政客的素描,让人觉察不出是在沦陷的北平,这副作派完全可以挪用到帝制时代的士大夫身上。不但是首脑王揖唐,就在这外交大楼的走廊上,鸦默雀静地走着同样穿着长袍马褂的书记们,捧着一大摞用小毛锥一笔一画描成的公文,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等因奉此”之类的套话,他们安详的神情姿态,以至于襟前垂挂着锁链的衙门的徽章,在柳龙光看来,“都好像并没有受过这次天翻地覆的大事变的什么影响”⑥柳龙光:《大陆视察报告(一)和平与中国》,《华文大阪每日》第6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第21—22页。。这便是传统意义上不受改朝换代影响的文吏阶层。在访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在地的半小时里,柳氏观察到的北京,不是事变后堕入歇斯底里的变相繁荣的大都会,而是长期浸泡在官僚传统中的帝京的残影。
三、士的蜕变
“士”的历史问题,在士阶层几乎销声匿迹的20世纪40年代,再度回到知识分子的视野。身处西南的林同济在《大公报》“战国”副刊上提出士的改造问题,旨在形成一批中坚分子作为抗战建国的基本动力。他通过“士”的词源学分析,试图从来路里求得将来的取径。①林同济:《士的蜕变——文化再造中的核心问题》,原载1941年12月24日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第4期,收入《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时,改题为《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偏于统相的摄绎,林同济用“由大夫士到士大夫”八个字笼括三千年的中国社会政治史。与烂熟的士大夫传统相对,他生造出“大夫士”这个名词,并强调两者乃代表两种根本互异的历史背景所产生的“人格型”。②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原载1942年3月25日《大公报·战国副刊》第17期,收入《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
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林同济认为西周以至春秋大部分是以大夫士为中心,秦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士大夫政治,而春秋末世与战国可说是转捩时代。中国政治从“大夫士”到“士大夫”的类型转变,不仅是结构上的大变动,更是社会动力的转换。林同济构造出“大夫士”与“士大夫”的更替,意不在历史过程的描述,而是以历史追溯的方式抛出现代中国文化再造这个指向未来的基本命题。
以西洋史为参照系,林同济将“大夫士”翻译为Noble-Knight,即贵族武士,“士大夫”则被译作Scribe-Official,即文人官僚。大夫士社会的特征是纵向的“世承”与横向的“有别”。这种社会生成的“人格型”,以义即荣誉意识为内核,包含忠、敬、勇、死四大原则,以此来贯彻世业的抱负、守职的恒心。经过战国的剧变以至于秦汉,中国的社会政治由封建的层级结构演变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刚性的“大夫士”逐渐官僚化、文人化,流变成二千年来牢不可破的士大夫传统。士大夫奉行的“世训”,由“义”流产为“面子”,“礼”敷衍为“应酬”,“忠、敬、勇、死”巧变为“孝、爱、智、生”这四德凑成的一种“柔道的人格型”。林同济将抗战类比为战国时代,在这列国阶段的高峰所急需的是刚性而非柔懦的人格型,是大夫士的风尚而非士大夫的做派。他期待的并非大夫士制度的复活,而设想在僵化的官僚体制内重新注入一种大夫士的精神。③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原载1942年3月25日《大公报·战国副刊》第17期,收入《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
士的蜕变,被林同济视为文化再造的核心问题,关键时期是从春秋到战国。其形塑的“大夫士”,即士阶层的理想型,以春秋之士为化身。在他眼里,春秋之士普遍具有技术的感觉,秦汉以后的士大夫则带有宦术气。“技术者,做事之术也;宦术者,做官之术也”,由春秋之士到当今之士,便是由技术到宦术,由做事到做官。林同济将春秋之士界定为技术阶层,一种“专门做事”或“做专门事”的社会阶层,其援引《说文》中“士,事也”的说法,证明在古代“士”与“事”本是不可分离的概念。如果要为士的发展史断代制名,不妨将春秋时代称作技术本位的时代。
进入孔子的世代,士的整个社会经济及行为标准发生激变,“士”在以孝悌为本、忠恕为方的儒家学说里,已大部分脱离了技术的含义,变成道德本位的代名词。林同济认为孔门在士的历史上的作用,在于趁着技术时代的末运,开创了“道的时期”。由孔门转入战国,“致道”的士摇身一变为“游说”之士,“士”字逐渐失却道德的含义,而抹上诡辩的色调,即“说术”或“言的时期”。秦汉以后,浪人式的游说不得不适应大一统的皇权政治,被规范为贤良式的贡举制,官僚体系渐趋稳固,士的“宦术化”正式揭幕。六朝文词相竞的风气,开启了士的“文人化”。文作为一种钦定的宦术,士的“文人化”,可以说是与“宦术化”凑合的一段支流。①林同济:《士的蜕变——文化再造中的核心问题》,原载1941年12月24日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第4期,收入《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时,改题为《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
由技术到宦术,林同济大致勾勒出“士”的蜕变过程,他以为了解这一过程,即可了解当今之士的症结所在:宦术化、文人化太深,乃至完全失去了技术的感觉。他观察到少数在朝的专家学者,想要在一向做假拟态的窝窟里培植出一种“技术傲气”或“职业道德感”,这或是中国政治上的一线光明。如果说士的蜕变,过去的历程是由技术到宦术,林同济指出此后士的新生,必须折返数千年的旧道,由宦术复归于技术。这一判断基于他对官僚传统及中国政治的文人性的反思。他所谓的官僚传统,不仅指一般官吏任免黜陟的法规与分权列职的结构,而且是指运用整个结构的精神、表现的作风,以及无形中推崇的价值、追求的目的。换言之,林同济对官僚传统的理解,不只是一种狭义的行政制度,而是当作活的社会态势、运动的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分析它在整个国史演化上的作用与反作用。林同济主张去除历史上官僚体制中包含的皇权、文人、宗法、钱神这四种毒素,彻底转变内向型的官僚传统,以应付四面洪流的战国局面。②林同济:《官僚传统——皇权之花》,《大公报》1943年1月17日,收入《时代之波》(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与《文化形态史观》。
林同济尤为关注官僚传统所中的“文人毒”,在他看来,文人作为士的主体,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所谓的men of letters。因为中国人看重的“知识”,只是文章;自诩为“知识阶级”者也不容与intellectual混为一谈,所谓“贤人政治”不过是文人垄断的政治。③林同济:《论文人》(上),《大公报·战国副刊》第27期,1942年6月3日。所以文人乃是二千年大一统皇权积威下锻炼而成的一种特产。“文人性”作为中国政治的底色,稍微夸张地说,可放大成一种“文字迷”的宇宙观。地道的中国文人,对一切事物,只能从文字中念到,甚至透过文字才能看见,已丧失了直接念及现实,看到现实的本能。④林同济:《论文人》(下),《大公报·战国副刊》第28期,1942年6月10日。以写景诗为例,号称即景之诗,却用不着即景描写。如到什刹海赏雪,妙诀端在闭目追忆古人的好辞句,而非睁眼呆望眼前的真景致。什刹海也罢,小卧房也罢,反正赏玩的不是堆庭之雪,乃是书中之雪。即景诗的内容,自有它超越时空的不变性,与一时一地的“幻象”何干?这即是释家所要破除的“文字障”。
林同济对文人的剖析,采取的方法是让“文”字本身说话。文人兼官僚的士大夫拜认文字即是行动,用英国历史学家唐纳(R.H.Tawney)的说法,西洋人办事,言论只是实行的起点;中国人办事,言论乃是一切的终点。⑤林同济:《论文人》(下),《大公报·战国副刊》第28期,1942年6月10日。无论帝制还是共和体制内的文官皆以议论为成功,亦以议论招失败。面对强势的武力,文士的策略是将文与德相结合,把德认作护身符,认作一种超越实力而存在的力量,而实力本身反成为无力的。这种“德化第一主义”,以德为最上之力,认力为取败之道,其实是弱者的自嘲,是无力者的催眠术。林同济焦虑的是,这种有意、无意的“德的迷信”,如何与当下“力的世界”“力的文明”相抗衡而生存下去?⑥林同济:《论文人》(上),《大公报·战国副刊》第27期,1942年6月3日。这确实是国运攸关的问题,也是晚清以降知识人共通的焦虑。把士定位在技术阶层,以技术对抗宦术、德术、文章术,是林同济为病入膏肓的士大夫传统开出的解药。同样关注士的现代命运,抗战时期还有另一种相反的声音,强调士作为“道德的人”的社会使命。
四、士的使命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主持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张东荪在沦陷时期作的一篇长文,论“士的使命与理学”⑦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作于1939年8月12日,《观察》第1卷第30号,1946年11月23日,第3—8页。。该文缘起于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迁至汉口,其与张君劢商议再办书院的计划。日后张东荪潜归北平,以为燕京大学如能存在,不如在沦陷区多照顾几个未能入内地的青年为宜。①张东荪:《士的使命与理学》附记。张君劢的书院在大理成立,来信邀约其兄张尔田、邓之诚等人南下任教,选择留在沦陷北平的张东荪为书院作了这篇文字,由书院教育引出宋明理学与孔孟之教的关系,兼论士的定义及其使命。
对应于林同济对士的历史阶段划分,张东荪凸显的是孔门塑造的“道义之士”,他援引冯友兰的说法,称孔子为士阶层的创立者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冯友兰在1933年自序中称,《哲学史》第二篇校稿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试图将“士”从“士大夫”这个固定词组中剥离出来。张氏看重的士,与各种专业技能,或林济同强调的“技术的感觉”无关,这种非农、非工、非商,尤其是非官僚之士,只是在社会上主持正义,靠“清议”来左右一个社会的是非判断。孔子讲学,讲的不是某种技能,而旨在造成一种“道德的人”。张东荪对士的定义,一言以蔽之,即“道德的人”,或“非官僚”这一点。用林同济反文人性的立场衡量,尽管在反“宦术化”上达成某种共识,张、冯二人都是他所忧虑的“德的迷信”者。
张东荪对士的定义,主要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去理解。在他看来,士阶层的兴起乃出于对抗威权的需要。作为自下而上的对抗力,士阶层的存在相当于威权政治自身分泌出的一种防毒素或防腐剂。孔子以前,士只是做官的预备者,此后被赋予一种特别的使命,即为密不透风的大一统皇权保留一个透气口。士对威权的反抗,不止于在野者的反抗,而是充当永远的反对派。不拘其反抗的方法如何,以复古为反抗亦不失为一种反抗。所以严格地说,孔子不是士阶层的创立者,但士的道义使命、政治使命却是孔门所创。
张东荪亲历并以政论家的身份参与过晚清至五四的社会运动,其深知任何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必须与道德合而为一。反过来说,表面上是道德革命,而内在诉求却是政治问题。张东荪所谓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只在于透气、防腐、减毒,而不可认为是革命。所以士阶层的存在,在他看来,一方面是政治上永久的通风洞,从另一方面说,却又是维持秩序的。士或知识分子不免干政,只是干政而已矣,并不要求执政,且在势亦永不能执政。在他眼里,社会运动背后的力量是心理的,也是道德的,由此可知其所谓的道德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即当事人觉得怎样才是对的,而对与不对的判断又受制于人与人之相与。社会的维持与改变,无不依靠道德力量的支持,没有一个社会理想其本身不是某种道德观念敷衍出的远景,同时没有一次社会变革不是从道德观念的动摇开始,纵使道德的抽象原则不变,其具体的应用与范围必大有变化,非如此不足以发动社会运动。
且不论佛教的影响,张东荪承认宋明理学确系继承孔孟之教,其着眼点在于欲提高道德必须以形而上学的神秘为背景,缺少形而上学的背景不能解决道德的保障问题。这牵涉到士与民的双重道德,以习俗、法令为表达方式的道德只能拘束常人,对于担负道义使命的士则不够,必须将凡人的道德视为非道德,而制定出与实际的利害祸福并不一致的,更严苛的道德标准。于是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好人?如果好人不得好报。这时必须把神秘经验抬出来,使个人觉得小我与大我是一体的,人生意义与道德保障完全寄托于此。所以理学内部无论有何派系之别,大体上脱不了神秘的整体主义(mystic integralism)。张东荪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主张整体乃是专为道德立一个最后的托子,使个人有安顿处。③近代民族主义的奥秘亦在于此,以国家为单位的民族史,其实就是为挣脱出宗法网络的孤零零的小我另造一个大我。这种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是为了满足士阶层超世俗的道德需要,虽只是添上去的布景,但这个添加却十分必要。
由士的道义使命,生出小我与大我打通的人生哲学,再生出万有一体的宇宙论或形而上学,张东荪这种逻辑推演无疑是一种逆溯,却祓除佛教的影响,将理学与孔孟之教勾连起来。张氏以为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不在于思想内容,而在于方法。孔孟之教本来含有神秘主义,却没有发明出修行之法以亲证这种境界确实存在。理学是把佛家出世的办法用于入世,把宗教性的神秘移用于起居日用上,让一切德目如忠孝节义都有了安托。治国、平天下才是儒家真正的目的,至于修身、诚意,乃至上溯到形而上学的领悟,都不过是直接或间接的手段而已。
张东荪最后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归功于士阶层的政治道德作用,他一边宣布士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一边又要保留士在知识、道德上相对于大众的优越性。他所理解的大众,不是把士剔除在外,而是士与大众打成一片。至于如何才能打成一片,在打成一片的同时又怎样维持士的领袖地位,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士在新时代的使命,决不能如产业革命者所主张的那样,化身为欧美式的中产阶级,张东荪以为士的出路,唯有融入大众,除了提供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依然是其在道义上的承担。
梁启超曾将“文化”一词定义为“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所谓“共业”是借用佛家的术语,他以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泡茶这道工序打比方:用一个老宜兴茶壶泡茶,多冲泡一回,壶的内容便生一次变化。吃完茶,倒掉叶梗,淘洗干净,表面上什么渣滓都没留下,然而这泡茶的精华实已“渍”在壶内,等下次再泡时,此前渍下的茶精会令汤的色味更佳。茶之随泡随倒随洗,便是身心活动的起灭,而渍入壶壁的茶精便是业。一个人的活动留下的魂影,遗传给他的子孙后辈,仅可谓之“别业”,还有一部分像细雾般霏洒到他所属的阶级、社会而永不磨灭,是之谓“共业”。①梁启超:《什么是文化》,1922年11月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演,《晨报副镌》1922年12月1日。
士大夫传统便是知识人的历史共业。身处大后方的林同济与留在沦陷区的张东荪对“士”的再造有不同看法:究竟是清除“文人性”的毒素,培植出一个纯粹的技术阶层,还是维持士在社会中特殊的道德功能?两人对士的理想型的不同设想,为呈现战时中国知识阶层面临的政治伦理困境,铺陈了一个同时代的思想史背景。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