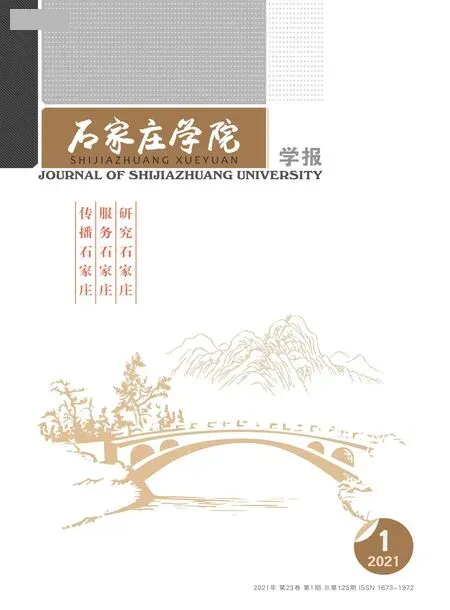“城乡配”心影印痕与身份索解
——以《我的父亲母亲》为例
许心宏,程 军
(1.安徽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历史上数以千万计的“知青”来说,“知青”一直是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纪实作品、知青回忆录的追忆与追叙对象,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知青文学”与“后知青文学”;同时,“知青”也构形于80年代以来的影视镜像叙事中。思想主题上,无论是表现知青岁月的苦难,抑或是高扬“青春无悔”的理想抱负,基于历史后视角,都成了青春过往的怀旧叙事。21世纪以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知青题材电视剧的“城乡通婚”(或称“城乡配”)适时性成为其重点叙事内容,诸如《麦子进城》《满仓进城》《我的父亲母亲》《盛开吧百合》等。源于“城乡配”的出身差异,“差异性”因为“标明了两个世界间的边界”,使得“差异性也被写进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因而“两个世界具有了双重指涉”[1]66。以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津)剧审字(2012)第001号,下文简称《我》)为例,“城乡配”的“合—分—合”叙事,内中承载着城乡二元的身份区隔与生存地位问题的思考。“城乡配”创伤叙事,既是原型叙事的影像重构,亦是身份索解的反历史证明。
一、“城乡配”叙事的身份解码
《我》以“城乡配”为主线,讲述的是先赋性身份“城乡配”的“问题婚姻”故事。根植于故事的“讲述时间”,“城乡配”叙事分为“接受—相处—分离”三个阶段。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身份阻隔,镜像建构了“城乡非婚”叙事的逻辑起点与创伤记忆。
首先,婚配契机与人物原型。剧情伊始,下放“哨寨”的城籍知青相继返城之际,陈志因为父亲“政治问题不清白”而无法返城。下放期间,村长女儿翠花爱慕陈志有加。如此,预设了陈志“有条件返城”,提升了剧情张力。后经村长“推荐”,陈志实现了大学梦。返城前,村长为女儿与陈志举行了婚礼仪式。对于翠花,陈志可接受,亦可拒绝,但拒绝则有违“苟富贵,勿相忘”的世俗常理,而接受则成了没有其他选择的选择。实际上,囿于特定历史时期,两者的结合是伦理本位与政治规训下的婚姻达成。婚后,陈志并未告知父母自己的婚事,表明陈志对待“涉农”婚姻的漠视心态。剧情的一个细节,就是翠花为返城读书的陈志做了绣花鞋垫,寄托的无疑是翠花的深情爱意,但陈志上学时却未随身携带,而是悄悄地藏于家中。显然,隐藏的是鞋垫,冷藏的则是婚姻,预示的是陈志的逃离心态。根植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河床,就古典戏曲“才子落难,佳人相助”原型而言,陈志的“下放”属于“才子落难”的当代翻版。当然,陈志的“落难”缩小了他与翠花的身份差距。作为“佳人”,指的是翠花作为村长女儿的角色存在。“哨寨”作为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村长有着至尊的话语权。如此,翠花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村长的女儿。返城后,陈志之于翠花的“私人空间”,预示着“城乡配”婚姻的解体,而情节的诡秘,在于陈志的“温柔以待”回避了“陈世美”角色的反讽。
其次,围城世界的身份冲突。基于陈志与翠花“城乡配”,翠花对城市的向往,则是对自我身份的放逐与对城里人身份的认同。因而,当记者以“模范夫妻”相访之际,陈志的躲闪与翠花的接受形成了心态差异。从躲闪到接受,陈志的心态转变源于“政治正确”话语征召,也是臣服特定历史情境的行为表现。究其因,则是在“翠花—秀箩—陈志”三角纠葛中,错位的婚姻与理想的爱情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就陈志的心灵“越轨”而言,他对秀萝的守望,使得翠花成了徒有婚姻外衣的“局外人”。溯其因由,则是在大学校园,适逢秀萝的爱情表白时,陈志自言“不配”。而“不配”是假,已婚才是真。“不配”源于对涉农婚姻的隐瞒与不满,也是自怨自艾的心理体现。当然,若是翠花在门第、身份、学历上可与秀萝比肩,则陈志的失落与怨恨心理也不会产生。显然,涉农婚姻表征的是两者的出身、门第、学历的不对等。如此,对翠花“农村人”身份的歧视,建构的是身份化的心理隔离机制。
再次,婚配“合—分”叙事。影视的“对白”功能之一是“表达一个可识别的角色”[2]45。《我》的结尾,翠花提出了离婚意愿后,陈志则说“我怎么有点爱上你了呢?翠花!”翠花回答:“我一开始就爱上你了,你现在才爱上我,这不公平。”极简对白,实为“城乡非婚”点睛之笔,身份与心态错位因之昭然若揭。翠花的“不公平”意在夺回“乡下人”的话语主动权。相反,就陈志“有点爱上”而言,一是表明20年婚姻的无爱,二是表明陈志的施舍心理,三是给予翠花的不过是聊胜于无的虚假慰安。所以,翠花的返身撤离,使其成了“城乡非婚”的宽恕者。离婚前,翠花对儿子说:“妈恨也恨过了,怨也怨过了,可是你妈对你爸的这份爱从来就没消失过。你妈这一辈子爱的就你爸一个人。要是,要是现在—就—就分手了,那你—那你妈不是白爱了?”(《我》第37 集)。显然,翠花的疼痛、不舍与纠结,源于对一己身份的不自知。通过其子的发现者视角,大志亲历与见证了父母婚姻的勉为其难。如此,对已是成年人的大志来说,他劝导父母离婚的理由,就是父母不必因为伦理的束缚而空置各自余生的幸福。离婚后,翠花与唐大哥复合;陈志与秀萝20年的“爱情遥望”得以梦圆。基于历史后视角,“下放”期间的陈志接纳翠花源于感恩,是恩情回馈的既定选择;而对大学同窗秀萝的爱情,则是自由选择的无从选择。其实,离婚前,陈志的“私人空间”设防的是翠花,守望的则是秀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陈志与翠花“城乡配”的曲终人散,折射的是“人因地贱/人因地贵”的“出身原罪”的制度性与心态性的社会现实。
二、城乡情感:空间角色化叙事
婚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映射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现实与心理遵从。在空间角色化“城乡配”叙事中,剧中主要人物承载着空间化、符号化与身份化的情感结构分析价值。
首先,空间角色化心理根植。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人进城有“招工当工人、参军当兵、上大学”三条路径[3]273。不同的是,翠花是“婚姻进城”。依附性的婚姻关系,缺失的是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体现在夫妻关系上,陈志的晋升引发了翠花“被遗弃”的防范心理,而翠花母女的跟踪监视更是激起了陈志的反感心理。翠花的“抓牢”心态,实为“人不自贱,贱却自生”生存与身份的真实写照。如此,在男权主义话语中,陈志的男权主义则由翠花所建构,即臣服于制度性建构的男权话语体系之中。同样,秀萝之于马庆升的“放手”心态,则源于制度性习得的身份优越感。陈志与秀萝的性别虽异,但身份相同。源于先赋性身份前置,规训的是城乡二元身份的“主/仆、尊/卑、上/下、贵/贱”心理根植。
其次,三角纠葛角色隐喻。基于“翠花—陈志—秀萝”的三角关系,翠花以泼辣甚至刁蛮的“傻、憨、粗”自我矮化姿态,冲破阻力为“政治不清白”的公公“平反”,翠花之刚与秀萝之柔的性格差异源于社会出身不同。当然,翠花的行动果敢,期待的是城里人的身份认同。源于身份差异,翠花与陈志经历婚姻的试错之后,翠花与同村的唐大哥再续前缘,而唐大哥正是当年翠花的退婚对象。剧情结尾,翠花的“生离”与马庆升的“死别”,秀萝与陈志各自从“所婚非爱”中解脱,继而各自重续前缘。在叙事反讽上,“大多数讽刺通过单一代码向读者传递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十分明确的关于讽刺目标的信息”[4]88。意即,在“城乡配”离散聚合中,表征“城乡配”身份不兼容问题。再就“陈志—秀萝—马庆升”三角关系而言,秀萝倾慕陈志,而马庆升苦追秀萝,婚配的竞争暗含着先赋性身份竞争。其中,马庆升扮演的是挑拨者、中伤者的人物角色。他挑拨陈志与秀萝的关系,诸如状告陈志“未婚同居”、陈志与秀萝“不清白”关系等,目的是猎获秀萝的爱情。如此“跪着爱”的卑微,凸显的是其农村出身的自卑心理在场;而自卑的自负,则表现为对秀萝的占有与征服。但是,马庆升的占有原则终究败给了身份原则。在马庆升眼中,秀萝是爱、美、自由的化身。相反,秀萝眼中的马庆升却是其厌弃的对象。究其因,它是在王书记的“文革”问题上,马庆升出于自保而违心地写了检举材料。在人名隐喻中,马庆升之“庆升”隐喻其“向上爬”的欲望、野心及其畸形人格。在仕途与婚姻之间,“获得权力”成为其汲汲以求的对象,而秀萝不过是马庆升仕途攀援的媒介对象。但是,马庆升“患癌”离世,“病”成为身份残缺的象征,“离世”意味着“城乡配”的永远缺席,隐喻同类婚优于异类婚的身份主题。
再次,身份化情感结构。随着翠花的离去与马庆升的离世,陈志与其说给秀萝送去了自己亲手制作的“望远镜”,毋宁说是20年的爱情“遥望”终究变成了婚姻现实。从“远望”到“相聚”,基于陈志视角的归罪心态,走出涉农婚姻的囚牢意味着重获自由。在“奔赴”秀萝的画面特写中,陈志的心态急切与动作迅疾,如担心“错过了车”与“赶不上时间”等,寓意20年来的情感压抑得以释放。不过,两者的“会面”采用了视听语言的“大写意”。意即,两者怎么见面、见面后说了什么、如何重拾旧爱等,镜像采用的是快进的叙事镜头。急促的结尾,暗示两者的结合是无需证明的必然。剧中“相见恨晚”场景的省略,则是陈志与秀萝内心窃喜的画面的删除。基于先赋性身份追问,翠花、马庆升出身农村。婚配的身份之别,印证的是“鱼找鱼,虾找虾”婚配现实的逻辑,翠花与唐大哥的再续前缘便是证明。如此结尾设置,或许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但实际传播效果又是另一个问题。“城乡配”离散之后的婚姻重组,难掩“城乡非婚”之实。“结构即是人物,人物即是结构”[5]99,经过“合—分—合”婚姻重组,反证的是身份区隔的婚姻匹配机制。当然,在伦理禁忌回避中,编导的障眼法,便是采用忧伤、哀婉又带有抒情色彩的音乐化叙事。如此,旨在缓冲城乡有别的生存地位与文化身份的冲突。在身份异类的“城乡配”中,陈志之于翠花则为形式化的“陪伴”关系,而“陪伴”源于感恩的伦理诉求。同样,秀萝之于马庆升亦为“陪伴”关系,而“陪伴”源于马庆升为其父“平反”付出辛劳的感恩。源于伦理向度的“陪伴”,无论陈志之于翠花,抑或秀萝之于马庆升,剥离伦理话语的爱情,“城乡配”仅存的不过是婚姻的外壳。
相异于陈志与秀萝的聚合,马庆升之于小田则是离散,前者为同类身份的理想婚姻,后者为同类身份的错配姻缘;就后者而言,“离散”则是各自身份承认的仪式,而权力话语在于马庆升一边,即马庆升舍弃小田的原因在于她的农村出身。其实,马庆升若非“因病离世”,那么他与小田的婚配未尝不是俗世婚姻的理想选择,剧情17 集有这样一段对白:
小田:“庆升,你一定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工作,为了农转非,对吧?没错,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可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了。我是真的喜欢上你。”
马庆升:“我也一样。”
小田:“不!不一样!我知道你的老婆是高干子弟。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她照顾过你、关心过你!我敢说,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庆升,你是个县长,可你也是个男人。你身边也需要一个女人呀。你要是把我支走,谁来做你的女人?”
马庆升:“小田,你别离开我,我也离不开你。”
在俗与欲充斥下,小田“色诱式”攀附马庆升,意在实现“农转非”的身份转变,但未能遂愿。马庆升身患癌症后,小田对其照料有加,先前的“色诱”转为“怜悯式”的婚姻渴望。然而,秀萝但凡对其略施“伦理式”的爱意,马庆升便将小田抛之脑后。进退于两者之间,在秀萝的“弃”与小田的“爱”的二元情感结构中,马庆升的心态微妙,颇具世相的反讽意味。在反讽叙事上,“反讽鼓励观众深入探寻人物生活中起作用的动机和因果力量”[5]379。换言之,马庆升的心态二重奏,内寓城乡二元心理症候的身份在场,即马庆升的婚配对象绝非同类出身的小田。如此,“同类相弃”表征身份区隔的心态在场。
三、身份创伤与败退的和解
“结构主义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如说是提出问题的方法。”[6]116经由《我》的“城乡配”叙事,则将制度性的社会问题置于历史解剖台上,解析的是“出身原罪”生存地位与文化身份差异。“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7]72基于影视镜像的历史构想,30年前有选择的“城乡配”镜像重构,昭彰了婚姻向度上的生存与身份创伤,反讽的是“出身原罪”制度性限定的身份不平等。
首先,城市视角的审丑叙事。基于城乡二元时间交错与空间并置,镜像中的农村一贯被格式化。城市视角的根深蒂固,使得无论是乡土批判还是乡土抒情书写,归根结底,不过是城市视角构想下的模式化叙事。于此,一是翠花原生家庭的官本位思想、宗族思想、报恩思想等成了“被看”与“被说”对象。实际上,剧情设置的陋习并非农村人独有,却成为城市视角预设的“应有”叙事,农村人因之缺失自我表述话语权。当然,对农村人的偏见、成见叙事并非该剧的独创。相反,它根植于五四以来启蒙话语的历史深处。如此,传递的是现代与传统的文化碰撞,内中潜隐的是“城乡非婚”的社会心理在场。二是在仕途发展上,陈志从公社副乡长、党委书记、副县长到市农委主任等,矢志一辈子做个教师的陈志虽有“厌官情结”却一路晋升,而马庆生迷恋仕途却又无从晋升。如此官场叙事,人物出身论“原型”叙事至高无上,因之生成“崇城鄙乡”的人物角色的审丑叙事。
其次,温婉的婚姻败退。剧情结尾,翠花劝慰陈志说“咱们是因为爱而离婚”。为此,两人举办了离婚仪式。矫情的剧情设置,看似祝福爱情,而实为制度性的身份归类,于翠花而言,则是败退式的自我身份认同。其间,无论是离婚还是举行离婚仪式,这些均由翠花主动提出,而陈志只是“等待”翠花提出。如此,则可洗脱“忘恩”与“忘情”之骂名。换言之,“城乡配”一厢情愿源于翠花,而“城乡不配”的困局亦由翠花主动解围。如此,陈志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形象得以构建。在归罪心理上,叙事者推诿婚姻的解体归于特殊时期的历史限定性,且单向度强化了陈志的“无辜”与“受难”意识。基于创伤叙事,“创伤记忆首先是基于个体的创伤性体验或经历的个体记忆”[8]92。但是,就创伤的互为主体性而言,权力话语倾斜于陈志的“无辜”叙事,即“知青下放”期间遭遇了一场无爱的婚姻。在镜像话语暗射中,陈志对翠花的谦卑与忍让,策略性地回避了“陈世美”角色的嫌疑。实际上,就陈志“厌官情结”而言,即便是仕途发展顺利,但无爱的婚姻则是其难以逃离的人生暗伤。于此,便不难理解陈志“私人空间”的心理幽秘,即陈志理想的婚姻失败便等于人生失败。无辜是相对的,但镜像叙述更倾斜于陈志的无辜,且深植于特定历史情境之中。史料记载,知青分为“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两类。1968-1980年间,大约1700 万城镇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下放知青”因之称为“失落的一代”。[9]1-3作为历史记忆的镜像再现,“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10]5。换言之,翠花“因爱离婚”与马庆升“因病离世”均不过是“城乡非婚”之隐喻。因此,“下乡知青”返城后,就“城乡配”离散后的同类婚配而言,温婉败退的是婚姻现实,凌厉在场的是制度性的身份隔离。
再次,先赋性身份索解。从陈志的“下乡”到翠花的“进城”,空间方位的“下乡”与“进城”权力话语,体现在无意识社会心理上,前者的“下乡”是“客”,后者的“进城”是“仆”。就马庆升进城而言,无论婚姻还是仕途,与其说是奋斗不如说是挣扎,而挣扎源于“出身原罪”身份焦虑。基于此,就其自私、狡黠、阴暗、猥琐的人物角色而言,构形的偏向使其成为“于连式”的异类人物。基于《我》的现实主义叙事,镜像话语潜隐对农村人先赋性身份的打压。根植于中国农耕文化传统,城市为“国”,农村为“鄙”,“国”与“鄙”表明空间区隔对应的文化身份的高低之别。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而在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则删除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条款,由此形成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里人与农村人各有先赋性身份,继而有了“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之别。于此,陈志与秀萝一度的“知青下乡”则自视为“受难”与“受苦”。不止于此,编导与观众在未经反思的话语认同中持此心理。极具反讽意味的就是“在知青所写的回忆和反思文章中,过去的一切,方方面面,都被缅怀、回味、咀嚼,不论是受苦还是受惠,所有的人都尽力表达各方面的酸甜苦辣。但令人吃惊的是,广大农民明明也是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一方,这场声势浩大的迁移运动无疑也涉及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但从来没有文章从农民的角度作评论和检讨”[11]。再者,就进城后的马庆升与翠花而言,马庆升成了“野心家”,翠花成了“献祭式”人物。对前者的“丑化”与后者的“神话”看似褒贬对立,但本质则为“崇城鄙乡”同一社会心态的内在暗合。因为,后者“献祭式”人物构形,满足的不过是城市视角“应有”的人物假想、道德征召与心理慰安。从“城乡配”到“城乡不配”,基于二元户籍制度的身份索解,镜像话语深埋城市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
四、结语
根据《我》的故事讲述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中,随着户籍制度的松绑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翠花与小田各自创业成功。她们打破了“二等公民”身份的束缚,逐脱了“婚姻进城”的人生依附关系。如此,婚姻向度的身份论叙事,既是对城里人先赋性身份优越感的消解,亦是对“城乡非婚”社会心影的历史性反讽。所以,就《我》的“城乡配”败退式创伤叙事而言,“书写创伤就是书写事后影响,它意味着要复活创伤‘经验’,探寻创伤机制”[12]186。21世纪以来,农村个体工商户、知识青年、农民工、打工妹进城业已不是问题,各地也相继出台了落户城市的相关政策,虽然“经济接纳,身份排斥”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城市社会各个角落,但终不过是思维偏见的心态遗存。21世纪以来城乡一体化发展,先赋性身份鸿沟不再不可逾越,应有的则是能力论、知识论对各自身份论的客观认知与文化心态调适,此为该部电视剧关于先赋性身份“尊/卑”“贵/贱”解构主义叙事的历史意义所在。基于历史后视角,“城乡配”的创伤叙事,既有历史记忆的沉重与艰涩,也有几分岁月过往的忧伤。但是,追叙是为了面向未来,建构的是身份区隔与身份和解的对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