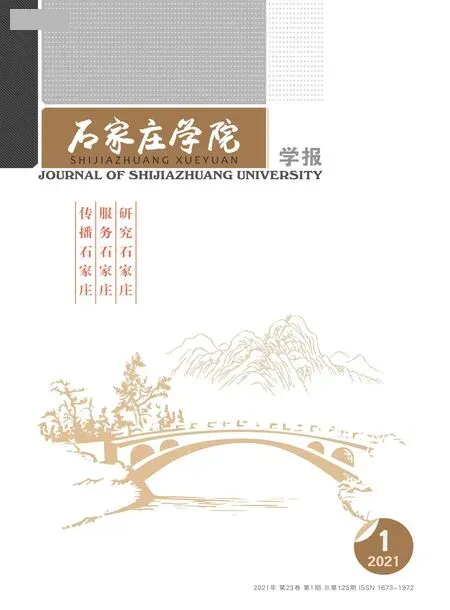《金山》的地理空间与身份焦虑书写
曾小月,郁叶梅,唐 园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作为一个华人作家,张翎热切关注华人在海外的生活状况以及身份问题。这不仅是作家的一个书写焦点,同时也是张翎作为华人一分子对于华人的关怀。对于《金山》这部小说创作的缘起,张翎在序中作了解答。最初的创作灵感萌芽于1986年,在去卡尔加里城外赏秋的路途中偶然发现了埋在野草中的墓碑,张翎从模糊的字迹和残缺的照片中推测出埋葬在此的人是“被近代史教科书称为先侨、猪仔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1]1。创作一部关于金山客的小说的念头在张翎心中燃起了一点火花,却还缺少足够的燃料让它绽放。直到2003年夏天,张翎去到广东开平——著名的侨乡,她又有了新的发现:开平的特色建筑群——碉楼、褪色旧衣、挂了丝的袜子……带着灵魂的追问,张翎通过实地考察、查阅丰富的文献资料,打下了坚实的创作基础,最终完成了《金山》这部40 多万字的作品。她希望:“那些长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独灵魂,已经搭乘着我的笔生出的长风,完成了一趟回乡的旅途——尽管是在一个世纪之后。”[1]6
《金山》是一部宏大的长篇小说,围绕广东开平一个方姓家族的历史故事展开叙述,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将整个故事容纳进来,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以及海外华人移民史。小说故事的发生、发展于广东开平以及加拿大两地,作者对两地的地理空间有相当多的笔墨叙述,这是由于地理空间作为人物存在的背景空间,不仅是人物物理活动的空间,而且通过地域差异构建了人物身份。本文旨在通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照分析《金山》中对于广东开平与加拿大的自然地理与人文风俗的叙述,深入探讨小说人物在两种不同文化地理空间中的身份问题。
一、《金山》的地理空间元素
邹建军教授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中指出,“文学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理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涉及空间的研究,则主要是关注作家在文学中所描写的地理空间与所建构的地理空间问题”[2]。借助“开平”“金山”两个地理空间,探究原乡与异乡的象征意义,可以为我们加深理解《金山》的思想意蕴提供契机。
从自然地理空间视角出发,可以看到《金山》描绘了广东开平和加拿大金山两个地区独具一格的自然地理风貌。
广东开平是方家祖籍所在地,更具体一点是在自勉村,“自勉村村头有一条小河,村尾是一片矮坡,中间是一片低洼之地”[1]13。以耕种为生的村民,依赖雨水、河流的灌溉。风调雨顺之时,农产足以糊口;若遇旱涝之年,则民不聊生。张翎是钟爱“水”的,故乡温州的那条藻溪流淌在她的许多创作里——《邮购新娘》《雁过藻溪》《羊》……在《金山》中,那条河流变身成为自勉村的“无名河”。“水”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直被关注的意象,或是吟咏“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直接展现自然山川之壮美,或是宣扬“上善若水”以言说道义,或是将河流比拟母亲以抒感恩之情……于此处,自勉村的无名河是养育村民的“母亲河”。它柔美、安静地流淌,又始终如一地哺育人类。自勉村的村民用它来灌溉土地、淘衣洗裤,同时,它还是一个乐园——“夏天全村的孩子都在河里游水”[1]189。河流与人类在社会生活的连结基础之上,继而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无名河成为了故乡的代名词。无疑,无名河地理位置的所在即涵括了方家所在地。在加拿大移民局拷问锦山的身份时,把无名河的相关信息也纳入其中。“你家住的村子里有河吗?”“河叫什么名字?”“从河里走上来往你家走,中间要经过谁的家?”[1]189沿着这个追问,锦山回答的路线目标逐渐指向方家碉楼。方家的金山客都沿着这条路线踏出又踏入,无名河成为了方家历史的见证者。
关于金山的自然地理空间,张翎主要聚焦于金山客对于异乡的疏离感,描绘出一幅寒冷、坚硬的冷色调画卷。风,这种无差别的自然现象,在作家笔下似乎也带上了国别差异,给人物不一样的体验感。阿法刚到金山时,便感受到风的不同:“心想这真是到金山了。家那边的风不是这样的。家那边的风是圆软的一团,擦着碰着了,都留不下痕迹。金山的风长着边长着角,刮着了,不小心就蹭掉一层皮。”[1]36从本质上来说,这里所描写的风的意象,既有对异国的“冷”的陌生感,又包含着对故乡的“暖”的依恋。张翎在描写两地自然地理风貌时作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性描绘。开平自勉村的夜晚极具平淡美的意味——夜风轻拂,蛙在池塘呱呱,宿鸟惊飞于眼前,云淡天蓝,星星如炬。而金山的四月天:“树上的雪还没来得及化完,又结成了冰棱,枝桠在风中舞动,发出沉重的撞击声。”[1]54这种冰冷色调既是对表层自然环境的描绘,同时也表现了华工在外的生存困境——既有修建铁路时自然环境的恶劣,又包含异国人对华人态度的冷漠。
而文化地理空间,由于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其存在不仅与人的创造紧密联系,并且在历史的雕刻下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文学中创造的地理空间并不一定能如实反映现实,因为文学不是社会纪实,文学注重把社会现实融入文化系统,进行新意义的解读创造。
开平方家的碉楼是方得法从金山寄钱回来给盖上的,取名“得贤居”,“得”取自方得法,“贤”来源于关淑贤,这样的取名在1913年的广东也是非常前卫的。这座碉楼在当时独树一帜,其设计目的,一是为了防贼,二是为了防水淤积。碉楼一共有五层,“顶楼的阳台用来搁置枪支武器,下面的五层都是住宅。天井设在中间,围着天井四个方向都有房间,是一模一样的布局:两个过道,两间卧室,一间储藏室”[1]77。整齐对称的布局象征一种严肃的传统秩序。碉楼里的住屋分配也是依照一定准则分配:最底下一层是用人所住,第二层是麦氏和六指所居,佛像和祖宗灵位也就近摆放在这层,其他三层各自住着方家族人。男性在家庭中的缺席,使得女性占据了家庭(碉楼)文化地理空间,但隐形的男权主义仍旧笼罩着碉楼。麦氏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在方元昌去世之后,成为了方家的权威,掌管家庭的大小事务。这种掌权直到麦氏死后,自然而然地移交给了六指。女性这种“主人”身份限制在碉楼这个文化圈中,一旦离开碉楼,其身份将无法建构。因此,碉楼在居所本义之上,更是女性身份构建的空间。
金山的文化地理空间以唐人街为代表,唐人街是华人聚居区,是原乡人在异乡的家园。唐人街所在的地势和自勉村意外地相似,都是处在低洼地。似乎唐人街成了金山的“自勉村”。在淘金热的浪潮下,一波又一波的华人奔赴海外。然而,外国的生存环境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生活居所简陋,“泥路的两旁密密麻麻地盖了屋,都是薄板钉的,大多是平房,也偶有两层的,不管是高的还是矮的,看上去都像工棚,墙上的木板和木板之间裂着大大小小的缝”[1]42。稍微拿得出手的房子都不是给活人住的,菲士街的平房是用来祭拜的谭公庙,士多街的扁楼房是存放金山客骨灰的“停尸房”。祭拜鬼神是中国传统祭祀礼仪之一,通过举行一系列的祭拜仪式、庆祝活动,表达对神的虔诚信仰,寄托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谭公庙从广东移植到加拿大唐人街,表现出金山客对传统信仰的坚持,同时也成为维系华人身份的一个途径。“停尸房”只不过是死去的华人的寄居点,他们最终的归宿还是那个养育他的原乡。
与原乡的连结基因流淌在华人的血液里,永远无法割裂,落叶归根成为金山客最大的期望。“自我与他者”的身份需要对照才能够进行定义、区别,原乡与异乡同样需要互相作为参照,以确定自己的特性。张翎利用“唐人街”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作为观察口,从街道上房子的外形到“居住者”,展现金山客的生存环境;而与异乡格格不入的祭祀传统、鬼神信仰,既区别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也加强了对自我身份的肯定。
二、《金山》的地理空间与身份焦虑
空间是个体存在之基本,空间与个体身份紧密相连。在对个体进行文本叙事时,时间与空间同时展开。“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3]274-275《金山》这部小说便是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中展开叙述,而这种叙事手法顺理成章地将空间与个体身份问题连结。地理空间给个体提供了基本立足点,即确定了个体基本身份之源;反之,个体对空间的塑造赋予空间更复杂的文化意义。
《金山》的空间呈现出来的既有身份认同的焦虑,也有身份重构的焦虑。认同问题是一种主体自我意识问题,认同感的产生是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4]188。认同焦虑的出现,是主体意识面临缺失或已然缺失的结果。伴随认同焦虑而生的是重构身份的焦虑,主体急需为自己寻求一种新的身份,或改变原有的身份形象,以重新获得认同感。
留在开平的女性,不管是麦氏还是六指,都面临着女性身份认同的焦虑。“‘碉楼’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文化空间都被方家女性所充斥,形成了独立存在的‘女儿国’,但这是一个处于东方传统文化下的女性世界。”[5]65碉楼是开平最独特的建筑,其封闭性的建筑风格,是一个家庭传统的体现,也是控制女性的象征物。以麦氏、六指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一生都被困在碉楼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她们的身份一个是被困者,另一个是传统的掌权人。一旦脱离碉楼,她们便被灌入新的身份信息;而空间的定型,使她们难以摆脱现有身份。在进入碉楼之前,六指是一个独立的女性,身上充满着斗争精神,用自己的生命努力与命运抗争,成功嫁给方得法。在进入碉楼之后,其女性身份的独立性被削弱了。她虽拥有了部分掌控家庭事务的权力,却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六指最初期待逃离碉楼,等待方得法给她买一张船票,共同去金山生活。后来,在麦氏的压力逼迫下,她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走上了和传统“留守”妇女同样的道路,即管理家庭事务、养育儿女、等待丈夫归来。媳妇、妻子、母亲——这三个社会给予的身份——将她牢牢地关在碉楼里,她的金山梦被抛弃在碉楼外。六指无法走出碉楼,象征着她无法打破传统的伦理规范和秩序,因此,其女性身份的个体性就无法实现。
“相对于‘碉楼’静止与留守的状态,‘金山’则处于文化主体流动的状态,而‘金山’的文化场域与闯入者之间存在着文化隔阂,即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5]62金山客在淘金浪潮下背井离乡,从开平小村去往加拿大金山,继而又参与修建铁路工程,他们被形容为“猪仔”,因肮脏的外表遭人厌恶,干的却是最辛苦、危险的工作。他们处在原乡的外围、异乡圈的边缘——“不但美国式的‘光荣与梦想’永远不可能属于他们,即便是在母语世界里,他们也基本上与历史无关。”[6]
方家几代移民都经历了这种他者注视下的焦虑。锦河在家里是小少爷,到了金山却做了亨德森先生家的用人。其原因还是因为华人在金山没有立稳足跟,体面的工作根本轮不到华人群体,他们只能做些低级的工作。锦河一次路过学堂时,被学校里的孩子们嘲笑,他闪躲着,却被他们追着闹,给17岁的锦河留下了阴影。锦河虽心里明白自己不受欢迎,但还心怀一丝侥幸,然而学校里的孩子们并没有放过他。这反映了即使华人在金山这个地理空间中沉默、忍耐,种族歧视并不就此消褪。
在方家第三代方延龄及其女儿身上,体现更多的是渴望重构身份的焦虑。方延龄出生、成长于金山,对于华裔身份的焦虑在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试图重构身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与白人男子交往,二是试图让女儿成为白人社会的上等人。在和庄尼寻找住处时,遭遇到许多拒绝。“这个世界没有一方空间,会留给一对没有婚约的男女,和一个中国人的。”[1]375这个土地连生存空间都不提供给中国人,华裔该何去何从?方延龄的离家出走,投奔白人男子的怀抱,象征着对自己华裔身份的厌弃,渴望获取白人身份,而得到社会的认同感。她也将这种身份焦虑传达给了女儿艾米,教导艾米人前人后都要讲究礼貌,阻止艾米了解家族历史,致力于将艾米打造为一个上等社会的白人。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下,方延龄为摆脱这种身份焦虑,选择放弃原乡身份,以求在异国生存。而艾米恰恰相反,在西方文化熏陶之下生长,却选择了接受中国文化,通过了解方家家族历史,承认自己身体里拥有中国基因,接受了自己的华裔身份。
张翎以“移民个体、家庭日常生活的‘小历史’去楔缝对接社会变迁、时代风潮的‘大历史’”[7],又借助描摹个体在不同地理空间的生活状态去展示个体的身份焦虑问题,这是张翎对个体、对华人命运的关注,也是她对移民如何跨越原乡、异乡两个国度边界的探讨。
三、地理空间与身份焦虑书写之因
根据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的界定,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8]5简单而言,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下拥有的身份,与社会公认的“成功典范”相差甚远,因而就会产生“焦虑感”。我们常常担忧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拥有的社会身份,是否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要言之,从个体而言,身份焦虑产生之源有二:一为自我意识的缺失,二为缺乏来自他者的认同。
首先,空间有意识地建构了主体特性,在此建构过程中,空间让主体产生焦虑感。通常而言,空间容易对主体形成压迫感。从大空间上看,譬如在当下的城市空间,人口暴涨,土地资源不足,人无法获取满意的住宅空间,无法为自己寻求足够的生存空间,因而较易产生焦虑感。在方家的传统观念里,土地是最为重要的保障,所以每当方得法从海外寄回银票,母亲都强调要买地。哪怕六指和锦河被山匪捉去,需要卖地筹钱赎人时,她心疼的竟是卖掉的土地和花去的钱财。在中国传统安土重迁的观念中,占有土地,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反过来说,是因为他们能从土地空间的占有中获得安全感和身份优越感,拥有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这个家更有财富,而财富可以决定一个家的社会地位。
从小空间上看,譬如家宅空间,房子将人“困”在其间,从表面看,是限制了人的活动范围;从深层看,其实是限制人的认知。人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更多的时候来源于与外界的接触过程,而“墙”阻隔了这样的接触。人在同一个空间生活久了,就会融入其间。碉楼禁锢了六指几十年,让她从一个妙龄少女等成了一个白头老媪。等到最后,她将自己的命融入了碉楼。广东开平乡下自勉村,这个看似不大的地理空间,却控制了她一辈子。
在空间的压迫中,阻断了人和外界的联系,甚至是至亲至爱之人的情感联系,只能守在方寸之地内,日复一日地感受生命的流逝,这种焦虑感是可怕的。麦氏是如此,六指亦是如此,那时的中国乡村千千万万妇女都是如此。她们一方面是被父权制大家长制社会禁锢,一方面被足下的三寸土地禁锢。尽管方得法父子都不曾真正留在碉楼,可碉楼代替了他们的角色,囚禁着留在那里的女性。
其次,与自我意识被切断相对应的,是外界认同的缺失。如果说,留在开平乡下的六指是由外而内的认同被禁锢,那么去往金山的方得法父子是由内而外的不被认同。“金山”是华人对温哥华的称呼,广义上可以用来代指整个加拿大。它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是一个被表征的空间,并且蕴涵着丰富的意义。方得法的洗衣房开在唐人街上,起名“竹喧洗衣行”,店外挂着宫灯,店内贴着字画,景观空间狭小,布置的都是他理想中的样子,符合他寻求故土与展现传统中国特色的心理愿景。然而,这样的装饰与加拿大的文化环境相差甚远,在异质空间文化的包围下,反而显得捉襟见肘。这间小小的洗衣房并不完全属于方得法,在洗衣房遭遇劫难时,他甚至不能出来阻挡。可是,作为“金山伯”,每次他们回乡,都是一场盛大的狂欢,他们带回去的新鲜事物和钱财,令他们得到了同乡人的尊重和羡慕。然而,在异国他乡的加国,他们也只是社会的底层人之一。这种落差感,让他们陷入自我矛盾和怀疑之中,在两个迥异的社会空间中,他们的身份形成了两个极端。
自带的原乡文化与陌生的异乡文化产生冲突,两种文化的夹击使金山客产生身份焦虑。方得法在未去金山之前,幻想金山是一个黄金满地的逍遥世界,结果在下船时却被围观、被扔石头;《维多利亚殖民报》的报道充满了族裔歧视;被误认为偷鸡贼,被绑在街市上羞辱;工作只能“做白番不肯做的烂活,工钱只有白番的一半”[1]129。此时方得法的焦虑是基本生活的困难,而这源于他的原生身份——华人。在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异国对他者的态度难以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他们是入侵者,凭借毫无理由的种族优越感来歧视华人。
作为一个“外来者”,华人在金山并不能得到认同,不管是社会身份还是文化认同。可他们必须要在此环境中生存下去,就要不停地挣钱,争取在财富上不输于白人。阿兰·德波顿认为:“在新的社会秩序下,人的社会地位只与每一代人的自身成就相关,特别是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成就。”[8]44然而,事实可能会与之相悖——白人并不买账,无论你的生意做得多好,他们都会眼红,都会想办法诋毁你、让你破产。华人在异乡抱团生活,其实就是不被认同的结果,白人拒绝他们加入,拒绝他们占用自己的空间和资源。来自种族的歧视,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空间的歧视”,这片国土属于白人,不属于华人,所以《排华法案》出来了。法案的实施,无非就是想将华人以及其他不属于白人的种族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华人对于身份的焦虑感,促使他们发声,为自己赢得认同,赢取生存的空间。
地理空间作为一种概念化的“容器”,标示着人物的身份、文化、价值观等。而人物的活动场域的变动,势必使其身份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可以通过书写得以抒发。地理上的错位产生的身份焦虑感,也可以通过地理的书写得到缓解。张翎把这种焦虑感诉诸于空间,并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地安排了人物行动的时间和空间。空间上的跳跃性加上时间上的延续性,使故事呈现出一种完满的姿态,完成了一次宏大的跨时间和地域的叙事。
四、地理空间与身份焦虑书写的现实意义
张翎在小说中运用了“过去—现在”“原乡—异乡”的叙事模式,形成了时间与空间上的二元对立。地理的书写凸显了空间问题的重要性,两个不同经纬度、不同地形气候的地区,形成了空间上的互相应和。这种“双地理”模式的书写,将人物放在不同地理空间之中,扩展了叙事场域,更凸显了小说叙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张翎的地理空间设置得如此清晰,地理位置定位得如此确切,让人感受到的焦虑感也如此清晰。
从地理空间维度进行身份焦虑的书写,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出国的方式和目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人们有很多条件可以出国。从中国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或加拿大,只需二十几个小时,相比方得法所处时代的在海上漂泊个把月,时间把空间距离给压缩了。方得法那种思乡不得见的焦虑感在当下可能已经淡化了,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空间上产生了新的焦虑。出国、归国方式的便捷,说明是否能攒够船票、是否能被目的国接受等问题已经不是当今出国人最主要的焦虑,他们焦虑的内容,更多的是“怎么出去”“怎么捞到金”到“出去是否安全”“出国我能获得什么”等问题。这就涉及到了当今人们出国与百年前祖辈出国的目的不同。
也即是说,如今的出国,不管是海外移民还是海外留学,都与过去的出洋捞金、躲避战乱不同。过去,人们之所以愿意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是为从别的地理空间中寻求更多财富、获得生存的物质基础。而如今,人们之所以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大多数时候更是为了个人发展。无论是出国旅游还是留学,他们的视野与总在一个空间内的人是有差异的。前面说过,空间会控制人的认知,而只有通过变换位置,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总而言之,如今空间位置的置换,更注重个体生命的体验和发展,而非仅仅停留在物质和为了家族发展上。
然而,在全球化语境下,人类生存面临着更多的问题,除去原有的族裔、性别、文化所产生的身份认同焦虑,多元的文化背景、多重的身份、难以融入的归宿感,因为空间的切割,让人更难以拥有一个连续的、固定的、温馨的、可以融入的空间,认同感也更加不易获得。当下的年轻人,住在高楼平地起的大城市里,挤着地铁公交,穿梭在办公大楼里的格子间。他们承受着来自经济、家庭、工作甚至他人的压力,在社会身份的建构中,精神压力来源于所处的城市、办公区域甚至居住空间。空间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压力网,罩住了当下人,让人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很大程度就来源于身份的焦虑。
对地理空间和其他空间的书写,是可以缓解这些压力和焦虑的。过去的祖辈,能够用双手在大洋彼岸开创出一番事业;而如今的年轻人,一样可以有一番作为——不管是在原乡还是异乡。一百多年前的方家,从开平的乡下远走,其实是环境逼迫他出走,因为如果他一直留在乡下,便不会有后来方家在自勉村的地位。相比方家男人的“被逼出走”,今天的人们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从被动转为主动,这是最大的优势。从人与地理空间的互动上而言,地理空间不再仅是作为提供物质基础、提供生存所需,人为地理空间赋予其更多的内涵。如果没有华人、唐人街文化的加入,北美洲的多元文化氛围定会逊色不少。
由此,人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更加自信。既然掌握了主动权,就积极构建自我形象,因为自我形象的构建可以影响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正面的形象可以为人赢来尊重。由阿兰·德波顿的观点可知,尊重是破解身份焦虑的第一法宝,尊重意味着身份(无论是社会身份,还是文化身份)得到认同:“我们的自尊心是由他人赋予我们的价值所决定的。”[8]107况且,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与世界接轨之面越来越广。作为个体,要摆脱身份的焦虑,就不能封闭在自我空间中、将自己与外界隔阂而自我孤立。哪怕易地而处,只要带着自身的文化自信,就不怕遭遇身份的焦虑。
最后一个问题,转换地理空间是否是解决身份焦虑最好的方式呢?方得法父子出洋谋生,的确为方家在开平的地位提升创造了条件,然而在异乡,他们遭遇了新的身份焦虑。由此可见,转换地理空其实是一种双向选择,有时它并不能缓解焦虑,甚至还可能带来更大的焦虑,但有时,它的确可以。由此也可以看出,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极大的。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个体对全球化空间的感知愈来愈强烈,“身份焦虑”其实早已是一个人类的共性问题了。通过《金山》对地理空间的关注,解读张翎对人物身份问题的描写,人物身份跟随空间位移所产生的焦虑感,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当下。因此,对该小说进行跨地域的观照,同时对新世纪以来的“留学热”“移民热”等问题进行探讨,能为我们解决当下人的精神困境问题提供一些积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