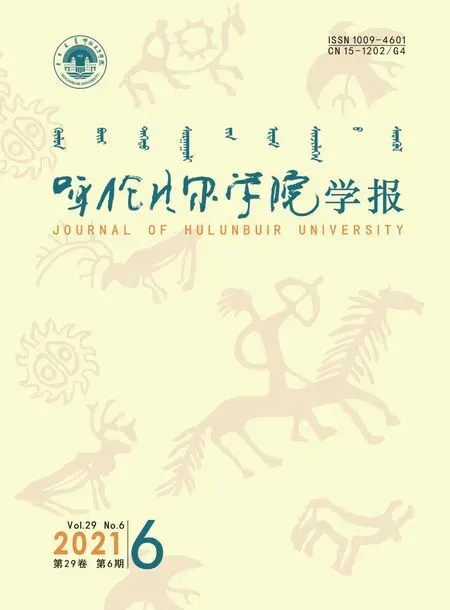论蒙古族狩猎仪式与文化
图 雅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30)
蒙古族先民在狩猎生活的初始阶段没有完备的狩猎工具(通常把木棍削尖刺杀猎物,或用石头击打猎物),因而捕获到的猎物极少,无法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所以在不安、痛苦、恐惧、绝望中,他们将一切归于万物有灵,认为对猎物来说,也有掌管它们的神灵:即山峦、树木、江河等。山野中的一切飞禽走兽都受到山峦、树木、江河之神的主宰。猎民认为只有在神灵的恩赐下才能捕获到猎物,所以在狩猎的整个过程中都会举行狩猎仪式,祭拜神灵祈求神灵保佑,祈祷狩猎顺利、丰收。这就是狩猎仪式即狩猎习俗。狩猎习俗是在长期的狩猎实践中形成的,是先民适应自然,缓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文明行为;是先民遵守自然规律,适应自然的一种体现;也是先民遵循自然法则、努力做到人与动植物平衡发展的一种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是先民长期从事狩猎经济过程中形成的文明作风。
蒙古族人仪式感十足。就连演唱史诗《江格尔》都会有相应的仪式,更何况满足先民衣、食、住、行的狩猎活动。猎民的狩猎仪式贯穿在整个狩猎过程中,即狩猎前、狩猎中和狩猎后。
一、 狩猎前的仪式
蒙古族猎民狩猎前要举行祭祀、唱颂词和器物的净化仪式。
(一)祭祀、唱颂词
猎民出猎前要祭祀长鹿角的画像,祈求长鹿角赐予猎物,使狩猎成功。西部蒙古兀良合部落的猎手在出猎的前一天晚上,请专门的说唱艺人演唱“阿尔泰山颂”。这一仪式是通过对阿尔泰山的赞颂愉悦神灵,祭奠神灵,使其赐福于人民的观念体现。猎人有时会带艺人出猎,在狩猎不顺时请他咏诵赞词。布里亚特猎民在狩猎前也会专门请民间艺人、狩猎经验丰富的猎手或长者来唱颂词,愉悦神灵。
青海地区的蒙古族人出猎前要进行占卜算卦(骨卜、炮绳卜、指卜等),看方位方向,预知收获,从而根据占卜的结果来安排狩猎活动。出行前要举行煨桑念经,煨桑时用香柏、白蒿、青稞炒面揉捏成丸放在火上,念“昂根仓”(天神地灵的祈祝词)[1]。在海西州乌兰县的“昂根仓”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长生不衰的/十三个天神地灵啊!/请赐我/十枝鹿角/肥壮的野牛/……/绸色青天/富裕的“路斯”啊!/请赐我/肥的走不动路/老的吃不了草/大的抬不起头(角)的(动物)……[2]
青海地区的蒙古族人出猎前举行的占卜、煨桑念经、昂根仓等仪式均是万物有灵观念的一种体现。“煨桑时最常用的长青草木——香柏和白蒿,这是一种生命崇拜的方式”[3],认为猎物是被天地之神掌管的,只有祈求天地之神开恩赐福予猎人,才能捕获到猎物。从“昂根仓”中得知猎民并没有贪念,只是简单地祈求天神地灵赐他们“肥的走不动路,老的吃不了草,大的抬不起头的……”这体现了猎民对猎物的大小、老幼、肥瘦并不挑剔,猎民认为捕获到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猎物,只要满足生活所需便可的一种朴素生存观。
猎民认为有专门掌管猎物的猎物之神“马尼罕—腾格里”(苍天),在猎民的意识里,猎神应该是位白发老人,他掌管着所有野生动物。所以,也叫他为“巴颜—马尼罕”或“巴颜—查干—额布根”,即“富有的马尼罕”或“富有的白发老人”。民间还流传着“马尼罕腾格里仓”的狩猎习俗。这一狩猎习俗是先呼唤马尼罕,再祈祷马尼罕赐猎物于人民。
天塑的银身,
千万野兽的主人马尼罕!
天塑的金身,
山狍野鹿的主人马尼罕!
天塑的玉身,
所有野兽的主人马尼罕!
箭囊之血还没来得及拭净,
就赐我一二十头猪物的马尼罕!
弓箭之血还未来得及擦净,
就赐我二三十头野牲的马尼罕![4]
猎民通过吟诵祭词的形式呼唤着马尼罕,并恳请山炮等万千野兽的主人马尼罕赐猎物于猎民。
把那锅里放不下的——
大头野物赐给我吧!
把那门里进不来的——
大角野兽赏给我吧!
把那不能放牧的——
驼鹿赶到我面前吧!
把那不听召唤的——
苍狼让我猎获吧!
把那不好牵拉的——
红狐准我猎捕吧!
我的马尼罕![5]
就这样一边呼唤马尼罕—腾格里,一边祈求把那锅里放不下的、把那门里进不来的、把那不能放牧的、把那不听召唤的、把那不好牵拉的动物赐给猎民。猎民向马尼罕—腾格里祈求猎物时并未表现出自私或贪婪之态,而是说请将给您马尼罕—腾格里带来不便和麻烦的猎物赐给我吧。
无论是演唱颂词祭祀万兽之王,还是念“昂根仓”经都是为了愉悦天地之神,祈求祈祷神灵保佑,赐猎物予猎人,希望狩猎成功,满足猎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朴素愿望的体现。
(二)器物净化
蒙古族先民信仰萨满,萨满巫师在人们心目中像神一样的存在,猎人出猎前试图用一种超自然的法术以及语言的魔力来战胜、消除狩猎中的各种不利因素,以确保狩猎成功。
猎人认为出猎最吉利的时间是清晨拂晓之时。所以在天亮前会举行一系列的出征仪式。
1.甘吉嘎仓
祭祀马鞍梢索,即马鞍上系栓猎物绳索的仪式。这种咏唱仪式叫“甘吉嘎仓”。“甘吉嘎”指马鞍鞍翘前后两侧的皮绳,俗称“梢绳”。用它来栓系猎物,栓系猎物就象征着狩猎成功。猎人希望出猎能够“甘吉嘎都容”,在梢绳上栓满猎物,寄托着满载而归之美好愿景。为此,在祭祀时,边往梢绳上涂抹动物血或油,边吟唱“甘吉嘎仓”。向山神和猎神祈祷:
把那叉角公羊满满地系在正侧,
把那竖耳狐狸满满地系在反侧,
把那白嘴母盘羊满满地系在正侧,
把那弯角公盘羊满满地系在反侧。
让那八条捎绳沾满猎物的鲜血,
让那细条捎绳浸透猎物的油迹;
让我那长袍后摆被猎物撑开,
让我那长袍前襟被猎物鼓胀。[6]
人们通过祈祷,希望狩猎者“甘吉嘎都容”而归,在八条鞍梢绳上都系满公羊、狐狸、母羊等常见猎物,长袍的前襟后摆都被鼓胀和撑开。出猎前的颂词形象地道出了“甘吉嘎都容”应有的模样。
2.阿米拉古鲁呼
狩猎前对狩猎所用的弓箭、猎枪、布鲁、夹子等工具进行修检,在所有猎具上涂抹动物的鲜血和油脂,并念祝词。在猎具上涂抹动物鲜血或油脂叫做“阿米拉古鲁呼”即“激活猎具”。这就是模仿和再现用猎具捕获猎物的情景,具有象征意义。猎人们相信只要将猎枪等猎具“复活”,猎具就会变得更加锋利,狩猎时就会百发百中,能见血、沾油,这对猎人来说是好兆头,预示着狩猎成功。激活的猎具要放在高处,忌狗闻嗅、忌妇女触碰。他们认为狗嗅、妇女触碰猎具会使其丧失魔力,影响狩猎成果。

图1 皮弓囊、箭囊、角弓、羽箭

图2 布鲁

图3 铜刀
“在鄂尔多斯地区,每逢大年初七,猎户都会杀一只野鸡或野兔等小动物,用其血涂抹猎具,用其肉喂养猎狗,称之为‘昂根·莫日·嘎日嘎呼’(为出猎开路之意)”。[7]科尔沁部也在出猎前举行一种以血涂抹猎枪口的狩猎仪式,该部人将此举称之为“阿米拉那”(意为新生)。[8]
猎人一边往猎具上涂抹鲜血、油脂,一边念咒语祝福:
你的杆子像狮身,
你的声音似雷鸣,
你的弹丸如星辰,
你的火花像闪电,
威力无比的火枪!
充满福运的猎枪!
把逃窜的野兽给赶回来,
把遇到的艰险变福分![9]
猎人们不仅相信这种仪式,更加相信在这种仪式中语言的魔力,话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咒语中将猎抢的杆子、声音、弹丸、火花进行一番比喻后,认为这枪不仅威力无比而且充满福运,持有这样猎枪的猎手,什么样的野兽都难逃其手。唱咏祝词就是用一些漂亮的、吉利的话语祈祷狩猎成功。
通过狩猎前的“阿米拉古鲁呼”再现狩猎场景,通过咒语祝福等语言的魔力,祈求神灵保佑,助猎人狩猎成功。“阿米拉古鲁呼”是猎民早期思想意识的体现,产生于先民的幼年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3.火净化
出猎前祭祀结束后,在蒙古包或者庭院前燃烧以白蒿、松枝为柴的两堆篝火,对猎犬、猎人进行净化。蒙古族称这一风俗为 “火净化”。狩猎前的“火净化”是祈求去除狩猎无获之晦气。“火净化”又分为猎犬“火净化”和猎人“火净化”两种。猎犬“火净化”就是在平地上燃起两堆篝火(两堆篝火有几步之遥),猎犬在两堆篝火间穿过,用带刺枝条轻轻鞭打猎犬的嘴巴、鼻端,并燃焦少许猎犬的尾巴尖毛。猎人“火净化”,是“先让猎人穿过两堆篝火中间,由其子女或妻子手拿一种叫做‘小叶锦鸡儿’的树条紧追其后,口喊‘温都塔必’(意为去除晦气)数声并用那枝条鞭打猎人袍子下摆处。”[10]显然,这种仪式来自于蒙古族先民的火崇拜习俗。狩猎前的火净化仪式是为了通过净化猎手或猎犬,提振运气,进而实现狩猎满载而归的愿望。
猎人待出猎前的所有仪式结束,以蒙古包的北面为起点,按顺时针方向绕蒙古包三匝后,猎民便向猎场出发,逮捕猎物。
“出猎前咏诵的祭词、吉祥词和猎杀动物后所说的推脱词等民俗,是古代蒙古族人民相信语言具有神奇魔力的蒙昧观念的体现。这类口述仪式以向山水神表达祈求原谅之意,担心由于猎杀动物而带来灾难,从而掩盖狩猎行为或转移重点等方式进行。”[11]
二、狩猎过程中的仪式与禁忌
如果说,出猎前的器物净化是猎民为了战胜自然力量,争取获得更多猎物,取得狩猎成功而采取的方法的话,那么狩猎的禁忌可以理解为,为了躲避狩猎不利因素而采取的自我约束。当猎民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遇到即使运用积极的方法仍不能解决的难题时,就会靠禁忌或回避的方式来解决,这就是狩猎禁忌。猎民在出猎前请民间说唱艺人咏颂山水并祭火。猎人不能说去打猎,忌在火堆旁说有关狩猎的任何事,包括狩猎的时间、地点,原因是为了防止火神(蒙古族认为火神的嘴比较快,爱传话)将猎人狩猎的事情传给山水之神,山水之神将猎物转移,导致影响到狩猎事宜。
(一)开猎前的仪式与禁忌
猎人全部到达狩猎地点互相问候后,在长者的带领下要咏唱《山水颂》和举行一些仪式。长者宣布狩猎纪律,要求注意人、马、犬的安全。猎人们一般以马粪球作证或用星宿之称以隐语相告围猎的时间、地点。猎人不许说不吉利的话及粗话,如:“‘没有猎物’‘打不到猎物’‘空手而归’等,也不能互相争吵,忌直呼野兽之名,认为动物听见猎人谈论自己的名字就会受惊逃跑,不利于狩猎活动的正常进行”。如,“把鹿叫‘庞大的’,驼鹿叫‘扁角兽’,野猪叫‘黑圆鼓’,狼叫‘著名的厉害’,狐狸叫‘帽子’‘巧尾巴’而狼的别称最多,如,‘天狗’‘野狗’‘灰狗’‘大嘴’‘大尾巴’‘不可说’等不一而足。”[12]猎民认为杀鹿会降福所以不说猎鹿,而说“去惩罚庞大的”等暗语来表达。根据地势、猎物规模等来制定具体的狩猎方法和每个猎人的职责,并宣告不遵从组织安排的惩罚办法。猎人将本次围猎的地点、聚集地、宿营地等商讨后安排下去。对于第一次参加狩猎的少年,长者会耐心地向他们讲述狩猎的规矩,如介绍遇见的猎物,猎场的山势情况,地名、动物的种类、习性等狩猎相关知识。
(二)开猎过程中的仪式与禁忌
在狩猎途中,根据遇见的猎物种类不同,预测此次出猎的吉凶。如,遇见狼、虎、鹿认为是大吉,遇见狐狸并未能猎杀则视为凶、不吉利。
狩猎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猎人忌讳带枯木、领伤狗、骑驴去打猎;忌捕老虎,因为虎被称为“山之王”“猛兽之王”。如果非猎杀不可的话,要手捧哈达磕头,并解释申辩说:“虎是怎样危害人和动物,人们是在哪个王、哪位官人的命令下合法的将它捕杀的”。还有的地区,“如果猎人偶然遇到了老虎,为了自身安全而杀害它的话,事后要去庙里磕头或者长者用羽毛鞭子敲打猎人降威。据说杀虎的人的胆子会变得异常大,什么都不怕很有威风,人们就摆出要戳他眼睛的状来吓唬猎人压降其威风。”[13]猎捕鹿时,鹿倒地后,鹿角朝上认为是大吉,如果鹿角朝下插入土中,则是不吉利的象征,猎杀鹿后猎人要叩拜鹿双角三下,并口中默诵咒语。猎鹿时还要注意不能将其皮损坏,并要将无损的鹿皮挂在树枝上。猎获熊时,也要将熊头挂在与猎人住所相反方向的树枝上。返程时,路中间横放三根树枝,并向熊头虚开三枪后才可踏入归途。
猎人行猎必须选择三、五、七、九等奇数的日子,认为这些日子是吉日。初一、十五、二十五日禁打猎。春夏时节不搞围猎,除皇帝和王公组织的大型围猎外,禁止去外地、外国打猎,禁止去封锁的山上打猎,防止在森林损害牲畜,在山上或原野中禁用火箭射杀猎物,这是为了预防用火箭猎杀动物在森林或在草原上引起火灾。
猎人不打哺乳期的动物、怀胎的动物、孵卵的动物和幼小的动物;忌全窝猎杀、忌用毒药毒死动物以及忌猎取受伤的动物、交媾的动物、在生死间挣扎的动物;天鹅的血虽可入药,但忌猎杀天鹅(一般是购买);如两只大雁中的一只被猎杀,另一只会孤单,所以忌杀大雁;不猎杀鹤、喜鹊、燕子等;忌破坏鸟窝、掏鸟蛋和小鸟,招惹迁徙之鸟;[14]还有的地方忌打鸟,在新疆卫拉特地区,“如果谁无意中抓回空中飞翔的动物,就会被训斥道‘看不到好东西影子的你!’。如果吃了不该吃的雪鸡的肉,不能把这件事告诉给任何人,因为吃了雪鸡的肉又不告诉他人,这肉就会变成药”;[15]忌用梢绳系死在野外的动物、忌捡他人猎打到的猎物、忌行走在野外有狐狸朝你呼叫,这不是什么好兆头,预示狩猎不会成功;忌在山坡上两个敖包间遇到狐狸,见到敖包要给添加石头祭祀,祈求神灵保佑丰收、顺利;老鸹从空中掉下(打到老鸹)预示永远打不到猎物,打到刺猬预示一年打不到猎物,所以猎人忌打到老鸹和刺猬;行猎途中忌遇见喇嘛、尼姑、空袋子、空车,认为这是预示狩猎的不成功,打不到猎物;最忌遇到秃了的枣红马。蒙古族不食蛤蟆、昆虫、蛤蜊等,所以不猎杀,乌龟又称金龟所以不招惹它。
忌用烟熏动物的窝或洞来捕杀猎物,当然除狐狸之外。大忌损坏任何野兽或飞禽的窝(居所)。[16]蒙古族先民生活的呼伦湖、贝加尔湖、克鲁伦河等地区有丰富的水资源,当地人依靠这种资源以捕鱼为生。《蒙古秘史》中提到了各种鱼名,还有一些鱼钩、渔网等捕鱼工具。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皇帝时代到了贝加尔湖附近,在描述当地人们的生活时说,“鱼成了家常食物”。[17]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鱼被尊为特殊动物而坚决禁止捕杀,从此,蒙古族很少食鱼了。后来卫拉特、喀尔喀部族一直禁吃鱼。[18]
狩猎对先民来说至关重要,认为狩猎无获是有物在作祟,或是猎人的晦气,或是猎神不高兴了,所以未将猎物赐予猎人。猎民认为神灵也和世人一样爱听故事,他们在行猎时会唱史诗讲故事,神灵听故事高兴了就会赐猎物予猎人。所以猎人在狩猎时特别是无获或者收获甚微的时候就会围坐在地上讲故事,来取悦神灵,得到恩赐。民间有一传说:“从前有两个猎人出猎,其中一位是民间艺人,另一位是占卜者。两人打了一天猎,一无所获,便坐下休息。这时那位爱讲故事的民间艺人为了消除疲劳和寂寞,讲起了故事。艺人一开讲就吸引了周围的山神、猎神。有一位瘸腿女神来迟了,没位置爬到艺人的鼻梁上,听得过于入神在关键时刻没站稳滑了下来,占卜人看到后经不住笑了出来了,艺人以为是在笑他,心中不悦便停止了讲述。听故事的众神也都很生气的怪罪瘸腿女神,因为她,艺人才停止了讲述。后众神商定将瘸腿女神的唯一的伤眼大鹿赐给两个猎人,第二天两个猎人真的捕到了一只伤眼大鹿。”[19]
猎人的狩猎过程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活动,在大型围猎中更是如此。长者在这里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既要组织安排整个狩猎过程,确定狩猎方法,布置给每一个猎人任务,也重视对少年新生力量的培养。狩猎是远古先民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狩猎过程中的各种禁忌是猎人自我约束的体现,禁止捕杀的猎物是蒙古族图腾崇拜的一种体现,也是自然崇拜的一种体现,更是维护生态平衡的一种体现。
善良的蒙古族先民讲究狩猎方法,严禁用残忍的办法捕猎,或者损坏动物的窝,对小动物更是倍加珍爱极力保护。大型围猎中必须放走一定数量的野兽。猎人像朋友般对待各种野兽,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使野生动物不遭受灭顶之灾,使动物可以在大自然中繁衍生息。这对猎人而言,既是对野生动物的一种人道主义关怀,更是超然意识的一种体现。
以上提到的狩猎过程中的动物不仅包含飞禽走兽,还包含着先民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所以说,先民的这些具有狩猎生活特色的禁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承至今。这是蒙古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狩猎结束后的仪式
狩猎仪式贯穿于整个狩猎过程中。狩猎结束后还有猎物分享、庆典和猎具的摆放等仪式。猎物分享从原始人分食所杀野兽肉演变而来。远古时代猎民的狩猎工具简陋,一人无法捕到凶猛野兽,只好靠集体力量,齐心协力才能共生并存。再加上狩猎经济具有转移性、不稳定性特征,猎人所获猎物不多,只能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所剩无余,因而猎物分享是当时的主要分配形式。
(一)猎物处理
狩猎经济的集体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决定着猎物分享习俗的产生和存在。猎民认为猎物是神灵赐给人民的,不能一个人独吞或者少数人享用,而是要每人都有份。分享“昂根—贺喜格”“甘吉干—贺喜格”,个人狩猎所得猎物也要分享给左邻右舍。猎人不仅视猎物分享为一种美德,更认为将猎物分享给他人会得到猎神的更多恩赐,福运会更加旺盛。民间也有猎物分享的传说:“从前有一个猎人向天神忏悔自己捕杀了很多猎物,而天神不仅没有惩罚、怪罪猎人,反而说他心地善良,将捕杀的猎物分享给他人,反而赐给他更多的猎物。”[20]从此,人们纷纷向这个猎人学习,将猎物分享给他人,渐渐地猎物分享成了一种习俗。由此可见,猎物分享习俗的形成,信仰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有生产形式和经济条件)。
猎物分享的类型有:“甘吉干好必”,一般认为分享猎物精肉或一条腿的份肉,“烧如勒嘎” 一词可能源于将猎杀的动物吊起,用篝火烧烤,大家分而食之的古代习俗。“珠勒都”猎物的头部、下颚、气管、肺等一整块连在一起没有分割的部分。猎物分享的习俗在《蒙古秘史》中也有记载。“成吉思汗的祖先朵奔篾儿干,就曾一人‘往脱豁察温都儿名字的山上捕兽去 ’。他在树林中见到兀良哈部落的人在那里杀鹿,‘朵奔篾儿干向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将这鹿取下头、皮带肺子自要了。其余的肉都与了朵奔篾儿干’。朵奔篾儿干将得到的鹿肉拿回家,在路上用它换了个穷苦的孩子,供自己使唤。”[21]
随着时间的推移、狩猎技术地更新、获取猎物的增多,猎物分享习俗也发生了变化。猎物分享从最初的平等分配,变为按贡献分配。如,直接射中猎物的人拿第一份,包括“珠勒都”,它代表着猎物的整体,是猎物的灵魂存在处,认为猎物的福分都在此,拥有“珠勒都”的人会在狩猎中捕获更多的猎物。被谁的猎犬、猎鹰捕住,猎物就归谁。前后到达猎物旁的人拿什么都有规定。以昭乌达地区分享黄羊为例:“第一名要腱骨部分,第二、三名剥皮卸取黄洋的后腿,第四、五名要其前腿,第七名取其脊骨,第八、九名取黄羊的四根肋骨,第十名能得到黄羊的肝脏。最后,亲手捕获者取黄羊的头及整张皮子。”如果对谁打中有争议的话,那就把该猎物放在一定距离以外,有争议的双方用自己的武器各击三次,全中者可得此猎物,如果双方都是三次不中,由主持官来断。如果无端起争议,就用响鞭责打之。[22]昭乌达猎民严格遵守这种习俗来分配猎物。科尔沁地区的分配方法是:谁的枪棒先打中、谁的狗先咬住,猎物就归谁。后来分配有了等级分化,王公贵族拿大份,平民百姓拿小份。可见猎物分享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猎物分享前要答谢神灵的恩赐,用“珠勒都”祭祀神灵,“珠勒都”是祭祀神灵的最佳供品,以此来表达对神灵的敬意,祈祷来日丰收。
(二)猎具处理
狩猎归来,须将猎具摆放在固定地点,这颇有讲究。“布鲁插入笆缝隙中,将猎枪斜挂在老人卧室的墙壁上,马具和马鞭子要停放在马鞍架上不得乱动,更不准妇人任意拿动。若走进一个猎户家庭如果整齐的停放着各种猎具、马具、马头琴、四胡和蝇甩子(用马尾做成的打蝇的用具)就视为高雅、尊贵、富有的人家。”[23]猎民摆放猎具都如此讲究,不仅体现了狩猎工具在狩猎中的重要性,也体现了蒙古族先民的狩猎习俗。
无论是狩猎前的准备还是狩猎整个过程的仪式、观念、习俗等,都是猎民在长期的狩猎实践中传承发展延续至今的独特文化。狩猎过程中的这些规则不仅丰富了狩猎的内涵而且加深了人们对猎民与大自然、猎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认识。
以上是狩猎整个过程中的各种仪式与禁忌。猎物是猎民衣、食、住、行的主要来源。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猎物与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生物链,循环往复,不能在某一个环节断裂,否则会打破固有的平衡。猎民对自然、对动物的原始观念,有些看似幼稚却体现出了他们的大智慧。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族群众注重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也是其“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