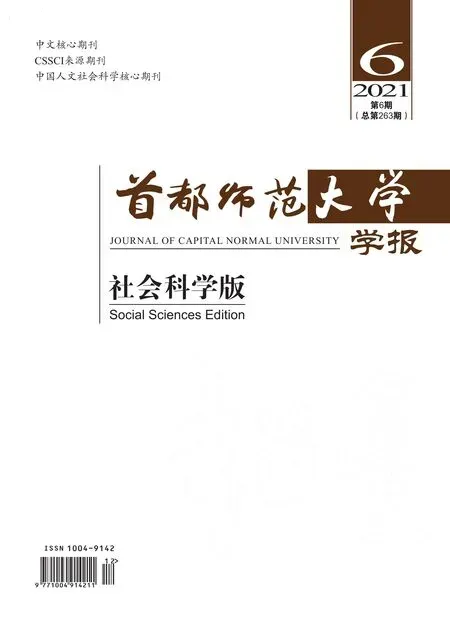作为抗战文学的《湘西》
李青果
《湘西》是沈从文湘西系列“散记”的第三部,成稿于1938年,连载于1938年8月25日至11月17日的香港《大公报·文艺》,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与数年之前写作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不太一样,这是一部记载作家1937—1938年之交,在战时环境下写作的湘西途程记。面对同样的河山,但时移世易,《湘西》带上了特殊时期的明显印记。其突出的特征是表现抗战来临时的湘西,欲图唤醒湘西人民的地方与国族意识,从历史联系时事角度,为湘西准备作成抗战的坚强前线或稳固后方发出呼吁,而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叙述出一个新的湘西。
与《湘行书简》《湘行散记》相异之处还有,蕴含在《湘西》中的个人抒怀和边地夸张的程度大大地降低了,作家反而为这片他熟悉的土地投下了非个人化和历史化的视野,其对于湘西民风民俗的存留,也从欣赏、炫奇的心态,转向冷静的反思乃至于批判的立场。而从写作的姿态来看,那种“乡下人”的眼光换成了代表地方发言的重要人物的口吻。沈从文在1932年就被他的老师、南社名诗人田名瑜视为“峻而气清,怀虚而志亢”的湘西后起之才俊①田名瑜:《送沈从文序》,《南社湘集》第6期,1936年3月。,1937年又获得了“沈凤凰”的称号②施蛰存:《重印〈边城〉题记》,朱光潜等著,荒芜编:《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2页。,从而和他的同乡前辈“熊凤凰”(熊希龄)一样,成为湘西人物的代表。因此,当他1938年以避战或逃难的方式重返故乡的时候,江山易色,其文章亦随之易色,突出在战时环境下,袪湘西之魅和纪乡土之实的目的,并且皴染上沈从文独有的模山范水如画笔墨。
一、地理与人物
1937年8月12日,沈从文和他的一干高校友人杨振声、梅贻琦、朱光潜、梁宗岱等,从沦陷于日寇铁蹄的北平乔装逃离,别妇抛雏,情态可谓仓皇。由于战事迅速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发展,沈从文一行水陆并行,经天津、南京等地,至武汉、长沙、沅陵时,才有了一段时间喘息小憩。在这里,沈从文发生了“向何处去”的困惑。然而无论何去何从,他都准备以一己之力参加到抗战的洪流中去。在长沙、沅陵,他曾和陈渠珍等同乡前辈讨论湘西的命运,也曾与曹禺等作家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访问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徐表示欢迎他去延安参加抗战,然而同时也表示,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文化人,作为统一战线的一分子,留在后方团结合作,进行持久抗战同样很重要。③凌宇:《沈从文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页。这被视为后来沈从文写作《湘西》的一个重要根据④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恰值此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联合大学,并准备分头西迁云南昆明。沈从文在长沙加入了联合大学的队伍,不久就再一次经过他的故乡湘西,于是,《湘西》因之敷彩成章。
上述背景构成了《湘西》的时代语境,同时也意味着,这部作品将探讨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并不再把湘西当作一方充满异质性的偏僻之地,而是作为抗战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来加以处理。事实上正是如此。作为在湘西内外已经具备较高文化资本的知名人物,沈从文首先考虑的是为湘西“袪魅”,改变外地人心口里对于湘西的原始性印象,把这块神秘的充满巫文化和土匪气的“化外之地”现实化,还原其既是苗区同时又属于中国的历史。沈从文把这件事当作自己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也将对他之前的湘西进行“翻转”式描写。读者应该都还记得,六年前他写作异域风情浓厚的《从文自传》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扭转清朝由官方写作的《苗防备览》给予人们的观感,还原一个充满地方色彩、奇风异俗的湘西⑤李青果:《回旋书写的沈从文“自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而在写作《湘西》的时候,沈从文一方面检讨仍然存在于民国的防苗政策,一方面却要改写《从文自传》神秘化、风俗化湘西的写作路线,“再还原”出一个新的处于抗战环境中的真实湘西。
正是出于这样的用心,《湘西》的“引子”是以一种驳论的写作方式出现的。针对外地人对于湘西的种种奇异的传说和印象,沈从文态度温和然而说理明快地予以否定——湘西既不是游宦于此的文人笔下任意涂抹的蛮愚凶险之地,同时也并非任意夸张浪漫的“世外桃源”;“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只是一种对于湘西的刻板而夸张的印象或表象。⑥沈从文:《湘西·引子》,《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这块土地烙印着屈原遭受放逐的行吟足迹,同时也是汉代马援西征困死之地以及五代马希范与土人立铜柱为记,进行分疆而治的地方。这样的历史脉络说明,湘西虽然相对独立却与外部世界有着长期历史联系的事实。这种状况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推展,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1935年,一条为备战、抗战修筑的战略公路——湘川公路,经过湘西通往重庆,不久以后,重庆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
众所周知,工业文明背景下产生的公路,代表着一种物质和文化上的现代性。在这样的文明视线之下,沈从文早前在农业文明视野里观察、书写的“湘西”,经由《湘行书简》《湘行散记》构筑的奇异景观,便让位于由工业文明与战争环境交织在一起的《湘西》。沈从文一行从长沙乘车到达常德,这个号称偏僻湘西的咽喉之地,便就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区域”:
湘西虽号称偏僻,在千五百年前的《桃花源记》,被形容为与世隔绝的区域,可是到如今,它的地位也完全不同了。西南公路由此通过,贯串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交通。并且战争已经到了长江中部,有逐渐向内地转移可能。湘西的咽喉为常德,地当洞庭湖口,形势重要,在沿湖各县数第一。敌如有心冒险西犯,这咽喉之地势所必争,将来或许会以常德为据点,作攻川攻黔准备。
正是这样的现代性视野的建立和对时事的敏锐预测,在《湘西》的开篇《常德的船》中,沈从文不仅揭示了常德在今时今世的战略地势,而且还原其在历史上处于洞庭湖“沿湖各县数第一”的枢纽位置。立足于这样的叙述姿态,常德这个陶渊明笔下的“武陵郡”,便不再是古时避秦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作为陶渊明叙事的反转,想象的武陵归隐,现实的湘西显形,这个地方所具有的古典浪漫气息让位于沈从文笔下的社会写实。①沈从文:《湘西·常德的船》,《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常德的船》本可借用陶潜《搜神后记》的一切典故,或者重拾他往日的笔墨,描绘出一幅诗情画意的水乡风景。然而作为湘西连接中部中国的水陆出口的历史事实,常德从《楚辞》发生的时代至于今,都是交换进出口货物的大码头,这成为沈从文书写的重点所在,而其指归在于一个富庶繁荣的湘西市镇,可作为战时重要的物资转运站和人员储备地。
值此之故,《常德的船》以一种十分铺排和写实的方式导引读者进入历史化而非猎奇化的湘西。大量来自外省和湘西腹地的船舶辐辏于常德,显示了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湘西血脉畅通而且富于生气。《桃花源记》中“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世外景象,被沈从文刷新重绘为一片现实社会的市声喧哗和桨声灯影。辐辏于此的船,来源广泛,名目繁多,包括“长江越湖来”的“乌江子”盐船,更多来自湘西腹地“富丽堂皇、气象不凡”的“洪江的船”,沅陵酉水“平头大尾”的“白河船”,凤凰、乾城苗乡“船舷低而平,船头窄窄”的“洞河船”,“极活动,极有生气”的“麻阳船”,以及“漂浮水面如一片叶子”的“桃园划子”和“颜色黄明照眼,式样轻巧”从湘西以西到达常德的贵州“铜仁船”。这些船只运载、交换着产于外江和湘西乃至川贵地区的物产,显示了湘西物资生产、商贸流通富裕丰足的一面。大量的桐油、木料、牛皮、水银、子盐、花纱、布匹、洋货、煤油以及各种轻工业日用品,由这里转口行销,在历史上成为盘活湘西经济社会“吐纳货物和原料”的“咽喉”,而战时则可望成为抗战物资的供给地,湘西的战略地位于此显露。文中特别引述了南宋《金陀粹编》记录岳飞乘“大鳅鱼头船”在洞庭湖水擒杨幺的故事,则于一片历史的硝烟中指示着即将来到的抗日烽火。
《常德的船》所具有的历史还原和地方写实的艺术特色,显示了沈从文对自我创作习惯的一次重大调整,其触机则是他希望创造一种由于“作者是本地人”因此力能胜任②沈从文:《湘西·引子》,《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并且具有自我风格的战时文学。这种战时文学,不涉及普遍流行的抛弃个人主义从而投入时代洪流的群体觉醒,也不关乎使用铿锵有力的笔调夸张弥漫硝烟的高亢抒情,同样处于身居后方的写作位置,它也不同于张天翼《华威先生》那样辛辣愤世的幽默讽刺。《湘西》宣示了一种写实的而非浪漫虚构的地方主义的苏醒,其方式是以社会学、地方志的纪实写史笔法,为湘西“袪魅”。既然过去任职于此的地方官、史学者、社会问题的专家,不仅不能呈现湘西的真实历史与现实,而且不断使之神秘化和污名化③沈从文:《湘西·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页。,那么,在“湘西沅水流域必成为一个大战场——一个战场,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一片瓦砾场”的态势下,对于湘西的“过去”和“当前”必须得到真实的揭示,方可应付“诱敌入山地”的战事走向。
这种对于真实湘西的揭示,还通过作家观察角度的调整,实现从“水土”到“人物”的递进。前文已述,沈从文此行的交通工具是长途汽车而非他习惯的水乡船舶,这使他对于湘西的观察,出现了一种抽离的、旁观的视角,刻画出一幅客观的有时甚至近于俯瞰式的全景画面。这与沈从文惯常操持的情景交融、人景互化的手法是不同的。在他之前的湘西笔墨中,人是自然之子,“自然而不悖于健康的人性”是其“水土”与“人物”的同构关系。这种以自然映照出来的人生形式,在艺术表现上极为具体细腻,在艺术哲学上却是抽象的、象征主义的。然而,这种为人称道的“沈氏风格”却在《湘西》中被他自己打破了。《常德的船》的结束部分出现了这样的叙述:“常德县城本身也就类乎一只旱船,女作家丁玲,法律家戴修瓒,国学家余嘉锡,是这只旱船上长大的。”“旱船”云云,其实喻示是一种前驱于时代而非归本于自然的历史方向。沈从文集中笔墨使湘西的真实人物群像出现在他的文字之中,这些人物以其个人成就和对现代中国的多方面贡献,证明了湘西的价值所在。在《沅水上游几个县分》《凤凰》等文中,向警予、熊希龄、陈渠珍、王家烈等政治取向、行事风格、社会贡献大异其趣的人物不时出场,他们也不再是沈从文笔下的自然之子。他们作为现代中国历史风云的代表被沈从文写进《湘西》,意味着作者把湘西从传奇转化成历史的努力。这种把湘西人物历史化的叙事目标,还更贴紧在那些为时代作出贡献的普通人身上,作者尤其感慨系之的是湘川公路的建设者:
一个旅行者若想起公路就是这种蛮悍不驯的山民或土匪,在烈日和风雪中努力作成的,乘了新式公共汽车由这条公路经过,既感觉公路工程的伟大结实,到得沅陵时,更随处可见妇人如何认真称职,用劳力讨生活,而对于自然所给的印象,又如此秀美,不免感慨系之。这地方神秘处原来在此而不在彼。人民如此可用,景物如此美好,三十年来牧民者来来去去,新陈代谢,不知多少,除认为“蛮悍”外,竟别无发现。外来为官作宦的,回籍时至多也只有把当地久已消灭无余的各种画符捉鬼荒唐不经的传说,在茶余酒后向陌生者一谈。地方真正好处不会欣赏,坏处不能明白,这岂不是湘西的另外一种神秘?①沈从文:《湘西·沅陵的人》,《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1938年3月成立的“中华文艺界全国抗敌协会”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倡议,对加入文协不甚措意的沈从文,却以实际行动响应号召,一早就加入了文学史的大合唱。通过对湘西地理与人物的再发现,沈从文叙述出这方水土新的历史与现实,其目的是为了袪湘西之旧魅,还原一个置于抗战烽烟之中并渴望对抗战有所贡献的湘西。而对湘西地处抗战咽喉要冲与湘西人民投身抗战事业的描写,体现了沈从文投身抗战的自觉和努力。可更值得申说的还是沈从文的创作方式,即使加入了大合唱,仍然保持了独有的身段,构建属于自己的“小文学史”:他坚持其习惯的湘西书写,却更新了表达旨趣;他贴紧其熟悉的风土人物,却挖掘、再现了新的主题。这个新的主题,犹如沈从文上文提到的“湘西的另外一种神秘”,也是通过他更改原有的叙述方式才揭示出来的。
二、“情魔”与“游侠”
写作《湘西》的目的之一,还包括沈从文要解开这个“地方,人与物,由外人眼光中看来俱不可解”的谜团。在外乡人看来这地方无事不奇,定然有它令人惊奇的表象。然而值得再次说明的是,这里发生的奇人奇事甚至也是沈从文通过自己的作品建构起来的。从这个层面而言,他之前构筑的湘西世界,也可以说是一次和外乡人的共谋——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为目的。无论是《边城》等讲述的儿女情事,还是《从文自传》记录的军中行旅,均以奇取胜,力求拍案惊奇的效果。惊奇效果的获得,是作家偏重于渲染自然主义与原始宗法主义,从而使其故事和人物与20世纪的中国甚至湘西的真实处境拉开了不小的距离。因此在《一个传奇的本事》的“附记”中,当沈从文说准备写作《湘西》的时候,他开始关注“人事和背景”以及“地方问题”①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附记》,《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如此一来,《湘西》所钩稽的“传奇”的“本事”,就成为作者对湘西的奇人奇事作出历史文化与社会意识上的一种新解释。
沈从文是从由情而“魔”的女子和游侠(军旅)未必“仗大义”的男子的异闻故事里发掘存在于湘西之传奇背面的东西的。纯情以至于一往情深,游侠以至于不避血腥,曾是沈从文极力夸张表现的题材,并且形成其作品的牧歌情调和原荒色彩。“这些人物,他们生活单纯”,使1934年写作《湘行书简》的沈从文“永远有点忧郁”②沈从文:《湘行书简》,《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可是到了1938年写作《湘西》,他们却成为被“历史习惯所范围”的人物而使作家“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③沈从文:《湘西·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从唯美范畴的“单纯”与“忧郁”跨越到社会观感的“激动”与“痛苦”,导致沈从文笔下的自然牧歌和原始宗法主义的脉脉温情让位于生活中的残缺部分,而辩证地看,这些残缺所隐伏的地方精神却有可能成为新湘西的历史文化基础。
流传在柳林岔的一个关于貌美如花的寡妇与虔诚修道的和尚的奇恋④沈从文:《湘西·沅陵的人》,《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透露了沈从文对于湘西子民深情执着而又深度压抑的生存状态的同情。故事叙述得相当冷静,却充满情绪的张力,隐含着作者对于地方、历史与人事的思辨意识。“寡妇因爱慕和尚,每天必借烧香为名去看和尚,二十年如一日。和尚诚心修苦,不做理会,也二十年如一日”。寡妇的儿子知道后,既不敢规劝母亲,也不能责怪和尚,只好雇请100名石工和100名铁匠,凿开山石修了一条长长的小路和一拱石桥,连接家里与山寺,并在路旁固定粗大的铁索,作为攀援和保护的设备。儿子完成这一切后,离开家乡再也没有回来。故事的结尾看起来和《边城》类似,但却不是那种“也许明天就会回来,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的开放式结构——这种结构给不完美的人间世营造一个担心揉碎了的梦境,因此保留了一种虚幻而又温柔的想象。对于寡妇与和尚的奇恋,沈从文揭出的是其中的眷“恋”和忍“苦”。和尚诚心修苦,寡妇二十年如一日不能公开的爱,也何尝不是修苦,其修苦的背面却是不能公开的恋爱。而儿子为了这对恋人凿石修路却不能公开说明、终至于离开乡土的行为,更是一种眷“恋”和忍“苦”。他们的苦恋并不涉及色空冲突的佛教意识,反是紧紧缠绕的承担命运的不恋之恋与忍苦眷爱的默然牺牲这样的人间情绪。他们眷“爱”而又守法不破戒,不失尽责敬人的品质。当这段三人奇恋从历史化为传说的时候,经行路过的行人因得益于这路桥的方便,沿河上下的水手因得益于坚固铁索拉纤,都赞叹他们“完成的伟大工程”。
沈从文书写的这段被他自称为“杂糅着神性与魔性”且富于理解和奉献的奇情故事,其“本事”与本地“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⑤沈从文:《湘西·沅陵的人》,《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楚国曾是产生屈原及其山鬼的地方,忠贞坚韧和敏于深情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流淌在楚人的血液之中,“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的维护和再造。如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相联系,那么这个奇恋故事蕴含的时代内容,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另一种奇恋故事中的情魔色彩则与湘西的巫鬼文化有关,这本是沈从文的惯常题材,但在写作《湘西》的时候,他指出这些流行于世的巫鬼传说并非供人猎奇的天方夜谭,而是人性压抑,尤其是性压抑的产物。⑥沈从文:《湘西·凤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这种情感生命受到压抑的原因在于现实社会的愚昧与不合理。行巫者多半是或贫或寡的妇人,其行事“必与仇怨有关,仇怨又与男女之事有关”。是正常的爱欲不能合理实现从而“产生变质女性神经病”,使她们或人到中年成为巫妇,或人到老年成为蛊婆,用变态行为发泄郁积的欲望,并且贫困痛苦的生存状态不为社会所理解。“落洞”则更是一种奇恋行为,年青姣好且知书识礼的女子,耽于美好浪漫的爱情幻想而不得,终至于以为和山里的洞神发生了恋爱,最后打扮如新娘自行落入洞中死去,“实在是一种人神错综的悲剧”⑦沈从文:《湘西·凤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沈从文道出悲剧的原因是社会性的,是一直以来存在于湘西的对于女性的严厉道德管制和情欲压迫,使这些女子游离出人间,寄情于原始宗教中的神鬼,造成种种难以理解的人间悲剧。
沈从文把这些行为总结为“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两者混而为一”,“神秘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①沈从文:《湘西·凤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页。浪漫缘于对美好爱欲生活的执念,宗教情绪则是流行于湘沅楚地万物有灵的人神合一意识。二者绾结生出的奇情奇事,看似神秘,其背后却是引人深入思考的社会悲剧。而在沈从文眼里,这种悲剧同时也是动人的歌诗,内蕴着不甘困窘压抑的挣扎反抗,虽然以悲剧为结局,其中的生命意志却值得表示敬意。和前述的僧俗之恋一样,沈从文把神巫之恋也视为“动人的诗”。而“诗可以怨”,一方面表达了沈从文对于他所述“情魔”主角同情之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发挥“怨”介入现实、批评社会的功能。沈从文深入神魔“秘境”,并把他们还原为历史,正体现了他袪魅湘西的写作主旨。
“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两者混而为一”,“在男子方面,则自然成为游侠者精神”②沈从文:《湘西·凤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页。;“宗教情绪(好巫信鬼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③沈从文:《湘西·凤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394页。。由此引发沈从文叙述了另一种湘西奇人奇事——“游侠”:“游侠观念纯是古典,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④沈从文:《湘西·凤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还能保存一点古风”⑤沈从文:《湘西·凤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页。。闻名川黔鄂湘四省边地的凤凰游侠田三怒,“身体瘦而小,秀丽如一小学教员”,“一见长辈或教学先生,必侧身在墙边让路,见女人必低头而过,见作小生意老妇人,必叫伯母,见人相争相吵,必心平气和劝解,且用笑话使大事化小。周济逢丧事的孤寡,从不出名露面”。他10岁就以和屯田士兵斗殴进入江湖,12岁身怀黄鳝尾小刀闻名同道,16岁即翻越600里山路到常德为友报仇。凭借行侠仗义和尚勇精神,田三怒在20岁时做了江湖龙头老大,成为维持地方秩序和道德礼俗的重要力量。由于“结怨甚多”,最后他遭到仇家伏击,因不愿受辱而拔枪自毙。
沈从文把田三怒称为“当地最后一个游侠者”。作为草莽好汉,田三怒正合于司马迁所欲表彰的“靡得而闻”的“布衣之侠”,他们身处民间,并不掌握国法赋予的财富、权力资源,却能以“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而从游侠行为有“不轨于正义”的一面,他们“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精神是值得进行一番现代意识的梳理的。⑥司马迁:《史记卷124·游侠列传第64》,万卷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页。这里的正义,即是为江湖武德所遮掩的民族大义。游侠者徒具地方性而少有家国情怀,因此“这个地方的人格与道德,便当归入另一型范”——必须通过教育、组织和管理的模范打磨,使游侠者不仅刚直团结,而且明白个人对于地方和国家的责任。就此而言,对于游侠者的教育和领导就变得十分重要:“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结合为一,便成为游侠精神,领导得人,就可成为卫国守土的模范军人。这种游侠精神若用不得其当,自然也可以见出种种短处。或一与领导者离开,即不免在许多事情上精力浪费。甚焉者糜烂地方,尚不自知。”古典的游侠者需要进行现代转化成为“守土卫国”之士,由此沈从文特别呼吁执事于湘西的老前辈,发挥领导模范作用。这些人物是当地的读书人、政治家、带兵将佐,他们同样是为游侠精神所浸润的“游侠者”:
这种游侠者精神既浸透了三厅子弟的脑子,所以在本地读书人观念上也发生影响。军人政治家,当前负责收拾湘西的陈老先生,年过六十,体气精神,犹如三十许青年壮健,平时律己之严,驭下之宽,以及处世接物,带兵从政,就大有游侠者风度。少壮军官中,如师长顾家齐,戴季韬辈,虽受近代化训练,面目文弱和易如大学生,精神上多因游侠者的遗风,勇鸷慓悍,好客喜弄,如太史公传记中人。诗人田星六,诗中就充满游侠者霸气。山高水急,地苦雾多,为本地人性格形成之另一面。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①沈从文:《湘西·凤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页。
湘西因地处偏僻,文化风俗相异,事事物物都被视为惊奇,使人以惊奇作为对湘西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反映,想象出奇幻而魅丽的异域世界。然而通过奇人奇事的叙述,沈从文揭开其神秘面纱,还原其作为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真实部分——湘西似奇实非奇。真实的湘西何以重要,乃是因为在战氛日浓之际,它即将作为抗日的主战场及人员与物资的输送地,承担重要的历史使命。《湘西》的写作旨趣,既是为国人讲述一个真实的湘西,使之合理地看待和使用这片水土,也是鼓励地方民气和自尊心,使湘西子弟明白身负的责任,建立超越地方的视野而为国家做出贡献。沈从文通过情魔和游侠者故事,深度挖掘人物浸润的坚贞坚韧品质和尚武勇毅精神,使湘西以新的精神面貌,从传说走向现实。
三、画意与文意
与沈从文的其他乡土书写比较,《湘西》属于写实纪事之作,并非之前专事以逞奇记异为主要目的;其风格不以抒情取胜,而是“作为关心湘西各种问题或对湘西还有兴味的过路人一份‘土仪’”②沈从文:《湘西·引子》,《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由于承担着与之前游历湘西的官吏、学者、记者,乃至包括作者自己的故乡书写进行“辩论”的任务,《湘西》体现出朴素而显豁的用意,促使其风格偏向史传的特色。然而这并没有削弱作品的艺术性,其状物记人的笔墨依然细腻精致,而更加突出的,是沈从文有意引入“画意”,使之为作品“调色”并为之“增色”。
“画意”,就是在作品中穿插使用中国绘画艺术。距写作《湘西》不到10年,沈从文就以对中国美术史的深厚了解为世人所知③沈从文:《给一论文作者(1947年1月19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462页。;但在写作方面,则是早在他初到北京之时,就经常品读含玩中国古代绘画,并将之学习、应用到作品之中,从而获得一种把作品敷写成既富诗情画意又寄意遥深的特殊技艺。④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相比古代文人“诗画合一”的审美追求,沈从文表现出一个现代作家在“文画合一”方面的努力。如其追忆早期创作经验时所说的:“范宽的《雪山图》,董源的《龙绣郊民图》,夏圭的《溪山清远图》,赵松雪的《秋江叠嶂图》……都深深吸引着我,支配着我,并产生种种幻想和梦境,丰富充实了我这方面的知识和感情,甚至于也影响到后来的写作,用笔时对于山山水水的遣词措意,分行布局,着墨轻重,远过直接从文学上得到的启发还加倍多。”⑤沈从文:《回忆徐志摩先生》,《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434页。
这种技艺在《湘西》中的充分表现,是借鉴绘画艺术体现地方风景的特色和变化,增益读者对湘西山川风物的审美兴味;更进一层,则通过挖掘景色如画中蕴含的历史精神,为抗战背景下湘西子民所担负的时代使命赋予地方文化的坚固基因。前一个层面,是沈从文借用“新安画派”作品的润秀与奇崛,通过画幅的渐次打开,由浅及深地表现湘西风景风物的迤逦之势:
汽车过河后,长沙地方和旅行者离远了……上了些山,转了些弯,窗外光景换了新样子。且还继续时时变幻。平田角一栋房子,小山头三株树,平净洒脱处,一个学中国画的旅客当可会心于新安画派上去。旅行者会觉得车是向湘西走去,向那个野蛮而神秘,有奇花异草与野人的地方走去,添上一分奇异的感觉,杂糅愉快与惊奇。⑥沈从文:《湘西·引子》,《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337页。
由三门水行七十里,到保靖县(过白鸡关陆行只四十里)。保靖是酉水流域过去土司之一所在地。酉水流域多洞穴,保靖濒河两个洞为最美丽知名。一个在河南,离县城三里左右,名石楼洞。临长河,据悬崖,对河一山山上老松数列,错落布置,十分自然。景物清疏,有渐江和尚画意。①沈从文:《湘西·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
前引“一个学中国画的旅客当可会心于新安画派上去”,是将入而未入湘西的宁乡、益阳景象;后引“错落布置,十分自然。景物清疏,有渐江和尚画意”,则是深入湘西腹地保靖县的风光。它们虽然分属两篇文章,却连接为一幅由平芜逐渐走向“神秘而野蛮”的湘西风景画卷,铺述、镶嵌十分得体自然。渐江和尚是成熟期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画风秀逸高洁,以遗民之身出家后,更显遗世独立、超然远引的气质。诚如沈从文所说:一个学画的旅客能够领会其中的新安画意,宁益地方“平静洒脱”的平田风景其实和“景物清疏”的渐江风度并不抵牾,相反地,成为它的一个“前景”。懂得画史的读者明白新安画派崛起于明清之际当地徽商的财富积累和文化提升,是经济与文化互动的结果。宁益地方商业富庶,文化相对开放,其“公路坦平而宽广”,“路旁树木都整齐如剪。两旁田亩如一块块毯子,形色爽人心目”的景色,正与新安画派发生的历史背景相对应。而到了湘西腹地,这块遗落在世外的风土,恰如出家后徜徉山水遗世独立的渐江和尚那寒鸟夜猿、空远沉寂的画意,透露出美丽空旷而又荒野漫漶的气息。沈从文利用自己的美术修养,以绘画意境逐渐加深读者对于湘西的印象,使湘西的山水世界与古人的艺术精神相融汇。这是沈从文在更高的文化修养和美学层次上打磨他的写作对象,无论对于题意的彰显还是阅读兴味的增强,都取得了独此一格的效果。
这种画意与文意的“互渗”“互答”,也不只是表现为单纯的山水秀色,或把抽象文字具象为直观的画面,增益文章的美学趣味。在如画的风景里,沈从文还特别注意挖掘内含其中的人的精神意态,使自然与人生及时事生发出一种新的关系:
由沅陵南岸看北岸山城,房屋接瓦连椽,较高处露出雉堞,沿山围绕;丛树点缀其间,风光入眼,实不俗气。由北岸向南望,则河边小山间,竹园,树木,庙宇,民居,仿佛各个都位置在最适当处。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堆蓝……就中最令人感动处,是小船半渡,游目四瞩,俨然四围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画。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在轻烟细雨里,一个外来人眼见到这种情形,必不免在赞美中轻轻叹息,天时常常是那么把山和水和人都笼罩在一种似雨似雾使人微感凄凉的情调里,然而却无处不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②沈从文:《湘西·沅陵的人》,《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54页。
其中,“各个都位置在最适当处”,使用的是南朝画论名家谢赫“论画六法”之“经营位置”③转引自张彦远撰,周晓薇校注:《历代名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一切如画”则不仅指所见风景如画,更指向画中人物与山水之美一样,令人“在赞美中轻轻叹息”。这段描写出自《沅陵的人》,令人赞美的,是沈从文花费很大笔墨描写的修筑湘川公路的湘西女子。这些平时给人以和善、朴素印象,多情如山鬼、神秘如云中君的女性,在“公民劳动服务”中毫不输于男子。她们“胸口前的扣花装饰,袴脚边的扣花装饰”,保持着“女子爱美的天性”,仿佛《镜花缘》女儿国中的人物④沈从文:《湘西·沅陵的人》,《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第350页。,激发人们深沉的敬意。“危立船头,视若无事”的湘西女子置身于既属险境也是美景的自然之中,其美与险也指向抗战到来之际渲染着悲壮色彩的大好河山。这使整幅画面皴擦出历史的波涛声色,浸透着山水之子朴素而伟大的创造活动,“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并因其埋没不彰,进一步引发作者“似雨似雾使人微感凄凉”的同情。这种描写达到的效果,也如谢赫“论画六法”之“骨法用笔”与“气韵生动”①张彦远撰,周晓薇校注:《历代名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曝露沈从文充分调和画意与文意,使之对照互动,丰富了文学表现力与审美品质的笔墨所在。
然而也应该看到,使用这种表现技巧,其本身也是通过改造、增补乃至“否定”宋元以来中国文人画的意境来实现的。上引为沈从文所揣摩、学习的范宽、董源、夏圭、赵松雪等画家,他们的山水画更多体现空寂深幽的道禅意境,和现实人生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从这些“人迹罕至”的画卷中读出人生情味,是沈从文把现实人生提升到与山水美质同等高度的价值认识,并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赋予它们美学上的意义。对绘画中人生情味的挖掘也关涉到沈从文对中国绘画历史更为古老的一种观念——和“文以载道”一样,文人画兴起之前的中国画论也曾主张“画以载道”。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开宗明义就是:“夫画者,成教化,足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②张彦远撰,周晓薇校注:《历代名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绘画与六经平起平坐,当然应该彰显它教化人伦、穷变测微的历史精神,否则不足以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值此之故,和湘西山水相映成对的“宋人画本”,又一转成为需要“反思批判”的“作品”:
石壁临江一面崭削如割切。河水深而碧,出大鱼,因此渔船也多。岩下多洞穴,可收藏当地人五月节用的狭长龙船。岩壁缺口处有人家,如为造物者增加画意……一切光景静美而略带忧郁。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满眼是诗,一种纯粹的诗。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即人与自然契合,彼此不分的表现,在这里可以和感官接触。一个人若沉得住气,在这种情境里,会觉得自己即或不能将全人格融化,至少乐于暂时忘了一切浮世的营扰。现实并不使人沉醉,倒令人深思。越过时间,便俨然见到五千年前腰围兽皮手持石斧的壮士,如何精心设意,用红石粉涂染木材,搭架到悬崖高空上情景。且想起两千年前的屈原,忠直而不见信,被放逐后驾一叶小舟飘流江上,无望无助的情景。更容易关心到这地方人将来的命运,虽生活与自然相契,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说起它时使人痛苦,因为明白人类在某种方式下生存,受时代陶冶,会发生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悲悯心与责任心必同时油然而生,转觉隐遁之可羞,振作之必要。目睹山川如此秀美,“爱”与“不忍”会使人不敢堕落,不能堕落。③沈从文:《湘西·泸溪·浦市·箱子岩》,《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376页。
其中,宋人画本“满眼是诗,一种纯粹的诗”,映射的是湘西的山水意境;“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即人与自然契合,彼此不分的表现”,则是融化其中“乐于暂时忘了一切浮世的营扰”的湘西子民的“人格”。这是沈从文从“一切光景静美”的画幅中读出的“忧郁”,对于纯粹审美画境的不满其实透露出对于静美生命形式的忧惧。犹如宋人画本纯粹如诗无益于宋辽金一连串的国难一样,湘西人融化于自然的生活态度,在事变之亟的当下也难逃被“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的命运。因此绘画必须“化人穷变”,湘西子民必须“深思现实”,重张五千年前祖先的开辟精神和两千年前屈子忠信爱国的传统。
“目睹山川如此秀美,‘爱’与‘不忍’会使人不敢堕落,不能堕落”,沈从文的这番读“画”心态,使人想起中国画史上一段不太为人提起的读画传统。北宋靖康之变后,不少南迁的文人打开前代的“宋人画本”,往往产生失国之痛,其“爱”与“不忍”既催生痛苦的历史情愫,也传递反思、振作的愿力。如范成大《题山水横看二首》之二:“霜入丹枫白苇林,横烟平远暮江深。君看雁落帆飞处,知我秋风故国心。”陈与义《题画》:“分明楼阁是龙门,亦有溪流曲抱村。万里家山无路入,十年心事谁与论。”生活在北宋末年国土为北虏蚕食时期的张耒,在《题周文瀚郭熙山水》中说:“洞庭碧落万波秋,说与南人亦自愁。指点吴江何处是,一行鸿雁海山头。”更在《题赵楶所藏赵令穰大年烟林二首》之二呼唤“平远起君千里恨,清诗可要助江山”④李德壎编著:《历代题画诗类编》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第43页、第32页、第31页。,显示披览故国江山图画蕴含着黍离之悲,文艺必须有助于“还我河山”的经世题旨。这和《湘西》表现的对“画”沉思,若合符节。可以说,识画懂画并且有兴趣把画意与文意互相调和含摄的沈从文,为这个读画题画绘画(写作)的传统,添上了精彩的一笔。
结 语
《湘西》是一部“文章合为时而作”的抗战作品。虽然在抗战文学观上沈从文和左翼作家有尖锐的分歧,但《湘西》以其独特的姿态丰富了抗战文学的风采。诚如作者所说,它是一部与一般通讯游记不一样的游历纪实作品,虽寄望对于抗战有明确的贡献,其预设的读者为入湘抗战的人员,并且包括他的湘西同胞桑梓,但仍然不出之于直截的“宣传”而是笔之于精细的“文艺”,使其“不仅是诗意的湘西,富裕的湘西,而且也是生气勃勃的湘西——抗战中的湘西”①萧乾:“编者按”,沈从文:《湘西》,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可见,作者在服务现实与传承审美之间努力平衡,保持着五四新文学的姿态并延续它的香火。在沈从文自己的文学轨道上,《湘西》还代表着自我扬弃与变化。和临近时间创作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长河》相比较,它和两个“湘行记”虽成系列,其实貌合神离,而与《长河》有一致的追求,更关心现实并形之于富有自我特色的“历史叙事”,显示了作家随时而变,调整写作方向的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