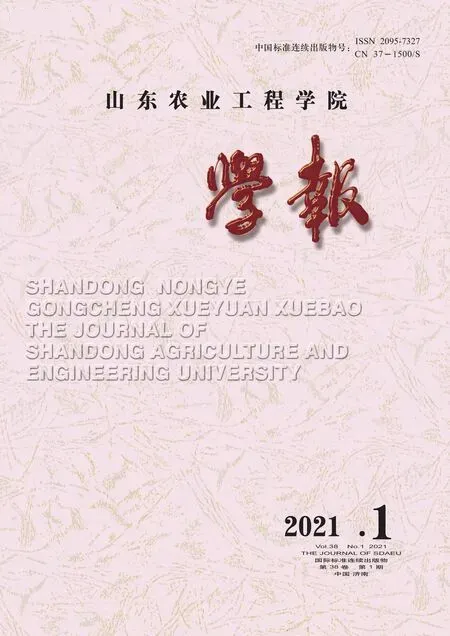发展中大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特点探析
——以印度、埃及、巴西和前苏联为例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50)
“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的普遍现象,研究发展中大国现代化中的“三农”问题,能够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本文将着重考察南亚最大国家印度、西亚北非阿拉伯大国埃及、拉丁美洲最大国家巴西以及地跨欧亚的前苏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特点。
1 印度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印度是南亚面积最大、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人口总数位居世界第二,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和金砖国家,是亚洲耕地面积最广的国家,光热充足,降水丰沛,地表径流与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分配不均,旱涝灾害非常频繁。除山区和沿海平原外,北部的恒河平原与南部的德干高原是印度最为重要的地理单元。印度农业农村现代化始于18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统治初期,已历经两个多世纪,其主要特点是:
在土地制度方面。在1947年独立以前,印度长期盛行种姓制度,多神崇拜纷繁复杂,北方频繁遭受异族入侵,村社制度一向坚韧,所以在政治上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很难实施整齐划一的土地制度。印度独立后,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重视保护私有地产,土地改革法通常强调和平赎买超额土地并稳定农业租佃关系。另外,独立后的印度没有实行中央集权制和总统制,而是采取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与议会制政体,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较大制约,在实施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受到城市柴明达尔、农村地主和无地少地农民多方掣肘,多次土改尝试收效不大。1972年春印度计划委员会所设土地关系组全面考察土改结果,继而认定:印度独立后的土改基本失败,主要原因是:各地当政者缺乏土改意愿;基层民众对当政者施压不足;中央政府未能恰当地协调各地当政者与基层民众;民法、刑法和司法机构过分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土改实施机构缺乏财力;土地档案提供的相关数据普遍过时而且不够准确。[1]
在农业现代化领域。印度独立后,长期实施以土地改革(参见前述)和农业合作化为重点的“制度战略”和以“绿色革命”为中心的“技术战略”。
一是农业合作化的“制度战略”。早在20世纪前期,英印殖民当局就在1904年、1912年和1942年制定并修改农业合作社法。1947年印度独立后,执政的国大党和尼赫鲁政府积极推进农业合作化。1948年1月,尼赫鲁任主席的国大党经济计划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占地较多的农户可兴办“家庭农场”,占地较少的农户可建立“合作农场”,使非盈利性的农业合作社取代横亘在直接耕作者和政府之间的所有土地中间人,具体做法是政府规定占地限额,征收超额土地并转交农业合作社经营。根据上述报告,同年12月,国大党年会表决通过相关决议,国大党土改委员会的J.C.库马拉帕指出:如果“没有各种合作模式”,“农业的有效性就不可能有实质性地提高”[2]。1954年1月,国大党年会通过的决议强调,在印度村社和自愿联合基础上发展农业合作社经济,这是土改的重要目标。[3]1959年,国大党年会通过决议,再次强调推进农业合作化,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实行土地联合经营,在分配农业收入时综合考虑土地要素和劳力要素投入[4]。在英印殖民当局和印度政府的推动下,印度农业合作社已涵盖超过三分之二的农户,主要涉及肥料、奶业、糖业、小麦、仓储等领域。以肥料和奶业合作社为例:2007—2008年,肥料合作社生产化肥584.7万吨,销售化肥932.4万吨;生产生物肥料415.15吨,销售生物肥料432.22吨。奶业合作社联合会分为村级、区级和邦级三种,既共同负责向奶农提供质优价廉的饲料,又分别负责收集牛奶、冷冻和加工牛奶、销售牛奶及奶制品三个环节,推动了奶业产业化,降低了奶农成本,有助于维持销售价格,从而提高了奶农收入。[5]
二是绿色革命,这是印度在农业领域推行的“技术战略”。除继续兴修水利外,印度政府重点采取以下三种举措。第一,推广种植高产粮食作物。印度独立后,效法苏联实施五年计划,在1961—1966年“三五”计划期间,在约一千万公顷耕地上广泛种植高产作物,主要推广喜肥、耐旱、抗倒伏、产量高、生长期短的粮食作物。“四五”计划期间,高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继续扩展,到1969年,全部高产粮食作物面积近2300万公顷,其中高产小麦种植面积达1184万公顷,高产水稻种植面积达662万公顷,高产高粱种植面积达171万公顷,高产玉米种植面积达96万公顷。高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印度粮食产量。1969—1970年,印度粮食总产量增至一亿吨,比1950—1951年增加一倍,其中从墨西哥引进的高产矮秆小麦产量达2000万吨。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产小麦在较为干旱且盛行面食的印度西、北方成为主要农作物,高产水稻则在较为湿润且喜爱米饭的东、南方逐渐推广,小麦和大米产量继续增加。到1999年,印度小麦产量高达7100万吨,大米产量增至1.12亿吨,全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亿吨,粮食问题得到有效缓解[6]。第二,增加氮磷钾化肥的用量。“四五”计划末期,印度钾肥用量达17.6万吨,比1961—1962年度增加五倍多[7];磷肥用量达40.8万吨,比1966—1967年度增加一倍多;氮肥用量达120万吨,比1966—1967年度提高近一倍。[8]肥料合作社发挥巨大作用。2007—2008年,肥料合作社生产化肥584.7万吨,销售化肥932.4万吨;生产生物肥料415.15吨,销售生物肥料432.22吨。[9]第三,增加农药用量。绿色革命期间,印度政府积极推广使用杀虫剂,以提高粮食产量。印度农药喷洒面积从1956年的约600万公顷增至1968—1969年的近一亿公顷,扩大近十六倍。[10]然而,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也在加重印度农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2 埃及的农业农村现代化[11]
综观现代埃及特别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笔者发现农地制度、农产品市场化、粮食问题、村民流动与乡村政治参与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
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农地制度对农产品市场化具有重大影响。土地国有制或限制私有化必然意味着由埃及政府主导农产品市场化,而土地非国有化与鼓励私有化则往往表明土地所有者将掌控农产品市场化,特定的土地制度总是与农产品市场化的主导权联系紧密。粮食生产能力不足系粮食问题的表现之一,而土地制度作为农业生产关系的核心要素能够对粮食生产能力造成间接影响。土地制度对村民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穆罕默德·阿里政权和纳赛尔政权恢复土地国有制或建立土改合作社,由此实现对小农人身自由的有效控制,进而阻碍乡村居民的人口流动;赛义德和伊斯马仪政权大肆征收苛捐杂税并且推动土地非国有化,迫使大量小农背井离乡,这客观上有利于乡村居民的人口流动;而1882—1952年与1970—2013年埃及政府通过废除徭役制度或弱化合作社功能,逐渐放松对乡村居民的人身控制,从而为乡村居民的人口流动创造条件;乡村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趋势与农业用地的占地不均,也往往构成村民流动的重要因素。农地制度也对政治权力产生重大影响。在农业时代,农业既是主要财源,亦为政治地位的主要支撑,大土地所有者由此掌握多数社会财富和巨大政治权力;在工业化亟需全面推进的时刻,自由军官组织利用耕地占有严重不均的现状,采取大刀阔斧的土地改革举措,依靠小农和中等地主压制在外地主和王室贵胄;在工业昌明时代,土地资源日渐稀缺,地租和地价呈现上涨趋势,地主的参政愿望和政治势力也将随之上升。
农产品市场化意味着农产品可被迅速转化为货币财富,进而为农业扩大再生产、工业建设、文化传播和争权夺利提供物质基础。追逐农业剩余的本能冲动,要求地主等经营主体掌握生产自主权,而经营主体若要掌握生产自主权就必须获得足够的土地权利和充分的人身自由。因此,农产品市场化开始对土地制度和村民流动发生重大影响。农产品市场化对土地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穆罕默德·阿里政权和纳赛尔政权极力限制乡村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以便掌控农产品市场化的主导权,进而占有全部或大部农业剩余;或者表现为,穆罕默德·阿里后裔统治时期的地主阶层试图实现土地非国有化,以及共和时代的地主阶层极力打破土地改革所造成的地权现状,从而掌握农产品市场化的主导权,同时推动更多耕地进入流通领域成为特殊商品。正是在农产品市场化的影响下,在外地主才能够寓居城市,而地权斗争也比传统社会激烈得多。满足市场需求的外部压力能够刺激经营主体适时调整播种结构,而粮食问题的产生恰恰与其他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减关联甚大。农产品市场化对村民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农产品市场化引发种植结构调整与区域农业分工,进而导致部分村民在一定时节流、向其他乡村从事摘棉或垦荒等农业劳动。
1952—2013年,埃及食品补贴制度逐渐完善,食品补贴数额不断上升,小麦和面粉始终构成食品补贴的重点内容。埃及的食品补贴制度,对农业生产和政治参与具有重大影响。埃及的食品补贴制度,减少农民所获利润,剥夺他们积累资本进而改进技术的潜力,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导致小麦长期短缺与品质低劣;食品补贴制度使市民的消费欲望空前膨胀,浪费现象空前严重,并固化城乡之间与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和权力格局。埃及的食品补贴制度,还会强化埃及的极权政治。
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劳力构成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村民流动则直接决定农业劳力的供给状况,进而影响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给、流通和消费。村民流动对土地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影响比较复杂,迄今没有定论。
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权力往往决定农地制度。埃及乡村居民的土地所有权,其合法性往往仰赖政府的默许或者恩赐,具有明显的不稳固性。在埃及外患严重且统治者力量强大之时,政治权力需要整合社会资源也能够排斥政治参与,往往限制农村居民的土地产权,以便独享农产品出口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如果埃及外患减轻或者统治者力量孱弱,地主阶级往往能够扩大政治权力,进而凭借政治权力加速地权私有化和土地兼并,国家则默认甚至支持这一趋势,以便取悦地主阶层。无论中枢权力强弱与否,小农都居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无法通过政治权力维护自身利益。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埃及农产品贸易垄断制度与极权政治具有共时性。简而言之,极权政治构成农产品贸易垄断制度的政治前提,而农产品贸易垄断制度则成为极权政治的重要物质基础。不仅如此,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央集权衰落也呈现共时性。粮食问题的另一表现在于食品补贴制度刺激城市居民的过量消费,而食品补贴制度深刻说明城乡居民政治参与的高下之别。乡村阶层与埃及市民和埃及政府的政治力量对比。直接影响城乡的经济社会差距,进而影响乡村居民进城打工;乡村居民能否出国务工,受制于埃及政府的对外政策,仰赖埃及村民政治地位的提升。
现代埃及的“三农”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根源。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其主要成因并不在于自然环境恶劣或科技水平低下、人口增长过快,而在于现代化这一特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政治权力分配不均,特别是政府与国民、城市与乡村、地主与小农、精英与民众在权力资源方面的巨大差距,具体表现为开罗和其他地区的差距、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工商业和农副业的差距、下埃及和上埃及的差距、以及尼罗河流域与非尼罗河流域的差距。从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就任总督到2013年穆尔西总统离职,埃及政府或建立土地国有制进而剥夺小农的土地所有权,或推动地权私有化进而纵容土地兼并,或推广土改合作社进而侵蚀小农对耕地的经营权和用益权,由此达到限制小农产权、控制乡村民众和转移农业剩余的多重目的。至此,即便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小农土地所有制也已沦为马克思笔下“徒有其名”的“所有权”[12]或曰“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13]。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时期,政治民主尚未实现,政府、城市、地主和精英在权力格局中占有优势地位,而小农则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政治权力分配不均,而政治权力在资源分配中依旧占据主导作用,由此导致土地资源的占有状况并不平衡,进而构成“三农”问题生发并延续的深层政治背景。埃及民主水平提高和小农政治参与扩大,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3 巴西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巴西是拉丁美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和金砖国家,在自然地理方面拥有多项第一,农业发展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巴西幅员辽阔,国土面积约851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热带面积最大的国家,光热充足,降水丰沛,地表径流与地下水资源极其丰富。除东南沿海狭小平原以外,北部的亚马孙平原和南部的巴西高原是巴西最为重要的地理单元。亚马孙平原地处赤道附近,是世界上最大的冲积平原与最大的热带雨林分布区,光热、水土、森林、生物资源首屈一指,未开发的可耕地面积可观;亚马孙河是亚马孙平原的塑造者,中下游贯穿巴西北部并注入大西洋,是世界最长、流量最大、流域最广的大河,为亚马孙平原提供了便利的内河航运条件与淡水资源。巴西高原位于亚马孙平原和亚马孙河流域南侧,地势平坦,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热带草原气候塑造了稀树高草的典型植被,已开发和未开发的草场面积广袤,畜牧业发达且潜力巨大。巴西极其优越的自然禀赋,使其成为类似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农业强国,出口的蔗糖、玉米、大豆、咖啡、可可、香蕉、柑橘及浓缩橘汁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被赞为世界粮仓之一。
巴西农业农村现代化始于19世纪初期的独立运动,已历经近两个世纪,其主要特点是:
土地制度方面。巴西乡村盛行大地产,这种状况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葡萄牙殖民时代。早在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人航海远来时,即将巴西分割为13块贵族封地。[14]巴西宣布独立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大地产继续发展。[15]到1920年,巴西土地普查数据表明,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地主拥有全国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三。[16]在1960年,大农场仅占全国农场总数的不足4%,却拥有全国土地面积的62%;相比之下,小农场占全国农场总数的35%,却仅拥有不足2%的土地面积。[17]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占地超过一千公顷的大地主,仅占全国人口的不足1%,却拥有全国土地面积的44%;相比之下,占地不足10公顷的小农,占全国人口的53%,却仅拥有不足3%的土地面积。2017年农业普查数据表明,占巴西人口0.1%的大土地所有者竟拥有47.5%的耕地面积。[18]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当代巴西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土地私有制,并未历经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或革命,较多地保留了葡萄牙殖民统治时代的大地产;地广人稀,而且农村人口比重较小。因此,巴西村民人均耕地面积广阔,但耕地高度集中,私人大庄园与农业雇佣关系十分典型。
在农业现代化领域。由于自然禀赋优越、大地产制盛行和出口贸易导向,巴西的热带经济作物大种植园异常发达。以甘蔗种植为例:在葡萄牙殖民时代前中期,巴西的甘蔗种植园面积广袤,蔗糖产量增长迅猛,一度跃居全球第一。2008年,巴西甘蔗的播种面积为800万公顷,产量为6.5亿吨;到2014年,相关数字增至1100万公顷和 7.5 亿吨。[19]近年来,巴西蔗糖出口量稳居世界首位。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在农业基础设施领域,巴西的短板在于交通运输业落后。2018年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中,巴西仅排在第 56位[20]。在公共服务领域,巴西较早建立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险体系,将社保支出视为政府应尽的义务,并且不断扩大其覆盖面。从1923年起覆盖国有和大型私营企业的工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涵盖全体城市工人[21]。20世纪70年代前期,巴西一方面将农村鳏寡孤独废疾者纳入社保体系,另一方面又规定只要是务农满20年且家境贫困的农村劳动者,无论是否已经缴纳社会保险金,凡65周岁以上的男性与60周岁以上的女性,一概被纳入社保体制特别是养老保险体系,按月领取约相当于一半最低工资标准的少量生活费,养老基金源于税收等财政收入[22]。1988年,巴西新宪法提高农业劳动者领取的养老保险金额,并下调领取者的年龄门槛,降至男性 60 岁、女性 55 岁[23]。
在农业剩余劳力转移方面。巴西城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农村生活水平通常不及城市,例如在教育领域,2017年巴西国家经济地理统计局农业普查结果显示,15.5%的农民是文盲,63.6%的农民仅仅受过基础教育。大地产发达,大量村民并非土地所有者,2017年巴西国家经济地理统计局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占巴西人口0.1%的大土地所有者竟拥有47.5%的耕地面积,因而大多村民渴望流向城市。[24]另一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巴西并无城乡户籍差异,村民可以自由迁徙到城市,并可在城市贫民窟暂时栖身。因此,巴西的城市化进程快于中国,城市常住人口比重远高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
4 苏俄—苏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发展跟不上,农村发展跟不上,农产品供应不足,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其深层次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25]。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暨面积最大的国家——苏维埃俄国与苏联就是如此,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和制度变革曾留下惨痛教训。
4.1 题解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前身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与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是主要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农民是主体人口,农村是主要聚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极端重要。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强调:“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26]十月革命后,俄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部门。”[27]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22年12月成立,到1991年12月解体。因此,本书论述的苏俄—苏联乡村农业现代化,特指从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俄国的乡村农业现代化,主要涉及土地制度和粮食问题,而这两个领域紧密相连。
4.2 沙俄农奴制改革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数百年,沙皇圣旨与国家法令残酷剥夺小农的择业和迁徙权利,严禁他们放弃农业生产和随意离开村社,将稀缺劳力固着于广袤土地之上,强制实现劳动力和劳动对象的紧密结合,进而确保农业产量和国家税收。俄国村社土地所有制则构成上述超经济强制的物质基础。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开始驶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但是,从农奴制改革开始到1905年革命前,沙皇以所谓“村社之父”自居,极力染指村社事务,企图通过控制村社进而奴役农民,终极目的在于扩大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进入所谓“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斯托雷平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下,在政治上中断民主化进程,在经济上加速自由化进程,将村社土地私有化并允许农民退出公社,“由维护‘畜群式的’农村公社急剧转变为‘强者的’私有化”[28]。 1917 年二月革命后,沙皇制度成为历史陈迹,俄国临时政府宣布废除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举措。
4.3 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的土地制度与粮食问题
十月革命后初期,苏俄在1918年1月27日发布《土地社会化法令》,明确规定要大力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认为“这种经济在节约劳动和产品方面都更为有利,减少个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29]。在当时,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实际上意味着复兴村社,意味着继续清算斯托雷平时期的土改后果,特别是打击斯托雷平改革期间出现的地主。
1918年春,苏俄开始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持续到1921年初。在乡村农业领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表现在取消一切商品交换,强制实行余粮征集制和口粮配给制,并以行政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和改变土地占有格局。苏俄内战结束后,全俄已经没有地主阶级,在全俄农户总数中,中农和贫农户数占96%,而列宁所称的“小富农”仅占4%;在全俄耕地总面积中,中农和贫农占 94.5%,“小富农”仅占 5.5%。[30]由此可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苏俄内战影响下,苏联乡村的土地经营已经相当分散,所谓“小富农”与中农和贫农只有细微差别。随着土地经营的变迁,粮食生产和占有状况也在改变。此时“地主经济……已经被消灭、富农经济……已经缩小三分之二以上”,“不仅从粮食总产量来看,而且从商品粮食产量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已经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农已经成为农业中的‘中心人物’。”因此“粮食生产已经从地主富农方面转到小农中农方面”[31]。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地区,农用土地所有权名义上归村社,经营权归农户,用益权归布尔什维克和苏俄政府,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土地国有制。
4.4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苏俄内战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且遭到激烈抵制,于是列宁和联共(布)开始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乡村农业领域以降低的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恢复粮食贸易,废除口粮配给制。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俄国农用土地所有权归村社,经营权和用益权归农户,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内战后,面对新的土地经营状况和粮食形势,列宁的思路出现变化。1921年初,列宁写道:“农民的‘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否可怕?他们的‘自由贸易’是否可怕?不可怕。”[32]1923 年 1 月,重病中的列宁口授《论合作制》一文,明确指出,涉及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农业合作社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33]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继续实施。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苏联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播种面积逐渐扩展,农业产量得以恢复。1925年,苏联播种面积达到一战前夕的99.3%,谷物产量比一战之前五年的平均产量高出11.2%,种植业总产值比一战前夕增加7%;同年,苏联除马以外的牲畜总头数超过一战期间1916年的规模。[34]随着农业产量的提高,苏联农民的粮食消费量有所上升,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新经济政策固然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小农生活水平,却没有改变工业品与粮食间的价格剪刀差,导致农民普遍惜售粮食。如果进行物物交换,650公斤燕麦的购买力,在一战前夕的1913年相当于2100公斤食盐,而到1923年则仅相当于410公斤食盐;因此“粮食在农民可能出卖的一切物品中成为最无利可图的东西了。”[35]
4.5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及其教训
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土地改革不仅取消大私有,也取消农民的小私有,“实际上是一场彻底的村社化”[36]。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俄国村社化,具有强烈的自治倾向和明显的内聚特征,天然地具有排斥联共(布)与政府的力量。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斯大林日益巩固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苏联的农业政策再度出现重大转向,新经济政策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农业集体化,联共(布)和政府通过控制集体农庄来操纵农民并提取农业剩余。1927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认为农业发展过于缓慢,而原因之一就是小农的狭小地块与分散经营。他强调:“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作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37]1928年1月至2月,斯大林视察西伯利亚粮食产区,宣布加速农业集体化进程:“第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个体农民联合为集体农庄。第二,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农民。”[38]1928年7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解释,苏联必须实现工业化,而这需要大量“内部积累”,这种积累必须从农业提取,为此国家需要压低农产品价格并抬高工业品价格。“这是为了发展……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类似贡税”“类似超额税”[39]。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指出:“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他兴奋地表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40]同年12月斯大林指出:“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势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41]1929年无疑是决定性的一年。斯大林回顾:“从一九二九年夏季起,我们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开始了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方面的转变。”[42]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表决通过决议,即《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详细规定各地农业集体化的形式,并要求1930—1931年在四分之三农村实现集体化。1931年8月2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即《关于加快集体化速度和巩固集体农庄的任务》,提出只有将68%~70%的农户与75%~80%的耕地加入集体农庄,才算完成农业集体化。在斯大林和联共(布)极力推动下,农业集体化在之后几年内迅速实现。1932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有62.4%,并入集体农庄的耕地超过80%;到1937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达93%,并入集体农庄的耕地达99%。[43]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继任领导人曾对集体农庄制度进行细微改革。例如,赫鲁晓夫曾发起垦荒运动和玉米运动,以扩大播种面积和提高粮食产量;勃列日涅夫曾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并提高集体农庄成员待遇,以保障农户的生活水平。两位领导人还曾扩大集体农庄的产销自主权。[44]但是,集体农庄制度直至苏联解体时依然存在,而且在后斯大林时代,集体农庄的公有化程度和范围一度得到扩展,农业领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始终未曾改变。
农业集体化的实质是,土地等全部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名义上归集体农庄,经营权和用益权实际上掌握在推行指令计划的国家手中。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后,确实提高了机械化水平、扩大了播种面积,却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农业集体化消灭土地私有制和家庭经营制,摧毁村庄原有的自治倾向和内聚特征,违反自愿和渐进原则,完全剥夺农户的产销自主权,使农业剩余长期流向工业和城市,从而严重打击农户的积极性,导致农业产量增长乏力,甚至出现多次严重饥荒。农业集体化将农民固着于集体农庄之内,成为所谓的贡税承担者,妨害农民的自由迁徙,事实上恢复了农奴制。农业集体化遭到多数农户的强烈对抗,而斯大林与联共(布)又将这种对抗视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从而给予严厉打击,造成大量农民死于非命。殷鉴不远,极其沉痛。
5 总结
农民的自由度扩大,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共性,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共性,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所有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共性,是地理大发现以来几百年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当代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两国均为发达国家,且其人口、农业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还不及中国的一个零头。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农业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的“超级大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无先例可循,也有极大难度。即使有朝一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90%,中国仍将有过亿人口常住农村。由此可见,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开创性、艰巨性、长期性和战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