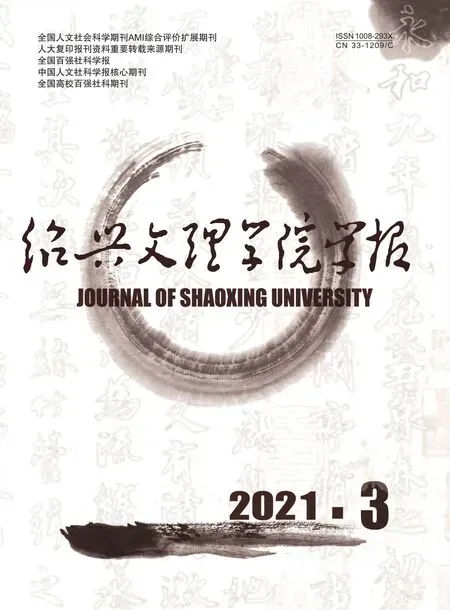越剧海外剧场翻译研究
——基于洛杉矶越剧团演出录像的分析
陶丹丹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越剧作为综合性的现代剧场艺术,以感召心灵的精神价值、雅俗共赏的审美取向、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承担着传播中华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重大使命。剧场翻译使越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在目的语语境中获得新生,对提高越剧的可交流性、促进越剧观众的多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越剧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化的文化交融开辟有效途径。然而,越剧海外传播虽已走过60多年的历程,但是其海外剧场翻译还有待改进和创新,国内不少越剧团的海外演出资料仍然缺乏质量保障[1]56。相较而言,一些海外越剧团的文本生产机制更加成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洛杉矶越剧团。剧团于2013至2019年在美国鲍德温公园市演艺中心公演了54出越剧折子戏,通过中美合作的模式翻译了演出字幕、报幕、海报、戏单等剧场文本,并将演出录像发布在剧团网站[2]和目前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平台YouTube上。本文将结合剧场翻译理论对部分演出录像进行分析,旨在探究剧场翻译在传播越剧价值内涵上的规律性,为越剧翻译理论的构建拓宽思路,也为越剧海外剧场翻译实践提供借鉴。
一、剧场文本及其翻译特点
西方戏剧学经历了从“剧本(drama)研究”到“剧场(theatre)研究”的转型[3]58。法国戏剧理论家帕特里斯·帕维斯(Patrice Pavis)曾提出,戏剧翻译研究应集中在舞台表演层面的戏剧译本上,而非一般文学意义上的戏剧译本[4]41。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对戏曲翻译进行研究,也需考虑翻译文本与剧场表演的关系,加强与剧本翻译研究的区分度,突显戏曲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本质。
与注重文学性的剧本之作相比,剧场之作注重整体性的追求。剧场除其空间意义外,是充满“诱意”与“解放”的艺术的“场”,是一个由剧本、表演、舞美及观众的反馈等因素共同营造的艺术整体[5]9。各种艺术符号协调创造,在观演的互为主体中,形成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往复。剧场文本观意在突出戏曲的舞台性、表演性,认为应将戏曲视为“立”于舞台上的“活”的艺术,因此比剧本文本观更能体现戏曲的本质。剧场文本观还认为,观众是剧场的一个有机因素,剧场文本不是单向度地取悦或教化观众,而是通过演员和观众双方的互动,调动观众主动参与到戏曲艺术的整体创造之中。这种戏曲文本观是对剧本文本观的积极扬弃,强调对剧场整体意蕴的挖掘。
同样,剧场翻译也有着不同于剧本翻译的特点。剧本翻译倾向于“深度翻译”,通过添加大量注释,或配以导读、鉴赏或评析性的文字,最大化地保留原作的语言形式和文化信息,帮助目的语读者构建理解剧本所需的知识框架。剧场翻译不再视原文神圣不可侵犯,考虑到剧场文本的特点,对原文的“某些叛逆是必须的”[6]1。首先,剧场文本具有瞬时性,译文须在最短时间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因此,在保留原剧中心意旨的前提下,译文通常作浅化处理。其次,剧场文本通过“高密度的符号”生产“复调式的信息”[7]5,译文的简洁也是因为语言以外的多重符号可以对译文进行补充,使剧作之“意”的阐释与舞台之“象”的呈现相互交融,在“象”与“意”的互补中传播戏曲的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再者,剧场文本要遵守接受系统的演出习俗,适应目的语观众的接受能力,还要符合具体剧院的要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一些语言成分进行适应性改造或创造性改写。正如爱尔兰翻译家、剧作家大卫·庄士敦(David Johnston)所言,表面“忠实”的翻译可能经常使一出外国戏剧拙劣无趣,如同从背面看一块土耳其挂毯一样黯然失色[8]9-10。可见,“忠实不美,美不忠实”是对剧场翻译特点的经典概括。
二、越剧海外剧场翻译的多层语境
剧场翻译叛逆性的背后潜藏着一系列的语境因素。剧场交流可被视作在特定语境下,人们运用多种符号资源建构意义的过程。意义的生成受到文本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制约。将这些因素按照不同层级进行分类阐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剧场翻译研究的主观性,使剧场翻译研究具有可观察性、可描述性和可论证性。越剧海外剧场翻译的语境因素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宏观层面的文化语境
越剧海外剧场翻译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制约。一方面,需要考虑新时代我国的文化战略。自我国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国家文化政策不断加大对戏曲海外交流的支持力度,积极拓展地方剧种的海外演出市场,推动戏曲作为中国文化的金名片走向世界。越剧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9]。越剧对外翻译是为了弘扬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完成跨文化的国家形象和民族身份建构。另一方面,这种在目的语文化以外策动的翻译活动,必须关照目的语文化的需求或期望。历史上无数的翻译实践证明,不符合目的语文化需求或预期的译作很难为之接受。在西方戏剧系统中,越剧尚处于边缘位置,欲穿越中心文化接受的屏障,越剧海外剧场翻译不能囿于本国文化立场和视野,也要从西方文化视角出发思考越剧之于西方文化的价值,西方观众对待越剧艺术的态度等问题。翻译时应更多关注越剧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传播,而非译文和原文形式上的一致性,才有可能使这种与西方迥异的艺术为西方观众理解。
(二)中观层面的情景语境
越剧海外剧场翻译也受到传播方式、媒介技术等情景因素的限制。传播方式不同,翻译策略也不同。目前越剧海外传播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演出原汁原味的越剧或展映越剧电影,同时提供外语剧情介绍。译文通常按照西方戏剧的叙事逻辑进行重构。二是在第一种传播方式基础上,提供唱词念白的外语字幕。字幕译配受到时空限制:时间限制是指字幕的出现要和唱词念白同步;空间限制是指字幕投影设备有字数限制,译文要精炼、明晰,避免分散观众注意力。三是演员配合越剧唱腔,用外语演唱越剧。译文要满足唱词的音乐性,调整译文语言的音韵,尽量合入音乐曲调。在使用同种传播方式时,媒介技术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起到关键作用。以字幕译配为例,早期的剧场字幕显示在舞台上方字幕屏中,后来不少剧院将字幕屏置于舞台两侧暗区,有的剧院还配有覆盖整块舞台背景的字幕屏或在观众座椅背面安装了小型字幕屏。2015年阿维尼翁艺术节上出现了一项新技术:用智能眼镜观看戏剧表演。智能眼镜可以将文字、图像叠加在眼前并描述舞台上的对话或声音效果,还可以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观众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字幕语言、字体大小、颜色和位置。这项技术使观众在剧院的任何位置都能舒适、自由地观赏戏剧、阅读字幕,提升了戏剧表演的可访问性和剧场体验[10]138。字幕屏的尺寸及其与观众的距离、字幕是否可调节等技术参数直接影响到观众注意力的集中方式,进而影响到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
(三)微观层面的美学语境
越剧海外剧场翻译还受到中西方戏剧美学思想的影响。越剧表演有鲜明的审美特色,融合了写意与写实的表现手法。写意是指越剧继承以歌舞化、虚拟化、程式化为特征的中国戏曲传统,注重对形式美的提炼,追求总体上的意境和神韵。写实是因为越剧吸收了话剧、电影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重视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刻画,赋予人物鲜明的个性色彩和强烈的情感色彩,以真情实感打动观众。对形式美的追求使越剧富含韵律节奏、清辞丽句、诗情画意,语言具有音乐性、说唱性和抒情性。不同于中国戏曲的意象论,西方戏剧的美学根基为摹仿说,认为戏剧艺术必须描摹和反映生活的真理,因此更偏重于写实的传统。西方戏剧表演以生活化的言语、动作来展示剧情,讲究情节的曲折和冲突的尖锐,强调表演中理智的参与。对真实性的追求使人物对话在西方戏剧表演中占有重要地位,语言具有逻辑性、精确性和思辨性。但无论是表现表演之美还是情节之真、注重以情感人还是以理服人,诗意的核心或内涵意蕴共同存在。这就意味着翻译时要在矛盾的两端之间找到统一性,既要充分再现越剧的美学特征,也要兼顾西方观众的审美意趣。
三、洛杉矶越剧团剧场翻译的多维策略
在多层语境制约下,越剧海外剧场翻译也必然经历一定程度的叛逆。洛杉矶越剧团的剧场翻译实践可作为典型个案加以证明。剧团成立于2003年,由美籍华人越剧演员和在美的越剧爱好者组成,以专场演出和学术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传播越剧艺术,这不仅增强了当地华人社区的凝聚力,而且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2013年,洛杉矶越剧团获得美国加州州政府及当地政府的奖励,以表彰剧团对于传播中华文化艺术、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剧团在美国公演了《追鱼·书馆》《打金枝·闯宫》《张羽煮海·听琴》《西园记·夜祭》《蝴蝶梦·圆梦》《柳毅传书·湖滨惜别》等越剧折子戏,演出时保留越剧的原汁原味,并提供中英文剧情梗概和唱词念白的字幕,还有中美主持人进行双语报幕。考虑到剧场翻译的语境因素,剧团从下列五个维度出发选择翻译策略,对原文本进行了适应性改造或创造性改写。
(一)叙事建构
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一种再叙事。每当一种叙事版本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总是会在新语境中被注入其他叙事元素,目的是要突出或抑制原文中隐含的叙事,从而操控人们对当前叙事的解读。洛杉矶越剧团在剧场翻译时采用的叙事建构策略主要有“标示性建构”[11]187和“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11]173。
标示是指用来指示或识别人物、地点、事件及叙事中其他关键元素的词汇或短语。越剧剧目就是非常有力的标示性建构手段。例如,《追鱼·书馆》这场折子戏剧目用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标示,英译时却用事件代替地点,将“书馆”改写为The Romantic Encounter(浪漫邂逅)。改写后的译文符合西方戏剧重情节的美学观,同时将鲤鱼精和书生张珍之间的真挚爱情前景化,为观众了解剧情提供了一个诠释框架。除了突出情节之外,越剧剧目翻译有时还会强化冲突。以《打金枝·闯宫》为例,原剧名“闯宫”强调驸马爷郭暧的单向行为,这个标示经过改写后被译为Argument(争吵),突出郭暧与升平公主之间的矛盾,进而将观众引向两人争吵的根源:民间道德与皇家礼法之间的冲突。译文既简洁明了,又与西方戏剧讲究冲突的美学语境相契合,能够吸引西方观众的注意力。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是通过添加或删除一些叙事元素实现的,常用于越剧剧情梗概的翻译。《张羽煮海·听琴》的剧情介绍中有这样一个句子“琼莲舍颌下骊珠,救其生还。”这句话在英文版本里对应的是“To save Zhang Yu’s life, Qiong Liangave up her human appearanceby losing the pearl under her jaw.”。“骊珠”是骊龙颌下的珍珠,若仅将其翻译成pearl(珍珠),不足以充分展现龙女琼莲为爱牺牲的精神。译文通过添加画线部分信息,意为“舍弃人形”(下画线为笔者所加,下同),强化了这种牺牲精神,此处的适应性改造对呈现追求婚姻自由的叙事立场起到推进作用。此外,考虑到剧场文本的瞬时性和字幕译配的时空限制,对传递越剧价值内涵关系不大的次要信息,翻译时通常作删除处理。简言之,在不背离原剧中心要旨的前提下,译者可以有选择性地参与叙事建构。
(二)语用对等
“对等”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分类,安东·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对等:语言对等、词形对等、文体对等和语篇对等;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阿尔布雷希特·诺伊贝特(Albrecht Neubert)认为对等包含语义对等、句法对等和语用对等;蒙娜·贝克(Mona Baker)将对等细化为五个层次,位于第五层的是语用对等。概括起来,对等主要涉及语言结构形式和语言使用效果两方面。语用对等关注的是语言使用效果,意指特定语境中话语内涵义的等效传递,从而使目的语受众获得类似源语受众所获得的感受。
出于越剧海外剧场翻译的交际目的,语用对等优先于其他层次的对等。剧场翻译必须联系观众,为了适应西方观众的理解和欣赏能力,译者应当根据语境,将原作中人物唱词和念白的语用意义用目的语恰当地表达出来。例如,《西园记·夜祭》里的丫鬟香珺有这样一句念白“这真是冬瓜缠在茄棚里”,她以为书生张继华把她当成她家小姐了。洛杉矶越剧团的译文是“Ha, he completelygot hold of 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画线部分习语的字面意思是抓住棍子的错误末端,语用意义是指搞错、完全误解,配合语气词Ha(表示惊讶)的使用,产生了与原文对等的喜剧效果,能够拉近与目的语观众的距离。同样,越剧唱词中的成语也可以译作对应的英语习语。《蝴蝶梦·圆梦》有唱词为“真王孙若无假,也算得百里挑一难寻求”,其中的成语“百里挑一”形容人才出众,对应的译文是the cream of the crop,常用来指精英、佼佼者,因此,译文传达了等效的语用含义,另外,这个习语押头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给观众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语用对等还可以通过转换意象来实现。唱词“我弱水三千舀一瓢饮”(《蝴蝶梦·圆梦》)被译作“You are the only beautiful rose in my eyes in this colorful world.”(在我眼中,你是这个多彩世界中唯一一朵美丽的玫瑰)。“弱水”比喻爱河情海,原文是说情爱心意很多,但我只取其中之一,译文用“玫瑰”意象进行替换,因为玫瑰在中西方文化中都象征忠贞爱情,这种创造性改写使西方观众能像源语观众那样理解和欣赏原唱词。
(三)文化适应
芬兰戏剧翻译研究者萨库·阿尔多伦(Sirkku Aaltonen)指出,在当代西方剧场中,他国戏剧的译作并不是为西方观众看见他者而打开的窗户,而是几乎成为让他们看见自我的镜子,因为那些熟悉的片段让观众感觉更为安全[12]52。文化适应就是通过融合熟悉事物和陌生事物,淡化异质文化色彩的翻译策略。除了受到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关系制约外,文化适应也是考虑到剧场文本的瞬时性以及字幕译本的时间、字数和技术限制。鲍德温公园市演艺中心的字幕显示屏位于舞台两侧暗区,译文如果太长,容易分散观众注意力,因此,剧场翻译不能像剧本翻译那样,通过添加注释的方式来传递源语文化内涵。
文化适应通常表现为借用西方观众熟悉的文化概念进行二度阐释。以《柳毅传书·湖滨惜别》为例,洛杉矶越剧团在其英文版剧情介绍中,将柳毅类比为Samaritan(撒马利亚人),柳毅急人所难、千里传书救危,撒马利亚人路遇一个被强盗打劫、身受重伤的犹太人,不顾教派隔阂帮助他,两者都有见义勇为的精神气概,这也是中西方价值的共通点,译文既传播了重信义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又联系了西方宗教文化,促进了越剧思想内涵的跨文化阐释。类似的例子还有:将神话剧剧目《追鱼》译成Mermaid Legend(美人鱼的传说)。虽然鲤鱼精和美人鱼的外在形象不同,但都是真善美的化身,她们为了追求爱情,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是相通的。译文通过创造性改写,激活了西方观众的认知结构,减少了文化干扰。再如,《西园记·夜祭》唱词“不烦月老牵红线”的英译是“no need to borrow Cupid’s arrow.”(不需要借丘比特之箭)。月老以牵红线来匹配姻缘,爱神丘比特用利箭射中情侣。译文回避了月老典故的出处,使用西方观众熟悉的文化概念,让他们产生相应的文化联想,有助于他们快速理解唱词的文化内涵。
(四)情感显化
越剧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体现情感浓聚的性格色彩。西方戏剧则更加注重理趣,强调理智对情感的主导作用。在不同的美学思想影响下,目的语观众和源语观众的情感反应也可能大相径庭。如何让目的语观众重温源语观众的情感体验是越剧海外剧场翻译的又一大挑战。为此,译者需要从目的语观众的角度出发,设法构建有可能产生相似情感的译作语境,并对剧中人物的情感进行显化,从而使目的语观众在跨文化意义上做到情感投入,最终建立和发展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显化人物情感的一种策略是在译文中添加指示语和情感副词。指示语又被称为语境化线索,不仅表明演员与舞台的关系,而且是连接身势语和话语的重要桥梁[13]65,还对舞台人物塑造起到决定性作用。越剧《打金枝·闯宫》讲的是唐汾阳王郭子仪寿庆,幼子郭暧因妻子升平公主自恃高贵不去拜寿,怒而回宫打了公主。郭暧闯宫时有这样一句唱词“迈开大步进宫廷”,洛杉矶越剧团的英译字幕是“Here I am striding ahead fearlessly.”。译文以情景为参照,添加了空间指示语here(这里),达到了唱词与动作的连贯性,引导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到郭暧这个人物身上。原文“进宫廷”省略不译,是因为舞台布景可以对文本进行补充,避免了信息冗余。添加情感副词fearlessly(无所畏惧地),更易于让观众感受到动作化语言所体现的人物的情感态度,进一步突显了郭暧年少气盛的性格特点。另一种情感显化的策略是合理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例如,《西园记·夜祭》中的书生张继华追悼玉英亡灵时唱到:“我手捧祭酒和泪悼”,对应的英译是“tears of blood falling from my broken heart.”。译文做出了适应性改造:首先,考虑到剧场表演的多重符号性,将“手捧祭酒”和“悼”省去不译,译文的简洁使演员可以通过动作对语言进行补充,促进了语言和身体之间的交流;其次,在“泪”字上增添笔墨、适当渲染,译作“滴滴血泪”,同时添加“从我破碎的心里流出来”,译文通过这种夸张的修辞手法,表现出人物笃诚专一的性格。充分再现人物情感有助于增强译作的感染力,也能够帮助目的语观众增加对异质他者的情感理解。
(五)审美再造
受越剧美学思想的影响,越剧语言也注重形式美。无论是唱词还是念白,越剧语言讲究音节对称、韵辙整齐、平仄抑扬,营造出一种和谐的音乐美。以感性、直觉、意象等方式表达思想情感,把情、景、意融合,产生富有诗情画意的意境美。对偶、排比、反复、比喻、拟人等多种辞格的使用给越剧语言增添修辞美。越剧语言的这些审美特质应尽量在译文中得到充分再造,同时必须兼顾当代英语的规范以及舞台呈现的要求,否则就会干扰观众。
音乐美的再造要求译文总体上做到节律对应,但不能因韵损义,最好还能与越剧的板式结构、唱腔曲调相配合。具体需要考虑译文的音步、韵式、格律等问题。在译文中使用与原文大致相仿的音步数。用英语中现有的韵式,或者创造出一种新韵式,对原文的音韵特征进行移植。考虑到汉语声调带来的音乐美感无法在英语中再现,可以用英语诗体的格律做出补偿。意境美的再造主要涉及意象的处理。意象的塑造使越剧语言彰显模糊之美,但这种模糊美感在讲究逻辑性的英语中必然遭到磨蚀,加上剧场字幕翻译要求精炼、明晰,“存象显意”和“舍象显意”的翻译策略较为常见[14]32。修辞美的再造可以通过保留原文辞格或转换辞格来实现,以达到和原文近似的修辞效果。
举例来说,《柳毅传书·湖滨惜别》有两句唱词是“夕阳西下晚霞红,骊歌声声催归鸿。”越剧属于板腔体戏曲,在唱词节奏上,依据其调腔特点形成了齐言的七字句、十字句。此例中的唱词是七字句,分为三个音步,音步的节奏呈二、二、三方式分布,如“夕阳/西下/晚霞红”。两句唱词分别在句首(夕/骊)和句尾(红/鸿)押韵,第一句句内也有押韵(夕/西、下/霞)(第二句的“催/归”在越剧舞台语言中不押韵)。第一句唱词平仄相交,声调高低起伏有致,第二句唱词声调较平。“夕阳”“晚霞”和“归鸿”等意象的并置烘托出离愁别绪和凄美的意境。两句唱词结构相似、字数相等、意义密切相关,用的是对偶的辞格,具有排列整齐、对称均匀的美感;另一种辞格是拟人,体现在一个“催”字上,形象地表达了龙女三娘和书生柳毅的难舍之意。洛杉矶越剧团的英文字幕是“The setting sun kindled the sky. The farewell song hustled the parting.”。译文进行了适应性改造,总体采用英语诗歌中的四音步抑扬格,创造了一种和原唱词相仿的节律。setting/sun/sky/song 押头韵,setting/parting和kindled/hustled 这两组词押尾韵,重塑了一种别样的音韵之美。为了再造意境美,使用“存象显意”的策略,将“夕阳”译为the setting sun(落日),既保留了意象,又显化了意思。使用“舍象显意”的策略,舍去“归鸿”这个意象,将其象征意义作明晰化处理,译为parting(离别)。“晚霞”这一意象则通过隐喻辞格进行复现:kindle本义是指燃烧,此处的喻义是指落日映红了天空。hustle作动词时表示“推搡”,保留了原唱词中的拟人辞格,和“催”字有异曲同工之妙。译文的平行结构是对原唱词对偶辞格的转换。总之,译文虽在细节上有所叛逆,但整体上有效传递了原唱词的艺术魅力。
四、结语
越剧海外剧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越剧海外剧场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越剧作品引入到一个陌生的文学和戏剧系统。面对系统中多层语境因素的制约,无论译者多么希望尽其所能地忠实于原作,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改变原作的一些内容,造成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说越剧海外剧场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越剧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译者只有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观众开展一次全新的艺术交流,使之在一个新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里获得第二次生命。洛杉矶越剧团的剧场翻译实践表明,叛逆性与创造性是无法割裂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体。洛杉矶越剧团根据剧场文本的整体性、瞬时性和符号性等特点,结合当代西方观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期待,在叙事、语用、文化、情感和审美等维度对越剧折子戏的剧场翻译进行了适应性改造或创造性改写。这种改造或改写具有叛逆性,也体现出创造性,两者的融合促进了越剧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有效传递。正是因为创造性叛逆,才使得经典越剧作品及其蕴含的中国精神得到了跨越时空的传播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