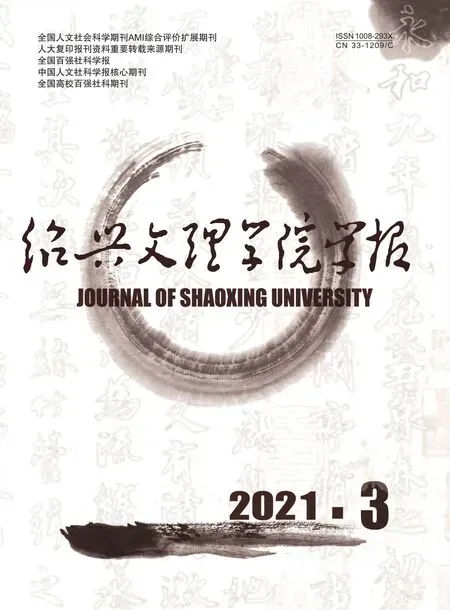隐逸文化与吴越历史的建构
——先秦两汉时期太伯、范蠡形象的演变
刘永学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隐逸思想的文化渊源,学者的意见相对一致,大都认为出自儒道两家(1)参见冷成金《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何鸣《遁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认为虽然儒道两家都有关于“隐逸”思想的理论,但二者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就儒家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原则而言,“出世”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或者说为了更好地“入世”。儒家更加推崇“隐士”高风亮节、韬光养晦的仁义楷模和道德表率作用,而并不是十分认同单纯的隐姓埋名、无欲无求、仅仅为享受山水田园之乐的行为。道家主张隐逸出于主动,要求回归自然,不受世俗权力的约束,道家的“隐逸思想”是建立在“道”“无为”“逍遥”的基础之上,因而是寻求提高人生的境界,体现的是对个体生命的珍视,注重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因儒道隐逸思想不同,所以他们塑造的隐士形象也各异。
在吴越的历史书写中,太伯和范蠡是影响吴越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太伯是吴国的开创之君,范蠡是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国,成就霸业的谋士。他们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被塑造成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太伯以儒家隐士的形象见诸史籍,而范蠡则被塑造成了道家隐士。笔者试图探析太伯、范蠡人物形象形成过程以及形成原因。
一、儒家隐士:太伯奔吴
太伯是吴国的开国之君,其生平经历关系到吴国的国家特征。太伯最为人所熟知的事例是太伯奔吴的典故。关于太伯奔吴的记载,见诸《左传》《论语》《史记》《吴越春秋》等书。
《论语·泰伯》中记载,“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2]在《论语》孔子与孔门弟子的对话中,有了太(泰)伯“三以天下让”的记载。“让”是儒家所倡导的礼仪规范。在《论语》的叙述中,吴太伯是因为要让天下之位而出逃。吴太伯被刻画成让天下而归隐的隐士,并得到了儒家文化的认可。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3]1445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中,首先指出太伯的身份为周太王之子,其身份高贵,出于周王室。关于太伯奔吴的原因,不同于《左传》中记载的“避祸”说,而是因为太伯的弟弟季历贤明,周太王欲传位于季历。太伯、仲雍看出了周太王的打算而选择出奔荆蛮,然后“文身断发”,表明自身无争夺王位之心。《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与《论语·泰伯》略有不同。在《论语·泰伯》中,太伯是主动三让天下,而在《史记》中,太伯并没有受到周太王的认可,周太王更倾向于将王位传给其更为贤明的弟弟季历。司马迁通过搜集先秦文献,游历各地,听取民间口传事迹,最终成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笔下,太伯的人物形象逐渐地丰满起来。
东汉时期,《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亦记载此事,“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4]3-5
在《吴越春秋》的记载中,太伯依旧是周王室的长子。而古公不再如同《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欲传位给少子季历,而是欲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太伯、仲雍通过古公为少子改名一事,推算出古公所指,于是在古公生病时,托名采药,奔走荆蛮。太伯、仲雍断发文身,融入蛮夷。古公在去世前曾令季历让国于太伯,太伯三让不受。古公去世后,两人奔丧,然后回归荆蛮。
《吴越春秋》在沿袭《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载的基础上,杂糅《论语·泰伯》的记载,增添了季历更名,太伯、仲雍解字、托名采药、奔丧,古公令让国而太伯三让不受的情节。可见至东汉时,太伯奔吴的故事在细节上又丰富了不少,最终定型。太伯让天下而奔吴最先见于《左传》《论语·泰伯》,经过儒家的叙述,太伯成为让天下的隐士。
二、道家隐士:范蠡浮海
自先秦始,范蠡的形象性格不断演进,他由一个忠臣谋士发展到如今的商圣、兵圣、情圣,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胡媛媛、邓富华《论范蠡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演变》一文总结了范蠡形象的演变过程(2)在中国文学史上,范蠡的形象性格有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从《国语》中的忠臣谋士,《史记》中的富商陶朱公,《浣纱记》中功成之后携西子泛舟的风流大夫,到《倒西施》《浮西施》中杀害西施的封建卫道士,当代作家李劼的小说《吴越春秋》中集隐士、情痴、琴师于一身的山中相国。参见胡媛媛、邓富华:《论范蠡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演变》,《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笔者在这里主要探究先秦两汉文本间范蠡隐士形象的形成与变迁。
最早有关范蠡的记载是《国语》。《国语·越语下》主要记述了范蠡辅佐勾践灭吴的故事。在灭吴回越的途中,范蠡就向勾践请辞,理由是作为人臣应该遵循“君辱臣死”的惯例,主动要求流放,在没有得到越王的同意后“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5]588。
越王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击败勾践于夫椒。越王只聚拢起五千名残兵败将退守会稽。吴王乘胜追击包围了会稽。越王派大夫种去向吴求和。吴王夫差将要答应文种求和请求,却被伍子胥所阻止。勾践再次派文种出使,利诱太宰嚭。太宰嚭欣然接受,把大夫文种引见给吴王。文种说动夫差。夫差未听从伍子胥的谏言,而赦免勾践。勾践回越国后重用范蠡、文种。越王勾践十五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兴兵参加黄池之会。越王勾践率兵而起,大败吴师。越王勾践十九年(公元前478年),勾践再度率军攻打吴国,大败吴军主力。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勾践破吴都,迫使夫差自尽,灭吴称霸,以兵渡淮,会齐、宋、晋、鲁等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南),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范蠡是勾践的得力谋臣,是越国灭吴的重要推动者。在越国灭吴后,范蠡请辞。范蠡上书越王勾践,请辞的理由是“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国语·越语下》的叙述模式中,范蠡离开的理由是“君辱臣死”而并非越王勾践的刻薄寡恩。范蠡最后浮于海上不知所踪,此时范蠡与隐士渔夫的形象还有一段距离。
西汉时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卷九《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对范蠡也有简单的记述:“大夫蠡,大夫种,大夫庸,大夫睾,大夫车成,越王与此五大夫谋伐吴,遂灭之,雪会稽之耻,卒为霸主。范蠡去之,种死之。”[6]599
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越王勾践与五位大夫共同商议谋伐吴国。最终吴越争霸中,越国获得胜利,一雪前耻,成为春秋霸主。在越王勾践称霸后,范蠡离去,文种去世。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范蠡离去不是因为“君辱臣死”的儒家信条,具体原因没有言明。但“种死之”一事暗含范蠡离去的原因是勾践的猜忌。
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详细记载了范蠡归隐的原因,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3]1752。归隐之后,范蠡自齐致大夫种书云:“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3]1746范蠡在向越王请辞不允的情况下,“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勠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3]1752。
在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叙述中,范蠡离开越国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不能久居大名,此点源于道家思想,道家讲知足退让,不敢为天下先。二是因为越王勾践只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相安。此处直接指出越王为人有缺陷。在范蠡归隐后,勾践在致文种的书信中叙述越王“长颈鸟喙”,不能与之共富贵。在司马迁的笔下,越王勾践刻薄寡恩的形象跃然纸上。范蠡收拾财物,变姓名,隐居后耕于海畔,迅速致富,家产数十万。司马迁为撰写《史记》曾游历吴越地区,博采众说。司马迁直接指出范蠡归隐是因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安,越王勾践刻薄寡恩。司马迁本人受道家思想影响深厚,故而将范蠡塑造成不执迷于权力的道家隐士,且在归隐之后经商致富。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大量取材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也采录了不少佚闻传说,范蠡的形象更为饱满,而且逐渐地偏向于儒家人物形象。在赵晔的《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中,越国灭吴后,范蠡虽看清勾践是一个“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的人,并毅然决定归隐江湖以避祸,但并未直接归隐,而是先从越王勾践入越,然后正式面君后再告退,“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辞于王,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义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则无灭未萌之端,后则无救已倾之祸。虽然,臣终欲成君霸国,故不辞一死一生。臣窃自惟,乃使于吴。王之惭辱,蠡所以不死者,诚恐谗于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须臾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赖宗庙之神灵,大王之威德,以败为成,斯汤武克夏商而成王业者。定功雪耻,臣所以当席日久。臣请从斯辞矣。’越王恻然泣下沾衣,言曰:‘国之士大夫是子,国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托号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将逝矣。是天之弃越而丧孤也,亦无所恃者矣。孤窃有言,公位乎,分国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闻君子俟时,计不数谋,死不被疑,内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从此辞。’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范蠡既去,越王愀然变色,召大夫种曰:‘蠡可追乎?’种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种曰:‘蠡去时,阴画六,阳画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关,涉天梁,后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视之者狂。臣愿大王勿复追也。蠡终不还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于是越王乃使良工铸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侧,朝夕论政。自是之后,计研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皋如之徒,日益疏远,不亲于朝”[4]171-172。
在东汉赵晔的笔下,范蠡之所以选择归隐是因为未实践到儒家所宣扬的“主忧臣劳,主辱臣死”的忠君观念,并表明自己不死的原因,“诚恐谗于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须臾而生”。越国灭吴,洗刷前耻,勾践选择归隐,并恪守君臣之礼,当面请辞于越王。这与司马迁记载有所差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3]1752在司马迁的记载中,范蠡归隐的原因除了勾践为人和“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外,更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而且关于范蠡归隐前后的举动,两书记载不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中,范蠡为书请辞,没有面君,而且范蠡退隐后,越王并没有追回范蠡的意愿。而在赵晔的笔下,范蠡归隐后,越王欲追回范蠡,文种以为不可追,究其原因在于范蠡通晓阴阳,有神异之术。范蠡不仅言行符合儒家礼仪规范,而且人物形象逐渐“神化”。范蠡人物形象符合东汉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展开的时代特色以及儒学与谶纬相杂糅的学术特征。先秦两汉的文本中,太伯、范蠡的形象不断变迁。人物形象的建构、重构与历史传统、时代情景之间互为关联、相互影响。
三、历史传统与人物塑造
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太伯大致是以儒家隐士的形象出现,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而范蠡则多是以不慕功名、追求自然的道家隐士见于典籍,在东汉时发生了“儒家化”的转变。太伯、范蠡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转变,除了典籍书写者自身的立场外,与春秋霸政的形成、吴越二国的发展历程有密切关联。
(一)春秋霸政与华夷之辨
东周初年,周平王东迁洛阳。王室衰颓,周天子的威望受损,各地诸侯崛起,礼崩乐坏。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成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为了阻止兼并混战局面的恶性发展,齐桓公首次建立霸政。霸政的建立,史学家比较一致认为是依赖“尊王攘夷”的号召力。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了诸侯,依靠周天子的政治符号,利用周王室原有的政治基础,建立了政治同盟。但“攘夷”与“尊王”并非一事,“攘夷”是与联合“诸夏”相关而非与“尊王”相关。颜世安先生认为:“齐桓公建立霸政,真正的基础是东部诸夏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西周权力体制的惯性力量。在春秋初年的混战危机中阻止了兼并战争恶性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历史长期孕育而成的中原文化共同体。诸夏认同是一个新的历史事件,尽管‘尊王’后来也成为诸夏认同的某种象征,但诸夏作为一个共同体,与西周时的封建政治共同体绝不是一回事。齐桓公的远见卓识(很大程度上是管仲的远见卓识),就在于以道义相号召,调动了这个共同体的潜在力量,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格局。”[7]
齐桓公建立霸政的基础不是来自周王室的权力,而是来自东部诸夏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东部诸夏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是通过新的“礼”观念文化逐渐确立。诸夏与蛮夷的区分不再是以种族和血缘,而是以礼乐文化。凡是认可礼乐文化的便是诸夏,其国力强盛、遵循礼制的国家便能得到诸夏国家的认可,成为春秋时代的霸主。凡是不认可礼制、不遵循礼乐制度的国家和部落则被称为蛮夷,成为诸夏国家所共同征讨的对象。齐桓公建立的霸政体系和礼乐文化被后代霸主所承认和继承。
(二)吴越历史与诸夏文化
吴越本是东南小国,不在华夏地域范围之内,与中原诸国不是一个文化系统。但吴国为了确立霸主地位,不得不改变自身文化属性,抛弃吴国当地的土著文化,积极与中原各国开展外交,学习礼制。为了论述自身政权的合理性,从而在追溯自己祖先时,有意与周王朝建立关系。吴王夫差为了与晋国争夺“黄池之会”的主盟权,同意了晋国的要求,自己去“王”号而称“吴伯”。且在会盟之时,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1]1791
吴王夫差称“吴伯”而不称“吴王”,并承认了其先祖太伯源自周王室,间接承认吴国历史源于华夏中心地区,既是为吴国谋求霸权提供合理性,也体现了华夏中心文化与华夏边缘文化的互动。吴王夫差正是在积极融合于华夏文化的努力下,才得到了东部诸夏国家的认可,最终成就了霸业。
吴国的历史在东部华夏诸国的记载中,不再是蛮夷之国,而是源于华夏文化。“太伯奔吴”“三让天下”等事例被推崇礼乐文化的儒家所记载,太伯被塑造成了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让天下的隐士形象,并为先秦两汉典籍所不断重构和增补,以致形成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丰富的人物面貌。
越王勾践灭吴后,曾经一度小霸,但因越国立国是建立在越地本土氏族的支持之上的,且其以武力占领吴地,诛杀吴王,其立国根基不稳固。勾践之后,越国三代发生了弑君的事件,所谓“越人三弑其君”。越王翳三十三年(前378年),越国发生宫廷政变和内乱,吴人也参与其中,趁机立错枝为君。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写成了《史记索隐》一书,引用《竹书纪年》的记载:“纪年云:‘翳三十三年迁于吴,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咎弑其君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吴人立子错枝为君。明年,大夫寺区定粤乱,立无余之。十二年,寺区弟忠弑其君莽安,次无颛立。无颛八年薨,是为菼蠋卯。’”(3)关于《索隐》记载的内容,参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1747页。
由此可以看出,越国立国根基不稳,并没有解决好与吴地贵族的矛盾,这也使得越国华夏化的程度受到阻碍,其整体面貌仍然带有吴越本土色彩,因此范蠡在先秦的文本中被塑造成了道家隐士的形象。直到东汉时期,随着儒学与谶纬的发展,范蠡的人物形象出现了“儒家化”与“神化”的色彩。
四、结论
齐桓公首创霸业,其建立基础是东部诸夏文化,凡是建立霸业者必须认可诸夏文化。吴越本是源于东南地域的部族,带有与华夏诸国明显不同的本土文化面貌。为了霸业的持久,他们必须舍去吴越本土文化,接纳东部诸夏国家的礼乐文化。但由于吴越与华夏诸国的距离远近,受华夏诸国文化辐射的影响不同,以及自身文化色彩的浓淡不同,吴越融入华夏文化的程度不一。这成为导致太伯与范蠡在先秦两汉典籍中面相不同的历史缘由。
在两汉时期,董仲舒、司马迁、赵晔等人受所处时代及个人经历之影响,或是丰富了太伯、范蠡的人物形象,或是重新塑造了其人物面貌,使得多元化的人物形象逐渐趋于统一,流传于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儒家隐士太伯奔吴、三让天下,道家隐士范蠡浮海、游于五湖等事迹的形成既体现了吴越的历史传统,也展现了两汉时期士人对先秦人物的不断建构和层层塑造,最终形成一个完整宏大的历史叙事。吴越历史人物存在着后人对其追忆与建构,不能简单将史书中所书写的吴越历史作为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