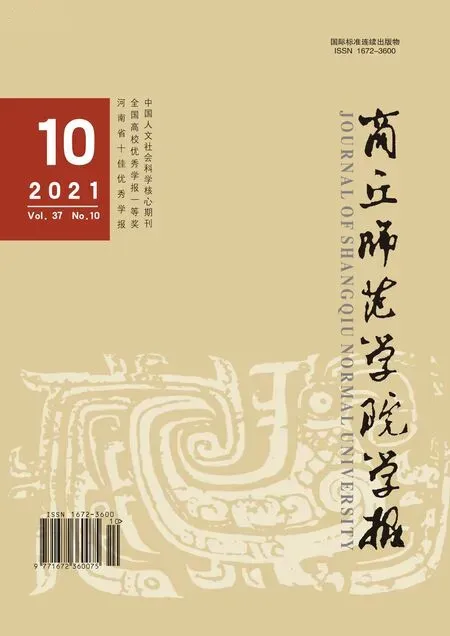论“庖丁解牛”存乎技中之道之心的义理探析
罗 惠 龄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庄子·养生主》中阐述庖丁替文惠君肢解牛体。手接触的、肩依靠的、脚踩踏的、膝抵住的,无不展现最到位的气势,无不符合节拍音律的姿态。“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文惠君不禁慨叹说道:“啊!真是太厉害了!究竟如何达到神乎其技的呢?”庖丁听罢,缓将珍视之刀妥帖地放下,才定神答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尼采以自身体验试图对跨越深渊的奥秘提出解释人生精神境界的三种变形,同时也是其对于超脱人间世中的超人诞生,与其精神三变的过程来作的变相呼应。三种变形分别为: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为狮子;到了最后,狮子再如何变成孩童。承此,本文亦试着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烂漫天真,到见山非山、见水非水的世故练达,再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老僧入定,三个层级和阶段,来探析“危丁解牛”存乎技中之道之心的义理。
一、山水是山水之族庖月更刀
庖丁还是一个解牛新手的时候,只能看到一头实实在在的全牛,凭借感官初识世界,一如稚子烂漫天真而懵懂好奇的真实纯粹。眼望便信,随心率性地将喜怒形之于色,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无不然是远望山有色、近听水潺潺的快乐崇拜。然而,世界规则岂是眼见为凭的过度乐观?不知山高水深,不究事物表面背后的存在意义,从而自顾自断然地给出定义。关乎纷繁复杂,蝇营狗苟,又岂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初入丛林迷兔所该兀自警惕的前行大事呢?“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郄,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养生主》)第一阶段的“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意指庖丁初入行,对于工作对象认识不清,实务经验不足,亦难于人世间的纷杂问题中游刃得当。故以其情识造作之我来观解牛体,因此眼中所见之牛,皆是摸不着头绪之复杂难解的孤立皮相。一如“族庖月更刀,折也”中的折为折断的意思,表示一般庖丁在用刀碰触骨头之际,常以顽强力道劈砍折损。由于使用方式不对,难怪刀子总是寿命不长,必须时常更替新刀。因此,不按牌理、不得其门而入之耗损心力、劳神伤身,这便是初阶的练技阶段。
初阶练技阶段的人生境界,其状犹如代表人类精神的最初阶段,象征着忍辱负重入世性格之沙漠之舟的骆驼,被动听命于他人并承受命运的主宰。骆驼孤独地在荒漠中行走,为了觅寻滋养生命的绿洲,为了突破逆境的坚毅生存,必须长期忍受烈日烤炙以及干涸无助的揪心苦难。即使面对漫漫滚沙,前路茫茫,依旧肩扛传统、屈膝承受。成就了只能负载, 只有敬畏顺从,不能创造,没有抗争能力,俨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的悲剧形象先驱。即如同初入行的社会新人,对工作对象认识不清,实务经验不足,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身不由己地隐忍,却又不知为何而战。以其“应该如何”照单全收的全然宿命信仰,来作为长期生活及成长的价值指针,这便是所谓的骆驼精神,即人生修炼的初阶技法。
“所见无非全牛”是庄子用来隐喻世人仅观其物而不明其理之认识上的滞碍,即为日用而不察之“滞于物”的生命常态。“‘滞’,《说文》云:‘凝也。’段玉裁云:‘凝,俗冰字。’”[1]559亦即如冰之凝,阻碍而不通之意。一旦人滞于“此”就会忽视“彼”,这就容易“一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2]60。“当一个人只见物而不见理的时候,人与物之间就会形成对立,要么人试图去宰制物,要么物来役使人,无论是哪种情况,人都会陷于‘滞于物’的状态。”[3]2于此层次,不但谈不上任何养生之理,而且还会出现以养伤生的状况,这就是大多数人“滞于物”的生命常态。“百骸,九窍,六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庄子·齐物论》)对于牛的理解即是生理结构的茫然无知,就像一个人在生活中“只见物而不明理”一样。由此凸显我们在看待世界时之只见物而不见理,从而衍生导致的荒诞。
执着于山,执着于水,执迷于事物的光鲜现象,分不清现实世界的金科玉律。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烂漫天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单薄,献上最热血的璀璨温度,终是仍未入门入定的第一境界样态。是初跌入喧嚣烦嚷、红尘俗世,不知愁为何物的天真单纯。面对于铺天盖地、迅雷不及掩耳的磕磕碰碰、伤痕打击,进而为天真烂漫到天真残忍的身心疲惫。“当一个人视物而明理的时候,人与物之间就容易沟通,对于物能观其间理,人就不会再被物所阻隔遮蔽,就能够不再滞于物。”[3]2据此,开始于“技”中设身处地、拿捏分寸、掌握技巧,深知唯有在屡屡的境界提升中,才能避免于硬碰硬的两败俱伤。换言之,从面对外界并开启了自我的保护机制,渐渐于逐次受伤平复的过程中,开始内反并省思顺应情势的道理。于此明白涵养心神的重要,始能更进一步地摆脱外物束缚,得以重获人格的自由。
二、山水非山水之良庖岁更刀
献上天真热血的温情来看待人生山水,靠得更近,处得更久,渐渐发现山外竟然有山,水外仍旧有水。红尘俗世中的黑白竟能自顾自地颠倒,是非对错亦能似随天气变化般随意地混淆。古道热肠的背后,是心细如麻的恶斗,虚伪面具下隐藏着太多人前手牵手、人后下毒手之机关算尽。于是雾里看花,于是似幻似真,于是再回不去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来时之路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烂漫天真之精神境界变形 ,在诸多的无力感以及崩溃边缘不断地与之招手,终于在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下,于精神上蜕变成反抗格斗的狮子。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齐物论》)人一旦出生,就在慢慢地朝死亡奔赴。即便在这样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我们还不断地“与物相刃相靡”,不停歇于“滞于物”的情境,从未停下脚步深思,岂不荒唐悲哀?
就职场而言,此时对于工作认识精确并有效把握,亦积累了足够人生阅历的实务经验。怀抱人生,活出梦想,开创崭新局面,处于高阶熟技的光芒象征。可人生岂有着绝对如骆驼般被动承载的宿命,又或是如狮子般义无反顾地勇闯宣战。卸除传统价值强加的负载,实现精神的自由解放,便意味着更要有着敢于承担责任的风险与担当。拳拳服膺谁与争锋之下的“我要”信条,在诸多困难的抉择中,不免于蛮横厮杀的野心、声嘶力竭的疲惫,在创造新价值的披荆斩棘里,终于迷失了自我。
我见山水多彷徨,料山水见我应如是。无论是选择积极奋进、向前奔驰,抑或是迷惑彷徨、痛苦挣扎于妥协后的宿命俗世,两害相权如何取其轻?两利相权又该如何取其重?患得患失,摇摆不定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际。试问,在人生颠簸初始之时,谁又能轻声召唤自己悬崖勒马呢?于是,真心一旦坠跌就无法展翅的天真烂漫,便活脱脱地镶嵌在见山非山、见水非水价值观瓦解的世故练达之中。
“盖庄子整个哲学精神,即不外在安顿无人之生命,无论是精神境界或现实生命,皆庄学所欲超越、点化、安立者。是以其逍遥之所以逍遥,即在其养生之具体生活上实现,而齐物之工夫修养,亦莫不在养生中表现。”[4]113第二阶段的“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意指三年的庖丁岁月,工作对象认识精确,亦积累足够人生阅历的实务经验。故庖丁眼中已非第一阶段所见的完整牛只,而是以牛之自然之性观牛,在心中有了清楚分际的视觉图像,据此作为目无全牛的“分割部位”,作为审视精辟的解牛蓝图。一如“良庖岁更刀,割也”。从族庖用刀硬砍骨头的“折”,技巧递进为良庖用刀切开筋肉的“割”,不硬碰大骨,而是缘着骨头切肉。庄子所谓的养生主,即是要吾人顺人我之旷达,循山水之自然,过犹不及,皆以适分为要。郭象注曰:“夫生以养存,则养生者理之极也。若乃养过其极,以养伤生,非养生之主也。”[5]121换言之,虽然因经验而了解如何避免困扰纷争,达至高阶的熟技阶段,但凭目视解牛,长此以往,虽技术熟巧,却仍不免于于不可测之境中摧折损伤。
三、山水即山水之道庖若新刀
从传统弱者、消极被动、敬畏顺从、拳拳服膺并一直被赋予“你应该如何”的骆驼境界,进化为重拾生命主导权的开创强者、积极主动、挑战权威、怀疑否定,从而开展出“我要如何”的狮子境界。两端不断抛掷的骆驼和狮子,在历经千锤百炼的成长艰辛路后,终于能够回归生命原点而再次出发。“方今之时,官知止而神欲行,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养生之道即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老子说:“复归于婴儿。”(《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专气致柔,能婴儿乎?”(《道德经·第十章》)孟子亦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超越了骆驼和狮子的被动至主动,脱胎换骨从而活活泼泼地在自在当下中展开心灵生命的新境界。风雨过后沉静,破坏转成创造,流放化为依归,丧失终将回复。“我是!”“我在!”的声音回荡,这便是内在催生、主体确立,精神完善了意志,天真烂漫的孩童境界于此出现。
孩童纯真的诞生,是狂暴肆虐的挣扎搏斗之后的和解。生命有了神圣肯定,天地大美至善存在当下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便是个体超人真切涌现的使命。此刻返璞归真的孩童境界,代表着内心宁静和谐的天空澄明。不再自我纠结,不与天地万物对立,抛掷陈旧故步,才能更上层楼,才能将其自我生命,安立在含德之厚的心灵本真当中。
山水即山水之道庖若新刀之第三阶段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老僧入定,“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顺应自然的心神运作,避开锋芒,如此谨小慎微地掌握规律,抓住本质,无怪乎“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意即刀用了十九年,刀刃还像新磨过的一样。“刀与牛,牛与人,不再是对象、工具、主体三者鼎立对峙的关系,而是浑然一体,无分内外彼此,不知手之运刀、刀之解牛而牛竟解。”[6]456因为牛的骨节之间有空隙,而我的刀刃薄的几乎没有什么厚度;以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入有空隙的骨节,自然是宽绰而游刃有其余地了,所以这把刀用了十九年,刀刃还像新磨过的一样。换言之,从处事谨慎的低调藏锋,泯除成见的化解对立,熟能生巧之经验积累的“技中之道”,升华提炼至“道中之心”境界。如此一来的不计得失、物我两忘、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的存乎技中之道之心,终将在游刃有余、保全自身而臻于“养生之道”的化境之中了。
海德格尔言道:人的一生,很少活在“我”、活出“自己”,大部分时间反而是活在“他者”、活在“别人”。匆匆过客,穷究一生,越过太多的高山峻岭,经历太多的形色事物。以锤子的使用为例:“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的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原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锤本身揭示了锤子特有的‘称手’,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7]3在大千世界经年累月的修持下,谨小慎微,掌握规律,抓住本质,避开锋芒,终于得以练就一身顺应自然、心神运作的老僧入定。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 ”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 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达生》)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外云卷云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地“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则更添显出豁达与淡定。
“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庄子·养生主》)可即便如此,每当遇到筋骨交错盘结的部分,我知道不好处理,也都会更加地小心谨慎,目光集中,举止缓慢,然后稍微一动刀,牛的肢体便会哗啦啦地给分解开来,就好像是泥土一样地溃散落地。“险阻之触之所以非必有,即因此险阻乃在自心之强求入,既不强求,即可‘因其固然’而得其间。而此不强求亦即是无厚其情、才、识,生命无厚,则间自得,而其游刃有余亦必然矣。”[4]119以一颗低调藏锋、沁除成见、物我两忘的谦卑心态来化解对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转境转、茅塞顿开,已然较第一阶段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烂漫天真,更添增了一份在岁月洗礼下的处世之道与为人内涵。
抛掉了乌云密布、云雾缭绕的迷乱混淆,抛掉了隐藏在本来面目后的纠结狰狞。“大名之所在,大刊之所婴,大善大恶之争, 大险大阻存焉, 皆大軱也。而非彼有必触之险阻也,其中必有间矣。所患者,厚其情,厚其才,厚其识,以强求入耳。”[8]81挥挥衣袖,拨乱反正,将心定住,便能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之后,见山仍旧是山,见水依旧是水。最终便能在灯火阑珊处的老僧入定中,体悟到人生处处皆美好的况味百态。
四、善护游刃有余之朴心山水
经由第一阶段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之族庖月更刀,折也——初阶练技,初始入行,工作对象认识不清,实务经验不足;接着步入三年之后的第二阶段,未尝见全牛也,良庖岁更刀,割也——递进高阶熟技,对工作对象认识精确,累积足够实务经验;再到第三阶段的方今之时,官知止而神欲行,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铸就养生之道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彼节者有闲,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庄子·养生主》)这个时候的庖丁便提刀站立,环顾四周,心满意足又从容自得地为文惠君解牛,展示极尽技艺功夫与道术境界的双全。最后,再将刀刃擦拭干净收藏起来。文惠君闻此不禁赞叹:好啊!我听了这一番话语后,便是懂得养生的道理了。
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道,早就已经超过技术的层次了。我在最早开始肢解牛时,所见到的不过就是一整头牛;三年过后,就不曾看见完整的一头牛了;就以现在的情况来说,我是以心神来领会这头牛,而不是以眼睛来观看牛,停止了感官作用,靠着心神随心所欲的充分运作。依照着牛体自然的生理结构,劈开筋肉间的空隙,引刀导向骨节的空隙,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下刀。那些经络相连、骨肉相接的地方连碰都没有碰到,更何况是那大骨头呢!好的厨师每年更换一把刀,因为是用刀割筋肉;普通的厨师则是每个月更换一把刀,那是因为他是用刀来砍骨头。而如今我的这一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肢解过数千头牛,然而刀刃仍旧像是刚从磨刀石上磨过的一样锋利。于此,庄子不言宰牛,不说杀牛,偏讲解牛,已然是将解牛血腥场面的夸张过程,巧妙铺绎成了韵律优美的肢体画面。如此一来的浪漫美感的视觉体验,叹为观止的道艺飨宴,极富文学巧艺之美。无怪乎文惠君会发出情不自禁的赞叹:啊!真是太厉害了!技术究竟如何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呢?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庄子透过这篇庖丁解牛的寓言,说明养生之道在于顺应自然,顺势而为。遇筋骨交错之际,就好比生活遭遇重重障碍、层层束缚的与人相刃相靡,而必须适时地集中精力,如履薄冰,巧妙回避并圆融解决。如此一来,象征自我的无有厚度之刀,便能在如复杂社会般的牛骨节间中的空隙里游刃有余。文惠君着眼于熟能生巧之“技”的“嘻!善哉!技盖至此乎?”相对于心领神会之“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的庖丁论“道”,两人层次不同、境界相异从而埋下了伏笔。换言之,将其自我之刀安放在心灵深处,如同漂流的人生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扣,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尤有进者,生活能够自如,生命不受折损,才能于安时处顺之中,安返哀乐不能入也之境。心的修行达致无有之境,泯除物我对立,超越利害得失,参悟养生之道,存在价值显像,便能尽享天年。
族庖、良庖乃至今日的庖丁,不外是致虚极、守静笃以至于无厚之由技入道的过程。庖丁解牛中的那头牛,比喻的就是“人间世”。牛体的结构异常复杂,因为牛的骨肉筋络相连一起,不当砍斫便会造成受伤折损。而庖丁手握的那把刀刃,便是象征着每一个人的“自我”,以自我为名的刀刃投身在牛体天下,与人相刃相靡。所谓的相刃即是互相砍斫,相靡便是将对方砍倒。人间世就是天下,自我活在天下,人物活在人间。本身的自我有限,而人间大道却又显得如此复杂无限,这便是人生存在的两大难关,同时也是《养生主》的主体寓言。
人间天地各有其规律存在,洞察客观环境的规则,使其常规成为自身的导航。善解牛者,刀不易折;善处世者,人不易损。于是庄子告诫我们,需从刀刃无厚做起。庖丁并非生而游刃有余而不伤,而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功夫历程得以致之。原本是要解开牛体,但必须在刀刃薄到几无厚度的无身之际,当刀刃没了厚度,牛体筋骨、骨肉相连的地方就算再狭窄褊隘,都可以轻松自如的滑过。何以故?精神在感知中驰骋,功夫在实践中涵养。如此一来,打开了自我,放开了自我,没有了自己,没有了厚度,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其功夫在“缘督以为经,顺中以为常”,意思是说处事的人若能依循事物自然之理而予以为常,持守着无偏无执的中虚自然之道,不过分、不强求。“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意指顺应现实,尊重自然,妥善保养身心的人生观点与处世哲学。谨小慎微地避开阻碍,即便外物搅扰如织,只要掌握要点,便能得心应手于做人处事。精神为主,感官为辅,便不会轻易让有形感官来损坏耗伤无形之心气神。
其境界在“游刃而有余”。当牛肢解后,庖丁心满意足于刀刃无损,从容自得于养刀如新。解牛后的刀刃,随即小心保养擦拭,而后藏于鞘内,锋芒不外显露,养刀如似养生。既能于有余之中乘物以游之,又能在人间道中逍遥又自适。身可以保,生能够全,亲得以养,年终将尽,终于在不伤自我之刀的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中,臻于养心护心之化境。所有的一切之上,都有光在流淌着,甚至暗黑里,也有着极其细微的光,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而看不见的,并非不存在。因为蕴藏于深处的那一道心主,经由阶段体悟经验,终臻神乎其技之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而至于那道安时处顺、哀乐不入的真境心光,每个存在当下所需护养的心主,亦复如是啊!
生命游于人世间,解牛而刀刃无割折,犹如生命游于天地而不伤。保全刀刃,就要避开筋腱骨骼;保全个人,则要避开社会的矛盾冲突。解牛之难,不在于所解之牛之筋骨错杂,而在于其解牛之刃未得其间。何以故?在其未能无厚也。个人在人间世中就跟刀刃一样,相较于牛骨,就好比那些社会的是非冲突、情感的矛盾挫伤、害人的陷阱机关。庖丁解牛前后历经了由最初的“所见无非全牛”到“目无全牛”的“技”艺,反复体验,多次琢磨,熟能生巧之后,才达致“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之挥洒自如、神乎其技的“道”境。
由“技”至“道”,从感官活动到精神运作的心程,手段方法熟能生巧,提炼升华成物我对峙的消解。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非以此纯亦不已之至诚而不能熟技至道成心。唯其如此通透道通为一之境,游刃无间于场域的道境中,更彰显朴心山水之精神生命不受外在左右的丰富性、自由性以及无限性。心灵是每一个人的神殿,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么,都应该好好护持它的强韧、美丽和清洁。如果用眼睛看是一种框,用心去体会就是一种宽,人在俗世外,心栖山水间,涵养精神生命之主,善护游刃有余之心。如此一来之养生必当以养心为要,善护游刃有余之朴心山水,才能对于现实生命加以调护,终能享拥安顿养生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