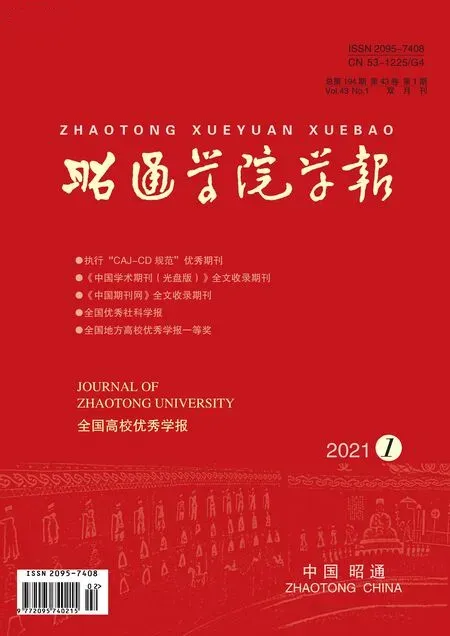《我弥留之际》中艾迪形象之尼采式解读
廖偲祺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11)
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主要描写的是美国南方本德伦一家在7月份为刚去世的女主人艾迪进行的长达10 天的送葬之旅。尽管小说故事主要在艾迪去世后展开,但艾迪的死至始至终都对本德伦其他家庭成员的心理反应和外在行为有着深刻影响。作为故事中心人物,艾迪在小说中却仅有一节的独白,并且该独白大胆袒露着自身生前隐秘的内心生活以及各种逆主流行事的经历,因此,该独白以及艾迪的形象不断吸引着学界进行各种角度的解读。福克纳在其作品中流露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艾迪形象的探询提供了广阔空间,“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形象已经融入他本人力图通过‘死亡’震醒人的价值意识的主体意向和对生存本质的严肃的哲学思考”[1]71。笔者认为,艾迪在独白中提及的各种颠覆性尝试本质上与尼采的生存美学不无契合。在尼采看来,生命的有限性让自身存充满悲剧色彩,但尼采所提出的生命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在于:即使深刻意识到这种有限性,也不应因此厌倦和否定自身生命的意义,反而更应以充沛的情感、勃发的生命肯定自身的有限存在。尼采在狄奥尼索斯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权力意志观,他将生命视作一种力的表达,认为生命通过力的自我积累与释放,彰显出生命的主动、积极、肯定的性质。本文将借助尼采的生命哲学视角,从生命的酒神精神和权力意志来剖析艾迪种种颠覆性行为,以此为《我弥留之际》的艾迪形象研究注入新的阐释角度。
一、艾迪的酒神特质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了日神和酒神两种精神。日神精神从日神阿波罗发展而来,引导人们沉浸在美好的幻象世界中,忘却存在的真相,它代表了强调“节制”“适度”“自知”的“个体化原理”,人们在这种具有秩序、法则和界限的阿波罗式现象世界中,可以应对存在的偶然性以及死亡的必然性带来的恐惧感。然而,尼采后来的学说主要强调了从酒神狄俄尼索斯发展而来的酒神精神,基本上对日神阿波罗已弃之不顾。酒神精神将个体落实到更为原初性的生命实体中,通过最原始的本能冲动,展现生命力的旺盛,肯定人类存在的价值。同样,艾迪也时常复归自然本体或原初的“太一”,肯定着生命本能的欲望和冲动。艾迪喜欢把自己和原初的自然链接,身为教师的她常在放学后下山到泉边,将自我沉醉在自然中去接近生命的本质:“泉水潺潺地涌出来流开去”“到处弥漫着一股潮湿腐烂的叶子和新垦地的宁静的气息;特别是在初春,这股气味特别浓烈”[2]156。弗洛伊德认为流动的液体和所有凹陷的物体是子宫的变体[3]73,潮湿又充满新生的气息、涌动的泉水为艾迪创造了一个孕育性欲的空间,使艾迪在远离现实指涉的“太一”状态中感知自然本体的冲动。艾迪在独白中多次谈到她对初春的感受,伯格曼(Jill Bergman)认为这种感受实质上与性欲挂钩[4]396。“有时候我真觉得无法忍受,半夜里躺在床上,倾听野雁北飞,它们的长鸣渐渐远去,高亢、狂野,消失在辽远的夜空中……”[2]157。时常回归自然的艾迪能敏锐地感受到自身的本能冲动,原初世界中那种“高亢、狂野”的声音拨动着艾迪内心深处的本能欲望,使她在半夜难以平复。她没有压抑这种的本能,当她意识到生命体内已出现这种强烈的本能冲动后,安斯刚好出现在她的世界中,于是她便接受了安斯。因此,对于性的渴求成为艾迪选择嫁给安斯的重要原因,这一动机反映出艾迪对本能冲动的重视。原初的“太一”代表着一种原始、野蛮、非理性的生命冲动,艾迪对这种冲动的重视,实质上是艾迪的主体意识一定程度上的觉醒。艾迪意识到女性释放性欲这种本能冲动后,随之而来的将是生育这一自然后果,而男性却可以不计后果地释放性欲。这种两性之间天然不平等的差异使得艾迪将自身狂热的意志投射于大地,认为自己与自然、与土地完美地融合,并将土地视为自身血肉的一部分,体验着将自身存在与世界本体融合的酒神式慰藉:“倾听着如今已成为我血肉一部分的土地的声音”“我的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是席卷大地的那股狂野、沸腾的血的……”。在艾迪眼中,血液一方面是沸腾的、狂野的,代表着一股席卷大地的生命意志洪流,是释放自身蛰伏生命力的原始冲力;但同时血液也是可怕的、痛苦的,会在女人经期和分娩时注入土地,是将女性的性欲释放与生育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天然“束缚”。但艾迪将血液回归土地视为自身生命与原初世界的元素融为一体,这种想象是其主体意识觉醒之后通过酒神式的心理投射从原初世界寻找的精神力量,从而应对现实中女性在生育责任上与男性的天然差异。
二、艾迪的强大意志
酒神不仅“同性、生殖及其伴随的痛苦相关”,同时还与“力量的增强的相关”,后来被尼采进一步发展为“权力意志的种类”[5]17。“权力意志萌芽于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和艺术是对生命的鼓励和刺激,他们分享了权力意志的一切特征:酒神不仅有一种吞噬万物的整体感,还有一种高度的力量感,他要强盛、强化、爆发和释放,要获得‘肌肉的支配感’……这,就是权力意志本身”[5]17。同样,艾迪身上也蛰伏着这种狄奥尼索斯式的“高度的力量感”。艾迪有着一份教师工作,但在其独白的开头,她坦白了身为教师时的残酷: “我总是期待学生犯错,这样我就可以拿鞭子抽他们了。”[2]156。艾迪可以通过虐待学生获得自身权力意志的增强。尼采认为,对他人施加的痛苦的动机最终是由个体的权力意志所激发[6]139-140。“力的本质在于向一切其他的力实施强力”[7]290,“实行残忍,就是享受权力的最高满足感”[9]18。艾迪对他人实施残忍的行为在尼采学说中可解读为:她的内在需求中有着力的较量。要使自身力量的增长和强化,就必须同别的权力意志进行较量,当艾迪感到她的自身力量受到削弱时,便想找到一种增强的途径。“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秘密、自私的想法,每人身上流的血彼此不一样跟我的也不一样……”[2]156。作为一名教师,艾迪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与学生之间是存在隔阂的,她很难通过与学生的接触产生亲密感,也无法与他们建立真正的交流。这种状态同“死亡”哲学的灌输一样使她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有限性,“这种日子看来就是我准备长眠的唯一通道了吧……”[2]156在学生面前,她陷入孤独与压抑的绝望中,她感到自身的内在经验无法有效地与外界互动,无法介入学生私密的经验中,这对她的权力意志构成了挑战。因此,她试图找到一种途径实现个体间的渗透,以扩张自己的内在的“力”。艾迪借助教师的身份,以残酷地惩罚学生这种“极端方式”来产生身体经验的互动,这些学生便也被迫通过肉体感受到艾迪的存在与强力。“随着每一鞭抽下去我就这样想:现在你可知道我的厉害了吧!现在我已成为你的秘密的自私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已经用自己的血永远、永远地在你的血液里留下了痕迹。”[2]156-157。艾迪通过鞭打学生这种肉体剥削的方式让学生们经受痛苦,是想凭借自身的“力”渗透他人的皮表,对他人的肉体造成影响,以彰显她本人的存在。这种攻击性的措施可以让艾迪本人感受到“力”的优越感和扩张感,尽管这种证明生命本质的方式自私且极端,但艾迪正是在这种隐秘的剥削和征服方式中流露出增长力量、强化生命的强烈意志。艾迪在否定他力中肯定着自身,使其作为“力”的本然生命更为强大。
三、艾迪的酒神式反叛
摆脱个体化原理、回归生命本质的酒神式冲动里孕育着一种荡涤外界囹圄限制的反叛之威。艾迪的生命里也蛰伏着这种酒神式的反叛之力。首先,艾迪选择用一种比语言更为直接的、本能性的表达来强化自身的主体性。艾迪生活中接触的语言是受父权文化深刻影响的语言,很多言词建立在男性的标准和期望之上,这种语言剥夺了女性的主体性,使得女性在具有母亲身份之后变得客体化,并在他人的欲求中模糊自身存在。例如,艾迪意识到“母性”一词只是将女性看作孩子需求的客体,当她的大儿子卡什出生的时候,她就意识到“母性”这一说法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词儿的人发明出来的,因为生孩子的人并不在乎有没有这么一个词儿”[2]158。在艾迪看来,“母性”这种说法是为了让女性自主地重视子女的各方面需求、强化女性爱护子女的意识而“发明”出来的,这是一种父权文化的体现。而艾迪的酒神式反叛精神则要将女性自身的意义从父权文化压迫下的语言中解救而出。艾迪成为母亲之后,根据自身经验,她认为女性并不需要在意父权文化创造的词汇,因为母子之间传递感情实质上无需言语:“卡什就不需要对我说这个词儿我也无需对他说”[2]159。她能读懂卡什醒后的哭声的意义,因此她让卡什睡在自己伸手可及的摇篮里,如果他醒来哭了,便会给喂他奶[2]159。用乳汁喂养是女性对孩子表达爱意最独特的方式。艾迪自由地、本能地凭借女性独有的经验——身体、乳汁、母爱,在现象世界背后享受着自我导向的原初之乐,这种无法言说的本能之乐是超越语言意义的更高满足。语言对意义的塑造未能束缚艾迪丰盈的生命,她以酒神式的反叛精神打破了语言的静态意义,用带着生命温度的自我经验实现了意义的重塑。女性相对于男性是更为深挚的感性个体,在生活中往往更能敏锐地感知一些非语言所能承载的意义。例如,艾迪的丈夫安斯喜欢表达“爱”字,但这种言词上的“爱”并不能满足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艾迪对于真正爱意的需求。因此她主动否定语言的力量,选择用无言的行动来撕破语言的面具,转向更加忠于自我的意义表达。
其次,艾迪与牧师惠特菲尔德的通奸也是一种通过“性”所具有的非理性力量反抗南方“父权”价值系统的颠覆性尝试。当艾迪与安斯结婚之后,艾迪实质上便进入了父权伦理的价值体系,女性不可避免地陷入成为客体的命运,成为生儿育女的工具。艾迪生完卡什后,不肯相信自己又怀上了达尔,但艾迪生育的小孩数量还不够满足安斯的期望。因此,艾迪抗拒这一伦理体系,凭借酒神力量摆脱父权伦理的桎梏。艾迪的通奸便是僭越父权伦理规范、追寻主体欲求的尝试。这种颠覆如同一股狂野之力使艾迪成为欲望的主体,生命中的各种能量被剧烈唤醒,生命经验以及个体自身的自由与意志便得以强化。然而,伦理规范的力量也是极为强大的,艾迪的颠覆性尝试也会伴随着父权伦理所施加的罪恶感:“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没完没了的认罪和赎罪”[5]153。但艾迪抗拒基督教虚无的赎罪方式,在现实领域中创造了一种超越上帝力量的个性化赎罪之道:朱厄尔的诞生将解救自身的痛苦。即使心怀罪恶感,艾迪也不愿被动接受父权制文化所塑造的命运,而是主动为自身命运负责,去真切地感受“自我”,其关于救赎的思考再次实现了自身意志的自由与独立。
四、艾迪的权力施展
艾迪对爱情的期望因安斯空洞的“爱”字和达尔毫无预料地诞生而幻灭,因而忍受着现实的煎熬:丈夫使用着具有欺骗性的言词;达尔的出生也让艾迪意识到“她的身体与外部的某种力量结盟,不受她本人意志的支配”[10]299。艾迪的遭受如同强大的阻力威胁到她的权力意志,因为她意识到了自身意志的有限性。然而,尼采的“权力意志”有着克服阻力的欲望[6]126,在阻碍意志的事物面前寻求反抗才会赢得“力”的增强。在这种意志的驱使下,艾迪通过寻求报复来增加自己的生命强力,从而对抗父权制文化下的生活带来的无力感。值得注意的是,艾迪的报复心理一开始是源于“力”的强化,而艾迪死后报复计划得以实施时,艾迪生前蛰伏已久并不断积累的生命强力便开始施展与释放。
当达尔出生之后,艾迪便要求安斯答应等自己死后一定要把自己运回到杰弗生去安葬[2]159。本德伦家族的漫长送葬之旅彰显着弥留之际的艾迪“高度的力量感”。首先,艾迪要求死后的埋葬地点是远离丈夫和孩子的城里,这是强大的艾迪对女人本分的有力颠覆,也是对“他力”——安斯所具有的夫权之力的变相征服,因为科拉曾谈及过父权支配下的女人本分:“既然是女人,就该死活都和丈夫、孩子守在一起,这是女人的本分”[2]19。父权文化通过对女性安葬空间的控制再次将女性客体化,而艾迪提出的要求成功地摆脱了这种控制。其次,艾迪要求丈夫安斯信守为她送葬的诺言,这也是艾迪在父权文化的“力”场斗争中的一次力的施展。“她的浪漫主义正在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强烈的意志,要将她生活里的元素置于她的统治之下”[10]300。这份承诺如同将安斯纳入艾迪控制范围的缰绳,使安斯在这场送葬之旅中至始至终顽强坚守着实现艾迪生前意志的责任。艾迪是强大的,即便生命在肉体上已经消亡,其意志、其生命之力仍在施展,弥留之际的艾迪似乎并没有真正“死去”。艾迪强大的生命之“力”在其弥留之际既彰显着凝心性,又发挥着牵引性。在漫长的送葬之旅中,本德伦其他家庭成员即使每天面对着日益腐烂、臭不可闻的尸体,也仍然要为艾迪躺在棺材里的躯体考虑,他们似乎仍旧无法从身体上或精神上与她分离。死后的艾迪就像是“一个强大的动态能量体系”[11]78,使心理上已经解体的本德伦一家仍旧围绕着艾迪集体“苦熬”地前行。艾迪“力”的施展与释放也使得散发臭气的葬礼延续,尽管本德伦一家的送葬之路总是节外生枝、颠沛流离,但始终被一股力量牵引着迈向终点。使他人“苦熬”是艾迪权力意志的一次胜利,她成功地使家人的意志纳入自身意志的统治之下。艾迪生命里的“力”已报复性地将其生前经受的对家庭、对生活的失望转换成本德伦全家为其苦难付出代价。艾迪在弥留之际的报复计划本质上彰显的是其强大的生命与夫权之力的对抗:即使生命是有限的,其生命“高度的力量感”仍能以不可抵挡之势在死后影响并控制着整个家庭,仍能在精神上或肉体上对家人的生活留下印记。因此,即使南方父权文化削弱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但艾迪死后权力意志对家人的深刻影响隐性地反映出艾迪对于这种地位的抗争。
五、结语
酒神精神以无形的反叛力量把个体的实在生存从现象世界的尺度、界限中解救出来。福克纳所塑造的艾迪形象是具有丰盈生命的感性个体,有着高度的“生命力量感”。面对南方强大的父权文化,艾迪并没有放弃获得自我、获得主体性的欲求,而是释放蛰伏的非理性力量,以酒神式的反叛,肯定女性生命的本能和冲动、激情与意志;以力的形式表达丰盈充实的生命,挑战父权文化的强力。其在独白中所展现的种种逆主流行为实质上是通过酒神式的实践形式艰难地抵抗着南方父权社会强加于自身的异己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