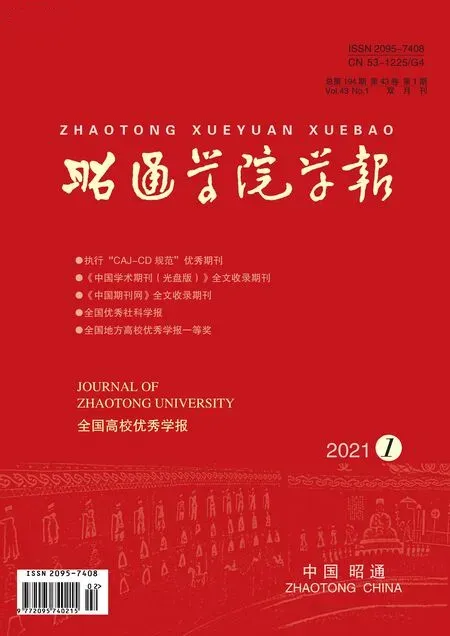虫的身体 神的灵魂
——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与小说《普罗米修斯》之间的关系探析
李蓓蓓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东欧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卡夫卡的小说题材“那么多地涉及到古典神话,动物学,梦魇般的幻想”[1]163。他对宗教和古希腊罗马神话有着深厚感情,著名神话小说可为证,如:《塞壬的沉默》《普罗米修斯》《海神波塞冬》等。卡夫卡的成功之处并不是原封不动的抄袭,而是在“产生心灵契合和视域融合的前提下,自主、主动地选择接受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接受影响”[2]35,改造创新,化为已用。
学者对卡夫卡的《普罗米修斯》和《变形记》分别做过详细研究,但将两者结合起来分析的则是凤毛麟角。发表于1931年的短篇小说《普罗米修斯》显然受到古希腊神话“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影响,而作者在最大程度接受原著影响的基础上又进行创新,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变成了被遗忘、被怀疑、被厌倦、被排斥的形象,甚至以往的英雄精神也遭到排斥与厌倦。学者卡西尔指出,“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等一起,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3]107,这让我们联想到另外一篇发表于1915年的经典作品《变形记》,与小说《普罗米修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文本细读,笔者发现卡夫卡的神话小说《普罗米修斯》实质是《变形记》的灵魂所在,进一步细说,尽管两部小说发表年份不同,但《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却是《普罗米修斯》主人公的神话人物变体,拥有甲壳虫的丑陋肉体,普罗米修斯的炽热灵魂与悲惨遭遇,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悲剧性更浓,更令人灵魂为之颤抖。笔者拟探索卡夫卡如何把创新后的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与格里高尔融为一体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热爱家人,心地善良,历经磨难而又惨遭遗忘,惹人生厌,最后惨死的“变异人”。
一、背叛遭困 化身为石
“他(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背叛众神,被牢牢地锁在高加索山上。众神派老鹰去啄食他不断再生的肝脏。在鹰喙不断啄食下,紧靠着岩壁的普罗米修斯痛不可忍,以至身体日益陷入岩石之中,直至完全没入其间”[4]252,《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的悲惨遭遇正是被缚在甲壳虫躯体内的天神普罗米修斯的境遇,甚至比天神惨遇更悲惨,更让人心酸落泪。
某日清晨,热爱工作、孝顺父母、疼爱妹妹的好青年格里高尔莫名其妙地变成一只巨大甲虫,此后也一直被困在硬邦邦的壳里直至死去。这一变身让人心生疑惑,如果说普罗米修斯为盗取火种拯救人类而违反心胸狭隘的统治者宙斯的戒条,因此被缚于高山之顶接受无辜的惩罚与痛苦。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在挣钱养家并为公司创造利润的好青年又背叛了谁?又违反了谁的清规戒律遭此劫难被缚于甲壳之中永不超生?小说中,主人公虽然变身为虫,但内心依然饱含对周围人的爱,期待有一天能够恢复真身继续养家糊口并为公司效劳,然而令人心酸的一幕是肉体被缚于虫壳内的善良人换来的不是同事、家人的同情与偏爱,而是“肝脏痛不欲生的被啄食”。刚刚变身时的格里高尔就感觉腰部隐隐钝痛,然而尚不明显。真正撕心裂肺的疼痛是在他尊重的“众神”,即:家人与同事化身为鹰鹫对他啄肝咬肺。第一只恶鹰是无赖的秘书主任,只把格里高尔当作工作机器,稍微懈怠一点就会恶语相加指责非难。得知年轻人没有赶上五点钟的出差火车时,立刻登门拜访。父母解释儿子可能真的病了,因为实在找不出什么误车原因,一年到头“这孩子只知道操心公事……这几天来他没有出差,天天晚上……看看报,或是把火车时刻表翻来覆去地看”[4]90,但秘书主任对此置之不理,只是一味的自私找借口认为做买卖人不能把这些小毛小病当一回事,指责格里高尔最近中饱私囊,私吞现款,工作效率低下。听到这些毫无事实依据的指责,格里高尔内心激动到控制不住地申辩起来,但是说出的话语在秘书主任听来根本就不是人的语言,而是一种动物的吱吱声。因此,主人公的血泪辩解没有被人理解,丝毫未起到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此时的年轻人如普罗米修斯一般被动接受秃鹰啄食而独自忍受钻心疼痛。秘书主任离开后,只留下家人,满以为不用再承受痛苦对待。恰恰相反,一只秃鹰离开非但不是痛苦的结束而是另一段痛苦的开启,因为家人看到格里高尔变形后的样子,以前所有的亲情与尊重都不见了。此时,第二个秃鹰出现,即:父亲。看到儿子变形,父亲不是心疼的拥抱安慰,而是“握紧拳头,一副恶狠狠的样子”[4]93-94,甚至“右手操起秘书主任……留在一张椅子上的手杖,左手从桌子上抓起一张大报纸,一面顿脚,一面挥动手杖和报纸,要把格里高尔赶回到房间里去”[4]96,嘴里无情地发出犹如赶猪仔的嘘嘘声。无助痛苦的格里高尔谦恭恳求父亲仁慈些,不要这么残忍对待亲生儿子,但是毫无作用,父亲只是把脚顿得更响。格里高尔吓坏了,好不容易退回到自己卧室门口,没想到腰被卡在门口,其中一只脚也被压得十分疼痛,锥心之痛还没结束,父亲就从后面不分轻重推了一把,使格里高尔跌进房间,身上鲜血汩汩直流昏厥过去。过了一段时间苏醒后,年轻人发现伤疤逐渐愈合,一条腿的毁坏并没有影响爬行。此时的主人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甲壳虫身份,承认两排细腿,承认虫子器官,但内心依然保存着纯真,“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庭克服他在目前的情况下必然会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4]99。当第三只秃鹰(妹妹)出现时,他以为看到了被解救的希望,心灵的痛苦可以减少些许,毕竟妹妹是这个家里和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但事与愿违,妹妹看望他就像是看望“一个重病人,甚至是陌生人”[4]99。每一次,妹妹在收拾哥哥吃过饭的专用盆子时必须用一块布包着盆子端走,态度无疑是在向哥哥受伤的肝脏上撒盐。当第四只秃鹰(母亲)口口声声说要探望儿子时,儿子开心极了,终于可以见到妈妈了,但是母亲对他的反应是吓的大喊大叫,头晕恶心惊跑出去,而主人公的反应则是平静而又疼痛,已经见怪不怪。
主人公日复一日对于家人的反应早已痛苦麻木,甚至已养成习惯。卡夫卡笔下的普罗米修斯逐渐陷入岩石,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渐渐嵌入甲壳虫,习惯了虫子生活,吃腐烂发臭的食物,喝变质的牛奶,视力退化到甲壳虫模糊的水平,喜欢胡乱爬行倒挂在天花板,流出许多粘液,躲到沙发下的黑暗中睡觉等等,唯有如普罗米修斯般的炽热灵魂还在提醒自己“人”的身份,但这种身份已经是“废人”的身份了。
二、惨遭遗忘 众生厌疲
“他的叛逆行为随着时光的流逝被淡忘了,数千年后,众神遗忘了,鹰鹫遗忘了,连他自己也遗忘了。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产生了疲惫,众神疲惫了,鹰鹫也疲惫了,连普罗米修斯的伤口也因不断地愈合而感到疲惫”[4]252。卡夫卡笔下的神话大英雄变成了被遗忘、被怀疑、被厌倦、被排斥的无用“废神”。久而久之,诸神、鹰鹫、甚至普罗米修斯自己都忘记了曾经的大英雄身份,正如格里高尔一样,时间长了,公司早就把他解雇了,家人也忘记了那个当初养家糊口的勤劳年轻人,父母忘记了儿子,妹妹忘记了哥哥,连格里高尔自己都忘记了曾为这个家立下的汗马功劳,只知道自己成了“废人”。
“卡夫卡的小说不仅从正面表现主人公对工作的热衷与渴望,同时也从反面阐释一旦失去工作,他们的命运会如何逆转。作为卡夫卡生前较为满意的作品,《变形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去工作将会怎样?答案是被遗弃和死亡”[5]20。作为长生不老的天神,普罗米修斯失去自由,失去为宙斯效力的能力,因此惨遭遗弃,格里高尔也在遭受这一切。在19 世纪的欧洲,工作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观念,别人会根据你的工作,对你做出评估,这种体制的形成,无疑也会影响到个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自尊心、自信心。变身后的格里高尔彻底失去工作能力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日子久了,家人早已忘记曾经有一位叫做格里高尔的家人,只知道隔壁房间住了一只令人恶心、浑身污秽、惹人讨厌的名叫格里高尔的怪物甲虫。妹妹和母亲彻底不把他当人看了,开始搬走原本属于格里高尔的家具。为了保护作为人类的标志,他趴在镜框上死死抓住,母亲由于看到这副德行吓晕了。妹妹恼怒的对他“又是挥拳,又是瞪眼”[4]109,全然不把他当作人。格里高尔对于把母亲吓昏一事深感内疚与焦虑。父亲回家后,格里高尔赶紧爬回自己房门口蹲在门前准备向父亲承认错误,但工作一天的父亲看到亲生儿子时丝毫不顾及父子之情,声音愤怒,表情严峻,把脚抬得老高准备踩死亲生儿子。格里高尔吓的乱跑,父亲并没有因为儿子受到惊吓而收手,反而把盘子里的所有水果装进兜里,一只接一只的朝着那只令他厌烦的虫子砸去,恰巧一个苹果打中后背并且硬生生嵌入虫壳,格里高尔疼急“挣扎着往前爬,仿佛能把这种可惊的莫名其妙的痛苦留在身后似的”[4]111,这次伤痛使得他一个月都处于瘫痪,伤好后的身体也是大不如前。此时,家里人都有了工作,而格里高尔已经成为累赘被关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正如普罗米修斯一样,几千年了,大家都感到疲惫。父亲成天抱怨“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就算是我的安宁、平静的晚年吗?”[4]113,父母、妹妹都在拼命工作,没有人真正关心他,所谓最亲近的妹妹每次送饭只是随脚一踢盆子,然后晚上回来用扫帚把食物扫出去,根本不管格里高尔是否吃过。房间里积满了灰尘,妹妹连看都不看一眼。家人只顾每天工作谋生,全然不顾他的感受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进格里高尔的房间。妹妹早就对他讨厌透顶,父母也是厌倦至极,全家人都疲惫了。终于有一天,格里高尔亲耳听到妹妹称他是怪物,是动物,不是哥哥,必须赶他走。父亲赞同妹妹的观点,也认为这个自称是自己儿子的虫拖累一家子。胆小怯懦的母亲则是露出疯狂的神色,恨不能这个化身为虫的儿子赶紧消失。格里高尔回到漆黑的房间,灵魂在冰冷的黑暗中颤抖,想到累赘身份,想到给家人带来麻烦,想到失去工作能力,形同废物,想到这里“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4]122。这个有着普罗米修斯灵魂的年轻人,彻底绝望了,麻木了,被遗弃了,但是那颗依旧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一家人的炽热之心,到死都没丢过。
三、功绩赫赫 凄凉一生
“如果留下的是那座不可解释的大山——这一传说试图对这不可解释性作出解释。由于它是从真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必定也以不可解释告终”[4]252。正如唐妙琴写到“卡夫卡的普罗米修斯神话预告了一个众神消瘦并隐退、英雄变形且枯萎的世界,一个失去任何可辨识之踪迹的沉寂世界”[6]21。随着时间的流逝,英雄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死了,甚至早已嵌入岩石面目不清,没有人记得他的丰功伟绩,徒留一座后人解释不清的大山,整个世界走向沉寂。
死亡是无法超越的生命底线,是不可预知的秘密,是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井,是无法穿透的岩石。死亡是不可以言说的,不可以解释的,如果你是一位生者,那么你的描述肯定是虚假的;如果你已经亲身经历过,那么你不可能再还魂讲述死亡。卡夫卡笔下年轻的普罗米修斯,纵然战功赫赫,也只落得凄凉一生以死结束。回想格里高尔一生,热爱工作,兢兢业业,是一名合格的旅行推销员。疼爱家人,孝顺父母,替父还债,无怨无悔,让母亲与妹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自己则是勤俭节约风餐露宿,为了家人连自己的婚姻也耽误了。
一个好青年究竟背叛了谁?又违反了谁的清规戒律遭此劫难被缚于甲壳之中?答案是他没有背叛任何人,是卡夫卡生活时期的资本主义冷漠的金钱人际关系戕害了他。年轻的普罗米修斯太累想要歇口气再继续工作。可是社会、家庭不给机会。他是一台二十四小时不停转动赚钱的机器,怎么能罢工呢?格里高尔刚想歇歇脚喘口气,就被残酷的社会、冷漠的家人发现,然后开始指责他,讨厌他,排斥他。面对毫无依据的指责,格里高尔不知道自己犯什么死罪,吓的躲进令人厌恶的甲壳虫内以期逃过一劫,但是这一劫却是将自己推向永不超生的死劫。失去赚钱功能的格里高尔无疑成了社会、家庭的“无用物”。格里高尔难逃一死,所有行动都是死亡阴影下的精彩表演,戴着镣铐跳舞。
卡夫卡生活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维系人际良好关系的纽带是金钱—利益,一旦纽带断裂,那么所谓的良好关系便被烧为灰烬。犹如一颗表面鲜亮,实质剧毒的苹果一样,一旦苹果裂开放剧毒跑出,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排斥、遗忘、厌倦、冲突。格里高尔与家人、社会维系关系的这颗苹果裂了,因此人情味也就消失殆尽,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在遥远的古希腊神话中,红苹果的出现拯救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那么卡夫卡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格里高尔)则死于这色泽鲜艳满身剧毒的红苹果。父母、妹妹、秘书主任是满身剧毒、色泽鲜艳的红苹果化身,他们让变身后的甲虫一口一口吃下红苹果慢慢死去。得知格里高尔死讯时,家人既不是抱头痛哭,也不是忙着举办葬礼,而是一身轻松,仿佛终于解脱羁绊。为了庆祝格里高尔的死亡,一家人选择去旅游,然后搬新家忘掉甲壳虫的噩梦。岁月流逝,英雄格里高尔早已嵌入岩石无影无踪。
四、结语
卡夫卡用其天才的笔触犀利改写出一位变形天神的悲苦遭遇,天神已经降下神坛落入芜杂社会中被残酷的社会绞杀、蹂躏、排斥,作者把一切真理赤裸裸的撕开给读者品看。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是小说《普罗米修斯》主人公的二次置换,是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变体。无辜天神所遭受的罪,格里高尔也在遭受,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产生一种震人心魄的悲剧力量。在以金钱、利益为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满腔热血却失去创造金钱价值的人无论如何努力的与命运斗争,都难逃外部力量的束缚与捆绑,最终走向死神。如果说神话故事的最后,卡夫卡尚且为天神留下一块岩石山,作为曾经存在过的一丝痕迹。那么,《变形记》的最后则是残忍的一无所有,甚至连荒冢也没给善良、孝顺的格里高尔留下,徒留“一把辛酸泪”,整个大地走向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