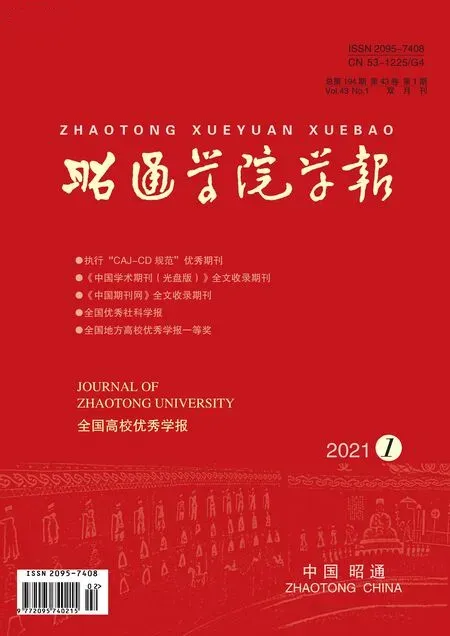姜亮夫与章太炎师承关系述论
唐 靖
(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章太炎是辛亥时期与孙中山、黄兴齐名的三大革命领袖之一,鲁迅称其“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民国建立后,章氏转而投身于国学研究,在学问方面卓有成效,终成一代国学宗师。为了培养国学传人,章太炎还十分欣赏中国传统的私人讲学方式,为此他曾拒绝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请,中意“学在民间”的私学立场,追求一种讲者与听者的对话和沟通,因而吸引了一批真正潜心向学的学者参与,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各自领域的文化重镇,“章门弟子”也随之名扬四海,能名列其中者其学术身价无形间陡然倍增。昭通籍国学大师姜亮夫,即是“章门弟子”之一员,本文以姜亮夫与章太炎先生之间师承关系渊源及教学互长为主线,探讨姜亮夫学术轨迹之一隅。
一、姜亮夫早年求学与章太炎的渊源
1922年9月,姜亮夫自云南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随即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受学于林山腴、龚道耕等川中名师。巴蜀学风较云南为盛,而章太炎在当时的四川学界同样具有不小的影响力。据姜亮夫晚年的回忆,林、龚二人在教法上各有风格,其中龚道耕给学生讲授《经学史》和《国学概论》,他认为坊间流传的《经学史》书籍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因而自编讲义供学生使用,只有《国学概论》一课则采用章太炎《国故论衡》作教材,而且“一句话一句话讲得清清楚楚”,要求学生认真记下。龚道耕不仅逐句讲解文句,重点还在分析章太炎前后思想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有时对某个观点某句话他觉得不对,他就批评。他说:‘我自己为什么不编这课讲义呢?我直率地说,我编这讲义不会比章太炎先生这个讲义高明,我也会有错误的,哪个没有错误呢?问题在于我们要知道错误是为什么产生的。’他讲,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中有些错误就是太炎先生思想有矛盾。太炎先生一方面在反对满清,反对专制,要倾向民国,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民国的故障多得很。这个时候已经是民国十三四年了,太炎先生已经是在不得已的困难时候了,所以他的文章已经开始回头讲经学、讲史学这些东西,同他在写《馗书》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所以龚先生教导我们,读书应该将著书的时代背景弄清楚。”[1]
因为有在成都高师就读期间的这段基础,姜亮夫在1926年8月选择到北京继续求学,最初考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科。当时在北师大担任教职的学界名流有黄侃、钱玄同、朱希祖等人,恰好都是后来学界戏称所谓章门“四大天王”的几个大弟子。虽然姜亮夫在北师大读书时间不长,但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与章太炎先生的一种间接学缘。
20 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学研究院,先后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组成“四大导师”的黄金团队,为民国学界留下一段佳话,并吸引全国有志学子纷纷进京赶考。正因为有“四大导师”坐镇,清华国学研究院除有超强的号召力之外,其门槛自然也高,因而在众多考生中流传“入学考试极难”的感叹,这却反过来激发了姜亮夫挑战和尝试的愿望。其时,清华入学考试的日期已过,已经在北师大就读的姜亮夫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提请补考,并意外得到允许,参加由梁启超和王国维分别主持的考试。王国维的面试题目是“小学”,姜亮夫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此前他已经把章太炎的《章氏丛书》反复研读,内心颇有一些感悟,所以当王国维先生出题考试相关问题时,他都能按自己的理解应对如流。王国维“看了我的卷子以后,便说:‘你可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我说:‘不是,我是四川来的。’他说:‘四川来的,怎么说的都是章太炎先生的话呢?’我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我突击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我说:‘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2]随后王国维便通知助手赵万里,让他向梁启超转告:“姜亮夫可以被录取”。由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在当时盛名卓著的王国维眼中,章太炎的学术地位依然不容忽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姜亮夫敲开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大门。
二、姜亮夫成为章太炎入门弟子的缘由与时间
1927年,王国维蹈昆明湖死,梁启超离京赴津,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一时间“群龙无首”,难以为继。毕业后的姜亮夫也离开清华,辗转到无锡、南通两所中学任教。因为王国维投湖事件的影响,他对屈原身世情有所感,遂收录楚辞材料,为之后写作《屈原赋校注》作资料方面的准备。此后,他又到上海担任了大夏、暨南、复旦等学校的教授,并在当时号为进步的北新书局任编辑。在此期间,“受余杭章太炎先生影响最大”,“一面教书,一面大量剪贴了唐宋以来的笔记、说部、文集等,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两史资料辑。”[3]
在孙虹所著的姜亮夫传中,曾提及姜亮夫列名章门的缘由:“章太炎先生最早知道姜亮夫的名字是因《国学商兑》(后改为《国学论衡》)上刊登的姜亮夫的七八篇学术研究论文。姜亮夫和章太炎先生的真正相识是在1931年,当时苏州公园有个学术演讲会,邀请章太炎先生、陈石遗先生、唐文治先生等人来讲学,而姜亮夫也被邀请去讲《易经》,于是在演讲会上认识了章太炎先生。1934年在云南老乡李根源的介绍下,姜亮夫正式成为章太炎先生的学生。于是在章太炎先生的指导下,姜亮夫的学术道路上又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4]
姜亮夫之得以列名章门,系经由李根源的介绍,这一点并无问题,但上文所述的时间却与事实稍有出入。据姜亮夫《自订年谱》1932年12月条下明载:“请列余杭先生门墙。李印泉丈为商之,先生欣然许诺,遂及曲室执贽三鞠躬之礼。先生知曾从廖、梁、王学,规以专家,且以顾、王之学励之。”[5]章太炎在近一年后的1933年11月14日《致潘承弼书五》的书信中也追述:“亮夫亦及吾门……亮夫既执挚于我”。[6]
由此可知,姜亮夫在1932年底且不晚于1933年11月,就已经正式成为章太炎的弟子,并非1934年。至于内中缘由,一方面固然因姜亮夫仰慕章太炎先生已久,一旦有当面接触的机会,即请托云南同乡且曾做过北洋时期国务总理的李根源从中说项,从而获得允准;另一方面,从章太炎角度显示,他在考察姜亮夫所著文章后,既爱其才,又惜其未得正确指引,因而慨然将其吸收入门墙,加以规范指引。
章太炎最早知道姜亮夫的名字,是因《国学商兑》(后改为《国学论衡》)上刊登的姜亮夫的几篇研究论文。而二人的真正相识,即在1931年。当时苏州公园举办学术讲习会,邀请章太炎、陈衍、唐文治等先生讲学。姜亮夫因为也被邀请讲《易经》,于是在演讲会上认识了章太炎。章太炎之所以认为姜亮夫“误入歧途”,是因为在创办国学讲习会的宗旨上,他与陈衍等人存在原则分歧,而姜亮夫此前又向陈衍主编的《国学商兑》经常投稿的缘故。
苏州国学讲习会创办后,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陈衍出任总编辑。陈衍字石遗,福建侯官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后任学部主事兼礼部礼学馆、北京大学等南北各大学教职,讲学40 余年,著书数十种,被唐文治誉为“诗文学大名家”。并应唐文治邀请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席。[7]陈衍既重考据,又重词章,讲究“通经致用”[8]。
章太炎与陈衍对国学会“宗旨不合”,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却都一直不公开言及内情,只是在隐忍多年后,终于在1935年于苏州锦帆路的个人居所,另外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并得到段祺瑞、宋哲元、马相伯、吴佩孚、李根源、冯玉祥等社会名流的赞助。[9]其中的李根源,既是原苏州国学讲习会的发起人,又列名章氏国学讲习会董事会名录,襄助章太炎。
从《国学商兑》第一期开始,章太炎就一直对刊名和载文颇不满意。他在给潘景郑的信中指出:《国学商兑》用“商兑”一词不妥,因为它与方东树《汉学商兑》高度重合;而方氏为今文经学家,本身排斥汉学,而国学会的《国学商兑》刊名取字相同,无疑就成了笑话,不如将“商兑”改称“商榷”,以避其嫌。除刊名不妥之外,章还认为陈衍的学识修养不足以担任主编,导致收录文章多有 “凭虚不根之论”,如果不加以删除,“非徒损害学会之名,亦且贻误阅者。”[10]
为此,章太炎进一步认为陈衍徒为人师,误人子弟,使姜亮夫等“误入歧途”,因此不避姜亮夫已为陈衍、金松岑弟子之嫌,接纳姜亮夫为弟子,以便引导。他在1933年11月14日《致潘承弼书五》中明言:“亮夫亦及吾门,始未知其深浅,今观《商兑》中所录二篇,其人误入歧途,较仲琪更甚,一方当以正言督戒……亮夫既执挚于我,亦非金(按指金松岑)、李(按指李根源)二君所专有。”[6]从书信文字可以看出章太炎对陈衍的不满,以及对门下弟子的高度责任感,姜亮夫的学术路径也由此经历从不完全成熟到成熟的转变。[11]
三、章太炎对姜亮夫学术路径的影响
姜亮夫与章太炎真正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列入门墙到去巴黎游学为止,不过三年有余,但这却是影响姜亮夫人生治学的关键时期。中年后的姜亮夫,计划为平生受教益最大的廖平、梁启超、王国维以及章太炎等四位先生撰写年谱,他自承:“余草《四先生合谱》,实以太炎先生为中心……四先生中,章公文虽深笃,而政治、学术之交叉最大。”他在《自传》中也回顾说:“此时接触了些学人,一些新知识,受余杭章太炎先生影响最大。”[3]通常认为,姜亮夫治学的方向,“大抵以小学立根基,以史学致宏大,而尤湛深于楚辞学与敦煌学。”[12]《自传》中所说的“影响”,在这几方面都有表现。
(一)语言文字学更加精细
姜亮夫在《自订年谱》中说:1932年12月列章太炎先生门墙,“先生知曾从廖、梁、王学规以专家,且以顾、王之学励之。”[5]他在晚年谈及个人治学方法时回忆说:章太炎先生三读《广韵》、九校《说文》,“根柢之学益精博”,才能写出《新方言》《文始》这样“总结三百年大成”的论著。[13]
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在研究汉语方言的方法、理论与材料诸方面,就多有直接学习和继承章太炎《新方言》之处。尽管《昭通方言疏证》的前身《昭通方言考》完稿于1925年,本身写作时间跨度长达六十余年,但仍然可以明显看出在方言词汇材料方面和研究理论方面与《新方言》之间的继承关系。有学者抽取《昭通方言疏证》第1 ~1 021 条词汇(占《昭通方言疏证》总数的50%)与《新方言》对比,发现这部分《昭通方言疏证》就有130 条与《新方言》所论词语音义相同或相通,约占抽查总数的12.7%,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情形: 一是《昭通方言疏证》明确引用《新方言》的材料,并以“师(按:指章太炎)曰”加以标识;二是《昭通方言疏证》引证了《新方言》的内容,但碍于表述不便而没有明确标明,如《疏证》第731 条与《新方言》的相关内容就相差无几;三是虽然《昭通方言疏证》没有直接引用《新方言》的材料,但二书所讨论词语音义相同或相近,所征引文献也相同或相近;第四类则是由于《新方言》所论不能概括昭通方言的内容,《昭通方言疏证》虽参考了《新方言》相关材料,但更多只能在《新方言》的基础上进行较为独立的探索。[14]
此外,20 世纪30年代姜亮夫讲授古文字学时所撰讲义《文字朴识》,也是结合王国维先生的古文字研究与章太炎先生的声韵学研究成果,考察文字孳乳演变轨迹的结晶。其《中国声韵学》一书,则如陈新雄教授在《几本有价值的声韵学要籍简介》中称道的那样:“叙述颇为简明,编排也颇有秩序,立论多本章炳麟、黄侃的说法,参以语音学原理,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声韵学要籍”[15]。
(二)楚辞学研究具有更宏阔的视野
研治楚辞需要有宏阔的视野,能够把触角伸展到楚辞之外,以经治骚,以史证骚,而不是就骚论骚,这是章太炎、姜亮夫两代学人共通之道。
研究楚辞学的难点之一,在于名物考证无确切和直接的证据,只能在其他领域加以印证。章太炎考证《离骚》“蹇脩”一词,就采用了以史证骚、以经治骚的方法。《离骚》“吾令蹇脩以为理”句,王逸认为其中的“蹇脩”乃是“伏羲氏之臣”。章太炎则在考察《汉书·古今人表》之后,发现上古人物中并无“蹇脩”之名,从而用“以史证骚”的方法推翻了王注。章氏进一步通过《尔雅·释乐》 “徒鼓钟谓之修,徒鼓磬谓之蹇”的记载,论证“蹇脩”实为声乐,其证据坚实,解决了两千余年来的一个文字悬案。[16]这一结论得到楚辞学界普遍的赞誉,汤炳正评价其“当为不易之论”[17]。姜亮夫对章太炎先生独具慧眼的发现表示钦佩,称“此说最为有致”[18]。但他对《尔雅·释乐》的记载仍然表示怀疑,因而将“蹇脩”一词改以通假释之。章氏师生所作的认定,实是以经学治骚的一大创获。治国学要有宏通的视野,仅限于楚辞的纯文学研究固然有其价值,却很难有大的突破。有鉴于此,姜亮夫、闻一多等楚辞学者,都能以宏通的视野研治楚辞,在这个流派的学者身上即隐约可见章氏实证之学的遗风。[19]
此外,对于《楚辞》的成书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是由刘向纂辑而成,王逸《离骚后叙》就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20]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肯定“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21]不过这个观点一度被现代学界所否定。朱东润就认为“《楚辞》出于后汉王逸”,所为“刘向所集”,不过是“王逸假以自重”而已。[22]汤炳正以《楚辞释文》排序为据,认为世传十七卷本的王逸《楚辞章句》,“乃先秦到东汉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中积累而成,并不是刘向一人所纂辑的。”[23]客观上讲,学界质疑刘向最早纂辑《楚辞》有其道理,因为在刘向之前的文献中早有“楚辞”之语。金开诚就推测在刘向编定十六卷本《楚辞》之前,应该有更早版本的楚辞选集,因为“汉时之书无非是联简成册、束帛成卷而已。”[24]
基于这样的事实,章太炎围绕《楚辞》成书问题,提出“《楚辞》传自淮南”的观点[25],姜亮夫则在章氏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自《离骚》至《招隐》为书,必刘安之所为”;“淮南都寿春,本楚之旧壤,屈子放江北,必曾流浪其地,则民间必多传屈子作品,安得与招致之宾客,从事搜集,故今传屈原作品,皆已在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此事中矣。此可谓汉人所传屈子文集之最早传本云。”[26]至此,在历代学者前后相继的合理推测下,学界才逐渐趋于定论,认为楚辞作品最初是以单篇形式流传,至淮南王刘安时始因封地之便,纂辑成书。[27]
(三)以历史学的宏大为学术归宿
章太炎晚年学术日益趋于史学。日军进逼,他预感国家将遭遇沉沦,因而当有人问及:可有永久宝贵的国粹?他回答:“有之,即其国以往之历史也。”对此,钱穆沉痛写道,章太炎“仅此一言,足以百世矣”[28]。
这样的学术心态影响到他对弟子的言传身教。姜亮夫拜章太炎先生为师后,即倾心于对历史学的探讨。曾立志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之体例为《宋史注》,为此阅读了大量的唐宋别集及笔记。因种种原因,《宋史注》后来未能完成,但另外成就了1933年上海民族月刊社出版的《夏殷民族考》、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等书,成为姜亮夫研究历史学的开端。[29]
姜亮夫自述说:章太炎先生曾切实指示他“从杜佑通典入手”读史,他自身也觉察到历史乃民族之大根大本,切实研读史学,才能使文字学、声韵学拥有坚实的基础。当时他一方面教书,另一方面为了生计而兼职编书,章太炎告诫他要做一个向着真正学术道路前进的人,并把“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这两句话提得很高,既透彻发挥“甚深微妙”之义,又紧贴民族兴亡,使姜亮夫深感“这是合于父亲影响我的爱国思想的,使我座上发大冷汗,誓本先生之言做去”;“章先生以历史为基础的教导,给我以勇气和信心”,“不要作空疏之学、哗众取宠之学”,从而实现姜亮夫继成都高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求学路上的“第三变”[30]。
(四)明了剪裁与选择为学术基本之道
在经历学术生涯第三变之后,姜亮夫对历史学的意义有了新的领悟。但正如他事后追忆:“当时我又有些发脑热,狂想遍注二十四史。大家批评《宋史》最芜杂,于是我就想从《宋史》着手,把宋人文集尽量看过,作为每个人物的碑传材料。要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例为之注,抄了三百来种的宋人文集,同时也看了些宋、元、明人的笔记,觉得可贵材料很多,每天扣足两册,作了记号,分类剪贴,成为社会、经济史料两类。”[30]
有见于此,章太炎对姜亮夫刻意旁敲侧击,借助谈及甲骨文研究的问题,便以“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喻,劝导他不必事事亲尝。同时又谆谆教诲说:“读书和闹革命是不同的。闹革命开始要有一股热忱,读书自然也要有一股热忱,但革命热忱是爆发性的,爆发后不回头;读书的热忱是咀嚼性的,要细细地体会比较。”这段话深深印在姜亮夫的脑海。
1934年,章太炎又为姜亮夫亲书一副楹联:“多智而择,博学而算;上通不困,幽居不淫。”其上联语出自《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第四十九》,意指有修养的人虽广泛学习,还要能够加以选择和鉴别。章太炎进一步对姜亮夫说:“亮夫,我老老实实对你说,你的毛病恐怕在‘博学不算’,你什么都要读,不计算自己有多少精力。‘多智’应有选择,做学问,不要不加选择。”[31]章太炎的教导切中姜亮夫的毛病,他当即叩头致谢,并立誓引以为戒。
四、姜亮夫对章太炎学术偏执的辩护与纠正
教学相长,学术的受益往往都不是单方面的,在文字学和楚辞学领域,姜亮夫对章氏的学问就多有延伸和发展。此外,章太炎治学严谨,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甲骨学却一直持不信任态度。章太炎知道姜亮夫曾随王国维治甲骨学,颇不以为然,于是就对姜亮夫发表一段针对甲骨文的看法:其一,对甲骨文的来源保持怀疑;其二,认为搞语言文字研究,重心应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适当参照殷周金文即可,不必钻研不可靠的东西。对于王国维借助甲骨文论证《史记》有关商代史实,章太炎委婉评价说:“王君证《史记·殷本纪》无虚言,说明史公书之可贵,而《殷周制度论》亦能服人心腹”,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成为后人研习甲骨文的理由,因为甲骨文“真伪难辨”,所谓“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即指此而发。章太炎又说:“凡大儒之学,以关族性为圭臬,何必定马肝?马肝亦有毒,何必为此雕虫小技?”对甲骨文的怀疑与蔑视,溢于言表。20 世纪初,中国学界曾因甲骨文、敦煌遗书、秦汉简牍及明清档案等新问世材料的运用,而使传统学术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但作为在学界一言九鼎的章太炎,却长期对这些新材料存有偏见,后人将其怀疑归纳为四个方面:“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
姜亮夫内心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但他对章太炎先生的初衷仍然予以肯定,认为“凡所勉勖者,皆期望与鼓励之辞;而所指斥,皆出真诚,有似严父,而爱护之实有似慈母。”[32]但在甲骨学研究方面,他并不打算遵照章太炎的意见去做,而是依然执着于甲骨研究,认定“甲文为中国较早之文学,杂证八卦后于甲文及《易》为春秋战国时术数之学”。这一观点刊布为文,引起章太炎极大的不满。章门弟子中地位最高的黄侃,也是姜亮夫极其敬重之一人,在其《日记》癸酉四月廿七日丁亥条下记载:“云南人姜寅清来,尝称从予讲,省记良是。其人盖用心于龟壳子者,王忠愍(国维)之徒也,非吾徒也”[33],其态度比乃师还要更显固执。
章太炎和黄侃对甲骨学的态度,姜亮夫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却并未退缩。在赴章门拜谒时,章太炎温语喻之曰:“凡学须有益于人,不然亦当有益于事。古史诚荒渺难稽,然立说固与前人违异,亦必其可信乎?治小学为读书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出之以谨严,亦可也,必以此而证古史,其术最工眇,要近虚造,不可妄作。”在姜亮夫赴欧洲留学前夕,章太炎设宴款待,席间“复言甲骨不能相信”。姜亮夫一方面为章太炎辩护说:“甲骨出处不明,又无其他有力佐证,当时唱之者如刘铁云辈,又非笃行纯学之士,孙诒让亦谨严无他规模,以一融通四会之学人,欲其贸然承认一种新学问,有所不能,亦有所不可,故早年之指陈吉金、甲骨之弊者,宜也”,对章太炎表现出相当的理解。另一方面,姜亮夫并未知难而退,反向太炎师笑以请曰:“倘有的证,足使先生信其为殷商时物,则先生亦将为鼓吹乎?”章太炎笑回:“但恐君辈终不能得的证耳。”从对话中可见,章太炎对金文及甲骨,并不是为抵制而抵制,而是因其“来历不明”而疑之。随着甲骨文研究的日益成熟,成果日益丰富,加之姜亮夫等弟子的宣传与说服,章太炎的态度也相应出现松动,“此固治学谨严者应有之态度,世人方以此见诟,盖不思之甚耳。”[34]
五、结语
在姜亮夫成为章太炎先生及门弟子之后,虽然二人当面接触的机会并不太多,但所受影响却不容忽略,以至姜亮夫事后追忆说:“暇日走同孚里问业,乃昫昫如老妪,字爱之情,悃直无私,既服其学,亦服其人,十余年馨香以祝者,得一二现实。”“太炎先生教益,使我一生受用无穷,使我一生不敢稍怠。”正是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几位学识宏通的大师引领,才为他开启了迥然有别于世俗人生的学术殿堂。
就章太炎方面而言,他门生弟子遍天下,同时行事复杂,缺点与优点一样突出,常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以致于以“疯子”名之。但他能针对每一位弟子的特长进行因材施教,对弟子的创新总是持积极鼓励的态度。章门弟子之所以能在各自领域有所创新和成就,与其理解与包容有莫大关系。太炎晚年曾引戴震语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原因在于“大国手”的弟子,往往在老师的阴影下亦步亦趋,不敢超越雷池。[35]有鉴于此,他鼓励学生“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36],即使是弟子“背离师道”,也宽容待之。对于章太炎晚年沉溺国学的态度,引领新文化运动风潮的弟子多半都不认同,周作人、鲁迅等尤其激烈。周作人干脆公开“谢本师”,宣布与章太炎倡导国学之路划清界限[37];鲁迅也曾说太炎先生“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38]。尽管如此,章太炎北游时照样与周作人共宴合影,并为其手书条幅;临终前的鲁迅,则依然对太炎先生怀有深厚敬意。包括姜亮夫在内的章门弟子,敢于突破师说樊篱,从而共同构筑起近代中国学术界最具魅力的新型师生关系。[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