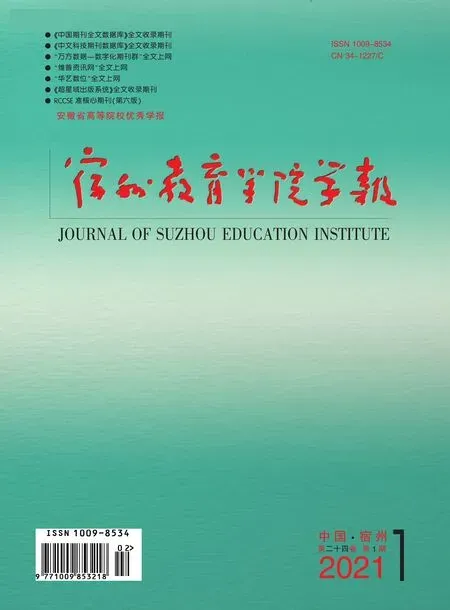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卷》中的入声理论
范春光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顾炎武是清代古音韵学研究的开创者,其音韵学成就集中体现于《音学五书》,其入声理论集中体现于《音学五书·音论卷》。 《音学五书》被誉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作”,主体上包括《音论卷》《诗本音卷》《易音卷》《唐韵正卷》《古音表》五部分[1]。 《音论卷》是全书的纲领,综合论述了汉语古音韵学的源流与发展,分为上、中、下三卷。 上卷探讨了古今学者对音韵的认识、韵书的始源与发展、唐宋韵谱的异同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下卷论述了顾炎武对转注、反切、反语及读若等方面的认识,中卷的《古人四声一贯》《入为闰声》《近代入声之误》等着重阐述了顾炎武的入声理论。
《音学五书·音论卷》包含两个重要理论:一是“古诗无叶音理论”,顾炎武在明代陈第“古音时地说”的启发下,著《音学五书》以证今音不同于古音,并提出“古诗无叶音”的观点;二是“入声理论”,主要包括 “古人四声一贯”“入为闰声”“近代入声之误”等,并在此理论基础上,首创以阴声韵配入声韵的理论,建立了上古音韵研究的入声系统,开创了古音研究的新局面。 现将顾炎武 《音学五书·音论卷》中“古人四声一贯”“入为闰声”“近代入声之误”理论阐释如下。
一、古人四声一贯
顾炎武认为“四声之始起于江左,四声之说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1],汉语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的理论始于南朝周颙《四声切韵》与南朝沈约《四声谱》,即周颙和沈约是四声声调理论的发现者与命名者而非创造者。 顾炎武认为古人在先秦时期创作诗歌韵文的时候, 声调就已经出现了迟疾、轻重的区分,即“长言”与“短言”的声调现象在上古音中就已经客观存在了。 上古音的“长言”就是今音的“平声、上声、去声”,“短言”就是今音的“入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声调的不同。 如《公羊传》:“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 ”何休注曰:“伐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 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 ”[2]汉代时期的学者已经懂得语音的音理描写,因此,顾炎武认为上古音虽无四声之名,但已有四声之实。
顾炎武也注意到“四声”的两个重要特征:“其重、其疾,则为入、为去、为上;其轻、其迟,则为平。 ”[1]从四声的轻重、迟疾方面区分了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也即是,一个字读得轻点、迟点就是平声字,读得重点、疾点就是上声字,再重点、疾点就是去声字,最重、最疾的就是入声字。 因此,从音长的角度来看,上古入声的特征是“短言”;从音强的角度来看,上古入声的特征是“重而疾”。
“古人四声一贯” 指诗歌韵文的字可以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的读法,即韵脚的四声是相互贯通的。 顾炎武注意到上古音的系统性,对《诗经》《周易》等先秦诗歌韵文进行分析后,发现了“四声皆可押韵”的音韵规律。 这是顾炎武在音韵学研究上的一大贡献。
顾炎武在《音学五书·音论卷》中还提出“有定之四声”与“无定之四声”的观点,却没有具体指出哪类字是有定的、哪类字是无定的。 朱晓农(1987)认为:“似乎平声字是有定的,而仄声字是无定的”[3]。 “有定之四声”指在上古非韵文中,平、上、去、入四声字都有固定的读音, 即每个字有一个固定的读音;“无定之四声”指在上古韵文中,平、上、去、入四声字为了押韵, 读音是可以相互贯通, 即平声字只有一个读音,上声字可以有平、上两个读音,去声字可以有平、上、去三个读音,入声字可以有四个读音。 平声字只有一个读音,而上声字、去声字、入声字都属于仄声字,可以不止一个读音,因此,平声有定而仄声无定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
顾炎武还提出 “有定之四声以同天下之文,无定之四声以协天下之律” 的理论,“有定之四声”适用于散文作品,我国最早的散文《尚书》并不讲究押韵,每个字都有一个固定的读音。 “无定之四声”适用于诗歌韵律,《诗经》《离骚》等诗歌韵文常用于歌咏,可以改变某字的读音进行押韵。 顾炎武采用“本证”与“旁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大量的先秦文献材料对古本音进行了论证。
二、入为闰声
理解“入为闰声”的关键在于理解“闰”字,《说文解字·王部》:“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 《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 ’”[4]依据《说文》,“闰”字最初是历法的术语,本义是余数。 古人根据历法推演出了闰月的规律,设置了闰月,故“闰”有“变”之义。 汉语音韵学的“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是由中国传统乐理的“宫、商、角、徵、羽”五音加上“变宫、变徵”二音构成的,“变宫、变徵”又称为“闰宫、闰徵”。 正如顾炎武所论,“故入声,声之闰也,犹五音之有变宫、变徵而为七音也。 ”因此,顾炎武认为入声是平、上、去三声的变声。
“入为闰声”也为《诗经》的用韵情况作出了合理解释,顾炎武对《诗经》入声韵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考证,得出了“入与入为韵者十之七八,而入声与平上去为韵者十之二三”的结论。 在上古音韵中存在入声字,入声字既可以与入声字为韵,也可以与平声字、上声字、去声字为韵。 因此,顾炎武把入声当作四声的闰(变)声,既可以独立成韵,也可以变为平声韵、上声韵、去声韵。 以此,顾炎武的“入为闰声”理论也解释了“平、上、去三声固多通贯,惟入声似觉差殊”的音韵学问题。
陈燕(1998)认为顾炎武的“入为闰声”含有极强的“叶声”之意[5],论文认为顾炎武“入为闰声”与“叶声说”有本质的区别。 顾炎武支持陈第“古音时地说”的音韵学主张,反对临时改变声调以求和谐的“叶音说”,并提出“入为闰声”理论来否定“叶音说”。 顾炎武认为在上古诗歌韵文中,平、上、去、入四声皆可押韵,入声是平、上、去三声的变声,并非临时改变声调以求和谐押韵,此与“叶声说”有本质区别。 “古人四声一贯”和“入为闰声”的观点是对宋代儒学“叶音说”的否定,江永对顾炎武反对“叶音说”的主张给予了肯定。 江永认为“顾炎武始去此病,各以本声读之。 不独《诗》韵当然,凡古人有韵之文皆如此读,可省无数纠纷,而字亦得守其本音,善之尤者也。 ”[6]
三、近代入声之误
顾炎武是第一个从上古诗歌韵文中的实际用韵情况来研究《广韵》中平声韵与入声韵的相配模式的学者,顾炎武认为《广韵》等韵书将平、上、去、入四声韵相承的模式当作古平声韵与入声韵相配模式是错误的,并列举了大量例证以证其观点,如:
①“屋”之平声为“乌”,故《小戎》以韵“驱、馵”,不协于东董送可知也。
②“沃”之平声为“夭”,故《扬之水》以韵“凿、乐、襮”,不协于冬肿宋可知也。
《诗经·小戎》首章:“小戎俴收,五楘梁辀。 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此章“屋”与“驱、馵”同韵。 《诗经·唐风·扬之水》首章:“扬之水,白石凿凿。 素衣朱襮,从子于沃。 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此章“沃”与“凿、乐、襮”同韵。
③“术”转去而音“遂”,故《月令》有“审端径术”之文。
④“曷”转去而音“害”,故《孟子》有“时日害丧”之引。
《月令》:“审端径术”的“术”通“遂”,入声字“术”应该读为去声字“遂”。 如《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郑玄注:“术当爲遂。 ”《周禮·地官》:“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孟子》:“时日害丧。 ”的“害”通“曷”,入声字“曷”应该读为去声字“害”。
⑤“质”为“不传质为臣”之“质”。
⑥“觉”为“尚寐无觉”之“觉”。
⑦“没”音“妹”也,见于子产之书。
⑧“烛”音“炷”也,著于《孝武之纪》。
《孟子·万章下》:“不传质为臣。 ”赵岐注:“质,执也”。 《诗经·王风》二章:“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 ”此章“觉”与“造”同韵。《集韵》:“没,莫佩切,音妹。 ”《前汉·武帝纪》:“见光集於云坛,一夜三烛。 ”服虔注曰:“烛,音炷。 ”
通过例证①“屋”之平声为“乌”、例证②“沃”之平声为“夭”证明入声韵可以变为平声韵,通过例证③“术”转去而音“遂”、例证④“曷”转去而音“害”证明入声韵可以变为去声韵,又通过例证⑤的“质”实际为“质”、例证⑥“觉”实际为“觉”、例证⑦的“没”音“妹”、例证⑧“烛”音“炷”证明入声韵可以变为阴声韵。 顾炎武借用诸多例子指出了近代入声系统上的错误,首创以阴声韵配入声韵理论,突破了中古韵入声韵配阳声韵的思维模式。
顾炎武研究《广韵》平声韵与入声韵相配模式的结果是“其韵中之字,随部而误者,十之八;以古人两部混并为一而误者,十之二。 ”顾炎武以上古音韵为研究对象,而《广韵》以中古音韵为研究对象,二者的研究对象完全不同,音韵系统、所收韵字、古韵分合也不尽相同。[7]
顾炎武认为“平之读去、上之读去,人不疑之。入之读去,而人疑之。 后之为韵者,以‘屋’承‘东’,以‘术’承‘谆’,以‘铎’承‘唐’,以‘昔’承‘清’,若‘吕之代嬴,黄之易芈’。 ”顾炎武“平之读去”以平声字“中、将、行”读为去声字“中、将、行”为例,“上之读去”以上声字“语、好、有”读为去声字“语、好、有”为例,“入之读去”以入声字“宿、恶、易”读为去声字“宿、恶、易”为例,发现“歌、戈、麻三韵,旧无入声;侵、覃以下九韵,旧有入声”,认为上古入声韵与阴声韵的联系紧密, 提出入声韵与阴声韵相配的理论。
结 语
“古人四声一贯”指四声在诗歌韵文中可以相互通贯,核心在于“有定之四声”与“无定之四声”。“有定之四声” 是指每个字都有一个固定的音值,“无定之四声”是指在上古诗歌韵文为了押韵,读音是可以不固定的,整体上来看,平声字是有定的,仄声字是无定的。
“入为闰声”指以入声配平、上、去声,以补足各韵之间的差额, 入声在上古诗歌韵文中可以变为平、上、去三声来押韵。 论文认为顾炎武提出“入为闰声”有三个目的:一是证实上古音存在入声韵,二是为《古音表》十部仅四部有少数入声字的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三是反对宋代儒学“叶声说”。
顾炎武在提出“近代入声之误”的理论基础上,首创入声韵与阴声韵相配的理论,突破了中古韵书以入声韵配阳声韵的思维方式,为阴、阳、入三分相配的古韵分部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顾炎武在“古人四声一贯”“入为闰声”“近代入声之误”等理论的基础上,首创以阴声韵配入声韵的理论,建立了上古音韵研究的入声系统,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开创了古音学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