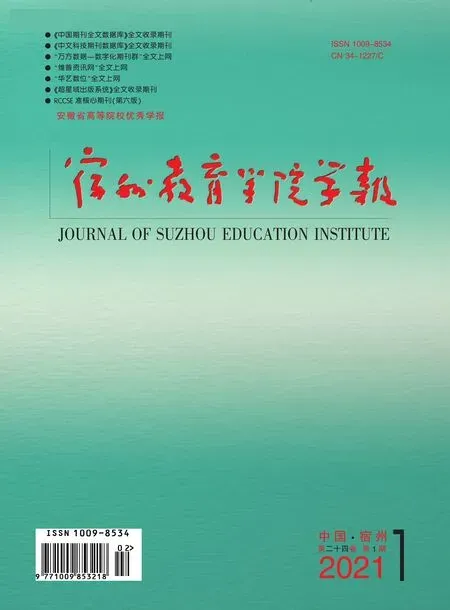小议科技翻译伦理的建构
邹幸居 何高大
(广东白云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450)
“伦理”一词源于希腊,包含了“道德”“价值”“正义”等意义[1],是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的结合体[2],“伦理产生的目的是处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困难”[3],因此,伦理具有普适性,包括了经济伦理、环境伦理、政治伦理、国际伦理、科技伦理、管理伦理、家庭伦理、翻译伦理。
近年来,翻译研究出现“伦理转向”的热点,然而, 科技翻译伦理的探讨却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当前科技翻译伦理的研究存在理论研究针对性不足、研究语料不足、伦理维度偏少等问题[4]。 鉴于此,本文将探讨如何建构科技翻译伦理,以推进科技翻译伦理的系统性研究。
一、科技翻译伦理的内涵
科技翻译是译者用译语表达原语科技信息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5],解决的是“译什么”“如何译”“如何评”的问题。 科技翻译伦理是科技翻译活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从社会道德层面和职业关系层面揭示科技翻译行为该如何规范,解决的是“该译什么”“要怎样译”“译得怎样”的问题。
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中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行为规范,调和了科技“求真”和“求善”之间的矛盾,科技家在追求科技突破的同时,受到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的约束。 科技翻译伦理和科技伦理存在着翻译要忠实传递原文本的科技信息和该科技信息“善”否的矛盾。
翻译伦理指的是翻译活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涉及到翻译主体间的责任和义务。 科技翻译伦理与翻译伦理有共性,但也有个性,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如下表所示:
二、科技翻译伦理的建构
(一)科技翻译伦理建构的理论基础——“善”
当前翻译伦理的研究以规范为特征,探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但是,规范无法涵盖翻译伦理的全部内容,必须关注道德价值问题[6]。规范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具有互补性。规范伦理学重规范人的行为,轻人的德性培养,但是能够在人面对实际的道德问题时提供行动的实践性帮助; 德性伦理学重人品德的培养却轻人的行为准则,对社会德性和个人德性的双重关注能够纠正当前只重视行为正当性的弊端。 科技伦理中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的融合有助于解决科技进步和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 纵观目前的科技翻译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文本存在“德”“能力”和“监督”三缺失的问题,而科技翻译伦理的建构必须依赖规范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相结合的原则。

伦理学是关于“善”的学问,伦理的讨论离不开“善”;科技翻译要准确传递科技信息,主要是“善”的信息。 “善”有三层含义[7]。 一是人性美德本位论,重点关注人性美德,与中国“善”的伦理内涵一致。二是从世界本体意义视角定位的善理念,认为“善”是指引一切的普遍原则,是“真”和“美”的导引,“至善”是指各方面的和谐,类似中庸之道。 三是在人类社会秩序本位领域定位的善或道德律令,亚里士多德的“善政”“国家的善治”观和儒家“以仁治天下”的主张一致。 第一类“善”指人的德性品质,强调了“善”的“自律”内涵;第二、第三类“善”指人类社会各领域行为的导引,强调了“善”的“他律”内涵。 中西“善”伦理观的融合体现了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统一。 因此,可把“善”作为科技翻译伦理建构的理论基础。
(二)科技翻译伦理建构的“自律”维度
科技翻译伦理建构的“自律”维度强调“善”的道德教化作用,包括了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两个层面。
1.科技翻译伦理建构的“善”德
(1)科技翻译“善”德的内涵
科技翻译的“善”德指的是科技翻译道德,科技翻译必须符合科技伦理, 既能准确传递科技信息,又能对读者、出版市场、翻译界、社会和国家带来正面的影响。
科技翻译活动各方的“善”德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古代,政府主持下的两次科技翻译高潮,即始于1606 年的以“科学传教”为宗旨的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5]和清朝末年出于传教、外交、洋务、维新、立宪、革命等需要的第二次科技翻译高潮[5],均达到了“开启民智”和“富国强兵”的目的。 五四期间,归国留学生们翻译外国书籍,介绍西方科技理论和先进科技。 文革期间,科技翻译人员翻译大量工业生产和国防科技文本,推动国家工业发展、加强国防力量。 如今,国家制定了科技翻译“请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跨世纪重大战略决策,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科技、生产力发展。
(2)科技翻译活动各方的“善”德
政府文化部门要把关控制, 确保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科技文本符合科技性,对读者、国家有益。
翻译发起人、委托者、出版商要把关控制选题的“善”;要挑选能胜任科技翻译工作的译者,重视译者的话语权,在符合伦理道德的前提下,让译者参与选题、享有更多选择翻译策略的自由。
译者的素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 朱自清、傅斯年、鲁迅都曾著文论述科技翻译者的素养[5]。 译者的“善”德表现为:自觉接受科技伦理的约束,选译不违背伦理道德的科技文本, 遵守科技翻译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具备科技翻译的责任感和责任心,对客户、译语读者、社会、国家负责;掌握科技翻译技巧、扩大科技专业知识面、提高个人双语或多语语言水平,与时俱进、学习新的科技翻译理论如变译论,为读者而变,从而推动文化间的交流,促进译者职业化进程[8];遵循科技翻译伦理原则,选择恰当的科技翻译策略,协调好原作、译语读者、译作的关系。
译语读者要对科技读物进行筛选,自觉抵制不符合客观事实、不利于人类生存、损害国家利益的科技文本。
校对者、编辑要以是否符合科技伦理和我国社会道德规范的标准确定译本的删减与否。
翻译评论者要具备良好的素养、胜任科技翻译评价工作,能够遵循科技翻译伦理的原则评价译本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与译者、译语读者为善,启发译者如何提高译文的质量、实现科技文本的语用价值。
(3)科技翻译“善”德的培养
首先,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作用,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教育人们,使得人们重视科技伦理和科技翻译伦理,自觉地接受“善”的科技和科技文本,从而推动科技翻译向“善”的方向发展。
其次,在当今的技术化时代,应当重视翻译伦理教学, 在大学翻译专业开设翻译伦理道德课,强化翻译教师的职业伦理[9],教师能够以身作则,向学生讲授科技伦理、科技翻译伦理的知识,培养未来科技翻译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最后,科技翻译人员要接受在职的道德教育。 哲学家们和研究者均认为,工作中的案例分析和同行道德问题研讨能够持续提高员工的道德修养[10]。 可让科技翻译人员参加工作坊形式的综合道德培训课程,分析真实案例并分享个人的科技翻译伦理选择经历,培养他们的科技翻译伦理观念。
2.科技翻译伦理建构的“真善美”
从中西“真善美”伦理观融合的视角看,“真”指正、不虚假,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规律;“善”指正的道德、“美”德,即人的行为实现对群体有利的目的;“美”、“善”统一,指客体使主体产生的精神愉悦的体验。 翻译伦理的建构以译者求真于原文、臻善于读者、达美于译文为目标[11]。 因此,科技翻译伦理的建构也要以“真善美”伦理思维为基础,规范科技翻译各方的行为。 求“真”是基础,追求科技性;求“善”是导引,追求译德;求“美”是效果,追求和谐性与艺术性;其中,“善”是统摄三者的灵魂。
(1)科技翻译活动的伦理
①求“真”是科技翻译的基础
科技翻译求“真”的前提是科技文本“善”。 科技翻译不仅存在“求真”和“求善”的矛盾,还存在是忠于原科技文本信息还是忠于科技伦理的矛盾。 译者“求真”即求“达意”,要确保译文能够准确无误地传递原文的科技信息,要用语规范、合体,顾及文本的内容是否对译文读者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损害国家利益;译者“求善”,即对译文读者和国家“行善”,要对翻译的科技文本进行筛选,甚至删减、改变内容。矛盾的调和点在于“求善”,只有科技研究和反映科技成果的文本“向善”,科技翻译才可以“求真”而“求善”,通过翻译传递科技信息,为译文读者和国家造福。
科技翻译求“真”的程度以文本“善”的程度作为依据。 若文本全“善”,全部内容符合科技性,不包含任何损害译语读者、社会、国家利益的科技信息,译者可根据全部译语读者需要考虑全译。 鲁迅、矛盾、艾思奇、陈康持认为科技信息的准确传递最重要,能够形意兼顾最好,若不能,就取意舍形、因意变形和因意造形[5]。全译是完全求“真”。若翻译材料只是部分“善”,包含有害的科技信息,译者可以根据特殊读者的需要选择变译。 变译的思想古而有之,道安、梁启超、严复、傅斯年都提出翻译不重要的科技著作可采用变译的方法[5]。 现代译论认为全译是微调,原文的结构、内容不会大变;而变译是大调,原文的结构、内容会随翻译目的和文本的性质而改变,若译者经过权衡,认为变译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促进文化交流,则可以选择不严格求“真”[12],因此,变译是部分求“真”。
②求“善”是科技翻译的导引
科技翻译的目的和后果必须是善的。 “善”的翻译目的意味着翻译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是正面的。 翻译发起人、委托人、出版商、译者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确保所选译的科技文本满足译语读者需要、向他们传播符合客观规律的科技信息、使他们增长科技知识,符合科技伦理,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还应该考虑国家的利益,保证翻译的材料有利于国际科技的交流和国家科技的发展,注重其现实性、实用性和效益性。
科技翻译的过程是善的。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以“善”为导引,处理好原作、译者、译作、译语读者之间的关系。 译者应在求“善”的前提下求“真”,根据翻译目的和文本的性质,确定倾向哪方。 例如,“真”是最重要的科技翻译原则,但是,“真”的前提是科技文本传递的内容是“善”的。 若确定科技文本中所有信息都是“善”的,译者就要求“真”,要根据全部或部分译语读者的需要选择与作者为善或与译语读者为善,使译作完全或部分忠于原作,再现原作的科技性、准确性、重理性。 若确定科技文本中只有部分信息是“善”的,译者应对原作进行增减处理,以防止译语读者受到不良科技信息的毒害。
③求“美”是科技翻译的效果
科技翻译求“美”即要达到“至善”。 “美”和“善”统一,孔子认为中庸之道为至善。 和谐是“美”的具体表现形式。 支谦主张翻译方法要适度,不偏不倚,达到和谐状态[13]。 这也是马建忠“善译”观和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的观点。 科技翻译中全译求的是原作和译作的和谐; 科技翻译要兼顾科技性和艺术性,要顾及译语读者的接受性,以达到传播科技知识的目的,变译求的是原作和译语读者的和谐。 科技翻译求“美”即求至善,既求善果,即译作产生的效果是有益的,还求“和”,即科技性和艺术性的融合,翻译主体和客体、客体之间的“圆满调合”。
(2)科技翻译批评的伦理
从是否“善”评价翻译目的和文本选择。 科技翻译评价的先驱梁启超提出译书“三义”,包括了“择当译之本”。 科技翻译评价首先看选题“善”否,是否能够增加读者的科技知识、是否对我国科技发展有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看是否满足委托者要求。
从是否“真”和“善”评价翻译实践活动。 首先评价全译或变译的选择是否恰当,然后,根据“信”和“达”的标准评价翻译方法。 在全译中,是否“信”即是否“真”,看译作是否与原作为善,科技信息的传递准确否,翻译方法是否能再现原作的科技性和规范性,译作和原作是否“极似”;在“信”的基础上看是否“达”,看译作是否与读者为善,着重评价语言的可接受性。 变译的评价标准为编辑后的原作是否“信”和“达”,既与读者为善又求真,在此基础上评价翻译方法是否使变译效果有效。
从是否“美”评价翻译效果。 全译的评价标准为是否“切”,即是否切合原作的风格;变译的标准为是否“雅”,即是否注重艺术性、语言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此外,评价的标准还包括是否注意各要素的和谐。
3.科技翻译伦理建构的“他律”维度
巴萨拉玛指出,当前翻译伦理建构的问题是国际法律并没有为伦理提供依据[14]。因此,科技翻译伦理建构还要强调“他律”维度,通过行为规范守则和法律约束让科技翻译各方履行职责。 中国儒家学说提倡良法善治;西方的“善”覆盖法律领域,道德、法律是“善”的法则表现,分别指心内法和外在法,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均认为“善”是法律的基础、是治国的出发点[7]。 因此,可把“善”作为科技翻译伦理建构中“他律”维度的基础,从制定行为规范守则到法律条文层层递进约束科技翻译各方的活动。 公司应当制定职业伦理规范, 并设立伦理道德委员会,监督科技翻译工作者和其他员工的行为,使他们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 中国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可参照《翻译服务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制定科技翻译行业职业道德规范,除了规定科技翻译活动各方的行为规范,还应突出科技翻译活动各方的科技伦理意识、译者的科技素养和专业能力。 鉴于科技翻译的失误对个人、社会、国家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国家应当完善法律法规,防范翻译不端行为。
结 语
科技翻译伦理的建构可以规范科技翻译活动各方行为,改变目前科技翻译市场混乱状况,纠正目前科研和翻译行为的不正之风,保证科技翻译伦理和科技伦理的一致性,有助于科技信息的准确传递,有助于翻译伦理建构的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结合,推进中西伦理融合视角的科技翻译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