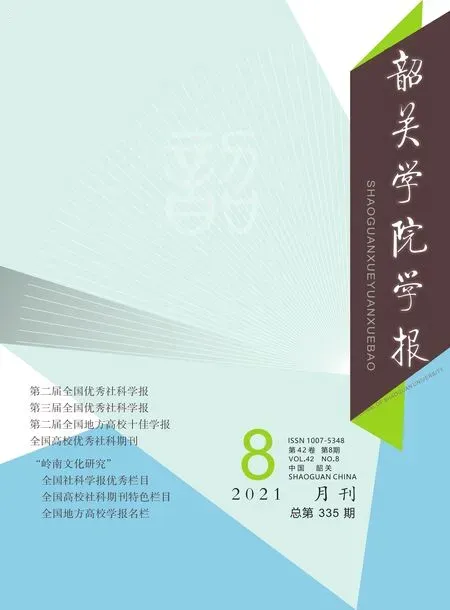救亡·治学·育人:抗战时期坪石先师的使命担当
——以王亚南先生为中心
赵燕玲
(韶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抗日战争时期,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华南部分中、高等院校内迁粤北各地,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办学,对华南教育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此期间,许多知名学者或在粤北任教,或作短期的学术讲座与交流,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坚守学术研究,传承家国情怀,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被誉为“坪石先师(先生)”。王亚南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于1940年至1944年在中山大学经济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一职。坪石的四年,是王亚南先生作为知识分子自觉担负救亡、治学、育人使命职责的四年,在其学术生涯和教育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救亡:对知识分子道德使命的自觉履行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救亡”成为知识分子必须承载的道德使命。这不仅是对古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使命意识和道德自觉的文化继承,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使命的延续。它要求知识分子坚守家国情怀,反对投降分裂,葆有民族气节,传递精神力量。
抗战爆发后,为避免日本的奴化教育,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内迁,知识分子也踏上了艰难的迁徙之路。大规模的内迁活动,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履行救亡使命的一种呈现方式。据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的统计,当时高级知识分子9/10以上、中级知识分子5/10以上、初级知识分子3/10以上参加了内迁过程[1]。他们筚路蓝缕,在艰苦环境中坚守民族文化教育传承与发展使命,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爆发后,华南地区高校遭到了日军的疯狂破坏。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山大学等院校开始辗转内迁,一大批华南知识分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征程。中山大学先迁罗定,再迁云南澂江。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在《西行志序》中记载了中大师生115天、1万余里的艰辛历程:“交通:步行、滑竿、骑马、公共汽车、自用汽车、货车、火车、木船、太古船、邮船、飞机;饮食:餐风、干粮、面摊、粉馆、茶楼、酒店、中菜、西餐、甜酸苦辣;起居:宿雨、泥屋、古庙、民房、学校、衙门、客栈、旅店、地铺、帆布床、木床、铁床、钢床、头二三四等大舱、天堂地狱。”[2]1940年7月,云南告急,中大三迁粤北坪石。迁校初期,校长许崇清打算把中大做成“与桂林遥相呼应”的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基地,特邀一批进步教授到中大讲学,王亚南先生即在受邀之列。
1938年王亚南和郭大力耗费10年心血的《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出版面世,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王亚南的一生都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痛恨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渴望国家实现独立富强。“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他加入上海“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支持、慰问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前线将士,1933年11月,参加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发动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出任福建人民政府文教委员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辗转上海、武汉等地,出任国共合作机构——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武汉沦陷后,他又辗转来到重庆。1940年9月,受许崇清亲邀前往坪石,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王亚南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是“与社会的火热斗争息息相关的政治活动家”[3],他抗战时期的爱国救亡活动,一是开展抗战宣传,一是发挥专业所长,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分析抗战时期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为抗战建言献策。福建事变后,他连发《伟大的革命战斗开幕》《革命战斗开幕之后》《国际和平空气笼罩下的中国战斗》等社论,指出福建事变的正义性,强调事变是“整个中国革命民众,对一切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反帝斗争的扩大”,是“解放中国者与出卖中国者的战争”,号召“每个有挽救中国危亡之决心的志士仁人”参加战争,“担负起战争中的革命任务”[4];在日本改变对华策略,采用“政治诱降”为主之时,他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发表《打击敌人的外交阴谋》一文,坚决反对投降,支持“持久战略”,指出:“以‘持久抗战’答复敌人的‘速战速决’是中国此次对日战争的指导原则,是中华民族当前争取生存的最高原则。在敌人侵略军队不扫数退离中国领土的限内,一切中途调解妥协的运动,都是为敌人运动,都是反民族运动,都是汉奸运动。”[5]在坪石期间,他继续宣传抗日,并把重点转向对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分析,先后发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1941年)、《世界战争与世界经济》、《当前的物价与物价管制问题》、《战时经济的重要性及中国战时经济政策》、《今年经济的展望》(1943年)、《抗战七周年来的经验与教训》(1944年)等文章,针砭时弊,建言立说。如在《今年经济的展望》一文中,针对抗战时期物价飞涨问题对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王亚南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客观分析物价飞涨的原因,痛斥上层集团的奢侈腐朽,一方面要求政府克服重重困难,从根本上重视民生,“推行民生主义经济政策,改造中国的经济,始能使当前的经济问题,得到有效而彻底的解决”[6]167,并满怀“民族的热情”, 将1943年视为是中国“经济改造年”[6]169。 他的这些立论和分析,专业具体,给艰苦抗战中的人们带来希望,也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治学:抗战不忘学术,学术为了救国
抗战不忘学术,学术惟以救国,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何谓知识分子?学界定义不一,但基本的共识是,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不以手艺或劳力为职业的一个阶层,包括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其中,高校教师和学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潜心学术,以知识服务于社会,是知识分子的“本业”。
抗战不惟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更需要学术(科学)。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看来,学术是救国的支撑,是战后建国的基础。时任西南大学教授的贺麟说:“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学术文化的胜利”[7]20,“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7]2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内迁的知识分子们,把报效国家的抗日热情化为扎实的学术研究,尽管条件艰苦,但他们却孜孜不倦,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辛勤耕耘。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昆明和重庆看望梁思成、金岳霖等人后,曾慨然说:“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了。”[8]正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坚守,中国学术并没有因战争而中断,许多后来在学术上享有盛誉的成果,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些成果不仅使中国的优秀文化得以传承,而且也提高了中国学者的国际声望,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国际支持。
作为知识分子而言,王亚南潜心治学的精神是学界公认的,“三角床”和“绑在柱子上读书”的故事早已成为他刻苦研学的标签。坪石期间,王亚南虽身居陋室,仍笔耕不辍。据朱立文《王亚南著译系年目录》统计,1940-1944年间,王亚南先后出版著作3部,发表论文、报告等19篇[9]。这四年时间,是王亚南学术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
其一,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王亚南自认其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在中山大学时期。他在《致中山大学经济系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高度评价中山大学独立探索的学术传统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影响:“中大,特别是中大同学同事所给予我研究上的益助,我是再也不会忘却的。我到中大以前,虽然也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但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的领域,特别是展拓到社会史领域——这个企图和尝试不论达到了什么程度,却显然是到了中大以后开始的……我念念不忘中大和中大经济系,在我自己一方面,并非因为我在那里留下了什么,而纯是因为我从那里获得了一些我前此不曾获得的东西。”[6]228
其二,《中国经济原论》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产生和缘起。《中国经济原论》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王亚南的学术代表作。前者在1998年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后者堪称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而这两部著作的构思和雏形,是在坪石时期。
1940年王亚南受聘中山大学经济系后,主讲“高等经济学”,为突出“高等”的特点,他特意选用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作为教材,但很快发现所讲内容与现实相距甚远,学生不感兴趣。于是他参考“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课程,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纲要”[6]111。1946年,他将讲义与教程整理后出版,此即后来享誉学界、影响至深的《中国经济原论》。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虽出版于1948年,但缘起却是1943年坪石任教时期与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谈话。关于此,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序言中已说得非常清楚,已成为学术史上众知的一段佳话,本文不再赘述。
虽然研究的缘起有些偶然,但王亚南深刻地认识到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处处都要求我进一步对官僚政治作一科学的说明。”[10]从1943年起,他在《时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17篇论文。这些论文于1948年整理出版,命名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极大反响,成为中国官僚政治问题研究中的经典之作。20世纪80年代,某省领导即将赴任,临行前拜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请其推荐几本书。于先生告诉他,把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带去就够了。由此可见本书的价值与影响。
三、育人:青年学业进步和思想进步的引路人
“古之学者必有师”,教师的根本职责在于 “育人”。
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始终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的双重使命。批判旧文化,传播新知识,宣传民主科学,塑造健全人格,培养民族精神,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培养人才的主要内容。他们不仅是学生的学业导师,更是学生人生成长的引路人。
抗战爆发后,师生共赴国难,他们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情感联系,知识分子的学术能力和道德品质对学生的影响作用更为彰显。时代呼唤“良师”,“良师”也造就了特殊时代的教育发展。王亚南就是这个时代的“良师”。
王亚南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学家。他认为,教育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教育制度本身是作为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上层派生物而产生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变革都要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基本变革[11]。他提出,现代教育要以科学教育与民主教育为核心,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教育并重。抗战时期,面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他大力倡导学术研究自由,赞誉中山大学“自己研究”“自己学习”的传统与学风,鼓励学生自己学习和研究。在讲课中,他不生搬硬套,而是结合实际,给学生以启发和指导。他批评那种拿一本美国或英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本,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的做法,说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敷衍的偷懒方法”[6]229。坪石时期,他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自编教材,还经常主动为学生答疑解惑。据陈其人回忆,王亚南的住所与经济系所在地有一江之隔,为给学生上课和答疑,他要上下山岗,然后过江,颇为费时费力,有时还要深夜往返,但他乐此不疲。答疑后,他会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和答疑情况调整教学内容。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连续不断的质疑问难过程中产生的。
王亚南不仅是学生的学业导师,更是引领学生追求进步的人生导师。他讲中国地主经济特征问题时,结合北伐战争时期对农民实行“二五减租”政策的失败,让学生同情农民,同情革命。他的讲课,特别富有感染力,很受学生欢迎。当时在经济系所属的法学院,逐渐形成了以王亚南为轴心的学术自由的小天地。有个学生写了一篇《法西斯细菌在中山大学》的文章,批评某位教授“为法西斯辩护”的政治观点,引发了师生之间的冲突。法学院的院长试图平息风波,但“他的世界观简直和王亚南不能比,更不用说学术地位了”,学生对其非常反感。事件最后在王亚南的帮助下平息了。王亚南“逐渐成为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权威,追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12]。据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炼成教授回忆,1947年他就读的武汉大学,全班24人有12人参加了地下党,就是受了王亚南及其《中国经济原论》的影响[13]。
不独王亚南,抗战时期,各地英才汇聚坪石,讲学不辍,不仅保存了华南教育的力量,也使原本比较落后的粤北地区迎来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先师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树立了不负使命、山高水长的高尚风范。他们当中,有临危受命、清风亮节的中大校长许崇清,有中国近代土壤学先驱和农业教育学家邓植仪,有坚辞日人之聘、坚守独立治学精神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有全心全意关爱学生、致力学术的爱国教育家冼玉清……这些先生的可贵品质和事迹、精神和风范,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