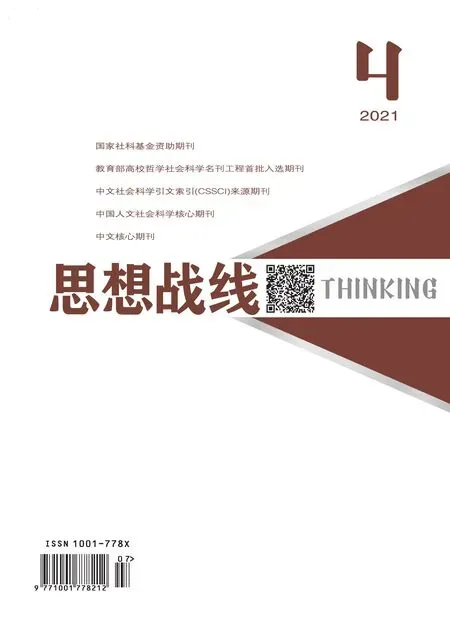论“变通规定”批准权
——兼评《立法法》第75条
沈寿文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下称《立法法》)第75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在一定条件下有权在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其中,自治区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所作的变通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所作的变通规定由所在的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1)《立法法》(2015年)第75条第一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第二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显然,自治区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果“变通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之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自然有权力和能力进行批准;自治州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果“变通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省级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而且所“变通规定”的该省级地方性法规内容不涉及法律和行政法规,自治州所在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当然有权力和能力进行批准;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果“变通规定”省级地方性法规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而且所“变通规定”的该省级地方性法规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的内容不涉及法律和行政法规,自治县所在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同样有权力和能力进行批准。但是,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第75条的规定却留下了一个疑问: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果“变通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自治州和自治县所在的省级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力和能力进行批准?换言之,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改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这种“变通规定”行为,是否具备法理基础和正当性依据?
针对这一问题,如果仅就法条字面作机械地解释,认为:(1)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第75条第二款的规定,本身“已经”赋予了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变通规定”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权力;只要省级人大常委会自己主观上“认为”,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所作的“变通规定”符合该条款关于没有“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属于“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的内容,便有权加以批准。(2)而且,根据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第96条和第97条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或者“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而,存在对省级人大常委会关于“变通规定”的事后救济机制。(3)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的、“变通规定”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内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因而这一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
然而,如果这种按照法条字面的机械解释行得通的话,则至少会带来两个相互关联的消极后果:一是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涉及“变通规定”内容时,对宪法、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等拥有过于宽泛的解释权,实践中容易滥用这一解释权,进而为“不适当”的“变通规定”打开方便之门;二是针对国家的利益(法律、行政法规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利益),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其下辖的自治州和自治县有着内在的利益关联(地方利益),因而,当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与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机关之间有着“共谋”的内在动力,容易导致批准“变通规定”的狭隘地方主义。
因此,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在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如果存在“变通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内容时,自治州和自治县所在的省或者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权是否具备法理基础和正当性依据,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是否有能力进行批准,仍然是一个“真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当前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自治州和自治县“变通规定”的立法实践,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变通规定”之“立法放权”与“立法监督”的关系
(一)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变通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之难题的出现
省级人大常委会作为“变通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批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宪法》)和法律(特别是1984年制定、2001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下称《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2000年制定、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规定的产物。
195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23条仅仅规定“民族自治区”(2)根据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4条和第7条的规定,当时的“自治区”泛指建立的在行政地位上“相当于乡(村)、区、县、专区或专区以上的”各类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自治机关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3)当时的“人民政府”是在广义上使用的概念,与现行《宪法》下专指行政机关的“人民政府”不同。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制定的“单行法规”,应当“层报上两级人民政府核准”并“层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4)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23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依其自治权限,得制定本自治区单行法规,层报上两级人民政府核准。”(第一款)“凡经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核准的各民族自治区单行法规,均须层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第二款)并不涉及“变通”上位法的情形。
然而,一方面,与197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下称《地方组织法》)不断向下扩展赋予一般地方立法权(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趋势相一致,1982年修改《宪法》时,将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权下放给了省和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5)当时,重庆直辖市尚未建立,辖有自治州和自治县的仅有部分的省和自治区。使得省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定机关,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第66条第二款(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第75条第二款),以及2001年修改后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所有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均可以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变通规定”的规定,从而,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州和自治县)在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内容上更加宽松灵活的“优惠照顾”条件。
当上述两方面相结合时,省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批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定机关,其实践难题和法理问题已埋下了伏笔。
(二)“立法放权”与“立法监督”的矛盾统一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下称《宪法修改草案》)和1982年《宪法》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放给了省级人大常委会,从修宪原因上看,是为了方便这两个层级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通过。这是因为: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相比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无论从层级上、还是时间上都可能更为便利一些;也“体现了这一法律制度的灵活性和现实性”。(6)康耀坤等:《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然而,这种审批权下放体现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生效较之之前更为宽松的条件,不应被过度解读为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权力具有当然的法理基础和正当性。这是因为,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报批程序,并不是为了所谓的“通过批准来提高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位阶”,(7)彭建军:《自治区自治条例所涉自治立法权问题研究》,《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张殿军:《民族自治地方一般性地方立法与自治立法比较研究》,《前沿》2011年第5期;曾宪义:《论自治条例的立法基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而“主要是出于国家法制统一的考虑”,(8)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页;冯 军:《新〈立法法〉条文精释与适用指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80页;郑淑娜:《〈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209页。在立法原则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遵循的“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的原则仅仅限于“变通规定”的这一部分内容,其他内容与一般立法相同,应当遵循“不抵触”的原则。(9)沈寿文:《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思想战线》2016年第3期。实际上,从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和2015年《立法法》的修正案均可以看出,立法者在下放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审批权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的、含有“变通”上位法内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监督。这种监督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的规定:第一,2000年《立法法》第66条第二款、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第75条第二款明确了“变通”的积极和消极条件,前者是“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后者是“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第二,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第98条第三项明确了“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
这种监督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是“变通规定”上位法),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立法意图,可以从2017年9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做好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专项自查和清理的函》(法工办函[2017]297号)(10)应当指出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本函中,题目上用的是“地方性法规”,在内容上却把与地方性法规并列的立法形式“单行条例”列入了“地方性法规”范畴,该函说:“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依法履行备案审查工作职责,杜绝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不一致、故意放水等问题,我委法规备案审查室组织开展了对相关地方性法规的梳理研究工作。经初步统计,涉及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共49件,其中既有省级地方性法规,也有市级地方性法规,还有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涉及地方多、范围广。”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做好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专项自查和清理的函》(法工办函[2017]297号)(2017年9月8日)。要求各地要抓紧组织开展“专项自查和清理工作”、杜绝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法规(特别是单行条例)“与上位法不一致、故意放水”的实践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首先,该函附件《有关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与国务院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不一致的情况表》涉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6年5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2016年5月)、《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1年3月)、《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2年3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松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1999年3月)、《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1997年3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1992年7月)等7部单行条例。其次,该函附件《有关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与国务院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不一致的情况表》所罗列的上述单行条例与国务院行政法规“不一致”,主要是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的10类禁止性活动,上述单行条例在文本中只是列举了其中一部分禁止性活动,没有完全罗列这10类禁止性活动,因而被认为“没有完全禁止”。(11)实际上,尽管对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没有明确规定,但《立法法》第73条第四款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的明确要求,同样也适用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换言之,在上位法已经明确禁止的前提下,下位法没有规定,并不意味着下位法改变了上位法的禁止性规定。下位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有上位法的规定,因而丝毫不影响执法机关应当依据上位法进行执法和行政相对人依据上位法进行守法。在本个案中,上述被认为与国务院行政法规“不一致”的自治州和自治县单行条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看来,显然并不涉及“变通规定”行政法规的问题。如果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具有当然的法理基础和正当性,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的函就不应该就“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即下位法立法时遵循“不抵触”的原则)做文章,而应该就单行条例立法时“可以抵触,但不违背”的原则做文章——换言之,要求省级人大常委会就“批准该单行条例‘变通规定’国务院《自然保护区条例》”提供辩护意见。(12)当然,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上述7部单行条例,并没有按照现行《立法法》的要求,在报送备案时,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然而,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是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第98条第三项增加规定的;上述7部单行条例,除《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6年5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2016年5月)外,其他5部均不适用。因此,本案至少表明:杜绝包括单行条例在内的地方立法违反上位法,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是最高立法机关十分重视的问题。
站在这一背景之下,把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放给省级人大常委会,意味着这两个层级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出台更为便利;但与此同时,立法者也强化了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的监督(审批和备案),尤其是针对这些自治法规“变通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内容。可见,“立法放权”与“立法监督”并不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正因为有了“立法放权”,为了维护法制统一,才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监督”。因此,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立场上看,当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存在“变通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时,省级人大常委会并不适合作为审批机关。
三、“变通规定”之“立法放权”与立法体制的关系
(一)《立法法》第75条难题的原因:“立法放权”的衔接错位
之所以出现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来批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上位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这种不具备法理基础和正当性的法律条文内容,与新中国立法体制的发展变化关系密切。1949年以来,我国的立法体制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在立法的法制化上有两大特点,即:立法权的不断下放和立法活动的逐步法制化、规范化。
一方面,就立法权的不断下放来看,1954年《宪法》制定之时,鉴于旧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国家没有法制统一的教训,以马克思主义人民代议机关集中行使权力为指导,借鉴了前苏联1936年宪法关于“立法权由最高苏维埃行使”的规定,强调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首先必须维护法制的统一。因此,1954年《宪法》将国家立法权统一于全国人大手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1954年《宪法》第22条)。尽管在1955年之后,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立法授权,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立法体制在1979年地方立法还没有获得法律地位以前——特别是1982年《宪法》出台之前,并没有根本改变。(13)刘松山:《国家立法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在这种背景和立法体制之下,1954年《宪法》第70条第四款和1978年《宪法》第39条第二款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大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统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既不涉及“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情形,更不存在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变通规定”上位法的问题。
然而,从1979年修改的《地方组织法》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开始,到1982年《宪法》对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确认,以及1982年全国人大修改《地方组织法》进一步赋予了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再到1986年再次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又进一步赋予了省会城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等立法权的不断“下放”中,均贯穿着“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一主题。(14)刘松山:《国家立法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在这种政策导向之下,首先,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自治法规的批准权,也发生了变化,即从1978年《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转变为1982年《宪法》和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两个批准层面:一是保留自治区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生效的批准机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是把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生效的批准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放给省级人大常委会。(15)1982年《宪法》第116条,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其次,这种立法权不断“下放”和强调“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的政策导向,到了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时,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内容上,也有了进一步的体现——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变通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的内容。(16)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仅仅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并没有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上位法作出“变通规定”。2001年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时,吸收了2000年《立法法》规定的内容。但是,当上述两方面相结合时,便出现了上文提及的难题:省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批准“变通规定”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内容的法定机关,是否具备法理基础和正当性依据。
另一方面,就立法活动的逐步法制化、规范化来说,2000年《立法法》的制定,是我国立法活动规范化的里程碑事件。2000年《立法法》第66条第二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作“变通规定”,并非空穴来风,它可以被视为是试图对之前散见于一些法律之中、十分混乱的“变通规定”授权条款进行的法制化、规范化。1982年《宪法》并没有规定“变通规定”的内容;尽管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在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时,认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谁,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但同样并没有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变通规定”法律、行政法规。
然而,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变通规定”的授权最早出现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尽管被授权的主体并不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而伴随着法制改革,这种授权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一些法律之中。在这些授权中,开始出现了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自治县“变通规定”国家法律的问题,比如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35条的规定。(17)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35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财产继承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治州、自治县的规定,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由于上述问题仅仅存在于单行法律之中,因而,在实践中并没有造成普遍性消极影响(比如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然而,正如学术界普遍认识到的,上述涉及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变通规定”的授权的法律中,法律授权作出“变通规定”的情况十分混乱,主要表现为“法律授权的变通规定的制定主体不统一”“法律对变通规定批准或备案的规定不统一”;(18)吉 雅:《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27~128页。而且,“变通规定”也俨然成为一种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并列的一种“立法形式”,比如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0条(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的规定。(1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0条(1997年《刑法》第9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国家权力机关(人大)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这种混乱局面,在2000年《立法法》颁布之后,在立法制度层面上有了根本的改变。2000年《立法法》第66条第二款(2015年《立法法》第75条第二款)至少在两个方面规范了“变通规定”:一是在“变通规定”的制定主体上,规范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二是“变通规定”不再是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并列的一种“立法形式”,而是“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中特殊情况下的某些立法内容。也就是说,“变通规定”仅仅是在制定“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这样的立法形式中,在特殊情况下在内容上对上位法个别条款进行“变通规定”,并不是独立的一种立法形式(法律文件名称),而仅仅是“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的某些内容而已。(20)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先前各部门法中的变通或者补充规定随着《立法法》的出台统一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变通规定,依据新法优于旧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原则,在这一关系问题上应将二者统一为《立法法》的变通规定”的判断(参见张大海《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基本问题法理分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是成立的;只是“《立法法》的变通规定”仅仅是“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形式中的内容(或者条款)而已。事实上,在当前的立法实践中,即便是仍然有效的一些单行条例在名称上虽然冠之“变通规定”,但在立法形式的性质上仍然是“单行条例”,比如《甘孜藏族自治州实施〈四川省旅游条例〉的变通规定》(2011年)、《凉山彝族自治州施行〈兽药管理条例〉的变通规定》(2012年)。
然而,上述制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授权“变通规定”的法律,大多迄今仍然保留了原来的条款,与2000年《立法法》的规定不一致,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后来在修改这些法律时,立法者没有修改涉及授权的条文,或者修改时不彻底。比如,2001年在修改《婚姻法》时,针对原1981年《婚姻法》第36条的规定,(21)1981年《婚姻法》第3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可以依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某些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规定,须报请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自治区制定的规定,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便有常委会委员提出,应当和在1982年修改的《宪法》、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的规定相衔接;当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将本条修改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变通规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区制定的变通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22)顾昂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1年4月24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1-06/01/content_5136919.htm。但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后的条文(第50条)并不彻底,与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以及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并未完全一致,或许是为了使得修改后的条文更为简洁,并没有在条文中出现“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形式”;“变通规定”看起来似乎仍然是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相并列的一种“立法形式”,仍然没有明确把“变通规定”纳入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之中,仅仅作为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特殊内容。
总体上看,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1982年《宪法》之所以将自治州和自治县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改为省级人大常委会,目的是让自治州、自治县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更为便利;但是,由于《立法法》在规范散见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一些授权“变通规定”的法律时,将似乎是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相并列的“变通规定”,改造为“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的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内容时,忽略了两者结合的困境,即当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这种“变通规定”是否具备法理基础和正当性依据的问题。
(二)《立法法》第75条难题的本源:“分工型”立法体制的规则
尽管2015年修正后的《立法法》第75条规定的是一个具体内容,即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内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通规定”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但是,本条文实质上涉及了中央与地方(民族自治地方这种特殊的地方)立法权限的关系,进而也涉及了如何对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性质)的正确理解问题。
按照一般的理解,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理论有中央集权主义和地方分权主义之分,(23)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法治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56页。立法体制因此可以相应地分为两种类型。在前一种类型的立法体制之下,整个国家的“法律性文件”呈现出一个类似凯尔森所说的法律规范等级结构,(24)[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41页;《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81~95页。处于最高等级的是宪法、其次是法律、再次是其他低位阶“法律性文件”制定机关制定的低位阶“法律性文件”,依次类推;在这种立法体制之下,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尽管低位阶“法律性文件”制定机关也拥有制定相应低位阶“法律性文件”的权力(广义的立法权),但是这种权力从属于高位阶的“法律性文件”制定机关的立法权;因而,在这种立法体制之下,尽管地方国家机关拥有宪法或者法律所规定的地方立法权,但是,该地方立法权并不具有与“分权型”立法体制下地方自治制度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立法权那样的排他性和独立性。正因如此,“集权型”立法体制本质上属于“分工型”(De-concentration)立法体制,即不管地方立法权是由宪法直接规定的,还是由法律赋予的,都是以中央和地方职权的基本同构、而非事权划分为前提,即并不存在“地方专属立法”事项,换言之,地方能够立法的内容,中央当然也有权予以立法。(25)秦前红,李少文:《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因应之策》,《法学》2015年第7期。因而,与“分权型”立法体制强调中央与地方立法权互不侵犯、注重解决双方立法权限争议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不同,“分工型”立法体制侧重的是审查地方立法是否违反上位法的制度设计——即“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当前,我国的立法体制属于典型的“分工型”立法体制,(26)沈寿文:《“分工型”立法体制与地方实验性立法的困境》,《法学杂志》2017年第1期。这种“分工型”立法体制的中央集权性质,可以从2000年《立法法》的如下立法意图中得到反映:“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国家权力由中央统一行使;同时为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央又赋予地方适当的自主决策权。这一制度表现在法制上就是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同时又要加强地方立法。这是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也不能划出一块只能由地方立法而中央不得涉及的权限。”(27)刘松山:《一部关于立法制度的重要法律[上]——〈立法法〉制定过程中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中国司法》2000年第5期。显然,承认和尊重当前“分工型”立法体制这一事实,是探讨2015年修正后《立法法》第75条难题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的逻辑起点。
在“分工型”立法体制之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无论是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等“一般地方立法权”,还是“自治立法权”(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均属于地方立法权的范畴,同样应当遵循2015年修正后《立法法》第4条的核心立法原则;民族自治地方的一般地方立法权当然应当遵循地方立法“不抵触上位法”的核心准则,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权”同样“在原则上”应当遵循地方立法“不抵触上位法”的核心准则。所谓“在原则上”应当遵循地方立法“不抵触上位法”的核心准则,指的是:当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内容上没有“变通规定”上位法内容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遵循地方立法“不抵触上位法”的核心准则;当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个别内容在一定条件下“变通规定”上位法的内容时,所作“变通规定”的这一部分条文内容,可以不遵循地方立法“不抵触上位法”的核心准则,但是其他没有“变通规定”的条文内容,仍然应当遵循地方立法“不抵触上位法”的核心准则。这是因为:一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并不是“分权型”立法体制下地方自治意义上的立法权,不具有对抗高位阶立法权的排他性和独立性,它在本质上属于“优惠照顾”权力,即一般地方国家机关所不拥有,而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之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所拥有的权力——实际上,赋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上位法的条文作“变通规定”本身,就是“优惠照顾”的体现;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上位法条文作“变通规定”的规定,这就意味着:《立法法》已经将“变通规定”从原先——即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婚姻法》《刑法》《森林法》《继承法》《收养法》《民事诉讼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的授权中视为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立法形式,法制化、规范化为仅仅是“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具体立法中的条文内容而已。因而,“变通规定”的条文内容并不能涵盖作出该“变通规定”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的全部内容。(28)沈寿文:《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种笼统地宣称“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原则不同”,一个是“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原则”,一个是“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的原则,(29)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254~255页;冯 军:《新〈立法法〉条文精释与适用指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79页;郑淑娜:《〈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208页。并不科学。从《立法法》没有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遵循“不抵触上位法原则”,并不必然能够推导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必遵循“不抵触上位法原则”的结论;实际上,正因为存在“变通规定”的例外,没有明确规定在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应当遵循“不抵触上位法原则”,也是完全符合立法技术要求的。
既然在“分工型”立法体制之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哪怕是其中的“自治立法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均属于地方立法权的范畴,除了在一定条件下“变通规定”上位法外,均应当遵循地方立法“不抵触上位法”的核心准则;那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中的批准机关,在批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便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如果该部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条文不涉及“变通规定”上位法时,批准的重点当然是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是否存在违反上位法的情形。二是如果该部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条文涉及“变通规定”上位法某些条文时,批准的重点便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该“变通规定”上位法的条文是否没有2015年修正的《立法法》第75条第二款所禁止的内容;另一方面,批准机关需要考虑的是自身是否有权力和能力进行批准的问题,因为“分工型”立法体制之下,低位阶“法律性文件”制定机关,当然无权(不管通过“批准”还是什么形式)改变高位阶“法律性文件”制定机关制定的“法律性文件”的内容。显然,当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要“变通规定”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内容时,自治州和自治县所在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能力进行批准;也缺乏批准的正当性。
四、余论:《立法法》第75条难题的解决思路
《立法法》第75条隐含的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改变”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这种“变通规定”的行为,的确不具备法理基础和正当性依据。
在“分工型”立法体制之下,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的关系十分复杂,从该地方立法有没有明确具体的直接“上位法”依据的角度,地方立法可以分为没有直接上位法依据的“创造性立法”(“实验性立法”),以及有直接上位法依据的“执行性立法”;(30)沈寿文:《“分工型”立法体制与地方实验性立法的困境》,《法学杂志》2017年第1期。因而,上述《立法法》第75条实际上还隐含着另外的类似问题。一方面,如果自治州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变通规定”的是省级地方性法规,则应当进一步区分:该地方性法规是“创造性立法”(“试验性立法”)还是“执行性立法”。如果是“创造性立法”(“试验性立法”),意味着该省级地方性法规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等上位法依据,因而,省级人大常委会自然有权力和能力进行批准;但是,如果是“执行性立法”,则意味着该省级地方性法规是为了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而制定的,因而,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表面上是“变通规定”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实际上可能存在“变通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内容,而法律、行政法规分别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制定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当然没有权力和能力批准对其进行“变通规定”。
另一方面,如果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变通的是设区的市(自治州)或省级地方性法规,同样应当进一步区分:该地方性法规是“创造性立法”(“试验性立法”)还是“执行性立法”。倘若是“创造性立法”(“试验性立法”),则意味着该设区的市(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没有上位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级地方性法规)依据,或者省级地方性法规没有上位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依据,因而,省级人大常委会自然有权力和能力进行批准;但是,倘若是“执行性立法”,则需要再进一步划分,即:(1)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变通规定”的是执行上位法(法律、行政法规)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或者设区的市(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因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省级人大常委会同样没有权力和能力进行批准;(2)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变通规定”的是执行省级地方性法规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的话,则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力和能力进行批准。
显然,在如此之复杂的众多可能之下,《立法法》第98条第三项关于如果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上位法时,“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在实践中,在报送给批准机关批准时便有必要“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
为了解决《立法法》第75条的难题,一方面,在《立法法》再次修改之前,为了化解省级人大没有权力和能力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难题,需要建立涉及“变通规定”的争议解决机制,即:自治州和自治县在自治法规制定时,倘若提出“变通规定”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必定涉及相关部门的职权,而这些部门的职权是由国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如果相关部门以自己的权限已由国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规定为由,不同意“变通规定”时,由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按照一定程序(比如通过省级人大常委会)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另一方面,最为有效和根本的措施是,在今后《立法法》的再次修改中,明确规定:不管是自治区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还是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要涉及“变通规定”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内容的,均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如果不涉及“变通规定”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内容的,可以继续将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生效的批准权交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