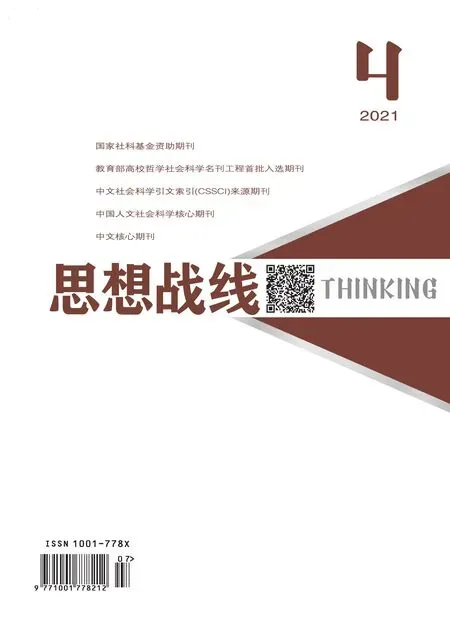同情的距离:远近的苦难、关爱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伦理人类学
曾国华,吴璟薇
引 言
在数字化媒介技术开始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出现。例如,就自然灾难、大型突发紧急事件和人道主义灾难来说,相应的信息在极短时间内可以到达极广的地理范围,覆盖数量巨大的人群。然而,同类的众多不幸事件信息的送达,并不一定会在某个具体的个体或者群体中获得同样的响应。汉宁·里德(Henning Ritter)广受关注的伦理哲学随笔《无处安放的同情》(Nahes und Fernes Unglueck,直译为《近处与远处的不幸》)中文译本封面,加上了一个直击人心的问题:我们为何对远处的灾难报以同情,却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1)参见[德]汉宁·里德《无处安放的同情》,周雨霏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在当下社交媒体时代,这句话中的“承担身边的义务”甚至可以缩减为“一刹那的关注”。对于大多数的重大灾难和不幸,无论它在近处还是远方,人们可能甚至都不愿意花一秒钟进行转发。或者说,在转发与不发之间,在社会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上“远”与“近”之间,有众多的日常生活伦理的复杂考量。
无论是在中国春秋时期还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以普遍的同情与关爱为主的情感伦理,在各种良善自我和社会的理论构建图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对情感可能天然具有的偏私性质的担忧和批评、对情感对象的等级划分所造成的非普遍性、对国族和地域认同带来的情感偏见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情感伦理普遍性的理论基石。同情和爱等情感具有典型的关系亲密性,具有偏爱关系上和心理上亲近、地理上临近的人或人群,要把这种情感平等、普惠地投射到“远方的陌生人”身上,具有难以逾越的障碍。(2)[美]迈克尔·L.弗雷泽:《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Soleman,P.& Henderson,L.,“Flood disast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ndia: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edia reporting”,Journalism,vol.20,no.12,2019,pp.1648~1664;Cottle,S.“Rethinking media and disasters in a global age:What’s changed and why it matters”,Media,War & Conflict,vol.7,no.1,2014,pp.3~22;Joye,S.,“The hierarchy of global suffering: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elevision news reporting on foreign natural disasters”,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ol.15,no.2,2009,pp.45~61.因而,早期伦理学对情感道德亲密性与距离远近的对应关系的判断,和前述汉宁·里德一书中对现代道德观念中远近关系的判断截然相反,也和当下在很大程度上被数字技术所中介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很大区别。要理解这种区别,尤其是要理解当下社交媒体时代、全球(部分)连接性的关爱伦理实践与经典伦理叙事的区别,需要将距离放入情感伦理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对于近处和远处的苦难的关注、关心和关爱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综合“伦理转向”(3)“伦理转向”是指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理论和方法论的范式转移。这种范式转移关注从伦理追问的角度,来反思现有的学科理论、方法论的封闭性,并通过引入伦理理论视角来寻找打开新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可能性。关于“伦理转向”下人文地理研究方面可参见Barnett,Clive,and David Land,“Geographies of Generosity:Beyond the‘Moral Turn.’”Geoforum,vol.38,no.6,2007,pp.1065~1075。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状况可参见Mattingly,Cheryl and Jason Throop,“The Anthropology of Ethics and Moralit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7,2018,pp.475~492;Black,Steven P.,“The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Car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7,2018,pp.79~95.媒介与传播研究可见Silverstone,Roger,Media and Morality:On the Rise of the Mediapoli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Corpus Ong,J.,“The cosmopolitan continuum:locating cosmopolitanism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Media,Culture & Society,vol.31,no.3,2009,pp.449~466.以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和媒介研究在关爱与情感、亲近与陌生、普遍主义和实存观念的深度讨论,那么从实存伦理(即实存生活情境中的伦理状况及对这种状况的伦理学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关爱和情感的实践,可能可以得到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一种更为实践导向、剥去规范性道德优越感的“道德”构建的考量。这种状况对于伦理人类学来说,可能更多意味着一种机遇,而不是挑战。
一、普遍主义关爱伦理的衰落与实践导向的关爱伦理的兴起
在中西观念史中,普遍存在甚至先验的情感在早期伦理观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墨子·兼爱中》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提出无等差的、普在的“兼相爱”具有“交相利”的效应。如果“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可以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美好社会,因为关爱可以化解一切的争端怨恨,“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孟子·公孙丑上》着重表述的“善心四端”的理论基石,则是一个“孺子入井”的理论讨论案例:人们对于即将掉入井里的幼童,之所以会觉得惊恐和同情,并非因为想要结交孩子父母、在乡党朋友中博取名誉或者厌恶孩子的哭喊(“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而是人天然就具有这种“恻隐之心”,没有这种同情心,就不是人(“非人也”)。因此,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同理,孟子认为可以推导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就是说,“仁义礼智”四端,是只要是人就都会具有的普遍伦理,寻回这种普遍伦理(“求其放心”),则是构建良善自我和良善社会的基础。因而,在这些基础理论中,普遍的爱与同情而不是等级差异基础上的伦理体系(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构成了建构良好社会的基石。普在的情感主义在启蒙运动中也占有基础位置,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和约翰·密尔,在18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期的100多年时间内,构建了一套体系化的、与同情/共情、情感有关的伦理哲学与社会理论。(4)参见[美]迈克尔·L.弗雷泽《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胡 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席卷了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伦理转向”中,出于当下全球相互关联的情境,关于同情、道德与地理分布的关联问题获得了比较多的关注。虽然“逆全球化”在过去数年中有明显的表现,2020年初以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对跨区域关联性产生短期中断性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全球总体上仍然在阿尔均·阿帕杜莱的“全球化流动的五个维度”意义上保持紧密关联。(5)印度裔美籍学者阿尔均·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消失的现代性》中提出,族群、媒体、科技、金融、意识的全球流动构成的五种“景观”,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征。[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 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43~48页。因而,同情和道德是具有普遍性特征?还是与地理分布以及基于地理分布的其他区隔性要素具有强关联性表现?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克里夫·巴奈特和大卫·兰德(Clive Barnett and David Land)系统地梳理了“伦理转向”理论下的道德地理问题。(6)Barnett,Clive,and David Land,“Geographies of Generosity:Beyond the‘Moral Turn’”,Geoforum,vol.38,no.6,2007,pp.1065~1075.他们指出,“远距离关怀”(caring at a distance)(7)Silk,J.,“Caring at a Distance”,Ethics,Place and Environment,vol.1,1998,pp.165~182;Silk,J.,“Caring at a distance:(im)partiality,moral motivation and the ethics of representation”,Ethics,Place and Environment,vol.3,2000,pp.303~322;Silk,J.,“Caring at a distance:gift theory,aid chains and social movements”,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vol.5,no.2,2004,pp.229~251.和“责任地理学”(8)Popke,E.J.,“Poststructuralist ethics:subjectivity,responsibility and the space of community”,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27,no.3,2003,pp.298~316;Massey,D.,“Geographies of responsibility”,Geografiska Annaler:Series B,Human Geography.vol.86,no.1,2010,pp.5~18.是这个议题中的两个核心问题。远距离关怀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无论中西伦理观念体系,都在理论或者操作实践中怀疑人们是否可以将自己对亲朋近邻或者同胞的各种美德,扩展到广阔范围内的其他人。例如,休谟早期的思想,尤其是在《人性论》中的重要论断,“就是两个个体越相似,它们的感情相似性就越大,感情的传递就更容易也更强劲”,(9)[美]迈克尔·L.弗雷泽:《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胡 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49页。所以同情一方面容易导致对亲朋近邻的偏私,另一方面不容易将同情扩散到远方。在中文学界,更为人所熟知的则是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带有批判性地提出的“差序格局”,在这种格局中,亲近性会随着物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的逐渐扩大而出现梯度衰减。(10)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28页。因此,在这类讨论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关爱是否能够惠及远方的陌生人。出于关爱伦理的普遍主义视角,众多研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对“偏心”(partiality)提出了异议,认为偏心将“自利、排除及与他人关联的地理限制排在优先地位”(11)Barnett,Clive,and David Land,“Geographies of Generosity:Beyond the‘Moral Turn’”,Geoforum,vol.38,no.6,2007,p.1066.,从而失去了道德的普遍性。
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提出的一个弥合性方案,是将“关爱”本身划分为建立在与非常熟知的人的个人关系基础上的“亲密关爱”(intimate caring),以及扩展到仅仅有点了解的人的“人道主义关爱”(humanitarian caring)。(12)Slote,M.,“Virtue ethics”,In:LaFollette,H.(Ed.),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Ethical The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这种策略并不算成功,因为这种观点的基础假设,仍然认为关爱的基础来源于亲密关系,意味着对于他人特定需求的敏感性,而对远方陌生人的关爱只是这种关系的投射和延伸。因而,这种亲密关爱与人道主义关爱(humanitarian caring)的区分,可能只是重复了早前的关爱(caring for,即直接的、亲密的关爱)和关心(caring about,即间接的、一般性的、对外界的关心)的二分法。(13)Noddings,N.,Caring: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19~23.在这个问题上,巴奈特和兰德提出,与其假设关心是建立在更为真实的关系基础上的次要延伸版本,不如从现实中的观察出发,认定任何的关爱实践,为了实现它作为“关爱”的特征,都需要注意到并灵敏地回应他人的需求。也就是说,任何关爱都和情感有关,更和关爱的实践能力有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费雪和特隆多所提出的关爱实践的4个层面,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4个层面是:1.注意到他人需求的能力;2.承担满足关爱需求的责任的能力;3.胜任地提供实际关爱的能力;4.能够响应接受关爱者的持续需求的能力。这种理论用实践的维度替代了出于同情和爱的关爱的普遍主义的先验道德维度,从而将其从一个普遍哲学问题转化为一个具体实践操作问题。(14)Fisher,B.,Tronto,J.,“Towards a feminist theory of care”,In:Abel,E.,Nelson,M.(Eds.),Circles of Care,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
然而,如果关爱是一种基于能力的实践,还是要回到一个基础的问题,即这种实践它是否具有跨越地理区域和社会距离的能力?这就将远距离的关爱问题放入地理扩展的责任伦理之中。早期伦理学,或者通过阐述关爱的社会后果能够产生对自己有利的社会后果,或者通过社会团结原则、个体或者群体相似性原则为基础,来将遥远的陌生人纳入关爱的范围。这种以社会后果的因果关系为出发点进行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的论述路径源远流长,在当下的关爱伦理研究中也有丰富的体现。如当下的主流叙事范式之一,就认为激励人们参与到对陌生人的关爱实践的关键,就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自己也是深陷在复杂的全球网络之中的。如戴维·哈维的《希望的空间》,即通过描述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全球尺度上带来了环境破坏和大范围贫困等严重问题,提出以共建的方式重新设计并创造出不同的生活与工作的社会空间,才能找到更好的连接身体、个人和全球宏观政治经济的方式。(15)[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以新的伦理方式来共建新的社会空间。在责任地理的文献中,类似的观点非常多见,并且形成了多种变体。(16)Massey,D.,“Geographies of responsibility”,Geografiska Annaler:Series B,Human Geography,vol.86,no.1,pp.5~18.总体来看,这种路径主要就是强调人们的行为与遥远的、间接性的后果之间有可以识别的联系,从而需要人们对他人的需要关注留意并进行响应。
但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很多情况下,作为个体的人们并不能为自己并没有做的事情负责,例如对某些地方发生的巨大自然灾害或者人道主义灾难负责。一个人的行为,也往往被社会文化、群体惯例等因素形塑,而不见得完全由自己的“理性”来掌握。用托马斯·奈格尔(Thomas Nagel)的话来说:一个人仅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道德责任,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是由很多他并没有做的事情所导致的,因此他对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没有责任的事情并没有道德责任。(17)Nagel,T.,Mortal Question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34.从带有实存哲学意味的实践伦理的角度来看,在实际行动中,“人们的道德行动往往不是出于对自己责任的某种独自的反省所导致的,而是由与他人的相遇(encounters)而导致的”。(18)Barnett,Clive,and David Land,“Geographies of Generosity:Beyond the‘Moral Turn’”,Geoforum,vol.38,no.6,2007,p.1069.
从而,采用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的责任代理人(agent)的角度来论述道德的地理性责任,并不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从实存哲学角度的伦理观念来看,无论是从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出发进行论证,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足够多的反例,从而使得这种论证变成“应该如何行动”的一种劝诫,从而变成一种带有知识权力的话语体系。在巴奈特和兰德看来,当代的一些重要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指出慷慨行为可能并不是一种规范性(不管是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的理想,而是“社会性、社区性和团结性的一种构成性的实践”(19)Coles,R.,Rethinking Generosity: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Carita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Diprose,R.,Corporeal Generosity:On Giving with Nietzsche,Merleau-Ponty,and Levinas,Albany,NY:SUNY Press,2002;Young,I.M.,“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labor justice”,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12,no.4,2004,pp.365~388.;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关爱和慷慨具有“道德”色彩,但可以不把关爱和慷慨行为看作是一种道德概念,而应该将之看作是一种政治概念,一种汉娜·阿伦特意义上的“权力模态”(modality of power)。从这种概念出发,关爱可以被看作类似于宽恕或者承诺的权力方式,一种将“人们生活在一起”的状态以惯例的方式在时空中延续下来的实践(20)转引自 Barnett and Land,Barnett,Clive,and David Land,“Geographies of Generosity:Beyond the‘Moral Turn’”,Geoforum,vol.38,no.6,2007,p.1070.。如此,将“道德”的规范性代之以政治性和权力模态意义上的惯例,关爱和慷慨就成了一种政治性的日常实践。这种实存伦理意义上的日常实践的一种可操作的形式,就是上文中提到费雪和特隆多的4个层次的关爱实践能力体系。
二、“礼物”的地方性、利他文化的困难与伦理人类学的实践政治化
在讨论社会文化、群体惯例对于普遍的同情与关爱是否存在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能够跨越地理空间的限制而对远近的陌生人都产生(同等)关爱这一重要问题时,很难绕开人类学的礼物研究。人类学的学术基础之一,在于通过带有强烈人文主义范式印记的实证主义研究,来进行地方性导向(locality-oriented)的知识生产,并以此反思西方的哲学和现代性理论。其中,关于礼物的理论争论最为直接地参与到关爱及基于关爱的慷慨行为的讨论之中,从而成为上述关于关爱与慷慨实践、地理距离、利己主义/利他主义讨论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莫斯的《礼物》,描绘了作为人们互动过程中互惠价值机制的礼物赠送行为,这为很多以利他主义为基础的伦理学构建提供了重要的论述思路。例如,在《礼物》一书中,莫斯提出礼物交换和互动构成了一种基础的关系链,礼物的接受者有义务回报礼物。扩展开去之后,礼物互动就构成了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循环的互惠关系,从而构建一种社会范围内的关系性的、以利他主义为主的社会情境。礼物关系从而经常作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关系体系,来对现代社会商业逻辑和契约关系的利己主义甚至“原子化情境”提出异议。
然而,批评者从两个层面提出异议。一方面,礼物的接收者既然对赠与负有强烈的回报责任,那么这种带有道德强制性的关系网络在哪些情境下能够称为利他主义,值得商榷。其中一种情境在于,如果这种强制性超出了接收者需求的接受与回报能力,那么礼物就可能造成伤害。例如,如果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系统扶贫赠予所附带的道德要求是对方迅速获得某种内生发展,甚至自立发展的能力和状态的话,那么这种强制性会带来明显的失衡效应,甚至会成为当地民众的某种负担。在一般的社会场景中,有权势的权力代理人或商业机构也常常利用礼物来要求某种回报。这种情境下的礼物赠与和互惠的强制性与利他主义没有明显的关系,反而和不平等与依赖性的创造与维持有更加明显的关系。另一方面,以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互惠关系的强制性。德里达的《给定的时间》(Given time)质疑了礼物关系的道德意涵:如果赠予总是期望一种可以被计算的、大致同等的回馈,那么它就不能算是慷慨的行为。(21)Derrida,J,.“Given Time”(trans.Peggy Kamuf),Critical Inquiry,vol.18,no.2,1992,pp.161~187.因为如果需要获得慷慨的赞誉,那么慷慨赞誉本身就是回馈,就不应该要求互惠的回馈。赠予和获取回馈这种关系就应该从礼物关系中去除。既然赠与取同时存在,那么礼物关系应该不是道德实践的范畴,而应该是一种契约下的行为。礼物的道德性在赠予发生的时候就被从这种关系中排除出了。
在中国语境的人类学研究中,礼物的道德性也同样被放入在具体情境实践中。例如,阎云翔通过礼物的交换考察了中国东北农村基于“人情”的互惠体系,指出当地的村民在借由人情的交换来培养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和社区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村社基础上的共同体文化。(22)参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 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种讨论与德里达的讨论形成对应性的探讨,德里达讨论的是在实践中纯粹的礼物关系从逻辑上来看是不存在的,用此来提醒将礼物交换作为普遍主义的规范性标准存在巨大的风险。而阎云翔则讨论,不纯粹的礼物互惠行为虽然形成了强制性的道德规范,但是仍可以作为村社共同体的文化实践机制。然而,中立地判断,这种机制虽然很难说是利他主义(毕竟利己主义色彩更为浓重)或是普遍主义的,但是它的确可以在村社甚至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某种文化实践的共同体。与阎云翔基于功能主义意义上的“礼物”机制相反,杨美惠通过对“关系学”在多重社区范围的探讨,讨论了礼物交换在米歇尔·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抵抗”的可能性,即关系的运作可以对“滴水不漏”的国家行政力量形成某种文化实践意义上的抵抗性。(23)参见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尽管如此,这种文化抵抗形式,虽然从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抵抗角度理解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然而这其中的礼物实践却也是高度利己主义、强调亲密性的。
对礼物交换的两个层面的批评以及中国的礼物研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伦理学界曾经对礼物关系在普遍主义的利他主义方面所寄以的厚望,也对礼物交换是否可以在更为广阔的现代社会发挥功能主义的整合作用提出了怀疑。例如,在礼物经济的现代扩展性上,李荣荣在托克维尔的“民意”概念的基础上,考察了云南某乡村具有“道义经济学”色彩的礼物互惠体系的运作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追问现代公益活动是否可能在莫斯原初意义上的“相互性”(而非“互惠”)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既具有现代社会的普遍意义,又能够和乡村社会的“民意”进行“链合”的公益体系。(24)李荣荣:《作为礼物的现代公益——由某公益组织的乡土实践引起的思考》,《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4期。然而,这种追问更多反映的是,在现代社会尺度上,礼物交换所带来的互惠性仍然更多地局限在小规模社群之中,对于打破地理范围约束的能力并不强。
除了关于“礼物交换”的讨论,在“伦理转向”的驱动下,人类学领域涌现了数以百计的伦理研究。(25)Mattingly,Cheryl and Jason Throop,“The Anthropology of Ethics and Moralit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7,2018,pp.475~492;Black,Steven P.,“The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Car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7,2018,pp.79~95.和所有的“转向”一样,伦理转向下的人类学研究驳杂多样,但总体上来说从伦理的思考挑战了人类学的很多基础概念和信念,比如传统人类学所关注的道德对于社区的整合作用,以及道德生活的稳定性。在这个伦理转向的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米歇尔·福柯的美德系谱学与自我伦理,新亚里斯多德主义的新美德实践主义,以及现象学的多重视角,都放弃了传统的道德信念,而将重点放在了日常生活的道德经验的实践过程的复杂性上。这种视角和前述的道德地理学的研究相互呼应,将伦理和道德的很大一部分关注放在“日常生活政治”实践层面,关注和讨论“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处境,共存的“相遇”与实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普遍主义的先验道德维度,将其从一个先验哲学问题转化为一个具体实践操作问题。从而,对经典礼物交换概念的反思以及在“伦理转向”下的道德经验的探讨,都质疑了道德普遍主义在日常生活操作中的可能性,从而转向了个体和(小)群体经验意义上的实存伦理。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媒介技术尤其是数字媒介技术的中介下,实现某种世界主义或者普遍主义的关爱实践的可能性?
三、社交媒体时代的关爱伦理与日常生活的权力实践
正如前文所说,虽然“逆全球化”在过去数年中有明显的表现,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更是造成了多层次的阻隔效果,但全球在阿帕杜莱所称的“族群、媒体、科技、金融、意识”五种全球化流动中,除“族群”之外的4种流动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活力。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平与发展、人道主义关怀和援助等众多事关人类种群生存的重大问题上,全球政策方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共识。由于数字媒介技术在连接性(connectivity)、参与性上具有的优势,当下时代的人们在与灾难信息媒介化层面(尤其是对自然灾难、大型突发紧急事件、人道主义灾难事件以及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大型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全媒体、多渠道直播的情境下),已经具备了超大规模、高速度、高饱和度、多种社会关系嵌入、多种形态监督与监视和“目击”观察的特征,(26)Cottle,S.,“Rethinking media and disasters in a global age:What’s changed and why it matters”,Media,War & Conflict,vol.7,no.1,2014,pp.5~6.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接近先哲和伦理思想家所设想的远近距离都消失了的、普遍“连接”的场景。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在这种高度的信息连接过程中,对于附近和远方陌生人的苦难的关注、关心和关爱,是否能够修正或者至少弥补前述道德地理和伦理人类学研究中对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的“认可”,从而回到一种普遍主义的可能性?
对数字媒介中介状况下的灾难研究已经极为丰富,覆盖了灾难预防、救灾和灾后重建等与灾难相关的全流程环节。(27)Houston,J.B.,Hawthorne,J.,Perreault,M.F.,Park,E.H.,Goldstein Hode,M.,Halliwell,M.R.,Turner McGowen,S.E.,Davis,R.,Vaid,S.,McElderry,J.A.and S.A.Griffith,“Social media and disasters:a functional framework for social media use in disaster planning,response,and research”,Disasters,vol.39,no.1,2015,pp.1~22;Potts,L.,Social Media in Disaster Response:How Experience Architects Can Build for Participation,New York:Routledge,2014.然而,其中大多数研究都在探讨灾难的在地情境(无论是当下或是历史的视角)的处理问题,例如对于以灾难发生地为核心进行关于灾难预防、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全流程环节的研究。对于“远方的陌生人”的灾难如何在本地(以及非灾难发生地的其他地方)产生社会关联的研究相对要少得多,对于数字媒介中介状况下的异地灾难研究就更加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
实际上,媒介与传播一方面对于地理距离有非常强烈的敏感性,另一方面也非常具有操纵性。相对来说,早期的研究者更加关注媒介信息超越地理空间的、在整个社会中的价值整合作用。例如,发表于1992年的《媒介事件》提出,对于征服、竞争、加冕这三种犹如“大众传播中的重大节日”般打断常规生活的重大仪式性事件的电视直播,可以跨越地理距离,在全社会(甚至全球层面)激起观众的忠诚回应。(28)Dayan,D.& Katz,E.,Media Events: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4.随后,伊莱修·卡茨(Elihu Katz)和塔马尔·雷博斯(Tamar Liebes)进一步提出,对灾难事件进行长时间追踪报道的“灾难马拉松”,作为“创伤性事件”(traumatic events),可作为仪式性事件的补充而被看作是“媒体事件”的一种新种类,因为这种事件同样具有在跨越地理距离的全社会层面、从“反向强化”的角度来加强社会的团结。(29)Katz,E.& Liebes,T.,“‘No more peace!’:How disaster,terror and war have upstaged media even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2007.
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远没有这么乐观。罗格·希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指出,媒介化的距离其实是一种被控制的距离,通过媒介呈现的具体实践,这种距离在合并(incorporation,即否认差异和距离两者)或者虚无(annihilation,即否认共同人性和距离两者)(30)Silverstone R.,“Complicity and collusion in the mediation of everyday life”,New Literary History,vol.33,no.4,2002,pp.761~780.之间摇摆。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受众每天都要面对大量来自遥远地方的信息,这些信息要么被组织为放入到可识别的、熟悉的框架中来叙述,要么被剥夺了可理解的解释框架。前者否定了事件的特殊性和“他者性”(otherness),后者则夸大了它们的差异,将它们变为某种难以理解的、外国的刻板印象。(31)Silverstone R.,Media and Morality:On the Rise of the Mediapoli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p.48.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灾难的媒介呈现中所蕴含的对地理距离的控制,很可能是全面性的。例如,保罗·索尔曼(Paul Solman)和莱斯利·韩德森(Lesley Henderson)比较了英国纸媒报道北英格兰地区和印度钦奈(Chennai)地区的洪水时的报道框架,发现2015年以前,英国纸媒不但更为关注英国本地的洪水,而且在报道国内外洪水时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框架。对于国内洪水,报道会通过个体故事、情感和苦难来强化灾民和目标读者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共享的价值观。而对印度洪水的报道则与此相反,报道会把印度灾民刻画成一种“遥远的他者”,会更加强调洪水本身的戏剧性而不是个人的困境。(32)Soleman,P.& Henderson L.,“Flood disast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ndia: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edia reporting”,Journalism,vol.20,no.12,2019,pp.1648~1664.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各类媒体报道中,西方媒体更加聚焦西方国家的游客伤亡情况,结果导致了“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报道聚焦在西方人身上”,尽管这些西方人“仅占了受害者数量的百分之一”。(33)Franks,S.,“The CARMA report:Western media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disasters”,The Political Quarterly,vol.77,no.2,2006,pp.281~284.在此基础上,斯顿恩·乔伊(Stijn Joye)提出,在西方的媒介报道中,存在一种“全球苦难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体现了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并且使得新闻报道中的不平等现象得以正常化。(34)Joye,S.,“The hierarchy of global suffering: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elevision news reporting on foreign natural disasters”,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vol.15,no.2,2009,pp.45~61.
甚至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易达性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可能也不是全球的紧密连接和对全球各地人们均等的同情与关爱,而更可能是诸多复杂的日常生活的政治权力实践。一方面,地理距离以及心理距离仍然处于一种受控制的状态。例如,曾国华等通过对“新浪微博”在较长时段内对于水灾信息的报道、转发和评论情况的量化分析,提出在水灾信息的社交媒体呈现中,水灾发生的物理地点成了一种重要的考量因素,从而呼吁关注地理距离和社会心理距离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灾难报道中的重要性。(35)曾国华,刘新传,崔啸行:《社交媒体地理偏好的传播机制实证研究——以新浪微博2009~2014年水灾传播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李静等分析了微信使用者对医疗紧急求助信息的回应,认为这些回应体现出微信用户对社会距离的复杂衡量,这种衡量决定了人们在资助求助人、转发信息和置之不理多层次的回应过程中的重要变化。(36)李 静,杨晓冬:《社交媒体中“医疗众筹”信息分享行为研究:转发还是不转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2期。针对这种现象,马丁·斯科特(Martin Scott)总结说,影响人们对于发生在遥远地区的不幸事件的关爱实践的,可能不是媒介文本甚至媒介技术形式,“至关重要的是预先存在的话语资源的性质和可接受性,以及这些资源如何被用户使用以证明其媒体使用的合理性”。(37)Martin Scott,“Distant Suffering Online:The Unfortunate Irony of Cyber-utopian Narrative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no.77,2015,pp.650~651.也就是说,无论人们使用的是何种媒介形式,长久以来的媒介权力结构、道德地理结构,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于“远方的苦难”的关注程度和关爱实践。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时代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首先,社交媒体的群体关注与回应所造成的“声势浩大”的媒介印象,正在将一大批互联网用户转变为“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或者“键盘侠”(clickactivism)。(38)Morozov,E.,The net Delusion:How not to Liberate the World,London:Penguin UK,2011,p.190.其次,信息的过度负载使得非常多的用户选择了退缩和“冷漠”,对灾难信息置之不理。(39)Cottle,S.,“Rethinking media and disasters in a global age:What’s changed and why it matters”,Media,War & Conflict,vol.7,no.1,2014,pp.3~22.正如上文关于微博灾难信息呈现和医疗求助信息回应的研究所揭示的,对这些不幸事件的同情与关爱的“响应”和实践,需要更多的基于道德地理和社会距离的伦理动机激发,否则不管灾情是否严重、处于困境的求助者是否迫切需要援助,人们可能甚至不愿意花一秒钟来转发和分享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前述关于懒人行动主义、键盘侠的担忧可能并不必要,因为人们可能根本就不会点击这些信息。再次,全球距离在信息层面的拉近,不但给予同情与关爱巨大的实践空间,也给了仇恨、排外、歧视和玩世不恭的实践空间。(40)Ibrahim,Y.,“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disaster event:self-imaging,morality and immortality”,Journal of Media Practice,vol.16,no.3,2015,pp.211~227;Marcus O R,Singer M.,“Loving Ebola-chan:Internet memes in an epidemic”,Media,Culture & Society,vol.39,no.3,2017,pp.341~356.对于民族主义情绪、社会心理或者个体情绪上的“敌人”的苦难,幸灾乐祸也成了一种常态。
如果对照前文费雪和特隆多所提出的四重实践框架,这种双重状况的出现使得人们在“注意到他人需求的能力”被削弱,“承担满足关爱需求的责任的能力”和“胜任地提供实际关爱的能力”和“能够响应接受关爱者的持续需求的能力”变成了一种高度情境化、个人体验化的一种实践,一种个人和群体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也就是说,尽管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社交媒体时代具有比之前任何媒介更强的连接性和参与性,社交媒体上对于远方的陌生人的关爱伦理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之前媒介的权力结构和道德地理结构,甚至增加了更多的微观权力模态实践的情境,从而将媒介的关爱伦理实践变成一种增强了的权力政治实践。
结论与讨论:社交媒体时代关爱伦理的重建与伦理人类学的机遇
本文通过对“伦理转向”以来的地理学、人类学和媒介伦理研究三个不同研究领域中,对于关爱与冷漠、陌生与亲近、普遍主义和实存经验的讨论的简要梳理,来探讨关爱实践、同情情感在实践层面的具体状况。本文提出,人们在社交媒体时代对不幸事件的关注方式和响应方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可被看作是对学术史上关于关爱、同情和一般伦理的长期争论的一种具体而微的具化,而从早期的普遍主义关爱伦理向实存(existential)关爱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关爱和情感的实践也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这个过程近乎“完美地”再现了人们如何在普遍主义关爱伦理的“理想状况”的想象中,进入日常生活状况下基于“权力模态”的一种实践政治意义上的关爱实践。这种状态把我们拉回伦理追问的起点,即多元群体如何在多元“权力模态”伦理状况下有德性地共处,并实现一种良善的社会。
多次对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迁移做出重要总结和预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类学家雪莉·B.奥特纳(Sherry B.Otner),在对1980年以来的人类学研究进行总结时,认为“阴郁的人类学”(Dark Anthropology)研究是1980年以来的主要主题。(41)Sherry B.Otner,“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vol.6,no.1,2016,pp.47~73.她认为,“伦理人类学”是这种“阴郁转向”的重要补充,但是她并没有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笔墨,她个人更为关注的是“批判、抗争和激进主义的人类学”。但其他学者接续了这种努力,将伦理追问带向“第三人称”的总体主义视角。然而,和普遍主义关爱伦理不同,实存主义关爱伦理的伦理追问,关注的是个体在实存状态下的关爱实践、状态及其意义。需要强调的是,前述三个研究领域,逐步从普遍主义的关爱伦理想象走向实存的、基于个体实存境遇的关爱权力实践,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关爱实践必须要完全屈服于实存的权力模态、道德地理结构和媒介权力结构。实存伦理的要义之一,在于激发个体和群体通过建立具有高度创造性、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性,抵抗各种本质主义权力的结构性压制。伦理转向下道德地理学、伦理人类学和媒介的伦理地理研究,都强调在放弃普遍主义之后,来重建一种关联性的关爱伦理。例如,前述费雪和特隆多所提出的关爱实践的四个层面,用实践的维度替代了出于同情和爱的关爱的普遍主义的先验道德维度,从而将其从一个普遍哲学问题转化为一个具体实践操作问题,从而为个体与个体之间关联性提供了一个可持续性实践方案和关爱能力建设方案。而媒介研究学者乔纳森·考普斯·王(Jonathan Corpus Ong)则从批判媒介研究的角度,在认识到现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与媒介权力结构的压制性之后,来考虑一种跨越地理空间距离和社会心理距离的“世界主义”的道德实践体系。从这种角度出发,人们可以探索一种新的构建“媒体内容和上下文”的实践模式/形式,以将我们对“接触的恐惧”转化为对他人的“爱抚”。(42)Corpus Ong,J.,“The cosmopolitan continuum:locating cosmopolitanism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Media,Culture & Society,vol.31,no.3,2009,pp.449~466.而实存伦理重建的重要推动者、人类学家杰森·特鲁普(Jason Throop)和贾莱特·西岗(Jarrett Zigon)都试图通过具体的民族志分析,将基于个体实存的关联性视角纳入到论述之中,前者的“开放性”(openness)概念和后者的“世界建造”(worldbuilding)概念,都试图从微观实存伦理实践经验的路径构建一个良善、关系本体论意义上的高度包容的社会。(43)Throop C.J.,“Being open to the world”,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vol.8,no.1/2,2018,pp.197~210;Zigon J.,Disappointment:Toward a Critical Hermeneutics of World building,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7.
这或许意味着,尽管普遍主义关爱伦理的失落可能让我们难以依照普遍主义的伦理准则来进行日常生活,我们仍然在竭力摆脱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媒介权力结构的压制,仍然试图在同时兼具高度连接性和分化性的社交媒体时代,与身边和远方的陌生人尽可能相互关爱,美好地“生活在一起”。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看到,当剥去普遍主义规范性道德的优越感和社会想象之后,更为实践导向的、关联性的“道德”构建的考量可以在此基础上重建。只是,和实存哲学和实存伦理在处理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关联性时的总体问题类似,这种实存伦理的构建需要在个体自省的基础上,通过谨慎且长期的努力,来建立个体与个体之间基于关爱实践的关联性,并将这种关联性扩展到整体社会。这意味着,尽管我们仍然抱有良善愿望,实存伦理意义上的关爱伦理需要人们做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为人们更好地面对当下数码时代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在这个层面,以民族志方法作为主要特征的人类学,在处理微观日常生活的伦理权力实践以及这种微观实践的社会关联性层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社交时代的关爱伦理的复杂性,或许为人类学提供了重建“礼物”理论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