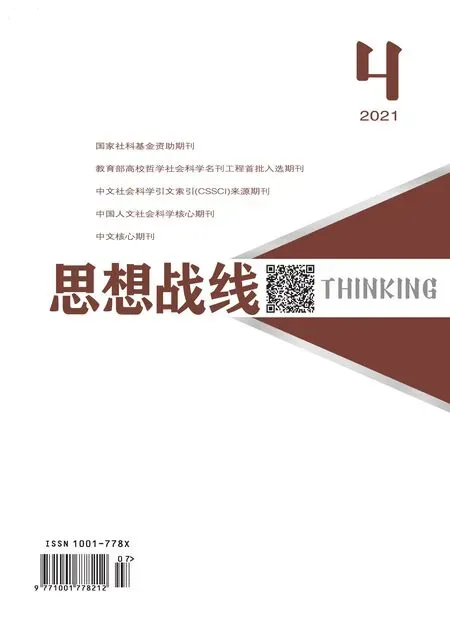走向历史的记忆
——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新趋向
朱洪斌
一般而言,记忆是指“人脑对过去经验的保持和提取过程”。(1)“记忆”条目,载《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1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它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记忆和回忆(记忆的再现)。具体来说,首先是感性经验的摄取、存储,其次是被存储的信息经意识和潜意识的加工,再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向外输出。记忆作为心理活动的集合体,最初是属于心理学及跟心理学相关的一些学科(教育学、精神病学等)的基本范畴,它关注个人的心理因素与认知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记忆与回忆为主题的研究风气日渐兴起,迅速发展为欧美学术界跨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记忆问题,主要关注集体记忆而非个人记忆,侧重揭示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记忆与身份认同、权力斗争之间的关系。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这股“记忆之风”在中国学界和公共空间激起一股“发掘记忆,重构历史”的学术意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里涌现了一批极具探索精神的学术新作,带有“记忆”之名的译著、课题和学位论文频繁地跃入眼帘,公众也热衷于追寻一切有助于强化认同的国家、地区和家族的历史文化记忆。与记忆研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是作为当代的社会文化焦点而显现,其自身也已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学走向深入的重要支点。
一、跨学科视域下的“记忆”理论
日常生活的经验表明,只有调动各种直接的、间接的记忆,个人才能清晰地把握眼前的境遇,从而制订出恰当的解决具体问题的行动方案。记忆之于个人,具有重要的认识功能和积极的现实意义。20世纪初叶,美国新史学领袖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指出:这些被唤醒的个人回忆,“即他曾经听说过或从过去的书中读到的事”,大都属于历史的领域,个人的回忆往往与历史交织在一起,故他认为:“我们可以把历史视为我们的记忆的一种人为的延伸和扩大。”(2)[美]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6~17页。鲁滨孙的这一观念,在另一位美国史家卡尔·贝克尔(Carl L.Becker)的手中获得精致的表述。1931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发表一篇著名的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例,具体而微地阐发其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在贝克尔看来,历史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个面相:“有两种历史:曾经一次性发生过的真实的事件系列,以及我们推断并记住的观念系列。第一种历史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它就是它;第二种历史是相对的,总是随着知识的增长或精炼而改变。”历史学家应当竭尽所能地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的历史,但在现实情况中,“真实的事件序列只能凭借我们所推断和记忆的观念系列而存在”。因此,我们的历史知识几乎等于客观的历史,而历史知识的本质是记忆,就是关于被推断和被考察的事件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历史就是关于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的记忆”。(3)[美]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马万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6~197页。换言之,历史(主观意义上的历史)是一种知识,知识来源于经验,经验则产生于人对过往事件的回忆,“记忆”是形成历史认知的核心因素,于是推衍出“历史即记忆”的结论。
大约在同一时期,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把记忆的问题引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开创性地提出超越个人记忆的集体记忆的重要性。他在《记忆的社会框架》(1925年)、《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1941年)、《论集体记忆》(1950年)三本著作中集中阐述“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尝试为集体记忆的研究提供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可归结为一句话:“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社会性和创造性的重构。”其理论的要点有三:首先,社会性是一切记忆的核心。哈布瓦赫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记忆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并从中获得重建记忆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4)[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 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页。记忆的主体是个人,内容却是在特定群体的情境中构建的;集体记忆透过个人记忆来实现,在个人的记忆中体现自身。其次,集体记忆不仅是一个群体内部所有成员共享的、有关过去的表述,而且也是基于现实需求的创造性重构。在每个历史时期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和愿望形塑而成。在理性或理智的主导下,“按照一种符合我们此刻观念的秩序,在库存记忆中进行挑选,抹去其中一些,并对其余的加以排列”。(5)[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 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借助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经验,人们重构的过去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描述”,是事实与观念、意象与价值的综合体。最后,不同的社会群体以历史、宗教、艺术和日常生活等各种象征性的形式,竭力保持集体记忆的鲜活,“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6)[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 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页。建立认同感,有效地维持群体成员间的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则是集体记忆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为代表的法国年鉴派史家提出“新史学”的概念,陆续推出《研究历史》和《新史学》两种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推动记忆问题成为欧洲历史研究的“新宠”。按勒高夫的观点,年鉴学派第三代所倡导的“新史学”,“是以集体记忆作为出发点,目的是创造出一种科学史。新史学可以被阐释成为‘记忆的一场革命’”。(7)[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从80年代开始,皮埃尔·诺拉动员120位学者,编纂出版由135篇论文组成的《记忆之场》,全书包括三部:《共和国》《民族》(三卷)和《多元而统一的法兰西》(三卷),分别于1984年、1986年和1992年出版。皮埃尔·诺拉对法兰西民族意识的演变及其窘迫的现状颇为敏感,他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史学以著名史家拉维斯为代表,“拉维斯不仅主编27卷的《法国史》,还是第三共和国历史教育的主持人,他的历史观念通过中小学历史教育而成为19世纪末以后几代法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在诺拉的笔下,法国的“历史记忆”就是建立在专业史学基础上的有关民族过往的共同记忆。但是20世纪以后,在法国社会与历史观念的双重变奏的背景下,“拉维斯主义”培育起来的法国民族精神凋零殆尽,诺拉尝试从凝聚法国集体记忆的各种场所入手,以“民族情感”的研究路径来取代过去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模式。(8)黄艳红:《“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记忆之场”是诺拉创造的一个新概念,它存在于记忆与历史之间,包括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三个层面。实在性指的是物质形态,象征性指的是象征意义,功能性是指“记忆之场”在不同时代的社会功能。按诺拉的列举,这些寄托记忆的场所,诸如档案馆、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条约、宪法等等,既可以是具有纪念性的建筑,也可以是带有象征意义和文化功能的仪式、组织和历史文本。(9)[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载《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页。《记忆之场》三部曲实际考察的记忆现象非常繁杂,以至有学者形容它是“记忆叙事的百货店”。(10)孙 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学海》2015年第3期。诺拉的文风飘逸、博雅,善用联想和象征的手法,理论阐发相对逊色,却使“记忆之场”这一不易把握的概念赢得了广泛的研究空间。
莫里斯·哈布瓦赫重视“记忆如何被社会建构”,而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视角中,进一步提出他的新问题,即“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11)[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他以“社会记忆”取代“集体记忆”,凸显对记忆的延续和传播的研究。康纳顿认为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忽略了社会习惯记忆,共同的社会记忆之所以代代相传,完全受益于记忆的传授行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12)[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页。要而言之,在纪念日、庆典仪式、宗教祭祀等一类的场合,人们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的方式,延续和传播社会群体的共同记忆。
近似的分析和阐述,见之于德国古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及其夫人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从德国的文化学传统出发,扬·阿斯曼从集体记忆中区分出两种类型:“人在这个世界生存需要两种记忆,一个是短时段之内的交流记忆,另一个则是长时段之内的文化记忆。”(13)[德]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载陈 新,彭 刚主编《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交流记忆”是通过人际之间的对话交流形成,是一种短时的记忆。“文化记忆”是一种长时段的记忆,当承载记忆的主体死去了,它仍能恒久地延续下去。如果不想让历史经历者的记忆消逝,则“交流记忆”必须转化为“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强调一个群体借助文本、文献、符号系统、媒体、各种机构诸如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事实,以及一个群体为了构建属于所有成员和被每个人所珍视的过去而举行的各种活动。”(14)金寿福:《评述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载陈 新,彭 刚主编《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40页。换言之,凡与记忆直接相关的文献、文物,或旨在促进记忆的形式和活动,包括神话、仪式、纪念物、整理、撰写、出版和普及文化传统的活动过程,都属于“文化记忆”的范畴。
二、“记忆”理论运用的若干实例
以上扼要梳理了流行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记忆理论,这些理论大都以哈布瓦赫的经典论述为源泉,同时结合各国的学术传统及经验研究而批判性地发展起来的。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各种概念互有交叉,内涵指涉也颇有重叠。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有自己的习惯称谓,“历史记忆”为历史学者所偏爱,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则常使用“社会记忆”或“文化记忆”。“集体记忆”等一系列相关理论的出现,为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倡导“科际整合”的历史学)提供了新颖的研究视野及方法,特别是围绕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已经取得不少值得重视的新进展。据笔者涉猎所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新世纪以来,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问题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现一大批地域性的微观研究,它涉及中国境内众多的少数民族(包括蒙古族、藏族、壮族、苗族、瑶族、彝族、畲族等等),考察的范围囊括神话传说、民间歌谣、地方史志、世系谱牒、民族节日、祭祀仪式和建筑遗存等。(15)李技文,王 灿:《我国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问题研究述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台湾学者王明珂谙熟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并有深入羌族村寨,从事田野调查的经历,他撰有“华夏边缘”的系列著作,包括《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997年)、《羌在汉藏之间》(2003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2006年)、《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2009年)。王明珂创立“族群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理论,收获最为丰硕,可谓胜义如云。
据他的研究,传统“族群”理论倾向于阐释制度、语言、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族群内涵”,把“族群”视为一有共同的客观体质和文化特征的人群,而他认为:“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形成与延续,并非全然是生物性繁殖或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更赖于其成员之认同与‘异族概念’(族群边缘)的延续与变迁。”(16)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希望历史地说明“什么是中国人”,可以采用“从边缘看中心”的策略,即通过考察“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说明古之华夏、中原帝国到今日中华民族与中国之变迁,从而解答“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对于这一研究思路,他做了一个简单而形象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1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序论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王明珂选取活跃在“华夏边缘”的所谓“羌族”作为研究对象,穿越长时段的历史隧道,透视中原汉族与西部各民族的互动历程,揭示出人类族群之间因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所产生的认同与区分的普遍历史现象。从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看,关于共同始祖的记忆是形成血源性共同体的关键环节。追溯起源的社会集体记忆,“它可以被选择、失忆与重新建构,因此族群认同可能发生变迁。”(18)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页。华夏边缘的扩张与变迁,正是在边缘人群的历史记忆与失忆的交替作用中完成的。
王明珂举秦汉以前中原与边缘的族群认同之变迁为例:“‘华夏认同’首先出现于黄河流域邦国的上层贵族间,然后逐渐向下层、向四周扩散。在地理上华夏认同向四方的成长扩张,主要透过其边缘人群的认同变化;不断有华夏边缘人群对本地古文明‘失忆’,寻得或接受一位华夏圣王祖先作为‘起源’,并在历史想像中将此‘起源’之前的本地过去‘蛮荒化’。在如此的过程中,汉代江南吴地的华夏相信春秋时吴国王室之祖为‘周太伯’,本地在太伯来到之前是一片蛮荒,因此对于当地良渚文化以来的精致文明所代表的过去失忆。西方蜀地的华夏,也相信蜀之贵胄为黄帝后裔,遗忘了三星堆文明所代表的本地之过去,或将蜀的过去神话化与蛮荒化。黄帝、大禹或一位商周贵裔不断被攀附而成为一些华夏边缘族群的祖先,华夏边缘(华夏观念中的异族)便在如此的过程中向外迁移,边缘内的‘多元’也因此成为‘一体’。”(19)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在笔者看来,在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似的一幕再度浮现出来。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接续汉代以来的官方史学传统,竞相设置修史机构,着手记录和撰写本民族的历史。在追溯其族群起源之际,他们从华夏历史传说或经典中寻求认同,把传说的圣王或汉族帝王看成是本民族的祖先,譬如匈奴族刘渊称自己是刘邦后裔,匈奴族的赫连勃勃自认为是大禹后裔,建立前秦的氐族称自己是有扈氏的后代,建立后秦的羌人姚氏自认是虞舜的后裔,鲜卑族自称是黄帝之苗裔,高句丽族的北燕王慕容云自称是颛顼的后代,鲜卑宇文氏自称炎帝神农氏之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一类“冒认祖先”的现象层出不穷,背后折射的是随着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的交融渗透,边缘族群文化认同的变迁及范围更大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传统意识的“中国”,并非近代主权国家的概念,也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专有名称,而是以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心理特征,以中原王朝的统治为象征的华夏文化圈概念。其边际和内涵随着民族交融而有变化,但始终维持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先秦史专家刘节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民族的向心力很强,在偌大的地域上,一切文化趋势,总在大一统的精神之上进行一切建设。伦理上,有宗法制度去维系;政治上,有大帝国的观念去笼罩一切。”不仅如此,中国民族一向多元,语言庞杂,而文字却有整合语言的力量,这为民族融合创造坚实的基础。刘节据此赞道:“这种力量,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20)刘 节:《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新路径》,载曾宪礼编《刘节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按王明珂的看法,“华夏边缘”理论是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的反思性注解与补充。针对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民族与历史的长期误解,他意味深长地指出:“以长程历史来说明今日被称作‘兄弟民族’的少数民族与自称‘黄帝子孙’的汉族,均非只是近代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两者在历史上紧密而又绵长之政治、经济与历史记忆互动造成的结果。”(2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序论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这些认识和论述,对于考察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脉络及其文化特性,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二)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忆
在历史人类学的影响下,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于民间传说的史学价值亦有新的理解与运用。民间传说通常是指流行于特定地域的人物、史事、风物的口头叙事文学,也是凝聚某一特殊历史记忆的地方性知识。有的研究者指出:“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作为某种历史记忆的符号,它们的产生和流传过程恰恰是包含着丰富社会舆论与情境的一个历史真实。在社会史研究中,如何理解和解析民众世代口耳相传的具有明显‘地方性’的民间传说,是每一个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问题。”(22)户华为:《虚构与真实——民间传说、历史记忆与社会史“知识考古”》,《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社会史学者把民间传说视为基层社会的“历史记忆”,解析这些传说和故事,就是重建基层社会历史的过程。
在社会史专家赵世瑜看来,无论是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在本质上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达形式。(23)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对历史学家来说,二者居于同等的价值地位。他以沈万三的传说为例,这一故事不仅被许多历史文献所记载,同时也在民间长期流传。沈万三与明初政治的众多传闻,显然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否定传说的子虚乌有,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唯一任务,这个传说的产生和传播的过程恰恰是另一个“历史真实”,是什么人、以什么动机创作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为何又流传至今,这才是最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赵世瑜等对清初以后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太阳生日及其信仰习俗的阐释,为这一研究路径贡献了一项精湛的案例。(24)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从清初迄今,在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流行一种说法,即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九日是太阳生日,而其他地区则不见这一传说的踪影。明清易代之际,这一带江南民众的抗清最为激烈,民族矛盾和抗争失败后的记忆也甚为浓烈。赵世瑜等深入“地方性话语”和“历史记忆”的历史情境,推理这一民间习俗的背后隐含当地遗民对于覆灭的朱明王朝的眷恋之情,认为它应该是在大规模抗清斗争失败以后被创造出来。制作这一故事及习俗的是江南士绅,他们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寄托内心潜藏的政治态度;民众接受了这种形式,却改变它的政治意涵,使之成为纯粹的岁时习俗。通过解读一个转化为民间习俗和传说的历史记忆,作者撩开了隐匿在历史深处的一段记忆,一段有别于胜利者“历史叙事”的历史记忆。
(三)社会记忆与乡土重建
对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显得更有热情,其成果也颇为可观。他们的目光聚焦于20世纪后半期经历一系列激进社会运动的乡土社会,致力于发掘农村的社会记忆里的历史图景。景军较早指出从社会记忆的角度,研究“社会记忆与乡土中国”的关系,认为这可以深化我们对社会史的理解,丰富我们的历史想象力。(25)景 军:《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学》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6~339页。原刊(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总第12期。
景军以甘肃省大川村重建孔庙的活动为对象,把一个乡村社会置于长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中,利用田野调查搜集的口述资料,细致还原大川孔庙被查封、毁弃及重建的社会历史过程,并且考察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包括仪式知识,族谱写作、民众脑海中的村史、人们的苦难叙事、复仇性的政治、仪式意涵的对立观点以及人们对激进社会主义的态度”。他特别关注这些活动是“如何成为人们记忆的载体”,“国家权力如何极力左右人们的遗忘与选择性追忆”。(26)景 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页。依据景军的研究,在大川孔庙从破坏到复兴的进程中,孔氏家族的成员“不断地使用文化创造,将神圣的传说、历史的变形与想象的现实加以整合,最终转变成为集体信仰”。(27)景 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3页。由此可见,历史文化的记忆不是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而是在新的语境中被不断地重新组合建构,它是一个不断选择和重塑的过程。
方慧荣对河北省归远市西村农民有关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研究,是另一项饶有意味的探索。该项成果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研究”之一。作者通过大量的口述调查资料和部分的档案文献,“逼近”农民隐蔽的记忆世界,细致入微地重建农村社区与外部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以“无事件境”的概念,刻画农民记忆的心理特征。所谓“无事件境”,是指农村生活的特有节奏——高重复率,像春耕秋收、婚丧嫁娶等等,这些活动“导致事件记忆上难免的事件间各种细节的互涵和交迭”,生活其间的村民“在心理上也‘无意’将这些众多的重复性事件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作者认为“这是传统农村社区中的村民与现代人的最大区别”。(28)方慧荣:《“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2页。依笔者的看法,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可以为分析农民集体记忆的心理特征提供重要的启示。“无事件境”里透露的“真实”,虽然缺乏职业历史学的精确性,却“真实”再现了他们对于某一类生活场景的认知与情感,是一个被他们创造出来的这一类场景的典型“缩影”。
这些运用记忆理论的研究案例,虽然还不能涵盖“记忆之风”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全貌,但也足以彰显一个强劲的趋势:“记忆”研究已经辐射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拓展了固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理论认识成果也日渐丰满。从现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学者们一方面继承实证史学的治学精神及方法,另一方面有意识地搜集、分析各种记忆史料,并从历史与记忆、中心与边缘、个人与社会、过去与当下等多个维度,深入地探索长时段的中国历史及文化变迁的复杂面相与内在肌理。而且更重要的是,集体记忆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独特表现,其参与历史进程的作用和价值,获得了重新审视和理性反思的契机。
三、基于多元记忆的历史书写
为何记忆及其相关问题会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包含历史学在内)的热点问题?许多中外论者的分析指出,这是由于20世纪后半叶国际政治、民族国家之嬗变与历史意识之转折互为推动的结果。在现代化、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无论是发达的欧美世界,还是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先后都在极短时间内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迁,经济、政治、民族、宗教等各种群体的利益及意识形态冲突不绝如缕,愈演愈烈,近代史学的统一、进步的主旋律被嘈杂多样的声调所袭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边缘文明、边缘群体(诸如少数民族、基层民众、妇女、移民等)的历史记忆终于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发达的信息技术和非传统主义的传播媒介,则助长了集体记忆的贮存与传播的能力。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文化标签,无疑当属多元主义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自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历史”一词,通常含有两层含义:一指过去的事件(客观历史本身、历史实在),二指关于过去事件的陈述(历史记载、历史著作),以及以此为业的一门学问(历史学)。对于19世纪的职业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起点……就是要区分确凿的事实与凭空虚构、区分基于证据及服从于证据的历史论述与那些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式的历史论述”。(29)[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前言,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页。历史研究的首要之举,就是按实证史学的标准,鉴定史料的真伪及时代性,划分不同史料的证明效力,记忆性质的史料(口碑、故事、传说等)则被当作“齐东野语”,视为无价值的虚假信息,弃之如敝屣。与实证史家追求客观历史的纯真信念相比,20世纪史家对于历史的不确定性普遍具有复杂的感触。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及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历史哲学经历从思辨到分析和批判,再到叙事的演变。伴随认识论和语言学的转向,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究竟是什么”和“历史学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怀有更为激进的反省。(30)[法]米歇尔·德·塞尔多:《论史学研究活动》,载[法]J.勒高夫,P.诺拉,R.夏蒂埃,J.勒韦尔主编:《新史学》,姚 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2页。思考的重心从“历史原来是什么样”“历史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发展到“历史是怎样被写出来的”,于是史学史(史学理论)就被推到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
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其生产流程,就成为后现代语境下历史思维的一般特征。具体的史学实践表现为:在历史观念方面,人们不太追求某种确定不移的历史(如英国史家阿克顿所谓的“终极的历史”),而是强烈质疑线性的历史进步论和以民族国家为主角的“大写的历史学”;在研究对象上,远离“宏大叙事”的历史人类学、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微观史学、记忆史等新史学蔚然成风。探索历史真相仍然是不可动摇的职业信念,但中外史学家更关注的是:人们是如何在既定的社会框架下,利用在历史中形成的各种记忆素材,驰骋其创造性的想象,重构有关过去的知识,也就是“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记忆与历史似有一道鸿沟,记忆更为亲切,更有温度,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稍纵即逝的鲜活影像;历史则是一套人为的叙述,是按照权力架构、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而有意为之的宣讲。记忆与历史的关联错综复杂,决非如此泾渭分明,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历史是一种记忆,它代表一个时代主流社会的历史意识;记忆也是一种历史,同样经过选择、制作、保存或遗忘的生产过程,同样无法摆脱社会权力的控制。皮埃尔·诺拉曾经说过:“历史的真正使命是摧毁记忆,排斥记忆。”(31)[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载《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页。这里所谓的“记忆”,指的是被权力控制的集体记忆,或者如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讲的“文化记忆”。除这种被控制的集体记忆以外,诺拉也注意到个别、多元的记忆现象在当代法国社会的兴起,包括地区性的历史记忆,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纪念活动等等。当现代民族国家稳固建立以后,历史的民族主义使命或将不再成为迫切的任务,建立基于多元记忆的身份认同和历史书写,可能会成为今后学术发展的一个新命题。关于历史与记忆之关系,勒高夫有一句颇有见地的评论:“记忆滋养了历史,历史反过来又哺育了记忆。”(32)[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这段话意味着历史学家需要担负起两种任务,一是运用多元化的记忆去“拯救”僵化的历史叙事,发掘历史演进中不同群体的“声音”,二是坚持职业历史学的求真信念,对一切记忆史料进行彻底的批判性解释,驱除一切偶像崇拜的魅影。
在记忆理论的关照下,一切历史信息都可以被当作特定群体的“历史记忆”,被实证史学抛弃的口头传说,与文献资料一样,具有同等的史学价值。对历史学家来说,探寻历史事实意味着两层意涵:一是事件本身的真实面貌,二是在事件发生以后被集体记忆重新构造的“社会事实”。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学以人类社会及其演变为研究对象,力图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真相,并以睿智的洞察力,理解和掌握人类自身的命运,最终增进人类的福祉;那么我们也应承认被集体“记住”的事实对于人类观念及行为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它同样是影响历史的重要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不应是“科学史学”的障碍;相反,它不仅拓展了通往“历史真实”的渠道,而且为认识人性之本相提供一种重要的路径。
中国古典史学的遗产绵长而丰厚,现当代“公众史学”和“口述史学”已经积累巨量的记忆史料,这些都是中国“历史记忆”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中国的学术界而言,只有植根本土的历史经验,保持对于中外记忆理论的兼收并蓄,并在跨学科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不断锤炼分析工具和话语理论体系,与“记忆”相关的中国历史研究必然会有更多惊艳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