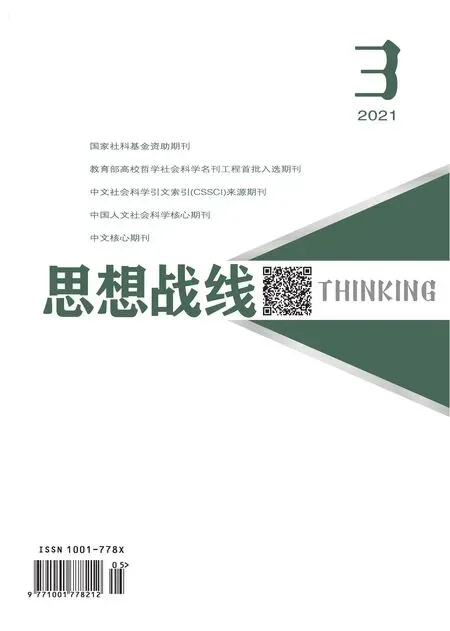迈向理解:灾难记忆的力量与档案部门的责任
丁华东,张 燕
现代社会自然灾害、战争等一系列重大灾难事件在引发公众深切关注的同时,也将灾难记忆一再拉回当下视野。“宇宙最不理解的事是宇宙可以被理解的”,以爱因斯坦这句话形容人类对灾难的认知过程有独特之处。“理解”或可成为理解灾难记忆的又一路径。国家、社会、民众如何理解灾难记忆?公众何以通过灾难记忆理解彼此从而汇聚共同体?何以通过“理解”之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为档案部门提出了现实命题和破解思路。
一、灾难记忆:人类的灰色记忆
(一)灾难记忆的内涵
“灾”在《辞海》中泛指水、火、荒旱等所造成的祸害以及疾病、损伤、死亡等祸事,(1)夏征农:《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2861页。灾难意指不幸的遭遇。(2)夏征农:《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430页。“灾难”与“灾害”近义,灾害主要体现为无意识的客观行为,如洪灾、旱灾等,灾难则含有苦难、受难、磨难之义,赋以一定的主观、能动意义。人类发展史亦即一部灾难史。洪灾、旱灾、火灾、地震、瘟疫、战争等比比皆是,大规模战乱对人类文明的戕害尤为触目惊心。作为人类历史链条的非常规冲突因子,灾难不仅能改变局部社会生活面貌,甚至在强度、幅度达到一定规模时可改变整体政治版图、经济格局以及内在文化流变。
“‘如何记忆发生了什么’,是当代文化领域内一个根本性和极具争议性的问题。”(3)[美]帕特里克·格里:《历史、记忆与书写》,罗 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作为重要的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灾难及其衍生的灾难记忆已从早期应用层面的自然科学研究,广泛延伸至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关注。仅在社会学领域,灾害社会学就历经经典灾害社会学、社会脆弱性到社会建构主义的学派演变和发展(4)周利敏:《从经典灾害社会学、社会脆弱性到社会建构主义——西方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比较启示》,《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二战”后对战争创伤的总结与反思推动了记忆研究的兴起,创伤记忆成为学界热点议题。综合社会记忆的界定,灾难记忆可视为一定的社会群体围绕特定自然或社会性灾难以各种媒介形式保存、传递、共享的社会框架、历史事实、价值理念与生活经验,包括灾难背景、灾难事实、伤害牺牲、痛苦体验、斗争精神、教训经验等。也有学者言之为苦难记忆、创伤记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维度观之,灾难记忆内涵丰富,融事实性和意义性于一体。
(二)灾难记忆的构成
灾难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自然灾难,如地震、洪灾、瘟疫等;二是社会灾难,如政治灾难(如战争、政治动乱)、经济灾难(如经济危机)、文化灾难(如文明毁灭等)、生态灾难(如核泄漏等)。灾难常互有因果,初时可能囿于一时一地一事,但牵一发而动全身。灾难记忆往往彼此联结、时空交错。灾难记忆因划分角度不同,可形成不同体系。从主体角度,分为受害者(个体、家庭或群体)记忆、施加者记忆、公众记忆、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等。从客体角度,包括各类自然灾难记忆、社会灾难记忆。从内容角度,包括灾难过程记忆、灾后记忆、灾难反思记忆等。从载体角度,可分为文本、影像、空间、仪式等灾难记忆。从时间角度,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等灾难记忆。从空间角度,可分为地方或区域、国家、全球等灾难记忆。灾难记忆本身又因构成要素的复杂性、时空场域的交织性,而呈现为一面透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记忆“多棱镜”。在整个国家、民族、地方、家庭以及个人记忆体系中,无论正视与否,灾难记忆均据一席之地,并与其他类型记忆相互贯通。
(三)灾难记忆的特点
作为人类的灰色记忆,灾难记忆构成了人类社会记忆的重要内容,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反思性,可从不同维度加以释读。源于灾难的突发性、破坏性、扩散性等,灾难记忆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首先,创伤性与修复性的统一。一方面,灾难记忆在社会心理上属于灰色调乃至黑色调,常伴有苦痛、屈辱、挫伤、失落、消极等负面体验。“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5)[美]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王志弘译,《文化研究》2011年第1期。从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出发,灾难记忆犹如心理伤疤轻易不得触碰,往往成为当事人或相关者有意回避、封存乃至刻意忘却的记忆。出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心态等因素,灾难记忆如大屠杀记忆等常受到外界不同程度的遮蔽,甚至有意识、有组织的清除记忆。另一方面,灾难记忆的存在使得灾难的创伤有所寄托、缅怀、反思。灾难记忆包含着斗争、抗争、和解,成为个体或社会修复文化心理创伤的空间和出口。
其次,断裂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一方面,区别于常态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破坏性强的灾难常以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形式出现、演变,从社会记忆的横断面来看,灾难记忆常表现为断崖式的记忆留存和闪光灯式的自传体记忆。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灾难貌似捉摸不定,实则有迹可寻,蕴含一定的自然或社会规律,甚或表现为历史的循环、重演,新的灾难记忆不断融汇其中。如对于地质灾害频仍地区,灾难记忆可能始自久远;对于一些历史地理因素饱受战乱侵袭的国家或地区,战争记忆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理痼疾。
再次,脆弱性与再生性的统一。一方面,社会记忆需要一定的承载和传播媒介,灾难记忆常因证物或人证等“证言证词”的消亡而湮灭。灾难记忆又交织权力的较量和作用,“反记忆”依然存在。譬如,对于南京大屠杀记忆,日本右翼势力公然篡改历史;慰安妇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依然受阻。时过境迁后,灾难记忆更加脆弱,常会产生结构性、大面积和长时段的遗忘。另一方面,灾难记忆的沉寂、隐匿并不意味完全逝去,它常以各种形式重生、再现,由社会的隐性记忆复活为显性记忆。同一灾难记忆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具有不同的表达差异和意义侧重。有何意义、意义几何,这一意义的流动性在贯通时空的同时,也使灾难记忆得以在当下时空再生、重构。
二、灾难记忆的力量
尽管灾难记忆对于人类个体或群体层面属于一种灰色记忆,但并非完全负面作用。与之相反,灾难记忆的特殊性,可使其对个体、群体甚或整体国民精神、心态的形成施加巨大影响,进而赋予其不同一般的社会功能或记忆能量。
(一)身份认同的力量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做什么?这些始终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身份在自我与他人的区别中得以认知,在社会关系的互动中得以确立。灾难对于人的身份认同冲击具体而强烈。由于灾难施加的是对特定时空、类型群体的危险和伤害,群体在共同面对灾难的过程中,可真切感受到共同的痛苦、边界和情感,国家、民族等这类“想象的共同体”就此得以显现和强化,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就此产生。“记忆体现为一个建构认同和验证认同效果的斗争空间”。(6)[法]埃里克·布里安,玛丽·雅伊松,S·罗密·穆克尔吉:《引言:社会记忆与超现代性》,梁光严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2年第3期。记忆能够提供公众的身份感、归属感、根源感,为共同体记忆发挥作用。这种认同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等。如地震、洪水、海啸等可能会荡平原有社会地理空间,但同时让心理空间更为紧密。电影《唐山大地震》所表达的,废墟绝非一块纯粹的土地,而是埋藏曾经生活记忆的家园。灾难记忆从负面角度,促使特定群体的主体意识得以觉醒,在灾难中激发认知、调动潜能,进而获得群体性认同。
(二)奋发行动的力量
灾难打断了既有的社会生产链条,在造成一系列破坏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在重大灾难后,往往倒逼出相应的社会修复和重建机制,如国际防疫合作机制、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国际事务治理机制等。灾难记忆包含克服战胜灾难的经验智慧,成为现实的行动指南和方向。人类终将战胜灾难,“化危为机”,这是一种有助于防灾减灾的力量。灾难记忆记录的不仅有牺牲、教训与苦难,还有重生、经验与勇气。灾难记忆可转化为国家治理必不可少的社会资本和精神动力,在国家精神、民族意识、信心恢复等方面提供思想动能。就个体而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或可成为千百年来人类走出灾难记忆的又一注解。
(三)批判反思的力量
从衍生现代地震学的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起,人类“经历了从宗教性的灾害观转向科学认知自然,进而对人类文明自身进行反思的思想进程”。(7)王晓葵:《灾难记忆与灾后反思,如何构筑一部全球人类史?》,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20/04/14/716571.html,2020年4月14日。思想的力量在于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批判只存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它是探求某个未来或真理的工具、手段”,(8)[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 福柯文选Ⅱ》,汪民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批判反思对于灾难记忆不可或缺。从文化创伤理论出发,灾难记忆相关的创伤记忆即以反思性和主体性为特征。这一批判性记忆场域最为复杂。在这一场域,受难者、施加者、公众、媒体等各方力量有着不同的话语权力、心理诉求和关注重点。灾难何以产生?后果几何?如何恢复重建?怎样避免重演?一连串问题不仅指向作为历史事件的灾难本身,更隐含“谁来记忆”“为谁记忆”等不同的政治文化立场、价值取向和叙事话语。诸如关于战争记忆,人们不仅关注记忆本身,更关注记忆何以形成、演变以及背后的复杂社会关系,进而达成更深意义的批判性思考。某种程度上,这可视为灾难记忆的“社会框架”,体现出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环境、群体心理下的不同思考方式和行动逻辑。正如灾难本身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灾难记忆同样是人类生活世界不可回避的重要组成。它能够为当下和今后提供值得沉思和警醒的记忆资源和意义框架,在灾难记忆由个体层面不断向集体的、公共的层面转移、汇聚过程中,相应的批判反思也得以展开和深化。
(四)理解和解的力量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记忆最终的目的在于促进理解与和解。“理解”是“应用已有知识揭露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认识新事物的过程”,(9)夏征农:《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3447页。它强调一种联系和面向新事物。这种理解既有对自然界,更有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自身关系的理解。人们对历史证言如地震受难者、大屠杀幸存者的重视和追寻,不仅在于藉此可填补历史链条的缺失一环,更在于对“失声”记忆群体的发现与尊重,重赋其尊严与话语,给予必要的救助与抚慰,达成面向未来的宽恕与理解。像“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卢旺达大屠杀独立调查委员会”等官方或民间组织的首要任务即调查和记录灾难记忆,最终寻求解决方案。面对人为施加的极恶灾难,灾难历史犹如黑暗深渊,面对尚需勇气,寻觅出口和亮光尤显艰难。但若非如此,理解和解终将难以实现。灾难记忆终极指向精神重建、创伤修复、身份认同建构,恰似迈向理解与和解的一剂苦药,帮助人们正视、理解和接受灾难,学会与灾难共处,而非回避与沉湎,更非强化冲突与对抗,从而实现人自身、他人、群体乃至世界和解的过程。正是在具有共情效应的灾难记忆中,理解与和解成为一种理想与吁求。
三、灾难记忆的纪念
尽管灾难记忆具有多重力量,鉴于其固有特点,始终潜伏着失忆、变形、失真等记忆的危机。这一危机在快速变迁的当下甚至愈演愈烈,以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谓的“历史的加速度”快速消失。以何种方式记忆灾难,成为灾难记忆对抗危机的焦点。阿莱达·阿斯曼分析了4种对待创伤性记忆的模式:对话式忘却、为了永不忘却而记忆、为了忘却而记忆、对话式记忆。(10)[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还是忘却:处理创伤性历史的四种文化模式》,陶东风,王 蜜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2期。记忆与遗忘共生相长,灾难记忆往往指向纪念,灾难纪念成为传承、建构、再生产灾难记忆的重点。
(一)纪念与记忆的“危机”
记忆的危机似乎不言自明,实则意蕴深邃。保罗·利科指出:“在记忆的危机中造成这个危机的,是表像的直观一面的消失和一个与此相关的威胁,即失去了对发生过的事情的证实。”(11)[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 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30页。相较而言,灾难记忆更易面对历史“证言”消逝、事实流于虚构的挑战。某种程度上,怀旧或纪念的形成也可从中得到解释。这种记忆的危机感伴随着历史的疏离感、陌生感,以及记忆特定群体的身份或认同危机。不同形式的纪念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而当记忆走向纪念时,也意味着另一种忘却的开始。“呈现为文字形式的作品本身就包含被遗忘、自动消失、过时和被尘封的危险,这些情况与其是连续,不如说是断裂。”(12)[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社会记忆中也倾向于传递主流一面,对灾难记忆中的边缘记忆、苦难记忆、同质化记忆等常略过不表或语焉不详。埃雷兹·艾登等人在分析为何越痛苦的记忆(如战争记忆)越易被忘怀时,绘制了集体记忆的铭记与遗忘曲线,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遗忘的半衰期在逐渐变短”。(13)[美]埃雷兹·艾登,[法]让·巴蒂斯特·米歇尔:《可视化未来:数据透视下的人文大趋势》,王彤彤,沈华伟,程学旗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0~161页。新传媒时代的注意力经济加速了这一人为的选择性过程,在某些记忆得到强化的同时,也使遗忘延续,直至将某些灾难记忆推向“记忆黑洞”。
遗忘具有两重性,也存在积极的一面。保罗·康纳顿认为,与被动的“失忆”不同,遗忘“牵涉到不同的群体行为与社会机制”,至少有7种类型的遗忘,包括强权国家的记忆清除、迈向和解的遗忘、重塑身份的遗忘、结构性失忆、避免冗余的记忆删除、有组织舍弃以及抗拒耻辱的沉默性遗忘。(14)Connerton P:“Seven types of forgetting”,Memory Studies,no.1,2008.出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环境或个体原因,遗忘同样不容忽视,且遗忘本身已成为维护权利的重要内容(如被遗忘权),甚至成为权力的象征之一。戈登·贝尔等强调对包括痛苦记忆的全面保存,但可不触碰。(15)[美]戈登·贝尔,吉姆·戈梅尔:《全面回忆 改变未来的个人大数据》,漆 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页。从社会心理角度,对灾难记忆、创伤记忆适度的选择性遗忘,也具有对个体或群体自我防御和保护修复的功能。如何辩证地理解、对待、平衡记忆与遗忘,值得深思。
(二)灾难之“记忆之场”
皮埃尔·诺拉提出了“记忆之场”的抽象概念,它指“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16)[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黄红艳译,载《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孙 江编,黄红艳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6页。灾难记忆同样需借助一定的“记忆之场”,如通过档案、历史遗迹、文学作品、仪式、空间等各类象征符号,实现灾难记忆的时空再现与意义建构。在既往记忆实践中,人们采用了多种方式生成各类纪念灾难的“记忆之场”。
一是史料纪念。“苦难唯有进入历史,才会具有一种社会的力量。”(17)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6页。史料纪念以记忆文本化、书面化的形式将灾难记忆固化、留存。档案在灾难记忆的存储和社会化中占据特殊地位。国际档案理事会在《档案共同宣言》庄严指出:“档案是决策、行动和记忆的记录。档案是代代相传的独特且不可替代的遗产。”(18)《国际档案大会通过〈档案共同宣言〉》,《中国档案报》2010年11月18日。作为历史的原始记录,玛琳·露丝·沃沙夫斯基通过对15个国家112个有关“二战犹太大屠杀”的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研究中心等的问卷调查,指出档案对于大屠杀记忆至为关键,档案提供了强化记忆和代际传递的官方、合法手段。(19)Warshawski M.R.:The role of archives in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96,p.226.其中,口述史料对于灾难纪念有着独特价值。
二是文学纪念。这直接反映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亦称为灾难文学。如上溯至史前大洪水,一直以神话传说、民谣、民歌等文学形式不断再现。地震、洪水、战争等灾难记忆,以其冲突性、毁灭性、人性的反思性等成为文学作品长期以来的热门题材。创作者以文学体裁、叙事话语再现,解读灾难记忆,引发历史思考。像“犹太大屠杀”记忆借助一系列文字作品、影视作品,代表性的如奥斯卡获奖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等,已成为公认的全球记忆和人类共同的创伤记忆。
三是空间纪念。记忆何以“栖居”?“记忆之场”的“场”本身就具有空间意涵。灾难记忆常导致物理和精神空间的大量流失,公众原先生活依存的记忆空间空洞化。通过空间或一种拟景的存在,可实现对既往灾难记忆的重现和复活,实现物质、精神双重空间的契合与重建,帮助抚慰和愈合精神创伤。通过各类纪念空间,如档案展览、纪念展馆、陈列馆、文化展厅、遗址保护等,生产出现实的“记忆之场”。如汶川大地震后原址重建的地震博物馆,全方位、立体式保存再现了这一国家、民族的灾难记忆,触动内心,激荡情感。虚拟现实、数字人文等新技术的运用更强化了空间纪念的“浸入式”体验和情感投入。
四是仪式纪念。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重在传达,除了刻写实践,还有容易受到忽视的“体化实践”。它以亲身举动和亲身在场为行为特征,以此说明“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表达和维持的”。(20)[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页。仪式纪念所具有的灾难记忆交流共享效果,具有普通记忆文本难以比拟的沉浸感和冲击力。如2020年4月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表达对抗疫中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相比典礼、集会等仪式,沉默的纪念象征意义更为深刻。
以上几种纪念方式常融汇一体,化作共同的“记忆之场”。纪念主体通过历史事件多元纪念的形式,表明和强化纪念的共同意义和对历史分歧的清晰态度。灾难记忆由此得以复活、回归,演化为当下意义体系的内在组成。
(三)从公共记忆到共享记忆
“纪念之场”的生成与建立,使得灾难记忆从个体体验汇聚、延伸进入公共领域,其关键在于形成与确立群体的共享记忆。公共记忆与共享记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公共记忆“有地域、文化、组织、阶层、年龄、少数族群和民族等之别”,(21)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载孙 江《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面向公共生活与空间。共享记忆面向社会群体内部,体现为包含各类形态、各个群体的共有的价值观念。它“通过设立制度(如建立档案),以及建立公共纪念设施(如设立纪念碑和为街道命名)等形式在人与人之间流动”。(22)[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49页。
共享记忆的特征在于:有着共同的记忆框架,有着共同的群体特征。它提供了群体和社会记忆得以理解、诠释与传承的框架。缺乏这一框架,时空的隔阂和疏离感就难以消除与克服,就无法连通不同时空社会情境的间隔。同一事件,于己为耻,于他为荣。“真实的和象征的创伤通过这种方式被储存在集体记忆的档案里。”(23)[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 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共享记忆为灾难记忆提供了贯通性的意义空间,起到弥补、粘合灾难记忆断裂、失根的作用。双方共享的记忆或经验范围越广,其传递效果越佳。这归因于共享记忆提供了一种自我与他者相互认知、互相理解的可能。如对于同一份抗战历史档案,中日民众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理解,除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歪曲、否认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日本民众缺乏共享记忆,进而造成对历史真相认识的隔阂与误区。“南京大屠杀”记忆从隐没到凸显、上升为国家民族灾难符号,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以其直面苦难、创伤的表达,转化为全人类的共享记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四、迈向理解:档案部门的责任
灾难记忆应不止于纪念,共享记忆的目标和方向则要达成理解。理解的一大基础和前提是“记忆”,“理解”也成为引导灾难记忆实践的行动逻辑。由此出发,人们可更加理解灾难记忆的意义所在,进而明晰档案部门在灾难记忆系统中的坐标和定位。
(一)构筑理解之基:灾难记忆的记录责任
“记忆”,首先要“记”,做好灾难记忆的历史记录。遗忘的形成既可能因为记忆的失落或隐匿,也可能因为人们失去了在特定情形下将之提取出的途径或能力。从理解角度看,灾难记忆包括起因、过程、结果、预防与救助等。2020年5月,国际档案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发表《新冠疫情昭示:危机时刻记录职责愈发重要不能停摆》联合声明,指出:“必须对决策依据、决策本身以及相关高层决策者进行充分记录,保证政府在应急事件中及事后均可问责,并使后代能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24)王一帆:《国际档案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发表联合声明〈新冠疫情昭示:危机时刻记录职责愈发重要不能停摆〉》,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93524827_734807,2020年5月17日。由此,确保若干年后,当下的决策、行为、结果可回溯、重建和理解,并为灾后重建与防灾减灾提供经验智慧。灾难记忆的形成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的“自然行为”,调控、干预力度较小。档案记忆的生成则体现为“自觉行为”,属于有目的性的生产,体现为生产性的过程,背后隐含着权力、技术控制下的主动选择与遗忘。通过制作成“档案”这一“档案化”环节,灾难记忆存储为人类的“刻写记忆”,转化为历史证据、证言,为其后灾难记忆的“社会化”(挖掘、活化、传承等)提供了前提与条件。
理解代表多元视角。由于灾难记忆与社会因素的复杂关联性,其生产机制更易受到破坏和干扰,导致记忆生产的离心化和“记忆之场”的空洞化。灾难记忆的“档案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与要求。以往档案部门作为官方记忆记录者,以档案管理体制、档案机构组织、业务规范体系等传统档案记忆制度,确保了灾难记忆的体制化、系统化生产与再生产。这一传统记忆模式随社会发展也面临多元记忆范式变迁的冲击。冯惠玲指出:“社会民主化进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少数人话语权的技术冲击,创造了大众记忆的新时代。”(25)魏智武:《数字记忆国际论坛热议社交媒体》,《档案学研究》2015年第6期。大众、新媒体视野中的灾难记忆,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灾难宏大叙事,更为注重个体体验。大众灾难记忆、新媒体灾难记忆的收集、记录愈加重要。“抗疫”期间,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均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展开相关资料征集、归档工作。国家图书馆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项目,广泛收集各类文献、实物以及口述访谈记录等。国外也有多个关于灾难记忆的数字人文项目如“飓风数字记忆银行”项目等。灾难记忆的数字化趋势突出。数字时代的大众灾难记忆采集与记录已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兴记忆领域,其中关涉的法治、伦理与技术考量将是意蕴深邃的课题。
(二)贯通理解之途:灾难记忆的叙事责任
记忆离不开时间、空间和叙事。叙事是诠释灾难事实,活化灾难记忆,达成受众理解以至形成互众的重要桥梁。保罗·利科认为,历史话语具有文献、解释/理解、对过去的文学表述三个层次的诠释。(26)[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 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4页。档案部门对灾难记忆的首要叙事途径即文本加工。自然灾难记忆方面,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同出版《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卷),下卷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人为战争灾难记忆方面,如中央档案馆公布出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系列专辑,在作为若干史实证据链一环的同时,也从抗战记忆视角成为激发公众民族认同的国家创伤记忆。内容叙事是档案部门以及相关历史研究人员的核心任务。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尺度出发,在不同的叙事语境下,灾难记忆有着相异的叙事策略和结构,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从政治叙事到生活叙事,不一而足。在此方面,档案部门拥有丰富的历史编纂经验。
结合当下媒体和技术发展,档案部门需重点关注空间化叙事、可视化叙事两大趋势。其一,空间化叙事。灾难记忆常以纪念展览、纪念场馆的形式出现。建造行为“强调了一种可理解性,‘被叙述'的时间与‘被建造'的空间之间既存在许多相似性,又相互影响”。(27)[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 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2~193页。档案展览因其生动形象、空间灵活等特点而备受青睐。通过展厅、展板或网页将时间进程转化为空间分布。“在这个空间(注:指回忆空间)里记忆被建构、被彰显、被习得。”(28)[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 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页。技术还实现了若干可能。如:2019年,南京大学ARMapper团队、“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共同开发了《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的AR故事地图》。其二,可视化叙事。参考“媒介的人性化趋势进化”(29)[美]保罗·莱文森:《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邬建中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页。观点,符合人类生理与心理适宜度的可视化方式成为优先选择。“我们的记忆已经不像在19世纪那样充满了故事和人物,而是充满了浮动的画面。”(30)[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载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 斌,王立君,锡 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115页。融图片、影像、图表、空间地理等的数字人文有望为档案部门的灾难记忆叙事开辟新天地。如在威尼斯档案馆的“威尼斯时光机”数字人文项目中,灾难记忆也是其重要内容。17世纪一场瘟疫导致威尼斯三分之一人口死亡,流行病学家就致力从大量死者档案信息研究流行病的爆发与传播。(31)[美]Abbott A.:《威尼斯时光机项目——机器学习如何重塑水城千年历史?》,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译,https://www.wxnmh.com/thread-1520446.htm,2017年8月20日。数字人文领域的灾难记忆叙事探索将极具张力和吸引力,这或将成为档案部门的新兴增长点。
(三)达成理解之旨:灾难记忆的共享责任
理解灾难记忆不仅在于它记忆什么,更在于为何如此记忆与遗忘,如何将“脱域”文本与现实世界重建关联,再次进入人的生活世界。这是一个意义发现、发掘、解释、传播、接受/再解释的再生产过程,包括个体生命、伦理、道德和民族精神等意义的复合体。灾难记忆的难点在于群体的认同冲突与灾难记忆的生产断裂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强烈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需求,另一方面是缺乏具有凝聚性的灾难共享记忆。信息时代网络空间的流动性对认同的冲击、对共同体边界的模糊,使得灾难记忆中的共享记忆愈加突出。
共享记忆意味一个群体围绕灾难形成、强化身份认同,消解身份冲突,弥合记忆创伤,打造记忆共同体。相关的共同体要素包括“过往的情感、艰难时刻的大团结以及可能的对共同敌人的敌意”(32)[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海 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塑造共享记忆的关键在于记忆框架、记忆渠道两大方面。档案部门如何让公众理解具有长久时空疏离感的灾难记忆,归根结底需要构建共通的理解框架和共享的价值观念。尘封的灾难记忆惟有获取与当下联通的意义,才有唤起的可能和必要。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要重视新的灾难史料的发现;从共享记忆的角度,要重视灾难史料的再发现。要着眼唤醒、激发、强化灾难记忆背后的关系联结、认同凝聚和情感体验,达到对灾难之“苦、痛、难”以及克服灾难后经验、成功、尊严等的共同认知、理解和体认。
灾难记忆的传播共享离不开媒体的作用。以“南京大屠杀”记忆为例,无论是“拉贝日记”还是受害者证词,“只有经过媒体再现、证言采集或纪念馆的收藏与展示,它们才有机会触及一般公众,进而变成‘共享记忆’”。(33)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页。人们首先是通过媒体视野来认识、反思灾难记忆。媒体中灾难记忆的显现频率、强度、关注度,直接体现了记忆的传承范围与效果。经由媒体传播,受众还有望转化为互众,成为共享网络的主动节点。档案部门需充分采用各种媒体传播手段、方式,不仅作灾难记忆的记录者,更成为灾难共享记忆的重要建构者。
(四)厘定理解之界:灾难记忆的伦理责任
对灾难记忆的立场与态度,体现出一种社会良知与责任。就档案部门而言,“责任与伦理并行不悖”(34)[美]Cox R.J.:“Archival ethics:the truth of the matter”,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o.7,2008.,其核心在于责任、良知、正义。如何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力量,保护保存灾难记忆?对于自然灾难,要重视汲取经验、防灾救灾减灾;对于人为灾难,尤其是扩张至人道主义灾难,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不可或缺。施加者需有承担的责任和反思的勇气,承认过错与罪恶,受害者亦当有表达、批评的权力。直面冲突、正视现实,而非回避矫饰、抹煞歪曲,方能达成真正谅解、理解、和解。如大屠杀、地震等幸存者,通过影像、口述等档案记忆形式浮现于世。这些少数、弱势、边缘群体虽不晓言说或无力言说,并不意味在宏大叙事中就可隐去,化入历史背后的阴影。“随着意义结构和评价模式的变化,以前不重要的东西在回顾的时候却可能变得重要了。”(35)[德]阿莱德·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载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 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灾难记忆要植根公众、面向公众、服务公众。这些记忆“微光”在何种情况下得以显现照亮,并永驻历史,有待档案部门进一步的探索。
普遍享有档案记忆的权利指向人类个体的尊严、权力和群体文化多样性。对于灾难记忆,谁担负有记忆或删除的话语权力?谁能代言受难者发声?谁决定告诉子孙后代何种过去?就如历史的史料不一,究竟编织何样历史?又取决于何种标准?这涉及到在一个强调记忆的时代,对记忆控制权力和记忆滥用风险的关切。一方面,关于灾难的记忆累积不绝;另一方面,灾难记忆的脆弱与复杂并存。关于灾难的记忆与反记忆、冲突性记忆始终存在于记忆场域。新传媒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基于不同身份、立场、视角,灾难记忆的个体包括亲历者、旁观者,如何记录、书写与再现各类创伤记忆,涉及隐私与道德,需遵循一定的伦理约束,避免不实歪曲、以讹传讹,导致灾难记忆的扭曲、变形。由证据和记忆视点出发,档案部门理当正本清源,廓清视听,切实担负记忆责任,坚守社会良知,维护社会正义。这既是一种外在社会要求,也应成为档案工作者的内在自觉。
总而言之,灾难在人类历史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衍生的灾难记忆如涟漪般回响古今未来。遗忘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灾难已让人类付出沉痛的代价,从理解视域出发,探寻其间的责任,不仅体现档案部门对灾难记忆所负的社会职责和伦理意义,更具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观意义。进而档案部门可通过灾难记忆的复兴和重组,达成对过去、当下的理解,以至对未来的改变。档案部门需要也一定能够担负起历史的责任与使命,这也有助于开启新的迈向理解之路的记忆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