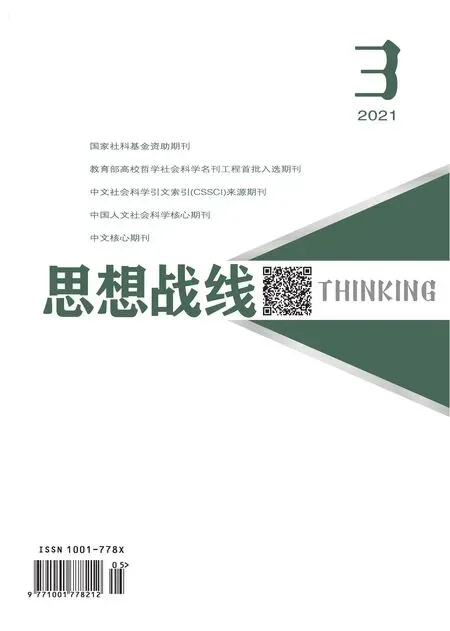铸炼社会之基、民众福祉学科理念下的知识生产
——经济民族学在云南大学的创建、传承与拓展
杜星梅,何 明
一、经济民族学研究的历史之基
如果把我们今天生存的社会称之为现代社会的话,那么,它最具本质性的特征,就是基于社会化的生产力这一全新的历史基础,把不同地区、民族的人类群体导进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即是“世界历史”的开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古老的中国是在19世纪以衰败的姿态跌落进这一世界潮流中的。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铺筑了最近三百年中国一切社会变化的全局性基础,它虽然也曾偶尔荡起过历史的浊流,但其最重要的贡献,一个是点燃了“实业救国”这一最普遍的社会热情;另一个则是把“社会之基、民众福祉”铸炼为20世纪上半叶整整一代学人至深的学术情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民族经济问题成为近代中国不同学科、不同背景学人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也正是在这一事实基础上,我们可以说,经济民族学研究在中国的起步甚早,整整一代不同学科学者的研究,拉开了中国经济民族学研究的历史序幕。
20世纪20年代,当陶孟和在北平开创社会调查部、社会调查所时,正是“社会之基、民众福祉”这一共同的学术信念,把来自不同学科的青年学子汇聚到一起:如汤象龙、梁方仲、千家驹、巫宝三、张培刚等,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由此而展开了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拓展历程。在这一批志向高远青年学子的共同努力下,社会调查部编辑出版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继之社会调查所也先后创办了《社会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等一批开创性的学术刊物。[注]经济所所史编写组:《九十年的奋进与荣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8页。这一重要学术研究机构的名称虽屡遭变易,但始终把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作为整个机构的研究重心。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聚焦于中国基层社会温饱与贫困突出问题;吴半农和千家驹则合作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严中平的《中国棉业之发展》,成就了中国实证史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倾情于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小农遭遇;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则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奠基之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已然确立起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并重的学术风格。1953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巫宝三为代理所长。曾在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的李文治、彭泽益、汪敬虞等皆入职该所。学术的传承,确立了社会与经济的理论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与分析和经济史研究三足鼎立的学术格局。[注]经济所所史编写组:《九十年的奋进与荣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8页。
“社会之基、民众福祉”这一共同的学术信念,把当今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术前辈,都推入了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如费孝通基于自己家乡调查所贡献的《江村经济》,展现了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外来强力支配下急剧变迁的动荡状态,至今仍展露着旺盛的学术活力与风采。也正是这一学术情怀,推动着他在1935年携妻王同惠进广西大瑶山开展对花篮瑶的调查。1934年,佤山班洪部落抵抗英军入侵所引发的中英滇缅未定界考察,推动了凌纯声、芮逸夫、陶云逵等对佤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等民族的调查。[注]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1~182页。基于长达三年的调查,芮逸夫为我们贡献了《拉祜族的经济生活》这一重要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成果。[注]陈庆德等:《经济人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杨成志数次组织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师生对广东北江瑶族和海南岛黎族、苗族的调查。[注]江应樑:《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页。当时就读于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江应樑,发表了《广东北江瑶人之生活》等一系列论文,他从1938年首次进入滇西芒市、遮放、勐卯、盏达等傣族土司区,调查傣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涉及土司制度、农业、商业、货币、手工业、耕地、佣工等广泛的经济内容。他不仅入巴布凉山半年之久,而且数度进入傣族居住的区域,以长达十余年的田野调查积累,为我们贡献了《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珠海大学1948年)、《摆夷的生活文化》(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和《摆夷的经济生活》(岭南大学1950年)等一系列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有任乃强对川藏地区藏、羌等民族的调查,[注]任乃强:《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页。马长寿两度入凉山,历一年之久而贡献的《凉山罗彝考察报告》等等。[注]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3页。
基于上述史实,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民族学并非是当今偶然落地的新生儿,对中国而言,经济民族学并不陌生,正是上述前辈学者的这一系列学术贡献,分别对虽已受到外力影响,但仍主要囿于旧有轨道运行的众多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常态,第一次给出的一个较为系统的全面勾画,拉开了中国经济民族学研究的帷幕。在“社会之基、民众福祉”这一学术信念的基石上,他们展露了各不相同却又为后人所景仰的学术风骨与人格魅力,培植起了中国经济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旨趣与趋向。
二、“魁阁时代”:中国经济民族学研究第一个高峰
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下西迁,给边城昆明带来了一个学术积淀与升华的空前历史机遇。1938年,随着西南联大落脚昆明,这个边隅之地成为了全国著名学者的汇聚之地。吴文藻此时也从燕京大学南下昆明创建云南大学的社会学学科,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青年学子随之跟进。如陶云逵、费孝通、林耀华等先后入职云南大学。云南大学也于1939年获洛克菲勒基金资助而创建“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因战事骚扰,该工作站于1940年迁至昆明郊区呈贡的魁星阁。在短短的七年中,该工作站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奉献了一批经典的研究成果,并以“魁阁时代”为名,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历程中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在吴文藻学术思想和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感召下,汇聚了十余名学者的这一学术共同体,在核心人物费孝通高效而富于创造性的组织运作中,工作站以“从实求知”为基点,在云南全境设立了12个田野调查点。正如费孝通坦言:“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注]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1~92页。这种通过微观的求实,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特征与性质整体认知的学术努力,彰显了微观基点与宏观视野的紧密结合。在这种发自内心情趣而又极为艰辛的学术探索中,费孝通奉献了《禄村农田》;张之毅奉献了《易村手工业》与《玉村农业和商业》后,又在白族聚居的大理马久邑写出了《榆村经济》;郑安伦在路南县完成《堡村商业》;李有义在路南县撒尼人聚居的尾则村完成《汉夷杂区经济》;史国衡在昆明中央电工厂完成《昆厂劳工》以及在个旧完成《个旧矿工》,安庆灡在玉溪大营完成《玉村之农业与手工业》;薛观涛在玉溪大村完成了《玉村农产之商品化》;田汝康在云南纺纱厂完成了《内地女工》后,继之深入滇西傣族聚居区,奉献了《摆夷的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魁阁学者的研究,涉及范围颇为广泛。诸如许烺光基于大理喜洲调查而奉献的《祖荫下》,胡庆钧的《云南呈贡二村基层地方权力结构》等。又如谷苞在呈贡的调查,就贡献了《化城城乡的经济传统》和《化城城乡的传统组织》两份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谷苞自1944年离昆赴兰州大学任教后,40余年终其一生聚焦于卓尼藏区的调查研究。有学者评价,这是魁阁成员继田汝康之后,第二次深入到不同民族的佛教社会所展开的最为细密的研究,“为我们保留了那个时代藏族土司社会最为丰满的政治和经济图景,同时也是第一次将费孝通所倡导的基于村落与世界市场之关系的经济人类学思想转变成边疆整体的政治经济关系研究”。[注]张亚辉:《土地制度与边政忧思:谷苞先生的卓尼经济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魁阁遗稿的整理中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魁阁学者所奉献的学术成果中,50%以上都聚焦于经济问题。即便在今日学科分类的基点上,我们也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在魁阁时代已然形成了一个品质极高的政治经济学流派。它也为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的研究奉献了最为深厚的学术底蕴。
比这一丰厚的学术底蕴更为重要的贡献,则在于魁阁成员以其身体力行给后学留下的深刻启示。
首先,这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赫然表明,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并非专属于经济学,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基点的切入以及不同方法的运用,对于经济问题研究的整体性理解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把这些研究冠以“经济民族学”之称的话,那么就意味着,经济民族学是以民族学为理论母体,来认识、理解和分析经济问题的。这就决定了经济民族学必须寻找新的理论工具,为自己建构起富有特色的基本理论体系;当然,这也决定了它的研究必须是以社区、村落为起点,但这些微观的个案研究,并不妨碍它拓展到族群、民族以及族际关系的基点,甚至可以说它必须得到这些宏观视野的支撑。它也可以拓展到民族国家的层面,探讨不同的民族国家,因自身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地位、方式和条件的差异,其经济的发展并不存在唯一榜样、唯一方向和唯一道路。如果说,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基质在于特定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那么,就必须从个人、社会、政治、自然等不同方面或要素所构成的生产力状态出发,进行富有成效的多样性选择。在某种角度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李斯特1841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民族)体系》,[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视为经济民族学在此层面展开研究的一个成功理论范本。
其次,当我们把魁阁时代学者称为中国民族学的政治经济学流派时,绝对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封闭的或狭隘的学派!费孝通曾坦言,魁阁“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而且在经常的讨论中,谁也不让一点儿,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注]潘乃谷,王铭铭:《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页。魁阁成员以他们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一个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拥有一个正常的、良好的富有魅力的学术空间和氛围,而其关键在于,充分开放的姿态。它不仅欢迎不同学科、不同观点和不同方法的加盟,而且它的研究范围也是充分开放的,可以是理论的,也可以是个案的或现实的、历史的,在研究的取向、聚焦的重点、理论的阐述等等方面,也是可以各有差异与特色的。有学者评论,魁阁成员的学术观点并非整齐划一,甚至与作为魁阁核心人物的费孝通的观点也并非没有龃龉之处。但这并未带来所谓的门户之见,也并未妨碍他们在一起进行共同的学术探索,并分享和交流不同的研究成果。如张之毅就格外强调村落内部的经济分化问题,田汝康从社会团结理论基点出发,更多关注休闲经济对社会维系的积极作用,而谷苞的卓尼藏区研究与费孝通、张之毅等人的边疆经济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取向。谷苞一直关注社会组织和经济变革之间的交错关系。可以说,在魁阁时代为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所做出的丰厚的学术积淀中,这是最为宝贵的贡献。云南大学的经济民族学研究,就是在魁阁学术精神的启示、感召与传承中起步的。
三、跨学科交叉合作: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在拓展中砥砺前行
20世纪50年代以后,数度的历史变化,曾导致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停顿。在此时期堪得一赞的,是1953年启动的民族识别这一“国家工程”。这一全面性民族调查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展现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生活的样貌,为经济民族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在此历史大背景中,魁阁政治经济学流派为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所做出的丰厚学术积淀,也只能借民族史、经济史等学科获得一席传承之地。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整个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导向的聚焦,推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经济问题的研究再度成为国人持续关注的热点。正是基于这一重大的转折,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学位制度的建立,前辈学者所铸炼起的“社会之基、民众福祉”这一学术情怀,再度点燃了20世纪80年代青年学子的探索热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魁阁时代所积淀下来的学术精神,为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1988年,执教于云南大学经济系的董孟雄,为新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呈献了一个专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变化”。[注]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07~338页。其基本的理论意义就是明确宣示,深切理解并澄清中国各少数民族多层次与不完整的经济结构,对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全面性把握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师从于江应樑的杨庭硕,作为云南大学第一批毕业的硕士,在1995年呈献了《相际经营原理》一书。他秉承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研究丰厚的学术积淀,以师承所获得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根柢,来剖析现代社会中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问题。[注]杨庭硕:《相际经营原理》,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567页。他聚焦于不同民族经济活动的跨文化背景、历史脉络和空间差异三大主题,以“相际”一词的使用,表达了如何去理解处于同一时空中不同民族的文化经济类型,以及处于同一经济过程中不同民族经济体系的理论意图。并提出了“民族文化生境”这一富于拓展性的概念。[注]参见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当今执教于吉首大学的杨庭硕,已然成为国内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他在此前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把生产力问题研究作为主要的理论聚焦点,所获得的一个重大拓展和升华。
高考入学云南大学经济系的一代学子,也从不同的角度开始了对民族经济问题的探索。云南大学经济系1978级的徐亚非、温宁军和杨先明,在1991年出版了《民族宗教经济透视》,[注]徐亚飞,温宁军,杨先明:《民族宗教经济透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作为同窗的陈庆德随即在1994年先后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开发概论》和《民族经济学》。[注]陈庆德:《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开发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陈庆德:《民族经济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彭泽益认为,《民族经济学》以“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基质”“民族经济成长的要素分析”“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实证与选择”三篇的写作结构,展示出三个研究特点:“第一,首次试图从基本理论框架上构造民族经济学的完整体系,并把经济人类学与发展经济学融为一体,企图实现新学科的突破。第二,全书贯穿历史与逻辑一致性的原则,力图为少数民族经济的历史演变同现实发展联为一体考察。第三,全书力图体现把基本理论分析同实践运用相结合的特点。在构造基本理论体系时,对现实发展的实践做了大量实证性研究。”[注]彭泽益:《序言》,载陈庆德《民族经济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提供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报告,也充分肯定了该研究在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上的多方面重大突破。各学术刊物相继刊出多篇书评。[注]何叔涛:《民族问题与经济发展兼评〈民族经济学〉》,《民族研究》1995第5期;徐敬君:《民族经济学在中国——兼评陈庆德新著〈民族经济学〉》,《经济问题探索》1995年第6期;修世华:《构建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尝试评〈民族经济学〉》,《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汪 戎:《民族差别和认同的经济学理解——评〈民族经济学〉》,《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高正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规范理论体系的探索〈民族经济学〉评介》,《开发研究》1996第2期;马传景:《磨剑十年,终成利器——评〈民族经济学〉》,《东岳论丛》1997年第1期。
同一时期就读于云南大学经济系的吕昭河,则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角度切入民族经济的研究,1988年在《民族研究》发表文章《云南省布朗山区生育状况的剖析》后,他相继发表了《人口现代化:一个历史过程的理论探讨》《超越经济人: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性质的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村寨生育行为与理性选择的分析》等一系列高质量论文,并出版了《制度变迁与人口发展》等代表性著作。[注]李光灿,吕昭河:《云南省布朗山区生育状况的剖析》,《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吕昭河:《人口现代化:一个历史过程的理论探讨》,《思想战线》1999年第4期;吕昭河:《超越经济人: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性质的探讨》,《思想战线》2003年第6期;吕昭河,余 泳,陈 瑛:《我国少数民族村寨生育行为与理性选择的分析》,《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吕昭河:《制度变迁与人口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云南大学一开始就意识到,学科建设必须将基础性的工作视为重心。随着民族学二级、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立,云南大学在1999年启动了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村寨调查这一对整个民族学学科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工作。21世纪初,云南大学开始陆续选取苗族、彝族、回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白族、独龙族、景颇族、基诺族、傣族、布朗族等不同民族村寨,创建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基地,并聘用当地村民进行日志记录,以文化主体的视角对自我村寨每天发生的事情进行叙述与评论。至2016年,已出版了10部连续记录时间都在一年以上的“村民日志”。[注]何 明:《文化持有者“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的研究,也由此获得了从结果的静态描述向对变迁过程进行持续性调查研究和较长时段的动态过程研究转换的基础。
在人类学学界,从某种角度上说,经济人类学似乎有某种“来路不正”的尴尬。“经济人类学”一词,是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兹把自己的一份个案研究《原始人的经济生活》,在1952年修订再版为《经济人类学:比较经济研究》时首次使用的。陈庆德一直认为,一项研究若要冠以“学”之称,必须进行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范畴的构建。当其《经济人类学》的修订版在2012年问世后,终于把经济人类学的分析范畴拓展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覆盖了经济全过程。完成了对经济人类学学科自身尴尬的一个回应。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民族经济学》的根基在于在经济学的话,那么,《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根基和范围则更为宽广。它把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引向了社会整体性分析的进路。经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不仅要分析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结构差异、不同文化模式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文化观念如何影响具体的经济利益,不同文化主导的价值体系怎样影响、培育和塑造不同的经济进程。《经济人类学》是以学理性分析作为对学科建设的追求,从一开始就避开国内该学科体制中关于是民族地区经济,还是少数民族经济等问题的争辩,而是以总体性的理论基点去解读同一经济进程中不同民族经济事实,分析经济事实与其他社会事实之间的关联,看到所有社会事实背后的经济性。在这一现实问题与运作层面,经济人类学更多聚焦的是,处于同一历史时空的不同民族的关系与位置,处于同一经济过程中不同民族的经济参与方式、参与地位,以及经济权益分配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警醒,《经济人类学》从初始就具备了对理论与现实的高度反思性。如今提出的经济民族学,展现出了对民族学学科理念的强调及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更强调的是民族学之根。
在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的砥砺前行中,同样具有深厚学术积淀的经济史学科,一直是一支重要的支撑力量。2001年,陈庆德基于经济史的学术训练,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查资料,完成了《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人类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一书,[注]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人类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云南少数民族近代以来社会经济中的诸多问题,如公有制与私有制等不同产权关系与制度的不同基点与局限、皇权制度的二重性与中国民族经济进程、劳动组织与社区组织等作了深入的理论阐述。更为重要的是,在云南大学的经济史学科队伍中,涌现了一批承继者及成果。[注]张锦鹏,苏常青:《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约束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林文勋,张锦鹏:《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陈征平:《经济一体化、民族主义与抗战时期西南近代工业的内敛化》,《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陈征平:《辛亥革命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形态及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陈征平:《西南边疆近代工业产权演化与民族经济融合》,《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正是秉承学理性思辨是学术研究之精髓的理念,云南大学的经济民族学团队在最近十余年的努力中,呈献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如郑宇在2007~2015年中,先后在《民族研究》发表了4篇重要论文,并且呈献了两本专著;[注]郑 宇:《哈尼族宗教组织与双重性社会结构——以箐口村“摩匹—咪谷”为例》,《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郑 宇:《箐口村哈尼族丧礼献祭礼物的象征性交换》《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郑 宇:《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结构转型与社会约束》,《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郑 宇:《社会变迁与生存理性:一位苗族妇女的个人生活史》,《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郑 宇:《箐口村哈尼族社会生活中的仪式与交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郑 宇,曾 静:《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坡龙乡坡龙街赫蒙族调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立足于传播学基点的孙信茹,关注互联网情境下新兴媒体运用对村寨生活空间的改变及所带来的经济异象,继《广告与民族文化产业》后,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文章;[注]孙信茹:《广告与民族文化产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孙信茹:《大众传媒影响下的普米村寨社会空间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孙信茹,王东林:《玩四驱:网络趣缘群体如何以“物”追忆——对一个迷你四驱车QQ群的民族志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1期;孙信茹,甘庆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孙信茹,王东林:《跨国流动中的社会交往与文化内涵——城市传播视角下的越南边民跨境生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罗康隆从云南大学博士毕业后,一直关注于生计与生态基础的问题,就这一方面的问题出版了十余部专著,并在《民族研究》《世界民族》等权威刊物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在“族群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等论题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注]如:《生态人类学理论探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草原游牧的生态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侗族生计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苗疆边墙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论人文环境变迁对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以西南地区为例》,《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侗族传统生计方式与生态安全的文化阐释》,《思想战线》2009年第2期;《对斯图尔德“跨文化整合”理论的再认识》,《世界民族》2010年第3期;《生计资源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以贵州黎平黄岗侗族社区为例》,《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等。张帆呈献了《现代性语境中的贫困与反贫困》;[注]张 帆:《现代性语境中的贫困与反贫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蒙爱军呈献了《水族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注]蒙爱军:《水族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张剑峰则在2016年和2020年,先后在《世界民族》发表了《从礼物到商品:新西兰婆纳穆玉的社会生命史》和《西方的本土化:新西兰毛利那塔胡人的现代部落》;[注]张剑峰:《从礼物到商品:新西兰婆纳穆玉的社会生命史》,《世界民族》2016年第3期;张剑峰:《西方的本土化:新西兰毛利那塔胡人的现代部落》,《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杜星梅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围绕独龙族的生计方式发表了系列论文;[注]杜星梅等:《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采集经济——来自独龙江峡谷的调查与分析》,《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杜星梅等:《独龙族捕鱼生计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杜星梅等:《20世纪独龙族山地狩猎生计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杜星梅:《独龙族传统农业劳作中的交换与互惠》,《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一直在云南大学攻读硕博士的此里品初,也分别于2014和2019年,相继在《民族研究》发表了《藏传佛教寺院的供养结构——云南德钦噶丹·养八景林寺的个案分析》《藏传佛教乡村寺院僧侣的长幼差序与生计差异——云南德钦噶丹·养八景林寺的个案分析》[注]陈庆德,此里品初:《藏传佛教寺院的供养结构——云南德钦噶丹·养八景林寺的个案分析》,《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此里品初等:《藏传佛教乡村寺院僧侣的长幼差序与生计差异——云南德钦噶丹·养八景林寺的个案分析》,《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等等。
该学术团队继2014年出版《民族文化产业论纲》后,[注]陈庆德,郑 宇等:《民族文化产业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又在2019年以先前的《经济人类学》为基础,将其修改更名为《经济民族学》出版。[注]陈庆德,杜星梅等:《经济民族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这既表达了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团队对学科理论理解和问题意识的深化,也充分表达了为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提供多学科视野的学术志向。简略而言,经济民族学的理论重心或研究聚焦,在于经济过程的文化解释与文化事项的经济分析。它迫切地需要生态的、文化的、历史的等多维度的参与;它的学术旨趣在于追求研究成果具有启发性和富于讨论性;它充分认识到,任何理论、任何学科都是在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乃至理论质疑中获得确立的。云南大学的经济民族学,一直是以其开放性来获得拓展与活力的。基于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云南大学的经济民族学研究能够为人们呈现更多不同观点与方法的经济民族学版本,也期待着更多以“社会之基、民众福祉”为学术理念的青年学子加入到这一团队中来,合力构建一个富于魅力的学术空间和氛围。
四、作为铸炼“社会之基、民众福祉”的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
20世纪30年代末,吴文藻、费孝通等先贤在云南大学创建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时营造出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学者们的研究议题丰富多样,举凡社会生活各领域几乎都有所涉及。然而,在学术带头人费孝通的示范下,铸炼“社会之基、民众福祉”成为“魁阁”学术共同体的理念和追求,经济生活成为学者们聚焦的领域,举凡传统农村的种植业、手工业、贸易各业,新兴的纺织、矿业等现代工业,少数民族经济、边疆经济、族际经济交往等均被列为研究议题,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犹如火山喷发式地涌现,不仅成果多、领域划分细、研究布局系统,且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成果,译成英文向国际学界推介。费孝通等“魁阁”学者们在云南大学如此集中、密集并极富创造性和特色化的社会经济生活调查研究,开启了中国学术界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社会科学的理念和方法研究经济生活的先河,奠定了可以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经济人类学或经济民族学的知识生产“范式”。
“魁阁时代”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戛然而止,但却在云南大学树立起一座无形的学术丰碑,引导着后来者的学术研究方向和道路。在之后的30年时间里,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学人们虽遭遇学科波折,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却并未中断,他们仍在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背景和政治生态条件下艰难前行。
改革开放的推进,逐渐复活了奄奄一息的学术传统,而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为经济民族学的恢复与重建创造了机遇、提供了动力。作为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及其人才培养获得了学科制度的支持和学术资源的支撑。学术带头人陈庆德受业于经济史诸位大家,并长期熟读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推出具有原创性的系列理论论著,并指导学生完成了一批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研究成果,形成特征鲜明的经济民族学云大学派,云南大学再次成为中国经济人类学和经济民族学研究重镇。
回顾与反思云南大学经济民族学的形成与拓展历程,铸炼“社会之基、民众福祉”为其孜孜探索的目标和方向,面向不同学科、不同理论取向、不同学术范式开放的包容性、多元化路径,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创新源泉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