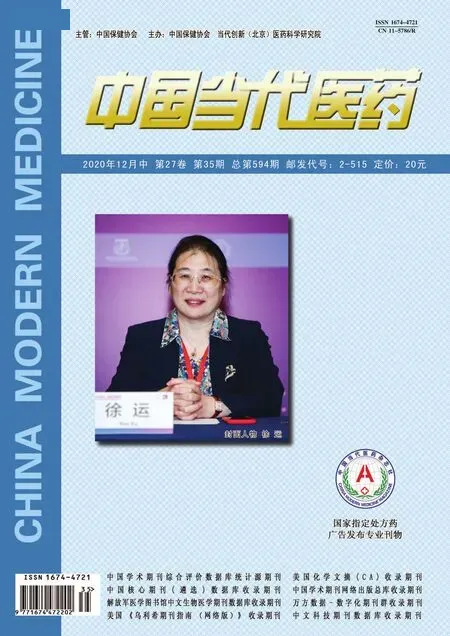阿帕替尼治疗恶性肿瘤致血压升高的危险因素分析
何 苗 曹佐锋 黄 莉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江西赣州 341000
恶性肿瘤在临床中较为常见,其致死率较高,对患者健康与安全的威胁极大[1-2]。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呈现出明显增长趋势。近年来,临床上逐渐将具有抗血管生长功效的抗肿瘤药物应用于恶性肿瘤的治疗中。阿帕替尼即为目前治疗恶性肿瘤较为常用的一种抗肿瘤药物,该药物在多种恶性肿瘤疾病治疗中的效果均得到了临床证实,这也使得其应用范围不断增大[3-5]。然而,该药物治疗期间还可能会引发多种不良反应,如高血压等。目前,临床中对于阿帕替尼治疗恶性肿瘤所致继发性高血压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就影响阿帕替尼治疗恶性肿瘤所致继发性高血压产生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后续临床治疗恶性肿瘤提供有效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18年1月~2019年12月收治的240例恶性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120例。观察组中,男68例,女52例;年龄32~77岁,平均(55.9±8.0)岁;肿瘤类型:非小细胞肺癌30例,食管癌28例,乳腺癌20例,直肠癌18例,胃癌16例,其他8例;病理类型:鳞癌42例,腺癌44例,浸润性导管癌16例,肝细胞癌12例,其他6例。对照组中,男70例,女50例;年龄34~75岁,平均(56.3±8.2)岁;肿瘤类型:非小细胞肺癌30例,食管癌25例,乳腺癌24例,直肠癌18例,胃癌16例,其他7例;病理类型:鳞癌45例,腺癌42例,浸润性导管癌15例,肝细胞癌13例,其他5例。本研究经相关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患者均经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②患者均知晓本次研究内容,经过思考后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③既往均无原发性高血压病史;④患者均意识清醒,有正常认知功能与理解沟通能力,可配合研究;⑤患者均对研究药物耐受。
1.2.2 排除标准 ①合并精神疾病、沟通障碍或认知障碍不能配合研究者;②合并原发性高血压史者;③药物禁忌证或过敏史者;④不愿参与本研究或中途退出研究者;⑤患者均对研究药物耐受。
1.3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放化疗治疗,根据患者肿瘤类型明确化疗方案,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采用长春瑞滨(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批号:20170923)+顺铂(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号:20171209)治疗;食管癌患者采用顺铂+氟尿嘧啶(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批号:10170822)治疗;乳腺癌患者采用环磷酰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20161212)+甲氨蝶呤(辅仁药业集团熙德隆肿瘤药品有限公司,批号:20161214)+氟尿嘧啶治疗;直肠癌以铂类联合氟尿嘧啶治疗;胃癌患者采用多帕菲(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批号:20140912)+顺铂+氟尿嘧啶治疗;均未服用阿帕替尼治疗。观察组患者则均接受阿帕替尼(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20140301)治疗,根据患者肿瘤类型明确用药剂量。胃癌患者每日给药850 mg,1次/d;肺癌、肝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每天给药1次,每次750 mg;乳腺癌、食管癌、直肠癌患者每天给药1次,每次500 mg,用药期间根据患者情况进行剂量调整,若患者出现明显不良反应,则可将剂量调整为500 mg/d 或250 mg/d;采用阿帕替尼治疗期间患者均不行放化疗治疗。分析高血压发生情况及高血压的影响因素。
1.4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统计比较两组的高血压发生情况;分析阿帕替尼致高血压的单因素,包括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年龄、吸烟史、用药剂量、性别、放疗史、化疗史、手术史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式分析阿帕替尼致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同时以单因素分析中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为自变量,行多因素Log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高血压发生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共42例出现高血压现象,发生率为35.0%;对照组12例患者出现高血压,发生率为10%。观察组的高血压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χ2=21.51,P=0.000);两组中继发高血压患者均未出现高血压危象,患者均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进行降压治疗,且患者血压情况均得到控制。
2.2 阿帕替尼致高血压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年龄、吸烟史、BMI、ECOG评分、用药剂量等因素和阿帕替尼所致继发性高血压发生有关(P<0.05);而患者性别、放疗史、化疗史、手术史等不会对患者治疗期间高血压的发生造成较大影响(P>0.05)(表1)。
2.3 阿帕替尼致高血压的多因素Logistic 分析
以单因素因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为自变量开展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为阿帕替尼治疗恶性肿瘤继发性高血压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表2)。

表1 阿帕替尼致高血压的单因素分析

表2 阿帕替尼致高血压的多因素Logistic 分析
3 讨论
恶性肿瘤俗称癌症,主要是指因控制细胞生长增殖机制失常而引发的疾病,为临床上发生率较高的一类疾病[6-7]。癌细胞具有无限制、无止境增生的特点,随着病情的发展可促使患者体内营养物质逐渐被消耗;同时癌细胞还可释放出多种毒素,从而引发一系列症状。另外,癌细胞还可发生转移,在患者全身各处生长繁殖,进而极易导致患者出现消瘦、乏力、食欲下降、贫血、严重脏器功能障碍等症状,甚至可导致患者死亡,严重威胁患者健康与安全[8-10]。流行病学显示,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及死亡率均呈现出明显升高趋势[6]。我国2015年新增恶性肿瘤人数高达429 万例,其发生率占据了全球恶性新增人数的22%左右;死亡人数高达28 万人,占全球的27%左右[11-12]。恶性肿瘤具有细胞分化及增殖异常、生长失控、浸润性及转移性等生物学特征,其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过程,与遗传、吸烟、感染、环境污染、不合理饮食、职业暴露等众多因素均有关联[13]。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及人们寿命的延长,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也呈现出明显升高趋势,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重要疾病,并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致死因素。
1971年,Folkman 教授提出了新的理论,即肿瘤生长需要新生血管生长,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有了新思路与方向。阻断新血管生成或破坏已有血管,进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转移的目的成为临床上治疗恶性肿瘤的关键[14]。现阶段,临床上治疗恶性肿瘤的抗血管生成药物较多,但因抗肿瘤血管较为特殊,在抑制肿瘤血管的同时还可能会对正常血管的生长造成影响,从而引发蛋白尿、出血、心血管并发症等不良后果[9]。因此,合理选择抗肿瘤药物非常必要[15]。阿帕替尼也叫甲磺酸阿帕替尼,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口服小分子VEGFR-2 酪氨酸激酶抑制,能够选择性地竞争细胞内VEGFR-2 的ATP 结合位点,同时将c-Src 基因、c-Kit、Ret 基因作为靶点,从而将下游信号转导情况阻断,进而可发挥较好的抗肿瘤组织血管新生的作用[16-17]。目前,该药物在结直肠癌、乳腺癌、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患者治疗中的作用均得到了证实,故逐渐在临床中得到推广与使用。然而,因受药物抗血管作用的影响,治疗期间还可能会引发相应的不良反应,如出血、蛋白尿、高血压等。目前,临床中尚未明确阿帕替尼致高血压的具体发生机制,通常认为与下述几点有关。①外周血管阻力增加:阿帕替尼可促使一氧化氮的合成及分泌量减少,从而引发血管收缩;同时血管内皮凋亡、退化还可能会导致毛细血管数量及血管密度下降,促使外周血管压力增加。同时该药物还可对VEGF 通路产生抑制作用,促使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血管狭窄等现象发生,进而引发血压升高。②组织损伤:阿帕替尼用药后还可能与正常组织器官内的相应受体进行结合,从而对正常组织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引发高血压等不良反应[18-19]。③影响信号通路:用药后阿帕替尼能够与VEGFR-2结合,并可激活部分c-Src 基因,从而促使患者血压升高。虽然高血压已经被列为心脏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20],但是对于阿帕替尼治疗恶性肿瘤致高血压危险因素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研究就收治的120例患者进行了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年龄、吸烟史、BMI、ECOG 评分、用药剂量等因素和阿帕替尼所致继发性高血压发生有关(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是导致阿帕替尼所致继发性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因此,临床中在予以恶性肿瘤患者阿帕替尼治疗期间还需加强对老年患者及高龄患者血压监测的重视,同时需严密监测患者临床症状,一旦有血压升高现象发生需及时通过调整用药剂量等方式进行干预。
综上所述,年龄是导致阿帕替尼治疗恶性肿瘤致血压升高的危险因素,临床上需要予以充分重视;但由于本次研究中所选取的样本量较少,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临床上仍需展开更大样本量的研究。
——评《卵巢恶性肿瘤诊疗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