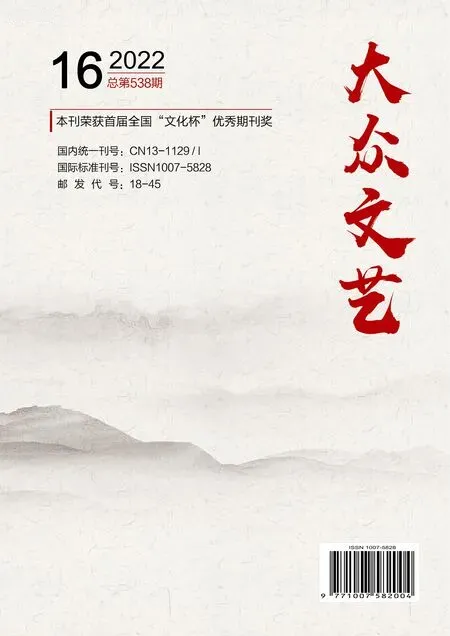论雅克·朗西埃“歧义”概念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 361005)
一、政治哲学批判
(一)重新厘定治安与政治
探究朗西埃对政治哲学的批判,有必要先厘清其对治安与政治这一对概念的重构。朗西埃笔下的治安摆脱了其传统意义,被定义为对社会个体的感性存在进行划分的原则,是一种分配体系。治安对身体秩序如行动方式、说话方式等进行界定,获得治安认可的个体成为社会的可参与者,不被认可的则被当成噪音,成为无分者。朗西埃对治安的分析竭力保持中立态度,他谈到,“治安亦有好坏之分”[1],但从根本上看,治安仍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是为阻拦无分者而设的门槛。
在重新定义政治时,朗西埃指出,“我提议将政治这个名词,保留给与治安对立的一种极为特定的活动,亦即,借由一个在定义上不存在的假设,也就是无分者之分,来打破界定组成部分与其份额或无分者的感知配置。”[1]从上述内容可知,朗西埃分析政治的切入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司法结构或政府治理层面,而是直击了政治本身的构成性基础——“错误”。此处错误指人民仅在名义上拥有自由。基于这一不平等的基础,朗西埃指出,政治注定走向对治安的扰乱或打破,从而为更多的无分者争取权利。
简言之,朗西埃笔下的治安与政治分属两条异质逻辑。治安指向封闭的逻辑,也是哲学对政治进行化约时所暗含的逻辑。政治则指向开放、平等逻辑,竭力打破原有秩序,使无分者得以参与。
(二)批判哲学对政治的化约
朗西埃对政治哲学持批判态度,常将其与“吊诡”“丑闻”相关联。在《歧义:政治与哲学》中,朗西埃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哲学实则是通过“‘取代’政治来实现政治”[1],并分析了“元政治”、“类政治”和“后设政治”对政治的化约。
“元政治”重视“规范”与“共同体法律”的作用,以柏拉图政治思想为基础。在“元政治”这里,无分者的参与问题通过《理想国》著名的金属谎言得以解决。金属谎言认为神在造人时为其灵魂添加了不同的金属,从而说服城邦中的人要安于本分、服从政治安排。朗西埃指出,“元政治”实则是“元治安”,其预设了共同体时间与空间的完全饱和,政治于此消失。由此可见,“元政治”正是通过扼杀精神之自由、向上的维度,来维持既有的治安秩序。
“类政治”是亚里士多德试图缓解两种异质逻辑冲突的政治哲学。两种异质逻辑之一是城邦应由最具德性者也就是哲学王来进行统治,其二是人生而平等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中,平民始终处于分散状态,无法真正参与政治生活,只能将权力运作留给贵族或政治寡头。由此,“无分者之分”的问题也得到了所谓的解决。
在分析“后设政治”时,朗西埃将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对其而言唯有假象才能成为其标记的真理”[1]。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显示假象的真相,由此政治成为了真理的谎言,社会诸多问题被简单地化约为政治的非真理,最终导致了政治的消失。
在朗西埃看来,无论是“元政治”企图用治安收编政治,“类政治”尝试调节两种异质矛盾,还是“后设政治”对假象、错误的暴露,都是政治哲学对政治的化约。不切实考虑无分者问题,任何试图通过哲学或精英来实现共同体的开明治理只能是充满幻想的“田园诗”。
二、朗西埃的“歧义”概念
(一)“歧见”/“歧感”①
朗西埃笔下的“歧义”有着丰富的政治、美学内涵,也是沟通政治与美学的关键概念。理解“歧义”首先可从其对立面共识出发。朗西埃曾谈到,“所谓政治的田园诗……通常被冠上共识性民主之名”[1]。简言之,共识预设了政治的饱和,取消了无分者的参与问题,其根本逻辑与治安相同。“歧义”与共识不同。“歧义”(mésentente)是不同的(més)理解(entente)[1],不但是对不平等的异议,还是对不可感知性的异议。“歧义”往往体现为异质声音的相遇或“感知不到的元素”对共识的挑战,从而打破既有的感性划分形式。
刘易斯曾以柴纳·米耶维的《城与城》来理解朗西埃的“歧义”概念。在《城与城》中,分属两座城市中的居民从小被教育要拒绝感知对方的存在。如刘易斯所言,“贝斯厄尔和厄尔科马并不是被地理距离或物理屏障分隔开的,而是被一种特殊的感官划分开的,这种感官决定了什么是可以感知的,什么是不能感知的。”[2]小说中这种严格的划分所隐含的即是治安逻辑,而侦探对于这一秘密的破解即是“歧义”之中两种异质声音逐渐展现的过程。
考察朗西埃的“歧义”还可以对照理查德·罗蒂的“反讽”概念。罗蒂的“反讽”与常识相对,表现为“拿新词汇去对抗旧语汇”[3],是对哲学、语言的持续质疑。朗西埃的“歧义”指向不同理解之间的差异,意在批判共同体中虚假的同一性。正是由于异质声音的存在,“歧义”才得以产生,从而推动感性分配的重新划分,使政治或艺术中的无分者得以进入。
“歧见”是政治产生的场所,政治始于异质声音对既有秩序的打破。如法国思想家巴隆舍对阿文庭山上罗马平民分裂故事的重写。在重写故事时,巴隆舍将重心放在了元老院议员与平民的冲突上,元老们视平民的发声为“牛哞声”,而平民则搭起了西西亚风格的帐篷,进行诅咒和崇拜仪式。如朗西埃所言,“他们建立起了另外一套秩序、另外一种感知的分配。”[1]这个过程就是“歧见”产生的过程,当被划分为无分者行列的平民勇敢僭越既有秩序时,“歧见”就激发了政治的产生。
美学中也存有“歧义”,通常称之为“歧感”,是指对“感性分配的美感变革”[4]。理解“歧感”可从朗西埃对艺术体制的探讨出发。通过梳理艺术史,朗西埃总结了三种艺术体制,包括“图像的伦理体制”“艺术的再现体制”和“艺术的美学体制”。其指出,在前两种艺术体制中治安与再现逻辑压倒了平等逻辑,而“艺术的美学体制”则从前两种体制中制造了裂缝,为艺术体制打开了平等、自由等美学维度。在“艺术的美学体制”中,“歧感”的展现使艺术体制得以革新,传统的艺术判断标准如伦理、再现技巧等被替换,许多过去被排挤的艺术形象获得了认可。
(二)沟通政治与美学的桥梁
将政治与美学进行关联的尝试早已有之。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就对艺术调节异质力量的能力给予了肯定,他谈到艺术应当可以传达、协调“最有教养的部分的理念与较粗野的部分”[5]。在《审美教育书简》里,席勒也谈到了艺术、自由与政治的关系,认为“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6]。
朗西埃的“歧义”概念沟通了政治与美学。以下从两方面进行阐释:一是政治的发生以感性分配即广义的美学为基础。朗西埃谈到,工人们如若要推翻划分各种层级的模式,就不能依靠现有的能力和思考模式,因为这种能力只能让他们从属其中。只有更新感性分配模式,引入“歧义”,原本不被认可,无法被听见的声音才能出现,工人革命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二是美学潜藏着丰富的政治能量——平等。在“歧义”的基础上,一些原本被排除在外的声音得以展现。在分析法国电影《亚历山大之墓》时,朗西埃就挖掘出了电影美学所蕴含的政治力量:当影像记录下路过的王室成员时,路边为其让路的普通民众同样也被记录了下来。在影像之中,“那些并不拥有同等地位的人,可以拥有同样的影像”[4]。虽然这并不能使他们直接平等,但对于记录下来的影像而言,大众已经和王室成员共享了某些东西。
沟通政治与美学,并非将两者进行简单的关联。正如朗西埃所言,那些强调审美艺术实现其政治许诺的人们注定要陷入伤感。美学政治功能的实现,是以影响既有可感物的分配为基础的,而不是直接推动现实中各种形式的政治革命。
三、“歧义”的意义
“歧义”蕴含着平等的逻辑,指向开放、自由的维度。朗西埃曾在访谈中讲述其与老师阿尔都塞的分歧,认为俩人分野的根源在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7]。在朗西埃看来,阿尔都塞否定了工人的实际能力,认为工人需要思想家带领才能走出被压迫的状态。这其实隐含了一条通过劳动分工来划分社会秩序的逻辑。朗西埃则认为工人本质上与思想家无不同,解放的关键在于激发人民对于自身可以开辟出新世界的能力的肯定。
“歧义”肯定了个体的向上能力,与康德谈论“何为启蒙”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康德将启蒙界定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呼吁个体要敢于公开运用自己理性,其实就暗含了一条人人都可以走向成熟状态的平等逻辑。朗西埃的“歧义”承认不同的感知之间的差异,认为每一种不被认可的异质声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有能力展现自身。由此可见“歧义”的平等、自由、开放意义。
“歧义”具有美学力量。在“歧义”的基础上,“异托邦”才能发生。朗西埃笔下的“异托邦”指对“作为位置、身份、能力分配之重构效果的他者”[8]的想象。这种想象并非传统的伦理想象,而是一种美学的想象。这种美学的想象将“习惯看法”如关注等级、权力等搁置一边,转而关注“重构效果的他者”。在重构过程中,美学的自由、平等力量才得以显现。
当然,朗西埃“歧义”概念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政治始于无分者的参与,对既有秩序的打断会带来更新,但也存有破坏。将美学与政治过度关联是否会带来感性的无序,甚至陷入乌托邦。朗西埃的思想主张具有多大的现实实践性,能有多远的发展,还需交与时间验证。
注释:
①法语mésentente一词本意为“不和,纷争,误解”。此处采用学者蒋洪生观点,谈论政治时译为“歧见”,美学则译为“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