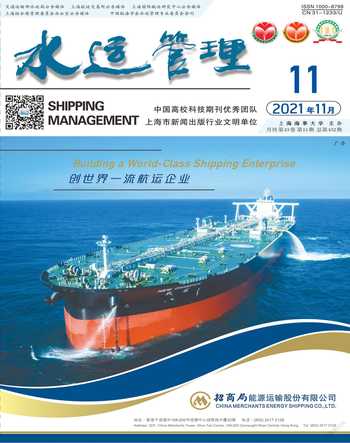船舶所有人与船舶经营人作为海事行政处罚对象时的认定条件
王洪兴
1问题的提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局作出的行政判决[(2019)鲁行终2060号],法院认定“苏兴隆货)×××”轮超过核定航区航行,并在黄海海域发生自沉事故,青岛海事局作为该海域海事管理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26条的相关规定,有权对‘苏兴隆货×××”轮的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作出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法院认为,即使船舶挂靠关系真实存在,青岛海事局对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记载的船舶所有人作出行政处罚,亦不违反前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案中,人民法院肯定了海事局有权对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记载的船舶所有人作出行政处罚。在实践中,海事管理机构也有权对船舶经营人作出行政处罚。通常在船舶所有人与船舶经营人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海事管理机构可以顺利确定海事行政处罚的对象;但当船舶所有人与船舶经营人不一致时,不同海事管理机构对同一艘船舶的同一类违法行为,可能处罚船舶所有人,也可能处罚船舶经营人。那么,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处罚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时,只有在法理上或法律依据上对如何选择海事行政处罚对象达成共识,才能在实践中达成一致。
2海事行政處罚对象认定的法理分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通航水域从事航行、停泊和作业以及与内河交通安全有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2条规定: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违反内河海事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实施海事行政处罚,应当遵守《行政处罚法》《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根据上述法规规定,我国内河水域海事行政管理是建立在“行为”基础上的,着重于对“行为”的管理。海事管理机构对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行为人因“违法行为”而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这事实上符合“对物行政行为”的概念。所谓对物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职权,对非属行政主体自有、而且可以作为物法上财产进行支配的物的各项权能进行规制,以产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对物行政行为旨在通过确定物的公法性质,达到产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目的,调整的不是个人的权利义务,而是物的法律状态,以物为受领对象,至于其所有权人是谁,则在所不问。“对物行政行为”源于状态责任的提出。违反法定义务的责任划分为行为责任(即因行为产生的责任)和状态责任(即因物之状态产生的责任),其中:当行为责任(船舶未按照规定倒车、调头、追越)不具有补正可能时,更多的是采取罚款方式进行处罚;而当状态责任不具有补正可能时,更多的是采取强制清除、强制卸载等方式将违法行为消灭。
对物实施海事行政处罚面临两种困境:(1)来自行政效率的挑战。考虑到水上活动的特殊性,海事管理机构如果要查明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将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且由于海事管理机构并不享有对人的控制权,将导致大量的案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处理。这不仅不利于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而且不利于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不符合依法行政的高效便民的要求。(2)不符合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要求。《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63条、第64条都赋予海事管理机构可以对船舶、浮动设施予以没收的处罚权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64条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但是,很多时候违法的船舶、浮动设施不属于行为人私人所有,海事管理机构依据“对物行政行为”理论的要求对不属于行为人所有的船舶、浮动设施处以没收的行政处罚,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为解决或避开上述困境,在实践中也可以适用“对物行政行为”。如在确定行为人且行为人适于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可以对行为人进行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等诸多海事法规规定了可以对船舶经营人进行处罚,因为船舶的很多违法行为是在船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对船舶经营人进行处罚具有合理性。
当“对物行政行为”确实有无法解决或避开的困境,处罚船舶所有人则成了必然的选择,这是基于“所有权人的法定义务”考虑的。在合法取得所有权时,这种义务是原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0条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基于此,海事管理机构对船舶所有人进行行政处罚也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3处罚对象的认定条件
基于“对物行政行为”和“所有权人的法定义务”的理论分析,选择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作为处罚对象时必须厘清以下4种情形:
情形一:法律明确规定可以处罚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2020修正)第55条第1款规定:船舶进出内河港口,未按照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舶进出港信息的,对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经营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情形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处罚对象,但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规定了可以处罚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如《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81条规定:船舶在内河航行、停泊或者作业,不遵守航行、避让和信号显示规则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海事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此明确处罚对象为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
情形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处罚对象,上级部门也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处罚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63条规定:应当报废的船舶、浮动设施在内河航行或者作业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停航或者停止作业,并对船舶、浮动设施予以没收。
情形四:法律明确规定了处罚对象,但涉及到船舶,上级部门明确规定处罚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43条第2款规定:在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内采砂,损害航道通航条件的,由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扣押或者没收非法采砂船舶,并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海事管理机构在处罚时,建议分4种情形选择处罚对象。
(1)情形一。建议优先处罚船舶所有人,但如果处罚船舶经营人更为合适时,则处罚船舶经营人。比如,某轮的船舶所有权证书中的所有人有1个公司、3个自然人,如果对其船舶所有人进行处罚,则必须对上述四方共同进行处罚,如此操作将会十分麻烦且面临执法文书难以送达的困境;但该船只有一个船舶经营人,针对该船未按照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舶进出港信息的违法行为,则可对该船船舶经营人实施处罚。
(2)情形二。选择处罚对象的标准同情形一。《海事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针对内河的处罚对象表述是“船舶经营人或船舶所有人”。海事管理机构在能确定船舶经营人的情况下,尽量对船舶经营人进行处罚。
(3)情形三。优先处罚船舶所有人,但对船舶、浮动设施予以没收除外,没收处罚只能针对船舶登记所有人或实际所有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武汉市水务局作出的行政判决[(2016)鄂01行终593号],认定:被上诉人武汉市水务局在执法过程中,通过查询发现“黄冈058”未进行船舶登记,遂以涉案该船舶实际负责人周某作为行政相对人,对其未经许可于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11日期间,在长江水域武汉段达8次之多的非法采砂行为,作出没收非法采砂船舶的行政处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该案中法院認为对船舶未进行登记的违法行为,可以以实际负责人作为处罚对象。如果有证据证明该船舶已经进行了买卖,且实际进行了交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买卖双方虽没有进行登记,但不影响实际所有人对船舶所享有的所有权利。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处罚申诉行政裁定书[( 2014)行监字第4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5条之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涉案船舶在被查扣时,处于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叶某的实际控制之下。该船舶登记所有人陈某在答辩状和书面证明中均予确认,涉案船舶已于2009年6月20日卖给叶某,双方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船舶已经交付使用。在无相反证据证明该船舶实际所有人为他人的情况下,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海警某支队在作出行政处罚前,未依照法定程序向叶某告知其权利,也未向其送达处罚决定书,属于违反法定程序。
(4)情形四。优先处罚船舶经营人,但如果该船舶的违法行为不是船舶经营人实施的且能确认行为人的,处罚行为人;如果不能确认行为人的则处罚船舶所有人,但没收船舶除外,没收船舶的处罚只能针对船舶所有人。
海事管理机构在处罚船舶经营人时,如果有光船租赁证书的,则处罚光船承租人。由于新版船舶国籍证书已经不记载船舶经营人信息,那么判断船舶经营人的方法是根据船舶的营运证,海事管理机构以船舶营运证上记载的船舶经营人为处罚对象。海事管理机构处罚的船舶所有人,一般应当是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记载的船舶所有人,但船舶的实际所有人,以及虽没有进行登记但签订了船舶买卖协议且船舶实际进行了交付的买船人,也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处罚对象。
4结语
海事行政处罚对象的认定是实施海事行政处罚不可或缺的前提,海事管理机构在认定选择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作为海事行政处罚对象时,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形,按照规定选择处罚的对象。同时,海事管理机构还要考虑船舶挂靠、买卖、实际占有对海事行政处罚对象认定选择的影响。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虽买卖、实际占有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海事管理机构在无相反证据证明船舶实际所有人为他人的情况下,应当对船舶实际所有人实施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