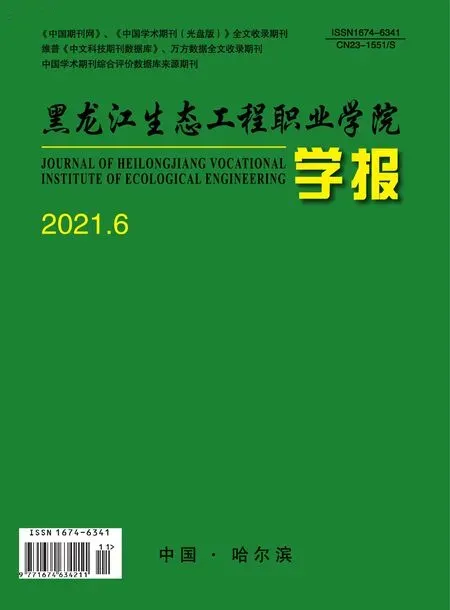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在地化”发展困境及对策
杨明伟 王绪尧
(沈阳化工大学 人文与艺术学院 社会工作系,辽宁 沈阳 110142)
2020年11月3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指出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坚持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社会工作开始更多涉足乡村振兴领域。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深入,社会工作下乡所面临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相较于以契约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法律制度支配着人们的活动,社会工作服务可以有章可循地开展;而中国的乡土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血缘社会又是建立在“长老统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差序格局[2],这就注定了中国乡土社会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对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产生了很大的阻碍。
1988年,中国社会工作正式恢复重建后,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一直立足于“本土化”建设,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方法糅进中国本土社会建设,在构建本土化社会工作专业的同时,协助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努力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在进行“本土化”理论构建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着“在地化”的实践探索。沈阳市利州公益机构在关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主导的“二区一县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项目”荣获了第三届“辽宁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工作“在地化”的发展。
“在地化”的发展为社会工作融入中国乡土社会提供了一条便捷有效的路径,使社会工作能够从深层剖析现代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开展乡村振兴服务工作。
1 社会工作“在地化”的内涵
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在不断“本土化”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着“在地化”。张乐认为,“在地化”是较小范围内的社会工作在地方上“落地生根”的过程,具有“扎根倾向”与“落地特征”[3]。高芙蓉指出,“在地化”是社会工作发展强势的中心区域向弱势的边缘区域扩散社会工作理念、价值观和专业模式,结合本土社会实际,形成可以指导地方实践的本地化特色理论体系的过程[4]。史铁尔认为,“在地化”是一种人才、产品或服务的应用,能够被某些特定文化或语言区域的人接受并长期发展下去[5]。何燕兰从在地资源的利用中找到了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6]。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末,东北地区合计净流出人口33.1万人。[7]其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失现象更为严重,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其农村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愈发艰难。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乡村因人口老龄化、空心化等问题逐渐呈现出“原子化”的状态,村民、村委会、利益集体、当地民间组织之间联系愈发松散,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每个农村都有其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属地性”,即当地特有的组织架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利益组成及分配等。而社会工作“在地化”发展应同时具有“组织性”和“属地性”两个特点。
综上,本文将社会工作“在地化”定义为:专业社会工作运用“在地陪伴”的行为逻辑[8],利用在地资源(包括项目实施地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培养在地人才(包括社会工作人才或具有凝聚力的组织人才),专业社会工作者与在地人才在为本地村民和基层政府组织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将专业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进行“属地化”,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探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工作实践路径。
2 社会工作“在地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2.1 行政化与专业化的两难选择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行政化” 与“专业化”推动了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岗位开发、社工机构建设、服务领域和效益等方面[9]的发展。但在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行政力量却成为其发展主导力量[10]。行政性力量的过多干预(多指政府购买服务)使大多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处于弱势地位,不仅要接受政府的监管、考核,还要接受政府下派的行政性任务,导致社工机构在政府部门的行政化工作和专业化服务之间进行着两难选择。即便开展服务,也体现不出社工服务的专业性,服务效果大打折扣。
2.2 无限管控与有限权责冲突
社会工作机构大多在本地民政部门注册,接受其监管。社工机构在接受政府购买服务后,监管权力大都落在民政部门手中。这使得社工机构不但要完成项目合同中所规定的责任义务,与政府部门的一致性也成为考核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
政府部门与社工机构的任务目标大体上是一致的,有时也会出现社工机构权责矛盾的问题,这会导致社工机构自身的有限权责会被放大,无法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无限管控还体现在基层政府(本文指村委会)与上级部门对社工机构的多部门管理,产生社工机构权责不清、机构运行成本增加、服务开展效果不佳等问题。
2.3 专业性和专业价值缺失
获得政府资金支持的社工机构,往往很难在服务中体现专业性及其专业价值,大多数服务活动停留在“吹拉弹唱,视频拍照”的层次,千篇一律,无法开展深层次的专业服务。同时,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政府部门往往又不能及时出台审查机制,这就导致社工机构鱼龙混杂,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稀释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2019年,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有53.1万人。“家里人有在社区工作的,说考取社工证进社区容易些,我这才考的。”这些诱人的条件是很多人考取社工证的主要原因,他们将社工证当作了进入社区工作的通行证、“敲门砖”,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暇顾及持证社工的专业价值和伦理守则,必然导致社会工作者队伍 “重数量不重质量、重结果不重过程”的畸形发展。
此外,专业性和专业价值的缺失还体现在社工机构超负荷运转,繁冗的行政事务挤压了社工专心本职工作的精力时间。薪资待遇低、晋升机制模糊,一些专业社工在出现职业倦怠时,却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地缓解,导致社工机构人才流失现象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专业社工机构在完成使命和活命的选择中陷入两难[11]。
2.4 融入性与排他性共存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在地化”发展,必然面临融入与排他的问题。乡村社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使社会工作不得不面临两种选择:被拉拢和被排斥。社会工作在乡村开展服务项目,往往需要村委会的引荐,如村委会不能对村民加以正确引导和宣传,极易被村民看作基层政府的“话事人”,极大阻碍社会工作后续工作的开展;若社会工作向乡村利益集体(指乡村中拥有较多土地、产业等优势资源的人或家族)靠拢,就有可能损害村中大多数人的利益,违背社会工作的初衷;社会工作如亲近乡村弱势群体,维护村民集体利益,就有可能损害利益集体的利益,社会工作在获取资源方面会受到较多的阻碍。多方面的利益权衡使得社会工作在乡村开展服务工作举步维艰。同时,乡村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和其他外部进驻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之间也面临融入与排他的问题。
3 社会工作“在地化”发展困境的应对之策
本文认为,在地职能、在地价值及在地关系的三大融入方向是解决社会工作“在地化”发展困境的有效策略。
3.1 坚持党的领导
要理清党的领导、行政化和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在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要处理好与其他方面的关系。社会工作独特的价值理念和专业服务精神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谋而合,将党的领导置于社会工作的核心地位,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的运行和顺畅地开展服务工作[10]。社会工作者在基层开展服务工作,其价值来源于基层社会,扎根于基层,服务基层民众是社会工作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同时,要尽力避免行政化力量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和制约,保持专业独立性和自主性,坚守专业价值伦理守则。
3.2 在地职能的融入
在地职能是指社会工作“在地化”的发展中角色定位的契合,价值理念的统一以及功能与目标的匹配[3]14-15,以实现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融入。社会工作在地开展服务,要善于发现问题,“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12]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从较宏观的层面思考作为政策建议者如何更好介入,通过社会工作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资料收集与问题评估,及时向上反馈,保证基层政府及时作出政策调整,使基层治理效能能够更好地惠及在地群众。
基层政府在划定社会工作责权义务时,要通过系统的民政工作基础评价标准来划定界限,不可将民政工作一股脑地置于社会工作中,要求其承担额外的责任义务,也要对社会工作行业规范严格监管,不可对其放任自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与当地民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商定社会工作薪酬奖励机制,应不低于当地最低平均工资水平,根据市场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对于社会工作职业者的倦怠问题,机构督导人员应根据个例或普遍存在的情况,积极进行调节,及时疏导,改善社会工作行业人才流失现象。
3.3 在地价值的融入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职业,但其独有的在地价值观念使社会工作明显区别于其他志愿服务。中国乡村社会独有的差序格局,使其形成了“十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在地价值观念。社会工作“在地化”式的服务工作,必然面临多种价值相互冲突和交融,社会工作在面对不同价值观拉扯时,需要保持价值中立。价值中立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合乎情理的价值介入,不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行灌输给服务对象,而是更好地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排忧解难[13]。
社会工作独特的接纳、同理、倾听等手段可以很好地拉近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尤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里聚居了朝鲜族、满族、回族等几十个民族,在开展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深入了解多方价值观念,找寻其中的平衡点,这有助于弥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缺失,也是对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念的修补和完善。
3.4 在地关系的融入
3.4.1 在地村委会、利益集体、村民的融入
社会工作者进入乡村开展相关服务工作,需要向当地村委会表明自己的身份立场,强化村干部对社会工作的认知理解,避免村委会对社会工作的行政化干预。开展服务时,可以邀请村委会主要负责人莅临指导,对于服务中双方有分歧和争议的事项进行协商,增进双方之间的了解,相互督促,共同进步。
中国乡村人际关系复杂,大多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群体,内部比较团结,家族产业在乡村也比较多见,社工机构的存在有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威胁。社工要尽力展现出友善的一面,讲明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服务要求,使他们放下戒备,接纳社工机构的服务。社会工作自身要明晰服务专业化与立场中立化[14]的辩证关系。
社会工作者在面对陌生的乡村环境时,除了要进村入户走访,合理规划政府机构派遣的服务项目,还要宣传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专业价值,挖掘与社工具有同质性的村干部和其中具有影响力的村民,进行专业社工培训,使其成为在地社会工作人才[15]。
在地社会工作人才的培育,可以更好地让社会工作在基层政府、利益集体、村民三方之间斡旋,协商、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纠葛。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成为政府治理、村民自治、社会调节的良性互动渠道,赋能社区协商议事,助力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水平[16],更好地为当地群众服务;在社工机构撤出后,也可以保证服务效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就实现了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和人才的在地陪伴逻辑。
3.4.2 在地社会组织融入
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多元力量参与推动,除政府和市场相关主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助力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社会组织大多可以分为外来输入型组织和本地内生型组织[8]。这两类组织在项目运行逻辑和自我发展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各个组织的价值理念和服务方式的不同可能会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乡村开展专业服务,必然绕不过这两类组织。为了更好地开展服务,社会组织各自为政的问题就需要妥善解决,将凝聚共识与尊重差异相结合,以柔性引导和弹性合作的方式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引导至增进乡村建设中[17]。
社会工作机构和人员在与各类组织接触的过程中,要向社会组织灌输专业性理念,体现社会工作专业性,树立权威性。宣传要适度,不能异化社会工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否则不利于民间社会组织力量的整合。社会工作还要对在地社会组织进行文化和能力建设,对社会组织进行整合,将专业性与本土性融合进社会工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服务理念和项目中去,通过组织领导和联盟,更好地实现社会工作的服务愿景。
4 结语
目前,社会工作“在地化”的发展已经从“教育先行,政府部门大力推动”进入到“各地普遍接受,专业依附和嵌入”的阶段,距离地方政府与社会工作步入“和而不同”的融入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行业发展来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完成使命和活命”的问题。无论是民间自发成立的社工组织,还是背靠高校建设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其定位也要随着政策走向而发生变动。如自身的专业伦理和价值使命在政府和社会之间不能两全,就会异化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使命。从外部来看,行政化干预使社会工作似乎成为了当地政府部门的“编外下属机构”,这就造成了社会工作与政府的不对等,使其难以保持专业独立性,更遑论为弱势群体向政府争取权益。
目前来看,在体制上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在主体上坚持社会协同、多方参与;在理念上坚持独立自主、助人自助;逐步建立社会工作相关方面的政策法规[3]16,使专业服务开展名副其实,“善于同当地人一起工作,努力发挥在地群众解决问题的潜能,发挥其优势,与他们协同解决面临的问题”[18],助力乡村振兴,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