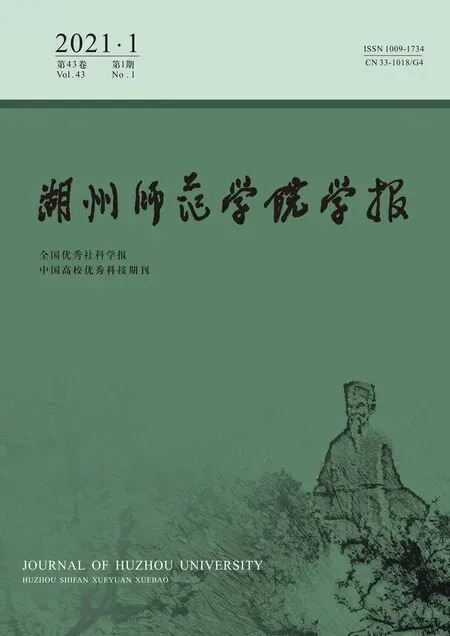从空间叙事看《福》中的“他者”逆写*
张晓明
(湖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福》是J.M.库切对经典殖民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改写,但却不是简单的仿写,更多的是颠覆。《福》是库切的第五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国内外批评家有从寓言或后殖民主义角度解读南非状况,也有从女权主义角度来批判父权话语体系,却少有从空间批评角度来阐释小说中的空间叙事模式。《福》一改《鲁滨逊漂流记》所运用的传统男性线性时间叙事模式,通过女性视角加入空间元素,对荒岛及城市的地理空间和女主人公苏珊及黑奴星期五的身体空间进行建构,从而向读者呈现出与经典故事完全不同的一面,展现出边缘与中心、控制与反控制的二元对立。库切在对历史进行大胆反拨的同时,也开拓了空间在叙事中的功能和意义。
一、地理空间
地理空间是空间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小说叙事发展的支点,任何故事都必须依赖某个地理空间而存在。现代小说对空间的处理已经出现转向,空间不仅限于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所,还可依据作家的选择而被改造。地理空间对人物塑造和主题表现有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空间体现了作家的艺术意图,具有了结构的叙事意义,已成为作家表情达意的一种艺术空间。可见空间与意识形态是紧密相连的,因而表现出正义与非正义、边缘与中心、控制与反控制等的二元对立[1]50。综观小说,读者可以发现,时间在故事的讲述中已经不再占据主导作用。随着主人公苏珊的生活轨迹迁移:落难的荒岛、伦敦的暂住处时钟巷、作家福位于纽因顿的房子、福的隐避之所,读者的视角在不断转变。通过对这些空间的建构,经典故事被解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群体得以展现,从而使不同的声音被听到。
(一)荒岛空间
库切在《福》中对地理空间的构造颇具匠心。故事的第一章节发生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来自不同阶层,具有不同身份和文化背景的人物在此偶然邂逅,发生对话和产生冲突。库切并没有花费大量的笔墨去描绘被克鲁索所统治的、彰显白人男性霸权的荒岛开阔地貌,而是更多地聚焦于克鲁索隐秘狭小的居住空间以及恶劣的生活空间,从苏珊·巴顿的女性视角来还原克鲁索在岛上生活的真相。时间概念在荒岛上是完全缺失的。克鲁索已经记不清滞留荒岛究竟多少年,也不想去记。此处的克鲁索不再是殖民文学经典中开拓进取、具有现代时间意识的白人英雄形象,而是一名地道的懒汉。通过对空间的设置,库切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克鲁索。
苏珊首先从克鲁索的住所开始描述。“在两块石头之间,克鲁索用杆子和芦苇搭盖了一间茅草屋,用围栏将营地围成三角形来阻挡猿猴。茅草屋里仅有的家具是一张狭窄的床。地面是光秃秃的土地,屋檐下的草席就是星期五的床。屋里的炉子也是就地取材,用石头堆砌而成。雨天时,屋顶四处漏雨。用以维持生计的只有野生苦莴苣、鱼和鸟蛋。”[2]5即便是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也没有激起克鲁索改变或逃离现状的意志。这里的克鲁索与《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那个冒险英雄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苏珊问“为什么你没有替自己造一艘船逃离这个小岛”时,克鲁索回答“我能逃到哪里去”[2]9。此处的克鲁索不是一个雄心勃勃、充满斗志和自救精神的资产阶级殖民者。在苏珊的眼中,克鲁索毫无作为,满足现状。陷入绝境让他绝望,进取之心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苟且偷生。他日复一日做着搬石头整理梯田和围墙的无用功,只为打发时间。在他的棚屋里,支撑屋顶的柱子和床脚上也没有关于时间的痕迹。克鲁索无意为自己的荒岛生活留下印记,也无意逃离海岛自救回归文明世界,他只满足于做这个孤岛统治者。这也预示着线性时间叙事将被打破,叙述将围绕着空间展开。在苏珊看来,克鲁索的眼界正如他那逼仄简陋的茅草屋一样狭隘。与克鲁索相比,作为女性的苏珊对于空间有着更灵敏的感知与积极的探索。她希望能够借助任何有利条件逃离孤岛。“我沿着沙滩漫无目的地四处走了一会儿,虽然目前还不可能出现救援的机会,但我还是时不时地眺望一下大海。”[2]15从苏珊这一女性视角展现出的荒岛空间,彻底颠覆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积极进取的白人男性殖民者的形象,同时也预示着故事的发展不再被男性叙事所主导,在经典故事中被淹没的女性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室内空间
随着主人公获救离开荒岛回到英国,读者的视线也从室外空间转移到了室内空间。从室外到室内,隐喻着女性试图通过占有独立的空间,实现叙述声音的独立。整个第二章节为书信体,由苏珊写给作家福先生的信件组成,也是整个故事中唯一出现具体时间的部分。苏珊在临时居所“时钟巷”按照自己的所见所想,写信向福先生真实地叙述自己的海难遭遇,并恳请借作家之笔让自己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一个有实质存在的人。“请将我失去的实体还给我,福先生,这就是我的恳求。”[2]45然而在极具隐喻意义的“时钟巷”发出的信件都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因为她的叙事打断了男性为主体的线性时间叙述,这种脱离时间、背离传统的叙述一旦离开居住的庭院便无人倾听。这也暗示出在看似真实客观的男性线性时间叙述中,女性话语往往被排斥的事实。在男性线性时间叙述中不允许展现的女性真实存在,苏珊希望藉由其他途径——空间占有来实现。
苏珊意识到对于女性而言空间占有的重要性。“如果要讲出完全充满实质感的真实,你需要一个安静的不受任何干扰的地方,一把坐着舒服的椅子,一扇能远眺的窗户。”[2]45苏珊希望通过空间的占有,争取发声的机会,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实质存在的人。在时钟巷不具备的条件,苏珊最后试图在作家福位于纽因顿的家中找到。当福先生突然消失时,“我们住进你的房子,我开始写作……我现在坐在你的书桌上,透过你的窗子向外看”[2]56。住进福的房子,是对占有话语空间的再次尝试的隐喻。然而男性主宰的话语世界拒绝平等交流,对于苏珊的真实记录并不接受,“最好只有克鲁索和星期五,最好不要有女人”[2]63。通过信件记录下的自传,被放进邮筒却无人阅读,最后她又被迫离开福的房子。苏珊试图通过占有空间,记录下真实的海难经历,成为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拥有实质存在的人,但她的尝试失败了。第三章节,苏珊找到了作家福先生的隐蔽之所,希望能够藉作家之手将自己悬而未决的人生得以呈现。“你的故事未完成,我的人生也就被悬挂着。”[2]55然而福先生仍然坚持在时间线性叙述的基础上完成故事,“我们这本小说包含了迷失、追寻、失而复得。有开始,有中间,还有结尾”[2]105。至于荒岛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不值一提,更不要说黑奴星期五的故事了。苏珊对话语权的争取仍以失败告终。
二、身体空间
在《福》中,话语权的争夺不仅存在于男女共存的地理空间中,身体空间也成为话语权争夺的战场。与空间超越单纯的地理内涵一样,身体也超越了纯粹的生理含义,而更多地反映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呈现的价值与意义[3]162。“身体是政治、文化、伦理、记忆和权力的承载者。自尼采已降,经过德勒兹和福柯等人的发展,身体日渐成为当代哲学的理论焦点。”[4]72国内外学术界对身体批评话语体系也在不断地建构与完善,空间批评学家普遍认为,身体与地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都存在密切的关系。身体具有感知空间的能力,也是空间建构的物质基础,一切空间关系的建立与维持都是在身体的基础之上存在的。正是身体与周围环境的接触才形成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因此用身体去体验空间,用身体叙事去探索空间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库切通过对女主人公受限的身体空间突破,以及黑奴星期五残缺的身体反抗的描写,赋予“他者”言语的权利,展现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一)女性受限的身体空间
在父权制社会中,身体成为一种承载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以及具有广延性的空间关系表征。男性主宰的社会空间往往对女性身体实施局限和禁锢,在这种背景之下,女性对身体的空间实践和探索经常成为被研究的主题,空间也成为具有生命力的身体体验。“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5]61-62因此研究小说中女主人公苏珊的身体空间实践和探索也是对库切小说进行探索的一个重要途径。苏珊通过身体活动空间的突破,用身体构建自我空间,并以性为武器抵抗父权意识对女性的限制,试图不让自己在男性叙事中被淹没,从而成为一个拥有话语权的实质性的存在。
小说中荒岛成为展现白人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的绝佳平台。在男权制的社会里,空间的权力结构就是男性为主体,女性为他者。男性因对空间的绝对控制而拥有话语权,而对话语权的争夺则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荒岛上,克鲁索是主宰者,任何试图改变荒岛生活现状的举止都不会被容忍。作为这个荒岛的“国王”,克鲁索视苏珊为他在这座孤岛上的第二个臣民,并严格限制苏珊的行动自由。首先是以岛上有伤人的猿猴为由,警告苏珊不能随便离开他的城堡。当苏珊不顾警告走出棚屋,试图去寻找被救的机会时,克鲁索大发雷霆,“只要你生活在我的屋檐下,你就要听从我的命令”[2]16。苏珊遭遇海难后,一直没有自己的鞋子。当她向克鲁索要针线,试图自己制作鞋子时,克鲁索以“鞋子可不像手绢一样,三两下就可以做出来”[2]16为由拒绝了苏珊的请求,并承诺到时会帮苏珊做鞋子。然而几天过去,苏珊仍然没有鞋子穿。从性别政治学角度看,性别、身体与空间始终是权力统治运作的场域。在父权制社会里,与象征权力、强大、自由的男性不同,女性的身体是被控制、压迫、改造的对象,因此女性的身体空间呈现出狭小局促性、自我圈限性、压抑扭曲性和道德训诫性的特点[6]4-5。鞋子的缺失直接限制了苏珊的行动自由与社会空间,而男性往往通过操控女性的社会空间以达到控制女性的目的。由此可见,空间往往是造成女性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反映了女性个体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当苏珊的请求遭到漠视后,她并没有放弃对自由行动权的争取。“在空间与权力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乃是身体,是那个不能被简化、还原的和不可颠覆的身体。”“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身体这个更加脆弱、更加容易折磨的东西吗?但是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具有反抗性的吗?”[7]18-19身体是一个行动体系,会根据拥有者的内心真实想法而作出回应。于是苏珊用猿猴的皮料做了一双粗糙却能带来行动自由的凉鞋。克鲁索却认为苏珊没有耐心去等待一双更好的鞋子。当苏珊回应“耐心让我成了囚犯”[2]20时,克鲁索又大发雷霆,将做鞋子剩下的材料使劲扔到围栏外去。获取行动自由的权利后,苏珊每天都会到海边去,并且尽可能走得远,目的是为了观察海上是否有船只经过以便获救。通过对身体活动空间的争取,苏珊实现了对男性权力空间限制的突破。回顾初登荒岛时,克鲁索还统治着小岛,作为遇难者的苏珊没有任何话语权。为了能在岛上存活下去,急忙向克鲁索倾诉自己的遭遇以获取在岛上安全的臣民地位。通过对克鲁索生活的观察,她了解到了克鲁索的真实经历和故事,因此在向作家福先生描述荒岛经历时拥有了部分话语权。正是在这种空间性的活动中,女性拥有了话语权的可能性,实现了对男性绝对话语权的突破。
在父权制社会中,性也成为男性压迫和约制女性身体的一种手段。男性作为欲望的主体掌握着主动权,而女性是被制约的客体。但是在克鲁索的屋檐下,乃至在床笫之上,他必须与她面对面,让渡出部分话语支配权[8]191。库切以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描写隐喻了女性话语权的获得过程。当苏珊进入克鲁索的生活一段时间后,克鲁索得了热病,此时的他只能依赖苏珊的照顾。大病初愈后的他也改变了对女性不屑一顾的态度,主动向苏珊求欢。苏珊本可以挣脱,“因为我比他强壮许多”[2]25。但此时的克鲁索仍然是空间的支配者和话语权的拥有者,他制止了苏珊的起身,占据上位,“按自己的意志行事”[2]25。然而在获救之后,在克鲁索临终之前,在船舱里他们再次发生了性关系。只是这次,苏珊拥有了主动权。“我的身体压在他身上。”“我在你的体内游泳,我的克鲁索。”“他的身材高大,我的身材也很高大。这种游泳,这种攀附,这种耳语——这是我们的媾和。”[2]39当苏珊回到文明社会,面对同样掌握着话语权的福先生时,两性关系的描写再次出现。“我希望我们共度的第一个夜晚,我能拥有一些特权。”“我褪去衬衫,骑在他的身上(让女人压在他身上似乎让他有些不自在)……同时觉得自己的四肢逐渐有了活力。”[2]128通过这种身体姿势,苏珊掌握了性主动权,从欲望的他者变成了主体。对身体宗主权的运用,颠覆了两性关系中的性别权力配置,扩展了身体空间,从而重构起女性被规约的主体身份。
(二)星期五残缺的身体空间
在笛福的作品中,话语权不仅掌握在男性手中,也掌握在白人殖民者的手中。星期五因为主人克鲁索的教导经历了所谓野蛮人被文明化的过程。然而在白人殖民者占据话语权的殖民话语体系中,血腥的历史真相被掩盖。“进入后殖民时代,白人文明与文化的欺骗性质依旧被其话语系统所掩盖。”[8]193库切试图通过赋予星期五话语权来挖掘历史真相。库切笔下的星期五舌头被割去,身体被阉割。这也暗示着“他者”被剥夺了话语权。与笛福书写的星期五有着明显区别,库切塑造的星期五已经从一个对主人唯命是从的黑奴变成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他者”。星期五既不能言语也不能书写,唯一能够进行自我表达的只能是他的躯体。整个故事看似是一个女性海难者试图用书写自己的遇险故事来让自己成为历史中实质性的存在,但故事的重心逐渐转向身有残疾的黑奴星期五。正如故事的叙述者所说,星期五沉默和残缺的躯体正是故事的中心,或是故事之眼。致残的身体诉说着贩奴历史中千万名奴隶所遭受的创伤,但残缺的身体不仅仅是对历史控诉的表现形式,更是一种反抗的武器。
星期五因为缺少舌头而保持沉默,但这种沉默只是表象,其实质是“他者”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不合作态度,拒绝让自己的实体成为殖民话语中的一个符号。正如福与苏珊争辩表达方式时所提到的星期五的身体叙述能力,“言语只是文字可以被说出来的方式之一,但言语不代表文字本身。星期五没有言语,但是他有手指,手指就是他的工具。即使他没有手指,假设奴隶贩子砍掉了他的手指,他也能像我们在斯特兰德大街看到的乞丐一样,用脚趾或牙齿夹着碳笔写字”[2]132。星期五没有舌头去诉说自己的遭遇,表达自己的意愿,但他从未放弃以自己的方式去诉说。在荒岛上,苏珊观察到星期五划着木头,在海面上撒花蕾和白色花瓣。苏珊以为这是星期五为了祈求捕鱼顺利而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正是这种仪式,解除了苏珊对星期五残缺身体的莫名恐惧,“撒花瓣这项仪式让我明白他是有灵魂的。这种灵魂在他那愚钝、不讨人喜欢的外表下,悠悠地波动”[2]27。然而星期五撒花瓣的地方,也许正是装载着上百个和星期五一样的奴隶的商船沉没的地方。撒花瓣正是星期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哀悼他的遇难同胞。通过这种肢体语言,读者看到的星期五不仅仅是承受了身体创伤,更看到了贩卖黑奴给他带来的精神创伤。
除了撒花瓣的肢体活动,星期五还试图用舞蹈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同样是处于“贱民”地位的苏珊和星期五之间,也存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跟随苏珊回到英国之后,他的沉默是对苏珊强迫式且带有控制欲教导的一种反抗。正如苏珊在给福先生的书信里所承认的:“我告诉自己,我和星期五交谈是为了教育他走出黑暗和静寂。但事实是如此吗?很多时候,如果撇开善意不说,我使用文字是为了找一条捷径,好让他听从我的命令。”[2]53“我曾经努力尝试让星期五开口说话或以言语亲近他,可是都失败了。他的表达方式只有歌唱或跳舞,叫喊是他的语言和文字。”[2]131由此可见,星期五的沉默与其说是一种身体的残缺,不如说是一种主动沉默。当苏珊和星期五寄居在福先生位于纽因顿的家中时,苏珊发现星期五穿着福先生的袍子,戴着假发,沉浸于自己的舞蹈之中。长袍和假发具有隐喻意义。“那是协会的袍子吗?我不知道作家居然也有协会。”[2]81穿上袍子戴上假发的星期五就仿佛被缪斯女神赋予了书写和叙述的能力。在阳光下,星期五乐此不疲地高举手臂,闭眼旋转,与平时的他判若两人,对于苏珊的呼唤也置之不理,跳舞时“喉咙里传来一种低沉的声音,比起他平常的声音更低沉,有时候听起来像在唱歌”[2]82。长袍加身、随性舞蹈成为星期五试图摆脱控制、表达自我、寻找归属的一种途径。这也解释了为何当苏珊试图拿走袍子时,星期五紧抓袍子不放。苏珊意识到“让他陶醉在其中的绝不是在岛上挖掘或是搬运的乐趣,而是之前他在野蛮人之中过着野蛮生活的时候”[2]84。在穿着袍子舞蹈带来的狂喜状态中,星期五的灵魂能暂时地逃离英国,逃离白人控制,回到埋藏在他记忆深处的非洲家园。苏珊终于意识到,星期五并非因为迟钝而自我封闭,而是有意识地拒绝与她有任何交流。其次,在舞蹈中星期五试图向苏珊展示西方殖民者对黑奴的身体残害。在跳舞时星期五只穿袍子和戴假发。“等他开始舞动,袍子便会跟着向上翻起,这样的舞蹈让人不禁以为他想借此裸露下半身。”[2]106这使苏珊意识到,克鲁索所说的奴隶贩子习惯割掉囚犯的舌头以驯服他们,其实只是个好听的托词,星期五其实不仅是被割了舌头,还是一个被阉割的奴隶。通过割舌和阉割,西方殖民者剥夺了黑奴的话语权,但通过舞蹈这种身体活动,星期五找寻到另一种自我表达方式,以此对西方殖民者对黑奴施加的暴行进行了有力控诉。
书写和绘画也是星期五试图表达自我与掌握话语主动权的又一途径。当苏珊试图教星期五写字时,她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是否在嘲笑我努力让他开口说话?”“他那黑色瞳孔的深处,是不是有一丝嘲笑我的意味?”[2]135在苏珊的努力和星期五的反抗中存在着一种博弈,星期五自顾自地穿着长袍,戴着假发,拿着笔坐在福先生的桌前,写着字母o也或许是零,而不是苏珊试图教他的a,这不仅象征着星期五对苏珊的挑战,也说明星期五才是真正拥有叙述自我的权利人。星期五对于眼睛的绘画也具有隐喻含义。苏珊发现星期五在石板上涂写眼睛而非花草。“睁开的眼睛,每一只眼睛都长在一只人脚的上面;一排排的眼睛下面都长着脚,成了会走路的眼睛。”[2]136星期五虽然被剥夺了言语的权利,无法亲自诉说自己及同胞所遭受的创伤,但他的眼睛却见证了贩奴历史的罪行。这些眼睛也是那些被枷锁套着,随船葬身海底的上百个奴隶的眼睛。画眼睛这一行为是“他者”对殖民者暴力的一种谴责,也是争取话语权的一种尝试。
库切的《福》改换了叙事主人公,彻底颠覆了《鲁滨逊漂流记》的荒岛故事,开拓了新的认知方式,更在女性叙事中融入了空间元素,用空间叙事扰乱了男性线性的时间叙事。库切对话语权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赋予了在经典故事中沉默的“他者”以言语的权利,为“他者”叙事从边缘回归中心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叙事解读打破了传统分析视角的局限性,也让读者有更多的可能性真正参与到小说的建构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