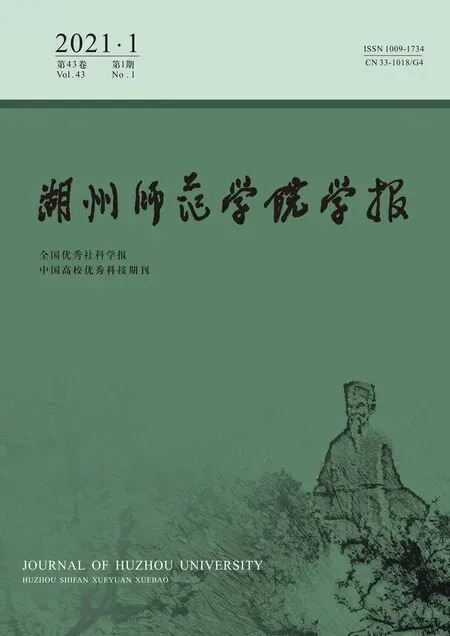莫里森小说《孩子的愤怒》的身体叙事*
金美兰,褚慧英
(湖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是美国知名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一生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11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式诉说着美国黑人种族的历史、黑人女性的命运和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主题丰富,寓意深远,颇受读者喜爱。“重复叙述”“音乐元素”等叙事技巧和主题的善用也使其小说风格独特,魅力超群。身体叙事手法的娴熟运用是其作品的另一大突出特点。
身体叙事源于哲学上的“身体转向”思潮。哲学家尼采振臂一呼“一切从身体出发”[1]9,这一号召扭转了哲学的“重理智、轻身体”的局面,将身体推到了前台位置,而后发展起来的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福柯的微观权力渗透学、伊格尔顿的身体美学,更是进一步启发人们挖掘身体的哲学、政治、经济意义。20世纪作家们受此哲学思潮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地融入了身体写作。
身体叙事是指“将身体维度纳入文学研究,重新审视身体如何影响文学叙事,以及作为身体性的存在者如何叙述身体”[2]72。它以身体为叙事媒介传达写作意图,体现写作意义。莫里森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她“特别擅长从身体的维度展开叙事。她的敏锐身体意识在其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推动着故事的叙事进程”[2]72。她深谙身体的意义,并在其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身体叙事话语,来反映种族、性别、阶级、历史和政治主题。她借《最蓝的眼睛》中小主人公对蓝眼睛的渴望来批判文化殖民的种族主义悲剧;借《宠儿》中奴隶母亲亲手割断女儿喉咙来控诉奴隶制的惨绝人寰;借《秀拉》同名女主人公叛逆的性爱观倡导女性的身体自主和精神自主;借《恩惠》中“卖女为奴”的故事“反映黑人种族被奴役、被压迫的历史现实,以及女性身体被男性霸权规训和惩罚的现状”[2]72等等。
在莫里森最后的一部小说《孩子的愤怒》(GodHelptheChild)中,莫里森“用她钟爱的多重叙事视角,让各色人物适时发声,表述其困顿的生活情态和复杂心理,看似平淡的叙事语言包裹着作者对当代社会环境宽泛而深刻的讥讽,外加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怪诞,共同筑造出莫里森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现代黑人故事”[3]108。国内学者从空间视域、创伤理论、消费主义等角度对小说进行研究。本文尝试分析小说中的身体叙事和身体政治。《孩子的愤怒》延续其一贯的重视身体叙事的写作手法,以身体为媒介,“利用身体刻画和身体体验的叙事情节来讲述重大的社会、历史和政治问题”[2]72,反映其在种族、女性、儿童保护等多层面的政治主张和写作意图。在《孩子的愤怒》中,莫里森首先一如既往地重点关注黑人女性遭受的肤色政治。此外,她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描述女主人公身体的奇妙变化来彰显女主人公从童年精神创伤中走出迷失、发现自我、与创伤和解、与历史和解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莫里森首次尝试将目光转向儿童,从儿童性暴力的角度入手,分析身体暴力创伤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呼吁关爱被忽略的儿童群体。这部小说的发表表明了莫里森小说创作的关注点已经从黑人种族问题转向更为深刻的人类共性问题[4]4,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肤色政治阴影下的女性悲哀
福柯说,权力和社会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5]27。身体是刻写历史痕迹的媒介,是“权力的符号”[5]111。身体自始至终受到权力的规训和惩罚,没有脱离社会而孤立的身体。黑人作为美国社会的少数族群,再加上长期的历史原因,他们的身体受到严苛的权力规训。在长期的权力运作下,黑人女性的身体困境,不再是简单的失去身体的自主性。在以白为美的肤色政治长期规训和微观渗透下,黑人女性接受不了自己的身体颜色,并将白人至上的肤色政治价值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标准才是她们最大的悲哀。
小说《孩子的愤怒》中女主人公卢拉·安(Lula Ann),长大后为了摆脱过往更名为布莱德(Bride),她就是肤色政治的受害者。莫里森并没有直接刻画黑人女性因为黑肤色受到白人歧视的过程,而是从女主人公母亲甜心(Sweetness)的角度出发,着力渲染在社会权力的长期微观渗透和规训下,黑人内化白人美学的评价标准,做出一系列不理智的行为,而疯狂的行为背后是对种族歧视的恐惧。母亲甜心“肤色很浅,头发顺滑”[6]3,完全可以装成白种人,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肤色越浅越高贵”[6]4的理念深入人心,让她在现实社会里“保持着少得可怜的尊严”[6]4。可是令甜心难堪的是,女儿“出生时皮肤像所有婴儿一样浅……但她飞快地变深,她在我眼皮底下变成了黑得发紫的颜色”[6]5。深黑的肤色使布莱德在父亲的缺席、母亲的嫌弃中长大,甜心甚至连“妈妈”“母亲”都不允许女儿叫。“她那么黑,嘴唇厚得出奇,从她嘴里蹦出一声妈妈,一定会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何况她眼睛的颜色也是奇怪,像乌鸦一样黑,黑的发蓝简直带着股邪气。”[6]7“她的肤色是她背上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十字架。”[6]8被白人至上和白人美学的社会权力规训的甜心,始终停留在传统的肤色认知上,自我意识里自觉地认同和内化了“以白为美”的价值观。她对自己女儿充满了嫌恶,想尽办法避免与女儿有身体上的接触。这导致女儿病态地渴望母亲的抚摸和碰触,哪怕是扇脸、打屁股都好。为此,她“故意犯些小错”,但是“她(甜心)总有不碰触她憎恨的皮肤也能惩罚我(布莱德)的法子”[6]35。在肤色政治阴影笼罩下成长的小布莱德,为了获得妈妈的微笑和妈妈的牵手,在法庭上故意做伪证,错误地指认女教师索菲亚猥亵儿童致使其被监禁15年。这种错误,让布莱德一直生活在过去,背负着无法言说的罪恶感,无法在精神上成长起来。
可悲的是,长期浸润在“肤色越浅越高贵”的社会文化中,甜心认同并建构了她的肤色理论系统。她自认为自己疏离孩子的方式是为了孩子好,“选择一种必要的方式抚养她长大”[6]196。“只有成为母亲,你才会发现自己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周围的世界也将向你展露真容,你将明白它是如何运转的,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6]198主流社会的审美观就是一种社会权力。在它的微观渗透下,如甜心一样的黑人女性自觉内化了白人价值却不自知,形成了她们畸形的肤色审美观。她们是种族主义肤色政治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践行者,她们造成了黑人种族的内部歧视。
二、性暴力下儿童的“替罪羊”式人生噩梦
在《孩子的愤怒》中,莫里森超越了种族界限,开始将眼光转向了儿童,以儿童承受的性暴力为切入点,揭示儿童作为弱者,成为社会不公和社会暴力的“替罪羊”和“出气口”,呼吁社会关注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成长问题。“性犯罪对孩子造成的童年创伤是非常惨烈的,而施害者往往隐藏得很深,未暴露前常常被世人赞为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残暴与善良并列的反讽让人警惕并思考当下文化中的暴力、欲望等问题。”[7]110莫里森又一次以文学的形式写出了旁人所没有关注的社会关切,体现了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意识。
儿童作为社会弱者往往最容易受侵害,而童年创伤后果极其严重。“童年的伤痕会化脓溃烂,永远都不会结痂痊愈。”[6]148莫里森没有直接呼吁保护儿童,而是从身体出发挖掘出儿童身体受侵害这一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孩子的愤怒》中,故事的主线之一即布莱德的男友布克(Booker)突然弃女友而去,布莱德一路苦苦追寻被抛弃原因。通过层层剥茧,他愤然出走的原因是无法理解和认同布莱德居然去探望被她指认猥亵儿童的女人。愤怒的深层原因是他走不出哥哥亚当被性侵杀害的心理阴影,摆脱不了童年的心理创伤。布克的哥哥“亚当被发现时尸体已经残缺不堪……很明显,这些孩子在遭受性侵害和折磨时是被绑起来的,凶手甚至还砍掉了他们的手脚”[6]132。这种残忍对布克造成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他想要身体的正义,让“凶手要背负着逐渐腐烂的尸体走来走去,这既是身体上的负累也是公开羞辱与唾弃”[6]133。可是他却做不到。他无法像父母和家人一样,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继续生活。童年心灵的创伤使他走不出过去,也找不到未来。
另一个性暴力的受害者是布莱德在追寻布克途中遇到的小女孩蕾恩(Raisin)。她的母亲为了钱逼之做雏妓,“那个相当老的家伙让她受了很重的伤,流了血,她妈妈然后用一种黄色粉末给她灌起下体”,“她很怕男人,他们让他恶心”[6]115。后来她咬了那个“常客”的生殖器,没把客人服务好,被母亲赶出家门,蕾恩不得不流落接头。小小年纪的她积累了令人心酸的生活技能:“得知道公共厕所都在哪儿,知道怎么躲开儿童福利机构和警察的视线,怎么甩掉醉汉和瘾君子,但最重要的是知道在哪儿过夜才安全……如何觅食并储存到下一顿。”[6]115蕾恩的不幸给她造成了身心重创,也引起有着悲惨童年的布莱德深深共情,为其之后理解布克,与布克和解,最终走出童年创伤并找到自我做了有力铺垫。
此外,书中还简述了类似的伤童事件。布莱德的好友布鲁克林(Brooklyn)小时候因其叔叔“蠢蠢欲动地想摸进我腿间”[6]153,她只能要么躲起来,要么逃跑,要么假装胃疼大叫。后来14岁的她选择离家出走,寻找更安全的栖身之所。姑妈奎因(Queen)的女儿汉娜(Hannah)遭遇继父动手动脚的“性骚扰”而母亲选择不相信,导致母女关系如“隔了堵冰墙,再也没能打破”[6]189。莫里森选取黑人男孩和白人女孩的不幸遭遇为例,跨越种族的界限,从多个角度刻画针对儿童的性暴力对各种族儿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呼吁关注儿童的成长和保护问题。王守仁评价此书说,本书“抓点非常成功,即从‘童年创伤’切入深刻展现二三十年来美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清白无辜的孩子无端承受了社会各色人等的‘惩罚’,而这些童年创伤也正是社会问题的聚积处,暴露出种族关系、暴力文化、人际隔阂等当代社会须得正视和审视的方方面面”[7]107,作为弱者的儿童成了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另外,“书中所涉及针对孩子的性暴力施害者均是白人或其他人种,这表明莫里森超越了黑白种族界限,关注当代美国普遍的社会问题”[7]111。
三、魔幻的身体变化下女性自我发现之旅
莫里森特别擅长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这种手法在前期的小说如《宠儿》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孩子的愤怒》中,莫里森又一次采用了魔幻现实的写作手法来表现女主人公身体上不可思议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和消费审美的变化,长大后的布莱德凭借自己非同一般的肤色,曼妙的身材,再加上造型师杰瑞白色着装以反衬肤色的建议,一跃成为时尚的宠儿,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美妆品牌。消费主义的到来,对女性身材的审视和“以黑为美”的流行审美给布莱德带来奇迹般的成功。正如杰瑞评价那样,“像冰里的黑貂,雪里的黑豹,然后加上你的身材,还有那双狼獾般的眼睛,天哪!”[6]37“黑皮肤是种卖点,是这个文明世界里最炙手可热的商品,白皮肤甚至棕色皮肤的女孩可要脱光了才能吸引到人们对黑色女孩的那种注意力。”[6]40一方面,她的黑肤致胜的成功是对白人美学的最大反讽;另一方面,体现了在消费社会中,身体和性无疑成了最具有交换价值的符码,她的黑色身体实际上是男人消费的对象,物化的商品,是一种虚假的主体[8]35。布莱德并不能凭借身体获取的成功来构建自己的主体性。与之相反的是,布莱德从未实现对自己身体的真正把握,没有身体的自主性,更别说精神的自主性。
莫里森赋予布莱德的身体一种魔幻的力量。即便是被索菲亚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惨不忍睹,也能奇迹般地愈合。皮肤痊愈得最快,“鼻子不仅痊愈了,还变得更完美……”[6]38如此完美的身体,在其男友突然不辞而别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除了“头发一如既往的浓密光滑”,其他体毛一根都不剩,“全没了,不是被剃掉或是被拔掉,而是像消失了,好像从一开始就不存在”[6]14。而一路向南追寻男友布克时,她的身体也随之变化。在厕所里,“她再次查看了让她担忧的私处,那里仍然光滑无毛,没有一点复原的迹象”[6]91。不仅如此,她体重骤减,她的胸诡异一般的消失了,“她的T恤在胸前没有一丝起伏,耳垂上也没有洞”[6]108。“他们不见了,就像做了台失败的乳房切除手术,只剩乳头还完好无缺,她没有感到丝毫疼痛,一切器官运行如旧,只有月经诡异地推迟了。”[6]105“针织连衣裙的领口歪的厉害,滑落下来露出了左肩。”[6]91这种反常的身体返童现象虽不具有真实性,但是莫里森借这种魔幻的身体变化表明布莱德的不完整自我。虽然已经长大却走不出童年的创伤,也走不出男友布克带来的创伤,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她需要回到童年,纠正错误,弥补创伤,找到失去的自我。而寻找布克,象征着自我身体的重新建构以及身份的重新建构,是她的自我救赎之旅[9]29。
经过苦苦追寻,布莱德找到布克,二人深入沟通,直面过去,澄清误会,在共同生活中,在精神导师姑妈奎恩的引领下,终于找到自我。此时其身体奇迹般地恢复,“看到自己完美无缺的双乳奇迹般地恢复,她无法压抑内心的狂喜”[6]183。莫里森借身体恢复暗示布莱德走出被忽视、做错事的童年创伤,也不再依附男性的消费眼光,找到身体的自主,从而确立精神的自我,最终以孕育新生命来隐喻走出过去,拥抱精神自主,拥抱未来之意。
身体是权力的记号,身体也是政治的记号[2]75。《孩子的愤怒》中,莫里森沿用其特别擅长的身体叙事,以身体为媒介阐述其写作意图和作家责任。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却通过身体阐释融入了多重主题,既包含非裔女性作家反种族歧视反男权压迫的主题,又表达跨越种族界限保护儿童成长的关切,且提出女性走出创伤找回精神自我的倡议。莫里森凭借其高超的写作技巧,给读者呈现出一部手法精湛、主题丰富、意义深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