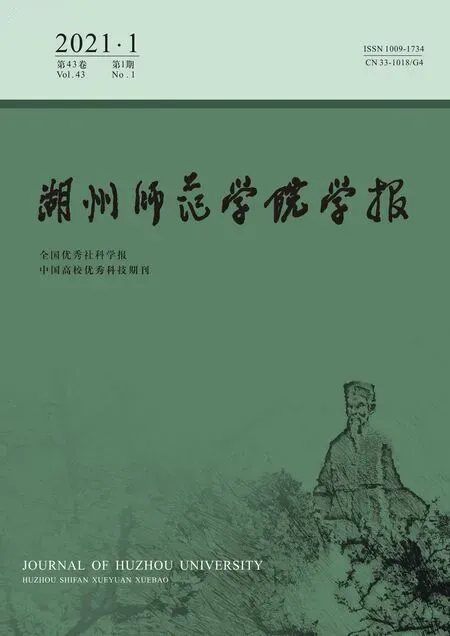扬州评话《武松》“斗杀”ECM的存在行为研究*
张靖宇
(扬州职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扬州评话《武松》是评话艺人根据名著《水浒传》故事重新编写而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书目。自明朝柳敬亭说“武松打店”始,历代表演者对小说原著的创造性改编从未停止。其中,又以王金章、王玉堂、王少堂一脉传承至今的“王派水浒”最具代表性。董国炎[1]148-165在评价《武松》时指出,该书目艺术成就集中反映在对小说的分解与创新、深刻的社会学性、传奇性和写实性高度统一以及审美趣味纵横观察等四个维度。因此,从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美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对其开展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话本是说书人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底本,它决定了评话的生命。因此,话本创作方式和过程自然成为评话研究的核心课题。李真、徐德明[2]49对话本改造方法和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董国炎[3]11-14则从书场叙事的阐述特点对扬州评话话本进行讨论。近年来,认知语言学蓬勃发展,该学科专注信息建构与阐释过程中的大脑反应机制,这一特点吸引众多学者关注其对文本研究的价值[4-7]。国内部分评话研究者[8]75-81还尝试将认知研究路径引入扬州评话的研究,探索话本创作中的概念建构机制。
本文将依循认知研究路径,结合意象图式与事件域认知模型相关理论,对《武松》[9]第三回之“斗杀西门庆”选段中的存在行为进行研究。本文试图揭示评话表演者在话本改编过程中,组织和建构存在行为事件的概念机制以及该行为的语篇功能。
一、事件域认知模型与存在行为
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下文简称ECM)[10]240-241兼顾了线性和层级性研究,适用于动态和静态场景,是解释概念结构和句法构造成因的分析工具。在该模型体系中,认知活动的主体以“事件域”为基本单位组织知识块,并储存于大脑中。一个事件域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事体(thing)和行为(action)。事体是行为的参与个体,可以是人、工具、事物等实体,也可以是抽象概念。事件域的行为往往由多个子行为组成。其中,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过程为动态性行为,而不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过程为静态性行为[11]57。在ECM中,事体和行为包括了各种特征或分类信息。
本文研究的话本语篇描述了武松替兄报仇斗杀西门庆的事件内容。因此,整个“斗杀”事件构成了一个事件域。这里出现的人物、工具、环境信息等构成了事体元素,而行为元素则包括了斗杀、会话、心理、存在等各子行为。“斗杀”子行为作为典型的动态性活动与事件主题相契合,是整个事件域的核心。于此,将另文讨论该类行为的概念建构方式。本文将聚焦于静态性行为的典型代表存在行为。
存在行为是表示事物存在的过程[12]84。在中文表达中,这类行为多通过“是、有、存在、坐落,存有”等动词加以表达。这类动词的典型特点是它们所表征的动作过程在时间维度具有相对静止性,而承担存在行为的事物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延续性。在语篇构建中,这类行为多用于对环境事物的描写。该回目有两处着重使用存在行为对环境因素进行的描写。第一处在回目开头部分,表演者着重描写了“望月楼”的地理位置和内部布局;第二处则对打斗地点之一“望月楼二楼”进行了细致介绍。以下将对回目中的存在行为展开具体分析。
二、存在行为与意象图式
如上文所述,“斗杀”ECM的存在行为需要由表征静态关系的存在关系和事体元素共同参与构建。这种概念组建并非自发的、随意的、先天的,而是需要认知主体通过调用特定的概念加工机制为元素与关系提供动态关联。意象图式在这一概念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意象图式是认知主体在感知互动程序中反复出现的动态样式,它为认知主体的经验提供了连贯性和结构性[13]115。意象图式是认知主体理解复杂概念的基础,也是建构知识的出发点。换言之,意象图式使得存在关系与事体元素的关联成为可能,并指导多个存在行为以特定方式构建概念结构,以服务于“斗杀”ECM。
Guy[14]73利用图式概念提出了家庭环境情景下的感知模型。这一模型体现了“容器(container)”“空间(space)”和“整体—多样性(unity-multiplicity)”等意象图式的融合。当人们将上述三个基本图式加以整合,就可以对场所事体进行识解,从而形成场所类概念框架。当需要描述特定场所时,认知主体激活该结构,根据主观需求使用具体概念阐释结构信息空位并构建语篇。具体而言,认知主体用“容器”图式识解客观场所,从而赋予其内外、容纳、内容等概念结构;通过“空间”图式构建远近、中心—边缘概念关联;以“整体—多样性”图式构建分类关系等。
(一)“容器”图式
研究发现,评话表演者在构建存在行为概念时,基本遵循了图式结构。在“容器”图式的影响下,表演者将“望月楼”和“酒楼二层”视为两个独立的空间,并对其内外做出了区分。对前者而言,酒楼陈设、结构布局以及老板、伙计、顾客等构成了内部空间,而酒楼周边环境,如狮子桥、河和街道则构成外部空间。对“酒楼二楼”而言,东山墙、房间、隔板、方桌、窗户、飞来椅等信息阐释了内部概念槽位,而大街、楼梯则属于外部信息。从对内外部概念的罗列中,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话本中内部概念包含的内容和种类远多于外部概念。
从内容的信息精细度上看,内外概念的差异度也很显著。例1a和例1b分别表征了外部概念和内部概念。例1a是对望月楼位置的描写。为清晰刻画其方位,表演者罗列了“狮子桥”“河”和“街道”三个概念。话本只是对这三个事体大小或方位等单一特性进行了简略介绍,其中既没有涉及更多特征也没有对某一单一特征做进一步的信息补充。与之形成对比鲜明的是,例1b关于内部元素“四仙桌”的概念构建则要精细得多。该句中,事物的多重特性得到了表述,如数量、位置、摆放,用途等。表演者还对其摆放特征进一步细化,将摆放原因(“有点活”)、加固方式(“绳子扎住”)、摆放功能等信息一一罗列出来。
例1a:我先来把望月楼的方向说明一下子:这座狮子桥又宽又高,桥下是条河。桥是头南头北,街道也是头南头北。望月楼就开在桥南爪子底下。
例1b:雅座外头靠板壁有两张四仙桌子,并在一起。并一起做什么?因为腿子有点活啦,腿跟腿绳子扎住,到还蛮牢靠。做什么用呀?跑堂的作案板的。
对“容器”图式主导下内外部信息的切分也导致认知主体注意力分布的不对称性。Langacker[11]70在讨论焦点调整(focal adjustment)时指出,在一个特定概念直接辖域(immediate scope)内,认知主体可以对部分事体概念施加直接关注,使其成为主要焦点(primary focus),其他概念则成为次要焦点(secondary focus)。在句法层面,这种注意力分布往往表现为主要焦点承担小句主语,成为被讨论的对象,而次要焦点则充当其他句法成分,用以阐释、谈论主语对象。例1符合这一观点。例1a本质上属于主从句,冒号前为主句,冒号后为从句。主句中“望月楼”虽未做主语,但因搭配“把”字句,其认知焦点地位得到提升;从句通过三个句子说明其方向。这三个句子又可以分为五个小句。前四个小句谈论“狮子桥”“河”“桥头”和“街道”四个外部元素,句中未涉及内部元素,所以它们承担了主语功能;其中三句又以“桥”为语义焦点。但在第五句中,原先焦点“桥”的突显地位被“望月楼”取代,作为定位参照点做小句地点状语。例1b的小句主语则全部为内部元素。
(二)“整体—多样性”图式
评书表演者通过容器类图式区别了内外元素概念,进而需要对内部概念进行梳理、归类。这一范畴化过程需要借助“整体—多样性”图式。认知主体在识解“容器”内部过程中,需要根据但不限于空间或功能等概念对其进行分解。根据需要,可以对分解出的子元素进一步实施分解处理,进而形成系列低层次的概念。这样不同层次的概念与“容器”构成一个多级阶整体—部分结构。在这一个概念结构中,元素概念之间并非只发生纵向关联,认知主体还可以根据概念化需要,对多个概念个体实施横向联结,从而使结构内概念形成网状布局。
上文谈及的“四仙桌、东山墙、房间”等元素可以视为第一层次的整体—部分结构。例2则体现了低一层级的分类情况。例2中“第三间”指的是明月楼一楼的三间房间之一,它与明月楼直接构成部分—整体关系。“第三间”内部的“柜台”又可以与“账桌、银柜、算盘、账簿、笔、砚、本子”等构成低层级关系。这样,例3就体现了“明月楼”—“第三间”—“柜台”—“账桌”等四级关系。例3描写了酒楼大堂内诸事物元素,它们一方面与大堂构成了部分—整体关系,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又通过空间关系产生横向联系。“屏风”与“楼梯”,“楼梯”与“墙”两对元素都是通过“前—后”空间关系构成的联结。
例2:第三间是柜台,柜台不小呀,柜台里头账桌、银柜、算盘、账簿、笔、砚、本子各项俱全,柜台里头一顺三张独凳,坐了三个人。
例3:店堂内有六扇屏风,当中两扇屏风开着,出入通行。屏门后头就是楼梯,楼梯那边有个钥匙弯绕过去,东面有一道墙,墙上有道腰门。
在语言层面,评书创作者往往采用独立小句对空间整体进行描述,随后再逐一描述其中的子元素部分。例2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典型例子。该句开头描述了“第三间”的账房功能,并使用形容词“不小呀”表述其空间大小,随后的小句则简略提及了各子元素。例3是对大堂空间内子元素的描写,相较于例2,明显更详细,对于各色物体几乎都单独成句描述。这种详略有别的处理方法更多的是基于信息度(informativity)的考量。篇章信息度是指对接受者而言篇章信息超越或低于期望值的程度[15]119。由于例2中子元素是听众耳熟能详的账房用具,其信息量低于听众的期待,因此在语言层面通过名词并列形式加以表现。听众对例3中子元素空间布局不熟悉,属于高信息度信息,所以通过小句形式加以表达。子元素间横向空间关系并不总是通过显性方位词加以标记,如例3中“屏门后头就是楼梯”里的“后头”,表演者也会通过动词暗示其关系。例2中“坐了三个人”和例3中“楼梯那边有个钥匙弯绕过去”,其中的“坐”和“绕”虽然属于表达动作的方式,却隐含了物体之间“上—下”“前—后”的空间关系。
(三)“空间”图式
在静态性行为的描述中,空间类图式对信息的建构作用已在上文低级阶元素横向关系中得到初步阐释,于此将结合视角进一步分析该类图式的使用情况。比较两段存在行为描述,可以发现评话表演者在处理场景的空间化时都是先区分中心—边缘。表演者依托日常感知体验,以门口位置为起点,面对空间内部,将目光投射出的路径视为空间中轴,由此构成了空间处理的中心区域,而中轴两段则成为边缘区域。中心—边缘的切分并不必然对应注意力的强弱分布。例3是对中心区域的显性化处理,空间中心区域与注意力焦点重合,因此在语言层面得到了直观表现。当中心区域与注意力焦点不重合时,中心区域只能作为认知参照点,帮助定位边缘区域。例4就属于这种类型。句中未出现中轴的显性表达,但对房间、东山墙、窗子等物体的空间布局表述则暗示存在中轴区域。
例4:楼上是三间,大向坐东朝西,东山墙是楼梯,西边檐下是一排窗子,窗子底下就是大街。
在区分中心—边缘区域后,话本在构建各区域事体分布位置时,遵循了由近及远、由上至下的安排顺序。例3中各元素的排列顺序印证了由近及远的空间布局,且这种远近关系在语言层面通过方位词“后头”以及指示词“那边”得到明示。“上下”空间安排在文本中有两种体现形式:一是基于地理水平线定位的上下关系,一种是由此产生的隐喻识解。前者体现在例5中。表演者自上而下地介绍了概念元素,突显了“檐”与“案板”以及架子里“酒瓮子”与“马架”的空间关系。这些概念关系在语言层面通过方位词“下”和“地下”加以表现。例6中也出现了方位词“下”,但这里的方位概念通过“上就是尊贵”的概念隐喻,将上下空间概念投射到社会结构概念中,从而派生出表达位置身份的“下首”概念。
例5:檐下搁了一张案板,案板上家伙、鱼肉,堆积如山。……架子高头有四个酒瓮子,酒瓮子底下有个三脚马架了个木马架桶,里面有大小酒端子,紫铜旋子。
例6:下首有一个六角门出入……这桌子下首右边有两张桌子。
上述分析证实,评话表演者通过使用多重图式建构了“斗杀”ECM内的存在行为。创作者通过“容器”图式切分场所内外概念,随后利用“整体—多样性”图式对容器内概念完成分类,形成概念层级网络结构,最后通过“空间”图式为视角设定提供保障。通过上述概念化操作,评书表演者完成了对存在行为信息结构的构建,为听众构建了一个关于“斗杀”事件发生地点的全息化图景。
三、存在行为与动态行为关联
“斗杀”ECM内的存在行为除了具有上文所述的场景信息搭建功能外,表演者更试图通过该行为的层级结构串联起“斗杀”ECM内各个动态行为,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概念框架。
在“斗杀”ECM内,“斗杀”行为只是诸多动态性行为中的一个。该回目至少还涉及了西门庆与打手的会话行为、店小二的送菜并从楼梯滚落的移动行为、老板算账行为和老板与伙计会话行为等。书目中关于这些动态性行为的描写浓墨重彩,这使得每一个行为都妙趣横生。这些行为本可单独成篇,但为了使其服务于主行为“斗杀”并推进整体语篇发展,作者利用了“路径”图式实现了语篇衔接,而存在行为中的元素则成为构建该图式的概念基础。
“路径”图式是认知主体为连接不同空间位置路线抽象而成的概念构型。Johnson[13]113指出,“路径”至少需要保护三个要素,起点、终点和两者之间的序列连接点。这些连接点概念需要被表达空间概念的事体元素阐释。空间性虽然是事体元素的先天属性,但该属性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被激活并得以突显。存在行为具有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的尺度性,就使其承担了激活存在者空间属性的功能。因此,出现在存在行为内的事体元素优先获得阐释“路径”连接点的权利,这也使“路径”图式在语篇建构中发挥作用成为可能。于此将讨论书目如何通过该图式结合存在行为概念元素完成语篇建构。
该回目中有两条路径:一条为贯穿文本的主路径,旨在推进情节发展;另一条为次路径,其串联了斗杀事件域内次要人物并增强了文本喜剧效果。
例7:武松这一刻站在斜对过巷子口,就望着柜台上……就在屏风后散出三起酒客来……到了柜台上会账……
例8:武二爷上楼了,踩了三档楼梯,眼光漫过楼板,朝楼上一望……楼上坐了三桌人……正当中这一桌首坐的这个,估计是西门庆……坐西边上一个小伙子忽然站起身,过来同西门庆说话了……
文本主路径的起点为“明月楼”外“离店门口三四家门面”,终点为“狮子桥”桥顶,途径“楼梯”“二楼房间”和楼下“阳沟”等位置点。作者通过图式叠加,将“路径”图式中的各个节点与其他表征动态性事件的图式融合,实现了行为串联。如例7所示,在“路径”起点明月楼外,表演者通过武松对店内的观察添加了“交易”图式,将酒客会账的动态行为纳入其中。而例8体现了“楼梯”节点与“传递”图式和“容器”图式的融合。该句描写了武松站在房间外观察到屋内西门庆与打手的言语交流。言语交流被识解为会话双方的信息传递过程。此外,话本将“房间”“阳沟”和“狮子桥”三个图式节点与“行为链”相叠加,将故事主角的斗杀行为与“路径”图式相融合。主路径与上述动态性事件的融合,引发了图式概念的隐喻性映射(metaphorical mapping)。Johnson[13]114提出“路径”图式是“目的是路径终点”这一概念隐喻的根源。在该基础上,多种行为的目标和终极意图被隐喻为路径的终点,路径的起点对应于行为初始状态,而各个节点则对应于行为过程中的状态变化。Johnson的观点在本文的主路径图式分析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起点处,对酒客结账行为的描述对应武松进酒楼复仇的观察阶段;在楼梯处,武松观察二楼屋内情况对应斗杀行为开始前的目标锁定阶段;房间内及阳沟两处的打斗是斗杀行为的开始和发展阶段;斗杀过程在狮子桥上演,武松也最终在桥上杀死西门庆,实现了复仇的目标。
例9:武松趴在楼梯上,越听(西门庆与打手对话)越来气……后头来了个人,就是楼上跑堂的,他在厨房里等清蒸白鱼……他右脚踏上楼梯……看见这颗头,(吓得)朝下一跌,同时又惊动了……柜台上的老板……小二看见老板来了,指着楼梯上,对着老板一嘴的话……(他们)又听到楼上有了动静啦……他(老板)绕过了小二,提着衣服上楼看看……
主路径聚焦了主人公武松的行为,而存在行为中的诸多事体概念,尤其是人物概念则通过次路径得到了关注。如例9所示,次路径的起点为二楼房间,表演者通过武松的视角对房间内西门庆与打手的会话行为进行了概念突显。该行为中的“催菜”环节激活了“跑堂的”这一人物概念,明示其当时的“厨房”方位,通过“跑堂的”“移动”图式来到下一个路径节点“楼梯”。话本通过表征“跑堂的”被吓倒的“阻碍”图式和“移动”图式将第四个路径节点“账房”激活。在这个节点内,话本利用“传递”图式构建了“老板”与“跑堂的”会话行为。最后,在“吸引”图式的构建下,“老板”与“跑堂的”听见来自二楼房间内打架“摔家伙”声,“提着衣服上楼”一探究竟。这样,整个路径的终点“二楼房间”被激活。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由“二楼房间”—“厨房”—“楼梯”—“账房”—“二楼房间”等五个节点回环而成的路径。由于起点和终点都是“二楼房间”,这就构成一个闭合的“循环路径”图式。这种概念建构方式旨在增加评书的趣味性,因为这一循环内的几个行为事件刻画了“打手”“掌柜”和“跑堂”的窘态,让受众听后忍俊不禁。同时,次路径是主路径在“楼梯”节点的一个派生结构,它将终点置于“二楼房间”,与主路径中斗杀行为的发生形成了有效连接,从而使得语篇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例10:楼上究竟是哪个摔家伙……
例11:惊动柜台上老板……
“斗杀”ECM中的事体概念在“路径”图式与前文图式内的概念识解方式上存在着显著区别。上文提到,在“容器”“空间”和“整体—多样”内,诸多事体概念都得到了概念突显,成为认知焦点。但在“路径”图式下,这些元素则不再处于注意力焦点区域内,它们只作为识解其他动态事件的环境背景。认知学科将这种视角调整现象称为概念辖域内的“图形—背景”转换。Langacker[11]57指出,在一个场景内被突显的次结构称为图形,而该场景中的剩余部分即是背景。背景为辨别图形提供认知参照。当存在行为中的事体概念通过三类图式实现表征后,作为已知信息,它们只成为识解其他动态行为的认知参照。因此,这些元素从先前的图形位置转变为背景。在语言层面,它们成为认知背景的元素而无法获得主语、宾语的句法位置,只能通过状语或定语得到表征。如例10中的“楼上”虽在句首,但担任的是地点状语;例11中的“柜台上”则对名词短语“老板”实施了语义限制,担任了定语。
四、结语
王派评书《武松》在故事情节、审美趣味、人物刻画、武打描写上都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斗杀西门庆”回目更是其中的代表选段。本文聚焦于语篇中的存在行为,对其概念结构方式、语言表达特征以及语篇功能进行了讨论。研究后发现,评书表演者通过使用“容器”“整体—多样性”以及“空间”三个图式类型,对“斗杀”ECM中的事体元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概念化处理。当这些概念被安置于注意力焦点区域时,表演者根据不同图式对其进行范畴化操作,切分出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种类以及层级的概念集合。这些概念集合进一步组建成跨范畴、跨层级的概念网络。根据语篇情节需要以及概念信息度差异,表演者调整存在行为表征的信息精细度,将高信息度的概念识解为主要焦点。这些焦点元素在句法层面承担主语功能,其特征信息以及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被详细地加以描述。当存在行为的参与元素不再处于认知焦点区域,他们则成为识解ECM动态事件的认知参照点。这些背景化的事体概念通过“路径”图式建构起两条识解通道。主路径服务于武松复仇主线,将“斗杀”行为的完整过程按阶段融合于路径的各个位置节点。次路径服务于表演的趣味性。表演者通过构建一个起点与终点重合的循环路径,将“明月楼”各空间区域及人物纳入其中,并将人物特征与行为窘态融入循环路径的位置节点内。这种安排不仅没有破坏篇章的连贯性,反而通过对市井人物的细节刻画,降低了听众听故事的疏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