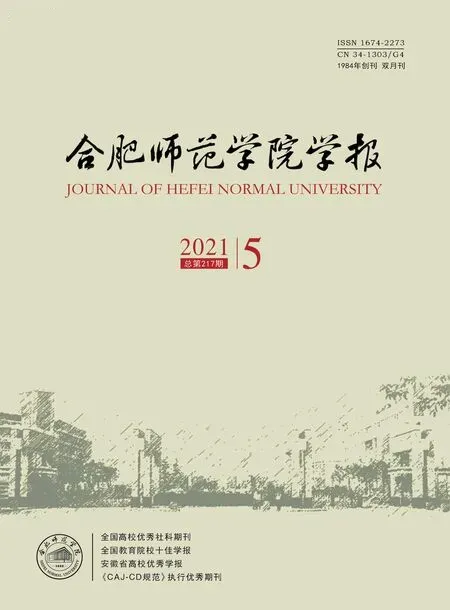再论《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对清代科举制度的批判差异
黄艳萍,黄 鸿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作为中国封建时期最为重要的一项分科选官制度,科举制萌芽于南北朝时期,正式确立于隋唐时期,到清代最终达到应试制度、科考主体等各方面的历史顶峰。“科举以才学为选拔标准,这一理念显然优于血缘、道德和门资,它的上升性指向无疑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向学热情”[1],因此,相较于此前的世卿世禄制、养士军功制、九品中正制等择仕制度,科举制能够延用一千多年而不被取代,本身就说明其存在的优越性与合理性。与此同时,科举制度在明清两代逐渐迈进顽固僵化的深渊,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同为清初长篇通俗小说,前后成书时间相差不到四十年,可以说这两部社会通俗小说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内完成的,又与古都南京有着牵扯不开的地域联系,两部小说作者的出身、经历以及命运境况较为相似,他们在小说内容的选择上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科举八股作为文本的重要方面。由此可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存在诸多相似性,本文将从二文所共有的内在相似性出发,结合明清科举制度的时代图景,从批判态度、批判方式和批判语言的研究视角进行切入,对明清两代逐渐走向深渊的晚期科举制度进行审视。
一、批判态度的差异:非彻底批判与彻底批判
吴敬梓出身于缙绅世家,曾祖父和祖父两代“科第仕宦多显者”[2]。自幼学识过人的吴敬梓也循着祖辈的显名之路,将科举作为实现人生抱负的第一块敲门砖,二十一岁那年参加举业并考取秀才,但很快由于父亲病逝、同族分家,加上自身不胜家计又性情慷慨的缘故,“不数年而产尽矣”[2]10。待二十八岁再入科场时,即被考官训斥为“文章大好人大怪”,此后吴敬梓便怀着“逝将去汝”的愤懑情状离开故土,寓居秦淮。在此期间,他又赴安庆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众相败露的夺产之变、三入两出的举业艰辛让吴敬梓看透了人情虚伪与科场黑暗,故而当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擢其入京廷试时,他“坚以疾笃辞”[2]68,自此不应科举。可以说,这段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一方面使吴敬梓洞察到了清初社会形态和科举制度的流弊,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一丝郁郁不得志的“酸葡萄”心理。因而,在这部沥血而成的讽刺小说中,吴敬梓对科举制的批判态度在果敢无情的同时,也有些许妥协与谅解的意蕴。
《儒林外史》前半部对恪奉“不愿文章高天下,只要文章中试官”的周进、范进、鲁编修、马二先生之流,以及迷醉权钱至心性扭曲地步的恶僚劣绅之辈,以极尽辛辣夸张又诙谐幽默的语气进行猛烈抨击,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也触及无限悲凉。然则翻至小说后半部又颇有柳暗花明、耳目一新的观感,作者笔下的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江南名士,他们慷慨结交贤士,热情切磋文道才思,重塑古礼古乐,在混沌功利的“普世价值”中独守情操。这些文士中亦不乏科举相关者,例如秀才出身的杜少卿、家学业师迟衡山、取中进士后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虞育德,不过作者并未将这些知识分子归入八股庸流一派,反倒以“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3]来称扬名士性情,可见其批判矛头并非单一针对僵化顽固的末代科举制,更直指与真儒士相背而行的假学儒、假名士。
此外,吴敬梓对明清科举制批判的不彻底性也着重体现在小说的最后一回。文本虚托明朝万历皇帝之口为已故儒生加恩赐第,礼部在查访地方、撰拟名单后上表公文,文中肯定“已故儒修周进等,其人虽庞杂不伦,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3]543,由此季萑、景本蕙、匡迥、严大位等士林囊袋也位列其中,这与前文对其丑恶乖张行径的否定存有明显区别,甚至不少学者对第五十六回是否为吴所作而争论不休。但换言之,这又何尝不是作为科举过来人的吴敬梓在痛定思痛之后,对制度残害下儒林众生的悲悯与共情,他宥恕了将八斗之才排挤在外却录用庸才奸人的科举选官,也放过了一直以来耿耿于心的自己,最终在文本结尾处与科举制达成了某种妥协与谅解。
曹雪芹与吴敬梓有着颇为相似的命运经历,曹雪芹也出身于显赫门第,祖父曹寅深受康熙信赖与赏识,其父在曹寅病故后奉命继续担任织造之位。直至雍正五年,曹家因亏空被抄家又牵涉统治阶层内部斗争等原因,从此便一蹶不振,渐趋衰败。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巨大落差,使曹雪芹深感世情的炎凉沧桑,在摆脱官僚阶层的束缚后,他以旁观者清醒尖锐的目光,看透了封建王朝无可挽回的败落之势。其笔下的不朽巨作《红楼梦》也势必承载着作者对封建制度进行彻底批判的义务,作为封建制度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一脉,科举制首当其冲地遭受笔诛墨伐。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为讨伐科举制而精心构思的文本话语主要集中在贾雨村和贾宝玉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身上,前者对仕途经济汲汲以求,后者则对时文八股深恶痛绝。贾雨村原是葫芦庙里寄居的穷书生,在乡绅甄士隐的接济下得以入都科考,得偿所愿登榜做官。在经历了短暂的仕途失意之后,他经由东家林如海指点举荐,成功攀上“护官符”家族,在做了一系列阿谀逢迎、以权谋私的卑琐行为之后,开始一路晋升并高居士僚显位。在曹雪芹笔下,功名利禄带给贾雨村更多的是人性的扭曲与泯灭,却不料毕生为之狂热的名利富贵在一纸参状后便化为乌有,真可谓“到头一梦,万境归空”[4]。
作为全书中最具反封建意识的个体,贾宝玉也是文本批判明清科举制的最强音。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中,就有一句关于宝玉对八股态度的内心独白:“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4]1007他也不止一次痛骂八股文章和举业禄蠹,直指“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4]1107。就连面对宝钗、湘云等亲近姊妹的劝诫时,宝玉也一反常态,毫不留情地回以“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4]473。虽然在小说结尾处,宝玉还是走上“正道”去应试赴考,但这种对科举制的迎合行为绝非软弱妥协,而是主人公即将跳脱大家族藩篱时,对尘世父母愧疚心理的弥补与偿还。在科考中举后,宝玉并没有入仕为官,而是在一僧一道的陪伴下离开尘世,归隐原籍。看似作者已对科举批判做出让步的故事情节,实则以退为进,将其对世俗捍卫科举正统的鄙夷之态推向顶峰,这一幕也足显曹文之匠心独运。
二、批判方式的差异:逐个批判与对照批判
《儒林外史》最为突出的行文特点就是结构上的独立性。小说主要由单一人物所引发的各种啼笑皆非的儒林故事连缀而成,鲁迅也曾评价其文章体式为“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5]。因此,作者借助文本来达成讽刺明清科举的时代任务,也被寄托在一组组形态各异又内里相似的人物身上。《儒林外史》或详或略地塑造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重点描绘了以周进、范进、严贡生、匡超人为代表的一群热衷于八股制艺和富贵功名的士林丑类,以及他们在科举弊病荼毒下所遭逢的种种厄运。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分为童试、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五级考试,而成为童生就是叩开科院大门的第一阶。周进在出场时就被描述成一个衣不蔽体、古板落魄的穷儒,他考至六十多岁仍只是尚未进学的童生,已无资格再教考中秀才的学生。后生梅玖也在席间对他发出“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3]19的讥笑,此时科举制度下唯及第而尊的主体意识已背离尊师重教的古朴观念,生存环境的功利性与压迫性极大践踏了这位老儒的尊严,进一步扭曲了周进日夜渴盼科甲登第的病态心理。被学馆辞退之后,周进走投无路来到省城,当他步入梦寐以求的贡院时,竟号啕大哭一头撞向号板,在客商许诺为其捐赠监生后,又转头“同众人说说笑笑”[3]28,吴敬梓以些许笔墨就将这个走火入魔、人格失控的封建昏儒形象跃然呈现于纸上。
作者笔下的范进和周进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科举制最虔诚的膜拜者,名字中共有的“进”字仿佛与生俱来就是为科考效忠的,虽然同为贫困潦倒、受尽讥嘲的白发童生,范进较之周进的入仕之路又更添一丝偶然性。正是出于举业维艰、命途坎坷的同理心,此时已身为钦点学道的周进在三看试卷后将范进取为院试第一,后又在他的帮助下,范进高中广东乡试亚元。这样一位经过科考层层选拔且能写出所谓“天地间之至文”[3]32的鸿儒,却与张、汤二人争论元朝进士刘基究竟是明代洪武三年进士的第三名还是第五名。成为山东学道后,范进又将大学士苏东坡认作本朝应试童生,种种无知之态着实惹人发笑。然则科举时弊在范进身上的深刻体现又远非于此,历经科考数十载而不第的后果显现在人物生活的方方面面:受科考半生拖累陷入家徒四壁、食不果腹的生存窘境;久试不中受尽亲戚乡邻的奚落与白眼;仕途的一次次挫折与打压又使文人心性逐渐变得自卑软弱、病态扭曲,因而在面对胡屠户劈头盖脸就是“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3]34的辱骂时,范进也丝毫没有心理触动和言语反驳。在如愿中举后,文本又紧接着描写范进疯癫痴狂、范母乐极生悲的情节,以画龙点睛之笔将科举戕害文士之状展现得淋漓尽致。
按照明清科举制的规定,优贡以其品行优劣来决定是否具有应选资格,文中提到过两次优贡,一次是严大位被前任学台“举了优行,又考出了贡”[3]66,另一次是匡迥被温州学政“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3]203。这位被授予优贡并口口声声喧嚷着“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便宜”[3]49的严贡生却光明正大地做着放泼撒豪、鱼肉百姓的违法勾当。与严贡生彻头彻尾的无赖形象不同,匡迥起初是一个勤学聪颖又孝顺善良的少年,在马二先生“荣宗耀祖”的鼓舞说教下,匡迥开始为八股文章夙夜不懈,很快便顺利通过童试和院试,并被举为优贡,但此时的匡迥反倒堕落成一个赌场抽利、包揽词讼、冒名替考、停妻再娶、颠倒黑白的势利小人,文本以这种匪夷所思的前后变化,将科举制屠戮人心的弊端在世人面前曝光。
与《儒林外史》“碎锦”式的散点透视法不同,《红楼梦》以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演变历程和宝黛二人的爱情悲剧为主线,进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式的行文聚焦,人物之间都存在着或远或近的必然联系。因此,较之吴敬梓的单一个体叙述,曹雪芹选择了一种更为立体丰满的批判方式,将主旨意蕴赋予不同人物间的正反对照之中,在种种矛盾冲突中达成揭露封建弊制的最终目的。除了前文所述的贾雨村和贾宝玉这一组矛盾对立之外,文本还设置了诸如薛宝钗和林黛玉、甄宝玉和贾宝玉等多组关于科举批判意识的冲突对照。
作为争夺宝玉婚姻拥有者的人物设计,宝钗和黛玉本身就是小说中一组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二者在举业态度上的迥然不同更深化了这种形象对照。作为推崇孔朱正流的大家闺秀,宝钗坚持“读书明理,辅国治民”[4]566的择优入仕观,认为“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4]1535,因而常常以金殿对策、孔孟之道来劝说宝玉,但这类真理在宝玉眼中却是“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4]474的混账话。小说并没有正面呈现宝钗、黛玉二人关于科举观的言语冲突,而是把主人公宝玉作为中间载体,将二者的对照关系烘托架构起来,以一句“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4]432道出黛玉未曾劝勉宝玉去迎合正统的意识行为。
在“惑偏私惜春矢素志,证同类宝玉失相知”这一回中,两个名字相同、年龄相仿、体貌相似的宝玉初见相欢,可是读者很快就从二人言语和内心独白的矛盾冲突中,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回应贾宝玉所问性情道理的试探时,甄宝玉满口都是“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4]1533,这与贾宝玉素日听闻反抗道统、尊崇个性的同心知己形象已经相去甚远。由此可见,甄宝玉较之贾宝玉,虽有诸多外在相似之处,但他却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妥协性,曾被诟病的不务学道正业亦不过是青少年时期的叛逆心理所致,并非源于对封建制度扼杀人性的本能反抗。当生存环境发生突变后,他很快便将顽劣憨痴之性加以摒弃,转而投向仕途正道,以此重振家门显赫。虽然贾宝玉对另一个宝玉的出现感到兴奋和期待,但当他看到这种背弃本心、附庸世俗的举止转变后,便大失所望,甚至发出“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4]1535的气话,以超乎尘世功利的独到见解,痛指“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4]1535
三、批判语言的差异:写实描写与诗化叙述
《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以通篇直叙、写实的艺术手法,将明清科举制度下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加工提炼而出,让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科举弊病带给整个时代的巨大危机。同为清初古典小说的《红楼梦》却与之相反,无论是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转世轮回的凄美爱情故事,还是一僧一道、太虚幻境等缥缈空幻之物,在主体白话的叙述语境下,曹雪芹极力营造出一个相对浪漫诗意的语义空间,正如“红学”泰斗周汝昌所评,红楼“处处是诗境美在感染打动人的灵魂”[6],这一艺术特点也毫无违和地作用于文本对明清科举制的辛辣批评。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大多以平铺直叙的话语手法来撰写人物形象、空间环境和故事情节。例如“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蓝缕破烂的。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3]31,这是童生走入考场时的体貌描写,作者以近乎平白的叙述口吻,将科举制度下儒林众生的体态缩影匆匆掠过。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文本话语远远超越了其本身所表现的艺术效果,以独到的文字张力使读者内心久久泛起酸楚与无奈之感。又如“头戴瓦楞帽,身穿大阔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3]312,文本以具象写实的寥寥数语,在读者心中顷刻塑造出一个忸怩造作、附庸风雅的儒林门生张俊民。通过后文杜少卿与蘧公孙关于“这人是相与不得的”[3]373谈话内容,可以得知张俊民就是当年虚设人头又装神弄鬼骗走娄家兄弟五百银两的盗侠张铁臂。他在攀附天长杜家后,又为自己儿子冒籍应考一事竭尽钻营,在落实考学之后,还不忘向恩人杜少卿索要一百二十两银子。作为府里医者身份的存在,张俊民所谓对医道的通晓亦是曲意逢迎、招摇撞骗的说辞,娄太爷在他的治疗下非但没有好转,反而“病渐渐有些重起来了”[3]322。封建科举制度对应试者道德品行的不加限制,增加了这样一个坑蒙拐骗的江湖强盗能够在学府、官衙为非作歹的可能,更纵容了汤知县、王惠、荀玫、冯君瑞这类士僚败类对朝纲法纪和黎民百姓的深重祸害。
相较于《儒林外史》对儒士出场时千篇一律“头戴方巾,身穿直裰,脚下粉底皂靴”[3]142的白描刻画,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文客则更显得貌如其性、各人各态,文本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也更添一丝浪漫诗化的审美倾向。正如庄克华先生所言,“《红楼梦》那迷人的魅力正是诗化的艺术力量产生出来的。曹雪芹成功地运用诗化的结构、诗化的意境和诗化的语言创作小说,打开了小说创作在艺术表现上的新路”[7]。小说以“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4]12来形容贾雨村未进仕时的体态样貌,衣衫褴褛的素人外表之下,却是一副平头正脸、八面圆通的士僚品相,这一叙事伏笔也暗示其日后及第成名、势力圆滑的形象转变。小说以具象诗化的叙述语言,将作者关于科举制度下对文人品性反思批判的意图,潜藏在人物外貌描写的表象之下,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语义表现形式能够充分引发阅读想象和审美体验。
在塑造顽劣小儿贾环时,简以“人物委琐,举止荒疏”[4]310八字概括。为科考习得的儒学道义并没有教会贾环修仁行义、尊卑长幼之理,反倒做出许多败德辱行之事:在王夫人处抄经诵读时,逮到机会“把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4]336;金钏跳井事件后,趁机在父亲面前煽风点火,诬陷宝玉“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4]442;在贾琏探病离开贾府之后,又因凤姐平日苛待,就要报复将巧姐许给外藩王爷。“人物委琐”的视觉观感恰好呼应了贾环种种卑琐庸俗的行为品性,看似有限、不甚丰盈的体貌形象,却留给读者无限延伸、立体开拓的诗美意境。
不同于对贾雨村、贾环这类迂腐文人的外貌描写,主人公宝玉出现时,文本以“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4]48之态极尽工笔渲染。紧接着又以《西江月》二词中“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4]49来表现主人公对封建制度的大胆叛逆和对个性解放的坚定追求,在貌与情上都达到了诗化的统一。曹雪芹将这样一个形容清俊、灵性洒脱的翩翩少年悄然放置在刻画入微、如梦如幻的诗画语境中,饱含超脱世俗功利的浪漫主义倾向,更以正面人物的神韵风流向读者展示科举制度下的鄙俗小人是何等丑陋。
除了人物外貌方面的表现差异之外,二文关于知识分子命运走向的语言叙述也有所区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吝啬鬼之一,严监生是《儒林外史》中一个极为特殊的知识分子:“家有十多万银子”[3]55却连猪肉都舍不得买;家中妻子也因常年营养不良、操持家务而早亡;自己病重后不愿花钱买人参,反倒“每晚算账,直算到三更鼓”[3]62。就算在弥留之际,严监生也不忘正在燃烧的两茎灯草,直到挑去一根,他才安然闭目。小说最后对严监生“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3]65的情节描述,更以现实锋利之话语笔刃,将这个爱钱胜过惜命的悭吝人形象深刻人心。然则文本意图却并不满足于此,科举体系下允许这类毫无才学又品性贪婪之人,靠着祖上荫庇或钱财捐赠就得以入监读书的现实,才是对科举制本身和中下层文士最大的嘲讽与冲击。
《红楼梦》在描写宁国府太爷贾敬的命运情节时,以一句“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脱去皮囊,自了去也”[4]880点明其服食丹砂而亡的结局。作为贾府唯一一个乙卯科进士,贾敬并没有通过科举出仕来治国理家,却是“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4]27,纵容贾珍等人毁家败业。对这样一个于国于家无功且终日贪求长生之道的举业进士,作者显然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但文本却以功行圆满、羽化升仙的委婉措辞来掩盖贾敬离奇荒诞、死相惨状的了局,这种表里反差一则能够使读者获得回避死亡、向往仙幻的审美愉悦,二则也更加揭露出贾敬因无限膨胀的个人欲念而摧毁本身的丑行。身为权贵子弟,贾敬早已跨越常人对功名富贵的渴求,希冀通过炼丹制药达成福寿绵延的永恒目的。小说最后以肉身毁灭取代荣华永生的情节设置,正是对这类避世绝俗、贪心不足的腐儒的极大嘲讽。
小说在处理贾雨村的命运结局时,除了交代“褫籍为民”的最终下场之外,还给予读者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文本对这一人物的结局叙述在“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这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4]1600的情景中戛然而止,对比贾雨村仕途得志时“恃才侮上”的丑恶嘴脸,这番超尘脱俗、婉曲空灵的意境描写,更能给读者带来诗意美的观感愉悦。曹雪芹以这样一种无声且诗化的话语表现形式,立足于内在精神危机和外在官场黑暗的批判视角,对科举制的现实迫害发出了最哀鸣的反抗与控诉。
综上所述,同为创作于十八世纪中期的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与《红楼梦》虽然在作者经历、空间地域和科举批评意识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对于批判封建科举制度来说,二者还存有诸多差别。吴敬梓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态,平静深沉地嘲讽着科举制度下形形色色的单一个体,但他的尖锐抨击却在小说结尾戛然而止,这或许是对曾经同样遭受过科考挫败的自我的灵魂救赎,又或许是对儒林后生的辛酸与悲悯,他最后选择了妥协与谅解,并透过写实、直叙的语言文字将这份“含泪的笑”传递给世人。而作为与科考并无直接联系的旁观者,曹雪芹对明清科举制的批判可谓丝毫不留情面,他将这种犀利尖刻的内心话语,深深隐匿在诗意化的文字外表之下,从不同人物之间的对立冲突中,窥视到科举正统带来的重重祸害,最终达成彻底否定封建弊制的主旨目的。正是由于二者这种差异互补,才让后人更加深刻地理解明清两代不断走向衰落、僵化与黑暗的科举制,而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极高成就的《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以其各自独有的价值与魅力,也足堪恒久屹立于世界经典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