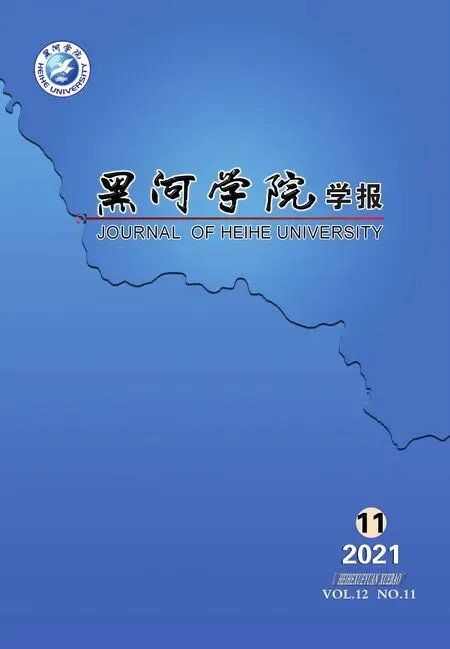论《尚书·洪范》中“五行”的思想意涵
迟希文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在中国思想史上,五行学说乃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尚书·洪范》作为中国早期的政治文献,提出了统治者所应遵循的九类施政法则——洪范九畴,且洪范九畴之首即为“五行”。因此,当论及五行学说的发展脉络时,《尚书·洪范》便是一篇不可忽视的材料。本文即拟通过对《洪范》中“五行”的思想意涵进行分析,借以廓清《洪范》“五行”在五行学说发展史中的定位,这实际上也对解决《洪范》的创作年代问题有所裨益。
一、洪范九畴的内涵包括“天”与“人”两面
西周初年,新兴王朝的贵族在总结反思殷周革命的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观念——天命观。所谓周人的天命观,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将其主体思想概括为“夏商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不能‘敬德保民’因而丧失了天命;而周所以兴起,是因为文王能够‘明德保民’,因而上帝授命于周,令周代商统治四方。”[1]冯友兰先生亦提出在周人眼中“天”的好恶赏罚有着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老百姓的愿望和统治者的‘德’。”[2]徐复观先生则对周人的天命观评价道,“于是天命(神意)不再是无条件地支持某一统治集团,而是根据人们的行为来作选择。”[3]要之,周人的天命观,既在“敬天”的同时,又要“明德”“保民”,其思想内涵包括“天”与“人”两面。
回到《洪范》的文本,可以发现其中问答的双方——周武王与箕子,正处在西周初年这一时期。因此,不妨以对西周初年天命观的认识作为知识背景来分析洪范九畴的内涵,考察其中是否包含组成西周初年天命观所必须拥有的“天”“人”两面。而欲分析这一问题,则首先需要考察《洪范》开篇的叙述,兹录于下: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4]297-298
在这一段武王与箕子的对话中,武王先提出“惟天阴骘下民”,《尚书正义》载马融释“阴”为“覆”、释“骘”为“升”,而伪孔传则释“阴”为“默”、释“骘”为“定”[4]297,参看《史记》可以发现史迁的记载中亦以“骘”作“定”[5],本文兼采之,以为此句意即“天荫覆安定民众”。这里武王在向箕子问政前先以“天”为引,已经多少体现出下文的洪范九畴是与“天”有着关联的。而在箕子的回答里,“天”的内涵更加显露。箕子说鲧因为在治水过程中“汩陈其五行”,即指鲧以堵塞的方法治水,结果使五行的规律扰乱了,而此处所说的规律指的便是五行畴中谈及的“水曰润下”[4]301这一点,即水总是自然地从高处往低处流动继而润泽万物的特质。最终,鲧对五行规律的扰乱导致“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的严重后果。而到鲧的儿子禹时,其用疏导的方法治水,这一措施顺应了五行的规律尤其是上文提及的“水曰润下”这一特质,所以“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此处即直言人间能否得赐洪范九畴是与“天”有着密切关系的。但也应注意到,在“天”之外,《洪范》开篇这一段话同样体现出洪范九畴拥有着“人”的内涵。可以看到,武王在问话中向箕子表达了“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的深切忧虑,所谓“彝伦攸叙”的解释古今学者说法颇多,本文参考屈万里先生的看法,认为其意为“恒常的道理”[6],指的便是人间君主为顺天安民所需要制定的治政法则。总之,不难看出武王的问话在“天”的背景下又带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性,即武王的问话是兼具“天”“人”两面的。因此,下文箕子的应答中所讲的洪范九畴既然是为解决武王的问题而提出的九类政治法则,其内里自然也应包含“天”与“人”这两面。
在得出这一初步结论的基础上,便不妨把本文主要讨论的洪范九畴中的第一畴“五行”先搁置不谈,来考察一下其余八畴是否与“天”“人”均有着联系。首先,上文已经述及洪范九畴是箕子为回答武王的现实关切而言说的九类政治法则,其拥有着鲜明的现实政治取向,此中包含着“人”的一面是不待多言的。故而,这里所需考察的乃是“五行”外其余八畴是否在指向人世的同时,又与“天”有着联系,如果有,其中的“天”又具体是什么含义?对此的考察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洪范九畴中“天”的内涵。
其实,在先秦至两汉时期的思想家那里,对“天”的认识可以分为很多种。例如,在殷人眼中,“天”或者说居住于天上的“帝”乃是绝对的主宰,殷人无事不占问以至于后世称之为“率民以事神”[7]485,其对“天”的崇拜乃类似于一种原始宗教;到周人那里,对殷商革命的历史思考衍生出了本族独有的天命观,与殷商时人相比,周人天命观中“敬天保民”的观念固然使人的地位得到提升,但毕竟没有完全否认“天”的权威,不能不说周人的思想中仍包含着对“天”的崇拜;至春秋晚期,孔子罕言“天”,其并不直接否认“天”对人世的支配性,但对“天”是否是儒家道德的源泉这一问题则是存有疑虑的;再至思孟学派,则大讲“天命之谓性”[7]1422,这一派学者认为“天”正是儒家道德背后的依据;其后的荀韩一系却对此不以为然,荀子倡“制天命而用之”[8]317,韩非则在言“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9]146后说“天得之以高”[9]147,不难看出,荀子、韩非认识的“天”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天,与人间的道德伦理没有关系,更不是万物的主宰;再看先秦道家,老、庄都讲“天道”,认为“天”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人要做的只是服从、顺应这种“天道”,这便是先秦道家思想中的“天”;等到战国之世终于秦,秦亡而汉兴,至武帝时乃听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董子的儒学体系实际已带有神学倾向,其后灾异谶纬学说大盛,汉儒眼中的“天”于是带有了一种宗教的、神启的性质,成为能够完全支配人间的力量。由此可见,“天”的内涵不是单一的,洪范九畴中的“天”的实际也体现了这一点,除第一畴“五行”外,余八畴中:第二畴“五事”讲君主的五种行为标准,第八畴“庶征”讲各种灾异的征验,两者之间是相配合的关系,君主行“五事”符合相应的标准,则“天”有“休征”,若君主的行为与标准相悖逆则“天”有“咎征”,这里“天”的内涵体现为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其与周人的天命观在逻辑上其实也是颇为相近的,即表现出善行人事方能顺天的观念;第四畴“五纪”讲五种纪时方法,古人观天以测时,这里“天”的内涵表现为自然天的观念;第七畴“稽疑”讲卜筮决疑之法,卜筮以观天意乃是殷商时便已十分盛行的传统,这里“天”的内涵体现为对“天”的崇拜;第九畴“五福”“六极”则指五种幸福与六种困厄,体现出“天”降祸福以儆戒、劝勉君王的观念,其背后的天人逻辑实际亦与周人的天命观相合;此外,第三畴“八政”指建立八种职官之长,第五畴“皇极”讲做君主的要道,第六畴“三德”讲君主的三种驭人之术,此三者表面看去似与“天”无关,但若将之置于周人的天命观下,视之为人间君主为顺“天”而必须做好的人事,亦未尝不可。总之,通过对洪范九畴中除第一畴“五行”外其余八畴的简要考察,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天”与“人”这两面。
在《洪范》文本之外,一些材料也可以旁证洪范九畴有“天”与“人”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史记》,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尚书》,其在撰述《史记》时自然也会以《尚书》作为叙述上古历史的基本史料之一,如在《周本纪》中,史迁这样写道:“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5]应有理由相信,此处正是史迁据《洪范》所记转写。而在这段记载中,武王询问箕子的最初指向是很明确的,即问“殷所以亡”,也就是询问强盛的商国灭亡的原因,寻找商周易代的合理解释,其人世政治的取向是十分鲜明的,目的正在于使新兴的周王朝不至于重蹈殷商灭亡之覆辙。箕子闻武王此问后,则因为“不忍言殷恶”故而“以存亡国宜告”,张守节释此句为“箕子殷人,不忍言殷恶,以周国之所宜言告武王。”[5]可见,箕子自然明白武王问询之意,武王问败国何以亡,而箕子则回答治世何由兴。总之,在史迁的记载中,无论是武王之问亦或是箕子之答均含有鲜明的“人事”一面,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后一句话,即“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箕子为商之王族,武王亦觉直问其故国灭亡之原因实有欠妥,因此,不再问“殷所以亡”而是改问以“天道”,即人间的君主如何顺应天道治民的问题。而正因为武王问询策略的变化,箕子也便不用直言其故国之恶,遂得以顺理成章将来源于“天”的洪范九畴这一政治法则用来回复武王之关切,其背后带有“天”的意涵当然也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可以说《史记·周本纪》的这段记载也为洪范九畴具有“天”与“人”这两面作了一旁证。
除《史记》外,后世经学家对洪范九畴的解释也体现了其中“天”与“人”的两方面内涵。如郑玄释“不畀洪范九畴”为“不予天道大法九类”[10],即释“洪范九畴”四字为“天道大法九类”,这“天道”即体现出洪范九畴之“天”的一面,而“大法”即人间之大法,意为统治者所须遵行的政治法则,其指向是人世的,体现的乃是洪范九畴之“人”的一面。与郑玄的解释类似,伪孔传释“洪范”二字为“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4]297不难看出,其解释中同样包含了“天”与“人”这两面。
总之,本节从《洪范》原文中有关洪范九畴这一人间政治法则来源于上天的说法进行切入,又通过考察发现除“五行”外其余八畴也均拥有着“天”与“人”的双重面相,后又以其他史料作旁证,基本确定了洪范九畴有“天”与“人”两方面的内涵。下文则将以此结论作为理解洪范九畴中第一畴“五行”的背景,对《洪范》中的“五行”所具有的多重思想意涵进行分析论证。
二、《洪范》“五行”中的天道、政治与民生
洪范九畴的内涵带有“天”与“人”这两面,那么以此为背景再看《洪范》开头武王与箕子的问对,便不难发现“五行”在箕子回答中的关键地位。即鲧“汩陈其五行”导致“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而禹则顺应“五行”,因此,“天乃锡禹洪范九畴”。由此可见,人间的统治者是否能从上天得赐洪范九畴这一治法的关键则在于其能否顺应“五行”的规律,“五行”在其逻辑中的的关键性是十分清楚的。既然洪范九畴有“天”与“人”的两方面内涵,那么作为人间能否从上天得到这一治法的关键点“五行”,当然也可以说其与“天”“人”两者都有着联系,笔者将对《洪范》中的“五行”观念所带有的这“天”“人”两种面相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来谈《洪范》“五行”中“天”的面相。笔者以为,《洪范》“五行”中的“天”体现的乃是一种“天道”的思想意涵。人间的统治者能否从“天”那里得赐洪范九畴这一治法的关键正在于其行为是否能顺应“五行”的规律,而在鲧、禹治水之事中,这一规律具体所指便是水的“润下”特质。毋庸置疑的是,在今人看来,水由高处向低处流动当然是一种可以得到科学解释的物质性的规律。但实际上,这样一种规律在古人眼中就可以被称之为“天道”,笔者即以思孟学派的学说为例来对古人的这一思想观念进行阐发。当人们翻开《中庸》,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天命之谓性”,孟子又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11]295,可以说,在孟子看来“善”是人从“天命”之中禀受的普遍“性”,人性之“善”与“天”有关,那么“就下”当然也可以被认为是水从“天”那里禀受而来的“天道”。思孟学派的另一篇著作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古人的这一观念,即马王堆帛书中的《五行》,其主要讲的是“仁、义、礼、智、圣”的“五行”说。在郑玄为《中庸》作的注解中有这样一句话:“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7]1422,其中将“木、金、火、水、土”与“仁、义、礼、信、知”联系起来,这里的“仁、义、礼、信、知”与帛书《五行》中的“仁、义、礼、智、圣”大体类似,李学勤先生认为,两处均指思孟学派所造之“五行”说[12],而荀子批评思孟学派时所说的“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8]94也正是指此而言。那么就可以说,思孟学派在“木、金、火、水、土”这旧“五行”说的基础上创造了“仁、义、礼、智、圣”的新“五行”说,而“仁、义、礼、智、圣”则是指人的道德品质而言,其与人之“性”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便能够推论,“木、金、火、水、土”这一旧“五行”说在思孟学派那里以“仁、义、礼、智、圣”的新“五行”说作为媒介,进而与人之“性”产生了间接的逻辑关系。清楚了这一点,便可以回答孟子所说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一句中,人性之“善”与水之“就下”为何并列提出及这两种属性背后与“天”相关的逻辑理路为什么会是相近的这两个问题。总之,通过对思孟学派这一逻辑的考察,可以认为,在古人的认识中无论是人亦或是其余的世间万物,其都很难撇清与“天”的联系。因此,当人们理解古代文献中所说的水的“润下”“就下”这一特质时,便不能用现代人的视角将这种表述理解为自然物质性的规律,而是应该通过代入古人的思想观念,来体会其中所具有的“天道”意涵。
另外,当考察《洪范》第一畴“五行”的完整叙述时,也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这种规律性的“天道”包含着哪些内容,兹将原文录于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4]301。
在这里,“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是“五行”各自表现出的不同的性质,这种性质在现代人看来均是自然的、物质的,但正如上文所说,其在古人眼里乃具有深刻的“天道”意味。同样,五种性质衍生出的“咸”“苦”“酸”“辛”“甘”五种味道当然也可以看做是“天道”规律的一部分。总之,《洪范》“五行”中“天”的面相乃是体现为规律性的“天道”意涵。
而探讨完《洪范》“五行”中“天”的面相所体现的思想意涵后,还需讨论的便是《洪范》“五行”中“人”的面相又包含着何种思想意涵。
毫无疑问,《洪范》“五行”所指的“水”“火”“木”“金”“土”乃是现实存在的五种自然物质,其拥有着人世面相是不言自明的。而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通过对“五行”的人间用途进行分析,便可以看出其人世面相中乃包含着“政治”与“民生”两种不同的思想意涵。当人们以“水”为例作为分析“五行”人世面相的切入点,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人如果离开“水”便彻底不能生存,“火”“木”“金”“土”则不具有这一特殊地位,那么就可以说在最早的“五行”观念中“水”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其事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故其长久拥有与民生相关的特质是毋庸置疑的。在此之外,“水”于民生的作用还有很多,例如,当人们务农时水被用于灌溉,行船交通时江河湖海是舟船的载体。总之,“水”于民生而言是不可须臾缺少的。但同时还应认识到,在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外,人也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荀子曾说人与牛马的一个区别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8]164,这里所说的“群”是指人的社会属性而言。正因为人具有社会属性,早期的人类便会逐渐结成一个个游团、部落、酋邦以至于最后形成国家,人的政治意识也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增长。因此,便可以推论,初民最早对“水”的认识仅限于民生,但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复杂化,人对“水”的认识遂逐渐与政治相关联。例如,人类获得水产品最早是为饱腹,但当人类社会组织复杂化后,这个组织内的统治者便会意识到要对水产品进行符合“天道”规律的管理,如若管理不善即会造成竭泽而渔的后果,孟子的政治构想中就有“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11]9的说法,其体现的正是人间统治者需要对水产品进行有序管理的思想,而这一思想的背后则正现出“五行”中的“水”与人间的政治已然拥有着密切的联系。总论之,“水”的人世面相乃是包含着“政治”与“民生”两种不同的思想意涵。
而在“水”之外,其余“火”“木”“金”“土”的人世面相所表现出的思想意涵同样如此。例如,“火”使人联想到人工取火技术,“木”使人联想到丰富的山林产品,“土”使人联想到早期的农业种植,初民对此三者的利用都在出现较成熟的政权组织与政治意识之前,这正体现出三者的人世面相中所包含的“民生”意涵;而当文明时代来临以后,“火”“木”“土”这三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便与人间的政治产生了联系,以至于后世流传的古史传说中便有了所谓“火正”“木正”“土正”[13]1506-1507的说法,而这“火正”“木正”“土正”即分别指掌管“火”“木”“土”的官员,这一说法反映出在文明时代早期,当时的人间统治者便已经认识到对“火”“木”“土”的管理乃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正体现出三者的人世面相中所包含的“政治”意涵。但对于“五行”中的“金”,则需要指出其与上文所述的“水”“火”“木”“土”有所不同,因为“金”的最初所指乃是用作制造祭器、武器的青铜,而并非在春秋战国以后与农业生产发生普遍联系的铁,因此,其与“民生”的关系在春秋以前似乎并不紧密,且“金”之所以被列入“五行”之中乃是由于商周时期有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3]755的观念。因此,“五行”中的“金”似乎只与政治相关,而与民生关系不大。但笔者以为,就与“金”有着密切联系的“祀事”而言,君主在祭祀的过程中是免不了要向众神、祖先祈福避祸的,而一个国家无论是得到赐福还是遭遇祸患,国家内的民众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戎事”也同样如此,在部落或早期国家的互相争斗中,如果一方没有足够的军事抵御能力,其自然难以避免灭亡的命运,对于这个组织内部的民众而言,无疑将遭受深重的灾难。因此,即使是“五行”中较为特殊的“金”,其人世面相也同样包含着“政治”与“民生”两种不同的思想意涵。
总之,《洪范》中的“五行”观念拥有着“天”“人”两种面相,其“天”的面相体现为“天道”意涵,其“人”的面相则表现为“民生”与“政治”双重意涵的结合。因此,《洪范》“五行”的思想意涵乃是包括天道、民生、政治三个方面。
三、《洪范》“五行”在五行学说发展史中的定位
《洪范》中的“五行”观念包括天道、政治、民生三方面的思想意涵,这一结论也将成为本文探索《洪范》“五行”在五行学说发展史中定位的一把钥匙。而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则不妨先对五行观念的早期发展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毫无疑问,在先民的最初认识中,“五行”只是五种可资利用的物质,故而此时的“五行”当然只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物质性观念;至西周末年时,史伯则提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14]的说法,这里所说的“五行”便具有了构成世界的“元素”意味,其与最初的纯物质性认识相比,已经体现出了抽象化发展的趋势;再至战国晚期,齐人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其中所蕴含的是五行相胜思想;及至汉武帝时,董仲舒则提出了五行相生的学说[15]114;而实际上,在神仙方术、灾异谶纬等神秘学说大为流行的汉代,当时的儒家学者,如夏侯始昌、夏侯胜、许商、刘向、刘歆等人更是对《洪范》中的“五行”观念进行了大规模的神秘化阐释[15]112-113。而且颇为值得一提的是,汉儒的这种阐释不仅是将《洪范》中的“五行”观念神秘化了,甚至也将整个洪范九畴都作了神秘化的处理,如东汉学者马融在为《洪范》一文作注时便说“从‘五行’已下至‘六极’,《洛书》文也”[4]299,即认为洪范九畴乃是大禹时代洛水神龟驮出的《洛书》中文字。总之,“五行”由最初的纯物质性观念发展到西周末已有抽象化的趋势,而到两汉时更是已经被神秘化。那么,“五行”观念在思想演变的过程中何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就成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洪范》“五行”中的“天道”意涵便是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关键线索。因为当人们试图将《洪范》中的“五行”观念在五行学说发展史中进行定位时,便不难发现其虽然拥有着“天”“人”两种面相,但这两种面相所包含的三方面思想意涵——天道、政治、民生,均不是抽象的、神秘的。在三者之中,“民生”意涵、“政治”意涵所面向的乃是人世,与抽象、神秘无关自是不待多言;而即使是听来颇具神秘气息的“天道”意涵,实际所指在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五行”的自然规律,因此,其同样也不是抽象的、神秘的。但同时也应指出,《洪范》“五行”中的“天道”意涵毕竟与古人眼中神秘的“天”有关,因此,其自然也为后世五行学说的抽象化、神秘化发展留下了一个思想诱因,并最终使“五行”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物质属性被掩埋在各种抽象的、神秘的阐释理论之下。而在廓清了五行学说的这一发展逻辑后,也就可以进一步推论,《洪范》中的“五行”观念应是至少产生在西周末年对“五行”进行抽象化阐释以前。而对于《洪范》创作年代这桩聚讼不已的公案,也多有学者指出应将之定于西周时期[16],这也与本文对《洪范》“五行”在五行学说发展史中的定位意见可谓不谋而合。
——《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