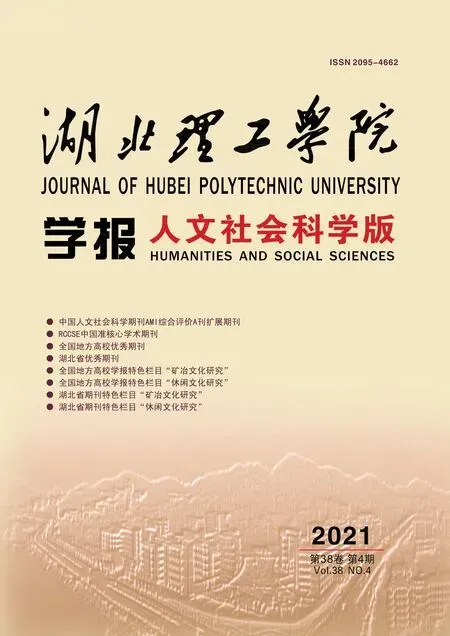鄂东南铜矿采冶与早期国家演变问题初析*
陈树祥 陈 晨 陈一鸣
(1.湖北理工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2.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71)
鄂东南主要包括今鄂州和黄石两个地级市域,这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矿冶文化底蕴厚重。然而,鄂东南冶金术萌兴与江汉地区史前遗址关系、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冶金术萌兴对本区域早期文明社会暨国家起源和演进等问题,皆是个谜团。本文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试作初步探析。
一、鄂东南矿产资源特征
本文所谓鄂东南,特指鄂州市和黄石市地域,其在晚唐之前为一个行政地域,早期区域的政治中心位于长江南岸的今鄂州市鄂城区的西山一带,三国时期这里是鄂县(武昌)治所,一度成为孙吴之都城、战略要邑,“一江天堑,……嘗为重镇”,“其地襟江沔,依湖阻山,左控淝庐,右连襄汉”[1]。晚唐的吴国,将鄂州东南部矿产区单列为青山场院。宋乾德五年(967年)南唐后主李煜升“青山场院”,并析武昌(今鄂州)三乡与之合并,在今鄂州东南边设置大冶县。此后,鄂州地域在历朝更替中不断缩小,逐渐成为今天国土面积为1 594平方公里的地级市[2]。1949年之后,黄石在大冶县的黄石港和石灰窑镇基础上升为长江南岸的地级市。鄂州也在鄂城县基础上升为地级市,其建市晚于黄石市,成为并立于长江中游南岸的两座矿冶城市,构成“冶金走廊”。古今鄂州和黄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属一个矿冶文化的共同体,诸如两地矿产资源同属长江中游鄂东南矿脉带。经勘探,鄂东南大中型矿床多集中分布于今鄂城—大幕山主干隆起带上,矿化类型由西北至东南呈现铁—铁铜—铜铁—铜—铜钼钨的有序分布,硫及硫铜矿的矿脉带呈弧形分布于两侧,铅锌矿化带大致向北突出的弧形作不规则分布。除铅锌矿床外,各矿带矿体皆位于接触带上。已探明本地域金属等矿床(点)达700余处,其中,大型铁、铜矿床5处,中型铁、铜矿床17处,小型铁、铜矿床37处,且都伴生有金、银等金属矿床[3-4]。如,铜绿山蕴藏12个铜铁矿体,有的埋藏浅,有的出露地表,氧化程度高,铜矿中的孔雀石、铁矿石祼露地面或矿山断面,成为古人寻找铜矿脉指示物。矿山之下皆有河湖环绕,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生活在这里的古人釆冶、运输等提供了条件。
二、鄂东南史前遗址及跨入文明社会因素认知
从本区域史前文化发展脉络观察,黄石和鄂州地处长江中游交通要道上,自古就是东西和南北文化的一个交汇地带,不同时期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经考古调查,鄂东南分布有新石器时代遗址76处(其中,黄石城区9处、大冶32处、阳新23处、鄂州市12处)[5]。迄今为止,在黄石市经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有黄石港区鲶鱼墩遗址[6]、阳新大路铺遗址[7]、大冶蟹子地遗址等[8],发掘的矿冶遗址有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9]。遗址中,最早见有薜家岗文化,稍晚有自西向东扩张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后石家河文化,商周时期本区域演变为大路铺文化[7]。目前,这里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了冶铜遗存,预示本区域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开始采冶铜矿。今鄂州境内发现的先秦时期聚落遗址多达51处[5]、矿冶遗址17处[10],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有12处。但是,鄂州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未进行考古发掘,从部分遗址位于铜铁矿山附近现象看,不排除某些遗址亦有相同时期的冶铜遗存。
青铜时代,铜矿料既是一种财富,也是国家“祀与戎”铸造礼乐兵器不可缺少的原料,无疑成为政治集团增强实力和扩张的战略物资。冶铜术从发明到发展到一定生产规模,经历了漫长岁月。从技术层面上看,应是在制陶业基础上技术积累而发展起来新型手工业。从后勤保障看,如果没有农业发展,没有生产剩余粮食、产生铜粮商品交易条件,铜矿冶难以发展成专门的手工业。由此看来,铜矿冶的萌兴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程或变革的助推器,也是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关于判断古代文明社会的标准,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于1958年提出。此后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者格林·丹尼尔在所著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中进行补充,成为主流观点。此标准共三条: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五千人以上的人口;第二个条件是文字;第三个条件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由于古代遗留的信息很少,一般认为只要有两条就够了,而在两条里面,文字是不可或缺的,有了文字再有其他的一种,就可以认为是文明社会了。中日部分学者认为这三条标准欠妥,提出了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也是判断上古文明社会的标准。事实上,若以文字为基本标准,选其三种标准任意一项,作为判断华夏新石器时代何时进入文明社会,均有失偏颇。如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在城内发现8座祭祀坑,出土文物叹为观止,反映了较高文明程度,但至今没有发现文字,是否就不认同三星堆人群没有进入文明社会?显然早期文明社会或国家出现,存在多元因素的政治实体。鄂东南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遗址,尚未发现城垣和文字,有着什么样的文明程度呢?如阳新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文化第二期发现和发掘了6座小型土坑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反映了贫富差距的社会现象。该遗址在石家河文化第二期发现冶炼坩埚残片,显示遗址上铜矿冶炼活动。铜矿采冶肇兴,既是一个科技发明,又是一个复杂技术生产体系,需要髙层的组织与支持,这实际上折射出政治实体的组织形态。大冶蟹子地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中发现大量碳化稻米[8],说明农业较为发达,这为铜矿业从农业、制陶业中分离提供了生计保障。鄂东南新石器时代诸遗址所处地形地貌有其独特性,诸如阳新大路铺遗址、大冶蟹子地遗址、大冶香炉山遗址等[11-12],均坐落于矮丘或较高的土墩之上,周围溪河环绕,这种高台深水之地势,如同古寨邑,既可抵御洪水威胁,又可防范外族入侵,具有双重防御的功能,其与江汉平原发现的人工修筑的史前古城垣和护城河的功能相比较,作用殊无二致。综合前述四个因素,鄂东南聚落遗址族群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可能跨入文明社会。
三、鄂东南史前与江汉平原的关系
鄂东南地处石家河文化东南边陲,是石家河文化的一个新类型,其族民进行铜矿采冶活动,其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核心地区存在什么关系呢?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时期除分布密集聚落遗址外,发现有12座史前古城分布其间[13],其中,以石家河文化时期古城为多,暗示石家河文化时期发达的社会文明程度。其实,比石家河文化更早的屈家岭文化乃至油子岭文化时期均发现了城址。如天门龙嘴城垣为油子岭文化时期营建,距今5 500多年。与古城垣同时或比城垣更早的一种现象,是在城址及附近的一些遗址上发现了孔雀石及冶铜遗存。具体而言,在天门肖家屋脊、邓家湾、殷戴家湾、罗家柏岭,荆门市屈家岭一百三十亩遗址、屈家岭遗址,随州金鸡岭遗址等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遗存中发现了铜矿石(孔雀石)和冶炼遗物。关于孔雀石来源问题一直是个谜团,学者们将调查和诠释视野或投向大洪山,或投向铜绿山。大洪山地区矿产资源勘探资料表明,这里分布了一些铜矿点,但因埋藏深、氧化程度低,矿量少,开采成本高,多数未列为现代开采项目。其中,数个铜矿点在现代开采中,也未发现史前开采的遗迹,因此,笔者曾推析出距今4 600年前后,江汉平原部分城址和遗址内出土的孔雀石极有可能从铜绿山及周边铜矿山输入的观点[14]。此后,天门龙嘴南城垣中部TG2第⑤层出土了一块孔雀石,城垣修筑于油子岭文化晚期,为公元前3650—公元前3350年[15]。但这块孔雀石的采掘时间应比龙嘴城垣营建时间早,推测为油子岭文化早期的遗物,这是迄今为止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最早的铜矿石。因此,有的学者推测这块孔雀石采掘时间大概距今6 000年,进而将上述发现于长江中游地区、时间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遗址出土的矿冶遗存与黄河流域等进行对比,提出了“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观点[16-17]。显然,这些观点亟需考古和两地铜矿检测数据的印证。检视鄂东南铜矿地带考古发掘发现的遗址,其年代最早有鲶鱼嘴遗址、大冶香炉山遗址,发现最早的考古学文化为薜家岗文化中晚期遗存[11,6],距今5 500~5 300年;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新石器时代不晚于距今6 000年[18]。鲶鱼嘴遗址虽然发现薜家岗文化遗存,但考古材料仅见零星报道,没有发现铜矿冶遗物资料,也期待今后考古发掘印证。
上述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铜矿石无疑是古人对铜矿资源的认知,而规模化的冶金活动,反映文明社会的组织与有效管理。与铜矿采冶发明的另一个更大的智慧工程,即古城的修建,更需政治实体的有力动员和组织才能完成,或者可认为古城无疑是一个古国的政治中心——都邑。由此看来,从天门龙嘴城垣的兴建与使用,可推测油子岭文化晚期跨入了早期的中国的“古国”时代,龙嘴古城所处的江汉地区,应进入了早期中国文明社会。
四、鄂东南考古学文化与古国产生的内在关系
鄂东南地区最早开拓者是薜家岗文化时期的族民,他们来源于今皖西,大概距今5 500年左右。距今5 200年左右,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的族民东进本地区,薜家岗文化从此消失。距今4 350年左右,强盛的石家河文化覆盖这里。然而,鄂东南发现的薜家岗文化,囿于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其社会文明程度尚不太明晰。本地区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皆来源于江汉地区的传播,考虑到本地区发掘的遗址出土工具基本为磨制石器,虽然发明了冶金术,但未发现青铜工具,因此,只能确定为铜石并用时代。由此推测,在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里的社会进入了古国阶段。
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前后发展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学术界对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所对应民族问题的讨论基本达成共识,一般认为这两种时代不同文化是三苗集团(或称“苗蛮集团”)创造。三苗集团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很大,诸如《战国策·魏策一》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正义》云:“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南与青草湖连;彭蠡湖名,在江州当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以西为左,彭蠡以东为右,今江州、郑州、岳州三苗之地也。”《尚书·地理今释》云:“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显然,鄂东南为三苗集团的势力范围。从考古资料观察,与三苗集团聚居地相对应的聚落遗址,既显示出遗址大小不同的差异性,也反映出文化发展与变化的连续性,一般而言,这里遗址上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少,目前仅在鄂东南鲶鱼咀遗址上层、大冶香炉山遗址、鄂州华容区和尚山遗址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存,多数新石器时代遗址见有石家河文化遗存。经初步统计,本区域发现的76处遗址中,根据遗址现存面积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遗址面积达80 000 m2以上的,有黄石铁山区李家院遗址(面积160 000 m2)、阳新大路铺遗址和大冶龟山遗址(面积皆为80 000 m2),其附近还分布一些较小的遗址。第二等级,遗址面积在20 000~50 000 m2的,有阳新王鹰咀遗址,鄂州梁子湖区大城垴遗址和三墩子遗址,大冶的老猪林遗址、三角桥遗址、三房众遗址、夏边林遗址、张家墩遗址、铁铺山遗址、茅陈垴遗址、摇罗山遗址,阳新和尚垴遗址和观音垴遗址。第三等级,面积在20 000 m2以下,这类遗址数量最多,有大冶蟹子地遗址和香炉山遗址、鄂州鄂城区富家畈遗址等[5]。多数遗址坐落于山丘或土墩之上,距周边地表高3 m以上,遗址均被河港环绕,呈现古城之态势。少数大中型遗址之间相距较远,有的发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铜矿冶遗物。由此推测,少数大中型遗址,可能是某些古国政治中心。
五、鄂东南传记中古樊国、鄂国兴亡之推测
鄂东南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受到中原文化强烈冲击和影响,这里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概在距今4 000年前后,中原南下的龙山文化晚期煤山等类型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碰撞融合,形成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注:亦称“三房湾文化”[19]“肖家屋脊文化”等),其时代相当于夏纪年。鄂东南调查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后石家河文化遗存,如阳新大路铺遗址石家河文化第二期2段出土陶鼎、甑、罐、壶、瓮、盆、缸等,这些器类可以在鄂西宜昌白庙子、天门肖家屋脊、黄梅陆墩等遗址所出土同时期陶器中找到相同或近似的器型。特别是阳新大路铺遗址第⑦层后石家河文化中,出土了青铜器残片[7];大冶蟹子地遗址后石家河文化发现了孔雀石和碎矿工具[8];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发现了一座夏时期墓葬,有趣的是该墓葬壁龛中随葬1件陶鼎足、3块铁铜共生矿石[9]。阳新大路铺遗址后石家河文化遗存中发现青铜器残片等,说明这里进入青铜时代,或许暗示鄂东南古国进入方国时代。关于方国之名,一直是一个学术谜团。
2004年重刊光绪十一年的《武昌县志》记载:今鄂州“唐为樊国、帝尧时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夏为鄂都……”[1]。这是地方志记载鄂东南最早的两个方国。但是,学术界对于樊国关注度很轻淡,基本持否定态度,这可能与文献记载极少、未发现樊国遗存等原因有关。关于樊国相关地名,仅有鄂州市鄂城区“樊山”“樊口”和“樊湖”之遗名,“樊山”即今鄂城区的西山;“樊口”指鄂州市长港流入长江交汇处,百里长港南连梁子湖(樊湖)和大冶保安湖,保安南畔一带就有许多铜铁矿山。由于鄂州城区70多年的现代城市建设,其地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樊国、鄂国之城邑的踪迹难寻,成为历史公案。从“帝尧时有樊仲文”之文意,以及《左传》昭公元年曰:“虞有三苗”,《吕氏春秋》内引文说:“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等蠡测,若樊国、鄂国之说的文献可信,可作以下假设:
首先,樊国立都于今鄂州城区“樊山”附近,扼长江交通之要道,可能是尧舜时期出现的一个方国。樊国之君为樊仲文,臣服尧舜,管理和贡献鄂东南铜矿采冶。樊国国民应是三苗族。
其次,樊、鄂两国此衰彼兴可能与禹征三苗有关,如《墨子·非攻(下)》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霄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官,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祇,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说苑·贵德》亦云:“昔三苗氏……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之不修,禹灭之。”禹征三苗打着 “德之不修” 旗号,征伐之履到达三苗族团势力范围,樊国或许叛夏,亦或不进贡铜料等原因,遭到夏禹征伐。从此,鄂东南樊国及三苗族衰亡。有学者认为,禹征三苗给古百越一支(即扬越族团)北进赣西北及瑞昌铜岭提供了机遇[20-21]。笔者以为,扬越族团乘机到达了鄂东南地区。此后,扬越人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汉水下游。如《吕氏春秋·恃君》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敞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根据文意,百越(扬越)分布的地区包括了今鄂东南地区。所谓“多无君”说明当初社会文明程度不高,但并不等于扬越人势力变强后没有建立一个国家。《武昌县志》记载,今鄂州“夏为鄂都……”说明至迟在商灭夏之前,扬越人在樊国都邑的废墟之上建立了一个方国——鄂国。然而,关于鄂东南“鄂国”之源流、地望、族属等问题,历来成为学术界讨论热点。目前,学术界形成了“东鄂”和“西鄂”两种主流观点,持“东鄂”之说认为,这里扬越族崇拜长江生长的扬子鱷(鳄),这是鄂州称“鄂”的源头[22];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东鄂”可能为越人所建之国,并非姞姓鄂[23]。笔者认同此观点。诚然,目前鄂东南考古发掘的夏时代遗址中,对夏代的扬越文化特征研究不够,其文化面貌尚不太明晰,这是一个短板。但是,扬越族团在商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身文化特色,这种文化以生活用器占主导因素的陶刻槽足鬲、护耳甗、长方形镂孔豆等一批典型器物为代表[24],这种考古学文化既有别于武汉盘龙城文化,也不同于江西吴城文化,是商代中后期鄂东南地区新出现的大路铺文化[7]。关于这个文化的去向问题,在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可获得些许诠释,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发掘了246座先秦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扬越人特征陶器上限时间为商代晚期,下限至春秋晚期,并融合于楚文化之中[9]。
揣研《武昌县志》记述,鄂州夏时有“鄂都”之语,看来并非空穴来风。扬越族于夏代在这里建国前后,向夏王承担铜矿料的贡赋。如《禹贡》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厥贡惟金三品。”学术界对鄂东南归入荆州或扬州历来存在分歧,但无论哪种观点,夏时期鄂东南生产的铜都是贡品。所谓 “金三品”,一种观点释为金、银、铜;另一观点是“三色铜”即青铜、白铜、红铜。无论哪种观点,“金三品”之中包括有铜应无疑。《禹贡》中将进贡物品和路线记载较为清楚,这大概是夏时期的“金道锡行”,即“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直达夏都。鄂东南铜绿山矿山脚下是大冶湖,东连长江,铜绿山可能是铜矿料的水运输出之起点。
六、小结
综上所析,鄂东南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创造者为三苗族团,是鄂东南铜矿采冶的开拓者,在距今5 200年前后建立了古国。古扬越族团在禹征三苗后进入了鄂东南,融合了衰弱的三苗族裔,建立了鄂国,并继承了三苗族团的铜矿业,向夏商王朝贡赋铜料,在商代形成了大路铺文化,历经西周,春秋时期融入了东进的楚文化。鄂东南萌兴的铜矿冶文化及国家起源演进,既是鄂文化形成的重要内涵和源头之一,又是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