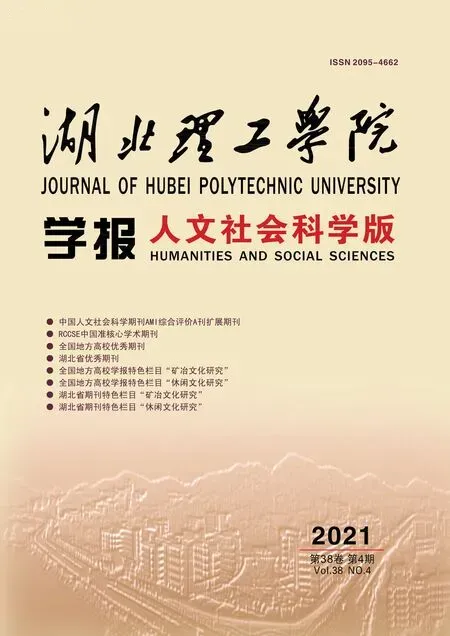近二十年汉冶萍公司史研究述评*
刘 洋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汉冶萍”),是亚洲最早实现机械化生产的钢铁煤联营企业,在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李江梳理了汉冶萍从创立至2005年的研究情况,指出1949年以前的研究侧重公司历史沿革等问题,“资料性较强,学术性则显不足”,1949年以后主要围绕“汉阳铁厂的选址、招商承办、中日合办及失败原因”等展开,“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推进”[1]。李海涛考察了2005—2015年间汉冶萍史的研究进展,提出加快整理相关资料、充分挖掘利用史料等建议[2],切中肯綮。
自2000年以来,汉冶萍史研究成果数量显著增加,且学术性更强,步入了研究的新阶段;2010年前后,李玉勤、李海涛等以汉冶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青年学者相继取得博士学位,为本领域注入了新鲜力量;2014年,湖北大学周积明教授申报的《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课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该团队以此为契机,相继整理了汉冶萍晚清民国报刊、萍乡煤矿档案等基础资料,不但在期刊论文方面屡有斩获,且连续数年稳定地产出了一批优质硕博论文;湖北师范大学成立“汉冶萍研究中心”后,于2014年联合相关单位召开了首届汉冶萍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两届会议分别于2016、2018年在武汉、萍乡召开,这三次会议共收录160多篇文章,汉冶萍史学术生产的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此外,萍乡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萍矿集团也结合地方红色传统刊发了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萍矿相关的论文,重庆市档案馆则依据其所藏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档案研究了汉阳铁厂西迁后的发展情况。除上述三次会议和四大机构外,张实、左世元及李海涛等人在汉冶萍研究上同样用力甚勤,成果突出。
为便于学者们把握学术脉搏,笔者决定以2000年为界,考察21世纪前20年汉冶萍公司史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李江、李海涛这两位学者已对2015年之前的汉冶萍史研究作了精彩评述,且为了显明近年研究的新动向,本文重点关照2016年至今的研究动态,兼及2000—2015年的国内重点研究成果,并简单评介两位学者未曾涉及的部分国外优秀成果。
一、汉冶萍公司整体史
近年来,学者们对公司发展历程、体制变迁、失败原因等传统议题作了更深入的剖析,也开始从历史地理学等新角度探究厂矿选址等课题。
(一)“全程史”的拓展
严格来说,作为股份制商办企业的汉冶萍公司在1908年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合而成,在1928年萍矿被江西省政府接管后,“汉冶萍”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已不成立。但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张之洞等在1890年创办的汉厂,与稍后开办的冶矿、萍矿在1908年合并前虽是独立经营,但三者在资源互助、人事安排等方面的交流相当频繁,体现了一种“在独立中联结”的样态;1928年后,受动乱局势影响,汉冶萍各厂矿分别经历了西迁或被日军占领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公司虽形态不如之前完整,但作为历史实体并未消亡,直至1948年资源委员会接收公司上海总事务所,绵延近六十年的汉冶萍公司才彻底结束。简言之,狭义的汉冶萍特指1908—1928年间三个主体厂矿共存的股份制企业,广义的汉冶萍则可延伸到独立发展的三大厂矿及上海总事务所。
汉冶萍整体史研究在近年取得较大进展,在于学界开始注重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汉冶萍,拓宽了公司历史概念的时间断限[3]。胡政、张后铨的《汉冶萍公司史》完整地呈现了汉冶萍从创立、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且首次系统研究了汉阳铁厂在抗战西迁后的历史[4]。刘云梳理了汉冶萍的发展历程,认为“公司过度依赖盛宣怀等洋务精英,未能建立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是其发展受挫的主要原因[5]。秦宁东聚焦于1920年代的“整理汉冶萍”问题,认为“国民政府最初介入整理公司的原因仅仅在于公司经营不善而引发的工人失业和工人运动”,日本的反对使“国民政府和舆论界对这一整理活动附加了民权、利权、国权等意义”[6]。王利霞论述了汉阳铁厂内迁的背景、过程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发展,认为这次内迁为重庆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7]。
(二)专门议题的深化
汉冶萍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的体制变迁,是公司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其对整体社会态势的调适。李玉勤认为,张之洞、盛宣怀“将经济事业的湖北矿务视为其政治事业的一部分,体制的选择和改变是从个人的政治私利出发”[8]。张实指出,盛宣怀在“张盛交易”中并未被胁迫,他“对铁厂的接办从酝酿、策划到实施有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9]。他发现“盛宣怀通过厂矿合并组建汉冶萍公司,以股票形式实现对汉冶萍资产的占有,并以钦派公司总经理而集决策权、经营权于一身,实现并加强了其对企业的垄断”[10]。闫文华考察了汉冶萍实行公司制的情况,认为“公司的组织结构为企业的内部整合提供了制度保证”[11]。李海涛指出,盛宣怀“只注重股份制的集资功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制度建设,忽视了权、责、利的分野,反映了早期中国股份制公司制度不完备、不成熟的地方”[12]。
汉阳铁厂选址问题,体现了政治传统对工业布局的影响。袁为鹏将工业地理学与传统政治史相结合,认为汉厂在初创时经历了宏观布局(铁厂“由粤移鄂”)、中观布局(设厂武汉、放弃大冶)、微观布局(定址于汉阳大别山一带)三个不同阶段。在宏观布局上,他指出铁厂由粤移鄂是“清廷中枢为了防止李鸿章集团势力过于膨胀,有意‘扬张抑李’,并考虑到湖北自然地理资源而作出的重要决策”[13]。在中观和微观布局上,张之洞“亦曾打算在大冶铁山附近建厂,因与李鸿章、盛宣怀等矛盾激化,彼此疑忌加深而不得不放弃这一在经济上更加有利的区位,最终定址于汉阳大别山下”[14]。“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张之洞、李鸿章两大洋务集团之间的斗争”对厂址布局产生了深刻影响[15]。左世元、姚琼瑶不认可张之洞因政治考虑有意舍弃大冶,认为“张氏是因为无法在黄石港寻觅到合适的地方才选择在汉阳设厂,且设厂汉阳有利于就近监督、管理,符合当时中国官场的传统思维”[16]。
汉冶萍背负着国人实业救国的期待,常被视为工业领域的民族主义符号。李培德认为汉冶萍与日本的关系错综复杂,承载了“民族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碰撞”[17]。周积明、黄予指出,汉冶萍公司所承载的“民族主义话语”呈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这二重属性,“一方面,民族主义话语赋予汉冶萍抗衡欧西、称雄亚洲的价值意义,使其成为标志国家、民族命运与尊严的符号;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国力贫弱但又具有维护民族独立和自尊的强烈愿望,汉冶萍经营者不得不在利用外资与维护企业生存之间取舍两难”[18]。周积明认为,汉阳铁厂乃“中国制造之权舆,外人观听之所系”,汉冶萍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了“拼搏、坚韧、担当、自立自强”的“汉冶萍精神”[19]。
近年关于汉冶萍整体史的研究进展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时间段和内容的拓展,由前期的经营管理扩充到中期的整理过程及后期西迁时的情况;二是考察角度更加多元,跳出了仅寻求失败原因的藩篱,也挖掘其经营中的成功之处;三是所论问题更具深度,学者们逐渐注意到汉冶萍承载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舆论对公司乃至中日关系的影响。
二、汉冶萍公司的内部管理与生产经营
为促进发展,汉冶萍公司积极完善各项制度、改善管理方式。学者们在公司的财务管理、人事制度、市场拓展、能源保障等方面用心钻研,使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日渐明晰。
(一)管理制度
汉冶萍规模庞大,完善的管理制度对公司的高效运营至关重要。杨洋认为,公司在职员的招收和管理方面具有现代化趋向,其背后“既有时代背景、各方利益博弈和国家立法的推动因素,亦有汉冶萍公司高层自身具备的早期现代化的视野及其相应努力”[20]。郭莹、杨洋发现,盛宣怀及其子盛恩颐相继掌控公司用人大权,“这种个人乃至家族专制集权的用人管理方式,虽然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其本质背离现代股份制公司的精神”[21]。她们指出,“把头包工制”在公司长期存在,而体现公平民主精神的合作制、领工制昙花一现后迅速失败,关键在于其触动了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22]。李超考察了民初大冶铁矿的改组,认为其“虽然实行了改编厂矿巡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内部的多重利益冲突限制了此次改组整顿”[23]。蔡明伦、高秀英探究了萍矿警长反复易主的原因,发现“其背后有地方政府、军方等各种势力参与角逐和博弈,警长之争的实质是萍矿矿权之争,不仅削弱了矿警防卫力量,更使萍矿受制于人”[24]。
(二)财务管理
钢铁业需巨额投资,汉冶萍一方面设法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订立契据、核算账目等方式加强管理。朱荫贵认为,汉冶萍资金的短缺与“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有效和强有力的资本市场,未能给汉冶萍提供上规模的资金支持有关”[25]。郭莹、陈锴指出,汉冶萍招股遇挫“有自身经营亏损、股市风潮影响、时局动荡金融市场不稳等多方面原因,还与国家未能对重工业发展给予强有力支持密切相关”[26]。李江研究了汉冶萍股票的形制、内容和基本发行情况,认为这些股票“记录了公司资本运作与生产经营的基本情况,浓缩了汉冶萍公司由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的历史演变过程”[27]。陈庆发指出,“萍矿创办后产能严重过剩,加上汉阳铁厂及其关联企业对于萍矿产品的低价购买政策,导致萍矿资本收益低下”[28]。左世元概述了汉冶萍的融资之路与外资利用情况,分析了外资与公司厂矿规模的初步形成及扩张、销售市场的开拓、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之关系[29]。
产业契据是厂矿房屋、土地等固定资产的产权转移凭证,蕴含着社会关系的变动。曾伟利用湖北省档案馆和萍乡矿业集团档案馆的资料研究了萍矿关于建设煤井、堆栈等设施的1 249张产业契据,指出产权变革的过程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引发企业与地方矛盾的根源[30];他发现官煤局为了摆脱地方大族控制下的民营煤矿对萍乡煤炭市场的垄断,更加有效地供应汉厂煤焦,购买山场、兴建厂房,建立了自主经营的萍乡煤矿[31];其“产权变革经历了从批山租井的零星开采,到归并土井进行规模开采的过程”[32]。姜志康以萍矿产业契据为中心,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梳理了萍矿产业交易,认为萍矿的产业交易深受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影响[33]。
公司账目记录了收支盈亏,反映了生产经营状况。黄领、黄婷分析了1908—1910年公司三届账本的内容、特点、差异和价值,发现此间主要产品产量大幅提升,销售收入也稳步提高[34]。彭兰考察了汉冶萍在1909—1919这十年间会计核算时采用的混合报告责任制,发现其糅合了中、西会计形式,目的在于满足国内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35]。张实考证了盛宣怀接办铁厂时的资金来源,认为“所谓铁厂‘创始老股账’应是光绪卅一年以后编造的……盛宣怀曾长期、系统地作假账”[36]。
(三)生产经营
为获取生产利润,维持稳定运营,汉冶萍时常更新机器设备、努力开拓市场。李海涛、张泰山考证了汉厂创建时的设备来源,认为“炼生铁厂以及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的设备均来自于英国谛塞德公司”,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37]。许龙生发现,公司在订购的德国电机受一战影响无法按时送达时,“积极寻求与北京中央政府接触,希望能借助中国与英国之间正式的外交关系帮助公司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公司还依靠其与日本之间签订铁矿石、生铁供应合同以及巨额的借款合约而产生的利益联系来推动日本外务省同英国政府交涉,帮助其实现利益诉求”[38]。代鲁发现,“在钢铁、煤焦、矿石各种产品销售中,钢铁销售收入占据重要地位,构成公司常年运转经费开支的主要来源”[39]。李海涛发现,“汉冶萍公司寻求与西方炼钢公司、大来洋行等美商合作,并非简单着眼于产品销路,还希望借此获得美国的资金支持,以解决厂矿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改变对日资过度依赖的局面”[40]。他注意到萍矿市场角色的转换受到公司钢铁产量的影响,“在冶金燃料生产企业和煤炭生产销售企业这双重身份间来回切换”[41]。李玉勤剖析了汉冶萍公司在1908—1911年间迎来短暂繁荣的原因,认为“企业的改建和扩建工程以及良好的市场机遇,为公司盈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公司能够盈利的决定性因素则来自盛宣怀的官权保护”[42]。李海涛、张泰山研究了汉冶萍的改扩建工程,发现“1904—1907年间,改良是铁厂发展的主要特点,主要目标是改善钢铁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炼铁炉产出率;1908—1911年为铁厂的扩充阶段,主要目标是扩大产能,增加产品产量”[43]。
汉冶萍的核心业务是制造钢铁,丰富的原材料供应是公司运转的保障。薛毅从煤铁关系的视角考察了汉冶萍厂矿的内部运作,他认为汉厂因萍矿的焦炭支持得以生产钢铁,而萍矿则不断提升了对原煤的筛分、洗选和加工技术[44]。闫文华指出,萍矿煤焦运往汉厂有“雇用民船代运、内部自运、和公司外的一些企业以及铁路工程局签订运输合同”这三种方式[45]。张宏森梳理了汉冶萍原料及燃料的运输方式由以水路为主到以铁路为主的变迁史,发现军阀混战的动乱环境影响了公司的运输秩序[46]。
汉冶萍通过发行股票、对外借款等手段筹集资金,并通过制定各项制度维持厂矿运行。但事实上,公司任人唯亲的现象层出不穷,且一直为缺乏资金所困扰,并因此陷入日债泥淖,为最终的失败埋下伏笔。
三、汉冶萍公司与国内政局
(一)公司与晚清、民国中央政府的关系
汉冶萍规模宏大,一直受到民国中央政府的密切关注。左世元指出:“晩清政府基本上能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对汉冶萍在政治、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47]李玉勤认为,袁世凯夺取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行动使汉冶萍失去了重要的资金挹注渠道,公司因此走上了大借日债的歧路[48]。盛宣怀为挽救公司的辛亥危局,“一方面以‘中日合办’抵制临时政府提出的抵押政策,另一方面疏通湘督谭延闿,阻遏鄂、赣地方政府接管公司的企图”[49]。1915年,袁世凯图谋利用“通惠借款”控制公司,“处于弱势的盛宣怀利用公司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及日、袁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从而达到既能获得政府的经济援助,同时又不被控制的目的”[50]。在国民政府“整理”汉冶萍时,公司再次向日本求援,使这次整理行动“转化为国民党政权与日本之间的博弈”[51]。陈庆发指出,成长于资本自由竞争机制中的萍乡小煤窑在被持续“整顿”的大环境下仍不断发展,而依靠行政垄断经营的萍乡煤矿却发展受挫,反映了“政治生态越是变化无常,资本运作及资本效益因素对资本经营的决定性作用则越大”[52]。
(二)公司与地方政府、民间势力的博弈
汉冶萍煤铁厂矿为重工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习惯截然不同,常与地方绅民发生冲突。肖育琼指出,萍乡名士文廷式与官煤局合作采购萍煤运销汉厂,令经营土井的士绅颇为不满[53]。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文廷式在后来转而提倡“官商分办”,团结地方士绅阻挠官局机器开矿的推进[54]。张实认为,“代表先进生产力,推进并完成萍煤从手工生产向机械化转化的是外来的洋务官僚盛宣怀,而不是主张维新的文廷式和代表部分本地士绅的广泰福”[55],不宜夸大后者在开发萍矿中的作用。Jeff观察到“官员张之洞和商人盛宣怀在推进地方工业化时形成了遏制地方士绅的联盟”,逐渐破坏了由地方士绅主导的社会秩序[56]。地方政府通过颁布通告等方式调和矛盾,“萍乡煤矿的经营者也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地位优势,从购井自立、增强财力、改善运道、联合商号、造福地方等方面积极谋求自立自强以应对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冲突”[57]。
民初政局动荡,江西军政府欲抢夺萍矿,汉冶萍一面与之交涉,一面请北洋政府和湖南省政府协力保护,日本势力趁机插手,反映了公司所处的复杂政治生态[58]。湖北地方政府试图将公司在鄂产业收归“省有”,“汉冶萍公司不仅积极与之周旋,而且寻求中央政府和日本势力作为支持参与其间”[59]。此外,倚仗日本的支持,公司与湖北省政府围绕象鼻山铁矿、纪家洛铁矿开采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因损害湖北地方利益、北洋政府的矿产国有政策以及民间激烈的仇日舆论而失败[60]。
政治环境对汉冶萍影响极大。总的来看,晚清政府的支持奠定了公司发展的基础,而民国各政府非但支持乏力,还意图武力攘夺,给日本通过债权控制公司提供了契机。
四、汉冶萍公司与日本
为持续获取大冶铁矿石,日本相继采取了煤铁互售、提供低息借款以及“中日合办”等措施笼络缺乏资金的汉冶萍公司。在近代中日关系的视阈下,双方围绕汉冶萍的攻守,已然超脱了纯粹的经济范畴。
(一)举借日债
借日债缓解了汉冶萍的资金危机,也使其跌入了日方精心布局的陷阱中。周积明、何威亚指出,日本获取汉冶萍资金情报的渠道包括领事、商人等多种[61]。李海涛比较了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的发展史,认为“国家扶植力度大小和市场环境优劣是决定两家企业经营成败的核心因素”[62]。易惠莉指出,“盛宣怀为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大举日债,实系形势所迫,是一种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对于盛宣怀的作法,应予以同情的理解”[63]。向明亮认为,“日资的渗透使原以生产钢轨、原料为主的公司逐步变为以采矿石及炼生铁为主要生产任务的企业了,大大偏离了它最初利用外资的目标”[64]。朱英、许龙生发现,“作为债务方的汉治萍公司,在对日借款问题上备受‘商业’与‘国计’的困扰,但两者均未完全达到目的;作为债权方的日本政府,通过本国金融机构不断向汉治萍公司贷款,虽然缓解了铁矿石供应之不足,但也累积了诸多无法偿还的不良贷款”[65]。
(二)中日合办汉冶萍
民初临时政府为获得日本借款,提出“中日合办”汉冶萍案。向明亮发现盛宣怀在此方案中“试图避开舆论的指责,同时谋求企业自救”[66]。刘远铮注意到谴责“中日合办”的與论风潮体现了“当时民众的觉醒以及舆论力量的成熟,舆论话语背后的利益纠葛与纷争也可见民初社会的纷扰乱象”[67]。左世元认为临时政府在该方案中居于主动,盛宣怀与汉冶萍处于被动,“是由于近代中国以国家为本位、以财政为中心的经济政策的思想以及相关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产权法律的缺失而造成的”[68]。他发现中外合办汉冶萍贯穿了数十年:“与洋人合办汉冶萍的提出者是张之洞,中日合办最先是日本首相桂太郎提出的,但获得了盛宣怀的赞同,并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1915年在‘二十一条’和通惠借款事件中两度被日本赤裸裸地提出,最终通过九州制钢厂得以实现”[69]。
(三)汉冶萍与近代中日外交
汉冶萍是近代中日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的关键争议之一。易惠莉发现小田切积极与盛宣怀联络,并向日本财、政界高层通报汉厂情况,日本高层则“动用政府和民间各方力量向汉阳铁厂贷款,以图长期控制优质的大冶铁矿石资源”[70]。何威亚指出,日本驻大冶制铁所技师西泽公雄同样积极向日政府报告大冶、湖北的各种情报,并参与了日本对汉冶萍的部分借款活动[71]。但张实认为,西泽公雄的《大冶铁矿历史谈》中“大冶铁矿为德人所发现、借款而握该矿之统治权,因日人的到来而德舰示威,终被西泽所战胜而多数德国工程师被革职交卸等,均是西泽心造的幻影”[72],不足为据。张实还根据《日本外交文书》等资料研究了《煤铁互售合同》,揭示了日方很早就将“攫取大冶铁矿的管理权作为目标”[73]。李柏林注意到,中日在1927—1929年间围绕汉冶萍接管问题进行了三次交锋,“日方通过抗议、施压等多种途径,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使得接管问题最终不了了之”[74]。
围绕日债及合办汉冶萍问题,中日双方激烈博弈。日本通过签订借款合同,实现了长期从大冶输入铁矿石的既定目标;汉冶萍则因合同的限制错过最佳发展机遇,最终走向失败。
五、汉冶萍公司人物研究
在汉冶萍公司发展史上,盛宣怀、张赞宸、李维格等管理者贡献良多;工人、职员、矿警等群体则是公司稳定发展的根基。
(一)公司重要人物
公司经理、厂矿长等拥有较高话语权,影响了汉冶萍的运营走向。科大卫认为,盛宣怀接手汉厂后有三大贡献:一是开发萍矿解决能源问题;二是购置新的适合大冶铁质的炼铁炉;三是处理财政上的问题[75]。彭晓飞发现“(愚斋)义庄在人事和决策管理上影响汉冶萍的经营”,汉冶萍也因经营不善难以归还对义庄的借款和利息,致使义庄财政困难[76]。张燕、武乐堂注意到张赞宸在萍矿时“采用机器作业方式、筹商煤焦运输线路、加强金融管理、协调各方关系,奠定了矿局发展的基础”[77]。黄仂认为,李寿铨为矿务鞠躬尽瘁,是“萍乡煤矿发展史上最具地位和最具影响的功臣”[78]。左世元发现张謇在任农商总长时“向袁世凯及北京政府提出通过官商合办,最后达到‘国有’的目标”,但因政府缺乏合办资金及日本的极力阻挠,其愿望未能实现[79]。
(二)人物群体研究
承担基础工作的工人、职员、矿警等群体,是公司发展的根本力量。陈文敏考察了冶矿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制度,发现其用雇工制、包工制两种方式管理工人[80]。刘洋论述了萍矿矿警保护矿区资产、维持矿厂治安、押运煤焦器材等多重职能,以及警员的任免规则、福利待遇等管理措施[81]。陈春亚发现,萍矿职员可分为“洋员、高级管理人员、工程人员、普通事务人员”四类,有“总公司直接派遣、管理人员推荐、公开招聘以及矿局矿务学校输送技术人员”等四种聘用方式[82]。史斌指出,“洋员协助中国管理者建立了人事管理制度、质量监督检查制度、产品销售制度、工业标准化制度等近代西方企业制度,使汉阳铁厂形成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制度模式”[83]。
重视人的能动作用,是揭示更鲜活的汉冶萍史的必由之路。但目前汉冶萍史的人物研究主要集中在盛宣怀等少数人身上,关于基层员工的成果仍然较少,且缺乏理论深度,需要学者们投入更多精力。
六、汉冶萍史研究的新趋势
随着史学学术理路的变迁以及汉冶萍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从技术史、城市史乃至文化遗产等新角度考察汉冶萍公司。
(一)技术史
技术革新是近代工业的基础,从人才、技术的角度考察钢铁工业,有利于更好地解读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历程。方一兵、潜伟认为,晚清政府的特殊关照及1905—1908年的大规模设备改造是汉阳铁厂的钢轨制造能够短暂繁荣的直接原因[84]。他们指出,汉冶萍派遣到英、美等国学习冶金技术的留学生在辛亥革命后的厂矿复建中逐步取代了外国工程师,“在中国从西方移植冶金技术的早期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5]。此外,方一兵探讨了以汉冶萍为核心的近代中国大规模移植西方钢铁技术的历史过程,推动了学界对汉冶萍乃至整个近代企业采用新技术的过程的探讨[86]。雷丽芳发现,汉冶萍“从1902—1918年至少出资委培了吴健、卢成章、郭承恩等10名钢铁工程师”,他们是“中国的第一代钢铁工程师”[87]。李月指出,萍矿采用了先进的勘矿、钻井、排水等工具,“在当时全国乃至整个东亚都是首屈一指的”[88]。张实反对“购炼钢炉是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三大错误之一,废弃贝炉、专用马丁炉炼钢以提高质量是盛宣怀、李维格的重大成就”的说法,认为“汉阳铁厂初期同时用贝炉和马丁炉炼钢是合理而实用的配置”[89]。
汉冶萍是中国首个钢铁煤联营企业,在应用先进技术、培养工程人才方面多有建树。从这一角度出发,能够更直观地揭示汉冶萍盛衰的细节纹理。
(二)城市史
汉冶萍厂矿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节奏,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姜迎春认为,围绕冶矿修建的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外来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经济业态和社会结构[90]。他和周少雄指出,大冶乡村社会流动以官方强行推动的工业化为背景,与经济发展情况呈正相关[91]。此外,姜迎春、李和山还以冶矿为中心研究了工业化背景下乡村教育的转型问题,“厂方对管理人员、技术工匠的培养与推崇以及更高经济收益的提供,无疑成为当地乡民钻研工艺、追捧新学的动力”[92]。徐旭阳、张铃注意到大冶矿山的开采促进了近代文明的传播,主要表现在播散新式教育、改变乡民传统意识和生活习惯、引进近代科技等方面[93]。李海涛指出,“萍乡煤矿的创办启动了萍乡工业化进程,萍乡城镇化也随之起步”,体现在增加人口、改善交通条件、活跃地区金融产业、提升医疗卫生事业等多个方面[94]。袁为鹏认为汉阳铁厂与武汉早期城市化的作用是双向的,并从近代工业的生产及集聚与城市人口的增加与集中、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区面积的扩张与地理面貌的变化等角度展开了讨论[95]。
汉冶萍的创办深刻影响了汉阳、大冶、萍乡等地的历史走向,促进了厂矿所在地的城市化进程,隐含了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解体、新型工业城镇徐徐建立的历史线索。
(三)工业遗产
汉冶萍包括汉厂、冶矿、萍矿及多个附属厂矿,其遗迹在当下成为不可多得的工业遗产。方一兵从器物、建筑、景观和文献等方面分析了汉冶萍工业遗产,认为应“充分地利用和挖掘现存冶金工业遗产的价值,形成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与技术史研究相互促进的局面”[96]。曹宇列举了大冶钢铁厂的物质遗存与非物质遗存,前者主要由“场地、建筑、设施设备、交通系统和配套设施组成,包括高炉残基、瞭望塔、水塔、工人俱乐部、冶铁厂界碑等核心物项,后者体现在矿冶艺术方面,主要包括小说、歌舞剧、钢铁手语”等[97]。田燕认为,“汉冶萍工业遗产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应以文化传播为无形(非物质)的线路,以适当的交通组织为有形(物质)的线路”,以城市、厂矿区、遗产点为线路上的核心资源重现汉冶萍文化线路,从整体上保护汉冶萍工业遗产[98]。
无论是从技术史、城市史还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研究汉冶萍,均表明其作为近代标杆企业的丰富历史价值。实际上,由于汉冶萍所处的历史生态的复杂性,一些传统课题也可能因视角的转换取得突破,如裴宜理发现,早期的共产党干部通过领导安源煤矿的非暴力罢工及开展对工农子弟的教育活动,传播了共产主义理想,这与后期的暴力革命模式有所不同[99]。
七、小结
近二十年来,汉冶萍公司史研究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得益于新的档案资料的出版,学界拓宽了公司整体史的研究时段,对诸如体制变迁、铁厂选址等议题的讨论也更为深刻;其次,以对公司重要人物及普通职工的研究为契机,学界对汉冶萍的内部管理及生产经营情况作了全面的考察,发现了汉冶萍在筹集资金、更新技术、开拓市场等方面的努力;再次,汉冶萍与各级政府、民间势力的博弈细节被充分展现,日本意图通过债权控制公司的过程也被深入挖掘,凸显了汉冶萍所面临的复杂生存环境;最后,学者们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汉冶萍公司与地方社会乃至整个钢铁业的关系,发现公司各厂矿的建设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变迁,促进了所在地的城市化进程,对西方煤铁技术的移植和在实践中培养的人才则奠定了中国近代钢铁业的根基。
但是,有关汉冶萍史的研究仍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首先,应加大汉冶萍公司原始档案的出版力度。据笔者所知,除了20世纪末出版的档案选编外,湖北省档案馆仍藏有大量公司档案,海外也散存着部分公司资料,若能组织人力精选数册出版,必能为汉冶萍史研究提供极大助力;其次,应加强对汉冶萍史“薄弱”时段及议题的研究力度。相较于20世纪单纯的政治、经济视角,近期成果的研究维度更为多样,但重心依然落在盛宣怀等重要人物及公司体制变迁、日债、厂矿选址等少数主题上,本应成为研究核心的日常经营管理、技术革新等议题所占比重仍然偏低,而有关近代人物与汉冶萍的关系、汉冶萍的国际比较、汉冶萍对区域社会的影响等的研究也还比较薄弱,公司整理及抗战西迁时期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这些“短板”亟待补齐;最后,应努力完善公司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完成与中国近代史的全面对接。当下的公司史研究以史实阐述为主,缺乏系统理论的支撑,显得较为零碎。将公司置于近代经济史乃至整个近代史的研究视野下,厘清所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提升汉冶萍公司史理论研究水平的有效方法,周积明教授等人从民族主义角度对汉冶萍公司的探索即是将企业与国家、社会发展进程进行联结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