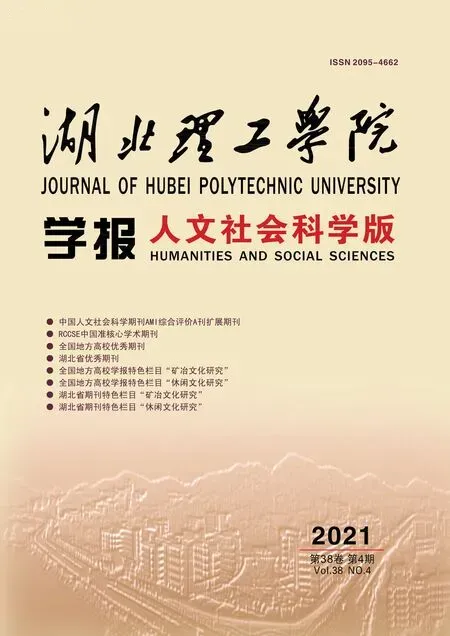生命体验与生死关怀:儒家文化生死救赎的另一种视角*
张耀天
(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疾病禁忌、死亡禁忌的大背景,导致死亡在中国主流文化层面一直是沉重、禁忌的词汇,也因此使得有关死亡的命题往往禁忌化、神秘化、宗教化。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也以极端情绪表达,如恐惧、抑郁、愤怒、震惊等[1]。儒家文化的价值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儒家文化有丰富的生死关怀资源。如,夫子的学生伯牛去世之前,夫子哀叹:“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夫子的学生颜回去世后,鲁哀公问及情况,夫子悲痛地讲:“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并且高呼:“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论语》中表述夫子对待生死的态度,既有理性的智慧,也有常人的哀痛。先秦儒家对生死的态度,大抵都继承了夫子的认知,如孟子讲“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荀子讲“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都可以看出先秦儒家文化对待生死既有情感性,亦开始赋予人以生命价值。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属于早熟的文化类型。西周时期就明确了“敬德保民”的理性主义倾向,把“尽人事、知天命”的认知成果纳入到政治伦理和生活伦理中。从夏道遵命、殷人尊神,再到周朝“以德配天”,可以理顺出一条先秦哲学趋向于理性主义的道路——人在不断争夺“神”的地盘,并不断呈现人类理性的胜利[2]。正由于儒家文化的早熟,使得生死关怀问题在文化源头期就抛弃了“彼岸世界”的追求,强调“三不朽”“舍身取义”的价值诉求,并在现实的道德世界寻求到类宗教的忠义文化、道义文化,替补了宗教的律戒并转换为现世知识分子的修齐之道。
理性只能解决现实的生活问题,却疏远了人的终极关怀——对死亡的恐慌。尽管不可否认儒家乐观、乐活的理智态度,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进程中战胜苦难的精神武器,但在远离了瘟疫、灾荒和战争等宏大历史主题的今天,形而上的思辨精神、生死超越的系列路径或许无法进入当下“日常生活场景”语境的芸芸众生。唯有从儒家文化中发掘体验的方法、生命的关怀,才能引导当代人理性对待生死认知、安顿个体价值,用儒家文化的生死智慧实现对个体精神世界的现实超越。
一、形而上与体验:哲学思辨和现实需求的角力
考察先秦文化的源流,发现西周时期业已形成以非宗教的思维方式来理性思考人生的范式:如果说夏、商两代尚有巫祝文化的影子,到周朝通过《周易》《尚书》等典籍,则总结和终结了中国远古时期对天命的懵懂信仰。无论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经》),或是“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尚书·多士》),可以看出,“天命”不再是具有外在的、神化的绝对权威,而是演化为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道德践行的依据,甚至于“天命”与人生之间可以形成某种“互动”,人未必是一定服从于“天命”,相反“天命”会服从于人:“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3]可见,对于形而上的“天命”和“性命”,先秦儒家文化已经呈现将之道德化的倾向——这可能缘于西周代商的政治需求,将商朝所推崇的宗教性质的、外化的天命观,偷换概念为“敬德保民”的、与民意博弈的天命观。西周所形成的天命观,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异己化的天命观,它既是理性的、具有意识形态内涵的文化符号,也是内化于人的、具有强烈道德意涵的行为规范。源于巫祝文化的“天命”范畴开始被严重泛化,它可以是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者所关注的“道”,也可以是墨子墨家学派所推崇的“天”,更可以是孔孟为代表的、道德主义者所秉持的仁义之说、仁民爱物——从这个角度出发,西周贵族对“天命”概念的改造,等于把夏、商两代的“宗教之天”进行了世俗化的改造。由此,中国古代哲学有关命运的思考,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的、理性思辨的意涵,失去了对个体生死关怀、彼岸世界构想及宗教体验的探索。“周仁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礼记·表记》)
换言之,先秦儒家文化在源流上,已经断绝了把现实生活和宗教体验沟通的路径,实现了“绝地天通”,此后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孜孜于构建现实世界的礼乐文明体系。先秦儒家文化以人类理性的力量,以“绝地天通”的形式,实现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神俗分离,并以礼乐文明的体系建构了新的社会伦理规范[4]。这意味着,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开始诉求于道德生命的不朽追求,而非彼岸、来世的宗教慰藉——既然不能实现“肉身成道”,儒家文化把生死关怀放置到现实、现世的情怀追求上,如“天人合一”的生命认知,“内圣外王”的信仰诉求,及后世宋明理学所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的使命天职。
如果宗教是通过彼岸世界的构建、生死循环的假设、来世往生的梦想,实现此生生命的救赎,那么儒家文化则更强调在此生、此世通过践行道德生命,实现冯友兰先生所谓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完成生命的关怀。单就个体生命的关怀而言,它表现为一种贵生主义的倾向,既表现为珍视自己的生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6];也强调珍惜此生此世,要修齐治平,要成贤成圣,“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7]。而遭遇生死冲突的时候,儒家文化则比较呈现出一种理性的、道德功利主义的倾向:在日常生活中, 要惜命、爱命。“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但在道义面前,要做到“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生死被纳入到道德功利主义的考量之中,可以为道义、大义而死,这种生死选择才是重于泰山之死。这是儒家生死观超越宗教关怀的表现。
但是这种超越式的生死观,对具体生死关怀而言,无法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形而上的、超越的生死观如何过渡到日常生活的生死情感和生命感受?以宋明理学为例,张载强调“为天地立心”,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历史感以“哲人王”的气质得以表达,既表达了士人的道统担当意识,也超越了现实的生死局限与时空障碍。在今天读来,依然能感受到哲学力量的震撼。问题在于,这种超越的生死观,只能是理性主义层面的、或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张载所强调的“民胞物与”、生命平等意识,无法激发民众对其它生物的生命平等感的觉悟。从这个角度出发,儒家文化的生命理念,依然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层面的理性之思。二是,儒家文化的生死关怀是建立在生命主题、历史主题的范畴之上,尽管也强调扫洒应对、人伦日用,但依然无法解决宏大的话语方式如何介入到当代人日常生活的难题。董仲舒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试图打通学理和生活的通道,完成“天人合一”的解释学构建,如提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8]8把人的生命、气化本体、道德天理、喜怒哀乐、性命夭寿,都纳入到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中。这种解释体系,固然能够在一个形而上基础上,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但却无法落实到现实世界的生命关怀中,它既无法形成类似“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宗教口号的普及现象,也无法完成生死关怀的情感支持,它甚至不及宗教式的生命体验给人带来的“神圣的欣快感”[9]。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讲,是生命发展的必然。较之于其它的生命感受,唯独死亡属于“自我”——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死亡的必然性,既是中国理性主义诞生的基础,“生死无碍”、生死无忧、生死不惧,都彰显了人类在死亡面前的勇气和悲壮;也是宗教文化产生的源泉,彼岸世界、天堂美景、生死轮回等虚幻场景的构建,则反映了人类和未知命运的妥协及退让。这意味着在死亡面前,儒家文化既要高扬人类理性的主体精神,更要体现哲学思辨的情感关怀——只有把哲学拖拽到生活、进入到生命体验的境遇,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事实上,儒家文化内涵着生活体验的要素,即使是最严肃的宋明理学,也以把形而上学理践行到生命实践作为理想的诉求。如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指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王阳明是把生命的本体和日常生活的伦理认知进行关联,把“气”范畴扩充到生活场域,这也符合儒家把“人伦”落实到“日用”、把“大道”践行于“生活”的传统。卢卡奇指出,如把人的日常生活视为一条漫长河流,那么生活的理念则赋予“长河”以新的意义[10]。从这个角度出发,生活和生命的体验,既是哲学的源泉,也是哲学的归宿。以体验的精神,进入到儒家文化的生死关怀,既完成了哲学话语突围的救赎,也完成了生命关怀的救赎。
二、不朽与死生:价值诉求和生命关怀的冲突
有关生命的讨论,是超越文化背景和地域背景的人类哲学最普适的话题。生命是哲学研究的起点,也是作为人的基本属性的起点——对于人的本质来讲,无论是社会关系的诠释,或是道德范畴的符号,或是文化使命的承载,说到底,人就是生命。哲学所研讨的对象,也无非是人的生命。生死是人类自然生命和人文生命永恒的主题,有关生死关怀既是哲学的命题,也是生命反思的本能。宗教有关生命、生死的关怀,往往把自然生命有限性和诉求价值无限性矛盾的调节者,定义为一个外在的命运或上帝:“人无限地关切着那无限,他属于那无限,同它分离了,同时又向往着它。人整体地关切着那整体,那整体是他的本真存在,它在时空中被割裂了。人无条件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内外条件,限定着人存在的条件。人终极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它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11]在蒂里希看来,人的命运是一场“悲剧”,原因在于,人生有限却诉求生命永恒,个体局限却诉求于整体圆满,最终缔造了一个“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决定着人终极的命运”,并把它外化、指向于一个“终极存在”的上帝或佛陀。从这个角度出发,宗教性的生死关怀,是一种导向于终极存在的,对有限生命同情和对有限智慧悲悯的、根本性的关怀,这种生死关怀既有对现实生命感受的关怀——佛教的苦集灭道、道教的长生久视、基督的原罪救赎;也在现实世界的背后寻求到一个本质性的、本源性的信仰,并把这种信仰作为现世解脱的“稻草”。
对“神”的崇拜,说到底是人类有限理性对生命无限性的追求与崇拜。“神”的出场,是人对自我缺陷的精神性“再造”[12]146。问题在于,理性和智慧的力量催发着人主体性的爆发,他既不会永远地屈从于一个自己制造的“神”——所谓的“神”,只能是一个大写的“人”。当人的力量足够强大,或者当人的认知足够强大时,“神”只能作为祭坛的神祗而不再介入现实的生活:在这种场景下,人类开始拥有在现实世界探索意义世界、在现世世界寻求价值世界的能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儒家文化就是在现实世界构建的一种“在者”的价值关怀:在本体论上,构建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宇宙生成论,天地万物、五行三材都是宇宙生生之流造化的产物;在价值论上,遵循着“天人合一”的路径,生生之德既是天道也是人道,既是宇宙生成的准则也是善恶伦理的依据;在人生观上,这种活泼而又规范的生活方式,是信仰与哲学的融合,把中华民族的哲学信仰和现实生活契合,落实到人伦日用、扫洒应对的日常生活之中[12]142。
儒家文化的信仰力量,丝毫不亚于信徒对宗教道义的践行。如《孟子·尽心上》就有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殉道、殉节、殉国者在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的道德位格。当然,儒家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强调“成仁”的文化,强调个体生命的德性成熟与境界提升。儒家的生命观,只能是一种信仰式的、理性的生命观,它固然强调以生命践行德性的重要性,高扬“殉道”,但却不鼓吹“殉道”,也不提倡“殉道”。它没有把肉体视为通往彼岸的“皮囊”“渡船”,也没有把现世蔑视为修罗场、地狱。相反,儒家文化把颇具自然主义情怀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内化到本体建构、生命认知、价值规范和生活伦理,并把“天人合一”作为生命发展的智慧导向:一则,明确了人之为人的价值高贵性,人禀赋天地之气而生,既与万物同生,又是五行之秀、天地之灵;二则,它是安生立命的形而上依据,人借助于个体对生命的认知力、理解力、觉悟力,实现了从“自然境界”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觉解,寻找到了现实、现世的内在超越之路;三则,“生生之易”的生命感,转化为一种人生进步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和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强调的“天职”不同,韦伯所谓的“天职”是外在的、是宗教神圣感所赋予的;而“生生之易”的使命感,则是一种内在的、元生的使命感,诚如张载“四为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正是由于对生命葆有的这种强烈意识,才促使儒家把“生生”看成是内在于宇宙、内在于天地人的绝对的、唯一的、永恒的、圆满的、最终的本体,看成是天、地、人及一切生物作为生命整体共通的本性[13],人的现实生命才能以成人成己作为生命发展的动力,追求不朽的现世价值。
问题在于,不朽的价值追求只能回归到人本的关怀,这个关怀只能实现于认知能力、心理状态,或者讲这种关怀本身是一种“孤独”的关怀。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了断生死之碍后感慨道:“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14]王阳明身处生死险境,非生即死,却能在洞中静坐,体验“濒死”,最终能超越生死、实现生命的达境。在“生死局”面前,王阳明以“此心光明”的生命觉解体悟到生死智慧,实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生命境界。王阳明对生死的觉解是孤独的,众人对生死的认知是孤独的,这两种孤独不同——王阳明的孤独,是自己对生死觉悟所达到的境界既孤独高冷,也无法分享,毕竟生死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只有一次;众人的孤独在于,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撕裂了人文生命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残忍地袒露于众人面前。“这种孤独感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灵之中,时时提醒人们死亡的来临,古人所说的一周岁制棺不为早的话就暴露了对死亡的恐惧感。”[15]王阳明认知到孤独并不可怕,却无法与众人分享;众人孤独于孤独,却无解脱之道——这意味着,儒家哲学尽管解决了生命的永恒关怀问题,却无法消解众人对生死的恐慌与畏惧:其一,生死恐惧是常态的生命反映。这种恐惧,内化到生活的每一天。生死相随,此消彼长,特别是身处于困境,生的希望越渺小,死的恐惧就与日俱增。这种生命的常态化心理感受,与儒家文化所言说的“或生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价值抉择,没有发生于一个统一的话语场景。儒家文化的生死境界,未必能够实现生活的救赎。其二,“不朽”的生命价值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生命价值诉求,但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所有人的生命价值诉求。特别是在价值选择多元化的今天,以及儒家文化的非宗教性,都意味着“不朽”所产生的生死关怀感极其有限。这就意味着,从儒家哲学生死关怀的资源寻找到救赎的价值,既关乎儒家哲学发展的路径突围问题,也涉及如何实现哲学意义上人的主体觉醒和对生死的终极关怀。
三、救赎与慰藉: 主体觉醒和生死无惧的和谐
“天人合一”的生命关怀,明确了生命的自然主义立场,既然无法实现宗教式的、彼岸的心灵寄托,以当时、当世的成贤成圣作为人生诉求的目标,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追求。在实现这一追求的路径上,个体心性的“发明本心”和推己及人的济世情怀融合为“内圣外王”的生命之道:“圣人”所处居的生命状态、生命境界,代表着智慧的觉悟和人生的圆满,既是修齐治平的理想人格,也是人生精进的认知目标;“外王”意味着要把生命体悟的成果,践行到“人伦日用”、人生实践上。“天人合一”的情怀,最终要落实到“内圣外王”的方法论上,“内圣外王”不仅是儒家的生命态度,同时也折射出儒家知识分子的主体觉悟——与其把命运寄托到遥遥无期的天国,不如在现世向死而生、实现大同,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外王”是“内圣”光芒由内而外的辐射,儒家知识分子个人的道德修养,演化为实现世界大同的精神力量[16]。从这个角度出发,“内圣外王”是儒家文化实现人的主体性高扬的明证,个体生命实现主体的“澄明”,对外拓展为创新进取、奋发有为。
“内圣外王”是儒家知识分子现世价值诉求的表征,也由此实现了个人主体价值的高扬。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坚守在理性主义的道路上。但是,“内圣外王”尽管通过“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道德觉悟,实现人由自然生命到道德生命的过渡,强化了个体主体力量和自由意志的能动性,但它无法完成生命关怀的两大问题,即生命关怀的大众化和对死亡恐惧的消解。首先,“内圣外王”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修身之学和人生哲学,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意义的普适化。夫子自己都承认,“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它既有专业知识的背景和门槛要求,也有对儒家文化信仰、至少是兴趣的要求。在当代,“内圣外王”很难真正意义地落实到现实生活的场景之中。其次,即使“内圣外王”能转化为文化语言、生活语言,它依然是一种理性的“境界之学”。“境界”是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发展的一个贡献,它在理性世界和宗教世界之中,寻找到了中和性的解决方案。“境界”既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体验,也是现实世界的心灵安顿[17]。换言之,“内圣外王”无法消解死亡的恐惧。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一种生存论的哲学,那么这种立场更加剧了儒家文化和生死关怀之间的矛盾[18]48。向死而生的生命历程,孤独的死亡之路,并没有因为“内圣外王”而实现生死无惧,相反生命的天平越是倾向于现世,死亡恐惧感的一侧就越加倾斜。
在这种场景下,重新反思儒家文化的适用性,成为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如果说,沿着理学的路子、继续言说儒家的形而上理论——如牟宗三、熊十力等新儒家代表人物所秉持的立场,那么徐复观、成中英、李泽厚、林安梧等人则代表了学科发展的另外一条道路——明确了儒学生活的方向,即当代新儒学不可能再过分强调良知或道德主体,而是回归到生活世界,以生活、生命而重新建构新儒学[19]。儒家思想要契合当代现实生活,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关联当下生活的问题——以哲学的智慧观照现实的生活,以本体的关怀提升生活的境界。同时要寻找到新的关联生活的方法论,如果说“内圣外王”实现了主体的觉悟和心性的自明,那么儒家哲学之于生命关怀的效用路径,可以通过“哲学咨询”的方式,实现真正意义的学科突围。
生命关怀是一个宗教性的词汇,当然不排除哲学也有生命关怀的因素。原因在于,生命关怀更关切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感受,宗教和信仰往往更能切入人心、更能关注负面情绪。“神话和原始宗教绝非毫无连贯性,它们没有丧失常识的理性。它们的连贯性体现在情感的统一性上,而不是逻辑法则。”[20]72有关生死的问题,既无先例可分享,也无经验可遵循,生死平等、人人一次,在生死面前,哲学未必享有绝对的话语权。但一个人内在的理性认知结构一旦形成,在理性认知的支持下,产生对抗生死恐惧的认知能力:个人与宇宙和谐相处,是哲学化、智慧化的生活方式,生死如常[20]9。卡西尔把哲学的认知力(如“天人合一”的“澄明”状态),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心理感受和心灵抗衡生死恐慌的力量,契合王阳明所说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从哲学认知到现实感受的转换,为儒家文化的突围发展提供了一个导向性的“通道”,即以哲学咨询的方案落实儒家文化的整体理念。哲学从形而上的“象牙塔”走向现实生活,尝试把学理转化为一种“可操作和可实验”的范式[21]。同时,哲学咨询在生死关怀问题上没有以一种主客二分、医患关系的方式来与“咨询者”沟通,它不同于心理诊疗——心理诊疗是作为医疗手段,咨询者本人往往被贴上了偏见性的标签。哲学咨询的互动双方是平等的,有关生死问题,哲学家提供的方案并不见得高明,但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生死恐慌是生命的常态,通过哲学化的咨询可以缓解对死亡的恐惧[22]。再则,从哲学生活化的价值出发,生死关怀问题不同于一般性的心理问题,它是关于生命存在的终极性问题,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对于一般性的孤独者,社会心理干预手段大多是有效的,但对于存在性孤独者,这些手段很难奏效。后者需要的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一种宗教或准宗教的信仰,或一种使他们重新理解世界与生活的哲学[18]49。从儒家的乐观、乐活、乐感、乐生的精神中,汲取出救赎生死的、超越人生的思想资源,既解决了儒家文化生活化的新出路[21],也实现了当下社会重压之下以理性智慧的主体觉醒方式和救赎生死关怀,抵达生命自由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