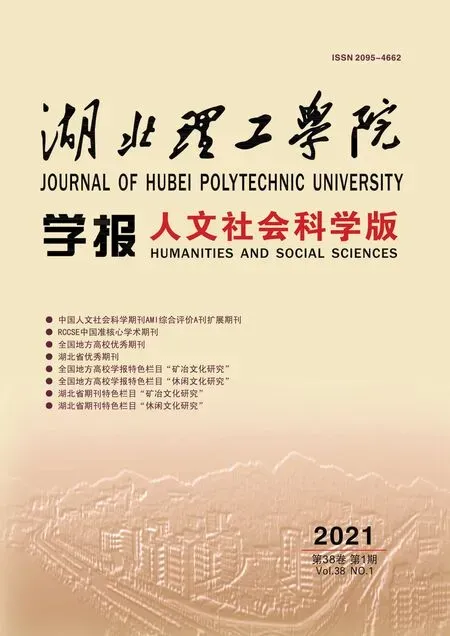先风与后雅:《张协状元》到《琵琶记》创作愿景的变奏
李春光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郑振铎先生认为:“《张协状元》篇幅甚长,叙张协富后弃妻事,大似《赵贞女蔡二郎》的结构,也甚似明人词话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情节。其剪发出卖上京求夫的一段,更似伯喈、五娘的故事。”[1]690冯其庸先生进一步认为:“现存南戏最早的剧本《张协状元》与《琵琶记》倒有一点渊源关系……《琵琶记》的思想情节与描写手法,与《张协状元》有很多相类似之处。”[2]321可见,《张协状元》与《琵琶记》,不仅结构、情节类似,从某些层面上说,还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一、主角人物的伦理变奏
从整体着眼,二戏讲述的均是负心男与苦情女历经波折终获团圆的故事。
负心男。无论是张协还是蔡伯喈,都是文人世界里蟾宫折桂的典范。当当朝宰相欲招新科状元为东床快婿之时,张协选择避接丝鞭,一心想要回乡照顾双亲,且置上门寻夫的贫女于不顾甚至命家仆将其乱棒打出;蔡伯喈则选择了委曲求全,入赘相府,虽然日夜悬心于家中双亲与妻子,最终还是未能以实际行动拯救家中的惨淡与危机。
张协与蔡伯喈的负心,似乎经历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宋代以文安邦,得势文人富贵易妻乃是常事,并无任何愧疚之感。文人地位的飙升,致使男性把情感背叛看做平常之事。加之,各大政治势力致力于拉拢新贵人才,致使新科状元炙手可热。张协入赘相府,乃是政治漩涡中步步为营的终南捷径,即便置结发之妻于不顾,也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波动与舆情波动。诚如黄仕忠先生所言:“在宋代,人们不惜以悲剧,以魂追、天谴来摧挫负心的书生,毫不假以辞色。这是因为宋代书生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美好的仕进前程,可谓天之骄子。无论是得意,还是潦倒,生活都向他们敞开大门,世界充满着阳光。然而,到了元代,书生们便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中了。”[3]54的确,到了元代,由于科举致仕之路被阻塞,文人的地位急剧下滑,仅仅高于乞丐位列第九。蔡伯喈们即便要负心也要三思而行。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一句当时的民谚:“三代仕宦,学不得着衣吃饭。”可见,在元代社会的价值系统中,“着衣吃饭”比“三代仕宦”更为人所重。入赘相府,的确是蔡伯喈们解决“着衣吃饭”问题的较好选择。高明在《琵琶记》中千方百计地为“非三代仕宦”的蔡伯喈的负心行为加以开脱,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可见,蔡伯喈的瞻前顾后与张协的处事绝决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由是观之,宋元易代导致的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最终促成了富贵易妻主题由谴责而开脱的价值呈现的大跨度变革。
苦情女。无论是贫女还是赵五娘,都具备中国古代底层妇女贤孝淑德与隐忍坚强的性格特质。正是由于一个个像贫女、赵五娘这样的“小她”,才铸就了浩瀚中国女性文学史里熠熠生辉的“大她”。贫女不惜剪发供张协上京赶考,自己却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上京寻夫,无端遭到丈夫门人的恶棍毒打,只得忍气吞声,行乞回家。贫女内心之苦可以想见。赵五娘在蔡伯喈上京赶考之后,隐忍着公婆的误解而辛酸度日;在蔡伯喈音信全无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双手埋葬了公婆。赵五娘的内心之苦也是可以想见的。
如果说,男人是悲剧的制造者,那么,女人则是悲剧的承担者、受害者。从贫女到赵五娘的演变,不是凭空而来的,同样也经历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过程。贫女归根结蒂只是在自己的情感世界中缱绻纠葛,并没有遭遇太多的社会规约。南宋无名氏民间艺人对“贫女”这一艺术形象塑造,更加贴近市井民氓的情感诉求。赵五娘的问题,则不仅仅是情感纠葛的问题,更多的则是纠缠其间且如影随形的家庭伦理层面上责任与义务的问题。元代成熟文人高明创作《琵琶记》的指导思想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他要把“有贞有烈”的“赵贞女”塑造成封建社会的艺术典型。刘小枫先生认为,“个人作为人之存在的真实基础”就是“人与存在本原的超验关系”,这种“超验关系”绝不应该被“个人与家族、国家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与民族性传统的历史关系来取代”[4]298。赵五娘形象的深刻性就在于,她并非为自己的“存在本原”而活,更多的则是为“民族性传统”而活。高明把赵五娘放在家庭困局与社会伦理之中挣扎,让她匍匐隐忍,进而使她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二、辅助人物的功能变奏
从局部着眼,二戏的辅助性人物经历了一个功能性的变革。
古道热肠的好心老人。李大公夫妇与张太公均是古道热肠的好心老人,他们对剧中处于弱势的女性,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与支援。但是,从人物的功能上来看,李大公夫妇的出现具有偶然性,对于《张协状元》剧情的推进是微乎其微的。例如第十九出《贫女借路费》:
(末出白)久雨初晴陇麦肥,大公新洗白麻衣,梧桐角响炊烟起,桑柘芽长戴胜飞。老夫闻得那张解元漾了浑家,要去赴试。是和不是,问取我婆则个。(净出唱)
【麻婆子】二月春光好,秧针细细抽。有时移步出田头,蝌蚪要无数水中游。婆婆傍前捞一碗,急忙去买油。
(末白)买油作甚么用?(净)买三十钱麻油,把蝌蚪儿煎了,吃大麦饭。(末)且是恶心!(净)恶心便吃白梅。(末)能吃能解。婆婆,你知件事?那张解元要去赴试。(净)贫女终不成也去。(末)它如何去得?兀底早来[5]98-99。
当经历了两出正戏之后,书会的才人们怕冷了场子,紧接着就让李大公夫妇说唱了一段幽默的戏文来调节场上气氛。在这里,作者通过“久雨初晴陇麦肥”“桑柘芽长戴胜飞”两句告知观众,春天来了,是进京赶考的好时候。显然,这两句景物陈述,起到了环境转换的作用,进而引出贫女前来借钱的戏份,也在情理之中。上述几个方面可以证明,李大公夫妇的戏份对于整个剧情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然而,《琵琶记》里的张太公,对剧情的推动作用远比李大公夫妇大得多。例如第四出《蔡公逼试》:
(外)孩儿,如今黄榜招贤,试期已逼;郡中既然辟召你,你的学问可知,如何不去赴选?(生)告爹爹得知,孩儿非不要去。争奈爹妈年老,家中无人侍奉。(末)老员外和老安人,不可不作成秀才去走一遭。
(生)爹爹说得极是。但孩儿此去,知道做得官否?若还不中时节,既不能够事亲,又不能够事君,却不两下担阁了。(末)秀才所见差矣。老汉尝闻古人云:……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秀才,你这般才学,如何不去做官?
(外)孩儿,你趁早收拾行李起程。(生)爹爹,孩儿去则不妨,只是爹妈年老,教谁看管。(末)秀才不必忧虑。自古道千钱买邻,八百买舍。老汉既忝在邻居,你但放心前去,若是宅上有些小欠缺,老汉自当应承[6]61-64。
从蔡公逼试的进程来看,蔡公与蔡婆的相反意见可谓势均力敌,正是由于张太公的出现打破了固有的僵化平衡,致使天平倾向了蔡公一边;当蔡伯喈为万一考试失利、忠孝不能两全发愁的时候,张太公搬出了“古人云”“自古道”等说辞坚定了蔡伯喈蟾宫折桂的信念;当蔡伯喈担心自己走后双亲无人照应时,又是这个张太公解决了蔡伯喈的后顾之忧,使其放心赶考。可见,张太公的辅助功能要比李大公夫妇强大得多。张太公起的作用均是实质性的作用,进而有效且直接地推动了《琵琶记》剧情的发展。
待字闺中的相门千金。无论是王胜花还是牛小姐,都已经基本具备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诟病的“才子佳人”类叙事文学作品中“佳人”的诸般特点。不同之处则在于,面对强作的姻缘,二者表现出了相反的价值取向。王胜花表现出了不合情理的“气死”:
(净白)覆夫人:胜花娘子病得利害,服药一似水泼石口,汤浇雪上。似病非病,如醉如痴。气长长价吁,泪泠泠价落。饭又不吃,睡又不着。扶将出来,消遣那情怀歇子。(后作病人立)(外)孩儿,你且放下心,依妈妈劝则个。(后唱)
【雁过沙】那一日过丝鞭,道十分是好姻缘。前遮后拥一少年,绿袍掩映桃花脸,把奴家只苦成抛闪。(后低声)被人笑嫁不得一状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状元[5]151-152。
加上后面的六个“被人笑嫁不得一状元”,一共是八句同样的话。一句话反复地从一个人的嘴里出现,足见此人对此事的介怀。张协拒接丝鞭,直接导致了王胜花的似病非病、如醉如痴、涕泪涟涟、茶饭不思。如果“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7]427,那么王胜花的最后时日就是在那一句无数遍重复的话中、无限的痛苦与无聊的精神世界中走过的,她的思维空间里除了痛苦什么都不存在、什么也没剩下。因此,王胜花之死体现出的是不合情理的“气死”。如果说王胜花是因为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那么,《琵琶记》中的牛小姐则更加理智,并没有因为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面对牛丞相的“羁縻鸾凤青丝网,牢络鸳鸯碧玉笼”,牛小姐的一番心事足可使王胜花相形见绌:
【剔银灯】(贴上)忒过分爹行所为,但索强全不顾人议。背飞鸟硬求来谐比翼,隔墙花强攀做连理。姻缘,还是怎的?天那,我待对爹爹说呵,婚姻事女孩儿家怎提?姻缘、姻缘,事非偶然。好笑我爹爹定要将奴家招赘蔡状元为婿,那状元不肯,俺这里也索罢了。谁想爹爹苦不放过。天那,他既不肯,便做了夫妻,到底也不和顺。奴家待将此事对爹爹说,只是此事不是女孩儿每说的话。好闷呵[6]153-154!
这种强作姻缘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在是习以为常之事,即使女方根本没见过男方,也要莫名地承受这一辈子的无言之爱。在福柯看来,现实世界中纯粹的身体是不存在的,它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文化权力紧密运作的对象:“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8]27同理,在封建社会,“身体”也有“任务性”。世家子弟的婚姻行为,往往是权力、政治相互苟合的媒介与通道,年轻人婚姻的符号性远远超出了感情的范畴与婚配的实质。反之,牛小姐认为强作之合是不会给彼此带来幸福的。因此,她抛出了一个闪烁着人文主义光华的关键性论点:“匹配本自然,何须苦相缠?眼前虽成就,到底也埋怨。”虽然牛小姐与蔡伯喈最终结为连理,但是这段婚姻是在牛小姐做出最大妥协甚至是牺牲(让出正室、甘为偏房)的情况下换来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完美,“由于他公平、正直、尽职,因此他有资格要求别人和生活公平地对待他……这种认为生活中的正义绝对可靠的信念给他以权力感。因此他自己的完美不仅是获得优势的手段,而且也是控制生活的手段”[9]209。正是由于牛小姐的极度完美才使得她获得了终身的幸福。因此,有学者认为,“概念化”的牛小姐是“最为抽象”的:“她几乎是没有一点思想感情的偶像,一切行动都受作者的封建礼教观念所驱遣。”[10]367她的功能性质比她的感情性质更为明显。
三、创作愿景的反向变奏
从传播效果着眼,二戏的创作意图与派生效果产生了不可预估的反向张力。
主观愿望的强化。早期的南戏演出大多是为了营利,其商业目的是极为明显的。不难看出,以负心汉富贵易妻为主题的叙事文学创作流传有自。宋人在面对这一主题之时,多持訾詈之态。书会才人在创作《张协状元》之时,并未改变前人或时人对待这一主题的价值成见。从文学流变的角度看,《张协状元》的文本呈现是对前述主题的踵事增华;从创作企愿上看,《张协状元》剧本的客观存在就是书会才人在不违背既有主题价值成见基础上的文化生产与创作谋利。而到了高明处,其创作意图则在于伸张官方哲学所重申的儒家伦理道德,即以浅显的戏曲的方式演绎天道人伦,进而用为蔡伯喈开脱的方式扭转了前述主题由于创作惯性所形成的价值成见。
《张协状元》第一出《开场 诸宫调张协》便把作者的创作目的一语道破:
酬酢词源诨砌,听谈论四座皆惊。浑不比,乍生后学,谩自逞虚名。《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5]3。
这种以否认年轻后生来标榜自己能够于“东瓯盛事”中“夺魁”的论调,显然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听众走进书场。可见,争取听众垂青以盈利乃是书会才人们的第一要务。九山书会的才人多“是不得志于时的小知识分子,他们接近市民阶层,和士大夫阶级的所谓明公不同”,这就决定了其创作目的的差异。《张协状元》的作者姓名无从知晓,也从侧面证明这些才人的创作目的不是“立言”以流播后世,而是单纯的文化产出与盈利。在“但咱们,虽宦裔,总皆通”处,钱南扬先生认为,“宦”为良家子弟,即当时的业余演员。在南戏的草创时期,业余演员为九山书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总皆通”,则说明这位业余演员其实身兼着编剧的职务。《寒山堂南曲谱》卷首《总目·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下注有云:“九山书会捷机史九敬先著”,根据《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附考《捷机引戏》条可知,“捷机”是古剧的角色名,因此这位“史九”便是以编剧的身份参加了剧作的演出。可以想见,在某种戏曲的草创时期,编剧客串演员是常有之事。关汉卿曾经“面傅粉末”“躬贱排场”[11]3,就连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也有同样的经历。一人兼两职,自然降低了草台班子的演出成本,营业的利润自然也会增加许多。
如果说,九山书会的才人们只是为了谋取利润、无关风化,那么到了高明处,则是以宣扬风化为己任了:
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6]29。
吴组缃先生认为:“在古代作家,特别是戏曲作家里,这样明白清楚地提出自己创作主张的,实属罕见。”[12]330在高明的戏曲观中,才子佳人、神仙幽怪类的作品是不足观的。在一个饱经离乱、百业待兴的年代里,高明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喊出了一句“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具有指导思想性的口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汤显祖同样曾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强调戏曲的社会教化功能:
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溃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13]1188。
汤显祖同高明一样,经常以“知识英雄”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经常“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14]2。高明认为,戏曲的社会价值应该高于艺术价值,对观众的内化濡染要强于外在刺激。他要把戏曲由“乐人”的境界提升到“动人”的境界。这其中隐含的信息则是,成熟的文人希图通过对戏曲叙事方式与主题思想的改造让“末技”变“雅品”。有例为证。为了给作为“小道”的小说在文学殿堂上争取一席之地,不少评论家在解读小说时不惜笔墨让小说的题旨向经史元典靠拢。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哂之,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15]166《红楼梦》对于“四书五经”的攀附刚好印证了钱先生之论: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张新之《红楼梦读法》)[16]153-154
古者著人之不善,无非望人之复善而。莫不善于淫奔,而《风》诗采之;莫不善于弑逆,而《春秋》笔之。可以知作者之苦心矣。(紫琅山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16]37-38
高明能够自觉地提升戏曲作品的政治站位、锚定戏曲作品的舆情导向,的确比后来的评论家更为机敏灵澈。《琵琶记》也确实曾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过统治阶层的认可与推荐。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不惜贬低四书五经来抬高《琵琶记》的价值:“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徐渭《南词叙录》)可见,高明的用心没有白费。
客观效果的乖离。九山书会的才人们似乎想凭借《张协状元》赚个盆满钵溢,但是从客观后果来看是事与愿违的。他们不但没有飞黄腾达,依旧贫困潦倒,就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文学史的账簿之上。这种现象,与南戏不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钱南扬先生在《宋元南戏考》中认为,“南戏不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戏十之八九非文人所作,所以辞句鄙俚,为后世文人所不喜”[17]95。“辞句鄙俚”的作品,不但难入“后世文人”的法眼,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阈之内。可见,在没有成熟文人介入的景况中,“南戏不传”与“作者失落”是互为因果的。
蔡伯喈这一高明倾尽全力塑造的“全忠全孝”的形象,吊诡地在《琵琶记》文本的内部出现了“不忠不孝”的潜在倾向。蔡伯喈对双亲“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实为极大的不孝。高明即便用所谓的“立生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来搪塞,仍然显得苍白无力;即便用“三不从”来突显蔡伯喈的无奈,亦是徒劳。反观蔡伯喈所谓的孝行,都只是言在嘴边,并没有付诸于行动。徐渭在《代尝汤药》处作评云:“难道差一个人,老牛也会来禁你!《琵琶》写尽伯喈不孝。”在《瞷询衷情》处亦云:“宁可饿杀爹娘,不可恼了丈人,一向辞婚是假。”[18]45-49《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同出也有总批:“世上有这般怕丈人的女婿,好笑,好笑!丈人还是牛,女婿狗也不值了。”[19]235这些恶评的出现,恐怕是高明始料未及的。更为讽刺的是,《琵琶记》居然成了后世“淫词艳曲”的代名词,成为后世统治者禁书、地方官员进献禁书名册过程中“箭垛式”的作品。据雍乾年间人郝培元在《梅叟闲评》卷一(《郝氏遗书》第十函,光绪十年东路厅署刊本)所言:“《琵琶记》……即全书极言其孝,而父母饿死一节,已令人难堪,其有不关名教乎?”并进一步认为:“戏不可演,《琵琶记》、《西厢记》污渎古人,淫词艳曲不可作。”[20]136高举“风化”大旗的高明,怎样也预料不到,自己成了“名教”的罪人、自己的《琵琶记》成了“污渎古人”的“淫词艳曲”。翦伯赞先生在《〈琵琶记〉的历史背景——在〈琵琶记〉讨论会学术演讲会上的演讲》一文中强调,高明在题岳王墓的诗中有“孤臣犹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之句,在题昭君出塞图诗中亦有“汉庭公卿无远举,却使娇娥嫁夷虏”之句,可见,高明的内心深处存在着“反对夷虏,怀念宋朝”[21]276的倾向。《琵琶记》在“夷虏”的统治下完成,中被朱明“汉庭”视为“山珍海错”,又终被“夷虏”视为“淫词艳曲”而屡遭禁毁。由此可见,作者的主观意愿与作品的客观效果背道而驰,俨然成了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南戏兴起之初,大量下层无名氏文人的倾力创作,让《张协状元》的价值取向更加符合市井民氓的情感诉求,也更能入俚耳。成熟文人高明对“富贵易妻”主题的伦理性发挥,让《琵琶记》的价值取向更能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也更能入文心。《张协状元》的质朴无华奠定了“富贵易妻”主题的原始底色,《琵琶记》的铺张扬厉提升了“富贵易妻”主题的教化功能。如果说,《张协状元》是“富贵易妻”主题的先风,那么,《琵琶记》便是“富贵易妻”主题的后雅。
——辨析聪明、精明、高明、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