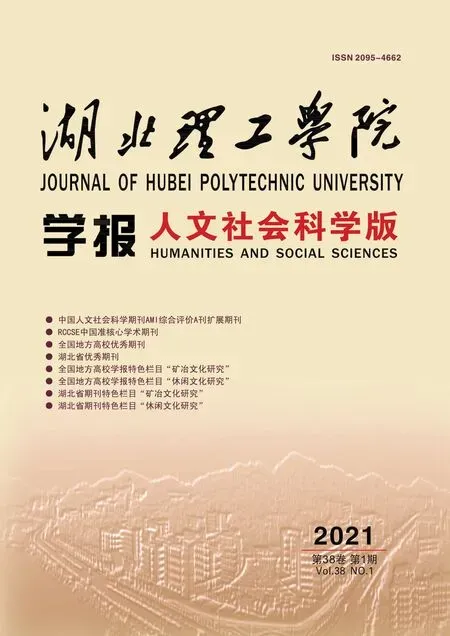休闲审美活动与形象创意
黄 健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旅游休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指出:“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1]刘勰道出了通过形象而创意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创作活动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在他看来,在以心灵自由为特点的休闲活动中,获得审美观感并赋情于形象之上,是形象创意的一个关键要素。
依据这种理路,在读陶渊明的诗《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时,人们就不难感受到诗中形象创意的鲜明特点,也即人在自然美景中,萌发了一种形象创意的冲动:“无车马喧”的“人境”,心境自然是悠远、幽静的,在这种境界中所形成的形象创意之意境和审美观感,也必定是清新、自然、淳朴的。从创作上来看,该诗显然是在一种悠闲的、自由心境的审美状态中创作的,如题为“饮酒”,就不可能是在劳作的状态,而是在轻松自由的闲适状态——心情舒畅,悠然自得,微醉眺望,通透爽朗,独得情趣,参禅悟道,脱俗去尘,故有真意、真言而出。诗以“结庐”,即筑室而开篇,展示在闲适的状态中,在休闲活动中,作者全身心地放松,虽处纷纭人世,却感受不到车马的喧闹,更无世俗琐事和功名利禄的纠缠,超尘绝俗而心有自由,虽在“人境”却无人境之俗,而是高蹈尘俗之上,旷选心怀,故得精妙机制,也就将其中情趣、意趣、理趣等淡淡传出;其中的禅味、禅趣,又是那么的浓馥、那么的淡泊、那么的形象,表现出一种静穆、优雅、自由之美的意境。
一、在休闲审美活动中感知美的形象
黑格尔曾强调指出:“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因为只有形象才是外在的显现。”[2]如果说,形象性是艺术和审美的一个特点,那么,它对于创意思维来说,也是一种动力之源,具有很强的启示性、启迪性的创意功能。由于受到形象的直观认知和启示、启迪,在思维活动中,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心理感知会随着形象的显现特征作出相应的调整,甚至会改变思维通道和方式,调整认识和接受策略,采取更合乎规律、合乎目的的举措,从而顺利完成创意思维活动。例如,人称北宋词人张先(张子野)的词《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写得如此令人称道,如其中的“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写的惟妙惟肖,妙就妙在它的形象的清新、自然、优美:一开始月光被浓云遮掩,笼罩花枝的是一片阴暗;后来,云漂游而去,皎洁的月亮露出来了,银色的月光洒在花瓣枝叶上,微风习习,花摇影动,仿佛是在娇憨地的起舞弄影。可见,没有自由的心境,没有闲适的心态,没有审美的体悟,也就不会有这样独特的形象美感。在这个由美的形象构成的美的意境里,任何人都会产生丰富的人生联想,从中获得审美的观照和心灵的启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高度称赞道:“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美,毕竟不是虚无飘渺的幻影,而是一种形象。所有美的形象,都是通过事物的具象显示出来的,这就给创意思维以非常直观的形象启迪、启发,并激励创造性思维的活力,从而使人们更加卓有成效地在实践中开展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活动。
美的形象,既可以是自然形态,也可以是社会形态、精神形态,同时,各自也是相互交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形态的形象创意,不是单纯地模仿自然形象,而是融入了人的情感和思想,是人化了的形象。同理,社会形态的形象创意、精神形态的形象创意,也会融入自然形象,形成自然形态的形象创意。马克思在谈到神话特点时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自然形态与社会形态、精神形态的形象创意相互交融的特点。因为各自的相互交融,也更能使思维活动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特征。一般来说,自然形态的形象创意,人们大都容易理解,如同朱光潜描述在北海公园散步的情景,无论自然景观形象(如“亭台楼阁呀,花草虫鱼呀,水光塔影呀”),还是人物形象(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呀”),首先是“在我们脑里留下一些映象,其中有一部分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就储存在我们记忆里”[4]。正是这种带有休闲审美特点的形象,让“我们开动一下脑筋,进行一点思维,这种实际生活所引起的思维大部分都是形象思维。”[4]社会形态、精神形态的形象创意虽然相对抽象,但也是可以被认识和理解的,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就展现了兢兢业业、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形象。
当然,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性创造和创意,形象创意是一种精神性、审美性的创造和创新活动,与人的闲适心情和休闲活动有着内在的关联,如同音乐家构思所得的形象要通过声音的节奏、音符和旋律表达出来,这是主体在休闲活动中的一种心智与审美情感活动及其传达。因此,创意思维要造就独特的创造性、创新性的风格,也就要善于刻画独特的形象和意象,进行独特的审美传达,尤其是在主体与客体对应的休闲审美活动中,将这种形象创意发挥得更为鲜明突出、更为自由潇洒、更为生动活泼。以文学为例,文学既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表现和重新审视、建构,又是对心灵世界的独特表现与建构。运用形象创意使文学充分表现人生的创造力,表现人对世界的审美把握,需要主体世界在闲适、自由状态中,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创造性想象,展示其独特的形象并赋予建构的意义。如舒婷在《致橡树》中,就借助“橡树”的形象,创造出一种新颖的爱情表达方式:“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可见,这首朦胧诗的形象创意是十分独特的。它以“橡树”为抒情对象,表达爱情的热烈、诚挚和坚贞。诗中的“橡树”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实像,更是诗人理想中的爱情形象。尽管这首诗不是就某一特定对象而纯粹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借助橡树的形象,诗人创意性地表达了一种全新的爱情理想和信念,既有托物言志的意味,也有直抒胸臆的情怀。全诗选择“凌霄花”“痴情的鸟”和“木棉树”三个独特的形象,形成一种极富意蕴的意象,表现和传达出一种全新的爱情观、人生观:以“铁枝铜干”的“橡树”的形象,形成独特的意象,象征男性阳刚之美;以“红硕的花朵”的“木棉”意象,象征女性阴柔之美,意喻两者间的平等独立、相亲相爱、携手共创人生的美好明天,给人以一种无限的遐想空间。
哲学家柏格森指出,运用形象创意创造出来的独特形象和独特情感,总是会使他“感到足够的兴趣而进入他的思想,融合到他的感情中去,重新处于被他化为诗句的原来的精神状态中。于是我和他的灵感产生共鸣”[5]。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麻雀》,就展示出在休闲审美活动中进行形象创意的特点。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这篇散文的形象创意是以绘画空间造型的形象方式,将生活的一个实景艺术地再现出来,从中展示爱的深沉和伟大。如果说,绘画艺术的特点能够将再现与表现、形象与情感较完美地统一起来,生动逼真地将生活的实景直接诉之于人的视觉,进而震撼人的心灵,那么,文学则是以语言为中介,通过读者结合自身人生经验和审美情趣的阅读,完成作品的第二次创造,特别是完成形象的塑造、认知、接受和融合,使所塑造的形象及其涵养心情的艺术功效得以真正的发挥。在屠格涅夫的这篇散文里,他所描绘的“老雀救雏”的实景,形象创意特别鲜明,也非常的独特,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然而,作者所描绘的形象却不是一个童话般的惊心动魄的动物故事,也不像《探索》《动物世界》《人与自然》等一样的电视片,更不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放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动物的性情与生活场景,而是截取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实景,表现出生活瞬间那种具有强烈的“爱”的情感特征场面,将它特写出来、定格出来,从中表现母爱的力量的深沉、执着和伟大。尽管这篇散文不是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但它描绘的生活实景,特别是所展现的形象,同样能够深深地触动每个人的心灵世界。因为,看起来这是一个个别事件,但是,他不仅仅只是表现动物的母爱主题,同时也是将这种母爱升华到一个哲理的高度,使之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尤其是具有“人学”主题的意义,这就使人们在细细的品味之中,不仅能够产生一种心理情感的共鸣,而且能够让人从中获得人生哲理的启迪,进而促使人性的不断淳化。
二、在休闲审美活动中观照美的形象
通过休闲审美的方式认识形象、表现形象、进行形象创意,不仅能够增强思维活力,而且能够对形象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观照。在这当中,人与形象始终是处在一种和谐的、亲近的、亲密的关系之中,并服从于人的自由意志而进行创意思维,形成主体对客体的超越,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从而展开创意活动,使形象更具新颖度和创新性;不仅拓展了主体的认知范围,而且也藉以实现主体心目中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并将主体的情感、意志和感受、体悟融入其中,使创意更具生动性和形象性。就像德国著名的美学家鲍姆嘉通所说,人对美的形象认识,始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思维过程,而且也是形象不断展示的认同过程。他说:“人们不能从黑夜一下子跨入阳光灿烂的中午。同样,人们也必须借助诗人们创造的令人眼花缭乱、但却是生动的各种意象,才能从无知识的黑暗转向明晰的思维。”[6]在形象创意中,创意思维的认识过程并不是被动地由形象所牵制,而是主客体在相对自由、闲适的审美环境和活动中,以主体的认知与感知方式,通过形象的观照、塑造来展示主体的活动,表现出主体对客体所具有的充分自主性和超越性,进而使其更具创造性和创新性。
形象创意思维活动往往是以生动、可感、可观照的形象和能够产生共鸣的心理情感、情怀的相互融合,来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在这当中,形象在展示创意思维时,总是能够把通常难以用抽象的逻辑语言传达的情绪、情感和深藏在心灵深处的内心活动,统统纳入思维活动表现的范围,把人在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进行精神探求中的那种说不清、道不尽、剪不断、理还乱的朦胧情绪与情感,真切而细腻地描绘出来,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因为这种情绪、情感,实际上也就是人在精神探求当中那种寻找家园式的绵绵乡愁和心理活动,特别是在相对自由、闲适或休闲的心境和活动中,这种极具审美意味的形象创意,更能引起人们的心理情感的共鸣。譬如,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的那首题为《回乡偶书》的诗,就借助“客”(“游子”)形象表现出他那种长期在外的对故乡的深情。显然,这种“客”的形象,不仅仅只是寄托他梦魂萦绕的故乡和家园之情,而且也更深层次地传达出一种人生哲学的涵义,即: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没有精神家园的人,犹如无家可归的人;精神家园残缺不全的人,当是世界上最可怜也是最可悲、最不幸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贺知章的这首诗,可以说,它通过形象创意的方式表现了人寻找、建构精神家园的人生哲理主题。诗中的“客”的形象既是写实的,也是写意的。这种形象中既包含着诗人渴望回到故乡的急迫心情,“乡音无改”式的对故乡的忠贞、赤诚,又有“近乡情更怯”的复杂心理感受,还有被乡里儿童“笑”作“异乡客”的隐痛之情,更有寻找精神的归宿、灵魂的归宿的心理企盼之情。这种形象所包含的“家”的内涵,并非仅仅是指现实生活层面上那个属于物质性的“家”,那个曾经的家乡、家园,更重要的还是指追求无限生命意义的那个“家”,那个精神的家乡、家园,显示出他对不断建构精神家园的一种情感诉求、心理渴望和生命哲理。因此,“客”的形象创意,就包含着对亲情、对故乡、对家园的不断寻找、不断建构的心理情怀和精神追求,告诉人们“家”“家园”的价值永远都是精神性的、内质性的,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还乡”心理情结。可见,当形象创意将美好的形象直接赋予对象世界时,这种形象就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种理想之美的熏陶。
再来看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的一首抒情诗《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诗的开头就以“假如我是”点明抒情主人公——“雪花”的形象(也可以看作是诗人自我的形象)特质:自由、超然、轻松、飘逸。在诗中,散发着朱砂梅清香的“姑娘”形象,不仅仅是诗人心中的理想爱人,也如“雪花”一般是美好、美丽的化身。全诗借“雪花”的抒情形象,用拟人化艺术表现,比如,借“雪花”的言语、行动,以及它认清方向寻觅中的专注、认明目标飘落的欢乐,抒发出诗人对心中美好事物的热情、勇敢、坚韧、执着和不断追求的精神。尤其是“雪花”的自然形象,已经完全被赋予诗人的主观情怀和主观感知,从而具有了诗人的生命意识,具有了人的生命灵性。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说,人生有了理想,才会有不断追求的精神动力。这就是人生的法则。赋予这个法则以美的智慧、自由的活力,就一定会起到进一步强化人生的理想信念的作用。因此,在形象创意中,将主观感知直接赋予对象世界并使之得以审美化的表现,就会大大地增强形象创意的精神内涵功能。
朱光潜在论述思维活动中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特点与异同时指出,二者共同构成了思维活动的整体,其中,形象思维的第一步是“掌握具体事物的形象”,第二步则是“把从感性认识所得来的各种映象加以整理和安排来达到一定的目的”,然后再“把许多感性加以分析和综合,求出每类事物的概念、原理或规律”,实现“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与“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一道形成整个思维的活动过程[4]。无疑,形象创意属于形象思维的活动范畴,与逻辑思维一样都是思维活动的一种形式或形态。运用形象创意就必须遵守形象思维活动的规律,在整个创意思维活动中都需要以鲜明的、新颖的形象伴随始终,使思维活动具有充分创造和创新的活力。当然,形象创意不仅仅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在其他的各个领域都会运用到,如朱光潜就以古代民歌《箜篌引》为例:“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指出形象思维是“一切艺术的主要的思维方式,不限于诗,也不限于比、兴”,在思维的各个过程、在认识的各个方面,都是需要形象思维的,这样才能真正地认识和观照美的形象,展现出美的形象所蕴含的一切美的特质[4]。
三、在休闲审美活动中表现美的形象
在休闲审美活动中,运用形象创意表现美的形象,除了在文学艺术领域运用比较广泛、全面、普遍之外,在其他领域的运用也很广,如在园林、建筑、平面设计等方面运用形象创意也是非常普遍的。中国园林就是最为典型的运用形象创意的例子。如苏州园林,它的形象创意就深深地凝聚了中国文人和工匠卓越的审美智慧,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宗教、美学、艺术等深厚的哲理内涵,表现出师法自然、融入自然、顺乎自然、表现自然、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思想和美学理念,突出了人在自然空间中的闲适审美心理,充分表现了休闲审美的形象创意特点。
中国园林在特定的空间内,选择诸如水、山(假山)、花木、动物(鸟、兽、鱼、虫等)、具有特色的建筑(堂、楼、馆、榭、轩、舫、亭、廊、桥、墙等),精心布局,采用抑景、添景、夹景、对景、框景、漏景、借景等方式,将时间凝固,使之成为对应人的心灵世界的审美形象物体,从中获得永恒的审美观照。正如李泽厚所言:“园林艺术日益发展,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为目标的建筑美出现了。”[7]在休闲审美活动中运用形象创意,表现美的形象。中国传统园林在形象创意上,更是彰显出主体的自由意志,以及认识客体、把握客体、超越客体的审美理念。在古代社会,尽管处处强调主体、处处受到理性的规约,但主体的自由意志仍然是要最大限度地追求情与理的融合,以主客体相融的自由和超越来进行形象创意,是要追求合乎规律与合乎目的的“顺其自然”,而非绝对化的“任其自然”形象创意。显然,这种审美理想落在实践的层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对应人(主要指士大夫阶层)的闲适心理,满足人的休闲审美活动的需要,更要让人在紧张、繁忙的世俗生活中,尤其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在休闲审美活动中获得心灵的休憩、宁静、超然和洒脱。陈从周就指出:“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8]的确如此,用形象创意追求园林建筑和环境布局的美学意境,也就是旨在园林这种独特的、非常适合人的休闲审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中,让人获得与心灵对应的审美自由,特别是通过闲适的生活方式和休闲审美来进行形象创意活动,就能够在主客体之间架设一座审美的桥梁,让生命的意义得以更加完整和完美地形象呈现。
在园林修复的实践中,陈从周就是秉着这种理念,非常注重将形象创意运用其中,最典型的是他指导杭州郭庄(汾阳别墅)的园林修复工程。他曾在《解放日报》上撰文宣称:“不游郭庄,未到西湖”,并称其为“海内孤例”。他如此偏爱郭庄的原因就在于,作为中国园林典范,尤其是江南园林典范的郭庄(汾阳别墅),能够充分地巧借西湖之景,与周边的湖、山、堤融为一体,以巧取胜,以一当十,布局典雅,别具情趣。如郭庄内设“两宜轩”,取“也宜风雨也宜晴”之意。从布局上来看,其巧妙而又形象地把园林分为两处:一处名“静必居”,为园内主人起居之地;另一处曰“一镜天开”,有曲廊围绕一池清波,如一块方镜可揽风月,池水更与西湖相通,有短墙一带隔出园外的一个平台,正对苏堤。进入平台内,视野开阔,一条长长的苏堤映入眼帘,远处的湖光山色也尽收眼底,可谓风光无限好,任我尽逍遥,好一个自由自在的审美快慰。在郭庄修复成功之际,陈从周特意写下一篇《重修汾阳别墅记》,立碑于园中,碑记写道,此园“园外有湖,湖外有堤,堤外有山,山外有塔,西湖之胜汾阳别墅得之矣”。他还特意题诗一首:“苏堤如带水溶溶,小阁临流照影空。仿佛曲终人不见,阑干闲了柳丝风”(《西湖郭庄闲眺》),这种闲适的情趣、休闲审美的活动,更是把他对郭庄的形象创意得以诗意地展现。
在建筑设计领域,形象创意也是应用非常广泛的。基于文化和审美的差异,相比较而言,中西建筑设计在形象创意上各自走了相对不同的道路,也呈现出不同的创意形态。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就曾对中西民族建筑的艺术风格特点进行了比较,认为西方哥特式建筑,总是以“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形象,让人产生“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的心理感觉,给人一种鲜明的对立感。中国的建筑形象则不然,为适应“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建筑形象是属于那种“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类型,其特点是以“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的方式,给人一种庄重而又亲切、严谨而又跃动、神秘而又世俗的审美观感,也即“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7]。也就是说,要充分地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人的休闲、特别是休闲审美活动的需求,让人在世俗生活中就能够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超越。可以说,依据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传统建筑形象创意的理念追求,目的是要在世俗生活的愉悦中对应闲适的内心世界,功能上也要求与休闲审美活动保持密切关联,做到“可望”“可游”“可居”,也即李泽厚所说的是“供享受游乐而不只供朝拜顶礼之用”,力图在世俗生活中追求闲适,注重以休闲的方式获得审美的愉悦,以更加自由的心境捕捉新的创意形象,进行饶有审美趣味和更为自由自在的创意思维活动。
而依据西方文化理念,西方传统建筑设计则受宗教理念的规约,其形象创意需要更多地展现“此岸”与“彼岸”的对应、对接和对话,寻求神的庇护与救赎,从中获得心灵的平静。相比较而言,西方的传统建筑,如哥特式建筑的形象创意,多以直耸苍穹的形象方式寓意与上帝的无限接近,其特点是以直立高耸的形象,营造出仰望天空、聆听来自上帝之音的建筑观感,因而在设计中多注重利用十字拱、立柱、拱门等大型的石块结构,展示出上帝与人间的互动感,尤其是其框架性的结构,增加支撑顶部的力量,使整个建筑能够以直升线条、雄伟的外观和教堂内的空间结合,配以镶着彩色玻璃的长窗,使整个建筑形象更加具有鲜明的宗教仪式感和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以此凸显生命意义的严肃、神圣、崇高和庄重。
与此相反,中国传统的建筑,其形象创意多在建筑的组群布局、空间、结构、建筑材料及装饰艺术上下足功夫,展现所塑造的形象的自然性、自在性和亲自然、亲人性的特点,让人在建筑中获得心灵的自由感和愉悦感。不同民族或南北建筑无论有何不同,也不论儒家崇尚“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还是道家推崇“自然无为”,都认同“天也,自然也”。中国建筑形象的自然理念和所追求的建筑实践效果,都旨在展现出生活在世俗世界的人们对于有限生命的精神超越,对于无限生命意义的热烈追求。如同《周易·乾卦》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强调的都是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天、地、人的类型互动体系,特别是要展示出通过休闲审美活动而获得世俗生活的超验价值和意义证明。由此可见,休闲审美活动与形象创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仅是大大地促进了创意思维、形象创意的创造活力和创新价值,也更是展示出创意思维,特别是形象创意所包含的深厚文化和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