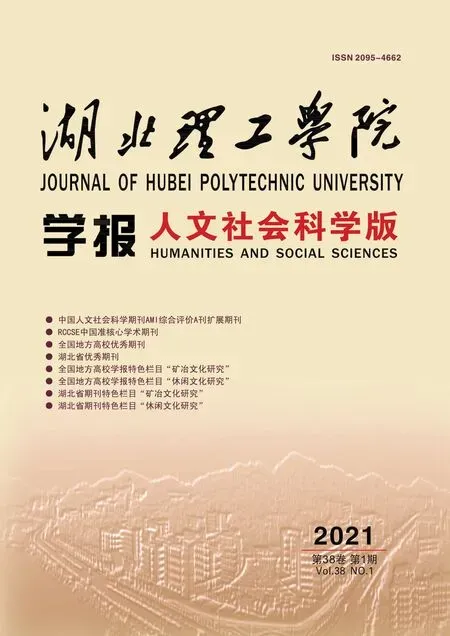鄂王城遗址研究
——兼论鄂、楚封鄂王
龚长根
(黄石市博物馆,湖北 黄石 435003;湖北理工学院 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黄石 435003)
最近看到一本官修《黄石文化简史》,其中对楚国历史的阐述有些地方与历史记载不符,尤其是对鄂王城遗址的论述。其作者以为:“西周末年,黄石隶属楚国。西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79年),楚王熊渠占领扬越,封中子熊红为鄂王,黄石时为鄂王封地。”“鄂王城作为丹阳之后的楚国国都,略可考订。”[1]此外,某些对鄂王城遗址进行探索的书刊、文章更是错漏颇多。本文不一一而叙,也不一一而论。
古鄂国、楚熊渠所封鄂与鄂王城遗址(今大冶金牛)这三者之间其实是相对独立的关系。即熊渠所封鄂与鄂国是不同地域的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鄂王城遗址与古鄂国、熊渠所封鄂时间上相距四五个世纪,空间上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一、关于楚封鄂王与鄂王城遗址文献资料概略
一些地理著作与史籍对楚封鄂王与鄂王城遗址多有记述,下文予以梳理,或可解开一些谜团。
有关《史记》楚封中子红为鄂王的相关记载比较早的大约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其卷三十五云:“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也,《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之名,某者为鄂王①。《晋太康地记》以为东鄂矣,《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2]
李泰为唐太宗第四子,其主编的《括地志》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完成。其卷四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史记·楚世家》中子红为鄂王。’”[3]
李吉甫为唐宪宗时宰相,地理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其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完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其第二十七卷《江南道·三》载:“武昌县,西至州一百七十里。旧名鄂,本楚熊渠封中子红于此称王,至今武昌人事鄂王神是也。”[4]
北宋初年,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载:“又世本云,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今武昌县地也。”“鄂王城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偕称王居此城。《九州记》曰,今武昌是也。九州记略同,今鄂人事鄂王神即遗像也。”[5]
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三十三载:“兴国界于吴楚之间。云,春秋以来属楚。楚世家云,楚熊渠伐扬越于鄂,封其子红为鄂王。《九州记》曰:鄂今武昌。”卷六十六载:“自周夷王时于楚,楚熊渠封其子红为鄂王(《史记·楚世家》)。又寰宇记引楚世家本云:今武昌县是也。鄂之名始此。”[6]
清初历史和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二》载:“武昌府东北百八十里。东南到大冶县七十里,西北渡江至黄州府十里。春秋时封鄂王于此。”“鄂城县西南二里。本楚邑。《史记》:熊渠当周夷王时,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又封中子红为鄂王。孔氏以为南阳之鄂,误矣。时楚兵未能逾汉而北也。”[7]
清康熙十二年修《武昌县志》卷一《沿革》云:“周夷王八年,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按史:熊渠、熊鬻、鲁孙甚得江汉民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今县西南二里有鄂王城。”卷二《古迹》云:“鄂王城在县西南二里,楚子红封国城。今马迹乡有鄂王故城。《土俗编》以为故鄂城是也。”[8]
清光绪十一年编撰的《武昌县志》则对鄂王、封地以及鄂王城记述是最丰富的。其《沿革》云:“周为鄂属楚。熊渠生三子。当周夷王之时②。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③。乃立其长子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9]卷九《古迹》又云:“鄂王城在县南(按当作西南)一百二十里。周夷王时,楚熊渠封中子红于鄂(《王会新编》)。鄂王城即楚封子红处,在县西南二里,东西九十步,南北百步④。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9]
关于楚封鄂王及相关内容还有其他文献资料有记载,如《大明一统志》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史记·楚世家》。梳理这些文献资料可知:
其一,北魏时期的《水经注》、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南宋的《舆地纪胜》、清代的《读史方舆纪要》述及周夷王时熊渠封红为鄂王内容时,均认为鄂王的封地是东鄂(今鄂州),如今这里还有庙宇供奉鄂王,如鄂王庙。值得注意的是,这几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都没有提及鄂王城遗址。
其二,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开始出现鄂王城遗址,并认为是中子红故城。此后清康熙、光绪年间的《武昌县志》进一步详尽阐述中子红与鄂王城遗址的关系。
据上述资料作结论为:1)所列文献均认为西周时熊渠所封鄂王的封地治所为今鄂州;2)认为“鄂之名始此”,即熊渠封鄂王时开始;3)因为马迹乡(今大冶金牛)有名为鄂王城的遗址,故历史学者们便把此城与熊渠所封鄂王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这些结论均不符合历史事实。
二 、楚与熊渠所封鄂王
关于楚,《史记·楚世家》有比较明确的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10]1689-1692所谓子男之田,也就是方五十里,爵位虽然低,但总算是有个名正言顺的封号与封地。那么丹阳在哪里呢?这是一个争论了2 000年的历史悬案。主要有五种说法,即江南、枝江、秭归、先秭归后枝江以及丹浙之说。虽然楚丹阳地理位置之争还会继续下去,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此时的楚人还未走出现在的鄂西山区。《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11]《左传》这段文字也证实了楚在熊绎之时也就是西周早期,还处于荒凉的原野山林之中。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为“子男之田”时,也就是楚国正式建国,那时楚人贫弱得很。《楚居》简4记载:“室既成,无以纳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是说,楚人的宗庙建成后,没有东西来祭祀,不得已便偷窃鄀人的小牛来祭祖。《楚居》亦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是其63篇书中的一篇,系战国中期楚国史官所写。
西周中后期,周王室中落,各路诸侯趁机作乱。“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10]1689-1692
相对于西周王朝,此时的楚国还只是小国寡民,虽然趁机在攻打庸、扬越、鄂时占了一些便宜,但仍然不可能占领族大势众的扬越,包括鄂。是时,扬越范围包括长江以南至沿海广大地区[12]。公元前877年,周厉王继位。面对凶狠、暴虐的周厉王,自知其力量还不足以与周王朝相对抗的熊渠,遂主动“去其王”,即取消了三个王的封号。事实上熊渠只是名义上封了三个王,庸、扬越、鄂并没有成为楚的领地。《史记·楚世家》载:“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红立。摯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因为继承人康早死,接着熊渠一死,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王位遂弑兄而立。残酷的内斗也削弱了楚国的实力,这段时期是楚国发展的低潮期,势力范围基本还在丹阳附近。
及至“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公元前790—前677年),土不过同”[13],这已是熊渠之后80余年的事情。按周制,“方百里为同”。楚“成王恽元年(公元前671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此时的楚国,还得韬光养晦,必须向周天子朝拜进贡,而天子则回赠腊肉,并要求楚国好好的镇守南方,不能让“夷越”犯上作乱,更不得侵扰中原地区。所谓“夷越”应该就是包括鄂东南、安徽东部、江西及湖南接壤今湖北的邻近地区。就是说直到楚成王(公元前671—前626年),即春秋中前期,楚国才取得了扬越地区名义上的统治权利。《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证实:“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疆。……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14]1491
或许由于历史和所谓正统观念的因由,《左传》的记载似乎对“楚蛮子”不屑一顾,甚至有些蔑视和偏见,但楚人也只是在春秋时期以后才落脚江汉平原地区,其地域尚未越过现在湖北的中部地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界先后在鄂州、大冶以及周边的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发掘了大批的楚墓和其他楚文化遗存,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只有极少数墓葬时代为春秋晚期,其他绝大部分楚墓的时代为战国时期。这说明楚国的势力是在春秋晚期以后进入鄂东南及周边地区的。
结论:熊渠因畏周厉王伐楚,即刻把分封三个王的封号取消了,即“亦去其王”;在楚人到达鄂东南地区以前,这里有一个名为“鄂”的政治实体或诸侯王;西周时期,楚人还没有统治鄂东南地区。
三、鄂
鄂,商周时期的诸侯国,见诸史册的主要为《史记》和《战国策》。《史记·殷本纪》载:“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疆,辨之疾,并脯鄂侯。”[15]106鄂侯,《战国策》也有记载:“鲁仲连曰:‘昔者之鄂侯、鬼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16]这与上述《史记》记载的是一回事。鬼侯,即九侯;文王即西伯昌。这些记载是说:文王、九侯和鄂侯曾是商纣王时的三公,地位很高。九侯有漂亮的女儿,献之于纣王。九侯女不淫荡,纣王非常不喜欢,并把敬献美女的九侯处死后剁成肉酱。为此鄂侯与纣王发生激烈争辩,纣王又处死鄂侯并将其做成肉干。
关于鄂,有学者认为:“一个以捕鳄为生,且以鳄为图腾的部族,便以噩为部族名称。在商代时形成了鄂国,地点在今山西乡宁县。西周初年,鄂国的故地被晋所并,遗族南迁到河南南阳,仍叫鄂国。因受楚的威胁,于西周中叶,又南迁到湖北鄂城,仍叫鄂国。”[17]也有学者认为:“东鄂之所以称‘鄂’,或许正因为它为越人所建,而越人则恰是崇拜扬子鳄的”[18],鄂原本就是南方扬越文化的一支。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有两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其一,至迟在商代末期,鄂、鬼侯与文王的实力已对商王朝构成威胁,于是纣王演绎了一场“醢九侯”“脯鄂侯”的政治屠杀;其二,商周时期,在扬越所属区域即今鄂东南地区确实存在一个鄂。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百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称谓,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19]《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臣瓒语:“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 事实上,那时的百越应该是一个比较松散而相对统一又多样的民族集团,这个集团是由不同的时空共同体组成的,他们在文化上也是有区别的。鄂就是百越其中的一支。大约从新石器时期开始,百越曾在大冶,当然也包括鄂东南以及周边地区繁衍、生息、创造。从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和考古资料综合来看,古越族的生存时空范围与考古学分布地域是相互重合的。也就是说,百越的一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生存于湖北东南部、江西等地区。“因而我们推测,最早在大冶地区开采铜矿的,当然也包括江南地区其他同时代铜矿的都是古越族文明所开采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大约是商至西周前后时期,鄂作为‘百越’的一支或方国,占有铜绿山古铜矿和大冶地区的铜矿资源。”[20]
据《竹书纪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公元前940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21]。这也告诉我们,在西周早期之前,江西九江和毗邻的鄂东南地区是越人聚居地,或者说是百越势力所辖地域。西周后期,楚熊渠“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即一直打到了扬越的鄂而止。
结论:在楚人抵达今鄂东南之前,鄂便存在于此,之后楚以“鄂”为王只是地理名称的沿用。
四、鄂王城是战国时期遗址
从20世纪70年代至2014年间,大冶市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鄂王城遗址进行过多轮科学的考古调查或考古发掘。其结论是:这座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征。
1982年9月—1983年5月,黄石市博物馆、大冶县博物馆联合对鄂王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对该城遗址周围分布的墓葬群予以初步勘探[22]。1983—1987年,黄石市博物馆单独对鄂王城遗址又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23]。2013—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市文物局亦对鄂王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24]。
鄂王城遗址位于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村胡彦贵湾,城址北约400米为陈经户湾,东距高河港约300米,西侧为九龙水库,西南、南分布着细屋下邹、坑下董、下邹等自然村。城址建于高出周边地表约8~15米的台地上,城址大体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20米,南北宽约360米,面积约151 000平方米[24]。在西南城角较高的台地上测得坐标为北纬29°59′20.1″;东经114°32′58.4″;海拔40米。
1982—1983年调查时,地面可见土筑城垣。其中,南垣、北垣因修水库及筑堤,地面部分遭破坏,东垣、西垣尚存。城垣为红褐色土夹黄斑土夯筑而成。城垣两侧面的夯土层内包含有较大数量的东周时期的陶瓦片。当时,城垣有缺口共7处,疑为城门遗迹的两处:一处位于东垣偏北,地名为大东门,缺口北端城垣向外伸出;另一处位于北垣中部,地名为北门,缺口东端城垣向外伸出。在鄂王城西部以及西南、西北岗地上发现有成片的封土堆和墓葬。至2017年,共发现封土堆、墓葬229座。墓葬区距离鄂王城1~4华里,分别分布在尖角山、下邹山、上邹山、石头咀山等岗陵地带。我们曾对部分封土堆进行了勘探,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根据鄂王城城址内外出土的文化遗物,如筒瓦、板瓦、瓦当和铜戈、铜箭头、陈爰(楚国金币)等来看,时代应为东周。至于现存城垣,因夯土内有较多的东周陶片,因此时代也可能较晚。”[22]
1983—1987年间,我们多次对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鄂王城遗址的城垣有二十余处横断面,城垣有两次修建现象,即两次所建城垣之间夹有东周遗物,因此两次筑城的时代都不会早于东周。再从鄂王城城垣平面结构来看,其东北角、西北角、西南角均呈切角形,这种建筑形式与江陵纪南城十分近似[25],而楚都“现存规模宏大的纪南城城垣形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鄂王城形成的年代应晚于纪南城[23]。
鄂王城内出土的陶器多为春秋战国时期遗物,以数量较多的建筑物残板瓦为例,瓦外表均饰绳纹,有的两端抹平;瓦里面多以素面为主,有少量方格纹、菱形纹、斜方格纹等。这些瓦的制作方法、风格及形制、纹饰等特征,都与江陵纪南城西垣北门第五层出土的残瓦比较接近。而纪南城西垣北门第五层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所出土的圜底壶,唇外折,颈较高,鼓腹圜底,腹饰绳纹,这也是春秋战国之际楚人常用器物之一。鄂王城内出土的半圆瓦当,这种浮雕式卷云纹半瓦当从发展趋势来看,战国晚期普遍向卷云纹发展。这些较为典型的器物证实,鄂王城筑成时间约是春秋末到战国时期[23]。
2001年6月25日,鄂王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2014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鄂王城遗址局部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如图1所示,其城垣周围有护城河环绕,在城址西南角被引水渠的堤坝隔断。城址东垣略靠北以及西垣靠南各有一缺口,疑为城门所在。此次调查发现,地表文化遗物较多,但大多为绳纹板瓦之类,器物口沿、器足等发现很少。为进一步弄清遗址的文化堆积状况,我们在城址2处铲开剖面,一处位于西城垣,堆积分为4层,4层以下为文化层,未向下清理,遗物多为板瓦、筒瓦残片;另一处位于城内西南角一处已开挖的水沟断面上,堆积也可分为4层,4层以下有文化层,遗物同样为板瓦残片及少量碎小陶片。
“初步判定城垣分四期:第一期为城垣修筑时期,年代为战国中晚期;第二期为城垣护坡期的加修期,年代为战国晚期至汉初;第三期为宋代;第四期为清代。”[24]
综上所述,鄂王城遗址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大冶鄂王城建成时已距楚王熊渠封鄂大约四五个世纪。

图1 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遗址地形及位置
五、鄂王城遗址绝非楚国别都
有学者非常热衷把鄂王城遗址论证为“楚国别都”或云“殷商时曾是古鄂国都城”[26],这些牵强附会的演绎,毫无节制的推理,完全忽视了一个科学的学科——考古学,这已经超出了学术争论范围。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已近一百年,采用多学科技术鉴定一个古城址的年代,是一件既容易、又靠谱的事。之所以有人认为楚曾经别都于鄂,大概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楚曾封中子红为鄂王,中子红又曾继承熊渠的王位;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武昌(今鄂州)嘉鱼县太平湖所出的一件楚公逆钟;而鄂东南之地又有鄂王城遗址。
其实,有关鄂王封地或城址还有多说:如西鄂(今河南南阳)、随州等。事实上,战国中后期“鄂君启受封的时间、地理位置与鄂王城遗址相符合,故而推断,鄂王城当是鄂启受封之故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战国之鄂”[27]。
关于鄂为楚别都,似乎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夜雨楚公钟跋》有关系。跋文云:“作钟者,为楚公屰,瑞安孙仲颂比部以为即《史记·楚世家》之‘熊咢’。咢本从屰,二字形声皆相近,其说不可易矣。此器赵氏《金石录》谓出鄂州嘉鱼县。复斋《款识》引石公弼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进’。武昌、嘉鱼,南境相接,盖出二县间矣。案《楚世家》言熊绎居丹阳,至文王熊赀始都郢,中间无迁都事。惟言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母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卒,子熊挚红立,后六世至熊咢’。今熊咢之器出于武昌者,武昌即鄂。盖熊渠之卒,熊挚红即中子红。虽嗣父位,仍居所封之鄂,不居丹阳。越六世至熊咢,犹居于此,故有其遗器。楚之中叶曾居武昌,于史无闻,惟赖是器所出地知之耳。”[28]先生说得明白,所谓鄂为楚国别都:其一,“《楚世家》言熊绎居丹阳,至文王熊赀始都郢,中间无迁都事”;其二,“楚之中叶曾居武昌,于史无闻,惟赖是器所出地知之耳”。说白了,就是说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资料证明楚曾别都于鄂,完全是因为武昌嘉鱼县出土了一件楚公钟(如图2所示),所以猜测楚别都于鄂。这实在是很牵强,甚至有些荒唐。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学者们把北宋政和三年武昌嘉鱼县所出的一件楚公逆钟用来证明鄂为楚国别都,还是情有可原的,毕竟那时非常缺乏科学考古资料,出土文物也有限。现在科学考古资料要丰富许多。1993年,考古工作人员在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8件楚公逆钟(其中一件如图3所示),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而云那个地方曾是楚国的“别都”,或云楚人在那个时代就统治了山西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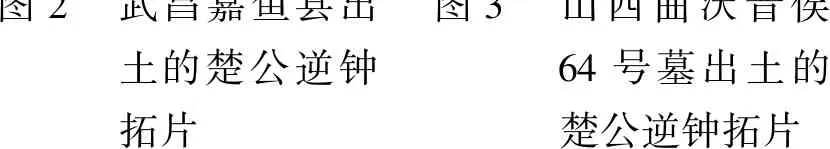
图2 武昌嘉鱼县出土的楚公逆钟拓片图3 山西曲沃晋侯64号墓出土的楚公逆钟拓片
如果鄂为楚别都只是猜想,那是另一回事。今天的学者们真没有必要非要把鄂王城这座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的小城址,拼命的往西周时期(公元前约11世纪—前771年)拽,如此甚是荒唐。鄂王城遗址与熊渠所处时代相距四五个世纪,这是经科学考古得出的结论。
注 释
① 《史记·世家》云,熊渠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② 按《竹书记年》作夷王七年,熊志作八年误。
③ 按《史记·正义》刘白庄云: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东,今东鄂州是也。《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
④ 《舆地纪胜》按《名胜志》引《九州记》: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属马迹乡。考,马迹乡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距府冶一百八十余里,与《寰宇记》所称在鄂州百八十一二里正合。今遗址关门石尚存,土人呼为鄂王城。其为楚封址无疑。《舆地纪胜》《名胜志》所据里数或是误说,今县西南二里滨湖,亦无故城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