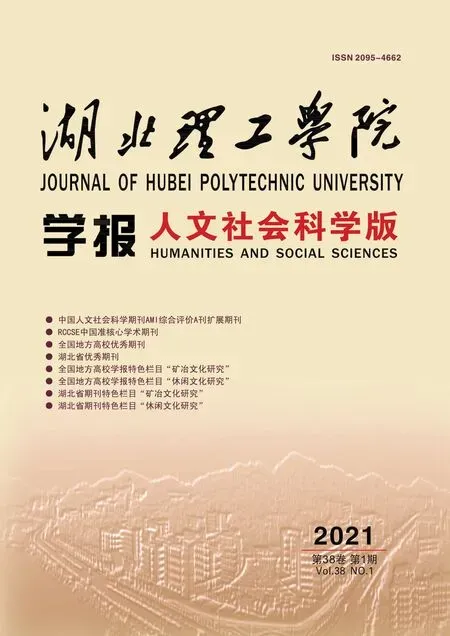孔乙己:丢了笔杆子的“堂吉诃德”*
——重读鲁迅小说《孔乙己》
孟 亮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孔乙己的“堂吉诃德气”
孔乙己是一个带有鲜明的“堂吉诃德气”的人物,然而在讨论孔乙己的“堂吉诃德气”之前,有必要对“堂吉诃德气”进行简单的界定。《堂吉诃德》一书中,塞万提斯在描画堂吉诃德整日整夜“沉浸在书里”,终于弄得“脑汁枯竭,失去了理性”,并满脑“荒诞无稽”“固执成见”,深信骑士小说“千真万确”,还打算将书里的事去“一一照办”的精神形象和气质时,曾两度指出他“失去了理性”[1],即最初对“堂吉诃德气”的概括与“理性”一词是紧密关联的。“鲁迅将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与‘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哈姆雷特’相对照”[2]的表述,就暗示了这种“冥想”和“怀疑”的理性的缺失。钱理群在分析堂吉诃德形象时,也认为堂吉诃德将内外世界混同,“以理性、想象代替感觉,内部世界代替外部世界,把幻想当做实质,形成了思想的混乱”[2],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堂吉诃德确实是一个‘文学病’患者,所谓‘堂吉诃德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于书本所构置的虚幻世界的迷恋。”[2]所以,“堂吉诃德气”最初是指堂吉诃德本人在失去理性后对书本虚幻所抱的迷恋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与书本文化和精神层面是紧密联系的。
随着堂吉诃德的传播和东移,“堂吉诃德气”也已超越了堂吉诃德的个人界限,成为泛文化意义和精神心理上的一种独特气质。在西方,匹克威克、罗亭、英沙诺夫等人共同组成了“堂吉诃德气”的知识分子圈[2]。在中国,人们同样把鲁迅笔下的阿Q看作堂吉诃德型人物,认为后者“主要是堂吉诃德精神的消极方面,即把想象、主观愿望中的世界当做现实世界的精神迷乱”,并“完成了从现实的物质失败到想象中的精神胜利的心理转换,从而形成了一个‘真实的失败——想象——虚幻的胜利(精神满足)’的心理模式”[2]。而这种模式,是“中国的农民,早已失去了西班牙骑士的积极进取精神,既无追求理想的执着,又无为理想献身的意志与热情”[2]后的结果。换言之,发展了的“堂吉诃德气”既包含了堂吉诃德本人及其他知识分子身上的进取精神的积极一面,也包含了精神胜利法的消极一面。
由此,我们可以对“堂吉诃德气”进行这样的界定,即“堂吉诃德气”最初是指堂吉诃德本人在失去理性后对书本虚幻所抱的迷恋,后发展成为一种泛文化层面和精神心理上的独特气质,泛指一切忽视现实的对于精神层面的迷狂。孔乙己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鲜明“堂吉诃德气”的人。
首先,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对孔乙己的“堂吉诃德气”进行精神上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孔乙己与阿Q的“堂吉诃德气”是不同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写得一笔好字”,满口“之乎者也”,是懂得“茴字有四样写法”的读书人身份。吴小美、李向辉对“孔乙己又正是封建主义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末代的落魄知识分子”的定位是无疑的[3]。但另一方面,孔乙己确实是一名堂吉诃德,是欧洲知识分子、“西班牙骑士的进取精神”和“中国的农民”阿Q“(精神满足)的心理模式”之外的另一样式的堂吉诃德,即知识分子堂吉诃德中落魄的一类。堂吉诃德本人曾有一番“文武两行”的奇论,把有识之士分为“拿枪杆子的”和“拿笔杆子的”[1],而当“拿笔杆子的”失掉了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知识和话语权时,就出现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个失掉了笔杆子的堂吉诃德。
这种身份的丢失直接导致了孔乙己对酒的迷恋。小说中的孔乙己终篇都在与酒打交道,因酒与咸亨酒店结缘,同时也在酒的心理满足中逐渐死去。在不少论者的论述里,都提到了“酒”之于孔乙己是有某种精神寄托在的[4]。“孔乙己嗜酒,有满足生理需求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是他企图通过喝酒来满足他社交、尊重的需求。”[5]王明科和柴平二人也提及“孔乙己是价值信仰的殉道者”,而酒就是这种精神信仰的内在逃避和寄托。由此可见,酒之于知识分子孔乙己的价值迷恋和逃避功用是很明显的。
其次,孔乙己对读书人身份的迷恋与他的话语迷恋是分不开的,即使只从表现上看,孔乙己也是“堂吉诃德气”十足的。孔乙己在面对酒客们的取笑时,曾有过不同种类的辩解。在他断腿时这样辩解:“跌断,跌,跌……”被人道破偷书的事时,又拿“污人清白”和“窃书”这样的词汇澄清,即使是分茴香豆这样的小事,也还要说出一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这样的文人语汇,更遑论他向来的“者乎”和“君子固穷”等言辞了。这些词句在他人面前是“半懂不懂”的,但在孔乙己而言,却是一个读书人对其身份认同的语言迷恋。以“堂吉诃德气”的原型堂吉诃德为例,堂吉诃德在对风车作战失败并面临桑丘的取笑时,曾这样辩解:“甭说了,桑丘朋友,打仗的胜败最拿不稳。看来把我的书连带书房一起抢走的弗瑞斯冬法师对我冤仇很深,一定是他把巨人变成风车”[1],而孔乙己在断腿时“跌断”的辩解虽然似乎与之并不相同,但在躲入幻想的精神世界以否认眼前事实的本质上,却是一致的。此外,当孔乙己以“读书人的事”来辩驳“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就自觉站在了读书人的立场来与他人相区别。作者曾多次指明孔乙己的话“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让人“难懂”和“一些不懂”。然而这种他人的“不懂”在孔乙己自身,却正如堂吉诃德答桑丘般“你太外行了……你要是像我读过那么多的传记(于孔乙己是书——笔者注),就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1]。正如钱理群所说,这种“对于来自书本的语言的描述本身,越是迷恋,越是坚信不移,这种真实感越强烈,反过来又加强了对语言的描述的迷恋与坚信。这是一个相互支持、相互加强的语言描述的迷宫,陷进去是难以自拔的”[2]。
再者,孔乙己作为鲁迅笔下一个讽刺儒旧科举的典型,却以“满口之乎者也”的旧书生的正统身份登场,“没有进学”却说着进了学的话、行着“秀才”的事。考察西方堂吉诃德形象系列,似乎也存在一条“不是,却自我迷狂是”的内在人物逻辑。譬如巴扎罗夫本人并不是一个坚定的行动者,却自我标榜着要推倒一切;堂吉诃德不是骑士却带着随从四处漂泊,这种作者写作意在讽刺,作品人物却迷恋于非己的精神特质的规律,是堂吉诃德人物圈中很多人的共有特点。由此可见,孔乙己“堂吉诃德气”的来源与巴扎罗夫等人相似,本质上则是根植于他读书人的话语和身份认同的。换言之,正是这种沉迷于“酒”和“满口之乎者也”的读书人的心理精神认同,使得表现在外的孔乙己就近乎痴迷和迂腐,并处处显得“高人一等”。因此,“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也就不仅仅是迂腐可笑,更是孔乙己的独特感受和心理认同了。迂腐的“长衫”不正是典型读书人的标志吗?而“站着喝酒且穿长衫”就成了贫穷条件下孔乙己这一读书人与短衣帮间的最大不同。
此外,“堂吉诃德气”的偏执容易造就人物思维的单调和片面,孔乙己也如此。屠格涅夫在研究堂吉诃德时曾指出,他“一心追求同一个目标,使得他的思想有些单调,思维方式有些片面;他知道得很少,而且他也不需要知道得很多”[6]。这于孔乙己也同样适用。在读书人领域中,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知道“茴”字“极少见”的第四种写法,可谓是一个资深人士,但在现实领域里,却是一个“不会营生”“好吃懒做”的多余人,只能“偶然做些偷窃的事”“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在某种程度上,孔乙己精神层面的痴迷助长了他的“堂吉诃德气”,而这种消极的“堂吉诃德气”又反过来使他思维片面,并削弱了他的现实行动力。
因此,孔乙己既是一个典型的落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典型的迷狂于读书人身份认同的堂吉诃德。
二、中国式堂吉诃德的产生原因
孔乙己这一堂吉诃德与阿Q一样,是中国式的,是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心理、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和心理因由的。
从文化层面上看,一方面,孔乙己精神世界的建立既是某种程度上的书本致幻,更是大环境下没落的封建科举和士大夫文化的致幻。知识分子孔乙己不似“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的哈姆雷特,缺乏认清现实的清醒,进而迷狂依附于“酒”,同时也缺乏堂吉诃德积极的“进取精神”,因此不是“完完全全的堂吉诃德”,即“完完全全的哈姆雷特们以及完完全全的堂吉诃德们是没有的,这只是两种倾向的极端表现”[6],但他有着与阿Q“(精神满足)的心理模式”类似却又不同的“封建主义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末代的落魄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气”。时代的变化造成了孔乙己信仰的士大夫文化的断裂和崩塌,而这种崩塌断裂在“惟有读书高”的旧知识分子身上造成了现实的落魄和心灵的空缺,而由此带来的“生命的浪费是触目惊心的:中国封建士大夫文化的没落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衰亡”[2]。
另一方面,中庸的儒文化性格是造成孔乙己这类消极堂吉诃德的深层文化原因。鲁迅就曾立足于这一角度来分析,他关于堂吉诃德“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7]的论断,就从根本上抓住了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核心。西方人比较“容易沉于‘幻想的波动’”,“喜欢‘精神上先构成一个甜蜜的、销魂的、热情汹涌的梦境’”,以至于“行动太迅速,往往趁一时之兴;遇到刺激,兴奋太快太厉害,甚至忘了责任和理性”[2]。而在中国,以儒家温良恭俭让为道德标准来培养的传统读书人,面对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时,要么屈服于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忍从”心理,要么独善其身隐居于庙堂之外徐图进取,很少以一种激进彻底的性格来图变革,所以中国旧读书人往往“既不会有堂吉诃德式的对精神的献身的追求,也不会有对哈姆雷特的真实的精神痛苦的真正正视与深切体验”[2]。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这种“‘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都必然表现为一种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彻底精神,而在中国这样的有着中庸传统的东方国家里,却必然将其钝化、调和化,从而失去了自身”[2]。鲁迅说:“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7]反观孔乙己,孔乙己不也常面对取笑一再逃避退让,躲到精神自慰中去,甚至断腿后也只“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全然失去了读书人士大夫阶层的尊严和骨气吗?这种儒文化层面上的内敛含蓄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钝化、调和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精神损耗在以孔乙己为代表的一类堂吉诃德的身上同样是惊人的。
这种文化性格和文化没落为孔乙己独特的“堂吉诃德气”提供了外在原因,而使得孔乙己最终沦落的还有他的精神心理,即“瞒和骗”的自欺心理以及无法变更身份所导致的迷醉心理。
鲁迅在批判“形形色色的自欺欺人的麻醉术”时曾指出一种“瞒和骗”的心理:“这是用‘瞒和骗’制造奇妙的精神‘逃路’”,“证明这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2]。这固然适用于阿Q所代表的“精神胜利法”的旧社会中国农民,却也同样适用于迷狂于“酒”和“旧科举知识分子”身份中的读书人孔乙己。从文本上看,孔乙己的自欺可谓是昭然若揭的,他以“长衫”和满口的“之乎者也”来表现自己的读书人身份,拒不承认偷书和断腿之事,拿“酒”来欺瞒与侵蚀自己的理智,在酒客的笑声中幻想别人的理解。换句话说,在“瞒和骗”的同时,孔乙己缺乏认识现实的能力,他最大的识见乃是认清了“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的事实,却仍不免于被打断腿后还要爬一般地前来喝酒,并“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其对“酒”瞒骗功能的迷恋和自身价值的丧失竟至于此。所以,在鲁迅看来,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早已失去了西班牙骑士的积极进取精神,既无追求理想的执着,又无为理想而献身的意志与热情。他们只是发展了堂吉诃德精神的消极面,在自欺欺人的精神幻觉中,回避正视自己的现实真实处境,最终屈服于现实,沦为现实的奴隶”[2]。孔乙己的悲剧命运,即与他“瞒和骗”的精神心理密不可分。
此外,从文本对孔乙己的精神进行深层次分析看,孔乙己是另有一种心理因素在的。孔乙己有钱没钱时是不同的,对上对下也是不同的。孔乙己在有钱时显得很神气,“不回答”别人的话,自顾“排出九文大钱”,而穷魄时则一面“颓唐的仰面”“恳求”,一面小心地“摸出四文大钱”;孔乙己对上(如丁举人等)不满,偷人家的书,以“窃书”满足自己,对下(如短衣帮、酒客等)也不满,不屑与之为伍,“站着喝酒”,拿读书人身份瞧不起酒客。换句话说,孔乙己是一个自我标榜的人,他一面被人所瞧不起,一面又拿类似的心理瞧不起人;一面被这种心理所捉弄,一面又循环实践着这种心理。孔乙己如果中了秀才,成了丁举人一辈的人物,也有很大几率会因瞧不起而打折另一个“孔乙己”的腿;孔乙己若不是读书人而是店老板和短衣帮,也未必不会拿话来取笑另一个“孔乙己”。这种身为底层时骂上层,等到做了上层又变成自己曾经骂过的人的循环,在孔乙己身上也是深有体现的,这与鲁迅说的“奴隶翻身做了奴隶主,会变本加厉地对奴隶”的心理是相似的。但孔乙己毕竟是无法翻身做主子了,所以只好在精神里过瘾,迷醉于自己仍是个有身份、有价值的读书人。
这种精神领域的内在瞒骗和迷恋心理,造成了孔乙己这类知识分子对外在现实的模糊,而这种心理的不断加强又与国民文化性格一起,相互依托缠绕并日益强化,从而使得孔乙己更加“好吃懒做”,并在“酒”的满足中日渐衰亡。所以鲁迅说:“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笔者注)只一个,他们是一团。”[7]
三、鲁迅对孔乙己“堂吉诃德气”的复杂情感
鲁迅对孔乙己这一堂吉诃德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着鲜明的批判色彩,又有着发自内心的同情。
鲁迅对孔乙己“堂吉诃德气”的批判在文中是显而易见和不证自明的,它一方面表现在对孔乙己“堂吉诃德气”消极堕落的批判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孔乙己大同世界的终极幻想的批判上。
首先,相比于孔乙己沉醉于旧科举的精神世界成了名副其实的多余人而言,鲁迅更欣赏带有乐观进取精神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精神本来包含了两个侧面:一方面是对于超越现实的理想的执著追求……这是鲁迅也热情提倡并且身体力行的;但另一方面,堂吉诃德又显然存在着精神的迷乱,将书本所描绘的,头脑中想象的虚幻世界、理想人生,当做真实的社会与人生。”因此,鲁迅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出发,将孔乙己身上的迂腐、自欺、瞒骗心理等“堂吉诃德精神的这一消极面,加以突出、强化,把堂吉诃德式的精神迷乱视为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麻醉剂”来进行批判[2]。 鲁迅曾指出:“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8]。因此,鲁迅在批评孔乙己的同时,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姿态批评“嘲笑堂吉诃德的旁观者,有时也嘲笑得未必得当”,并说他们“缺乏启蒙者和挑战者的献身精神”,而更多是“劫取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9]。由此可见,鲁迅对孔乙己消极的“堂吉诃德气”的批判是与对积极的堂吉诃德精神的肯定并行的。
此外,鲁迅对孔乙己作为读书人最深层的“大同世界”的虚幻心理也是深刻批判的。孙逊在考证孔乙己的原型时认为,孔乙己的孔姓、给茴香豆“一人一颗”的公平态度以及鲁迅注明的第四种茴字“极少见”的情况是对孔门颜回的象征[10]。笔者不置可否,但“一人一颗”的公平态度,也可象征孔乙己对封建旧科举这一公平的“黄金世界”的寄托。很多西方“堂吉诃德气”的知识分子也有一种“黄金世界”的幻想,如“堂吉诃德气”的创始人堂吉诃德就不止一次地对它进行赞美,而这种“黄金世界”于孔乙己恰恰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理想中的大同境界。由此就不难理解孔乙己“窃书”于上层阶级何家、丁举人的同时,还“君子固穷”“品行却比别人都好”,这也正是读书人的某种兼济主义和对“黄金世界”的追求。
但鲁迅是最反感和否认黄金世界的,“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2]。“在一般人认为无限光明、美好的黄金世界里,鲁迅看见了新的矛盾、新的黑暗、新的危险;在一般人以为将获得永恒的天堂里,鲁迅看见了死”,即“鲁迅在《野草·墓碣文》里所说的‘于天上看见深渊’”[2]。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1]为历史任务,才会猛烈地抨击自欺欺人的麻醉术,以求唤醒沉睡的国民。所以鲁迅对孔乙己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他不但对孔乙己这种消极的“堂吉诃德气”予以否定,还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堂吉诃德气”所带来的大同世界的终极幻想,可谓是鞭辟入里。
然而,鲁迅除了对孔乙己消极的“堂吉诃德气”进行否定,同时也给予了孔乙己一种深层心理上的同情。这种同情藏于批判的描写之内,也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孔乙己的“堂吉诃德气”根植于他读书人的精神认同,是大环境下落魄的封建科举和士大夫文化使然。换句话说,孔乙己是新旧时代交替下的典型文化牺牲品。而鲁迅正是一个由封建到现代的过渡时期的读书人,也身历过旧文化断裂之苦,在某种程度上对孔乙己可谓感同身受。他不止一次地表露自己“历史中间物”的尴尬所处,并塑造了一个“黑暗会吞并我”,“光明又会使我消失”[12]的影的寓言,饱含知识分子的彷徨无助,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这种文化断裂所带来的精神无助,正是孔乙己“堂吉诃德气”的一大致幻根源。谢晴雯在分析孔乙己时,认为其封建社会落魄知识分子的无力暗含了鲁迅在现世作为知识分子的孤独感和普遍无力感[13],而新旧时代交替下读书人的相似遭遇,使鲁迅对孔乙己这一“堂吉诃德”抱有深切的同情,笔者深以为同。
其次,对孔乙己的同情与鲁迅对启蒙和看客的思考是分不开的。鲁迅作为一个“铁屋子”里率先醒过来的启蒙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具有某种堂吉诃德精神的。而孔乙己这一“堂吉诃德”既迷狂于传统读书人的身份,自然也是热衷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笔者认为孔乙己对小伙计的教导——“你读过书吗?”“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正是带有鲁迅般的知识分子的启蒙色彩的,而小伙计将孔乙己看作“讨饭一样的人”的“毫不热心”与孔乙己的“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更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鲁迅作为启蒙者不被理解后的心境。
孔乙己如同堂吉诃德般的形象既是与西方的一些“堂吉诃德”一样,注定了供人娱乐、受人调笑的,同时也是伴随着看客心理、隐喻了鲁迅本人的悲苦的影子的。如塞万提斯自己就曾发现“堂吉诃德的疯狂和高明,以及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滑稽,都注定是供全世界娱乐的”[1]。与之相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似天生供人娱乐的,孔乙己之所以被小伙计和众人记得,正是他的娱乐功能。“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对孔乙己而言,“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种只供人任意娱乐又被人随意抛弃忘却的冷漠是触目惊心的,同时也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而店老板满足好奇的言辞“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以及第二年端午时对“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的念念不忘,将鲁迅对看客的自私自利与冷漠麻木的批判推向了极致。
这种对启蒙的同理和对看客的批判,又反过来加深了鲁迅对孔乙己的同情。鲁迅作为思想家,可悲启蒙者被嘲笑和“人血馒头”的命运,又可叹“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山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12]般的看客心态,所以孔乙己启蒙失败后的“叹一口气”和“极惋惜”的心理,正如鲁迅自己的叹惋般有着掩不住的失落,而文中众人对孔乙己“堂吉诃德气”的嘲笑,更为鲁迅在批判看客的同时增添了对孔乙己的恻隐之情。
此外,孔乙己信仰下的悲剧命运和他为人的良善,也使得鲁迅对他难免同情。孔乙己的命运是悲惨的,在见证了他“中秋之后”对于咸亨酒店的“归来”后,小伙计就再也没见过他。孔乙己腿被打断,使其彻底失掉了笔杆子和赖以信仰的“站着喝酒”的读书人身份,尽管他仍迷狂于“酒”的寄托,但信仰的失去在深层次上注定了其必死的结局,即交出了“梦想”而进“天堂”。换句话说,孔乙己的悲剧是值得深深同情的信仰悲剧。同时,从终篇来看,孔乙己是个良善的人,他虽然消极堕落、“好吃懒做”成性,却并不使人太过厌恶,反而处处带给人笑声。所以欧阳凡海称“孔乙己是一个无害而纯真的人物”[14],吴小美也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读书人”[3]。鲁迅在小说中有意突出了他“品行却比别人都好”的一面,即使在刻画孔乙己偷窃时也弱化了他的不良行为本身,并更多地用“君子”“窃书”等使人发笑的词汇描绘了他的可悲与可爱。孔乙己人性上的单纯良善及其信仰悲剧,使得鲁迅在对他进行批判之余更具有一种温和与同情。
鲁迅曾对孙伏园道出他写《孔乙己》的“主要用意,在于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10],而正是这种对“一般社会”的讽刺性揭露和对“苦人的凉薄”的同情性描写,使得鲁迅对孔乙己的“堂吉诃德气”抱有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对他进行批判,怒其不争;另一方面又对他抱有同情之心,哀其不幸,所以鲁迅才把孔乙己塑造成了一个“笑中含泪”的典型。废名所言的“《孔乙己》虽有‘刺笑的笔锋,但令人笑不出’”[14],就形象地概括出了鲁迅对孔乙己“堂吉诃德气”的复杂情感。
四、结语
孔乙己既是一个新旧交替时期的没落知识分子,也因其对“酒”的迷恋,对“长衫”和“之乎者也”话语等读书人身份标志的迷狂,使得他成为一个丢了笔杆子的“堂吉诃德”的典型。但这种典型与阿Q一样,乃是民族性和中国式的,有其特定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心理因素。同时,鲁迅既站在启蒙立场上对孔乙己的“堂吉诃德气”饱含批判,又立足在知识分子心境上对他深有同情,表现出了鲁迅对其形象的复杂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