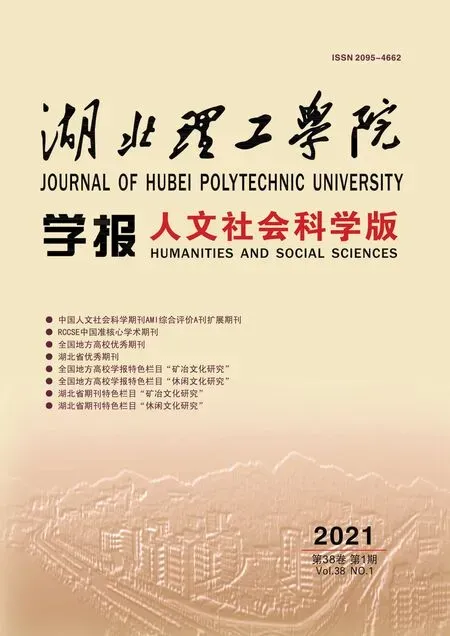论休闲审美活动的存在场域与精神生态*
王东昌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要从事休闲审美活动,追求闲情逸致之美,固然以悠闲的、超逸的、审美的心态或精神状态等为主要条件,但是毕竟也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为其提供支撑,其中,休闲审美活动的特定存在场域就非常重要。只有在这些场域中,休闲审美活动才更容易孕育、生发和产生,对闲情逸致的追求、体验和享受才更容易被酝酿、诱导和激发出来。目前,国内休闲学界对休闲审美活动存在场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划分标准不够明确,划分比较随意、琐碎、混乱,层次不清,涵盖面不全。吕尚彬等人编著的《休闲美学》、陈琰编著的《闲暇是金:休闲美学谈》、张玉勤撰写的《休闲美学》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特定的标准出发,对休闲审美活动的存在场域进行进一步的概括、提炼和提升。本文试图从更高的精神境界出发,从有利于休闲审美主体精神生态的和谐、稳定、平衡出发,从有利于休闲审美主体精神生态的调整、优化、成长出发,对休闲审美活动的存在场域进行新的概括、提炼、提升,认为休闲审美活动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存在场域,以文学艺术为主要表述场域,以故乡家园为主要诉求场域,以自然之道为主要境界场域,以“生命的留白”为主要价值场域,从而实现了其广泛的覆盖性和较强的概括性。
一、日常之美:休闲审美的存在场域
究竟什么样的场域才容易让人展开休闲审美活动,让人产生和享受闲情逸致之美?这样的场域有很多,每个人的切身体验也都不一样,而日常生活则是其主要的存在场域。日常生活作为人们生命存在的重要场合或平台,虽然有时显得平庸、单调、琐碎、芜杂、乏味、无聊,但却非常重要,它构成了人们的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和价值。而休闲审美活动就更多、更广泛、更普遍地存在于这一场域。美国休闲学家杰弗瑞·戈比指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1]14从这个定义就可以看出,休闲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这种生活往往并不存在于工作、事业、义务、责任等对个体具有较大压力的场域,而是存在于这些场域之外的场域,重要的、具有广泛涵盖性的场域——日常生活场域——构成其主要组成部分。正如张玉勤指出的:“休闲并不居于真空,而现实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我们是在生活中休闲,也是在休闲中生活。”[2]119赖勤芳也指出:“休闲活动是日常生活中的特定部分,它蕴含在日常生活之中,既超越一般的日常生活活动,又反哺于日常生活活动本身。”[3]234进一步说,人们休闲感的获得,对休闲的价值和意义的体认,往往是从日常生活中得来的。
休闲活动是这样,作为休闲活动高级存在形式的休闲审美活动也是这样,它主要存在于日常生活场域。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审美传统,打破了以往传统审美活动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人生而蜷缩于形而上的高雅的象牙塔(如文学艺术中)的局限性,推动了审美活动走进日常生活、现实人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如潘立勇所说:“休闲对于平民已不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审美通过休闲进入生活已是生活的普遍现实与必要需求;……‘全民有闲’使休闲在公民的个人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如何将审美的态度和境界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休闲方式,已是刻不容缓的世纪课题。 ”[4]休闲审美活动在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场域的同时,也丰富和提升着这一场域,使其充满了精神的、审美的、诗意的、新奇的、快乐的因素,从而实现了“人生的艺术化和情趣化”[5]26。赖勤芳指出:“休闲美学的旨趣就在于还原日常生活世界的诗性,通过祛除日常生活世界的平庸而体验它的神奇。”[3]234-235更进一步来说,休闲审美活动甚至会使人们的日常生活达到理想状态,成为人们理想的精神乐园。正如陈琰所说:“作为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休闲是我们美丽的精神家园,这是因为在对生活的雕琢和自由的创造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当我们扔掉种种心灵的枷锁,就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里面,还有一个宁静、和谐、从容、欢乐的世界足以安顿我们疲惫、浮躁和盲目的心灵。”[5]6总之,休闲审美活动只有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场域相结合,才能获得不竭的生命源泉,才能焕发无穷的生机和活力,才能产生无限的魅力,才能对人们精神生态的和谐、稳定与平衡发挥积极作用。
当然,休闲审美活动主要存在于日常生活场域,并不意味着它就沉溺、黏着、沉沦于日常生活场域,它还要从这一场域超越、升华出来,朝着精神的、文化的、审美的高层境界提升,这样它才会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吃饭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有人吃得漫不经心,有人吃得随随便便,有人吃得急急匆匆,有人吃得狼吞虎咽……这都使它显得平凡、琐碎、无聊,难以让人回味无穷,更难以让人产生美好、诗意与浪漫;但是如果怀着一种超越功利的、悠闲的、审美的心境去吃饭,它也可以变成一种休闲审美活动——人们可以在其中吃出快乐、情趣与滋味,吃出闲情、雅致、诗意、美好与浪漫,吃出某种深沉的情感、精神的享受,这就实现了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场域的超越与升华。再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也可以一个人什么事不做地闲坐着,放松身心,在远离精神上各种纷扰以后获得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平和,享受着“无言的快乐”、无限的惬意,自由地审视、畅想、思索着生活与人生[5]129-130。这一过程也就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当然,人们也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闲坐着,喝茶、聊天、吃零食,这作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作为休闲审美的重要方式,也可以带给人们轻松、愉快、自由、舒适、惬意、超然与散淡,别有一番人生的情趣、乐趣与滋味。在这样的日常生活的休闲审美活动中,人们自然而然地超越了日常生活,实现了精神的升华。而就文艺作品中描写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细枝末节来说,比如《红楼梦》中的看戏、饮酒、赋诗、吃饭、赏花等,它们作为休闲活动和休闲审美活动,通过审美化、艺术化的描述,更容易超越和升华出来,带给人们精神的审美的享受和深刻的思想启迪。可以说,休闲审美活动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闲逛于街市、购物于商场,还是淘货于地摊、留连于书店,或者是毫无目的地游荡于老街、村落、胡同、古巷,看人们下棋、打牌、品茶、聊天,欣赏市民百态,观察民风民俗,……。只要怀着非功利的、悠闲的、审美的心境去看待日常生活中的这一切,人们都能从中感受到生活的宁静、闲适、自由、从容、洒脱、温馨,体味到生活的乐趣与滋味,获得难以言表的精神享受,进而实现精神的超越与升华。
二、文学艺术:休闲审美的表述场域
文学艺术场域是休闲审美活动的表述场域,休闲审美活动往往在其中得到经典的、理想的表达,从而使休闲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场域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正如赖勤芳指出的:“如果说休闲是一种以自由为旨趣的艺术生活,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哲学家、文人、艺术家等拥有。”[3]68“哲人、文学家、画家其实就是追求休闲的‘生活专家’,或者说‘休闲人’就是‘艺术人’。”[3]69一方面,正是因为作家艺术家那种非功利的审美的精神气质、那种超越性的艺术人格、那种自由洒脱的人生态度、那种深邃的人生思考和非凡的精神境界,才使得他们的生活天然地成为了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生活,一种休闲审美的生活,一种充满闲情逸致的生活,一种能带给人们精神愉悦和自由的生活;另一方面,休闲活动以及休闲审美活动滋养了人们的心灵和性情,开启了人们的思考和智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开拓了人们的精神空间,带给人们精神的自由,当然也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美的体验和美的形态,酝酿了浪漫的诗意,产生了优美的文艺。
具体来说,在休闲活动及其高级形态——休闲审美活动中,人们往往会在自由散淡中畅想过去、现在与未来,明确人生的追求和理想,自由的展开发散性思维,实现感知、意象、思绪、知识等在大脑中的自由连接和碰撞,实现情感的翻腾激荡与想象力的自由飞扬;灵感也可能在此时趋于活跃,激荡而出,突然而至。这些由休闲活动和休闲审美活动带来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变化,往往构成文学艺术发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正是在休闲活动和休闲审美活动中,才产生了自由、诗意与浪漫,才产生了悠闲的审美的心境,才产生了审美体验和美感,才产生了文学艺术。正如张玉勤所说:“像魏晋人的‘濠上之乐’、许棠的‘闲赏步易远,野吟声自高’、陶渊明的‘北窗下卧’、郑板桥的‘置榻竹林’等,分明就是一首首绝美的诗,典型地折射出休闲活动与审美情趣、审美体验的统一。”[2]7进一步地说,休闲活动和休闲审美活动还推动了人们“艺术心灵”的产生,例如“坐忘”这种休闲或者休闲审美的精神状态,就有利于人们摆脱外物的奴役和束缚,在精神上获得自由,产生“艺术心灵”:“坐忘不仅不是心灵的沉寂和空无,反而恰恰是一种超越了日常之我的那种心旷神怡、虚静恬淡而又生动愉悦的心灵状态,是在‘忘’的境地中艺术心灵的诞生。”[5]133而“艺术心灵的诞生”,则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展开和文艺作品的产生,正如赖勤芳所说:“无论从何种维度而言,人类的艺术都不可能离开休闲。休闲是促进审美意识、艺术及其形式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审美意识、艺术及其形式的发展又表征着人类的休闲状况。没有休闲就没有艺术,这不是危言耸听。”[3]50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重要文学作品,往往是在休闲或休闲审美中创作出来的。以诗歌创作为例,正是在诗人们悠闲自得的审美心境和自由无羁的精神状态中,正是在他们随性散淡的诗意情怀和审美情趣中,正是在他们游山玩水、登高望远、饮酒品茶等消遣娱乐活动中,他们的思绪才开始自由激荡,他们的情感才在不知不觉中发酵和积聚,他们的想象才开始自由飞扬,他们的灵感和艺术创造力才得以迸发,他们的诗思才得以酝酿,他们才得以创作出优美的诗篇,其中也包括以休闲和休闲审美活动为题材的诗篇。而就散文创作来说,正是在散文家们的休闲和休闲审美活动中,在他们的悠闲散淡、自由从容的生活方式中,在他们侃侃而谈、谈笑风生中,在他们的趣味盎然的饮酒品茶中,在他们的悠闲遛弯、散步中,清新、散淡、自由、闲适的心境油然而生,使他们优秀的散文在自由挥洒中水到渠成。再以小说、戏剧创作为例,正是由于小说家们、戏剧家们对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审美活动以及闲情逸致的体认,才使得具有休闲审美倾向的小说、戏剧被创作出来,而读者观众阅读观看小说、戏剧也成了他们在劳动之余、茶余饭后的重要娱乐方式。此外,如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都和悠闲的、从容的、自由的休闲审美心境紧密相关。
总之,文学艺术场域的诸多休闲审美活动往往都超越了世俗功利的羁绊,让参与者在“无事人”般悠闲的审美心境中达到入迷、沉醉的精神状态——一种“忘我”“忘世”甚至“忘时”的状态,一种无欲无求、挥洒自如、恬淡闲适、意趣横生、其乐无穷的状况,最终指向“自在澄明”的心境——一种自由的、超越的、审美的精神境界。这对参与者性情的陶养、精神状态的“内养”、精神世界的充实、精神生态的平衡,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三、故乡家园:休闲审美的诉求场域
休闲审美活动另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场域就是故乡家园,休闲审美主体的精神的、心灵的、情感的诉求往往在其中得到满足。故乡家园是个体生命的始发地和摇篮,它构成了他们早期生活的基本寓所即“个人的直接环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个体生命得到滋养、孕育、丰富、成形、成长,性情得到陶冶,气质得到涵养,爱好得到发展,情趣得到培养,性格最终定型。可以说,这里滋养孕育了人们的肉体与灵魂,既是他们的生命“本质力量对象化”得到充分展开的地方,也是他们“对象化”了的生命。正因为如此,这里往往给人们留下了印象深刻的生活往事、魂牵梦绕的生命情感。人们对故乡家园的怀念、眷恋、沉迷与向往,可能有诸如生物本能的、亲情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故乡家园意味着工作之外的地方,意味着一个充满浪漫、诗意、美好的地方,意味着一个快乐、放松、自由、随性的地方,意味着一个温馨的心灵港湾——那里有其乐融融的温暖的家,有关心、呵护、牵挂自己的爷爷、奶奶、外祖父、外祖母、母亲、父亲等亲人,有让自己的天性得到自由挥洒的美好童年,有曾经和自己尽情玩耍、游戏的童年玩伴和无限的童趣。故乡家园是一个充满绵绵无尽的情思的地方,是一个先天具有诗情画意、让人流连无尽的地方,当然也是一个能带给人休闲审美的生活和让人自然地产生闲情逸致的地方。对此,著名作家韩少功在《我心归去》中有生动的描绘:“‘故乡’是什么?‘故乡’意味着故乡的小路、故乡的月夜、月夜下草坡泛起的银色光泽,意味着田野上的金麦穗和蓝天下的赶车谣,意味着一只日落未归的小羊,一只歇息在路边的犁头,意味着二胡演奏出的略带悲怆哀婉的《良宵》《二泉映月》,意味着童年和亲情,意味着母亲与妻子、女儿熟睡的模样,甚至也还意味着浮粪四溢的墟场。”[6]594这些场景不正是充满着浪漫诗意的休闲审美的场景吗?当人们见到故乡这熟悉的一切时,就像见到了久未谋面的亲人好友,自然会产生亲切感,也自然会孕育出闲情逸致,探亲访友、饮酒品茗、聊天下棋等活动也会自然而然地展开。
故乡之所以称为故乡,也意味着你曾经或者已经离开这个生你养你的、充满诗意、浪漫、美丽、温馨而又带给你闲情逸致的地方;但是,你又对这个地方无限眷恋、魂牵梦绕、朝思暮想;特别是对那些在现代化的城市、在钢筋水泥筑就的高楼大厦里居住的远离故土的、失去了“根”的人们,或者在其中生活得局促不安、失魂落魄、无以安放灵魂的人们,故乡往往成了他们永远的心灵港湾、温馨的精神家园、温暖的母亲的怀抱。于是,“回归故乡”就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游子持续不断的向往和心理冲动,从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可以看出游子归乡的迫切之情。老家作为故乡具体而微的体现,往往给遭受风吹雨打的人们提供了躲避风雨的小窝,那里有夫妻之间的爱情、温情,有父子、母子、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温暖,它们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安慰、自由、温馨、安乐、享受,是悠然的人伦乐趣。中国古代的诗人常常从其中获得闲情逸致和人生的幸福,并用生动优美的诗篇把它们描绘出来。例如,明代诗人王瓒的诗句:“钓得红鳞个个鲜,妻儿倒瓮醉灯前。人生有趣心常乐,不羡王侯食万钱。”就表明了虽然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太好,但是有妻子儿女陪伴在身边,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钓鱼、做菜、喝酒,有说有笑,充满了生活的乐趣。再如陆游的《闲意》一诗写道:“学经妻问生疏字,尝酒儿斟潋滟杯。安得小园宽半亩,黄梅绿李一时栽。”也是道出虽然家里的住房环境并不宽敞,连一个可以种树的小园子都没有,但是有美酒可以品尝,有爱妻朝夕相伴,生活倒也情趣盎然。类似这样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这些来自故乡和家园的生活乐趣,往往构成一道道牢不可破的防线,给人们以强有力的支撑,使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外部世界,帮助他们抵抗各种各样的压力。正是在故乡和家园的生活乐趣中,漂泊流浪的游子超越了劳顿困苦、孤寂冷漠、分裂破碎的外部世界,找到了生机勃勃、诗意盎然的自然和精神上的归宿,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之根。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回归故乡、回到老家总是乐此不疲。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故乡最本己和最美好的东西就在于:唯一地成为这种与本源的切近——此外无它。所以,这个故乡也就天生有着对于本源的忠诚。因此之故,那不得不离开故乡的人只是难以离弃这个切近源位。但既然故乡的本己要素就在于成为切近于极乐的源位,那么,返乡又是什么呢?返乡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7]24塞缪尔·约翰逊也指出:“居家的幸福,是一切雄心壮志的最终归宿。人们所有的进取精神和辛勤劳动,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8]9
故乡在精神层面上的延伸是“精神的故乡”,那是个体生命的精神家园,是人们心灵的始发地、栖息地和归宿地,是人们在精神上安身立命的地方,“当人彷徨于人生的路口而不知所措时,当人生的意义被判为虚无时,人就面临失去家园的危险”[9]122,因此,“对于精神家园的梦中回归,已经成为现代人价值追求的新的起点”[10]310。“寻找家园,是人类的一种最执著的努力。这里的‘家园’,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赖以栖身的所在,更是心理意义上的一种精神空间,是一块自由表现生命的空间。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百折不挠地寻找家园的艰难历程。”[11]32而休闲美学也往往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10]69。那么,这样的精神故乡和家园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它是一个自由的、快乐的、充满闲情逸致的精神空间,是一种悠闲的、审美的、充满闲趣的心态或心境,这构成了很多人的生命理想。陈琰指出:“真正的家园是人的所来之处、所在之处和所要去之处。家园不在浪漫的远方,也不在彼岸的天堂,它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由此,家园的意义就是生活世界的敞开,而它所敞开的就是生活的快乐。”[5]2而生活中的休闲审美活动以及它带给人们的欢乐、情趣和闲意,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向那个地方,让他们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找到生命和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正如陈琰指出的:“惟有休闲才是敞开精神生活最大限度的本源之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休闲建构了我们美丽的精神家园。”[5]4特别是在这个物质生活丰富而精神生活贫乏的时代,一些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丧失,精神故乡和家园遭到毁弃而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下,休闲审美活动就显现出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抚慰而获得温暖,使他们重新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过上自由、充实、丰富的精神生活,达到精神生态的和谐、稳定与平衡。
总之,故乡、家园中蕴含着丰富的休闲美学内涵,它们是容易滋生美好、诗意、浪漫、快乐的地方,也是休闲审美主体精神的、心灵的、情感的诉求容易得到满足的地方。因此,它们也往往构成了人们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的精神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生态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维护着他们的身心和谐和生命健康。
四、自然之道:休闲审美的境界场域
自然作为休闲审美活动的重要存在场域,往往使休闲审美主体获得精神的提升和超越,甚至达到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现代城市能给人们提供有诱惑力的工作,方便他们事业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从事休闲审美活动的诸多条件。但与此同时,它也往往意味着竞争、压力、紧张、疲惫、焦虑、郁闷、空虚,有时甚至是人生价值与意义的丧失。因此,它在总体上不是人们展开休闲审美活动的理想场所。相反,休闲审美活动展开的恰当场域在于自然。自然是人类从中孕育而出的地方,人类始终离不开自然、依赖于自然、生活于自然。因此,自然构成了人类生命存在的重要场所或者环境。人类对自然总是怀着一种本能的感情,“一种乡愁般的冲动,渴望回到自然生命的源头,回到生命的根”[5]96。天然的具有美感的自然往往能带给人们身心的愉悦和审美的享受,甚至在较高的层面上陶冶着人们的心灵。相应地,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从事休闲审美活动的重要场所。身处其中,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与它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忘却了工作中的竞争、压力,生活中的疲惫、紧张、焦虑,进入一种完全放松、从容、随意、散淡的身心状态,达到一种悠闲的、审美的、充满生命闲趣的精神境界。陆庆祥指出:“人在自然中的休闲活动是人的休闲活动及休闲方式中最主要的一种,也是休闲感最为强烈的一种。在大自然中的休闲活动也最能直接体现休闲的自然化本质。”[9]8“在休闲美学看来,人在大自然中游玩休憩当是最典型的休闲活动,它最自由无碍而又充满了形而上的精神性。”[9]20因此,在自然中从事休闲审美活动,在休闲审美活动中走向自然、欣赏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走向自我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让自身能够面对自我,获得自由、愉悦和美好心境的过程。
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似乎对自然怀有更深的情结,人们自古以来就对自然山水兴趣盎然,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其中去欣赏、体验,享受在其中获得的闲趣、美好、诗意与浪漫。春秋时期的孔子就常常“见大水必观焉”,痴迷、沉醉于欣赏自然之美的休闲审美活动中。魏晋时期的邺下文人在自由闲暇的时间里往往游山玩水,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游览山水就成了他们消遗闲情的主要方式”[11]282,“六朝名士们常常游山玩水,乐而忘归。王羲之辞官后,与他的同道尽情地游山玩水,钓鱼射鸟,遇上风和日丽的日子,还扬帆海上。孙绰住在风光秀丽的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11]173。自此以后,“国人的闲情以山水为情结的美学核心终已凝成”[11]283。一代代中国文人在悠闲的、自由的、自在的、自得的审美心境中,常常身临其境地感受和体验自然,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并且不吝笔墨地去歌咏、描绘它们,将自己在其中体验到的闲逸之美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留下了一篇篇美妙的诗词文赋、一幅幅优美的山水画卷。
以自然为场域的休闲审美活动,在使人们放松身心、消遣娱乐、享受生命闲趣的同时,也必然影响其精神世界,有利于他们精神生态的和谐、稳定与平衡。具体来说,人们对自然的欣赏与其特定的精神状态紧密相关,它往往影响他们的情感、情思、心境等,使其精神世界得以摆脱各种各样的干扰,实现精神的放松、自由、解放、超越、创造;在打破既有精神生态平衡的同时,他们的精神生态在新的层面重新走向平衡,从而改善和优化了他们的精神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无论是漫游名山大川,或是郊游踏青,亲临实景体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都是我们修身养性、解放自己、美化心灵、体验自由的一种理想的审美活动。”[11]285大自然变化无穷,神奇莫测,人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从事不同的休闲审美活动,会产生不同的体验、感受和精神状态。当看到溪水潺潺缓流、花朵娇艳欲滴、草木茂盛清秀,听到鸟鸣清脆悦耳的时候,你在其中发现了闲逸之美,感受到人生的无限美好,这往往预示着你的精神生态是和谐的、稳定的、平衡的。有时,人们怀着休闲审美的心境,对粗犷、壮观、充满无穷变幻和创造力的自然景观的欣赏,又会震撼他们的心灵,使他们获得积极、健康、乐观、向上、豪迈、自信的人生态度,高洁的人格情操,高尚的生命情怀,超然的精神境界,从而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自然崇高以其荒蛮原始的动荡的感性形式,强烈地暗示出主体的存在,象征着人性的自由。”[11]284曹操当年在碣石山上面对壮观的大海,就产生了非凡的豪情,萌生了要掌控和经营天下的远大抱负;范仲淹在登上高楼欣赏不同时节湖面的优美景色时,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生命情怀;毛泽东在欣赏北国壮丽的雪景后,产生了乐观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情怀……。这些对独特风格的自然景色的欣赏,作为休闲审美活动,陶冶了人们的道德情操,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状态。有时,在大自然中从事休闲审美活动,还会启迪人们的智慧,让他们获得透彻的人生感悟和深刻的哲思。吕尚彬等人认为,人们在大自然中游山玩水,在使身心得到放松、休息的同时,也会获得“意想不到的顿悟和发现”,体悟到“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和谐”以及“宇宙及人生的真谛”[11]281-282,从而达到休闲审美活动的最高境界。陶渊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在大自然中从事休闲审美活动,也会让人们产生爱心、同情心、善心等。正如有学者所说:“在投向自然美的涌动的情感中,我们会孕育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它会使我们对世界万物产生同情心,让我们想到爱。一丛野花,一片秋叶,一朵白云,一泓清泉,似乎是最平凡的、最常见的,然而,即使在这种平常而又单纯的自然景物中,真挚情感的酝酿仍然可能唤起理想,唤起一种心灵深处的激动和最细腻的柔情,产生一种难以遏制的向往至善的渴求。”[11]285在这些不同的状况下,休闲审美者的精神生态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和谐、稳定与平衡。这种在大自然中的休闲审美活动和一些学者提出的“生态式休闲”是相互契合的——“生态式休闲同样关注精神生态,体现为人与自身关系的契合。……生态式休闲客观上要求人们在选择休闲活动的时候,……应追求诗意、审美的东西;休闲……应是令人神往的精神家园。”[2]103
五、“生命的留白”:休闲审美的价值场域
休闲审美活动的场域,较少地存在于工作、事业、责任、义务以及对功名利碌不竭追求的名利场中,而较多地存在于人生的自由之地、生命的留白之地,在这些地方,休闲审美主体将体会到,空白的地方并不是生命白白的浪费和毫无价值的虚度与虚无,而是包含着丰富的价值和意义。“留白”不仅是深刻的人生哲学、高境界的处世哲学,也是广泛地体现在世事、人生、艺术等方方面面的玄妙的艺术哲学。例如在国画创作中,画家对“留白”艺术的运用往往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在国画里,空白不是无形的‘虚无’,而恰恰是为了找一个更大的空间给主体物像有活动自由的余地,是‘藏境’的重要手段。……常常起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11]182;很多人在为人处事时,总是不把事情做到极端,而是为他人、他物留下足够的“空白”或者说生存空间;人们在开发自然时,往往进行自我约束,不过度开发,从而为保护自然生态留下足够的空间;古人在捕猎野兽时,有时会“网开一面”,为部分野兽的逃生留下空间;渔夫在水中捕鱼时,往往有意识地使用网眼足够大的渔网,从而给幼小的鱼苗留下逃生的空间;学者在用笔记本做笔记时,往往在纸张的边缘部分留下足够的可以做批注的空间;在生活中,有时人们会像“无事人”一样闲坐着,什么事也不做,给自己的身体和内心留下“空白”,使它们得到休息,这样的“闲坐”有时会达到比忙碌的做事更好的“留白”效果;……。这些都是“留白”的哲学在世事、人生和艺术中的运用,其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
就个体人来说,他要保持精神生态的和谐、稳定与平衡,就不能将自己的人生安排得过于沉实、饱满、拥挤、繁忙、劳碌,而应该有意识地留下一点缝隙、空白、间隔,留下一点不工作、不做事、不思考的时间,留下一点看蓝天白云、红花绿草、飞鸟游鱼的时间,也就是留下一点能够自由支配的从事休闲审美活动、追求闲情逸致之美的时间。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闲暇自有其内有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源泉;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12]410-411现代社会的人们,总是在想着如何用更短的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很少有人想着把各种各样的几乎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撇开,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一点“空白”,让自己什么事也不做,如其所愿地发发呆、看看天,或者去做一些发自内心想做的轻松愉快的事情,去过一种休闲的审美的生活,去享受一下人生中的闲情逸致之美;一些人到退休的年龄却还不愿意退休,而是仍然习惯性地去拼命工作,这实际上是不懂生命的“留白”艺术和哲学的缘故。事实上,他们不妨在半生劳碌之后,试着换一种方式去开始新的生活,这种新的生活也许充满了自由、闲散、诗意,能带给他们更加美好的体验。而去从事休闲审美活动、追求生活中的闲情逸致,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不仅是到退休年龄的人,事实上,任何人在生命历程中的某个阶段或某些时候,都完全有权利把生活和工作中各种各样的平日无法脱身的繁杂事务撇开,去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毫无用处、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的事情,例如去回望一下往昔美好的岁月,去追求一点生活中平日不曾有的别样的情趣、诗意与浪漫,这也许就是生命“留白”的一种方式,其中包含的意义甚至是阐释不尽的。可惜,很多人在忙忙碌碌的生命状态中,体会不到这些意义。
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鲁枢元在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会把“留白的艺术”潜移默化地融入其中,不仅传授学生“留白”的学习、研究方法,并且他自己在学习、研究生活之外,还留下生命的“空白”,比如常常和学生聚会,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让学生顺次表演各自拿手的节目,或者畅谈各自的兴趣与爱好,并嘱咐他们不论再忙也要留下一份闲心去培养一点业余的兴趣与爱好。这样的观念和做法往往带给人深刻的启迪:人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也应当有一些缝隙、间隔、“留白”,让人们去休憩、娱乐、沉思,去追求一些生活中的情趣、滋味、韵味、欢乐、幸福,而不应当永远都是劳作。只有这样,人生才会更加精彩、更富弹性和韧性、更具活力、更有生机,才不至于像被拉直的弹簧一样成为无用的废物;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人们精神生态的和谐、稳定与平衡。
总之,在“生命的留白”的广阔空间中,休闲审美活动得以在日常生活、文学艺术、故乡家园、大自然中自由而广泛地展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生态。可以说,休闲审美活动超出了一般的生命境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