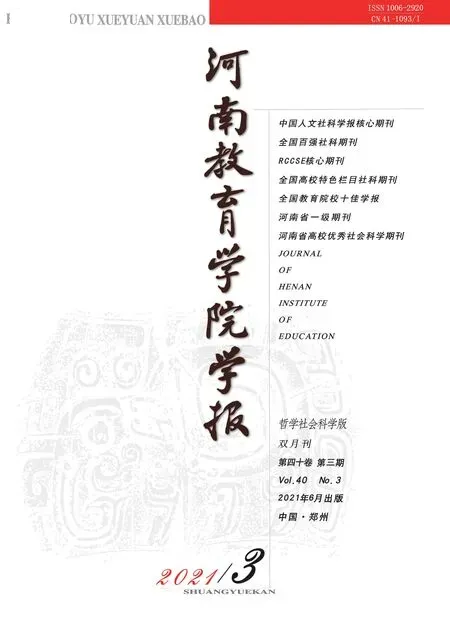作为解释文化的舞蹈人类学
孙继黄
一、引言
舞蹈人类学,无论我们将之视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细化后的一个分支,还是视为以舞蹈为核心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其功能指向都趋于一致,即通过舞蹈对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作出阐释。众所周知,舞蹈并非人类学的议题中心,但是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往往会探讨特定对象的舞蹈形式。舞蹈因作为一种对文化的阐释形态而常被人类学家所关注,许多原始宗教和巫术的内容都需要通过舞蹈的形式来实现,“在那些没有文字的土著民族中,艺术几乎就是其文化的公共符号,以及意义的象征世界,还有社会的背景知识”[1]3。
舞蹈是时空中运动着的特定人体动作形式,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不同的社会文化决定了舞蹈符号以何种律动方式与空间方式而存在,反之,人们也可以通过相应的符号来解读其背后特定的文化风俗。因此,解释文化便成为舞蹈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当然,要想说明舞蹈人类学的确可以用动作符号解释文化意义,我们就必须从“何以”与“以何”的角度来证实。
二、文化何以被舞蹈人类学所解释?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文化的概念,因为解释文化的前提在于确立文化是什么,进而才能讨论文化可以被什么所解释。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其著作《文化的解释》(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中说:“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重所指的,也不是含糊不清的:它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2]109按照格尔茨的观点,文化是通过符号所表现出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凝滞的,而是在历史流变中发展而来的概念系统。文化具有复杂深刻性,需要被解释。解释某种特定文化可以明晰其创造者的生存形式、生活态度和交流方式。文化就是这些意义模式的述说体。作为意义的文化必须以具体的形式才能表达其抽象内涵,当人们选择用身体动作的形式来表达时,舞蹈就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作为意义的文化凭借舞蹈者的身体符号实现了传承与交流。同样,舞蹈作为意义模式的外化象征,也在表现为文化的历史流变中得到了发展。无论是已经被定义为艺术的肢体动作或是尚未从实用功利性抽离出来的身体形式,其本质都是人类创造的象征性符号。在书面语言尚未形成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通过指向某种意义的动作形式得以实现。彼时,人类能够实现最大化控制的表现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人类通过塑造一些特定的动作形式来传达相应意义,所以,身体便成为承载生活经验与思想情感的媒介,成为表意的优选符号。
舞蹈创建了与文化相表里的身体符号形式,在所属人群中建立起强有力的沟通机制,这种机制与由生产实践发展出的宗教、风俗和情感等因素直接相关,《毛诗序》中将手舞足蹈作为表情最高层次的论述恰好就说明了这一点。人通过一些具有象征性的动作方式进行情感意识间的互动,并由此建立了舞蹈艺术领域特有的语言符号。当这些身体动作在其生成与传播的语境中被不断重复和再度创造时,就具有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比如具有生殖崇拜意味的湖南土家族“毛谷斯”舞,祭祀氏族保护神的图腾拟兽舞蹈等,这些原始舞蹈实质上就是一种动作符号和文化意义的充分互动活动。正如苏珊·朗格提出的“舞蹈包含哲学意义”的命题一般,人类那些节奏化、律动化了的肢体创造并非无意义,相反它们蕴含着非凡的意义,它们是抽象与形而上的具体表达。人们通过舞蹈给无形以形状,把对人生的思考与态度带进当下现实,用特殊的律动方式加以保存和传播。美国的舞蹈人类学家罗伊斯在《舞蹈人类学》(TheAnthropologyofDance)一书中将舞蹈视为“身体于时空中所创造的模态”[3]5,这种模态在不同时代与民族中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因为它的身体构建总是基于特定的文化意义,进而在具体场域中表现出特殊性。舞蹈作为一种“活在当下”的身体模态,它总是象征着更为内在的、抽象的和一定时空范围中相对普遍的文化意义。因此,我们在面对舞蹈时,不能仅仅从偏重于个人独立创造的角度去判断,而是要站在文化决定与象征的角度去解读。汉娜在《人类才会舞蹈》(ToDanceisHuman:ATheoryofNonverbalCommunication)中为舞蹈确立了定义,其中一条就是“文化性的模式序列”[4]19,也就是说,舞蹈本身的意义需要我们超越动作,进入到更大的文化结构中去理解。因为人就是这样一种符号性的动物,其行为活动大多具有象征意义。舞蹈从本质上来说是人所创造的一种具有节奏和律动特征的身体符号。凭借这种可被感知的方式,人们给予不可见的文化意义以具体形态。在象征意义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将舞蹈视为用身体表达的话语形式,它是一种可以被直观认识的符号,象征了特定的文化意义。
“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2]5按照格尔茨的理论,当我们再度讨论文化何以被舞蹈所解释时,这个逻辑就很简单了:文化以舞蹈符号的形式来表现,那么舞蹈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探索文化的关键媒介。文化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2]17-18,既然文化是一种对社会事件、制度等人类活动的深描,那么知晓文化的特有样式就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自身,而这一点需要建立在解释符号的基础上。当我们以文化符号的方式来看待舞蹈时,解释文化的途径便在于解释舞蹈符号的象征含义。“所谓文化分析是(或者应该是)对意义的推测,估价这些推测,而后从较好的推测中得出解释性结论。”[2]26因此,只有正确推测并认识舞蹈动作的运动方式如何形成、有何意义,才能解释其文化内涵,这是文化分析的正确思路。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文化可以被舞蹈以符号的方式解释,而舞蹈人类学就是解剖舞蹈符号的手术刀,用它我们可以分析舞蹈符号的象征意义,最终用以解释文化。比如泰勒所做的关于舞蹈内容的人类学研究,其本质就是一种了解特定社会的手段,而博厄斯就文化概念的理解又与泰勒不谋而合,因此他针对舞蹈现象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同样取得了解释文化、了解社会的效果。当文化以某种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动作模式中时,舞蹈人类学便可以通过观察、识别、分析特定的动作模式进行文化阐释与还原。因此,解释舞蹈符号要用到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它可以研究特殊身体符号的叙述内容、象征方式和传达效果,最终探析出舞蹈这种社会性符号的文化意义。
舞蹈人类学作为一种解释途径,建构起的是对深层文化的理解。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将经由身体形式得出的解释与身体背后所发生的文化割裂开来,而是要带着人们走进文化的内部纵深处。所以,舞蹈人类学的理论边界不应划在身体语言的形式美或者创作表演人员的技法上,而应向更为本质的文化靠拢。舞蹈人类学将身体符号的特定风格、交流模式等拓展开来,并进行内在的逻辑分析,挖掘出动作背后那更加广泛、深刻的文化属性。
三、舞蹈人类学以何解释文化?
这一部分要讨论的是方法问题,也即舞蹈人类学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准确地解释文化。前文说到,舞蹈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象征符号,但是如果我们身处以少数专业人士为主导的建构语境中去看待舞蹈现象,就很难突破那种固定的、具体的舞蹈形式思维,也就难以把握形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属性。舞蹈人类学要迈出专业话语的阶层限制,以同一文化场域内部各成员,以及不同文化场域成员的平行对视为新的视角。舞蹈人类学视野内的舞蹈形式不是研究结果,而是开端,也即从舞蹈的符号身份出发来解读它所象征的文化意义。被誉为“舞蹈民族学之母”的库拉斯充分肯定了舞蹈人类学研究与多样文化内容之间的关联,其中包括文化内在的连续性、文化的传播与转型、文化的衰落与复苏等。[5]相比其他理论学科,舞蹈人类学更有能力将舞蹈现象与文化意义相勾连,这要归功于它在方法上的优势——田野调查。
我们知道,虽然当下舞蹈人类学的体系建设、标准制定与范畴确立颇为广泛和模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始终以科学的、客观的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宋·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田野调查是串联舞蹈人类学与文化解释的重要工具。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可以找出内在文化因素如何或积极或消极地决定舞蹈生成与发展,反之也可以解释作为符号的舞蹈动作并以此来阐释特定社会的文化内核。从“anthropology of dance”这种以舞蹈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来看,田野调查始终是其核心的方法论;从“dance anthropology”这种以舞蹈为核心的人类学方法研究倾向来看,它同样也是直接借用了田野调查这一文化人类学的主要方法来研究作为本位的舞蹈。无论是哪种偏向与视角,田野调查的方法都是舞蹈人类学阐释身体符号及其文化意义的有力工具。
舞蹈人类学家要想获得对特定对象及文化内涵的准确解释,就不能只停留于二手资料,他应该将现存的活态舞蹈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深入其中,实地体验一年或数年,学习、参与当地人的日常或仪式舞蹈活动,以此来研究特定地区的文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研究社会文化的基础与前提,田野工作中所观察记录的相关习俗内容便是民族志。民族志既是舞蹈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研究的重要文本形式,它要求在细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度描述。内斯在《身体、运动和文化:菲律宾社区的动觉和视觉象征主义》(Body,Movement,andCulture:KinestheticandVisualSymbolisminaPhilippineCommunity)中就采用了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来进行舞蹈研究:“在菲律宾宿务的卖蜡烛女性的舞蹈的民族志的描述中,解读了宿务住民的文化性惯习,再加上舞蹈动作的分析,完成了对宿务当地文化的理解。因此舞蹈动作的分析再加上民族志描述,可以在他者的文化逻辑中理解他者的身体行为。”[6]
主位和客位的两种认知方式在民族志中都应有所体现。不过,作为一种对解释文化的舞蹈的再度阐释,民族志更需要“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7]5,即以本土眼光来探索动作符号的生成结构和内容,这应该是舞蹈人类学在解释文化过程中的根本原则。“文化的符号学方法的全部要旨,在于帮助我们接近我们的对象生活在其中的概念世界,从而使我们能够与他们(在某种扩展的意义上)交谈。”[2]32舞蹈人类学的研究要解释文化,就是要通过田野调查来发现动作之后的抽象普遍的文化属性与意义,而非描述具体的动作本身,这需要研究者站在生成特定研究对象的立场去对待对象,尽量避免由客位视角所带来的偏差与误读。专业的舞蹈人类学家要尽可能地把握理想“自我”与现实“他者”身份之间的度,要考虑田野调查目标“文化差异最大化”的前提,要秉持理性和客观的独立态度。当然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它是一种带有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的独立,否则将难以触碰到舞蹈符号背后的文化核心层,也就难以理解符号的发生元点与流变过程。或者可以说,客位认知是文化鉴读者的本然视角,研究人员在面对特定的舞蹈动作时,甚至不需要去刻意强调这种研究方法属性,因为舞蹈动作生成的场域是一个有边界有范围的文化圈,对某个特定的文化圈来说,研究者本来就是来自外域文化的“圈外人”。相反,主位认知则需要被着重强调,因为它是研究者在面对陌生舞蹈形式和异质文化时本身所不具备的视角,要想深入挖掘符号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就要充分向主位认知的视角靠拢。
当然,主位认知的立场并不能完全复现舞蹈文化现象的生成,因为它依然是来自外部社会的舞蹈人类学家用他者认知而形成的一种“建构”。与本地人那种自然流淌而出的文化本性不同,舞蹈人类学对特定舞蹈符号象征意义的解释还是要次一等的,但它并非等同于虚假。所以,舞蹈人类学的民族志应从主位认知的立场出发作自然述说,但是也不能否认客位认知视角的解读属性。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使舞蹈人类学的研究更趋向于格尔茨所说的“交谈”,既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舞蹈文化符号创造者的交谈,也是试图作为文化阐释者的研究人员进行的自我交谈。
四、舞蹈人类学解释文化的矛盾
当我们把解释文化视为舞蹈人类学的功能时,会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舞蹈作为文化符号产生于社会中的人类互动,舞蹈人类学的研究绝不能脱离身体符号原本的语境,但舞蹈人类学只有在多元要素的语境中才能解读出身体符号及其背后文化的最完整的意义,因此,舞蹈人类学的语境研究和文化解释构成了一种互为目的与前提的矛盾。比如大多数的民间舞蹈都服务于某种特定文化的表达,当我们要解释某个民间舞蹈动作的符号意义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就成了研究得以展开的语境,这时研究的目的转而成了研究前提。这种研究逻辑的矛盾也导致了舞蹈人类学出现不同的研究路径,比如欧洲的舞蹈人类学倾向于以社会与文化语境来解释舞蹈符号的形成,关注的是舞蹈本身的内容;美国的舞蹈人类学则通过舞蹈去解读社会与文化,将舞蹈背后的意义作为研究重点。
舞蹈是人类整体生活方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动作,在它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整套看不见的文化体系,这套体系促成了舞蹈动作的发生与交流,也成就了动作符号的核心意义。所以,为了理解特定的动作方式,舞蹈人类学必须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文化语境,这个语境包含音乐、诗歌、宗教、观念、仪式等内容。语境研究是舞蹈人类学不可或缺的方法,它是整体视野中对舞蹈内容、形式和结构的具体研究。例如,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特罗布里恩岛岛民的舞蹈受其民族文化所制约,布朗在描述安达曼岛岛民的舞蹈时也体现出社会文化对舞蹈活动的决定性作用,等等。
如此看来,舞蹈人类学的功能之一在于通过研究舞蹈形式来解释特定社会的文化风貌,但是它的基础又不能脱离先于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语境。那么,语境在舞蹈人类学的结论中究竟是先于研究发生还是通过研究被构建?是自然流露出的意味还是来自他者视角的解读阐释?正是这些疑惑导致了第三部分提到的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在方法论中的程度问题。当我们深陷于舞蹈人类学为一条研究单行道的观点时,语境研究和文化解释的矛盾便被彻底激化了,它直接导致了具体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路径,以及主、客位视角所参与的不同比重。至于舞蹈人类学究竟是“anthropology of dance”还是“dance anthropology”,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源自对矛盾某一方的认知与选择。所以单行的研究道路要么是在文化语境中理解舞蹈,要么是通过分析动作体系来解释文化,似乎只能两个方向中选择其一,情况果真如此吗?
看似二律背反的语境研究与文化解释,其实在本质上并不矛盾。舞蹈人类学家可以把握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建构出的具体舞蹈符号以及集中表达这些符号的活动,这是研究的基础,也是所谓矛盾的集合点。舞蹈的意义产生于创造者身处的社会文化圈层内,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得出详细的民族志内容来确立特定圈层的文化内涵。无论是重点关注语境作为前提的意义,还是以挖掘动作中的文化属性为目的,都离不开对舞蹈动作细节的研究判定。人类学视野中的舞蹈动作体系是一种介质,是通往社会文化观念的解释手段,而舞蹈研究中的动作体系就是目的本身,构建舞蹈的社会文化只是解释动作体系得以形成的背景条件。由此,舞蹈人类学的研究属性体现出一种以动作为基准点而各有侧重的双向进程,它在身体动作与社会文化之间构造出两条路径:从文化意义到舞蹈动作的演变,这是以人类学为方法的舞蹈研究;从舞蹈动作到文化意义的探究,这是以舞蹈为要素的人类学研究。二者都是舞蹈人类学的研究路径、方式与意义,无论是通过舞蹈人类学来说明文化,还是依托文化背景来明确舞蹈的形成,都能实现积极的结果——解释特定的社会文化。所以,语境研究的直接结果依然是阐释文化。只不过由于二者的立足点不同,文化阐释所处的位置有所差异,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在前者中作为前提条件,在后者中作为目的结论的不同罢了。
五、结语
总的来说,无论是将舞蹈视为人类学研究的特定分支,还是以舞蹈为核心进行人类学方法的研究,我们都可以明确文化是舞蹈动作的成因且被动作所代言。舞蹈人类学可以解释舞蹈背后的文化属性,由这一点还可以衍生出人类学之于舞蹈研究的更多意义。舞蹈的实践工作以动作方式发展文化原点,舞蹈的理论研究则从动作形式出发把握更深层的文化属性,由于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方向偏差,舞蹈实践和理论之间通常会产生错位与隔阂。舞蹈人类学可以起到沟通二者的作用。舞蹈人类学以动作来解释文化,使舞蹈理论不再脱离实践,沦为自说自话的空谈。舞蹈人类学赋予舞蹈实践以更加自觉的文化认知。舞蹈人类学给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范式,这当然也要归功于舞蹈人类学借助田野调查的方法,最终以动作解释文化的积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