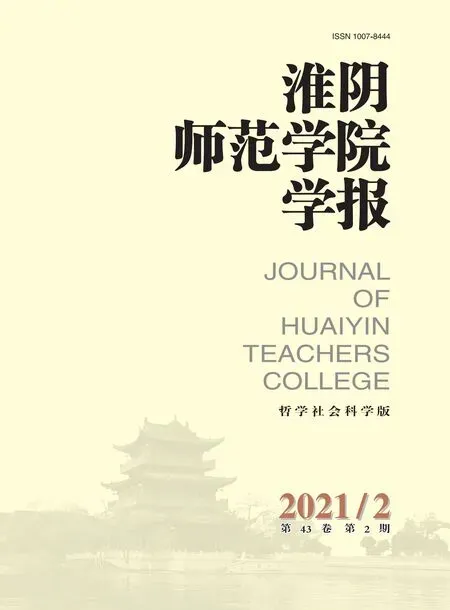“民歌学”场景下的民歌批评史料整理与研究略议
周玉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200)
在从事历代民歌整理与研究的同时,近年来,笔者开始着手民歌批评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希望在此基础上,撰成体例完整、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细化与补充的《中国民歌批评史》,笔者并将其与民歌创作传播研究、民歌发展史研究并称为“中国民歌学”理论体系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三位一体,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共同呈现传统民歌这一中华民族优秀文学/文化遗产的瑰丽风姿。此处所谓民歌,按《毛诗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的说法,包括合乐的歌与徒歌的谣;“合乐的歌”部分,既包括通常所说的民间歌曲,也包括民间流行、深受群众喜爱的绝大部分俗曲时调。所谓民歌批评,指集中或者散见于历代总集、别集、选集、笔记、小说、戏曲,以及方志等各类文献中与民歌有关的评论、评判和部分叙述性内容。笔者的计划是以整理与研究并重,全面系统地梳理存世文献中有关民歌批评的资料,辑为《历代民歌批评史料汇编》,在此基础上撰成《中国民歌批评史论》。若依旧例,前者可称作“民歌话全编”,是对已有“诗话全编”“词话全编”“曲话全编”等的补充,后者重点考察民歌批评在规范和推进民歌发展、文学发展以及调整两者关系过程中的作用,可视作对文学批评史、韵文批评史的丰富和拓展。目前整理与研究工作已过半,谨将若干体会和想法公之同好,并祈方家不吝赐教。
一、历史的回顾
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刘半农、周作人、郑振铎、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史意义的民歌整理与研究的先河,并在此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一是对民歌的功用有了新的认识。20世纪初,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梁启超、李伯元、陈独秀等人在其主持的《新小说》《绣像小说》《安徽俗话报》上,相继开设“杂歌谣”“时调唱歌”等专栏,收集刊载民歌、拟民歌,向民众讲述时局,输灌救世救国的道理。1913年2月,鲁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执事,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册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1];1920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倡议征集中国近世歌谣;1922年12月,《歌谣》周刊创刊,由周作人起草的发刊词指出,歌谣除可作民俗学研究的资料之外,还可“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2],同时重视歌谣的民俗学与文学功用,对此前梁启超、陈独秀等片面强调民歌的社会功用是一个突破。
二是在民歌的收集、整理与传播上取得重要成果。民歌收集的手段更加多样,除已有文献的挖掘(如冯梦龙辑《挂枝儿》《山歌》的发现、校点与出版)外,在“到民间去”(1)详见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思潮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开始面向民众,做具体、广泛的田野调查工作,民歌“活”的特性日益受到重视(如顾颉刚对吴歌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刘半农赴绥远调查、收集民歌并予录音)。与此同时,借助新兴印刷技术和传播媒介,各类民歌出版物迅速覆盖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在相继成为全国民歌唱本编辑、出版中心的同时,也成为各地民歌艺人的汇聚中心、民歌艺术的传播接受中心,民歌并在娱民乐民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醒民化民的作用。
三是民歌研究别开生面。
其一,以《歌谣》周刊、《民俗周刊》为主要阵地的民俗学派,从特质、内容、价值、艺术、起源、分类等多个维度,对民歌(主要是“徒歌”)本身及其与社会的互动进行了充分讨论。在《歌谣》周刊与《民俗周刊》的具体编辑与参与者的研究实践中,始终存在两个偏向,其一,作为征集与研究对象的“歌谣”,偏重“徒歌”即“口唱/说的歌”,而轻视、忽略“合乐的歌”。其二,以《歌谣》《民俗周刊》为阵地的近世民歌研究,其方法偏于民俗学而非文学,目的如周作人所说,是“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3]33。
其二,以朱自清、郑振铎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者,从文学与俗文学的角度,对民歌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歌谣》《中国近世歌谣叙录》《歌谣与诗》《古诗歌笺释三种》等著述,从源头上梳理民歌与文学的关系,视野宏阔,立论公允,新人耳目。如其对“歌谣”内容的界定,就很开明。《中国近世歌谣叙录》云:
歌谣的范围,有两种说法:一是以徒歌为限,一是兼包徒歌与乐歌。中央研究院民间文艺组将俗曲与歌谣分开,似乎采用第一说。笔者以为徒歌与乐歌很难严格区别,许多俗曲都可徒歌,而徒歌也有歌与诵的不同,一般的徒歌是只能诵的,山歌才是能歌的。山歌既可不另列为一类,乐歌徒歌,似乎也不妨并论。笔者只说不妨并论,却不是说不能分论,须看研究的目的与方便如何,不必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本篇所有歌谣,是取二义,是广义的。[4]
此处以“乐歌徒歌”并论的“广义”说,即较分论的狭义说更符合中国民歌发展史的实际。
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及一系列介绍讨论传统民歌的著述,是在雅俗文学交融互动的框架内,为民歌在文学史上争得应有的地位与名分,而且将民歌与杂剧、鼓词、散曲、子弟书等置于同一阵营的做法,客观上也为民歌的生成发展研究拓展了空间。此种做法,具有发展史观与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中国俗文学史》第十章《明代的民歌》,这样论述民歌与文人文学的关系:
元代散曲到了第二期,已是文人们的玩意儿了,和诗词是同流的东西,离开民间是一天天的远了。到了元末明初,刘东生、贾仲名、汤舜民等人出来,虽使曲坛一时现出不少的活气,却也使散曲走入了魔道,永远的不能翻身。……他们是那样的陈陈相因呵!……文人学士们的作风在向死路上走去,而民间的作品却仍是活人口上的东西,仍是活跳跳的生气勃勃的东西。而不久,又有许多文人学士们厌弃其旧所有的,而复向民间来汲取新的材料,新的灵感,乃至新的曲调,而立刻,他们便得到了很大的成功。[5]
周作人《歌谣》以为,“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从文艺的方面,我们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或做新诗创作的参考”[3]34。郑振铎的上述观点,与知堂所谓民歌研究“从文艺的方面”,“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或做新诗创作的参考”说,性质相近,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是以条理化、系统化的方法,对此说进行了全面的溯源性的论证。此外,任半塘、胡适等人对明代民歌与拟民歌的看法,亦与《中国俗文学史》意见类似,如1922年,胡适在《读书杂志》第4期发表《元人的曲子》一文,对明代民歌下过这样的评语:“明代的小曲,也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不幸是没有人留意到它们。”此一评语,可与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评论《儒林外史》时所说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并举。“伟大也要有人懂”被《儒林外史》研究者奉为圭臬,“最有价值”却“没有人留意”说,则鲜有提及。
其三,以刘半农、李家瑞、胡怀琛等为代表的民歌研究者,开始尝试确立以民歌(俗曲)为主体的研究范式,撰写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北平俗曲略》《中国民歌研究》等专书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意义。诸人之中,尤以刘半农的贡献最为突出。刘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是近世歌谣征集研究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与运动其他发起参与者多数偏于徒歌、偏于歌谣的民俗学研究不同,刘半农向来重视“乐歌”即通常所谓时调俗曲的整理与研究。1918年3月29日,其在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作演讲,题目是“中国之下等文学”,将“下等小说”分为三种,“第二种是俚曲或称作小调——下等小说出版家称它为‘时调山歌’——字句完全与音乐配合,句法之长短无定,唯每有一曲调,即自成一格律,只可按谱填字,不能互相移用。其或曲短而词长,则以一曲叠唱至四次(如《四季相思》)、五次(如《五更调》)、十次(《十杯酒》《叹十声》之类)、十二次(《十二月花名》《十二月想郎》之类)不等,亦有叠至十二次以上者(如《十八摸》之类)”[6]55。演讲随后评说了“下等小说”的文学性与思想性,如文学性,曰“做下等小说的,大都没有在文学上用功夫,所以描写中下等社会的情状虽能惟妙惟肖,字句中却全没有审美的工夫,文体的构造上也全不讲究,往往一篇之中,开场甚好,到后来便胡说一番”[6]69。其后他指导常惠编成《北京小曲百种》,与李家瑞合作编撰《中国俗曲总目稿》,指导李家瑞撰成《北平俗曲略》,大大改变了近现代民歌整理研究重“徒歌”轻“乐歌”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当下,民歌整理与研究呈现了不一样的面貌。
一是论者开始在文学发展的宏观格局中,分析民歌与其他文学体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代表性著作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水照、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等,对《国风》、乐府民歌、竹枝词以及明代民歌、清代民歌的成就及其在各个文学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均有专题评述。
二是民歌的收集与整理取得了新的成绩。代表性成果有关德栋主编《明清民歌时调集》,蒲泉、群明主编《明清民歌选》(甲、乙集)以及各地先后出版的“歌谣集成”等。陈书录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民歌整理与研究丛书”,对上至先秦、下至清代的传统民歌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为民歌发展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支撑。
三是专题研究引人注目。日本学者大木康、中国台湾学者鹿忆鹿的冯梦龙辑民歌研究,中国台湾学者张继光的明清小曲研究、舒兰编《中国地方歌谣集成》(理论研究1—10册,实是《歌谣》《民俗》等民国出版物中民歌研究文章的汇编),大陆学者张紫晨的歌谣简史梳理,赵敏俐的《诗经》与乐府民歌研究,吕肖焕的古代民谣研究,赵瑶丹的唐宋民谣研究,陈良运、张德建等对“真诗乃在民间”说的探究,柳倩月的晚明民歌批评研究,板俊荣的历代俗曲曲牌研究,李秋菊的清末民初民歌时调研究,徐新建的民国时期民歌学术史研究,康凌等对左翼诗歌歌谣化、红色歌谣生成机制的关注,周玉波的明代、清代、近现代民歌及婚嫁喜歌研究,以及新近出版的陈书录先生等著《中国历代民歌史论》,使得民歌研究在专题化、精细化、系统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相适应,文学发展与民歌发展、民歌批评与民歌发展等的相互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
总体而言,以上整理与研究,一是主要着力于历代民歌文献的收集整理,二是多以断代或专题的形式,讨论民歌及其与社会发展、文学发展的关系。但是对历代民歌批评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重视不够,更无人以“中国民歌学”为宏观背景,以文学史、民歌史为主体,在占有充足史料的基础上,整体性地开展民歌批评史的研究。
二、内容与架构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者尝试建构的“中国民歌学”理论,兼具总书记所说的“传统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多重身份,理论体系中包含若干细目,细目有不同分法。一种是二分法,以坐标系为例,纵轴为民歌生成发展学,横轴为民歌接受影响学,自然形成的第一象限,即为“民歌学”覆盖区域。生成发展基于民歌内涵(主体),包括民歌发生机制研究、民歌艺人群体研究、民歌创作表演研究、民歌发展史研究、民歌理论批评研究、民歌主题研究、民歌音乐研究、民歌审美研究等;接受影响着重民歌外延(客体),包括民歌受众构成研究、民歌民俗学研究、民歌方言学研究、民歌地理学研究、民歌考古学研究、民歌社会学研究、民歌戏曲学研究、民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诸多方面。一种是三分法,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民歌创作表演研究,二是民歌史研究,三是民歌理论批评研究,三位一体,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无论何种分法,各部分均互有关联,共同组成“民歌学”理论的完整架构。无论二分法还是三分法,民歌理论批评研究在其中都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民歌批评史在民歌理论批评中,又是重点的重点(2)有关“民歌学”理论体系问题,详见周玉波《“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刍议》,《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8—31页。。
细而言之,民歌批评史的研究对象是历代(先秦至民国)学者关于民歌的评论、考辨,包括部分叙述性文字。这些批评意见,集中或者散见于历代总集、别集、选集、笔记、小说、戏曲,以及方志、类书等各类文献中(如晋崔豹撰笔记《古今注》中,有数条介绍《陌上桑歌》《董逃歌》等背景的文字;历代史书的《乐书》《乐志》《音乐志》《礼乐志》中,多有评说民歌功能与价值的内容),长期以来,少见系统性梳理。本研究综合考察其发生发展的文学、思想、文化与社会背景,在完整的历史链条上讨论其内容、价值及相互间的影响,认识其在民歌发展史与文学发展史上所发生的作用。
在具体实践中,笔者将整理与研究分为两大板块:
一是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最终成果为《历代民歌批评史料汇编》。以时间为经,作品为纬,次序编撰,成为专书。大致分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辽金元、明、清、现代等段落。其中现代部分,因为作品众多,只做截取处理(如顾颉刚的吴歌研究,朱自清的歌谣研究,胡怀琛的民歌研究,李家瑞的俗曲研究,均有专书,“汇编”只选取部分内容)。
二是在完成史料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撰写《中国民歌批评史论》。其参照系有二,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是中国民歌发展史,同时适当借鉴文学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新兴学科中与民歌批评有关的成果。
史论部分大致框架如下:
第一部分,先秦民歌批评——我歌且谣,言志观俗。中国诗的滥觞期,也是民歌的起点。重点围绕民歌的发生与功能批评展开。如民歌发生。《诗经·魏风·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吕氏春秋》云“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这是从不同方面,指出民歌的起源与人的情感需求(忧)与生理需求(举重劝力)有关,归结为一点,即民歌是人类本性的自然外现。再如民歌功能。《礼记·王制》载录陈诗说,郑玄注云:“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孔颖达曰:“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战国竹简《孔子诗论》亦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这是对风诗(民歌)功用的明确界定,“观人俗”“观其政令之善恶”,都说明民歌有着工具的功能。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拟设“新乐府”栏目,“专取泰西史事或现今风俗可法可戒者,用白香山《秦中》《乐府》、尤西堂《明史乐府》之例,长言永叹之,以资观感”(黄遵宪《与梁启超信》,《新民丛报》第14号)。时移世易,沧海桑田,内在的精神却代代相传,相隔2 000余年,人们对民歌“以资观感”与“观人俗”“观其政令之善恶”功用的认识,仍是一脉相承,由此亦可觇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而历代民歌,正是这一生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本部分另从“诗言志”入手,对民歌言情与体物传统、民歌内容的多样性、民歌形制及功用等进行思想史、美学史层面的钩深探赜,味道研机。
第二部分,汉魏晋南北朝民歌批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此为民歌初步定型期。如果说《诗经》还在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之间有所纠缠的话(《诗经》既是文学经典,同时也是民歌经典),那么到了两汉,专门机构的设立、采歌谣观厚薄的职能定位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功能描述,使得民歌从机制到内容、功用都基本定型。从此以后,民歌与文人创作的分野基本清晰;南北朝民歌的绚丽多姿,更使得言情民歌在《诗经》的规整(多是齐言)与规矩(“温柔敦厚”“乐而不淫”)之外,显露了清新活泼自由自在的另一面。本部分另设若干专章,集中梳理汉儒有关《诗经》中风诗的意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的价值等。
第三部分,唐宋辽金元民歌批评——起诸民间,孕育新变。竹枝词的流行,民间俗词的勃兴,为全新韵文体裁——词(曲)的出现,做好了铺垫。此一段落,可称为民歌的新变期。本部分重点围绕其时文人对俗词的评价、对词体(曲体)产生的讨论而展开。另,唐代民歌的新变还体现在文人大量创作催妆词、障车文、撒帐歌以及上梁致语等,大大扩充了民歌的体裁与题材。元稹《唐故工部元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言及,“秦汉以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俗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全唐文》卷六百五十四)。催妆词、障车文等的流行,表明到了唐代,“天下俗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不但“随时间作”,而且已经蔚为风气,《全唐诗》《敦煌变文集》以及《司空表圣文集》等辑有众多此类作品,即是证据。俗谣、民讴、嬉戏之词的繁盛,表明民歌在世俗化、民俗化乃至庸俗化道路上又有长足进步,民歌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强化。其时的民歌批评,对此类新词俗词多有关注,对其兴起发达,功不可没。本部分亦设专章,专门讨论元白新乐府运动理论与郭茂倩《乐府诗集》所体现的民歌批评意见等在民歌批评史上的特殊意义。
第四部分,明代民歌批评——我明一绝,曼妙多姿。明代民歌以其与文学革新思潮的紧密关系而在文学/民歌发展史、文学/民歌批评史上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本部分重点讨论李梦阳“真诗在民间”说产生的文学、文化及社会背景,进而分别讨论李开先、袁宏道、冯梦龙等人在民歌批评方面的特别贡献,讨论“我明一绝”说的由来与含义。
第五部分,清代民歌批评——旧调新声,竞胜一时。清代民歌既继承了明代民歌的传统,也有自己的特色。最大的特色,是进入晚清,因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鼓吹,民歌承担起了醒民救世的功能。此外,底层文人开始重视劝世民歌的创作,劝善歌较前代劝善文更受一般民众欢迎,而且影响深远,直达当下。
本部分另对高棅等《全唐诗》、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古诗源》、屈大均《广东新语》及吴淇《粤风续九》(李调元《粤风》)等涉及的民歌批评材料,均以专题形式进行研究。如《明诗综》与《古诗源》。前者以整整一卷的篇幅,专门辑录《京师童谣》《宫大稔民歌》一类无名氏作品,以其与文人作品并列,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较《全唐诗》虽然收录杂歌谣词但又多系于具体作者名下的做法,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编选者对民歌的态度,即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民歌批评意见。后者以古逸民歌《击壤歌》《康衢谣》等为后世文人诗的源头与典范,沈德潜在《古诗源·序》中,充分表露了其通达的民歌观:
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今夫观水者,至观海止矣,然由海而溯之,近于海为九河,其上为洚水,为孟津,又其上由积石以至昆仑之源。《记》曰:“祭川者先河后海。”重其源也。唐以前之诗,昆仑以降之水也。汉京魏氏,去风雅未远,无异辞矣。即齐、梁之绮缛,陈、隋之轻艳,风标品格,未必不逊于唐,然缘此遂谓非唐诗所由出,将四海之水,非孟津以下所由注,有是理哉?有明之初,承宋、元遗习,自李献吉以唐诗振天下,靡然从风,前后七子互相羽翼,彬彬称盛。然其敝也,株守太过,冠裳土偶,学者咎之。由守乎唐而不能上穷其源,故分门立户者,得从而为之辞。则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予前与树滋陈子辑唐诗成帙,窥其盛矣。兹复溯隋、陈而上,极乎黄、轩,凡三百篇、楚骚而外,自郊庙乐章,讫童谣里谚,无不备采,书成,得一十四卷,不敢谓已尽古诗,而古诗之雅者,略尽于此,凡为学诗者导之源也。昔河汾王氏删汉、魏以下诗,继孔子三百篇后,谓之续经,天下后世群起攻之曰僭。夫王氏之僭,以其拟圣人之经,非谓其录删后诗也。使误用其说,谓汉、魏以下,学者不当搜辑,是惩热羹而吹齑,见人噎而废食,其亦翦翦拘拘之见而矣。予之成是编也,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夫宋、齐后之作者。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夫。[7]
“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云云,是民歌批评的重要史料。
第六部分,民国民歌批评——杂花生树,另出机杼。刘永济《词论》云:“文艺之事,言派别不若言风会。”[8]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巨变,民国民歌也进入真正的转型期,与其时社会现实更为贴近,形式与内容更为丰富多样,与曲艺乃至戏曲的联系更为紧密,传播速度更为快捷,覆盖范围更广,民歌研究一时间更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本部分以《歌谣》周刊、《民俗》周刊刊载文章及刘半农、郑振铎、顾颉刚等的著述为重点,考察其时学术界在民歌整理与研究领域所作的探索,以及民歌在参与社会文化变革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史论》部分坚持史、论结合,在“民歌学”场景下,对民歌批评在民歌生成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与匡正作用进行回顾与总结;对民歌批评与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关系作细致辨析;在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背景下,突出民歌批评在当下文化建设中的借鉴与指导作用。
三、价值与创新
笔者以为,民歌批评史料整理与研究的重点,是对民歌发生发展的几个关键段落,如《诗经》时期、两汉乐府时期、南北朝民歌时期、敦煌俗曲时期、明代民歌时期、清代民歌时期、民国民歌时期,结合民歌批评意见与民歌创作传播情况,进行切片分析。一是考察其时民歌批评与民歌发生发展、传播接受的互动情形,进而在“民歌学”体系中,确认民歌理论批评在规范调整民歌创作表演实践、民歌繁衍发展史实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二是考察民歌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长时段的民歌批评史的基本规律与特性。在此过程中,既要确立文学本位观点,又不能简单地将民歌批评视作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一个部分,必须正确处理两者关系。为此,笔者以为此项工作,须有明确的目标追求。
首先是学术价值。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歌,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如《诗经》,既是最早的民歌总集,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相应地,与民歌有关的批评意见,对民歌发展、文学发展也始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从源头上,为民歌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合理性、正当性的依据。传统文化极重正名,正名即是“合理性”“正当性”的另一种表述,如《诗经·魏风》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指出歌谣的产生,是人的天性所致,歌谣具有化民辅政的功能,因此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正当性。数千年的民歌发展史,借着此种“天然正当性”的庇护,而光明正大地汇入浩浩荡荡的文学发展史的长河中,成为中华民族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民歌批评对民歌的发展,始终扮演着鼓吹、约束并重的角色。以明代为例,顾起元等人对民歌“诲淫导欲,亦非盛世所宜有也”(《客座赘语》卷九《俚曲》)的訾议,实际上是对民歌传播接受行为的调整和制约,不能简单地视为卫道士对新生事物的打压与歧视;李梦阳“真诗在民间”说,则是完全正面的激励,对明代民歌的兴盛有着“导夫先路”的积极作用,对明代的文学生态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民歌批评既依附于民歌发展的实际,也从属于文学批评,同时更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其对民歌发生、发展轨迹与兴衰演变规律的探究,对民歌社会功能与美学特征的阐发,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固有的理论色彩与思想体系,而其与文学批评的融合互动,客观上为民歌批评与民歌发展都拓展了宽广的空间。以上说沈德潜《古诗源·序》对民歌与文学关系的论述为例,由此角度切入,即可深入探究清代民歌在正统文化语境/主流文化圈中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如有文章云:
《古诗源》是沈德潜系列诗歌选本中较有影响的选本之一,承载着他的诗学理想、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是历来的研究焦点和热点。学界现有研究多着眼于选本整体、沈氏诗学理念、古诗诗学观念等方面……与沈德潜的唐诗观、宋诗观方面的研究文章相比,沈德潜汉代诗歌风貌构建状况、诗学观念研究则更显寂寥,目前仅见郝青霄的《论沈德潜汉代诗歌的接受》,少数硕博论文粗略涉及沈德潜的汉代诗歌选评问题,如康兆祯的《沈德潜的先唐诗歌评点析论》。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文拟从沈德潜对汉诗的选录、点评及其诗学倾向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学界对沈德潜的诗学思想研究。[9]
相较于唐诗观、宋诗观、汉诗观,沈德潜由《古诗源》的编纂而显性表达的民歌观(“童谣里谚”也可使人“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包括民歌与文人诗的源流关系,同样值得重视,《古诗源》与《古今诗删》《古诗纪》《古诗归》《古诗评选》《古诗镜》等透露的正统文化语境/主流文化圈对民歌的看法态度,更可做整体性梳理。
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民歌批评的历史与作用,尤其是其独具个性的理论色彩与思想体系,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如目前学界关于民歌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固然丰硕,却少有人在文学批评史与民歌发展史等的场域中,全面系统地总结民歌批评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全部过程,更无人以“民歌学”为宏观背景,深入探究民歌批评与民歌发展的互动关系、民歌批评与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本研究即旨在弥补此一学术缺憾。笔者试图全面系统地汇集存世文献中与民歌有关的批评资料,并作仔细钩稽,借此清晰呈现历代学者对民歌的看法态度,回溯传统民歌的生长历程与所处环境,展示客观上处于亚文化(民间文化)地位的民歌的风采,探讨民歌批评与主流文化(文人文化)批评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民歌批评的思想史与美学史意义,助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歌学”理论体系。
其次是应用价值。本研究的应用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历代民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唐诗、宋词一样,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之一。本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是为“文化自信”寻根,是贯彻落实国家传统文化复兴战略的具体举措。其二,民歌是极具典型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研究对当下的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对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民间文化资源普查工作,更有着明确的理论指导意义。
实际工作中,笔者始终强调思路清晰,创新第一。
具体思路是用竭泽而渔的方式,从各种总集、别集、选集、笔记、小说、戏曲,以及方志、类书中,全面搜集和整理历代学者有关民歌批评的文献资料。其次,在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甄别整理的基础上,在文学批评史的框架内,全面系统地总结民歌批评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全部过程,进而详细探究民歌批评与民歌创作表演及传播接受的互动关系、民歌批评与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在研究中注重四个维度的考察:从横向上考察历代学者对当代民歌的批评(如明代学者对明代民歌的批评);从纵向上考察历代学者对前代民歌的批评(如清代学者对汉魏乐府民歌的批评);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历代民歌批评观念及其史料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历代文人推崇、重视民歌,并非文学发展史与批评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可以从儒家的民本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中寻得足够的顶层资源支持;适当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在大众文化、文学社会学、口传诗学与采/陈诗文化的多重场景中,考察历代民歌批评的成绩与局限,及其对世界文学发展的贡献。
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新。文学演进始终存在两条路径,一是文人文学/雅文学,是显性的,主流的;一是庶民文学/俗文学,是隐性的,非主流的。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绚丽图卷。此前的文学史著述,要么将这两条路径混而为一,在叙述主流的过程中捎带提及非主流,要么分作两途,各说各话,很少做交叉研究的工作。笔者以为,历代民歌是庶民文学/俗文学的主干,历代民歌批评史料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批评史论,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爬梳整理,既是对民歌研究的深化,也是对文学批评的细化和拓展。
二是方法新。注重民歌批评史料与具体的民歌作品互补互证,民歌批评与文学批评互补互证,民歌史料整理与民歌批评史互补互证,传统理论与新兴理论互补互证。如传统理论与新兴理论的互证。传统理论如上所说,“观风俗,知薄厚”(班固《汉书·艺文志》卷三十)与“诗言志,歌咏言”一起,在传统民歌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完全可以称作纲领性的宣言,传统民歌发展史与批评史的撰写,不能也不该离开这个纲领性宣言的语境。但是,借鉴西方新兴的批评理论,对传统民歌的发生发展史实以及有关观念进行新的审视,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也可以丰富研究的内容,提升研究的层次,典型者如大众文化理论、艺术人类学理论、文学社会学理论,都可以作民歌批评史研究的有益补充。如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引述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意见,认为民歌是大众文化的一种,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唯有民歌依旧保持了早期诗歌的道德效力,因为它以口相传,和曲吟诵,并负载实际功能”[10]。赫尔德所谓的“道德效力”“负载功能”,与我国“陈诗”“采诗”所说的“溥观人俗”“观其政令之善恶”,等等,有共通之处,如此则可尝试在大众文化理论与采诗传统的双重场景下,揭橥民歌批评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
三是最终成果新。《历代民歌批评史料汇编》与《中国民歌批评史论》,无论具体内容还是最终形式,都有一定的独创性,是民歌发展史研究的丰富和补充,也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延伸和拓展。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传统民歌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样式,民歌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是民歌史、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累积的大量的民歌批评史料,是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史的珍贵文献。因此私心以为,在传统文化复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已经上升为国家策略的当下,加强对历代民歌批评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加紧建构、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歌学”理论体系,非常重要,也很有必要,前景广阔,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