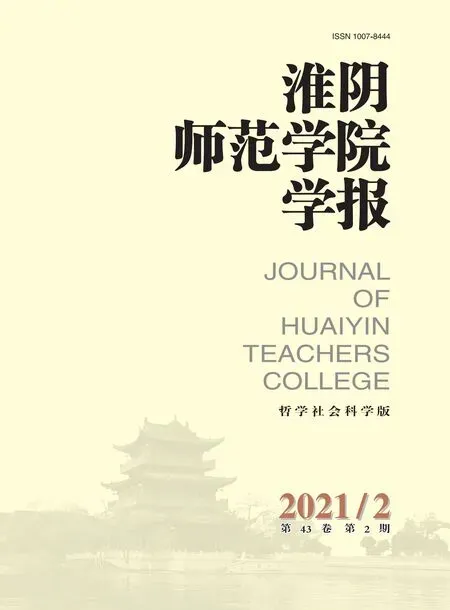战国楚简姓氏人名问题研究述评
张淑一, 郑晓璐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先秦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与秦汉以后有很大差异。当时姓氏人名的表现形式、功能作用等,也与后世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它们不单纯具有名号的属性,还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家族形态、礼俗文化等方面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的发展演变能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性质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末,古文字学家刘钊教授曾经指出:“目前的姓名学研究存在着两个倾向:一是研究姓氏多,研究人名少;二是对古代,尤其是汉以前的人名研究还不够。第一个倾向是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历史上几乎历代都有研究姓氏的专书,却从无研究人名的著作。第二个倾向是因为汉以前典籍中的资料太少,难以入手。其实汉以前的古文字中有许多人名数据,可以与典籍中的人名进行对比,进行各种角度的研究。”[1]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被大量发掘,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战国简牍更是井喷式涌现,其中的包山楚简[2]、望山楚简[3]、曾侯乙墓竹简[4]、郭店楚墓竹简[5]、新蔡葛陵楚简[6]、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7]、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8]等,都包含大量先秦时代的姓氏人名。如果较为系统地进行考察,摸清战国楚简姓氏人名的总体面貌和相关研究态势,可以为很多先秦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随着楚简材料的大量发现和对其中名号问题复杂性认识的深入,学界对于楚简“姓氏人名”的理解亦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某人的姓或名,而是把能够起到指称某一具体人物作用的所有名号——包括姓、氏、名、字、谥号、一些人物的官职、某些封君的封号以及某些目前性质尚不明确的上古人物称谓如尧、舜、禹等都纳入考察范围,从广义的“人名”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所述之楚简“姓氏人名”,亦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
一、学界已有研究成果
学界目前对战国楚简姓氏人名材料进行的整理与研究,最基本的当属简牍整理者在对简牍进行编连、释文、句读和解释时,对其中姓氏人名所进行的判定与释读。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嗣后相关研究打下了基础。之后一些学者在对简牍进行综合研究时,也对部分姓氏人名有所考证和订补。如刘信芳的《包山楚简解诂》,陈伟的《包山楚简初探》《郭店竹书别释》,季旭升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读本》系列,以及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等。(1)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伟:《郭店竹书别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季旭升主编,陈霖庆、郑玉姗、邹浚智合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读本》,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季旭升主编,陈美兰、苏建洲、陈嘉凌合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读本》,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季旭升主编,陈惠玲、连德荣、李绣玲合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读本》,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专门对战国楚简姓氏人名资料进行研究的论文论著,分为以下几方面。

其二,对楚国以外的国家人名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总数不算少,但相对于对楚国先公先王先妣及公族世系的研究,则显得缺乏系统,较为分散。包括宋镇豪的《谈谈商代开国名臣伊尹》[49];刘信芳的《郭店简所记吕望身世辨析》[50];董珊的《清华简〈系年〉所见的“卫叔封”与“悼折王”》[51];陈伟的《“苦成家父”小考》[52],《包山简“秦客陈慎”即陈轸试说》[53];颜世铉的《上博楚竹书“苦成家父”名字解诂——兼释三则“雠”和“丑”通假的文献》[54];程浩的《君陈、君牙臆解》[55],《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56],《由清华简〈良臣〉论初代曾侯“南宫夭”》[57],《小议〈良臣〉中的“叔向”》[58];宋华强的《〈上博(七)·吴命〉“姑姊大姬”小考》[59];广濑薰雄的《释清华大学藏楚简(叁)〈良臣〉的“大同”——兼论姑冯句鑃所见的“昏同”》[60];黄锦前的《“许子佗”与“许公佗”——兼谈清华简〈系年〉的可靠性》[61];王宁的《清华简〈良臣〉〈子产〉中子产师、辅人名杂识》[62],《清华简六〈郑文公问太伯〉之“太伯”为“泄伯”说》[63];罗小华的《战国简册中的女性人名称谓研究》[64],《清华简〈良臣〉中的“女和”》[65],《试论清华简〈良臣〉中的“大同”》[66],《试论清华简中的几个人名——兼论“卞”字的产生》[67];周书灿的《姜太公称谓及清华简〈耆夜〉“吕尚父”问题》[68],《清华简〈封许之命〉“吕丁侯于许”新解》[69];黄庭颀《论古文字材料所见之“伊尹”称号——兼论〈尹至〉、〈尹诰〉之“尹”、“执”(挚)》[70];马楠的《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与郑国早期史事》[71];谭生力的《由清华简〈赤鸟咎之集汤之屋〉看伊尹传说——兼论该篇传说的文化内涵》[72];袁金平的《由清华简〈系年〉“子眉寿”谈先秦人名冠“子”之例》[73];白显凤的《百里奚氏名及其身份事迹考论》[74];马卫东的《清华简〈系年〉项子牛之祸考》[75]等。

其四,专门针对战国楚简人名中谥号谥法材料的研究。包括李零的《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重读“秦王卑命”钟铭文》[88];董珊的《出土文献所见“以谥为族”的楚王族——附说〈左传〉“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的读法》[89];罗小华的《试论清华简〈系年〉中的几个多字谥》[90];马卫东的《文献校释中的周代多字谥省称问题》[91]等。
其五,有关战国楚简人名材料的总论性研究。包括白显凤的《战国楚简人名异写研究》[92],《出土楚文献所见人名研究》[93];何淑媛的《战国楚简中的楚国人名研究》[94];陈美兰的《战国竹简东周人名用字现象研究——以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为范围》[95],《近出战国西汉竹书所见人名补论》[96]等。
此外,对于楚简中的部分神灵名和传说时代上古帝王的名号,也有学者进行过考察,包括刘信芳的《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祇》[97];宋华强的《新蔡简两个神灵名简说》[98];郭永秉的《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99]等。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是一个充满新问题和新挑战的领域。如著名学者陈伟先生所言:“任何一批时代较早的出土文献,都会在原始材料公布之后有一个历时较长、由较多相关学者参加的讨论过程,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阐释上,达到较高的水平,形成大致的共识。”[100]战国楚简姓氏人名资料的整理研究也不例外。已有的研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学者们通过字形分析、辞例比较、文意对勘、音转识别等,考释出了绝大部分的姓氏人名;对于楚国的先公先王、某些家族的族源世系以及楚简人名的用字特点、取义方式、异写原因、一些人物的身份事迹等,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已有的成果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后续的研究,无论是赞同采纳还是订补修正,都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有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才有后人一步步地拓展和推进。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研究力量的分配不均衡。目前,对楚国姓氏人名的研究较成系统,对其他国家姓氏人名的研究则比较零散;对楚国先祖、先公先王和公族的姓氏人名研究较多,对平民阶层姓氏人名的研究较少;对某一具体姓氏人名的个案研究较多,把相关姓氏或人名整合起来进行分析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对姓氏人名本身的文字构形、用字特点、异写通假等进行考释的文献学研究较多,对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规则、社会变迁、观念形态等进行分析的历史学研究较少;等等。这些问题的造成,当然有材料本身的原因——楚简首先反映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其所包含的楚国姓氏人名因素远超其他国家,其中作为统治者的楚国王族公族的姓氏人名材料比普通民众的远为系统和丰富。作为出土文献,楚简文辞佶屈聱牙,较早接触该材料的都是古文字和古文献整理者,从文献学和训诂学角度所进行的形音义考释自然也比较多。尽管如此,其他方面的研究也还是有必要逐步开展,并且已经具备了一些开展的条件。
其二,已有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比如谥号问题,楚简中西周春秋以下的周天子、各诸侯国国君以及某些国家的卿大夫和封君,其人名多以谥号的形式出现,这类人名占据了楚简人名相当大的部分。在中国古代,谥号不仅是一个人死后的称谓,还能反映其生前的政治地位、道德品行、社会贡献,以及国家主流话语对其的评价。这种评价又与当时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以及该国的统治态度、舆论导向、价值取舍和政治变迁密切相关。通过对楚简人名中谥号和谥法的研究,可以丰富对于先秦人物和先秦历史的认识,为传世文献中某些长期聚讼的问题提供新的解释。对此,前人进行过一定的探究,但无论是在成果数量还是研究的系统性上,都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提升。
其三,某些研究结论有待不断修正。楚简所记载的姓氏人名形式非常复杂,有单字名,有二字名,有冠姓者,有不冠姓者,有时会造成研究者难于判定此类人名究竟是单名还是姓+名;楚简所记载的姓氏人名常常与某些官名、地名相混杂,为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部分楚简的文意尚未完全明了,言人人殊,其中的姓氏人名资料亦不好把握。往往要等到相关研究达到一定深广度,或者更多的材料出现之后,上述问题才能被发现或解决。这些都导致已有的一些意见或解说还不到位,需不断完善。
其四,某些被视为已经无须论证的常用方法,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比如在姓氏的溯源中存在的随意对应的问题。先秦时期有以先祖之谥为氏的命氏方法,因而研究中存在只要见到有人的姓氏与某位楚王的谥号相同,便将该氏归为该楚王之后的做法,如悼氏被归为楚悼王之后,穆氏被归为楚穆王之后,等等。然而这种随意的对应,是有违科学研究的严谨性的。因为如果悼氏被归为楚悼王之后、以“悼”为氏的话,那么包山楚简中的“悼滑”在传世文献中又作“邵滑”或“召滑”,为何不能是楚昭王之后、以“昭”为氏?类似的还有不加论证的通假的问题——因为某人之姓或名与传世文献中的某姓或名在音理上可以相通,便在不给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径直将二者画等号,这也是容易造成“刘邦就是吕布”的草率之举。学术研究贵在证实。不加考证地随意“认亲”,违背了历史学对求实的基本要求,需要重新检讨。
此外,研究中存在“喜新厌旧”、浅尝辄止的问题。随着近些年简牍出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往往是旧材料的内涵尚未挖掘透彻,新材料就扑面而来,甚至一年中就有几种新材料同时发表,令人眼花缭乱。追逐新材料的热情使学者的注意力很快从稍早的简牍上移开,去抢占新的高地。楚简姓氏人名研究领域也存在大量“旧”材料的遗珠剩义尚未被充分认识,就被冷落一旁的境况。研究速度赶不上出土文献涌现的速度是当前的客观事实,但是如果过度追求新材料,对“旧”材料浅尝辄止,显然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毕竟出土文献姓氏人名本身就带有孤立零散、与其他材料建立联系困难的特性,如果既有材料都没能被深入挖掘,自然也起不到为新材料的研究搭桥铺路的作用,最终整个研究都将受到影响。
三、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可看作今后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努力的方向。
第一,包山楚简、望山楚简、曾侯乙墓竹简、郭店楚墓竹简、新蔡葛陵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简册,由于数量巨大、性质内涵丰富,其所包含的姓氏人名材料亦多种多样。将丰富的楚简姓氏人名资料以科学的体例编订成姓氏人名汇编,标明其所出简册的名称、简号,并依简文内容及相关文献作简要介绍,可为考古学、古文字学、上古史研究者提供一部翔实有用的工具书。此前虽有学者做过类似工作,但或只是对某一时段(比如东周)的姓氏人名进行收录,或只是从姓氏的角度进行收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随着新简牍的不断发表,每隔一段时间便有一批新的姓氏人名补充进来,姓氏人名汇编也需要与时俱进。
第二,楚简除了有见于包山与新蔡葛陵等简牍中祭祀祷祠材料上的楚国上层贵族的姓氏人名,还有大量见于包山司法简和行政文书简以及曾侯乙墓竹简遣册随葬品清单中的下层民众的姓氏人名。利用后者,可以研究当时社会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司法行政文书记写制度等,同时,还可以与同为司法和行政文书的秦简相对读,考察两者不同的记名方式对于文书行政效率的影响。
第三,楚简中除了包含属于固有之楚国的人名,还包含大量春秋战国时代陆续为楚所灭之国如陈、蔡、黄、宋、曾、邓等中小国家的人名。中国先秦时代诸侯林立,小国占了其中的大多数,但是由于影响力弱的原因,小国往往被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鲜为人注意,尤其在它们被灭国以后,其历史似乎也戛然而止,再也无人问津。然而事实是,小国的国家政权虽然被灭,但是他们的国人仍然存在,广泛活动于战国社会。将楚简姓氏人名材料与传世的其他出土文献以及考古发掘材料相结合,可以考察这些小国从夏商历经西周春秋直到战国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足迹、亡国之后遗民的境遇又如何、征服者对其持怎样的态度等问题。这对于丰富先秦时代的历史面貌、利用多重史料探索传世文献记载较少的先秦小国有重要意义。
第四,楚简中除了文献阙载的姓氏人名,也有可与其他文献相对读的姓氏人名。将楚简姓氏人名材料与《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秦汉简牍等相结合,可以勘正一些人物事迹在文献记载上的错讹,理清错讹发生的文献学和历史学缘由,说明古书在成书及流传过程中与作为其史料的零散篇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破解某些历史记载与注疏解说上的谜团,同时为一些传世姓氏书勘误补正。
第五,楚简中既有见于《厚父》《皇门》等上古思想文化类文献上的姓氏人名,也有见于《容成氏》《系年》《郑武夫人规孺子》《越公其事》等历史类文献上的姓氏人名。透过某些著名历史人名的表面,可以阐发与之相关的某些大问题,比如从大禹看“禹画九州”传说的起源与流变问题,从武姜与郑庄公看两者母子冲突所反映的先秦母子关系及其背后更深刻的“孝道”问题等。将姓氏人名放到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和思想观念的大背景下观照和考察,可以超越浅层次就事论事的平面叙述,进入与之相关联的先秦社会制度、观念形态等纵深方面的探究,为解决先秦重要历史问题贡献思路。
此外,像前述已经提到的谥号谥法问题、研究方法的问题等,也都是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的方向。
综上,战国楚简姓氏人名问题的研究目前既有成就也有不足,总结经验成就,弥补教训不足,将研究向纵深扩展,这个题目就可以释放出新价值、新活力,开创新的研究局面。
———楚简制作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