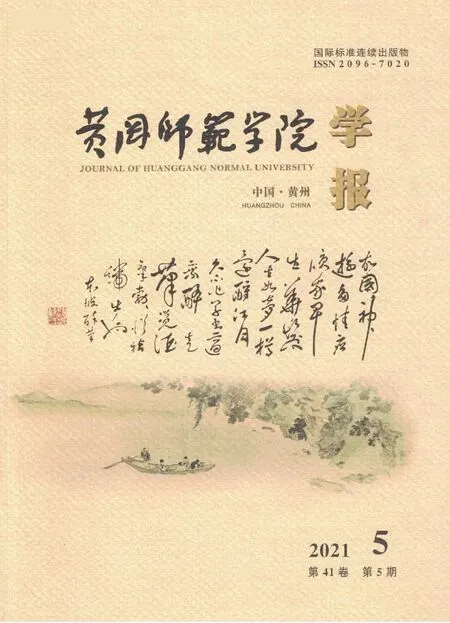康白情需要重新看待
——从《康白情研究资料》说起
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要不是康白情先生曾经在海南师专中文系担任过教职,可能就不会由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两位学者来编纂这部《康白情研究资料》①了。海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49年创立的国立海南师范学院,1952年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更名为海南师范专科学校,恢复海南师范学院建制和更名为海南师范大学都是后来的事。康白情就是在院系调整过程中由华南联合大学来海南师专任中文系教授的,具体时间是1952年8月至1953年7月。1953年秋,康白情复又回到广州,在华南师范学院任教授,直至1958年3月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退职处理,5月离校,乘船回四川途中病死于湖北巴东港,结束了他不无悲剧意味的一生。康白情在海南师专工作只有一年时间,但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十分珍视与康白情先生的这一缘分,因为在文学院院史上,像康白情这样在新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的教授绝无仅有。作为后来者,今天海南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同仁,追溯康白情这位前贤的生平、思想、文学成就和人生道路,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编辑成书,公诸同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既是义务和责任,也是对前贤最好的纪念。
一
康白情是以诗人的身份进入中国新文学史的。在中国新诗的草创期,康白情以白话诗的创作在诗坛上赢得盛名。191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现场,成为文学革命运动的参与者,1918年与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顾颉刚、孙伏园等同学一起成立了“新潮社”,此后在《新潮》上发表了大量诗作。至1922年出版诗集《草儿》,他已经是新诗运动中最有成果也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在他前边出版新诗集的只有胡适(《尝试集》)和郭沫若(《女神》),而郭沫若此前提到,他是读了康白情的诗歌才鼓起勇气创作《女神》的②。不只是创作,康白情还以诗论为新诗站稳脚跟打扫了场地,他的长篇诗论《新诗的我见》在当时对新诗的本质属性及特征、内容和形式、写法与条件论述得最为全面,在今天对认识新诗仍具有参考价值。然而,仅从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本中去认识康白情是不够的。康白情的历史意义,超出了诗歌,也超出了文学。在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黄金期,身处旋涡中心的北大学生康白情,应时而动,拥抱新潮,为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的改造而奋笔疾书,奔走呼号,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姿势矫健的弄潮儿。除了新潮社,他还与李大钊、王光祈、曾琦、邓中夏、田汉、宗白华、周佛海等一起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创办了《少年中国》刊物。1919年正是这个“中国少年学会”,组织、领导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康白情是其中的骨干分子。这期间他还任职于全国学联,南下济南、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为工作奔忙,且参加过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工作以及与黄日葵、徐彦之、孟寿椿等组织北京大学游日学生团赴日本作宣传及视察等重要活动。他的新诗,多是这些社会活动中的交游之作,因此,写新诗既是他对胡适倡导白话诗的积极响应,更是他改造中国与更新文化的情感迸发,是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会、学联活动的思想、见闻与感想的实录和信息的交流。如果说诗歌是他参与新文化创造的一种实践方式,那么,对诗歌和文学以外的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新社会的求索,才是康白情的主要兴趣所在,这从“五四”期间他为妇女解放撰文和留学美国后为制宪及国民会议组织法做总体设计就看得出来。这部资料集收录了康白情文学之外的书信和杂论写作,还原了康白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形象——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康白情留给我们的研究课题,既有文学史的,也有思想史的,后者同样需要展开。
二
从这本书里所收的研究性资料来看,到目前为止,研究康白情的成果并不多。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以来的新时期,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现代文学”成为显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其研究领域对现代文学运动、思潮、流派、现象、作家作品、史料,等等,几乎实现了全覆盖。单就作家研究而言,但凡新文学兴起后在文坛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都有多位研究者对其进行研究,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都有涉及。然而康白情似乎是个例外,这位在二三十年代就受到胡适、朱自清等人高度肯定的诗人,在新时期获得的关注度却不高。80年代最早评论康白情诗歌的论文出自台湾诗人痖弦的《芙蓉癖的怪客》。大陆1984开始出现康白情研究的论文,但为数寥寥,本书收入的仅3篇,其中发表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上的《“五四”时期诗坛上的一颗明星——康白情》,作者管林是康白情在华南师大任教时的学生,因而文章有特殊意义。痖弦的文章在历史视野里,运用现代诗艺标准对康白情的诗歌进行评价,与当年梁实秋批评康白情《早儿》所持的美学尺度相接近。1924年梁实秋评论《草儿》时断言:“《草儿》全集五十三首诗,只有一半算得是诗,其余一半直算不得是诗。”他之所以下这样的断语,是因为他判定是否为诗的标准是“以艺术的美为极则”的③。而在他之前,胡适只有肯定,说“在这几年出版的许多新诗集之中,《草儿》不能不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了。”在胡适这里,康白情的成就在于他敢于“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在当时的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因而无意间促成了诗体的解放④。对于此时的胡适来说,重要的是白话诗这一体式的确立,至于新诗应有怎样的艺术内质,他还没有考虑。新月派出现,标志着中国诗坛对新诗有了艺术自觉,新诗的美学尺度开始形成,用诗歌美的尺度衡量,康白情诗歌菁芜并存的实情难免会遭到指摘。到痖弦这个时代,中国新诗早就完成了从胡适开创白话诗,到新月派形式意识的觉醒,再到象征派、现代派追求现代性的三级跳,作为熟谙中国新诗发展史,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思想要深,情感要真,技巧要新”的好诗标准的著名诗人,痖弦回看新诗发生期的诗人康白情,少不了从艺术价值方面加以估定。他跟梁实秋的看法差不多,认为康的作品“在诗艺的表现极不平衡,良莠不齐,有超出当时同辈作家写作水准之上的,也有低于一般水准的劣作”,其根源在于“忽略了诗质的要求”。但痖弦也客观地指出,草创期新诗的简陋,是“历史发展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缺失”,值得肯定的是康白情和他的前驱者白话诗写作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早期诗人的盲目摸索,勇于接受失败的尝试,中国新诗便不会从草创到壮大。”[1]实际上,他肯定的是康白情的文学史价值,而不是文学价值。尽管痖弦同梁实秋一样,并没有全盘否定康白情诗歌的艺术成就,他们都从康白情的诗集中找出了艺术性很强的作品,大加赞誉,然而,康白情在1919年、1920年的两年间创作出一百多首新诗,多半是急就章,艺术上难免粗糙,与后来成熟期的现代诗富有匠心相比差距不小,加上康白情很快就放弃了新诗写作,因此,80年代以诗歌为先导的文学复兴,并未将康白情作为现代新诗传统加以发掘就可以理解,毕竟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冲激下,八十年代诗坛焦虑的是诗歌现代性品质的获得。
90年代,康白情研究的情况有了改观。进入9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批评意识弱化,学理性增强,史料文献的考掘成为研究的基础和方法。康白情在这一文学研究转型的背景上浮现了出来。1990年,由诸孝正、陈卓团合编的《康白情诗全编》正式出版,康白情的诗歌创作成果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书中所附的《康白情生平及著作年表简编》,是编者研究康白情的前期成果,它为了解和研究康白情提供了方便,指引了路径。此前,这两位编者还写过《康白情参加三K党说质疑》一文发表在1989年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作为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员,为前贤辩诬,说明康白情是位需要重新看待的文学前辈,研究康白情首先需要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1990年、1991年,《新文学史料》先后发表了《矛盾而复杂的五四诗人康白情》和《有关康白情的几件事》两文,1990年《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还发表了诸孝正、陈卓团的《论康白情在新诗史上的地位》,不能不说起到了带动康白情研究的作用。
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有多篇关于康白情的史料性文章和评论研究论文发表。这些论文,都能将康白情放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现场,对其新诗创作的起因、内容、意象、美学特征以及诗人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加以分析论述。不光白话新诗创作,康白情的旧体诗也成为研究对象。康白情在文学革命高潮中创作新诗,只有两年时间,而在此前后他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这与他幼年在四川乡下读私塾,接受旧教育打下的旧学功底分不开[2]。传统诗教所塑造的心灵,在应世临事时产生的情感反应,会本能地诉诸音乐性和形式感很强的格律诗,康白情的文学成就,自然包括这部分艺术成色更高的诗作。也不光是诗歌创作,康白情的诗论包括其中的一些有争议的命题(如“诗是贵族的”)也得到了分析阐释,这方面的研究使康白情诗歌思想的丰富性得到了展示。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的作家作品研究,是建立在百年文学思潮、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已足够全面深入并取得丰富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康白情这位新文学发生期名噪一时而又留下了争议的诗人进行历史考察和价值评判,不能没有新的视角和问题意识。这部资料集里所收的研究论文,有的就角度新颖,观点独到,推进了新文学的解释。例如《早期新诗中一种特殊的诗歌观——论康白情对新诗、旧诗功能的区分》一文,就发现白话诗的创立者胡适,由于是以新旧对立的模式来考量新诗是否实现了以旧汰新,因而始终存在着形式焦虑困扰,其他新诗人身上也存在新诗和旧诗的复杂纠葛,但康白情例外,“他以几乎毫无旧诗‘杂质’的面目出现在早期新诗坛”,这就表明,“康白情在新诗观念上和胡适体现了微妙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以前的研究者几乎无人发现。有了这一发现,胡适为什么赞赏康白情也就得到解释了。对于康白情异于甚至超越胡适诗歌思想之处,这篇论文也多有发现,比如,在评价康白情时,胡适“是以新诗旧诗的对比谈形式解放的成绩”的,而康白情“在如何作‘新诗’的问题上,书写精神、内容的重要性超过对语言形式问题的关注”,也就是说,在“胡适还集中在新旧对立模式的框架内谈论新诗形式”之时,“康白情已经显示出关注重心的转移”。这一发现,更能突出康白情在新诗史上的地位。此论文还发现了康白情写作的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那就是“用新旧两种诗体处理同一类题材”,说明他比胡适在文学观念上更开放,“他没有在观念上以二元对立的态度来‘打倒’旧诗,而是有意识地区分新诗和旧诗两种文类的不同功能”。[3]像这样能证明康白情研究的可开掘性的,《诗可以群——康白情与“少年中国”的离合》一文也有代表性。该文根据康白情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将他的创作定义为“作为‘社交’工具的新诗”[4],这一准确的定义,不仅决定了康白情诗歌阐释与理解的进向,也坐实了诗歌这一文类的合群功能的历史与文化规定性。这篇论文的研究视野开阔,材料掌握全面,梳理细致,分析入理,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北京大学的思想氛围,康白情的气质与个性、社交活动的轨迹与对象、社会理想与诗歌观念、诗的类别与性质、在文坛得到的评价等诸因素的逻辑关系中,推演出康白情的卓然于五四诗坛的独特价值:他以作为社交工具的诗扩展了我们对新诗的想象,修正了新诗人常见的形象。这样的研究及其结论,不仅启发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康白情的新诗创作,也让我们对诗歌乃至文学的功能有了新的认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能动性所在。
三
这部资料集,为康白情诗歌的研究确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方法的借鉴,相信会推动康白情诗歌研究的深化。然而,康白情之值得研究的,不只是他的诗歌,或许更值得研究的,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思想者的康白情在新文化运动和留学国外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以及写下的论文、杂感和书信,这些活动与文字,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史乃至教育学,都不难从中找到研究课题。曾被历史埋没的康白情,不啻现代启蒙运动主体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个案,对其进行跨学科研究,很有意义。康白情算得上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五四期间北大最活跃、发声最多最响亮的青年学生之一。1916年21岁的他从四川考入北京,第二年又考上了北大哲学系。作为大学本科生,康白情和他的同学,并没有闭门读书,而是积极投身社会变革潮流,组织社团,创办刊物,跨校进行交流,开展社会活动,关心国事,批判现实,做演讲,写文章,发表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看法,实然既为新文化运动所推动,也成为新文化创造的一分子。在新潮社和少年中国学会里,他就写过讨论社会文化问题的文章,如《“太极图”与 Phallicism 》,反对国粹派;《大学宜首开女禁论》,极力主张妇女解放运动;三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论中国之民族气质》,讨论治国安邦与国民气质的关系。在学校里,他还写过近万字的《南游漫记》,在文中表达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意见,反映了他独特的政治思想。大学生能有这样的视野、胸襟、思想和写作能力,是五四时期独有的文化现象。五四能够兴起启蒙运动,连大学生都有相应的知识、思想与能力的准备,说明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有一群特殊的人,因缘际会造就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不可再得的文化奇观。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了思想和才情,康白情因而成为北大为人瞩目的拔尖学生。1920年由企业家捐款保送北京大学毕业生赴美留学,在三届毕业生中只选了六人,康白情就在其中,当年9月六人中已毕业的五人同船赴美,被誉为“新五大臣出洋”。康白情与少年中国学会其他会员有所不同,他不因学会对纯洁性的要求而放弃政治活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他一开始选修的就是《晚近社会改造学说》,这跟他自我规划的“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为社会制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是农工或教育在方向上正相符,他的职业理想就是劳心与劳力相结合。康白情十一岁时就在四川老家参加了洪门哥老会,也许是帮会文化的影响,他对政治活动的理解就是通过社会团体来宣传他的社会理想。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期间,他先后加入了旧金山华侨的致公堂和美洲中国文化同盟,并在致公堂的基础上筹建“新中国党”,虽遭人作梗而流产,但其政治抱负可见一斑。在加大,针对少年中国学会和其他团体在如何立国的问题上分歧甚大,他为此写了《团结论》一文寄回国内发表,提出许多重要的政治观点。1924年康白情因国内资助中断而提前弃学回国,次年在民国大学任教师,同时又经章士钊介绍兼任北洋政府善后会议法制委员,还发表过《国民会议组织法刍议》,表明康白情始终关心的是政治问题。不过康白情关心政治更多的是出于知识人的探求心理,所能做的不外按照心目中的少年中国提出制度设计的想法,而并不以现实的政治权力为追求目标,他后来之不为国民党所容,跟他的这种政治自由主义姿态不无关系。
纵观康白情,他是一个新诗人,但没有完成;他有政治兴趣,而无政治功业;作为留美研究生,后来在学术上亦无建树:他的人生只有过短暂的辉煌,大半生都在黯淡中,令人扼腕叹息。然而,如果仅仅用性格悲剧或自我设计失误来解释,肯定会将这位五四冲锋者生平和思想中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无意摒弃掉。康白情留给我们的绝不只是关于个人运命的思考,若以20世纪的两次启蒙运动为坐标系,康白情的人生轨迹,暗示给我们的是一连串的世纪之谜。20世纪的第一次启蒙运动跟一代人的文化准备(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教育)和以现代大学为中心的思想平台有什么关系;知识人的政治想象对社会改造的作用何在;现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社会运动是否将一代现代型知识分子卡在历史的夹缝之中;康白情自谓“虽有成一个学问家底可能,却深不愿意成一个学问家”响应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询唤;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一多半为四川籍学人,地域文化在现代文化革命运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康白情自传材料中为何对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红楼梦》研究批判和胡适批判等运动中自己怎样过关避而不谈;大学文科师生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运行需不需要发生有机联系;当代留学生同五四一代留学生相比,在思想素质上有何差异等等这些问题,在《康白情研究资料》里不是没有留下草蛇灰线,也许这就是编者的劳作对当代学术生长的一份贡献。
注释:
①王学振,吴辰:《康白情研究资料》,海南出版社,2019年版。
②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经过》里说:“我第一次看见的白话诗是康白情的 《送许德珩赴欧洲》 (题名大意如此)(应为《送慕韩往巴黎》——引者注),是民八的九月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上看见的。那诗真真正正是白话,是分行写出的白话,其中有‘我们喊了出来,我们做得出去’那样的辞句,我看了也委实吃了一惊。那样就是白话诗吗?我在心里怀疑着,但这怀疑却唤起了我的胆量。”(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③闻一多,梁实秋:《冬夜草儿评论》,清华文学社,1922年11月。
④胡适:《康白情的<草儿>》,《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1期,1922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