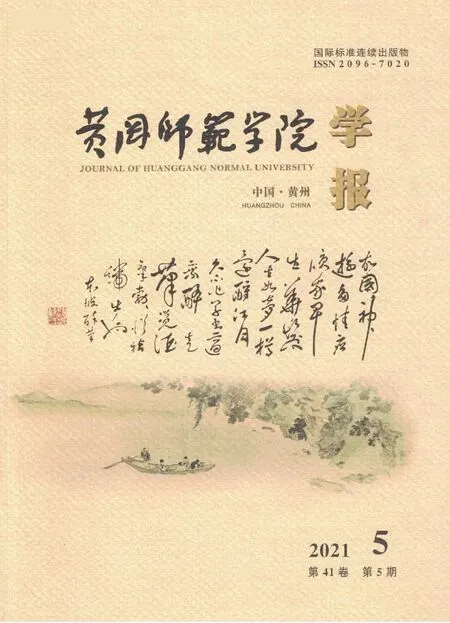文化视域下《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创作动因
白银银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00)
熙宁七年(1076),苏轼罢杭判知密。这是苏轼为避免朝廷党争波涛,“通守余杭”后“求为东州守”[1]265。苏轼知密期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和务实精神,“勤于吏职”[1]373、“不计劳逸”[1]31,在词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成果——“密州三曲”。“密州三曲”之一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被学术界认为是苏轼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一个经典文学作品的产生,是时代风潮、学术思想和个人才华等多方面因素结合的产物,“故所谓性灵抒写者,虽出于此一作家之内心经历,日常遭遇,而必有一大传统,大体系,所谓可大可久之一境,源泉混混,不择地而出。在其文学作品之文字技巧,与夫题材选择,乃及其作家个人之内心修养与夫情感锻炼,实已与文化精神之大传统,大体系,三位一体,融凝合一,而始成为其文学上之高成就。”[2]因此,笔者试从宋学经世济民思想对词创作导向的推动;“尊王攘夷”华夏中心主义情结的凸显;密州自古以来崇武尚兵地域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江城子·密州出猎》出现于苏轼知密时期的原因。
一、宋学经世致用思想对词创作导向的影响
苏轼生活时期正是宋学勃兴之时,是儒学继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又一次全面复兴。在宋代,宋学是最著名的一代之学术,词是最璀璨的一代之文学,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学术思想,便是那一时代的人,在那一社会环境中,对社会人生问题的一种新的解说。”[3]由唐入宋以后,词的创作主体逐渐转变为士大夫,词在题材、内容、风格等方面都产生巨大变化,除了词体自身演进过程以外,宋学勃兴对词创作导向的巨大影响不可忽视。
宋学以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为发端,流派众多:王安石父子的“荆公新学”;苏轼三父子的“蜀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张载、张戬兄弟的“关学”等。宋学虽流派众多,学术观点各异,但都强调文学要突破传统、经世致用,将学术探索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宋学作为一种新儒学,其探究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人在天地自然之间、社会人伦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视人‘与天地参’的自主自觉性。所谓‘内圣外王’,所谓‘圣贤气象’,就是要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和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学结合起来,把道德自律和事功建业统一起来。”[4]宋学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冲击和影响,促使宋词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突破一己小我、风花雪月、羁旅愁思藩篱,注重反映广阔、深沉的社会内容和思想。
宋学开创者之一的范仲淹,率先将宋学经世致用思想用于词的创作,扩大了词的题材,“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5]。他的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格局宏大、气势豪迈壮美,描绘边塞粗犷风光,展现守边将士艰辛,表达忧患边塞、壮志难酬的复杂情绪。夏承焘说:“北宋词坛出现这样感情深厚、气概阔大的小令,是五代以来婉约柔靡的词风转变的开端,从词史的角度看,范仲淹的《渔家傲》是苏轼、辛弃疾词派的先声。”[6]宋学另外一位开创者欧阳修,则在宋学影响下扩大了词境,塑造了“深厚宛转”的美学空间。他的《玉楼春》(尊前拟把)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表达了一种“历尽仕途沧桑以后的一种交杂着悲慨与解悟的难以具言的心境”[7]。宋学中期主要代表人物王安石,把词内容推向更为深广阔大,以词咏史怀古,从根基上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如《桂枝香·金陵怀古》(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站在历史角度抒发对王朝兴替的感慨:“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表达自己作为政治家渴望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王安石对词所作尝试对苏轼产生了重要影响:“词学上王安石与苏轼之关系,一般是将王作为苏的导夫前路者。”[8]
学界普遍认为,苏轼初试词笔始于熙宁倅杭时,从熙宁五年(1074)春作《浪淘沙·探春》,到熙宁七年(1076)秋离杭赴密所作的《减字木兰花》,共计49首。总体观之,这些词都是应歌体,“以‘谑浪游戏’的态度,应歌填词,以作一般的佐欢取乐之用。”[9]这与“吴越俗尚华靡”的杭州地域文化,擅长婉约词创作的词坛名宿张先的影响,以及苏轼初涉歌词创作难逃旧习,都有密切关系。但是可以想见的是作为一代文豪的苏轼在熟练掌握词创作技巧后,不可能满足于这样歌筵酒觞风格的作品,离开彼地、彼时的外部影响,求变是必然的事情。并且,苏轼所代表的蜀学也是宋学重要分支,蜀学内容比较庞杂,对《六经》和先秦众多著作都有研究,实现了儒释道的广泛融合,“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10]。朱熹轻视蜀学原因,就是认为蜀学缺乏一个固定思想体系。但正是蜀学不承师和博采众长付诸实践的做法,更有利于苏轼发挥主体精神,改变词的创作导向,将词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在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对词题材、格局、功能积极开拓实践的基础上,离开杭州的苏轼将宋学中经世致用思想运用到词的重构当中,对词创作进行探索、求变与创新。苏轼密州任上作词19首,其中15首为豪放词,与其在杭时期词作相比,一扫柔媚之态,可以说密州时期是苏轼词风格巨变的开始。“密州三曲”中,《江城子密州出猎》豪迈奔放,壮志凌云;《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婉约深情,被誉为千古悼亡第一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旷达超脱、充满哲理,可以作为佐证。《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作之后,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11]1560苏轼明确表示自己词创作方向要 “自是一家”,风格上与宋词原来的“柳七郎风味”相区别。苏轼已经意识到,宋词原本的“柳七郎风味”不适合,也无法承载宋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宏大主旨,因此尝试对词体和词风做出变革——“自是一家”。《江城子·密州出猎》率先体现了这种改变,苏轼把词作为自己抒怀言志的工具,“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表达的正是“苏轼借此表示希望朝廷委以边任,能奔赴边疆抗敌”的理想[12]。
总之,作为贯穿整个有宋一代的学术思潮——宋学,其经世致用观念对于宋代文风产生了巨大影响,并通过文人士大夫创作心态的改变流向作品。在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尝试基础上,苏轼最终完成了词体改造,“新天下耳目”。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江城子·密州出猎》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二、“尊夏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驱动
“华夷之辨”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是在中国古代文明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已具备雏形。《礼记·王制》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3]先秦时代的华夷之辨不仅仅是方位上的含义,文明程度不同也是区分华夷的主要标志,“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 ’。”[14]“华夏”,“华”指文化高的人,“夏”指文化高的周礼地区,“华夏”合起来就是指中国,“中国”主要含义是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核心地位,是天下之中,“被发文身衣皮”是夷,被认为不开化的象征。这种观点在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候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在唐代唐太宗提出了华夷一家、一体的理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5],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长久以来“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传统观念。
北宋是在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纷乱中建立起来的,为了避免武将专权,宋建国后实行右文政策,对北宋士风养成有巨大涵育作用。因此,北宋的知识精英起身为士大夫之时,便有着以“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自觉精神”[16]。历史上长期华夏一统的文化熏染,使宋人有着强烈恢复故国荣光的愿望,而实际国情却残酷的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不仅如此,“宋元之际,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实力大为增强。”[17]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宋人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上有着鲜明反应:北宋时期的华夷之辩有了较大改变,不再是主要强调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层面上的差别不同,宋代士大夫开始严格区分“中国”与“四夷”,大力提倡“尊王攘夷”。宋代知识分子对国家社群的维护,体现出强烈的“尊夏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对少数民族文明侵扰中原抱有强烈仇恨,“‘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18]174在宋代,“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于文明的概念,而是一个标志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概念。清华大学葛兆光就认为宋代是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他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论》中,不仅强调“中国”与“四夷”的文明差异,而且在方位上区分华夷:“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严格要求“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19]。欧阳修也在《正统论》里极力论证大宋王朝作为华夏正统的历史定位。苏辙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中说:“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显示强烈的“尊王攘夷”思想。随着宋、辽、金三者关系的不断变化发展,宋朝士大夫“尊王攘夷”思想也随之进一步发展,朱熹说:“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20],黄仲炎甚至把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比作禽兽:“夷狄蛮戎近乎禽兽,奈何使与中国齐也。”苏轼本人也有很强的“尊王攘夷”思想,在为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所作的《教战守策》中说:“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考察史料我们发现,这个时期宋与辽、西夏的关系较为平和,没有大的军事冲突,苏轼却仍然认为“其势必至于战”,这种观点一方面是提醒北宋统治者不能耽于承平无事,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其强烈的尊王攘夷情绪。
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轼知密期间正是宋辽之间重大政治事件“熙宁划界”的存续期。宋辽熙宁年间的河东边界谈判,是宋辽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从熙宁七年( 1074 年) 夏四月:辽枢密副使萧素议疆界于代州境上[21]6177,到(熙宁)十年六月:“(韩)缜以分画之劳,赐金带。十二月癸巳,上地图”结束[21]6936。 “熙宁划界”前后漫延长达四年之久,最终以宋“弃地七百余里”[22]153,一说“弃地五百余里”[22]156的屈辱结束。“熙宁划界”引发两国政治势力的博弈旷日持久,辽国使者萧禧故意滞留宋都开封,时间上超过了“使者留京不得过十日”之规定,显示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强硬态度。面对辽人军事与外交上的施压,宋神宗开天章阁,组织宰执官讨论划界事宜,在整个熙宁划界过程中一直遥控指挥。这次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的边界厘清,再度引发宋人强烈的“尊王攘夷”观念。而“熙宁划界”的胶着时期,苏轼正任职密州,密州属于京东路,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熙宁划界中双方争论的地理矛盾中心。虽然知密时期是苏轼政治上低潮时期,但比照后来的黄州、惠州、儋州时期,苏轼知密是其初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内心充满奋发有为的情感。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他密州任上的种种积极作为中可以看出,其实最早在他赴任密州途中创作的《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中就已经展露,全词英气勃勃,充满对朝廷政治的厚望[1]340。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密州期间苏轼创作了不少洋溢尊王攘夷、保家卫国情感的作品。《和梅户曹会猎铁沟》“山西从古说三明,谁信儒冠也捍城”[1]151,苏轼将自己的“近枭数盗”看作是“捍城”,保卫国家。《祭常山回小猎》中“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1]150更是强烈表现了苏轼安边守疆的豪迈情怀。
可以说,宋辽久悬不结、多种政治力量卷入的熙宁划界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士大夫“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这种情感成为他创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主要动因之一。苏轼表达了自己虽为文臣但也要披甲射虎的愿望:“亲射虎,看孙郎”,而且只要朝廷任用自己,就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就是指西北的少数民族契丹和西夏,其“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密州地区崇兵尚武的地域文化熏陶
密州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兵文化。密州地区最早是骁勇善战的东夷族群居住地,这个部族首先发明使用金属工具和兵器,有很强军事力量。被后世视作“兵主”“战神”祭祀的蚩尤,是东夷继少昊之后的族邦首领。历史上关于蚩尤的传说多和制作兵械以及战争有关,“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23];“黄帝伐蚩尤,未克。西王母遣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24]东夷人以崇兵尚武、勇猛善战而著称,三代时期夏王朝就是因为商人和夷人结盟而失国[25],也有人认为商人就是夷人的一支[26],周人和东夷人的战争更是连绵不断。春秋战国时期,密州受齐影响,齐是中国古代“三大兵学文化”发源地之一,齐的开创者姜尚、管仲、齐桓公是著名军事家,其他如孙武、吴起、孙膑、田单、蒙骜、蒙恬等人也是名声赫赫的军事家。姜尚的《六韬》一向被认为是古代兵学的开山和奠基之作,《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也是公认的兵学巨著。在密州地区的民间信仰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兵文化崇拜,除武成王庙供奉齐国开创者姜尚,还有常将军庙供奉东晋将领常玄通。
从先秦至北宋,密州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与密州地理位置相关的著名战役有长勺之战、城濮之战、鞌之战、马陵之战、乐毅破齐等。秦汉时期,楚汉之间的转折性战役——潍水之战,主要战区就在密州。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密州地区权属变动频繁,先后属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战事不断。唐安史之乱到五代时期,后梁、唐、晋、汉、周都统治过这个区域,仍然是战争高发区①。北宋王朝建立以后,密州属京东路,“至道三年,以应天、兖、徐、曹、青、郓、密、齐、济、沂、登、莱、单、濮、潍、淄、淮阳军、广济军、清平军、宜化军为京东路。”[27]2107宋王朝建都开封,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由关中转移到中原,因此京东地区成为北宋王朝北部防御前沿地带,成为拱卫政治中心开封的“东大门”。与以前封建王朝相比,宋王朝地缘政治环境十分恶劣,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比以往更为强大,“‘契丹’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21]3641由于石敬瑭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中原政权的长城防御体系被打破,北部边防门户大开,北部千里都需要防范敌军。因此,京东路的军事重要性凸显,“山东自上世以来为腹心根本之地,其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安危。”[1]269为了加强京城的藩卫,北宋把密州所在的京东地区划分为防御州,并不断提升京东路的军事地位,加强京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政和)五年有旨升登、菜、潍、密四州为次边。”[28]宋人所说的极边,是指宋统治疆域最外围的区域即边防一线;次边,是指俯逼边界[29]。长期的战争环境和北宋时期防御州的战略位置,使密州地区的兵文化一直长盛不衰。
宋王朝定都开封后,出于首都战略,宋王朝统治者在“天意”之下最终听任黄河改道北流,不再流经京东路故道:濮州-郓州-齐州-淄州-棣州-滨州[30]。黄河北流的积极后果是长久以来的京东河患得以基本解除,消极后果是大量河北流民涌入京东地区,“河北水灾,其流民尽来京东界内。”[31]大规模流民涌入使京东地区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京东地区在北宋中后期成为著名“盗区”,有史料可查的北宋时期京东地区农民起义就达43次之多,“齐鲁盗贼,为天下剧。”[27]1058苏轼本人也强调说,“自来河北、京东,常苦盗贼,而京东尤甚。”[11]1058出于防御“盗贼”目的,密州地区民俗中豪爽劲悍的风气一直延续、保留和发展下来,“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剿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11]
密州地域文化对苏轼影响很大,梳理苏轼知密期间作品,我们发现相当数量与狩猎有关作品,与苏轼其他宦游地的作品相区别。苏轼借狩猎活动反映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感情,诗歌如《和梅户曹会猎铁沟》与《祭常山回小猎》等,词首推《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明确展现了密州地区“武悍”的民风:“倾城随太守”“千骑卷平冈”,在这样的阳刚气概鼓舞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渴望投身疆场、效力边防,“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1]34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出现与密州地区崇兵尚武的地域文化熏陶和渲染密不可分。
“作家和作品都是文化的载体,研究文学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研究文化。”[32]宋王朝特殊的立国环境,促使儒学复兴并成长为蓬勃的宋学,复归醇儒的学术环境进一步深化了宋代士大夫“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叠加密州阳刚雄壮的地域文化,三者共同作用促使天才苏轼写出《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样不朽的作品。
注释:
①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王蕊.魏晋十六国青徐兖地域政局研究[M].北京:齐鲁书社,2008;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