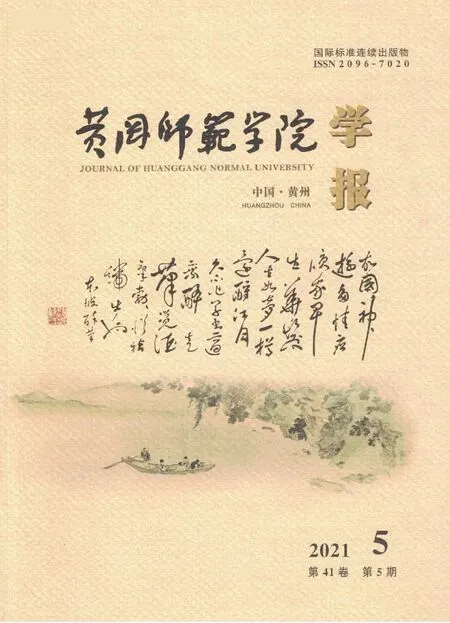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文学地理学思想研究
殷虹刚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江苏 苏州 215104)
王葆心,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公元1869年1月),卒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公元1944年3月),字季芗,号晦堂,又号青垞,湖北省罗田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第三名乡试中举,光绪三十三年(1907)举贡考试名列第一,对经学、史学、方志学、文学、哲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均有深入研究,《古文辞通义》为其文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古文辞通义》原名《高等文学讲义》,四册六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出版,而《高等文学讲义》以其1900年前所作《汉黄德道师范学堂文学讲义》为基础订补而成。民国五年(1916)八月,著者对《高等文学讲义》进行大幅度的重订补充后,原书扩充至十册二十卷,并更名为《古文辞通义》再版发行。《高等文学讲义》出版后,广受欢迎,次年三月经“学部审定,作为中学堂以上参考书,刊之学部官报及《审定书目》”,被广西、河南两省各学堂采用,“分科大学文科诸君多展转购求以去……其辽东、沪上学校闻之,函索者不可枚数”。马其昶、姚永朴、林纾、陈衍等学者都对这部讲义赞誉有加,林纾称为“百年无此作”。经修订更名《古文辞通义》再版后,更是受到学界的美誉,王先谦称之为“今日确不可少之书”,众多同仁“为诗纪之”[1]识语1-2。由此可知,《古文辞通义》是当时一部水平高、成就大、影响广的学术著作。遗憾的是,《古文辞通义》自1916年出版后,在大陆一直未重版发行。1964年,经王门弟子徐复观、成惕轩努力,该书得以在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但由于两岸隔绝,该书在大陆仍一直湮没无闻。直至2007年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收录该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经熊礼汇先生推荐并标点,武汉大学出版社将该书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出版。
2007年后,王葆心的学术思想才逐渐引起当代学界的注意,但发表的相关论文仅十余篇。2009年,复旦大学吴伯雄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文辞通义>研究》考证了王葆心生平和《古文辞通义》的版本情况,整体梳理了该书主要内容,对其文学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文末附有《王葆心年表》和《王葆心主要著作目录》,为后来者提供了方便。以后的论文,或聚焦于对王葆心所著地方文献的研究,或聚焦于对其文章学的研究,或聚焦于对其生平、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总体情况的研究,偶有涉及王葆心的文学地域性观念,但都未从文学地理学视域对其思想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对王葆心《古文辞通义》中的文学地理学思想展开论述,并阐释其在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的地位,以期能补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之阙如,使学界对王葆心的学术成就有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
一、《古文辞通义》文学地理学思想分析
《古文辞通义》共六篇二十卷,其中十三至十六卷为《总术篇》,该篇所论第四方面内容为“从时世、地域、人性角度论文”[2]。从地域角度论文的部分在卷十四和卷十五中,标题为:“文之总以地域者”,主要“区南北以论文”[1]568。著者先作一篇长序,然后分周季(春秋、战国、秦)、两汉、六朝南北、唐、宋、元、明、清等八个历史时期讨论“文家流衍之地域”问题,即历代文学的南北地域问题。
文学的地域问题是文学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曾大兴先生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将“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征与地域差异”[3]12列为文学地理学的三个研究对象之一,并在书中设专节讨论“中国文学的南北之别与东西之别”。王葆心“文之总以地域者”部分的研究实际已创现代文学地理学之滥觞,不少观点不仅在当时新颖深刻,至今看来仍具启发意义。本文将以该部分为重点,剖析其所蕴含的文学地理学思想。
(一)首倡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 “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不同学科的跨学科研究”[4],这是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范式。今天学界一般将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南北文学不同论》视为现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轫之作①,但细读刘氏该文,仍然囿于《隋书·文学传序》等历史文献论述南北文学的传统,并未表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现代意识。而在《古文辞通义》中,王葆心已明确提出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思想。《古文辞通义例目》明言:
盖自近世分业之说兴,其用不第施于职业家,亦且用之学术家,由是而学校中之专科、选科与分科之法以立。抑自普通学有序有机之说兴,每一秩然有序之学科中,又必赖他科学相因而成体……是编之范围,于《总术篇》中,胪文与历史、地理、政治之相关者,又详文与经、史、子之相关者。[1]例目13
清末西学东渐,高等学堂开设不同学科,文学只是其中一种,著者已认识到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依存的关系,并产生了跨学科研究的思想,于是有意识地在《总术篇》中探讨历史、地理、政治等对文学的影响,故“文之总以地域者”部分属于文学和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
《古文辞通义》出版于1916年,但其前身《高等文学讲义》出版于1906年,仅比《南北文学不同论》的发表晚一年。根据比较,“《高等文学讲义》基本上与现行的《古文辞通义》篇名相同,两者同出一辙”,《古文辞通义》之所以篇幅远超《高等文学讲义》,是因为著者出于通义体制的需要而广加荟萃,“说明性材料增多”,“同意之文增多”,但两者“在内容结构上大体相差无几”[5]30-33。也就是说,《高等文学讲义》虽然篇幅不如《古文辞通义》宏大,但已包含主要学术观点,两者无本质区别。考虑到《高等文学讲义》是王葆心以1900年前所作《汉黄德道师范学堂文学讲义》为基础订补而成,可以推测,王葆心形成文学与地理的跨学科研究思想并进行实践的时间应该早于1900年。从现有资料来看,王葆心应是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明确提出学跨学科研究的第一人。
(二)系统考察文学与地理的关系 近年来文学地理学发展迅猛,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部分既有成果甚至存在着地理加文学的简单化倾向”[6]。 这种“地理加文学”的研究,往往通过机械比照,罗列相关的文献材料做表面描述,分析问题机械生硬,不能深入到地理影响文学的内在机制,其实质是仍将文学和地理看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因此,在文学地理学研究过程中,将文学和地理相融合的系统性思维很重要,而王葆心在《古文辞通义》中对这一点已有相当的自觉。
1.在文化地理学的广阔视域下考察地理对文学的影响。著者在“文之总以地域者”部分的长序中指出:“岂惟文事,盖凡吾华文明盛大之业,莫不如此”[1]568,认为华夏文明都有南北地域的区分,接着胪举了绘画、学术、书法、戏曲、宗教、堪舆、武术等大量文化艺术的南北之分。可见著者具有宏观的观察视野和系统的思维方式,除文学外,同时看到了地理对其他文化艺术的广泛影响,是在文化地理学的广阔视域下考察地理对文学的影响。而文化地理学恰是现代中国文学地理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学术资源,陶礼天先生即指出:“最近20多年之所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为显学,也是与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和近年来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移译、输入分不开的”[7]。
2. 在时、地、人的三维坐标系中考察文学的发展。《总术篇》小序中,著者提出:
夫文者,时与地与人,三者相积而成者也。时以区之,地以别之,人以差之,而文乃千其流、万其术,而卒不可以齐。然苟能总以时、括以地、契以人,而不齐者齐矣。[1]502
著者认为文由时、地、人“三者相积而成”,由此构建了一个考察文学发展的三维立体坐标系,地理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一方面,从外在的具体表现来看,地理的不同使文学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地域差异,“地以别之”;另一方面,从内在的抽象本质来看,地理对文学的影响有规律可循,可以通过“括以地”而实现“不齐者齐”。这种理解是将文学与地理的完全融合,体现出辩证统一的思维特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著者将地理维度置于文学现象之内,也就是表明其研究过程中,文学是根本目的,地理只是一种切入角度或分析方法。这点符合当代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李仲凡先生就曾强调文学地理学应以文学为本位,“文学地理学中的文学与地理学,二者并非平分秋色,而是有一个主次或主宾的关系”[8]。
(三)对地理影响文学的途径的认识 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它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9],在《古文辞通义》中,王葆心的表述已经内含了地理影响文学的途径。对这些表述进行梳理和分析,对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仍具有借鉴意义。
“文之总以地域者”部分的序中,著者先引用龚自珍《定庵续集·己亥杂诗》中的观察:“渡黄河而南,天异色,地异气,民异情”,随即云:“此盖本乎自然,不可勉强者也”,指出龚氏所言黄河南北在天色、地气、民情方面的差异是因为受到地理(“自然”)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人为改变。然后著者引用俞樾《九九消夏录》中的观点:“凡事皆言南北,不言东西,何也?盖自郑君说《禹贡》‘导山’有阳列、阴列之名,而后世遂分为南北二条。南条之水,江为大;北条之水,河为大。……南北之分,实江、河大势使然,风尚因之而异也”,继而指出俞氏这是“以地势言之”。这表明著者已经认识到,大山巨川的地形地貌(“地势”)是造成南北“风尚”不同的一个原因。接着著者说:“若以天时言,则大江以北,麦花昼开;大江以南,麦花夜开。江以南,谷熟为有秋;江以北,豆、麦熟为有秋”,“天时”指气候条件,因南北气候不同,导致不同的农作物生长表现和成熟时期。最后,著者推导到文学,得出结论:
凡此,皆因乎夙成而不能更定者也。惟其如此,故列朝之文,略有南北之异状,亦乘乎时风、地气而偶然,非人之所故为,亦非人之所矫强能使不为也。[1]568
也就是说,著者已经认识到,地理(“自然”)中的气候(“时风”)和地形地貌(“地气”)这两个方面是影响文学发展、造成文学南北差异的重要原因。
那具体而言,气候和地形地貌又怎样影响到文学呢?对此著者也有所认识,其在“周季文家流衍之地域”中指出:
周季官师政教,升降之局既分,而文家肇启南北两派。大河流域,土风膇重;大江流域,土风轻英。轻英炳江汉之灵,其人深思而美洁,故南派善言情。膇重含河、海之质,其人负才而敦厚,故北派善说理与记事。[1]572
著者认为,南北不同的气候和地形地貌(“大河流域”、“大江流域”)影响当地的风俗习尚(“土风”),然后风俗习尚影响到人的性格气质,人的不同最终造成了南北文学之异。在此,著者其实已经揭示出一条地理影响文学的完整途径,即:地理→风俗→人→文。
关于地理对风俗和人的影响,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述,《礼记·王制》即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0]关于地理对文学的影响,古代典籍中也不乏记述,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即言:“夫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盖文之所起,情发于中。”[11]故著者所述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总结提升,在“文之总以地域者”部分来展开论述,可见其对地理影响文学的途径已有清楚的认识。
(四)肇启对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的研究 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是当代文学地理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著者在“文之总以地域者”部分,从八个历史时期分论“南北文家之流衍”,其实已肇启对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的研究。而且,著者多有创见,已与当代文学地理学思想相合。
1.注意到文学活动中心的存在和变迁问题。在论述“周季文家流衍之地域”时,著者指出:“春秋之时,大都以齐、鲁为中心……当时文学悉趋于齐、鲁矣。此春秋时北派最雄之都域也……战国时北派之最著者,又在此地矣……秦时北派,又以长安为雄剧。”此处所说的“中心”即当代学者所言“文学活动中心”[12]修订版前言19,文学家聚集密度高,对周边地区具有辐射功能,但对文学家没有发号施令和组织管理的功能。
2.意识到长江黄河对文学家地理分布的影响。著者不仅认识到长江黄河对文分南北的影响,而且意识到长江黄河对文学家地理分布的影响。其指出:
文家地域,举北可以概西,举南可以概东。北方地域,为黄河巨川所经,起关陇而迄齐、鲁者也;南方地域,为扬子江巨川所经,起蜀滇而迄吴越者也。[1]609
接下来著者引用明代陈霆《两山墨谈》所言:“长淮为南北大限,自淮以北为北条,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为南条,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可见著者已认识到地理上以淮河为界,分为“北方地域”和“南方地域”,而北方实为黄河流域(“大河流域”),南方实为长江流域(“大江流域”),黄河和长江对南北方各自的文学家分布(“文家地域”)和文学作品有很大影响。
当代学界对著者此观点已有更加详尽深入的研究。例如曾大兴先生在研究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后,总结出“文学家分布的‘瓜藤结构’”,所谓“藤”,“就是中国境内的黄河、长江、珠江这三条大河以及它们的众多支流”[12]547;再如梅新林先生在《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中设有“流域轴线与文学地理”专章,其中就包括对“黄河流域文学轴线”和“长江流域文学轴线”的研究[13];又如杜红亮先生《江河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流向》第五章“中国文学流向的规律”就主要分析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历代文学家分布的规律及原因[14]。
3.揭明全国文学重心由北向南变迁的历史规律。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是动态的,会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带来全国文学重心的历史变迁。对此著者在分论历代“文家流衍之地域”时有多处揭明,例如在论及“唐代文家流衍之地域”时说:
要其归,则自汉以后,文家在北方者,至唐代又再盛于北方,然则由汉逮唐,均为文家南风不竞之时期也乎?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曰:“……南渡后,专尚时文,称闽、越、东瓯之士。山川之气随时而为衰、盛,谈风水者乌能知此?唐诗人,江南为多,今列于后。”云云。此亦始盛于北、终盛于南之说也。李西涯论诗,亦称诗家始盛于北,而终盛于南……南北诗、文盛、衰之转关,从唐代区其大势,证以盛氏、李氏之言而益信。[1]579-580
著者不仅认识到全国文学重心由北向南的历史变迁,而且注意到在历代发展过程中,唐代是转变的关键,可谓洞见。
全国文学重心由北向南变迁的历史规律,在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等论著中,已通过对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的数据统计而证实,有更加具体翔实的论述。著者在百余年前能有此分析和判断,足见其渊博的学识和宏观的视野。
4.指出文学家个体流动对南北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在对全国文学重心的历史变迁作宏观分析时,著者还屡屡指出微观层面上文学家个体流动给南北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例如在论及文学发展的源头“周季文家流衍之地域”时说:
然北派记事之传,实自南派流入。其先开于左史倚相,惜无传书。及邱明载而之北,北派遂以叙事雄于后世。铎椒仍载而之南,南派叙事,亦未尝绝于后世也。……叙事一派由南而输入北,而说理一派亦似由鬻子著书先之。鬻子入西周,转而递衍于北、东,在老子之前。老子亦南派也。是说理派亦可云南方输入之产矣。[1]572
在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分为“静态分布”和“动态分布”两种,“文学家的籍贯(出生地)分布,属于‘静态分布’;文学家的迁徙、流动地的分布,则属于‘动态分布’”[3]57。 著者注意到了这两种情况,而且特别留意到文学家流动——即动态分布对南北文学发展带来的改变,足见其目光敏锐,独具只眼。
(五)对南北文学之间竞胜与参合规律的揭示 在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有人过分夸大地理对文学的影响,因而导致“或轻或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15]。在论述“文之总以地域者”时,著者虽标示地理对文学的影响,但并未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误区,而是看到在时、空的限制中,“人以差之”的个体差异性和主观能动性。一方面,如前所述,著者在微观层面上注意到了文学家个体流动对南北文学发展带来的改变;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著者也注意到了南北文学之间竞胜与参合的相互影响关系。著者在论及“两汉文家流衍之地域”时即指明:“由区分而略加参合,以后依乎此种轨辙者,实不绝于世也”[1]574。在对历代文家流衍之地域的具体阐述中,著者又反复阐明这一观点,例如在论及“国朝文家流衍之地域”时说:
吾观北人之文主理,南人之文主情,此其大都也。然南人主情之文,迄唐初而止;北人主理之文,至唐后而大炽于南方。叙事之文,在唐以前,亦北方为之宗主,南方为之附庸,唐以后南北皆互有名家。故三者之于南北,常有直接与循环两种之观焉。汉代南北,各操其土风,而彼此平均,无盈绌。自后,或由南弊而北弊、而北振、而北大之者,六朝至唐是也。……或南弊而北振、而南大之者,五代至宋是也。……元、明两朝,北人多主秦、汉,南人多主唐、宋,两者常相龁,为南北之竞胜……于是南派辄胜,北派常衰。入本朝,南派全归优胜,而北派泯焉无闻。[1]610
由此可知,著者已充分认识到南北文派相竞相合的历史发展规律。杨义先生将此列为文化地理学的十大命题之一,名曰“南北朝效应”:“胡风南煽,久居而中原化;衣冠南渡,开发南国而沾染蛮风,然后归于一统而实现更为博大的南北融合。”[16]
二、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的地位
经过以上对《古文辞通义》“文之总以地域者”部分的考察后,我们不难发现著者在阐释文学地理学思想时表现出鲜明的科学性特征。著者按照八个时期,以历史的眼光考察文之南北地域区别问题,分期细致,论述全面。另外,不同历史时期的论述详略不同,其中以清最为详细,明次之,六朝南北、宋再次之。究其原因,可能一是由于著者是清末学者,对清代文分南北的现象有切身的观察和体会,故所论最详;二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变化,明、清时期文分南北现象愈加明显,著者在序中就说:“通观辙迹,其事至近数百年而两派愈显真形”[1]571, 故明、清两代需要详述;三是因为宋与六朝一样,国土曾南北分裂,且都有北人南渡,文分南北的现象比较复杂,故也需要较为详细的论述。由此可知,著者在分述前应有系统深入的思考。另外,从上文分析可知,著者并未将文分南北现象简单化,而是辩证地看到了其背后的细节性复杂。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充分体现了著者论述的科学性。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在诸多方面已是现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端,分析其文学地理学思想的形成渊源,精深广博的国学修养是基础。“文之总以地域者”部分征引各类文献多达一百四十余种,囊括史籍、笔记、诗话、文话、诗文集、地方志和文征等各种类型的古籍资料,时人“叹为博达,惊为传人”[1]识语2。王葆心不仅能广征博引,而且其治学方法“始于条理,终于贯通;始于剖析门户,终于不分门户”[17],因此其能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总结提炼,形成“文之总以地域者”的系统思想。《古文辞通义·例目》云:“是编多所引据……然每立一义,或先本己意以贯串旧说,或先依据旧说而剖析折衷以己意”[1]例目14,在“文之总以地域者”部分,这“己意”就是著者的文学地理学思想。成惕轩也评价道:“细如竹屑而弗遗,巧借金针而度与。悬古为鉴,馈贫以粮。诚粲乎其大备矣!……穷百家之阃奥,假多士以津梁。语贵能周,义期必现。”[18]
此外,方志学实践和西学东渐的时代风潮也是王葆心形成文学地理学思想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王葆心学术生涯中一贯重视对地方史志、文征和诗征的研究,晚年更是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地方志的书写和乡邦文献的整理之中,其《方志学发微》“更是近现代方志学的开山之作,乃‘集方志学之大成’(张春霆语),是‘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先驱’(闻惕生语)”[19]。这种方志学实践无疑能深化他对文学地域性的理解。另一方面,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王葆心积极“探索新式学堂教育与传统学术传承之间的契合点”,曾于1904年“创办罗田第一丙等私立小学堂,以此为契机精研域外教授法译著达数百种之多,并留心新式教科书的写作方法”[20]。这种对西方教育的关注和研究,帮助他形成了中西会通的学术视野。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他在西方学科分类观念的指导下认识到文学与地理、历史、政治等学科的异同,进而产生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最终形成较为系统的文学地理学思想。
今天回顾文学地理学学术史,都会论及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因为这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的第一篇系统的论文”[21]附录393。现在看来,《古文辞通义》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的地位可能与刘氏该文同样重要,甚至过之。
首先,刘氏《南北文学不同论》为其《南北学派不同论》的五篇系列论文之一,其余四篇论文分别考察诸子学、经学、理学和考证学的南北差异,可见其主要是从学术的视角讨论南北文学的差异性,对此刘氏在“总论”中也有表述。相比之下,王葆心在文化地理学的视域下考察地理对文学的影响,视野更加广阔,进而提出南北文化之别“本乎自然,不可勉强”、南北文学之别“非人之所故为,亦非人之所矫强能使不为”的观点,对地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更加深刻的体认,因此更契合当代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思想。
其次,刘氏《南北文学不同论》继承《隋书·文学传序》中对南北文学风格 “文质”区分的观点,叙述语言表现出与传统文献的亲缘关系,乃至在具体论述中隐含褒质贬文、扬北抑南的基于儒家立场的价值取向。例如其在讨论魏晋南北朝“北方之士侈效南文”的“文体变迁”时说:“惟刘琨之作,善为凄戾之音而出以清刚,孙楚、卢询之作亦然。郭璞之作,佐以彪炳之词而出以挺拔,北方之文赖以不堕”[22],将这一时期文学风格“由北趋南”现象视为走向堕落的过程。对此学者吴键指出:“这里对‘南/北’‘文/质’的轩轾抑扬也正构成了《南北文学不同论》的‘现代特质’的暧昧所在”[23]。学者靳大成也曾指出,刘氏《南北文学不同论》“其论述一般并不出传统范围,虽然……曾经或多或少受过西方现代学术的洗礼”[24]。而王葆心在《古文辞通义》中明确提出“文之公理,不以方域、乡曲限也”的观点,对南北文学之区分能超越传统价值取向,一视同仁,不分高下,相比之下更符合当代文学地理学的理念。
再次,刘氏《南北文学不同论》聚焦于不同地理环境影响下南北两地文学的不同艺术特色和风格面貌,而对于南北文学深层的互动交流讨论不多,对此钟仕伦先生指出:“这部著作……见异不见同,忽略南北文化的交流”[25]。而《古文辞通义》则能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都注意到南北文学“由区分而略加参合”的演变规律,并将此思想贯穿于对历代文家流衍之地域的具体阐述中,相比之下王氏的论述无疑更加符合南北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最后,如前所述,《南北文学不同论》仍未脱《隋书·文学传序》等传统文献对南北文学论述的框架,刘氏当时似乎尚未形成跨学科研究的自觉意识,未明确提出历史与地理共同影响文学的理论框架。有研究者即指出:“在论述‘南北文学不同’时……想要论述涵盖所有中国文学家的刘师培不免有些流于分析而缺少成熟的理论构建”[26]。而相比之下,王葆心的《古文辞通义》不仅资料宏富,而且表现出一以贯之的理论构建意识,这从其著作命名、凡例和《总术篇》长序中均可看出。《古文辞通义》明言:“是编之范围,于《总术篇》中,胪文与历史、地理、政治之相关者,又详文与经、史、子之相关者”,已明确将传统四部分类与西方近代分科相融合,表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思想和方法特征,其所提出的“夫文者,时与地与人,三者相积而成者”的理论,也与十九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1828-1893)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的著名的“种族、时代、环境”[27]三要素理论颇有契合之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文辞通义》对文分南北的论述要比《南北文学不同论》更加科学和深刻。《古文辞通义》是一部“框架完整、结构谨严、博采众长、中西互通的集大成式的近代文章学著作”[20]。著者撰写该书时,“每篇自为小结构,统众篇又成一大结构”[1]例目16, 所以若将其中“文之总以地域者”部分析出单独成册,完全可以视为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的第一部专著。等到民国十八年(1929)段凌辰出版《中国文学概论》,受王葆心影响,在书中除“文学与时代”外又设置“文学与地域”专章,并言:“文学作品,就时间而言,则一代有一代之特点……若就空间而言,则一地有一地之特性……文学之因地而异,乃事理之所必然者矣”[28],已表现出明显的通过时空并置的方式来研究文学的思想。后来袁行霈先生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中设置“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专章,可以说是对半个多世纪前王葆心和段凌辰所论的承继与发展。
通过以上与《南北文学不同论》的简要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说,《古文辞通义》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学术价值等同于、甚至超过《南北文学不同论》。此外,梅新林先生在《文学地理学原理》中将20世纪初视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现代转型期[29],而上述分析足以表明,王葆心《古文辞通义》的文学地理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现代特质,因此,《古文辞通义》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现代转型发展过程中更占有奠基和发轫的地位。
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学术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很重要,因为这是“本学科的文献根基与思想根基”[21]12。遗憾的是,因《古文辞通义》长期湮没无闻,曾大兴先生《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略》、梅新林先生《文学地理学原理》第一章“文学地理学的成长历程”、李伟煌和曾大兴辑录整理的《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均未列入该书,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的一个重要遗漏。蒋寅先生在讨论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时提及该书:“六朝时代,人们已注意到地域与学风的关系……都指出南北方学风、民俗乃至语音的差异,后引发王鸣盛《蛾术编》卷二‘南北学尚不同’、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十四、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的全面研究”[30],惜乎未展开论述。
长久以来《古文辞通义》之所以被忽视,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四”狂飙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致命打击,王水照先生曾指出:“第三个‘遮蔽’,就是按‘五四’新观念建构的文学批评史或学术史遮蔽了许多‘旧派’的文章学批评专家和专书,这在清末民初尤为严重。”[31]今天,我们不仅应将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列入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确立其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现代转型发展过程中奠基和发轫的地位,更应整理其所征引的繁富的文献资料,分析其方志学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梳理其文学地理学思想的承继、传播和影响。
注释:
①曾大兴先生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片断言说阶段(前544—1905)”、“系统研究阶段(1905—2011)”和“学科建设阶段(2011—今)”,其中系统研究阶段的划分依据即1905年刘师培发表《南北文学不同论》。详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附录《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略》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