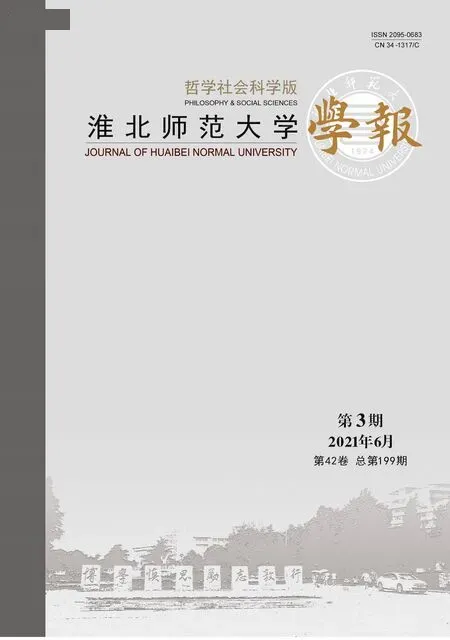科马克·麦卡锡小说《长路》中救赎的重构
周艳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33—)是美国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被称为福克纳的后继者。《长路》(The Road)2006年问世,是其第十部作品,获得普利策奖,并拍成电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小说描写灾难后的世界: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存活下来的父子俩踏上一条吉凶未卜的艰难长路,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与死、善与恶的抉择。根据后启示录小说的叙事模式:“末日—劫难—拯救—新生”[1],这部小说自然而然被中外评论家们归为此类,但值得关注的是叙事链在最后一环“新生”上断裂了:父亲死了,孩子遇到了不明身份的一家人,作者用“是地图,也是迷津,导向无可回返的事物,无能校正的纷乱”[2]285这样暧昧不清的表达将读者继续留在文字构成的茫茫废墟中。后启示录小说关注灾难幸存者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变化,但叙事的终点大多归于“如何挽救分崩离析的文明、采用何种新的末日伦理与法则等”[1]。科幻小说批评家Gary K.Wolf对后启示录小说叙事结构进行总结时,也将最后一步归纳为进行一场决定何种价值观在新世界保留的殊死决战[3]。国内研究普遍认为,小说通过孩子身上的善以及父亲所坚持的道德伦理底线,实现人类的自我救赎[4-5]。国外学界在该小说的救赎路径上产生了分歧,一部分评论者认为作者采用开放式结局,是要将末日坠入完全的虚无状态,“强调灾难是毁灭性的”[1],无可拯救。而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作者在恢复末日秩序的问题上产生了软弱的情绪,在未知中寄托了希望,“破坏了其对‘虚无主义’一贯的坚持”[6]。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分别偏向文本和作者,而本文将两者同时纳入评论体系,发现麦卡锡在这部小说中打破了传统叙事结构,开创了新型的救赎模式。
一、救赎的困境:上帝缺席的“末日危途”
(一)基督教语境中上帝的缺席
作者未能在小说结尾提供一幅“重生”的场景,而是选择让读者与活下来的“孩子”一起宿命般地继续在混沌的时间里跋涉。但是读者会持续期待“救世主”的到来,结束这场无休止的炼狱,让良善的生灵得到拯救。这种期待不是凭空形成的,部分是出于传统叙事阅读的惯性,但更大程度上与作者创造的宗教语境有关。首先,麦卡锡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基督教词汇,仅“神”(God)一词就提到了三十多次。其次,作者描写了有意契合《圣经》启示录的情节。小说没有交代灾难发生时的情景,尽管大多评论者认为是核辐射,但“小说中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核战争的词汇”[7],“小说中的描写与《圣经》启示录里约翰描述的很多主题都有呼应的地方”[7]。细心的学者还发现父亲回忆灾难发生的时间是“凌晨一点十七分”,“一道光焰画破天际,其后是一串轻微的震荡”[2]57,“影射了《启示录》里的一章17节,上帝向约翰显现的情景”[7]。
在神学主题世俗化的创作大环境下,末日景象书写已不再是对《圣经》末世论的注解和演绎。当代美国的后启示录小说已经弱化了宗教背景,聚焦灾难和重建,在极端环境中激发读者对当下给人类带来生存焦虑的自然和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然而这部小说中麦卡锡仍然选择使用宗教性的叙事语言,让读者误以为他会像福克纳或者弗兰纳里等南方小说家一样,“借助基督教原型表现自己对美国南方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8]。被代入基督教语境中却未能盼到救世主出场的一些读者和评论家,并不认为作者颠覆了传统的救赎概念,他们寻着蛛丝马迹对一些意象进行了符号学的解读。例如:结尾峡谷里的鳟鱼被认为是“拯救者的形象”,因为在美国文学史上,从梭罗到海明威,鱼的行为通常隐含救赎和精神恢复[9]。男孩被解读为“圣杯”,是“上帝传下的旨意”,“接过的火种是上帝的呼吸”,“暗喻人类生生不息”[10]。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读者并不会在这种充满玄幻感的符号解读里得到救赎的安慰,缓解悬置的结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二)缺席的上帝带来的问题
“在这部小说中,上帝是公然缺失的。”[11]而在灾难话语体系中、顿失所依的末日里,缺席的上帝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小说中除了父子之间的对话外,出场时间最久、对白时间最长的是一位神秘的老者,他自称“早知会有这天”[2]168,并对父子俩说:“世上没有上帝,你我都是先知”[2]170。先知是宗教体系里的词汇,是指可以通过领会神的旨意而对未来有预测能力的智者。老人这句话存在的逻辑悖论,是“典型的麦卡锡风格:提及上帝,以及上帝为幸存者解决困境的可能性,并非通过角色全然否定或者肯定上帝的存在,而是将其问题化”[6]。
麦卡锡风格的形成与其出生成长在田纳西州天主教家庭的环境不无关系。早期的作品例如《看果园的人》,以田纳西州作为故事背景,动用基督教的主题,救赎的意象和语言占据核心地位,被归为“南部作家”。而当他小说的创作背景转向西南部,在“边境三部曲”中描绘了尼采式的人物和景物,用暴力抹去了一切救赎的痕迹时,又被归为“西部作家”[12]。《长路》虽然在末日的灰烬中很难辨认出地理界线,但大致仍然可以识别出他又回到了熟悉的南部,进入了他曾经的宗教话语体系,以至于有些评论者在解读作品时认为作者带着深深的宗教情怀,将父子的长路旅程看作“信徒们弃恶向善追求心灵圣洁的‘心路历程’,这种虔信程度随着情节发展而加深”,“引领人们奔向光明”[13]。
当我们不考虑作者的信仰背景变化,就很容易将小说中的救赎问题简单化。“麦卡锡认为‘上帝的死亡’是个悖论:对一些人来说,是希望的陨落,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又是对生命荒唐的确认,诅咒他们生活在末日的悬念中,无望地等待。”[6]他在小说中对“救世主”模棱两可的态度,怀疑与相信并存,是受大陆哲学中对上帝概念不断演化的影响所造成的,一方面,他相信尼采说的“上帝已死”,但是同时,又觉得救世主仍然存在。他的信仰困境在文中体现为:父亲不停暗暗诅咒上帝,又同时给孩子编造“上帝使者”这样的谎言。
福克纳的“圣杯”放置在被尼采解构的虚无世界里,闪着悠悠的微光,不辨方向,这是麦卡锡的精神困境,也构成了父子二人在“长路”上的救赎困境。问题化的上帝不再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让人类对存在产生困惑。一边否定、一边寻找,也是当下西方人的信仰状态。上帝此时的意义,只存在于寻找的过程中,而非寻找的结果中。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和评论者对“救世主”的寻找也成全了文本的意义。
二、救赎的新路径:上帝缺席下的“弥赛亚精神”
(一)对“裂缝”状态的正义化
对上帝的“质问”并非Isak W.Holm所说,始于十八世纪,尽管“1755年,Gottfried Leibniz将希腊语中theos(God)和dike(justice)组合,创造出了一个新词theodicy(神正论):如果上帝是全能和善的,为何世界充满邪恶以及像地震如此无意义的事件呢?”[11]早在圣经的约伯记中,被剥夺财产、家人、健康的约伯在他的信仰认知环境里,不停地申诉和问求,质疑神的公义:“善恶无分,都是一样;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尽。”[14]483虽然《圣经》中描述他最后仍然信靠指望上帝,生活得以恢复,但也显示了人在面对无法承受的厄运时,委屈和抱怨是自然的情绪,而希望恢复到灾难前的秩序状态,是无可指谪的逻辑。小说描述的父子俩在灰烬中前行,父亲却在面对着这晦暗可怕的世界,说出了让人费解的一句话:“若他是造物主,也会如此安置这世界,不作任何改变”[2]219。
这句话使得“救赎”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精神上都变得不可实现。一个备受灾难折磨的人为什么对恢复世界秩序连假设的憧憬都规避不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父亲的这句话,就无法探究麦卡锡在这部小说中的救赎理念,很容易将其误解为一个彻底放弃救赎的虚无主义者。
麦卡锡通过父亲的这句话呈现了自己理解灾难的视角:将父子所处的“裂缝”状态正义化。海德格尔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进行翻译和阐释时,将希腊文dike译为德文fug,“接缝”,因此否定式的adikia就被译成了un-fugs“裂缝”[15]。海德格尔说“处于裂缝之中,或许就是(wāre)一切在场者的本质”[16]376,但这一个虚拟式的使用,暴露了他对于裂缝状态的态度:它是过渡的、消极的、有待克服的,即它是非正义的。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中以哈姆雷特“这是一个脱节的(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17]7展开了对阿那克西曼德这条古老箴言的解构式解读。“在德里达看来,如果说公正法律源于复仇,那么正义就是对于复仇之宿命的摆脱。”[15]
理解了德里达对“公正”与“正义”的区别,就能进入麦卡锡在《长路》中给父子俩劈开的“裂缝”里,这个裂缝不是海德格尔存在论中消极的亟待克服或者恢复的过渡状态,而是德里达说的本源性的、从开端处即存在的“裂缝”。小说没有谈及末日发生的原因,甚至没有过多描述末日发生的场景,直接进入到大灾难后的景象里,沉溺在这种悬置状态,挑战了阅读的逻辑,无视读者对“裂缝”状态的不适应和不耐烦,作者否定存在“接缝”,在叙事链上不提供任何通往更高价值的“连接”,也不迎合阅读者盼望的秩序“回返”。“这种回返的经济学或复仇的经济学,永远也给不出一个新的或别样的开端,一个新的或别样的未来,同时也给不出正义。”[15]
麦卡锡用两种方式保持着“裂缝”的正义性:首先,客观上将这个世界抹去了名称所指,包括人物的身份:所有的角色都没有姓名或者身份信息。“你是医生?我什么都不是。”[2]69也包括二元对立的指称意义。“万物名号随实体没入遗忘;色彩,飞鸟,食物,最后轮到那些人们一度信以为真的事物。名目远比他想象的脆弱。究竟流失过多少东西?神圣的话语失却其所指涉。”[2]91其次,主观上切除了恢复的念头。梦和回忆试图牵引父亲与“过去”连接,但立刻被自己清醒的意志冷漠切断。小说中出现过好几次对妻子的回忆,场景唯美,与处境形成巨大反差,这种描述方式让人忍不住留恋,觉得主人公也会从中得到慰藉,但他每次睁开眼都对梦境抵触拒绝,他选择残酷地清醒着来抵抗与过去的连接。“他相信每缕回忆都对记忆源头有所折损,道理就像派对常玩的传话游戏;所以应知所节制;修饰后的记忆背后另有现实,不论你对那现实有没有意识。”[2]131男人丢掉钱包和钱,包括在末日世界里毫无意义的信用卡和驾照,最后是妻子的照片,带着孩子在这混沌世界的豁口里,行走,活下去。
这种不复回返、“日趋恶化的失调”,不是麦卡锡坠入彻底虚无主义的宣告,而是因如此彻底的断裂“成就了其他事物的可能性”[17]33。裂缝作为本源性的存在,在场者(幸存的父子)于这样一个腐烂脱节的世界里不担负让它回归导致它破碎的灾难前秩序的宿命,才能允诺出新的关系和未来。
(二)对“救世主”的盼望转向“弥赛亚精神”
后启示录作品的读者已经习惯的“美国式救赎”:“起初的无罪和良善——接下来的沦陷、挣扎或者分离——最终的拯救、恢复或者变革”[12]被麦卡锡创造的“裂缝状态”打破了。
读者跟着父子俩在末日长路上见证了这个世界的完全破碎后,很难被结尾闪着幽微亮光的“宗教情怀”所安慰。麦卡锡在小说中构建的裂缝正义化,是对上帝出场的一种拒绝,这种拒绝并不旨在使读者坠入虚无主义的深渊,而是将他们从对“救世主”的盼望引向对“弥赛亚精神”的理解。德里达认为作为宗教的弥赛亚体系是狭隘的,但弥赛亚精神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结构,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一种对公正社会的期待和信仰”[18]。麦卡锡在小说中营造的叙事语境,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为“宗教性”的,主人公摆脱了对救世主盼望的宗教心理,救赎转向更开放的“救世主降临性”,即“弥赛亚精神”上。此时的救赎不再局限于哪一种教义、信仰、玄学或者超级英雄,“这种‘救赎’是在没有‘事件’发生保证以传统信仰承诺的形式带来拯救的状况下产生的。这意味着不再指望上帝的救赎,只是承诺本身而已。”[6]
Shelly L Rambo评价“麦卡锡最擅长的写作特点之一,就是他拒绝给读者提供安慰。”[12]James Wood认为作者没有解答末日神学的问题,“救赎的概念都被纳入了灾难的范畴之内”,宣布他“关于救赎的叙事是破碎的”[19]。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承诺本身,而非承诺结果,构成了麦卡锡式的救赎叙事特点。
首先,父亲的“许诺”成全了悬置状态中的伦理要求。
小说的叙事是由萧瑟悲戚的景物描写和简单利落的人物对话融合而成的,构成了特殊的末日景致。在此场景中,语言失去了雄辩的逻辑,显得脆弱,但同时又因箴言般的智慧而格外有力量。二元对立的打破,是麦卡锡式的悖论。小说中的人物存在于创伤的“断层”或“裂缝”里,日复一日的艰难行走、寻找吃食、躲避危险,仿佛落入了西西弗斯式的“永恒轮回”中。
如若“万物以相同的形式不停循环,就不会存在某种外部的叙事秩序来支撑生命的意义。”[11]在上帝缺席的末日里,男人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接近两百次)就是“Okay”,这是男人对孩子疑问与恐惧的回应,他内心里也许根本没有任何答案,但是用这个词维持了孩子内心的秩序,于破碎中重建了意义,而这又反过来成为父亲生存的意义。小说中父亲给儿子虚构了一个价值身份——“carry the fire”(毛雅芬译“神的使者”,杨博译“我们有火种”)。这便是德里达所说的“弥赛亚性”,“它通过许诺的基本言说行为得到阐明”。德里达认为,“许诺”是从未出现的“礼物”,能够燃起人们“对不可能事物的热情”[20]。各界评论中,将孩子视为道德与神性的化身,成为父亲保有良知的提醒与保护。但是在拥有绝对价值的上帝不能出现的末日里,父亲才是尼采描述的“超人”,他“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自己为自己设定价值”[21]、“就这样吧,召唤规矩与形式;一无所有时候,凭空构造仪典,然后倚靠它生活下去”[2]77。日渐衰弱最后消亡的肉体,呈现出来的挣扎与懦弱,使得这个角色被误读为人性弱点的象征、孩子的“圣杯”光芒下值得思考的罪恶。但是在笔者看来,父亲在明白这世界“无以复回”的真相后,仍然具有“许诺”的勇气,为孩子建构末日世界的意义,把万物从“被恢复”的奢望中解放出来,让“未来”敞开在孩子的认识中,被思考,变成礼物,完成了作为父亲的伦理要求。
其次,孩子的“许诺”敞开了结局的伦理空间。
与经历过灾难前世界的父亲相比,儿子于末日中成长,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与一个正常的世界拥有一个共性——未知性。小说中父子之间简单的对话体系里,孩子的语言是发生变化的,从开始不停惊恐地发问:“我们是好人吗?”“他们是坏人吗?”“去哪里?”“在哪里?”“怎么办?”“我们快死了吗?”到后来,减少了需要确定答案的提问,开始默默帮助父亲做事,长路过半时,他们经过尸横遍野的路面,父亲要孩子牵他的手,不希望他看到这些画面。孩子反过来安慰他:“不要紧的,爸爸。”“这些画面早在我脑袋里了。”“孩子情态异常平静”地跟父亲说“继续往前走好吧。”[2]191在遇到可疑的人时,孩子不再恐惧无措,淡定从容地帮父亲出谋划策:“我觉得我们可以趴在草地里等,看看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2]194这些变化无疑显示出人本身的成长规律。而对孩子“弥赛亚化身”“圣杯象征”等的宗教解读,在麦卡锡这部小说中,被过度诠释了。神话孩子这个角色,会降低故事的普适性,这有悖于寓言故事作者的初衷。
父亲为孩子建构的属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引领了孩子的成长,孩子在父亲几百次对他们身份和处境的确认中,逐渐接受这个对大人和读者来说的“裂缝”状态,而对他而言的“绝对存在的唯一世界”。
从孩子的角度,没有需要回返的世界,没有救世主降临的需要,没有救赎可谈。父亲给他的“许诺”,并非救世主的到来,“他的不出现是我们继续提问和生存的必要条件”[20]。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孩子使用的很多句子都是用将来时的。“假如有太空船,去的了火星吗?”“那里会有食物和日用品吗?”“如果你是乌鸦,会飞很高去看太阳吗?”[2]155-156Stefan Skrimshire认为“救赎是一种想象力”,“是我们还能问出将来时态句子的能力。”[6]小说中的孩子并非象征意义的弥赛亚,他只是在末日中出生成长,在父亲建构的意义中认识这个破碎世界的一个小生灵,他由于父亲的“许诺”而产生对生存的思考与对未来的想象。结尾父亲死去,意义存留,孩子体验悲伤,学会承受:“我每天都会跟你说话,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忘记。”[2]284孩子此处对父亲的“许诺”,完成了生命的接替,构建了自己生存的意义,这种角色的转换,对“许诺”的继承,使结局的压抑与迷茫得到了纾解。
三、救赎的意义:信仰危机下的“终极秩序”
(一)于虚无中重建意义
虚无主义者对“存在”的理解并不一致,但拒绝上帝的出场几乎是他们成为一个阵营的标志。上帝的消亡带走了传统的价值体系,在西方文明中留下巨大的深渊,成为虚无主义者无家可归的失落诗意。“用生命对抗上帝,几乎是现代虚无主义最隐蔽的形式,它的极端表现是赤裸裸的‘毁灭性的虚无主义’。”[22]“毁灭”到底被解读为一个序幕还是目的本身,是甄别“毁灭性虚无主义者”的指征。麦卡锡小说区别于大多数后启示录小说的特点便是描述了一个无法回到原来模样的世界,一个前途未卜的“裂缝”状态。所以,才会有评论对文中的基督教语境表示不解、对结尾的一丝温和之光施以苛评。
在西方,“上帝死了”与虚无主义发生在同一个时代,但并不能将二者等同。虚无主义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的社会病症,它的表征,尼采看来:“既表示现代人的自我沉沦和无所适从,又表示现代人在对传统的价值观的彻底厌恶和失望中转向重估一切价值,为一种增强生命活力和权力意志的价值观开辟道路。”[21]尼采在对基督教基本价值意义批判的同时,希望在这种否定和破坏中赢得生机,重建新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是与德里达的“弥赛亚性”不谋而合的。“虚无主义之‘虚无’不是说‘存在的世界’不存在,而是说这一世界并不天然地存在什么‘价值’,‘虚无’揭示的是价值在生存意义上的虚构性或存在论意义上的非自在性。”[23]71在这一点上,对尼采的误解,也是对麦卡锡的误解。当孩子告别死去的父亲,转身离开,走回父亲领着他踏上的长路时,无法不让人想到变成孩子走下山去,向昏沉的人类讲授全新思想的查拉图斯特拉。麦卡锡与尼采一样,用一种全新的生命力克服着下沉的分崩离析的虚无世界。尼采打破的是道德的等级秩序,他的新价值就是“要人勇敢地承担起无信仰的全部重负和苦难,勇敢地面对事实,不逃避到价值判断中去。”[24]麦卡锡正是在这种“虚无”中向人们呈现出小说主体身上体现的人类的“终极秩序”。
(二)于末日中呈现“终极秩序”
麦卡锡喜欢将角色置于绝望的境地里,看似“无”的虚空里,万物无序的状态里。将外部秩序击得粉碎之后,得以呈现人作为存在的内部秩序。麦卡锡的小说被描述成“消极的”“颓废的”“血腥的”“绝望的”,是因为他以极其冷酷的文字打破了世界的秩序,这种秩序被称为“世界的善”(cosmodicy),Isak W.Holm将其定义为“万物各归其位”[11],我们还可以将其理解为苏格拉底的“理性”,基督教里上帝的“绝对价值”。
评论者们认为《长路》对后启示录小说范式的打破是开放式结局,没有期盼到救世主,也没有出现被赋予使命的超级英雄,所以很少探讨救赎的话题,更多聚焦于灾难的启示意义。如果我们从尼采“超人”理论出发去看待父亲这个角色,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剥下虚幻的外衣,现出其真相,回到大地,再竖起生命”[24],在绝对价值的上帝拒绝出场的世界里,“超人是那些敢于为自己树立远大目标并勇于追求这样的目标的人。超人没有提出普遍的价值,而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自己为自己设定价值。”[21]近年来影视剧对于“超人”形象的商业打造通常是被赋予超能力的普通人于千钧一发之际用超能量翻转乾坤、拯救世界。而小说中身体孱弱,疾病缠身,最后没有逃脱死亡命运的父亲,很难让人构建起“超人”的概念,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在一个彻底沉沦的末日世界里,有继续行走的力量,睁开眼睛活过每一天的勇气,并且为自己的孩子设定价值,这就是“超人”。与尼采不同的是,在末日跋涉的父子俩,没有落入无家可归状态后深入骨髓的悲观,他们用尼采式的悲壮面对末日,避开了“造成怨恨和复仇”“导致自我蔑视”的价值判断[24],却在万物轮回中彼此形成意义,克服了深不见底的虚无。
当世界的外部秩序—世界的善—被摧毁的时候,人类是否存在一种内部秩序来维持生存呢?当救赎不是回到旧世界的路径,而是直面困境,接受裂缝的正义性,是否还存在一种终极秩序运作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呢?对应“世界的善”,Isak W.Holm还提出了一个概念“人的善”(anthropodicy),认为“小说对其探索是由‘好人’和‘坏人’的区分构成的”[11],他认为“儿子坚持着灾难前世界的道德理想,而为了在与一切的斗争中生存下来,父亲必须变得冷漠和自私”。如果终极秩序被狭隘地理解为人的善良和旧世界的道德约束,裂缝状态就失去了它的正义性,它依然是带着回到旧世界的愿望来向末日复仇的。在列奥·斯特劳斯看来,“克服虚无主义的唯一道路就是回到对‘自然正当’与‘超越理性’的朴素信赖,即回到对‘天理’与‘良知’的朴素信赖。”[22]若是在深渊和末日中存在一种终极秩序的话,那便是存在本身了,它不需要带着回到旧世界的宿命,也能在前途未卜的虚空中,生长出承受现实的能量。这个故事对于经历创伤、精神上逐渐荒芜的现代人来说,救赎的意义简单却深刻。
结语
虚无主义贯穿在当代灾难小说中,探讨“救赎”的意义不仅仅在悼念不可逆转的逝去和消亡上。《长路》这部后启示录小说最后一环被打破的无论是具有绝对价值的神还是可以临危救命的超人,都将读者置于一种彻底虚无的境地中,虽然作者描述的是一个彻底毁坏的物质世界,但反照了当代人日益贫瘠的精神家园。
人们在末日里怀念造成末日的那个世界,是一种逻辑悖论,麦卡锡对“裂缝”状态的肯定,是因为“回返”给不出真正的正义,是一种病态的怀旧情绪。这种情绪也在恐怖主义开始挑战西方的政治结构后蔓延在西方的民粹主义中,麦卡锡在这部小说中呈现的哲学思想,也解释了当下美国在经济和政治的变革中,企图恢复白人至上主义的浪潮,是一种情绪主导的历史逆流。
“回顾麦卡锡对宗教的大陆哲学发展中关于‘救赎’的探索,首先是体现在‘上帝神学的消亡’形式上;其次,是救世主的‘不可摧毁性’上。”[6]对“结局的拒绝”,保持了裂缝状态的“正义性”,切断了怀念旧世界的感伤、脱离了恢复旧世界的宿命。在此基础上,去审视“存在”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于虚无中对恐惧的驯服、完成生存需要的每一步,便是存在的绝对意义。父子俩在裂缝中向读者展示的人类终极秩序,在没有上帝出现的世界里,保守了弥赛亚精神,完成了麦卡锡式的救赎。